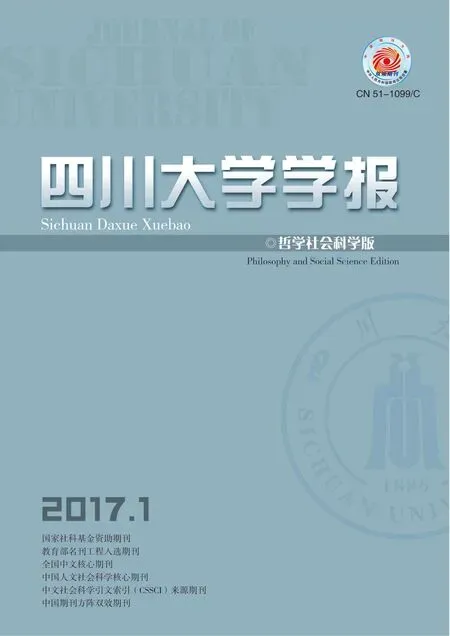权益保护与规范指引
张家勇
§民商法学研究§
权益保护与规范指引
张家勇
民事权益是侵权责任法明定的保护客体,权益侵害由此成为所有侵权责任的构成要素,并通过不同的规范形式作用于侵权判断。侵权客体的考察服务于加害行为有责性的判断,当其不能提供明确的指示时,基于加害行为性质及方式的考察就具有功能替代的效果。不同规范设置反映了侵权法价值平衡任务的不同配置,并具有不同的规范指引效果,立法的抽象化以及侵权判断的情境化始终要求法院结合侵权客体要素和加害行为要素进行具体权衡。
侵权责任;民事权益;价值平衡;规范指引
引 言
侵权法既保护权利也保护利益,这是共识。这不仅说明权利和利益在规范属性上不同,而且表明权利对于成立侵权责任并非必要。现行侵权责任法第二条将保护对象概括规定为民事权益,权利和利益在受保护程度与构成要件上亦无差异,此种模式依循的是所谓权利和利益的“平等保护论”,①参见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23页以下。有别于区分权利和利益而予不同保护的“差别保护论”。②两种理论立场的争论源于对德国法传统的不同认识,该传统区分权利和利益的主要意义在于二者违法性判定标准的差异方面,就此问题在台湾地区的情况可参看陈忠五:《论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保护客体:“权利”与“利益”区别正当性的再反省》,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6卷第3期,第97页以下。大陆主流学者一般否定违法性的要件地位,所以通常对此并无专门论述。只有坚持德国进路的部分学者,主张保留侵权责任的违法性要件并区分权利和利益而做不同对待,典型代表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陈现杰法官。(参见陈现杰:《〈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中的违法性判断要件》,《法律适用》2010年第3期。)在侵权责任法立法过程中,是否继受德国模式引发了争论,具体情况参看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释义》,第22-28页。
从文义上看,现行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客体范围包括了几乎所有民事权益,其会否引发现有法律体系的混乱,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认为应根据情况加以必要的限制;③参见葛云松:《〈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权益》,《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该文作者认为,对于侵权法保护范围应在实质上遵循德国模式,并在无过错责任、推定过错责任、公平分担损失和适当补偿等具体规范情形内,将保护对象限制于绝对权甚至特定的绝对权。特别是在解释上借鉴他国经验,注重权利概念规范功能的发挥,对权利和利益原则上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④参见龙俊:《权益侵害之要件化》,《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这种解释进路仍然坚守传统“差别保护论”的立场,多少超出了法律起草者意欲贯彻“平等保护论”的初衷。
应当看到,“平等保护论”与“差别保护论”的对立或分歧更多关注的是如何认识权利和利益的不同规范功能。不过,要真正发挥权利概念的规范功能,就不能不对“权利”概念的使用有所限制,而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尽管在理论上可以为其设定各种限制条件,但该概念的使用在理论或实践上其实都难以“规范化”。“权利话语”频频出现在侵权保护诉求或各种论说中,被当作保护诉求正当化的理据,侵权责任法甚至也甘冒将“民事权益”等同于“民事权利”的风险,对受保护权利作出特别列举,⑤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该法涵盖极广的例示规定,恰恰没有对“利益”作任何指示,反倒有将“权益”等同于“权利”的倾向,尽管这显然不是一个能够得到认可的理解(参看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法释义》,第26页)。对此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以致有人不无疑虑地发问:“债权”“身体权”等各种未被列举的“民事权利”是否也受侵权法的保护?
这种现象的出现虽有其复杂原因,但与我国民法理论受德、日传统的影响,以侵权客体为中心的思考进路不无关系。*我国侵权法理论经由台湾地区以及日本民法理论的途径受到德国法模式的更大影响,但是,除少数学者外,多数学者都没有注意到由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确立的侵权模式更多类似于法国而非德国立法模式。由此导致的结果就如同日本侵权法理论和实践遭遇的情况一样,法国模式的立法与德国模式的解释与适用奇怪地结合一起。本文无意于对这种现象作发生学上的讨论,而是集中关注侵权法规范与司法裁判在保护民事权益方面的协作关系。就此而言,以下问题是需要加以明确的:
首先,在侵权法上,权利和利益的概念区分具有怎样的问题意识?“同等保护论”与“差别保护论”是否冰火不容?“差别保护论”的肯定性价值在现行法体系下能否或者如何贯彻?
其次,民事权益作为侵权客体发挥规范功能的边界如何?当其无法为侵权裁判提供足够指示时,裁判者又将以何种要素作为考量因素?这种替代侵权客体的考量要素在何种意义上与现行法的结构相符,并如何运作?
最后,侵权法上权益保障与行为自由的价值平衡任务应当由谁并依怎样的方式实现?在权衡任务的配置中,司法裁判者处于何种地位?
为此,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考察权利和利益区分的规范意义,说明概念区分对于侵权裁判的非必要性。其次,从概念区分论肯定与否定立场出发,说明区别对待民事权益内在属性差异的必要性,并结合侵权纠纷的两极关系结构,通过侵权裁判的实质考量,探讨区别保护的实现方式。第三部分将从功能分析的角度,说明行为禁止要素对侵权客体要素的功能替代关系。第四部分在前述分析基础上,结合法律规范的特定模式,分析不同规范模式对于侵权裁判的不同指引效果。第五部分以现行侵权责任法的一般规定为例,分析侵权法中的司法权衡空间,阐述立法和司法活动对于侵权法价值平衡目标实现的任务配置关系。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一、权利与利益区分的侵权法规范意义
在侵权责任一般构成上,现行侵权责任法将权益侵害规定为所有侵权的共通要素,*参见侵权责任法第2、6、7条。民事权益由此取得侵权客体(或对象)的地位。*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民事权益通常被拆解为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而概念细分是为了发挥概念的规范而非说明功能,*参见龙俊:《权益侵害之要件化》,《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因此,有必要考察这种区分的规范效果。
侵权法上主张权利和利益概念区分的观点,除了依据法律形式或法律比较提出的论据之外,最重要的论据是这种区分为侵权法价值权衡所必要:虽然从受害人角度,不分权利与利益实行一体保护最有利于实现损失填补目标;但从加害人角度看,将生命、健康等人格权、所有权、知识产权等财产权和其他利益特别是纯粹经济损失等视同观,未必能够妥当兼顾调和行为自由的价值。*参见陈忠五:《论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保护客体:“权利”与“利益”区别正当性的再反省》,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6卷第3期,第98-99页。要实现区分目标,必须首先确定区分标准,尤其是明确“权利”概念所指为何。
权利的界定或本质问题通常被当作一个法哲学的理论问题讨论,五花八门的权利定义往往从权利的目的、客体、享有、行使、效果等某个或某些方面论说,*比较全面的介绍和分析可以参看盖斯旦等:《法国民法总论》,陈鹏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33页以下;徐国栋:《民法总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64页以下。通常不过截取多面向权利概念的某一方面强调之,对于权利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始终无法获得共识。就法律适用而言,权利的界定则更多依循实证法的思考进路,毕竟在实证民法上权利的范围是相对有限的。确证实证法上权利存在的方法通常是看制定法有无授权规定存在,是否有权利之名则是一个粗略但简便的方法,就如同界定有名合同一样。例如法人名誉权是被法律认可的民事权利,而信用权则因无法律规定,故不得视之为权利。当然,权利的确定也可以通过司法裁判、习惯和学术研究的共同努力,“创设”或者“发现”实证法上并不“有名”的权利。如“采光”利益在立法上并没有被定名为“权利”,仍不妨在司法审判中认可采光权的存在;*如南京中院“孟昭风等诉江苏省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等相邻采光案”((2001)宁民终字第745号)。德国法院之“发现”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更是这方面的著例。
如果将制定法上有无规定作为确定“权利”的依据,通常不至于发生问题,在侵权规范直接列举了受该法保护的民事权利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在特殊情况下,基于法律解释原因,也可能会出现相反的认识。例如,尽管现行法上有保护法人商业信誉的规定,但因为没有正面确认其为权利,其是否权利或为何种权利,认识上就莫衷一是。对于司法惯例、习惯或学理上所形成的“权利”,就更容易产生认识分歧了。
于是,学者转而寻求其他可能的区分标准。他们认为,权利与利益的差别,关键在于内容方面的具体特定性不同。权利在实质上虽然亦属“利益”,但其主体、内容或范围等具体特定,经由既存法律体系确认而成为一独立类型,并被赋予一定名称,从而具有“社会公开性”,一般人很容易从外界予以知悉和预见;反之,利益则因其具体特定性不足而仍维持“单纯利益”的地位,欠缺前述“社会公开性”。*参见陈忠五:《论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保护客体:“权利”与“利益”区别正当性的再反省》,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6卷第3期,第151-152页。
不过,“社会公开性”或明显可辨性并不总是能够成为区分权利和利益的有效标准。非公开性是“债权”的典型特点,但不妨碍其债“权”之名。“营业权”或“企业权”亦复如此。*德国法有关已设立且运行的营业利益的保护是借“营业权”之名实现的,但其从发生学上看却是为了实现对企业纯粹经济利益在既有法律框架下保护不足的目的,所以,其保护的并非权利而系纯粹经济利益(See B. S. Markesenis, The L aw of Torts: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7, pp.61-62.)。虑及此点,遂有论者认为,“债权”“企业权”性质上更接近于利益,侵害此等权利不得谓为权利侵害。*参看陈忠五:《论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保护客体:“权利”与“利益”区别正当性的再反省》,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6卷第3期,第99页以下。况且,社会公开性对于侵权责任构成的意义,并非在其抽象确定的社会公开性上,而是在侵权事实发生时,加害人是否可以辨识权益的存在与内容而已,此系具体而非抽象的判断。因此,债权纵无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公开性,但如其存在与内容已为加害人所明知,则社会公开性对于侵权行为的成立与否就无影响。
因此,欲从权利与利益的概念区分实现权益明显可辨性所发挥的价值平衡或责任限制功能,显然并不可靠。恰如学者所见,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作为“框架性权利”,不过是出于保护目标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是一个有权利之名而无权利之实的“权利”概念,其所保护的恰恰是“非权利化”的人格利益。它一方面被作为“其他权利”能够获得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保护的资格,但另方面又得解决效果区分问题,由法官根据个案的利益衡量来决定具体案件中人格法益的保护可以达到的范围和程度,结果导致构成要件的不确定性。*参见薛军:《揭开一般人格权的面纱:兼论比较法研究中的体系意识》,《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5期。即使为了避免外延模糊的框架性权利所生弊端而采狭义权利概念,*龙俊:《权益侵害之要件化》,《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概念区分的难题仍然无法解决,德国司法实践基于所有权侵权解决“后续损害”与“功能损害”等问题时面临的困境可以作为质疑前述认识的比较法上的例证。*福克斯:《侵权行为法》,齐晓坤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2页以下。同时,将框架性权利作为利益加以保护,在奉行利益保护以故意为原则的指导思路下,*龙俊:《权益侵害之要件化》,《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又可能产生救济不足的弊端。例如,在具体人格权只有有限规定的立法体制下,相当多的人格法益需要借助一般人格权思想获得保护,且只有采过失而非故意归责方可获致充分的保护。*如身体、信用、贞操、与人格尊严相关法益等一般都应以过失为归责原则。学者就此恰当地指出,为强化利益保护而将利益纳入权利保护的形式理由之下,不过是贯彻一种隐藏的法政策而已。*参见于飞:《侵权法中权利和利益的区分方法》,《法学研究》2011年第4期。
这说明,对于侵权构成而言,权利的确认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使确定了权利的存在,也不意味着侵权判断任务的完成。当我们习惯性地将“民事权益”分拆为“民事权利和民事利益”之后,反而丧失了“民事权益”概念的灵活性。有鉴于此,对于侵权裁判而言,“民事权益”就是它本身,没有必要将其分拆而归类为“民事权利”或“民事利益”。
作为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权利和利益是从侵权发生前的角度观察的,属于事前视角。其意义在于,民事权益的存在既是侵权事实发生后对受害人给予救济的根据,也是进行权益保护与行为自由价值权衡的基础:权益存在的事实及其归属与效果越容易辨识,权益保护对他人行为自由的不当妨碍可能性就越低,施予加害人责任的正当性就越强。虽然多数绝对权在其核心部分能够满足这种要求,但将各种民事权利(甚至绝对权)的规范效果作一体化处理,不仅对于权利边界模糊事实未予足够关照,而且将权利化利益的价值位阶等同视之,显然难以适应侵权法对复杂利益冲突关系的调整需要。不过,质疑权利和利益概念区分的价值和必要性,无论如何不能等同于对区分本身的价值和必要性的质疑,毕竟目的妥当性和手段妥当性分属二事,必须分别对待。
二、民事权益的特性差异与区别保护的实现途径
权利和利益概念区分的积极价值在于,权益内在特性差异的区别对待有助于实现侵权法价值平衡任务。因此,一旦确认了受保护民事权益的内在特性差异,如何在侵权责任规范和裁判中实行区别保护就需要认真对待。
(一)民事权益的内在差异与区别保护的必要性
侵权法保护的民事权益内部是存在特性差异的,其不仅表现为社会公开性或明显可辨性的不同,也表现为价值位阶的不同,在与其他受保护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方面也存在强度或性质差别。这些差异并不完全依赖于其是否可以归类为“权利”或“利益”,它们既可以“权利”和“利益”的概念区分表现出来,也可以“权利”内部的规范效果差异表现出来,如物权与债权在绝对性上,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在对物支配效果上的区分;或者表现为“利益”内部的差别,如物质(财产或经济)利益与精神利益、人格利益与身份利益等的区分。因此,将“民事权益”或“民事权利”视为均质性的对象,就可能发生过度抽象的问题。不论是从法律实践的角度,还是从比较法的角度,我们都不难发现,生命、身体、健康等人格利益所受保护程度通常既高于财产或经济利益,也高于对名誉、隐私等其他人格利益;物权、知识产权等财产权所受保护既强于对债权的保护,也强于对纯粹经济利益的保护,尽管基于各要素整体权衡结果也可能会有相反的情况出现。*H·考茨欧主编:《侵权法的统一:违法性》,张家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76页。将特性差别极大的民事权益等同保护会在法律体系及保护效果方面产生难以克服的问题,比如按照法律文义将债权纳入侵权法保护范围并给予与物权等绝对权相同程度的保护,不仅在理论上无法获得支持,在实践中也不可行。*参见葛云松:《〈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权益》,《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
虽然平等保护论在立法上的确立标示其合理价值获得承认,但由此导出所有民事权益在侵权法上的保护条件和保护效果则未免可疑。现行侵权责任法采纳“平等保护论”的基本立场,只是否定了基于权利和利益的概念区分而实行差别保护的必要性,并未否定因民事权益特性差异而实行不同保护的可能性。学者在论及两种立场的关系时恰当地指出:同等保护权利与利益并非意指二者毫无差别,而是不应在归责原理上依侵害客体为权利或利益而限制过失责任的适用范围,“差别保护说”“虽然指出了‘好的法律政策’,却使用了‘不好的法律技术’”。*参见陈忠五:《论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保护客体:“权利”与“利益”区别正当性的再反省》,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6卷第3期,第156页。传统差别保护论强调受保护客体因特性差异而应受不同对待的立场无论如何应受肯定评价,*参见陈忠五:《论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保护客体:“权利”与“利益”区别正当性的再反省》,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6卷第3期,第97页以下。依据受保护权益的特性差异而采取不同级别的保护(包括构成要件的宽严限制在内),可谓为修正意义上的差别保护论,从而能够与同等保护论立场共存。
就现实需要来看,关注侵权法中权利和利益概念区分的立法以德国法传统为典型,目的是要确立过错责任侵权形态中的违法性的不同判定标准。*对于德国法中的严格责任来说,其并不涉及违法性判断问题,因此,权利和利益的区分在构成要件上就没有意义。(参见福克斯:《侵权行为法》,第256-258页。)违法性的功能在于限制侵权责任的成立,但基于概念区分而确立的归责却导致了僵化的后果,为了扩大值得保护的利益范围,司法实践不得不通过创设框架权(如一般人格权或营业权),或者扩张解释绝对权规范效果——如扩张所有权效果以保护所谓“后续损害”——以扩大侵权法的保护范围,或者通过扩张合同法的保护手段,确立合同附随义务、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合同在保护当事人固有利益方面的意义。这样的经验或教训提示后来者,侵权法价值权衡是一个难解之题,任何单一化的解决方案都将面临质疑。肯定了民事权益特性差异在法律评价上的重要性,就需要以弹性的方式应对这种差异所引发的评价需要。
于是,在现行法框架下,问题就并非要不要实行差别保护,而是如何贯彻差别保护论的合理价值。
(二)民事权益差别保护的实现
侵权法需要权衡的权益保护和行为自由分属于受害人和加害人两极,权益保护从受害人角度指向侵权客体,受害人对受损利益享有的正当性表明其救济要求的正当性;行为自由从加害人角度指向致损原因,行为的不当性表明施予责任或限制行为自由的合理性。客体要素与行为要素由此构成判断侵权责任的两极:前者涉及权益侵害(或损害)问题,后者涉及加害行为的不当性或可归责性(违法性或过错),将受保护客体与加害行为连接起来的是因果关系问题。不论是采取何种侵权构成要件的区分,都不过是对上述要素的不同组合而已。
例如,加害行为是否应作为独立的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我国理论上有不同认识。有认为加害行为应为独立构成要件者,*代表性观点请参见王泽鉴:《民法研究系列:侵权行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6页以下;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0页以下。有反对将其作为独立构成要件者。*代表性观点见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8页。这种表面分歧遮蔽了另一个更具根本性的分歧:加害行为是否包含违法性判断在内?一种看法认为,加害行为乃导致权益侵害的法律事实,其仅需从客观事实层面观察其有无,而无需价值评价介入其中。就此而论,其是否独立为构成要件,当取决于因果关系要件的判断内容:如不为因果关系要件所包括,则应独立为构成要件;*王泽鉴:《民法研究系列:侵权行为》,第87页。反之则否。*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第348页。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加害行为乃侵害他人权益的不法行为,行为的违法性是该要件当然的判断内容,从而加害行为就包含了违法性这个价值判断。*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0-52页。在违法性是否独立为构成要件上,也有不同看法,其分歧则关乎过错要件的内容。结果,在加害行为、因果关系、违法性与过错等要件区分上,各种观点歧见纷呈,莫衷一是。构成要件论不过为思考侵权问题的工具而已,本文这里将忽略一般侵权构成要件区分的理论争议,唯从诉讼操作角度,结合侵权关系的两极结构展开相关讨论。
1.损害(或权益侵害)的触发作用。任何侵权纠纷的发生,必以权益侵害或损害为其触发因素。该因素引起受害人的保护诉求,如同引擎发动使汽车得以运行一般,它也使得整个侵权审查机制得以启动。因此,侵权审查的首要内容当属侵害事实的存在与否。其又可以区别为两个思维阶段:
一是判断诉请保护的利益是否正当。只有正当的利益才能获得保护,不法或不当的利益都将被排除在外。此时,权利相对于利益具有更强的正当性标示效果,可能会产生一种“保护诉求权利化”的诱导。当事人为了正当化其利益保护诉求,将某种法益上升为“权利保护”,能够产生正当化其主张的心理支撑作用,减轻其在诉请正当性方面的论证负担,这对于裁判者亦可获得类似效果。实践中不断涌现的“商业信誉权”“公平竞争权”“生育选择权”“生活安宁权”甚至“亲吻权”等形形色色的“权利”概念都可以由此获得解释。但是,这种借助“利益权利化”获得的正当性,更多源自权利话语的修辞效果,与作为侵权客体的受保护权益并不能相提并论,理论上有必要将作为侵权客体的权益(或权利)与作为正当化保护诉求或施予侵权责任的权利加以区分。*这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作为侵权客体的权益必须为私法性实体法益,作为正当化保护诉求或施责根据的权利则可以不反映为实体利益的技术性或程序性权利(如婚姻自由权、继承权)和公法上的权利(如宪法上的受教育权、平等权等)。讼争利益的正当性审查通常仅需抽象判断即可,无需对何种权益受到侵害甚或受到怎样的侵害作具体判断,只要法律没有明确禁止利益的享有,或者规定利益主张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况,所有利益就都被推定受侵权法的保护。*考茨欧主编:《侵权法的统一:违法性》,第35页。
二是判断损害的“确定性”与“严重性”。诉请保护的利益具有正当性通常只确立了受保护的可能性,损害的确定性与严重性才确立启动诉讼机制特别是损害赔偿机制加以保护的必要性。损害的确定性涉及证明标准问题,原告要对其权益遭受妨害或因侵害而受到某种财产或非财产损失的情况加以证明,在主张损害赔偿时更要依其选择的损害赔偿方法就损害内容(如实际损失或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利润)举证,其举证须至少达到如此确定的程度,使法院可以合理相信其已遭受某种程度的损害,并能够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酌定侵权人应予赔偿的数额。*根据现行法规定,损害赔偿额的确定方法按照赔偿标准可分为依原告所受实际损失、被告因侵权所获利润或由法院酌定赔偿三种形式。三种赔偿额确定方法的区分,在实践操作层面更多体现为对损害确定性的举证负担方面:在依前两种标准确定赔偿时,原告应通过举证使法院可以据以确定一个具体的赔偿金额;如果其无法做到这一点,而只能就其损害概括举证,那么法院就会根据查明的案件情况酌情确定赔偿金额。因此,从损害确定性的证明负担角度,法院就可以控制其不欲支持的侵权诉求。*如上海高院在“携程计算机技术(上海)公司诉上海蓝豹旅游服务公司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纠纷案”( (2008)沪高民三(知)终字第48号)中,以“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因不正当竞争所受到的经济损失或者名誉损失,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对方所获得的利润”,对双方所提的损失赔偿均不予支持,但没有说明不根据现行法规定酌定赔偿的理由,实际上可以认为是通过损害不具有“确定性”为由排除了损害赔偿责任的使用。损害的“严重性”虽然对保护对象同样具有筛选过滤功能,*参见陈忠五:《论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保护客体:“权利”与“利益”区别正当性的再反省》,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6卷第3期,第159-162页。以确定相对人基于社会结合而必需对轻微损害予以容忍的限度,但通常也仅就损害赔偿有其意义。对于其他侵权责任,如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等,则难以依据该标准驳回当事人的救济请求。
2.加害行为的不当性判断。一旦确定了权益侵害事实,责任分担的需要就产生了确定致损原因,特别是被请求承担责任者是否存在加害行为的问题。对于加害行为同样可以分别不同层次加以观察:
首先,加害行为是作为客观的致损原因而受审查的。在这个意义上,加害行为(作为或不作为)并不涉及当与不当的判断问题,而只有存在与否的问题。虽然在逻辑上可以将致损原因、侵害结果(或损害)以及二者的因果关系分别考察,*这是德国法侵权行为三阶层中构成要件符合论的内容,就此请参看福克斯:《侵权行为法》,第12页;另见王泽鉴:《民法研究系列:侵权行为》,第86-88页。但在具体操作上它们则组合为一个完整的分析单元(事实构成),加害行为是作为损害的原因而被认识的,确定了加害行为也就确定了因果关系,*理论上有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与责任承担的因果关系之分,前者在于确定致损原因,后者在于确定损害范围。就笔者所见,这种区分的实践意义并不明显,我国司法实践也罕见进行这种区分的案例。本文这里仍遵从理论分析,主要关注作为构成要件的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反之亦然。要确定加害行为,必须先确定行为人负有某种义务。行为人是否有某种行为义务存在,*应予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行为义务与判定过错的注意义务有所不同,后者涉及的是“必需的行为标准”,也即履行行为义务的标准。在逻辑上要先于义务违反的判断,只有有义务并违反该义务才成立责任构成意义上的加害行为。由于法律有不得侵害他人合法利益的一般义务要求,且绝对权基于其规范效果通常也可以标示具体的行为禁止要求,因此,经由积极的行为致人损害,确认义务违反通常不会有太大问题(其否定通过抗辩事由完成)。在应有所为而不为的不作为侵权情形,则需借助法律的特别规定与法律体系的整体构成判断,避免将道德要求以法律的名义强制实施。*王泽鉴:《民法研究系列:侵权行为》,第91页。此时,行为义务的判定就具有浓厚的价值判断色彩,法院往往藉此实现对受保护利益的限制或扩张目标。在违反行为义务的情况被确定之后,因果关系则成为过滤受保护利益的另一手段,以排除“过于薄弱、牵强、偶然或不确定的损害项目”,合理控制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参见陈忠五:《论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保护客体:“权利”与“利益”区别正当性的再反省》,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6卷第3期,第175页。
其次,加害行为也可以从不当致损的价值评判角度加以考察。对于多数大陆法国家的侵权法来讲,违法性都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且通常只在过错责任领域发挥作用,并存在结果不法与行为不法的不同认识。*参见陈忠五:《论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保护客体:“权利”与“利益”区别正当性的再反省》,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6卷第3期,第172页以下。这方面具有典型性的是德国民法典,其第823条第1款对侵害绝对权和人格绝对法益的侵权行为采结果违法立场(但在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问题上例外需要权衡具体情况),同条第2款对违反保护性法规侵权采取违反保护性法规指引违法立场,效果上与前者类似;*参见福克斯:《侵权行为法》,第153页。第826条对背俗性侵权的违法性则需取向于社会伦理和法律伦理因素确立被普遍认可的行为标准,以判定违法性是否存在。*参见福克斯:《侵权行为法》,第163-164页。这表明,存在权益侵害的事实本身虽然能够表明损害对于受害人的不当性,但行为方式(是否违反法律禁令或者违背善良风俗)则减弱了从权益保护角度考察违法性的压力,从限制行为自由的角度反面加强了保护需要。
行为违法既可以从一般社会观念角度考察,表现为防免侵害他人权益的客观注意义务;也可以从行为人的主观角度考察,表现为行为人对行为不当的主观认识。客观注意义务越清楚,可归责性越强;行为人对行为不当的主观认识越清楚,其可归责性也越强。从而,不论是采主观过错或客观过错标准,行为的违法性都可以纳入过错中作一体考察。即使否定违法性为独立要件,*我国侵权责任法是否承认违法性构成要件,理论上存在不同看法。从法律文义上看,应持否定看法。不同看法请参看陈现杰:《〈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中的违法性判断要件》,《法律适用》2010年第7期。该文是从权利和利益区分角度提出类型化的侵权体系构成思路,更多是出于对德国模式的偏爱,并未结合现行侵权责任法作更具说服力的说明。就此,遵循一种日本民法理论主张,将权益侵害问题转换为违法性问题(有关介绍情参见圆谷峻:《判例形成的日本新侵权行为法》,赵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61页以下;也见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144页以下),倒是能够弥补前述不足。但是,这种替换的必要性尚值得探讨。其仍然可以经由客观注意义务或者违法性认识而进入过错要件的判定过程中。故意加害相比于过失致害更容易被确定责任,反映的就是违法性认识对于施责效果的强化作用。违法性和/或过错要件因此也就成为区别不同权益的有效机制:将过于抽象或边界模糊的利益排除出保护范围,除非行为人存在故意加害的情况。
(三)小结
对于侵权裁判来说,侵权客体的考察既要服务于权益救济的目的,也要服务于责任限制的目的,从而更好实现受害人权益保护与加害人行为自由的价值权衡。从受害人角度来看,民事权益的考察主要包括权益本身正当性、损害结果的确定性与严重性等判断;从加害人角度来看,民事权益考察则应着眼于加害行为不当性的判断。由于受保护权益根据其具体特性而有差别,法院需要根据情况采取多种方式确定保护级别或条件,以实现对受保护利益的选择或过滤。
三、行为要素对客体要素的功能替代
至此,我们看到,法院在进行侵权裁判的过程中,需要在权益要素和行为要素之间往返穿梭,建立侵权客体与加害行为之间的连接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是被作为独立的要素发挥规范功能的,为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民事权益中心化”思考的局限性
现行侵权责任法不仅将“民事权益”确立为侵权保护的对象(第2条第1款),而且将其确定为侵权责任构成的表面要件,无论是过错责任(第6条第1款)还是严格责任或无过错责任(第7条)都莫不如此。在理解权益侵害要件时,裁判者可能会陷入如下认识误区:在侵权纠纷中,裁判者须就原告何种权益受到侵害取得确切认识。这种看法将权益侵害要件的判断,拆解为确定民事权益(侵害前提)和确定损害(损害后果)两个方面。实际上,侵害结果(或损害)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只需指涉抽象的受保护利益(表现为财产与非财产利益这样抽象的类别区分),行为违法性和/或过错才将被侵害权益的具体考察纳入加害行为的判断之中。并且,无论前者还是后者,被侵害权益的确定都不具有绝对意义。如果被侵害权益并不确定,或者因其过于抽象而无法判断其禁止效果,那么,从被侵害权益角度进行的分析就不会有什么成效。将损害判断系于受害权益之上,会导致侵权保护目标与为实现目标采取的技术手段相混淆。
兹以纯粹经济损失为例加以说明。有观点认为,纯粹经济损失(pure economic loss)是有关纯粹经济利益(pure economic interest)或整体财产(patrimony)的损失,因此,该种侵权保护的客体亦属其他法益范围。*参见王泽鉴:《民法研究系列:侵权行为》,第307页以下。这种看法虽有阐明侵权保护对象的说明意义,但对于侵权裁判而言,将损失回溯到利益的思考则是没有必要的。纯粹经济损失是与附随(或间接)经济损失(consequential damages)相对的法律概念,*布萨尼帕尔默主编:《欧洲法中的纯粹经济损失》,张小义、钟洪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5-7页;另请参看詹姆斯·戈德雷:《私法的基础:财产、侵权、合同和不当得利》,张家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446页以下。处理的都是某种经济损失是否应予赔偿的问题:附随损失是从受保护法益来确定损失,而纯粹经济损失则是指不依附于特定法益侵害事实而发生的经济损失。*参见福克斯:《侵权行为法》,第162页。这种区分是要解决某种损失应否给予救济的问题,但不论是这种概念区分本身,还是由纯粹经济损失构造出纯粹经济利益的概念,都不过是将损失系于侵权客体的概念思维产物。*参见詹姆斯·戈德雷:《私法的基础:财产、侵权、合同和不当得利》,第449页以下。除非意图以形式推理的技术手段掩盖实质保护目标(请再次想想德国司法通过营业权保护纯粹经济损失的经验吧),这种反向的利益构造对于侵权责任构成不会有任何影响,这正是德国三种过错侵权类型的差异所在:第823条第1款以具体、特定的法益(绝对权及人格绝对法益)侵害为要素,而第823条第2款以及第826条则并不指向一个确定的法益。
就侵权损害赔偿来讲,恰恰是损害,而非损害所由产生的特定法益才是各种损害赔偿责任的共同之处。损害是侵权行为或事件的结果,这使得侵权损害赔偿一开始就是结果导向的,从损害所由发生的法益角度开始思考会不必要地增加侵权判断的难度,甚至走入误区。因此,大多数国家的侵权法都以“损害”*参见奥地利民法典第1295条第1款、比利时民法典第1382-1384条、芬兰侵权责任法第1章第1条、法国民法典第1382-1384条、西班牙民法典第1902条、瑞典1972年侵权责任法第2章第1条以及荷兰民法典第6:98条。而非权益或权利侵害为侵权构成要件就是这个道理。反之,少数反对这个做法的立法在实践中则遭致了困难。日本民法一度将侵权要件确定为“权利侵害”,结果为了扩大救济,不得不舍弃权利概念的限制效果以使侵权法能够保护非属权利的利益,甚或干脆扩大权利范围直接将后者纳入“权利”概念之下。*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第153页以下。尽管通过法律修订已扩大了保护范围,但这里所面临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尚不得而知。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虽在过错侵权的类型构造上最终继受了德国的做法,但将权利作为侵权客体的类型划分也同样面临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其他权利”引致的问题,理论上有关“债权”“营业权”等是否纳入“权利”保护的理论争论与徘徊、模糊的司法实务立场就是证明。*参见陈忠五:《论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保护客体:“权利”与“利益”区别正当性的再反省》,载《台大法学论丛》第36卷第3期,第96页以下。
就侵权责任的构成来讲,权益侵害虽然指示了保护目的,但从技术角度看,其同时(甚至更多)是从受害权益的角度昭示对加害行为的禁止效果。这种效果越明显,从受害权益角度考察侵权责任就越有效。绝对权始终是请求保护的重点,就在于这种权利所具有的排他性明显(较高的社会公开性),如果再辅之以高价值位阶,其禁止效果就会倍增。这类权益引发的价值权衡经由权利的界定通常已得到解决,侵权裁判的再权衡空间就相对有限。反之,要是被侵害权益因其过于抽象以致于无法提供有效指示,基于受保护权益进行的思考就不会提供什么帮助。比如,如果因房前开阔的他人草地上建造了棚屋而使房屋观景利益减损,通常只能认定为“反射利益损害”或“纯粹经济损失”,不得因此而认为存在“所有权侵害”。只有那些纯粹基于损害分担目的的侵权规则,如公平责任或环境侵权、产品责任、高危作业致损等严格责任,法律才赋予权益侵害在侵权判断中的更重分量。
应当看到,权益侵害只是侵权判断的一端,另一端是加害行为的不当性或可责性,只有将两端加以连接才能确立特定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特殊联系。“权益中心化”的做法或认识将侵权客体的功能不当放大,在侵权领域导致“权利泛化”现象,使违法性和/或过错问题几乎成为权益侵害要件的推演结果(尽管这不总是很明显),从而偏离侵权法的价值平衡目标。
(二)从“民事权益”到“加害行为”
正如民事权益的归属能够指示对他人行为的禁止,对加害行为的禁止也可以反面塑造对他人利益的确认,日本法上的日照权、美国法上的隐私权等正是通过侵权判例得到确立的。这体现了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关联效果:从受保护权益角度可以确定行为义务;从行为义务角度可以反面塑造受保护权益(侵权禁止的权益构成效果)。从而,不同构成要件因相互关联引发“共振”效果。侵权客体对行为义务的指向越弱,行为方式或性质在侵权判断中的重要性就越应被强化。故意侵权通常可以为任何权益侵害提供正当化基础,其道理即在于此。从我国现行法有关故意侵权的规定来看,尽管它们中的一些也涉及特定人身、财产权益的保护,但故意要素是明显作为强化责任限制的平衡目的而被规定的。例如,著作权侵权通常仅过失即可成立,但网络服务提供者只对故意侵权担责。在其他情形,被侵害利益根本就无须在侵权判定时加以特别考虑,如利用无效专利故意加害的侵权责任,或者广告经营者或发布者因虚假广告承担的责任等。这表明,行为的性质(是否故意)成为责任成立的基础。
从德国法的经验我们也可以获得同样的启示。绝对权和人格绝对法益因其明显性或高价值位阶而为侵权禁止效果提供了较强的指示,在违法性判定上表现出“权益侵害征引不法”的效果。反之,一般人格权和营业权因其所保护利益的抽象性,则需要个别权衡。结果,二者虽同样被归并到第823条第1款之下,其违法性的判定却判然有别。第823条第2款和第826条虽然也一样涉及过错侵权问题,但和第823条第1款表现出以下差别:1.前两种侵权都没有直接规定被侵害客体,而后者有这方面的要求;2.前者将后者的违法性判定替换为违反保护性法规或违背善良风俗;3.背俗性侵权提高了过错要求即需故意方可成立。2、3两点属于加害行为要素特征,故而可以认为,违反保护法规和故意背俗对权益侵害违法性的功能替代是区别于1的最好解释。
在依结果确定责任的情况下,只要存在损害事实,一旦确立了因果关系就确定了责任。在这种关系中,权益侵害的事实具有决定性意义,法律关注的重心落在权益保护之上。如果不考虑免责机会的存在(即在确立因果关系之后还可以不承担责任),严格责任就与结果责任一致,也即,严格责任是以权益救济为中心的,侵权法价值平衡是通过一定抗辩事由而实现的。与之不同,在过错责任情形,行为不当性具有独立的法律意义,其只是在受保护权益具有行为禁止指示效果时才会与民事权益的规范效果相联。在这个意义上,将权益侵害作为独立的要件就融合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两个阶段。权益侵害本身只能作为损害事实被认定和评价,而不能将不当性评价纳入其中。侵害或损害是从受害人角度观察的,而不当性是从加害人角度观察的。在不当性的评价方面,受侵害权益的具体属性(是否具有公开性或明显可辨性,价值位阶等)只是不当性裁判的可能内容之一,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特性(如特定身份关系或密切关系),公共利益或政策取向(如言论自由与竞争政策等)都是评价因素。而且,这种评价还需取决于具体情况而有所偏重,这都需要对加害行为进行独立评价,受害人权益保护只是这种评价的可能结果之一。
权益要素和行为要素的功能替代关系反映了侵权关系两极结构的辩证关系:侵权法既可以从权益保护角度确定行为自由的边界,也可以从行为自由角度确定权利保护的边界。承认这种思考重心的替代可能性,实际上就是承认侵权关系法律调整的复杂性。侵权法是权益救济法还是权益救济限制法,*这对概念的使用源自本文写作过程中与王竹教授的讨论。他认为,侵权法的功能其实不是救济法,而是救济限制法。如果作为救济法,侵权法只需规定侵害权益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实际是结果责任)。但各国侵权法其实都在这个要件之外规定了其他的限制条件。所以,只有理解为侵权救济限制法才能准确反映这种复合要件限制的情况。不过是从侵权关系的两极中选取其中一极观察而已,如果视角选择能够产生某种规范意义,那么,两种角度就可能具有不同规范重心和要素,其意义在这种功能替代关系中就能够得到适当诠释。
行为要素对于客体要素的功能替代能够为法律适用活动提供有益的帮助。当民事权益的禁止效果较为明显时,一旦确立因果关系,责任成立的可能性就较高;相反,如果被保护权益由于其过于抽象,或者在利益冲突中很难做出孰轻孰重的权衡时,被告加害行为的性质就成为重要的考量因素。如果民事权益的禁止效果及被告过错同样明显,施予被告侵权责任的正当性就有了双重保障。因此,或许可以认为,权益要素和行为要素的功能替代关系为侵权裁判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正当性说明模式。
四、法律规范模式对侵权裁判的指示效果
侵权责任的判断取决于对权益要素和行为要素的适当评价,而评价活动需要有所依循,评价结果也需要有外在于评价本身的验证标准。在成文法体制之下,评价标准首先由立法者制定的法律规范提供。不同法律规范模式的评价指引效果是存在差别的,理论上对这种指引效果加以考察就有其实践意义。
由于从权益确认角度和从禁止侵害角度设置规范可以产生不同规范指引效果,因此,在立法技术上,前述视角选择就可以产生如下三种规范模式:从正面确认权益归属;从反面禁止权益侵害行为;同时并用二者。
如果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享有某种受保护权益,该种规范的存在就能够被用来确证权益侵害以及结果不当。特别是,如果这种权益确认同时具有对被告行为的明确指示效果(要求或禁止),被告侵害行为的不当性就更容易确定。不过,该种规范模式的缺陷也正在于此:如果没有对相对人行为的明确要求,在认定是否侵权时需裁判者结合侵权行为的具体情况加以判定,那么,该种授权规范是否包括对讼争行为的禁止就不确定。例如,我未经你的同意而开走了你的车,你可以基于所有权要求我停止侵害,这个效果是明确的。如果我因为太喜欢你的车了,趁你不在场的时候,靠在你的车身上拍了一张照片并四处炫耀,看上去那车就像是我自己的一样,你是否有权要求我销毁我的照片或要求赔偿呢?你的所有权包括这种内容的禁止权能吗?仅仅有所有权的宣示不足以为前述行为提供清楚的指示。在权利的核心部分,利益归属对他人行为的指示效果最为明确;在权利的边界部分,就会出现权利与非权利化利益趋近的情况,利益归属对他人行为的指示效果就逐渐减弱直至非借助其他手段就无法确认的地步。此时,从权益归属的角度建立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责任关系就较为困难。另外,授权规定的存在可能被误解为是对受保护权益的穷尽列举,由此可能引发某些本应受到保护的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的问题。例如,虚拟财产、形象利益等保护都没有可资依据的直接法律规定,如果着眼于法律的明确规定,就意味着这些利益损害得不到任何救济。当然,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概括性的授权规定或一般条款而得到解决。
具有明确的行为指示效果通常是禁止规定的优势所在,该种规定明确指出了民事主体不得实施的行为,一旦违反,损害后果就可能被推定应由其承担。这种责任推定有两种可能的运行方式:一是行为方式的不当性直接指向责任承担,实际损害或过错是否具备都不是判定责任的考虑因素,如WIPO认为,有效制止商业诽谤的典型做法是,不将实际损害或主观意图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原理》,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第327页。就是这方面较为典型的例子。二是违反禁令推定加害行为存在过错,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如果不能证明自己对于侵害(或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现行侵权责任法上的例子见该法第58条有关推定医疗机构过错的规定,比较法上例子参看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张新宝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45页注137。不过,根据禁令判定侵权责任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首先,禁令可能只是服务于国家管制目标,如果把禁令违反当作侵害私益的判定标准,可能就会导致公法目标与私法救济在功能上的混淆。例如,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的基本目标在于维护良好的经济秩序,其对市场参与者利益的保护效应可能只是其附带效果,并不能成为其他市场参与者直接诉请保护的理由。只有那些确实也具有保护市场参与者利益的规范,如横向竞争者之间从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才会授予特定市场参与者以侵权救济手段。其次,将禁令违反作为过错推定的理由,可能会不当地加重行为人的责任。因为,过错的判定应当限于对他人利益保护的注意,如果法律所要保护的利益本身是不明确的,将违反禁令作为推定过错的理由,就将使这种责任事实上转化为严格或无过错责任。比如,两位出租车司机都看到了对面有人要打车,其中一位不顾交通指示灯闯红灯把客人“抢”到了,依照遵守交通规则,本来应该是另一位司机接到那位顾客。这位闯红灯的司机是否侵害了另一司机的权益呢?违反禁止规定的事实能够为要求保护的司机提供支持吗?*类似案例的分析请参见考茨欧主编:《侵权法的统一:违法性》,有关案例3的国别报告。因此,只有禁止规定对拟要保护的利益指示明确时,其对于侵权责任构成的促成效果才会是明显的。
于是,更好的做法或许是在确认权益归属的同时,规定特定方式的禁止侵害行为。这在我国现行法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不论是民法通则、物权法,还是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都在确认民事主体的权利时又规定了权利的保护,同时从正面授权和反面禁止的角度实现规范目标。*不过,并非所有的法律都可以采取这种做法,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这类混合法性质的立法,因其私法手段(通过私人侵权诉讼)的运用在于实现公法规制目标,且保护经营者的纯粹经济利益,因此正面确权的内容就不是这类立法所能实现的任务,确权的任务只能通过其他法律完成。当然,这种做法也仍然存在不足,禁止规定所例示的行为方式有可能被理解为是对权益侵害方式的穷尽列举,认为只有以禁止规定所指的行为方式侵害权益才能被认定为侵权行为。这方面的著例是民法通则第100条有关肖像权保护的规定。该条第2句有关“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长期被理解为肖像侵权的唯一形式,特别是“营利目的”被当作肖像侵权的构成要件。这是典型的误读!该条第1句为确权规范,其保护效果是禁止任何没有法律或合同(同意)根据使用肖像的行为,第二句不过是这种禁止效果的一种列举规定,按照列举规定不限制概括规定效果的解释原则,“未经本人同意,也不得非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就属于第一句当然的效果。如果仅仅着眼于禁止规定,结果就会导致“非以营利为目的而使用他人肖像”的侵权行为不当地被免除责任。
不同规范设置方式对于司法裁判提供的指示效果是存在差异的,行为禁止效果可以从权益归属规定中被清楚判定的授权规定,或者受保护利益能够被清楚界定的禁止规定,都极大地减轻了法院在权衡冲突利益时的论证负担,使法院可以较为容易判定原告的请求是否有据,或被告是否应当担责。相反,如果法律的规定不清楚,那么就需要法官结合整个法律体系和案件事实的具体情况进行判断,这种裁量要素的复杂性以及裁量空间的大幅提升不仅要求法官具有较高的法律判断能力,对法官的业务素质或职业素质也提出了较高要求,并增大了法律适用统一化的障碍。
五、现行侵权责任法的裁判指示效果
尽管法律规范的特殊结构能够减轻裁判者的论证负担,但这种减轻不但取决于规范模式的选择,也取决于规范设计者对于受保护权益特性把握的准确性以及被禁止行为的典型性。在任何时候,不论立法者如何努力,裁判者的权衡空间始终存在,裁判者如何看待这种权衡空间并合理行使裁量权力,对于法律适用效果将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这里,我们仅以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为例加以说明。
(一)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
侵权责任构成的一般规定因其抽象性,对于法官裁判的指引效果最值得关注。
1.侵权责任法第2条
从侵权法整体来看,该条发挥的规范功能可以概括为两项:一是将权益侵害确定为侵权责任构成的规范要素,为后续有关侵权责任基础规定确立基准(第1款);二是确认了侵权法的保护范围或侵权客体(第2款)。*杨立新教授认为,《侵权责任法》第2 条作为大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其基本作用在于:“第一,确定侵权责任的范围,规定凡是侵害民事权益,依照本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违法行为,都是侵权行为,都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确定《侵权责任法》保护的范围,所有应当依法保护的民事权益,都在《侵权责任法》的保护之下。第三,提示符合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要求的侵权行为,都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第四,不具有过错要件,但符合《侵权责任法》第15条规定的承担其他民事责任方式的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这些侵权责任方式。第五,对于造成一方损害双方当事人都没有过错适用公平责任分担损失的情形,确定各自承担的责任。第六,对于将来发生、目前没有预料到的特殊侵权责任预留法律适用空间,当出现这种特殊侵权责任而具体规定没有规定、又不符合过错责任原则的一般侵权行为要求的新型侵权行为,可以适用大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适用法律,确定侵权责任。”(杨立新:《中国侵权责任法大小搭配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法学杂志》2010年第3期。)
“侵害民事权益”作为侵权责任规范要素应当如何解释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除侵权责任法第15条“停止侵害”规定外,“侵害”在该法其他规定中均做动(谓)词使用,即指针对“民事权益”的加害行为。这和“损害”概念除在同法第7条作动词使用外,其余各处均作名(宾)词使用刚好相反。*在侵权责任法第7条中“损害”被作为谓词使用,其他各处规定均作宾词使用。也就是说,整个侵权法64个条文中工使用“损害”概念90次,只有一次是作动(谓)词使用。因此,可以推定,作宾词使用时“损害”指代侵权结果,作谓词使用时“损害”除了含有“侵害”意义外,还有强调侵权结果的意义。据此推断,“侵害民事权益”在规范功能上首先包含了侵权责任构成理论中的加害行为要件。同时,由于侵权责任法在侵权责任形式上不以损害赔偿为中心,“损害”要件就不是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而是强化侵权责任构成的要件,也即,非损害赔偿责任仅以具备“民事权益被侵害”的规范结果为已足,不要求发生可获赔偿的实际损害或损失,与损害赔偿责任中则刚好相反。*参看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第6条第1款、第16条、第19-23条及第36条第1、3款。这表明,加害行为的规范效果而非实际损害结果才是所有侵权责任构成的一般要件,它只是在规范功能上与传统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中的“损害”要件相当,而意义则迥异。在包括过错推定或严格归责在内的特别侵权中,“损害”要件始终作为强化责任构成要件而发挥着限制责任的功能。根据前文所论,*参看本文二、(二)。在加害行为和加害结果确定后,因果关系要件也就同时得到确认。由此,在我国,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应当是:加害行为、权益侵害(规范结果)和因果关系。
这样,第2款通过对民事权益(主要是民事权利)的列举就具有确认权益侵害结果的指引意义。尤其是,该款将隐私权与名誉权并列具有确认隐私权独立权利地位的效果,从而消除将隐私权纳入名誉权保护可能引致的混乱。但是,该款基本上是宣示现行民事法律中已有规定的民事权利,其本身所具有的侵权裁判指引效果是极为有限的:一方面可能使未受列举的民事权利被误认为被排除在侵权法保护范围之外,另一方面在保持开放性的同时(使用“等人身、财产权益”表述),则又反面减弱了其指示效果。也就是说,只有明确而有限的权益列举(如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才能发挥最大限度的规范指引效果,但穷尽列举显然会引致僵化,对于权益保护目标的充分实现有害无益,这早已为各国实践经验所证实。只有裁判者对于这两方面的问题有清楚的认识,其可能引发的问题才有望被消除,而要做到这一点,法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权衡无疑是必要的。
2.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
作为一般规范,第6条第1款的核心要素是过错。“过错”在何种意义上是“一般要件”?换句话讲,过错之下有故意和过失之分,而过失的过错程度轻于故意,前述问题因此也可以替换为:过失是过错归责的一般要件吗?肯定回答意味着,任何基于过错的侵权责任只需过失即可成立;否定回答则意味着,过错不过是抽象的归责条件,并不决定具体情形下的侵权过错形态。
从现行法的规定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在侵权责任法内外,都存在不少要求以故意为必要的过错侵权。例如,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他人利用网络服务侵权而未采取措施的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行为人故意避开著作权技术保护措施或删除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侵权责任、*著作权法第48条第6、7项。广告经营者或发布者就虚假广告的连带责任,*广告法第38条第1款后段。以及专利权人恶意利用被确认无效的专利给他人造成损害的责任*专利法第47条第2款第2句。等。此外,最高法院通过大量的司法解释,也确定了多种故意侵权责任,如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他人避开著作权技术保护措施侵权提供帮助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雇员、帮工故意致人损害时的连带责任,*最人民法院《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第1款第1句、第13条第3句,该规定在侵权责任法实行后其应归于失效。期货交易所或期货公司故意误导致损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2条。恶意抢注域名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域名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技术合同中介人故意隐瞒信息对委托人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会议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纪要的通知》第87条。以及注册会计师故意出具不实审计报告的连带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5条。等。尽管这些责任的归责基础各异,但其作为实质意义上的侵权责任规范,仍然可以说明侵权责任在归责原理方面的内在差异。
由此可见,不仅受保护权益的具体情况能够影响客观注意标准,*参见考茨欧主编:《侵权法的统一:违法性》,第176-179页。导致过失标准出现内在分化,而且故意侵权的特别规定也凸显过失与故意区分对于过错侵权的实践意义。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过错归责不过是对形态各异、对行为人主观或客观行为标准有着不同要求的侵权构成的高度概括,其作为“一般要件”的特性是外向性的,即区别于没有主、客观行为标准要求的侵权责任形态(严格责任或无过错责任),在过错责任内部,仍无法形成对侵权行为的均质性要求。
辨明过错要件的这种外向而非内在的一般特征,也就为在过错要件要求下法官裁量留下了空间。在具体裁判中,法官总是必须权衡包括受保护权益属性在内的各种案件具体情况,以确定被告是否具有可归责性。法国法的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尽管第1382条并未对过错形态做出区分,但仍不妨碍司法实践中区别情况对不同侵权设置不同过错形态的要求。例如,对干预他人契约的侵权诉讼虽然以第1382条作为基础,但并不适用该条规定的广泛意义上的过错即过失和轻率行为,而仅适用故意过错。*张民安:《过错侵权责任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93页。对于滥用诉讼的侵权行为,针对财产损失的赔偿请求,通常以“恶意、滥诉或者有相对于欺诈的严重过错”为必要,而对于精神损失,普通过失即可。*参看《法国民法典》,罗结珍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078-1079页。我国司法实践的情况也基本相似。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一旦确立了被告行为与原告人身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被告的责任就几乎总是被肯定*例如,用人单位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安全管理规定致损,劳动者无法通过工伤赔偿获得充分救济时,用人单位仍然可能承担补充责任。(参见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纪敏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公正司法 一心为民 廉洁自律 一生平安》。)(这种情况在财产侵权中则不常见),精神损害赔偿需要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第1款第1项。就现行法上并无一般规定的第三人侵害债权,司法实践也应基于利益权衡要求侵权以故意为必要。*马强:《侵害债权制度及在审判实践中的适用》,《法律适用》2005年第4期。
(二)损害后果的公平分担
侵权责任法第24条由来有自,但在比较法上罕见其例。*该规定源自民法通则第132条,有关该规定在我国立法上源流,请参看王竹:《我国侵权法上“公平责任”源流考》。有关公平责任在大陆法中的情况,请参看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张新宝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10页以下。从该条的规范功能来看,属于所谓“公平责任”的一般条款,乃公平原则在侵权法中的表现形式之一。*民法公平原则在侵权法中的作用,一方面是公平确定侵权责任(包括责任减免),是各具体规定的基础原理;另一方面是作为无过失分担损害的基础规范。侵权责任法第24条发挥的是后一方面的作用。如果真如学者所论,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1款包含了公平责任的规范要素,*参见杨立新:《中国侵权责任法大小搭配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法学杂志》2010年第3期。那么,第24条的适用就应具备第2条第1款规定的侵权责任一般构成要件(与过失责任相同)以及损害后果和无过失要件(与无过失责任相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公平责任的适用可能既不要求损害是由行为人造成,也不要求受害人对损害发生无过错(受害人过失仅作为确定损害分担份额的考量因素),从而使公平责任演成没有免责事由的真正意义上的无过失责任。*参看“周开凤等诉宜昌县建设局人身损害赔偿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4期;“李萍、龚念诉五月花公司人身伤害赔偿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2期。
从比较法的考察结果来看,公平责任作为侵权责任的例外主要是为了克服加害人欠缺责任能力导致受害人无法获得赔偿的特殊情形。*参见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第110页以下。不论是贯彻矫正正义的过失责任,还是贯彻分配正义的严格或无过失责任,都必须以实现权益保护与行为自由的价值平衡为目标。一般性的公平责任单纯强调侵权关系两极中的受害人一极,必然会与前述要求相违。的确,现代侵权法有偏重权益保护的趋向,但是,放大这种趋向则可能会导致侵权责任构成规范追求价值平衡功能的失效,使过错责任与严格责任规定仅在加害关系明显充足责任构成要件时被适用,而公平责任则成为损害分担的统括性或兜底性的规范基础。这样一来,损害的公平分担就可能成了不问条件的损失转移,导致侵权法社会功能的过度膨胀,并使之根本丧失存在价值。
如此结果显然并非包括立法者在内的任何人所乐见,要防止其变为现实,同样需要限制公平责任一般规定的适用。要做到这一点,显然不在于是否承认其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地位,或者是否将其定位为侵权责任还是损害分担义务,而应将其限于特定适用范围。作为损害分担机制,其只有与特定类型的损害发生情境相联系才不至于破坏侵权法的结构平衡,就如同无过失责任须以“法律规定”加以限制一般。为此,最为稳妥的做法是采取各国公平责任例外规定的一般做法,仅在替代责任无法发挥救济功能、加害人突然失去意识等场合用之。鉴于现行侵权责任法对此已有专门规定,第24条实际就只能发挥宣示功能,和同法第7条的作用相同,而不宜单独作为确立损害分担效果的规范基础。
(三)小结
侵权责任法就其基本属性来看,更多是为侵权纠纷的裁判者提供裁判依据,在这个意义上,其裁判指引功能需要受到特别关注。现行侵权责任法顺应现代侵权法注重补偿的趋势,将保护民事权益作为首要任务,*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法学家》2010年第2期。通过确定侵权责任和损害后果的公平分担加以实现。在侵权责任方面,过失(过错)是实现价值权衡的基本手段,民事权益作为侵权客体的功能也主要藉此实现。无过失或严格责任在承认致害活动合法性的同时,基于风险分配原理让无过失的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通过类型限定,无过失责任对行动自由的消极影响能够保持在合理限度内。但是,无过失责任一般规定的设立则构成对限定目标的破坏,需要通过司法克制确保其不致引发重大问题。公平原则作为民法基本原则在侵权法中为责任构成与减免提供了正当性,但当其被作为损害分担的直接规范基础时,由过失责任和严格责任建立的侵权法基本结构就可能完全丧失价值,从而将侵权责任法变为“社会保险法”。因此,从实践的角度看,侵权判断的情境化特点要求裁判者结合既有法律规定对抽象的侵权责任构成要素进行具体化作业,并警惕一般规定导致侵权法过度社会化的问题。虽然具体权衡的必要性可能导致侵权法规则的确定性降低,加重裁判者的论证负担,但借助学术研究的合力与实践经验的积累,其风险能够得到合理控制。
六、结 论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权益侵害是所有侵权责任的构成要素,其与侵权行为不同要素(违法性和/或过错)的关联效果并不相同。作为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对象,民事权益不能单纯被拆解为权利与利益并以之作为思考前述关联性的基础,这种拆解只能产生权利话语膨胀的效果,无法为真正的利益冲突提供有效的解决思路。因此,民事权益作为侵权法保护的总体概念相较于以权利和利益为中心进行的侵权构造就更为适当。
但是,过于抽象的权益保护目标会引发法律体系的混乱与实现侵权法价值平衡目标的障碍,为此而提出的权益限制论以及差别保护论即使在现行法框架下也仍然是可行的。抽象保护目标的规定满足了侵权法的指示功能,但差别论则是贯彻侵权法实质价值目标的必要手段,通过不同级别的客观注意义务以及不同过错形态,侵权责任法能够对不同民事权益实现不同程度的保护。
在具体规范功能上,民事权益作为侵权客体的规范功能在于指示救济主张的正当性与加害行为不当性。当被保护权益由于其抽象性或不确定性而无法提供明确的指示时,基于侵权客体的思考反而阻碍了法律判断的顺利进行。基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关联性,关注侵权行为其他要素(比如过错和侵权行为方式)就能够从功能替代的角度为侵权责任的认定提供助益。
正是由于这种功能关联及替代关系,不同法律规范模式对侵权判定具有不同的指引效果。授权规范既可以明确权益归属效果,也可以间接指示对加害行为的禁止效果;明确的禁止规定则以相反的形式对侵权责任构成提供帮助,既可以直接彰显加害行为的不当性,同时又从反面产生权益确认甚至权利构成功能。
不同法律规范设计的指示效果对于法院裁判活动会有不同影响,越清楚的指示越有利于法院确认侵权,从而实现由立法预设的权益保护和行为自由的平衡。反之,不清楚的指示要求法院根据自己对于法律和具体情事的理解而分配损害,实现价值平衡,这对法院的职业或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不同规范设置以及其规范内容的明确性实际发挥着侵权法价值平衡任务的分配:要么主要由立法机构设定,要么经由司法过程由法院完成。现行侵权责任法的若干规定在彰显自身创新性的同时,也导致了新的问题,只有经由司法裁判者不放弃并妥当行使具体权衡的任务,侵权责任法才能在保护民事权益法的同时,能够维护适度的行为自由。
(责任编辑:魏 萍)
On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with Its Normative Indication Effects
Zhang Jiayong
The civil rights and interests as objects to be protected are explicitly stipulated by Tort Liability Law. Therefore, the infringement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becomes one of the elements of all tort liabilities, and influences the judgment of torts through various types of rules. Exploring the object of tort contributes to the judgment of blameworthiness of the wrongful acts. When definite indications are unavailable, exploring the nature and modes of wrongful acts will be functionally substitutable. Different settings of rules reflect different allocation of balance tasks, and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f normative indications. The abstraction of legislation and the situational judgment of tort require the court to make judgments b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tort object and wrongful act elements.
tort liability, civil rights and interests, balance of values, normative indication
张家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武汉 430073)
DF526
A
1006-0766(2017)01-013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