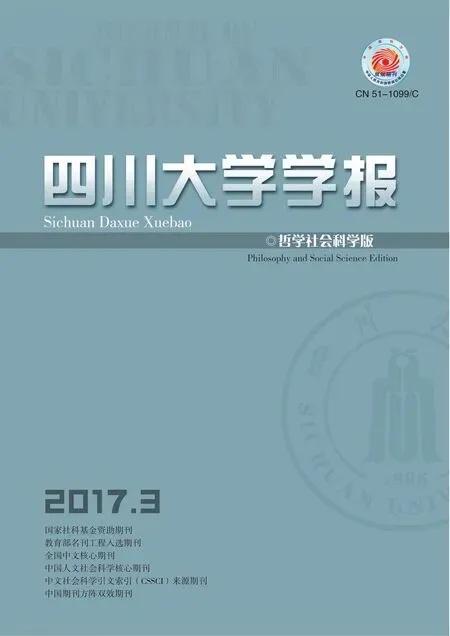技艺、生活世界与艺术
汪文圣
技艺、生活世界与艺术
汪文圣
胡塞尔现象学有三层技艺概念,最高为哲学的层次。因重视技艺概念,其哲学深具艺术性的内涵,虽然这点不为胡塞尔本人所强调。藉助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与形而上学,可解读出德性为一种技艺,以及技艺扮演着从人为到自发再到自然生成的角色。前者引发出胡塞尔的纯粹或形式伦理学,以及哲学是一种高层次的技艺;后者发展出艺术作为合自然目的理念。生活世界两层科学性与技艺三层次间的对照关系,更能显示技艺的哲学性一面,而胡塞尔《观念二》里蕴含的深意——现象学方法作为一种技艺,企图让实事本身在自然态度中显现——则可引导出胡塞尔哲学理论的艺术性义涵。
技艺;生活世界;艺术;胡塞尔;亚里士多德;现象学
一、技艺的前理解中浮现的问题——技艺与哲学或与德性的关系
技艺 (téchne)这个概念在西方历史中有长远的渊源。据考证,téchne源于欧语系的字根tek,意味着“将一个房子的木制作品组合起来”(to fit together the woodwork of a house),可能早期为造房子的意义,同时关联到作为木匠意义的tekton。之后,téchne的意义更延伸到造船、铸铁、医术。早期荷马 (Homer) 的《埃利奥特》 (Iliad) 与《奥迪赛》 (Odyssey) 已提到技艺的概念,公元前四、五世纪的《希伯克拉底文集》(HippocraticCorpus) 讨论了医术的技艺。这些或早或晚的技艺概念皆有个目的导向,以及对于某个特定事物以及环境的控制与征服。古希腊的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 所写的《安蒂冈妮》 (Antigone) 以及埃斯库罗斯 (Aeschylus) 的《被缚绑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Bound) 的告白等,皆表示技艺对环境以及对命运之征服情境。*Tom Angier, Techne in Aristotle's Ethics: Crafting the Moral Life, New York: Continuum, 2010, pp.3-4.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皆谈及了技艺,后者既强调技艺所得的知识是不精确的,而技艺与德性的关系似乎是不明确的,因德性是否是一种技艺,或二者本质上有所不同,还有待讨论与厘清。另一方面,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技艺扮演着从人为到自发再到自然生成的角色,这个技艺的意义值得重视与发挥。技艺概念在希腊罗马时期表现在七艺上,被称为artesliberales的文法、修词、辩证、算数、音乐、几何、天文七个学门即当时流行的技艺学,旨在教化与形塑自由的人格。而塞内加以为哲学才是技艺学的本质,才足以让人格自由。*参见Christoph Horn, Antike Lebenskunst, München: Beck, 1998, S.53-54。
如果塞内加的哲学是亚里士多德以德性之谈论为核心的实践哲学,那么塞内加与前人对于七艺或哲学让人格自由的争论,似乎即是亚里士多德所面对的德性是否为一种技艺的争论。
二、胡塞尔关联于生活世界的技艺概念
技艺的概念早为胡塞尔所关切,这显示在其所著《逻辑研究第一卷:纯粹逻辑学导引》与早期《伦理学与价值论的基本问题》中,此时他质疑纯粹逻辑学与伦理学是否为一种技艺学(Kunstlehre)。这似乎也是哲学与技艺是否能同一的问题。从晚期的著作《危机》来看,胡塞尔直接将“技艺”视为与哲学对立的生活世界活动。*Edmund Husserl,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Hua Bd. VI, Hrsg.: W. Biemal, Den Haag: Nijhoff, 1954, S.48.(Krisis)(以下引用该论著仅在引文后标示页码)因哲学与技艺皆是在讲究精确性的科学前,也就是在自然尚未披上数学理念的外衣前的阶段,哲学又被称为“实践的技术”;(第23页)相对之下,科学与科技被胡塞尔称为“单单的技术”。(第46页)
其实受科学与科技影响甚至指导的哲学亦属于“单单的技术”,这种哲学虽也可归为一种技艺,却是一种脱离生活世界的技艺。这是胡塞尔在《危机》的开始所指出的欧洲科学危机的问题所在:“科学的理念被实证主义地化约到单单的事实性科学,科学的危机即是生活意涵的丧失。”(第3页)事实性即是实证的同义词。“单单的技术”让技艺与哲学成为“浮在表层”(第121页)的同一,而我们在前面提出的技艺与哲学的同一关系,应是在超越了实证科学的牵制下,从只在表层的人所不知的“深邃维度”(第121-122页)来讨论的。
对胡塞尔而言,超越实证主义的牵制,重视生活的意涵,这主要表现在主体意向性所建立的活动上。前述“实践的技术”以生活世界经验与他物建立了非精确关系后,虽在要求更完整的动机与理念下往精确性去迈进,但这始终是开放的、无法达到的“极限型态”而已。(第23页)但主体的意向性不能脱离经验直观而直接到思想的层次;胡塞尔警告我们,一旦仍依赖于经验的“实在的实践”被以纯粹的思维为主导的“理想的实践”所取代,那么原本的开放性就终止了,极限型态被思想所锁定。更具体来说,思想透过数学来规定理想的型态,以至于精确性被建构起来。故胡塞尔说,理想的实践毋宁即是“数学的实践”。(第23-24页)
上述的意向性活动确实关系到人的自由性,但这自由不是脱离生活经验而腾空至纯粹思维活动的自由。胡塞尔指出事实性科学所造就的单单“事实性的人”正丧失了人真正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是人鉴于自己存在的意义与否,在关系着周遭世界做决定的自由,使自己可能去理性地形塑自己与周遭世界。但在形塑的过程中却不可因为人的存在历史千变万化,人的生活条件、理念、规范流动不定,而立即将涉及这种人类历史的精神科学弃之在旁,并以实证科学为指导原则的事实性精神科学来取代。(第4页)这些皆显示人的自由应是面对生活经验中的理性与非理性问题,借助不单只重视理性的纯粹思维,更包括涉及非理性的直观一起来做决定。其中非理性实隐含地指向着理性,故直观的地位反而更为重要,进而演变成为生活世界的问题。(第13、137页)
三、生活世界的几个科学性层次
针对生活世界的问题,胡塞尔区别了部分问题 (Teilproblem) 与普全问题 (Universalproblem) 两种。当对生活世界做科学论题处理时,若将它放在一般客观科学的视野,并役使后者,那么就导致生活世界的部分问题;若生活世界的存有方式被视作问题而提出,并不论及客观科学问题,那么就导致生活世界的普全问题。(第124-125页)鉴于此,胡塞尔提到,针对生活世界自身所发展的认识论、知识论、谓说、真理、先天规范的逻辑等科学性问题,皆将以崭新的面貌呈现,而原先的客观科学反成为生活世界之普全问题的部分问题。(第137-138页)
在《危机》35节以后,胡塞尔就在处理生活世界的科学性。它虽是主观-相对的,但仍被揭示出固有的先天性,譬如其具有普遍的结构,包含前科学而非精确的时空性、其中物体皆有的形体性质、事件之间的因果性。这些皆不是理论的观念化、几何学与物理学家所假设的基础结构,相反,后者所属的客观-逻辑层次的普全先天性却是奠基在就发生学而言更早的、另一个普全的生活世界的先天性之上。(第142-144页)
将生活世界做科学性处理,当然是对原先我们直接地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发生“兴趣的转变”,而让世界的“前被给定性”——包括世界的显现方式、给定方式、价值样态等——一方面呈现出主观-相对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带出了对于原先直接存在于世界所具的统合性意识。但这尚是在世界的基础上所做的兴趣转变与反思,因而所形成的生活世界的科学——如上述先天的生活世界普遍结构——尚是第一个阶段的。(第149页)胡塞尔要展开的是“在前给定的生活世界回溯中通往现象学的超验哲学之路”,(第105页)而在39节后所处理的,一方面表示出世界生活最终由超验的主体承担其价值或有效性,另一方面却也突显了生活世界的科学性应以超验主体的科学性为基础,生活世界普全问题的科学性尚需往作为其基础的超越主体的科学性去延伸。
生活世界因此扮演两个角色:一是作为人类世界生命的基石,(第158页)另一是作为往超验现象学去开展的引线。(第175-177页)就此而言,生活世界具有两个功能:基石功能与引线功能。此外,针对前者的基石功能或前说的生活世界科学第一个阶段,胡塞尔提出了生活世界存有论的概念。若从后者的引线功能,揭示了超验主体之阶段来看,先前的生活世界或称作超验的现象,或称作具体的超验主体性的成分,其先天性也可被视为超验性所具普全先天性中的一个层次;但要注意的是,生活世界已成为超验主体的对应项,其意义已从我们直接所介入的、作为什么的生活世界,转为它如何必然与普遍地显现给作为超验主体的我们。(第176-177页)生活世界科学性也从它是“什么”更深入至它“如何”的内涵。
生活世界的两层科学性,以及它与超验现象学间的关系,可否转嫁到技艺的多层意义,以及它与哲学间的关系呢?我们从现象学的观点可否回应亚里士多德的问题:德性是否为一种技艺?
四、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之德性与技艺关系
我们先整理出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对于技艺与实践或德性间的关系并胪列如下:
1.技艺与研究,同样地,实践与选择皆在追求某种善,但至善是它们共同的目的。(1094a 1)
2.技艺产品所呈现的精确性不一,政治学所研究的道德之高贵与正义,也是如此的不同与多变,以至于使我们认为它们是来自于习俗,而非为自然法则所规定。(1094b 12-17)
3.德性的获得要靠修炼,如同发生在技艺的行为里。任何事我们要学着去成就 (如成为建筑师或成为正义的人),就必须在实际的操作中去学习 (如实际去建筑或行正义之事);这些不是靠天生的,否则我们不需要老师。(1103 a 32-1103 b 14)
4.技艺不同于德性,因为技艺产品在其自身而为善 (按:表示做出来就是善的),但德性除了产品呈现的性质外,还要来自于一种状态。(1105 a 26-b 4)
5.仔细言之,1) 德性出于行为者的意识 (按:如苏格拉底的智即是德),2) 行为者为行为之故而做出选择,3) 行为者出于确定而稳定的质量而做出选择 (按:这即是第4项所谓的状态)。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特殊性在上述第2)与第3)项,因技艺仍可属于第1)项,由此显示德性之行动,而非只是知的重要性。(1105 a 33-b 4)
6.鉴于灵魂质量的三层次:感情、能力与品质。(1105 b 18)人不只有能力生出感情,且在面对所生出的感情时,因长期的作为而蓄积了行为的倾向,以至于具有德性的质量,让德行出自有德性的人,而非只是合于德行而已。故德性属于品质的范畴。反之,技艺的活动可以只合于技艺而已。(1105 a 20-35)
7.实践的知识是粗略不精确的。(1103 b 32ff.)但另一方面德性的精确性表现在中庸适度上。如果好工匠也寻求适度,而若德性像自然一样,较技艺更精确、有效,那德性要以中庸为目的(1106 b 14-16)。重要的是中庸之道如何被具备善的质量与智能的人落实到特定的环境中:适当的人、时间、地点、理由、方式。(1109 a 27)
8.人的灵魂中有五种达到真理方式:技艺、科学、实践智、智慧、洞察。(1139b 15-16)实践与制作的质量不同,彼此也不互相包含;又若没有与制作相关的质量则没有技艺,而没有技艺则没有此品质。技艺是让事物生成的方法,而其原因在制作者而非被制作物。如果制作与实践不同,而制作和技艺相关,那么技艺就不与实践相关。技艺一方面与自然的生成无关,另一方面则和运气相关于同样的一些事物。(1140a 3-18)
9.实践智不同于科学,因实践的题材包含着变化。实践智不同于制作,因为实践与制作在始因上不同 (制作的目的是外在于制作活动,实践的目的就是实践本身——做得好自身就是一个目的)。(1140 b 3-5)
10.技艺中有德性,而实践智中没有德性。技艺出于意愿比违反 (不合于) 意愿犯的错误较轻;实践智则像德性一样,出于意愿所犯的错误则较重。故实践智是一种德性而不是一种技艺。(1140 b 20-25)
11.智慧用来说明在技艺上最完善的大师。虽然这仅是指在技艺上的德性,智慧毕竟是指在总体上的智慧,而不是在某个方面,因智慧毕竟是各种科学中最完善者。(1141 a 10-17)
技艺与德性的共同性在于它们皆追求善,它们的知识是不精确的——尽管德性依循中庸之道被认定为一种精确,并且它们的获得要靠修炼学习。有几处明显表示技艺不同于德性,如技艺可以不计较出于何人的质量,德性则需要。换言之,技艺可以合于技艺,但德性必须出于德性。制作的目的是外于制作活动,但实践的目的是实践活动本身。在这里实践的用语可适用于德性,制作是否即完全等于技艺,这是个问题;而上述技艺与实践不相关的表示似乎是个条件句。实践智是一种德性而非技艺的说法,似乎确定了后二者之不同;但技艺又与智慧被等同视之,技艺似乎可提高到德性的层次。
至此,我们可就两个问题来提出本文的主张:第一,对亚里士多德整体思想而言,实践的目的是否即是实践活动本身?或也和制作与技艺一样,是以外于它们之活动的至善为目的的?事实上,沉思而具有神性的智者生活才是第一义的幸福或至善,德性是人在现实生活中透过伦理所达到的第二义的幸福;(1177b 30-1178a 10)“德性保证我们指向目的的正确性,而实践智保证指向目的之方法的正确性”。(1144a 6-8)这个说法中的“目的”一词指的应不是实践活动本身,而是第一义的幸福或至善,即它是作为第二义幸福的德性的最终目的。如此以目的在活动自身与否来区别实践与技艺的主张是有问题的。第二,亚里士多德是否以技艺所提供的模式与例证作为伦理与政治思想的诉求?这特别是针对二者相同而言,汤姆·安吉尔 (Tom Angier)即持此观点。*Angier, Techne in Aristotle's Ethics, p.36.
五、胡塞尔之技艺学与生活世界几个科学性层次间的关系
若站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立场来看亚里士多德的问题,是否能从生活世界的两层科学性进一步厘清技艺的意义呢?其实胡塞尔哲学本身也有对于技艺的歧义,得先从生活世界的理论来做厘清。
如前所述,胡塞尔早期已提出纯粹逻辑学与伦理学是否为一种技艺学的问题。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一卷《纯粹逻辑学导引》中简单将具规范性的学问称为技艺学,并表示“在基本规范是一种目的或能够成为一种目的之处,且在经由这基本规范任务的明显扩展之下,技艺学就从中产生了”。*Husserl,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Erster Band: Prolegomena zur reinen Logik. Text der 1. und 2. Auflage, Hua XVIII, E. Holenstein (Hrsg.). Hague/Boston/Lancaster: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75, B 27.“在经由这基本规范任务的明显扩展之下”,所朝向的目的扩大,随之达到目的之方法的深广度也会扩大。我们以为这应该是个重点,因为“技艺学”会随之有不同的层次。
同样在《纯粹逻辑学导引》中,胡塞尔指出较狭隘的技艺学,“如只是就绘画讲究如何握笔和用笔,唱歌讲究如何用胸及用嗓,骑马如何收放缰及夹腿”,乃至于“增强我们记忆的方式”等等。*Husserl,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Erster Band: Prolegomena zur reinen Logik, B 28及该页脚注1。他在20年代的《伦理学导引》中指出的建立目的设定与方法规定等行动的实践性判断与论述,呈现的是对实践活动的建议、指示、规定,它们各司不同活动的实践性功能,呼应上述的较狭隘技艺学,可被规定为第一层的技艺学意义。接着,他指出这些技艺可自成体系,形成了现实性的科学学门,但不构成连成整体真理的、属理论科学的系统;这尚在理论科学实践地应用,或实践命题的理论化的阶段,可归为第二层次的技艺学。值得注意的是胡塞尔最终的说法:若不来到纯粹与自由 (摆脱)于实践的科学型态,理论就会去服务实践;过去常看到一种半调子的态度,即在理论中并不超越出何者能对实践者有用的考虑;相反,正是开始不顾及实践要求的纯粹科学,后来才足以有最大的实践成就。这实表示技艺学的第三个层次,鉴于此,胡塞尔所诉诸的纯粹逻辑学与纯粹伦理学实是第三层次的技艺学。*Husserl, Einleitung in die Ethik: Vorlesungen Sommersemester 1920/1924. Hua. XXXVII, H. Peucker, Dordrecht (Hrsg.). The Netherlands/Boston, Mas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4, S.4,25-26,30-32.
技艺学的第三个层次是哲学的层次,我们是否可从这个关系回头看亚里士多德关于技艺与德性间关系的讨论?胡塞尔又怎么看亚里士多德的呢?
六、从胡塞尔对亚里士多德的评论看二者的关联
在1914年《伦理学与价值论的基本问题讲义》中,胡塞尔指出逻辑学起源于对抗希腊的怀疑主义,当时亚里士多德建立逻辑学为科学认识的方法学,可称为科学认识的技艺学。他认为,一直以来,学者们都在寻找促进实践的认识成果与科学的认识成果,以及实践的规则;曾有不少学者将此实践的规范求之于心理学,而实不知亚里士多德的 (形式) 逻辑虽独立于所有实践与心理学科,却可作为实践技艺学的理论基础,因为形式逻辑和形式本体论不能分割,后者即和对象的应用性有关。*Husserl, Vorlesungen über Ethik und Wertlehre, 1908-1914. Hua. XXVIII, Ullrich Melle (Hrsg.), Dordrecht/Boston: Kluwer, 1988, S.4-5, 8-9.
当人们首先对于生活中的行为涉及善与幸福等作反省先出现了质料伦理学后,更进一步去对最普遍的、适合所有情形之下的善或至善去反省,就有了形式伦理学。胡塞尔以为这是人类行为之最高理性的目标。(第37、 39、48页)
但胡塞尔对于形式实践学的强调,反遭致一些读者的批评,认为他在早期的伦理学论著中过于模拟逻辑学的形式规则,而忽略了质料伦理学或价值学的讨论。某些学者指出胡塞尔本人亦强调质料价值学的重要,但在晚期仍未将它发展开来,继而讨论胡塞尔中晚期重视人的天职、社会伦理与爱的伦理学,以及和早期静态分析区别开的发生现象学立场,企图补充属于质料层次的伦理学。*Melle, Ullrich. Edmund Husserl: From Reason to Love, in: Drummond,2002. J. J. and L. Embree, eds.,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o Moral Philosophy: A Handbook, Dordrecht/Boston/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p.229-248; Janet Donohoe, Husserl on Ethics and Intersubjectivity: From Static to Genetic Phenomenology,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2004, p.127ff.
我们则要特别提示,以胡塞尔的立场而言,形式伦理学即为纯粹伦理学,而这是属于技艺学的第三义,质料伦理学则为技艺学第二义。而从技艺学的义涵来看,往纯粹或形式伦理学的发展是理所当然的事。但胡塞尔伦理学之别于知性伦理学的地方,即在于其亦接收了经验伦理学重视人感情的部分;而感情如何与知性综合起来,即成为重要的课题,这也是悠关于技艺学如何从第一义往第三义发展的问题。我们与其批评胡塞尔早期伦理学著作未对质料伦理学多着墨,不如从中去发掘质料与形式结合的可能,而从生活世界通往超验现象学之路正是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若我们进一步观察,拥有智慧的沉思生活既是自然发展的终极目的,技艺的修炼是否最终成为自然的生成一样,这关联到本文的第二个讨论主题:技艺如何扮演着从人为到自发再到自然生成的角色?而在胡塞尔的技艺第三义或是生活世界科学性第二个层次是否亦有类似的意义?
七、技艺扮演着从人为到自发再到自然生成的角色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二卷讨论“道德之善”问题前即指出德性不是天生于自然的,也不是相反于自然的。感情与感情的能力属于人的自然或质料层次,但人的德性是经过理性的审度与选择而来的,且必须在习惯中才能将之完全地发展,让人具备德性的质量后再自然而然地将德性展现出来。质量的养成是教化与修炼的事,修炼是将总原则方向的“中庸之道”落实到人所在的特殊环境,而将之培养出具有德性的质量。*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lated by J. A. K. Thomson, England: Penguin, 2004, 1103a 20-26,24n.1.故当人之理性介入了质料层次的感情,再让习惯发展为善良的人格,便说明德性虽不是出于自然,但仍不相反于自然的特性。
当亚里士多德以具神性的沉思生活为最高幸福或至善时,其整个哲学体系便是以自然的机体性发展为终极目的,而关于技艺的哲学论述皆以这个终极目的为依归。这种技艺纳入到向自然目的生成的思想雏形见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他将技艺生成定义为:“经由技艺而生成的物体,其形式是在技艺家的心灵里。”(1032a 35)之后,他举了建造房舍与恢复健康的两个例子。
房舍的技艺生成包含两个部分:思维与制造,亚里士多德表示:“思维是从起点与形式开始进行,制造则从思维的结论出发而进行。”(1032b 15-16) 换言之,心灵里的形式被应用在质料,思维被实现在一座房舍里。惟健康的生成常被亚里士多德用来刻划自发性的生成。房舍的建造不是自发的,因为形式被应用在质料的过程始终需要一个施作者有目的地促成。但在从生病到健康的产生过程中,有技艺、自发、自然生成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1) 当身体在被磨擦生热后,2) 会产生自身的运动,以达到 3) 身体处于一种和谐性的健康状态。(1032b 7, 25; 1034a 12)亚里士多德对此也做了说明:“这个问题可被提出,为什么一些东西的生成是技艺以及自发的,例如健康;而其他东西则否,例如房舍。理由是在一些情况下,质料可以激发自身的运动,在其他情况下则不然。”(1034a 9)恢复健康的例子呈现了技艺扮演着从人为经自发,再到自然生成的角色,它果真对于德性之出于人为,但经培养修炼成合于自然的质量,提供了模式与例证。
胡塞尔的技艺学所具的深刻意义,也蕴含着技艺虽来自人为,却以自然的生成为依归的意涵。问题是,技艺学的第三义或生活世界通往超验现象学的科学性如何显示其根本上是自然的生成呢?这个问题要从超验主体的静态分析过渡到发生学的说明来解决。
在属于静态现象学时期的《观念二》里,胡塞尔一方面主张“纯粹我”奠定与构成最终的精神或人格世界,另一方面却将“纯粹我”和“精神或人格我”混为一谈。*参考Manfred Sommer, “Einleitung: Husserls Göttinger Lebenswelt,” in: Die Konstitution der geistigen Welt, 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Manfred Sommer, Hamburg: Mainer, 1984, S.IX-XLII。他提出了数个理由质疑胡塞尔在《观念二》将纯粹我与精神或人格的我混为一谈:1. 主动与被动的我究竟是纯粹我还是人格我 (Husserl,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Zweites Buch: Phänomeno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ur Konstitution, Hua. IV (Ideen II), Hrsg.: M. Biemel, Den Haag: Nijhoff, 1952, S.97-99, 212-215),2. 纯粹我的意向性与人格我的动机性是否相同(S.215-216),3. 人格我像纯粹我一样是反思的产物还是在自然态度下为不自觉的(S.182, 223, 247-252),4. 具备个别性的绝对性究竟为精神我还是纯粹我所有 (S.297-302)。从前者来看,“纯粹我”的超验层次和“人格我”的被构成层次固然有别,但若依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力求除去人为干扰或扭曲事物对我们的呈现,以“回到实事本身”,“实事”包括世界与超验主体,“回到实事本身”意味着回到世界与超验主体未被人为干扰,也就是自然本性显现,那么精神世界与“纯粹我”皆属于我们在自然态度中的世界,如是“纯粹我”也可隶属于更广义的精神或人格的概念,这岂不让超验主体的技艺活动显示为具有自然生成的性质?胡塞尔虽在《观念二》以为“纯粹我”与“人格我”皆是“反思的自我统觉的对象”,但这不表示在反思前它们不以自然态度的方式存在。胡塞尔强调的“我原本不是来自经验……而是来自生活”,*Husserl, Ideen II, S.247,248, 252.完全适用于它们两者在前反思阶段,未受人为干扰,以其自然本性存在的状态。
这里举出两点来看发生学的方法,并连接到我们关心的技艺过渡到自发、自然生成的问题。首先,胡塞尔从发生现象学的观点处理生活世界通往超验现象学之路,此因他发觉回到“纯粹我”本身的过程不是一蹴可及的,要搁置的还包括历史习性的沉积,而历史的概念即被纳入到他晚期生活世界概念来讨论的问题。
其实在《观念二》已有“生活世界”的概念,且有两个意涵:一是不论自然科学者或精神 (人文) 科学者所共处的世界,另一是精神科学者所处的世界。自然科学具自然主义的态度,以因果性解释世界;精神科学是具纯粹意识构成的自然态度,以人格的动机来解释世界。(第189、 288、374-375页)上述第一个生活世界意涵只是显示为各个科学家以不同态度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虽对于各个科学没有价值的评价,但已透露了晚期在《危机》中经由“生活世界的搁置”*Husserl, Krisis, S.140.所产生的生活世界意涵:让自然科学家自觉到除了科学研究的生活世界之外,尚有处在家里、自然界、娱乐场所等的不同生活世界,以及察觉与尊重从事其他领域者的生活世界。第二个生活世界的意涵较具理想性,是各个主体在彼此沟通交流中构成的社群主体联盟,是理想的精神世界。*Husserl, Ideen II, S.138-39, 196.它要以纯粹我为构成的基础,让构成活动以动机而非因果性为根据。
但如前述,要还原到纯粹我非一蹴可及,《危机》所做的“生活世界的搁置”与“普全的搁置”实是将《观念二》那两个生活世界结合起来,让自然科学家如何鉴于精神世界作为现象学构成的终点,而将自己的研究纳入此历程中。发生学的分析显示了:自然科学的生活世界是源于历史上伽利略作为代表人物的新发明,他将前代人建立在经验上对于世界相对性的理解,转变成建立在数学思维上的绝对性理解;*Husserl, Krisis, S.20ff, 157.自然科学家(也包括现代人类)能对这些历史习性的沉积有所察觉,让为自然科学影响的生活世界更有效地脱离自我的绝对化,以纳入到更宏观的生活世界里。
其次,发生学的分析也显示了《观念二》里作为理想的精神世界的社群主体联盟却已蕴含在比纯粹我更深层的领域:内在时间意识讨论中出现的“原我”概念,被视为具有内在社群化的意义;*Ebd., S.188; Klaus Held, Lebendige Gegenwart. Die Frage nach der Seinsweise des transzendentalen Ich bei E. Husserl, entwickelt am Leitfaden der Zeitproblematik, Den Haag: Nijhoff, 1966, S.156-160.被动综合解析里出现的前我概念,被视为自始即与他者处于一共在的状态。*Husserl, Zur Phänomenolog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Texte aus dem Nachlaβ. Dritter Teil: 1929-1935, Hua Bd. XIV, Hrsg.: I. Kern, Den Haag: Nijhoff, 1973, S.172-173, 604.这其实有着亚里士多德往自然目的生成的质形论思想背景。
因此,前者对于历史习性的发生学分析,让我们更确实地以自然态度活在精神世界里。后者的对于超验主体的发生学分析,显示了个体生命本身即本着自然目的性进行自然的生成活动,它让我们在自然态度下从事技艺的精神生活取得了自然生成性的意义来源。
八、技艺与感性或美感
技艺最终是自然生成。无怪乎海德格尔说,最高层次的制作是自然生成。在《自然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一般来说技艺一部分是去完成自然尚不能完成的东西,一部分是去模仿自然。”(199a 15-17)整体而言,技艺以自然的生成之目的为目的。这固然呼应了本文强调的技艺是往自然生成过渡,但出现在这里的“模仿”一词,是否与一般人以为艺术是模仿自然有关?
“模仿”是亚里士多德《诗学》的主题,但这里却没有明言诗人以语言模仿的对象是自然。文中强调的悲剧不是对人的模仿,而是对行动的模仿,对于场景、对于情节的模仿。第九章更区别了意在描写普遍事件的诗,与意在记录个别事实的历史;故诗人不是叙说确实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即使可能发生的事出于偶然或出于必然。鉴于对这种可能性的叙述,诗人反成为对于事件与情节的创制者。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起源》中强调诗是艺术的本质,*Martin Heidegger, “Der Ursprung des Kustwerkes,” in: Holzwege, S.1-72, Frankurt a.M.: Klostermann, 1980, S.61.更要注意的是,他在《人文主义书信中》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第九章做了呼应与诠释:作诗比对历史之存有者作探查更为真实,而对于普遍性的揭示是像被悲剧所揭示的东西一样。一般而言,悲剧英雄常做冒险以面对未知的命运,而海德格尔理解诗之成为诗,正在于其所具的“冒险”特色。但它的冒险是被存有命运所指使,因而诗人本身嵌合着存有命运,他不是真正的冒险家。*Heidegger, Über den Humanismus, Frankfurt a.M.: Klostermann, 1981 (1949), S.53.海德格尔似乎对于诗人的能力要求得更多,它不只能应和着自然,更能应和着在古希腊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命运。对亚里士多德而言,诗人是位有智慧的人,洞察与掌握了自然的终极目的,诗人实具有着前述第三层次的技艺能力。
历来的哲学家,如康德对于美感形成了所谓无目的但合目的之论述,也是建立在技艺最终犹如自然生成,因它朝向自然的目的。而在《对科技追问》里海德格尔指出,若一种技艺能产生出美的艺术,是要像古希腊人一样:“怀着虔诚的心,顺从真理的支配与保存。”因而我们顺从于历史命运的揭蔽,反而即是一种艺术。这里海德格尔也将艺术的本质——持续、继续授予——归于诗;对命运顺从的诗性的揭蔽让艺术得以持续,它授予了各个艺术,让艺术得以养护救星的生长,也就是让历史命运的揭蔽充分展现其授予性。*Heidegger, “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 in: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Teil I, S.5-36, Tübingen: Neske, 1967, S.34-35.鉴于此,海德格尔理解的艺术不是建立自合乎自然目的,而是建立在合乎凌驾自然目的之历史命运的基础上。这也意味着技艺在扮演着从人为过渡到作为更广义自然之命运的角色。
在合乎自然目的或历史命运之下,一些哲学家提出了美感或艺术的概念。我们在前面对于生活世界的发生学分析,也企图连接到自然目的作为最底层的生命动机。技艺与生活世界的主题关连到sthetik一词的双重意义:美学与感性论。
在康德知性之规定感性与否造成了认知与美感之别,对于胡塞尔之强调生活世界而言,感性一词在连接超验概念成为transzendenatlesthetik(超验感性论)时,指“经排除了所有判断性的知,也就是排除了建立在直观之上具规定性与谓说性的思维之后,所局限的直观、乃至知觉,以及世界现象,只要它是知觉的现象”。《被动综合解析》的编者Msrgrot Fleischer指出,在1918—1926年间的上课讲义与研究手稿中,胡塞尔多次用了“超验感性论”一词,但它除了关涉知觉现象之外,还作为一种被称为“世界逻辑”建构的首要基础,这是区别于传统的“分析逻辑”以及其所具“空洞的形式的一般性”,所形成的“超验逻辑”。惟因“超验感性论”并不局限于康德所言的时空,而关涉较康德的“超验逻辑”更深广,故为避免误解,Fleischer宁愿使用“被动综合解析”作为书名。*Husserl, Analysen zur passiven Synthesis. Aus Vorlesungs-und Forschungs-manuskripten 1918-1926, Hua Bd. XI, Hrsg.: M. Fischer, Den Haag: Nijhoff 1966, S.295, XIV-XVI. (Einleitung des Herausgebers)
对于意识流及其对应的经验世界的被动综合解析,即是前述生活世界议题中进行“普全搁置”所做的超验主体发生学分析。故对胡塞尔而言,感性论最终与生活世界第二层次的科学性意涵,也与技艺学的第三义关联在一起。而技艺学的第三义启示着我们,当人为活动进入到不以知性概念支配的自发活动,再到如同自然生成的状态时,技艺即能产生出美的艺术。故胡塞尔虽就认知的发生学谈到感性论,感性论为认知而服务;但感性不受到知性概念的规定,它反而发生地构成胡塞尔式的范畴,感性终将顺着对象的合目的性而成为美感。但这个感性论所具的美学意义却未为胡塞尔本人所强调出来。
(责任编辑:曹玉华)
Technique, the Life World and Art
Wang Wensheng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there are three levels of the notion Téchne, and philosophy is at the superior level. His emphasis on this notion leads to the artistic nature of his philosophy, even though he does not explicitly mean that himself. Following Aristotelian tradition of ethic and metaphysics, virtue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technique, and that technique goes from the realm of artificial production through that of spontaneity to natural genesis. The first idea provokes Husserl's pure or formal ethic; in another word, philosophy is a high-level technique. From the latter develops an art as idea conforming to the End of Nature.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binary scientific nature of the life world and triple artistry of technique manifests the philosophical aspect of technique, and hence whatIdeaIIof Husserl implies—the method of phenomenology as a technique tends to present the fact in natural attitude—could guide us to understand the artistic nature of his philosophy.
technique, life-world, art, Husserl, Aristotle, Phenomenology
汪文圣,(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哲学系教授
B5
A
1006-0766(2017)03-0052-08
§外国哲学研究§
——专栏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