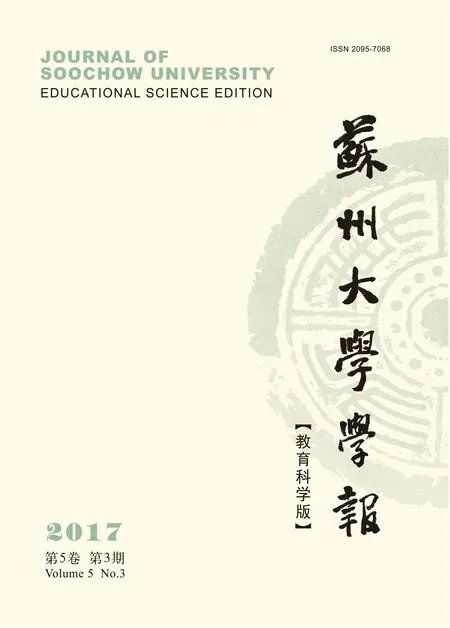政府权力边界与杰出人才培养
陈 先 哲
政府权力边界与杰出人才培养
陈 先 哲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国内大学的学术人员为何难以成为“钱学森之问”所言的“杰出人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学术职业化程度太低。学术职业化程度低则主要源于政府权力的越界,使得学术场域难以成形,学术逻辑无法得到尊重。在新的发展时期,应在反思政府对于学术人才培养和管理的目的、职能和手段的基础上,厘清政府的权力边界,建构成形的学术场域,提高学术职业化程度,营造杰出人才辈出的制度环境。
权力边界;学术职业化;学术场域;杰出人才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钱学森之问”始终在拷问中国。这么多年过去,也不知有多少人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钱学森之问”。仅仅从教育的解释来看,有人认为是中国高等教育活动陷入了以知识为中心和以考试为目标的“范式陷阱”[1],从而制约其创造性的产生;也有人认为不能仅归咎于高等教育之过,更来自于基础教育之失,从小开始的应试教育抹杀了创新的可能性[2]。从理论演绎的角度来看,这些解释都颇有一定道理。但若就现实而言,不少在世界上取得出类拔萃成绩的华人,尽管通常具有国外留学或工作经历,但很多也都完整地经历了国内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因此,仅从教育角度出发的解释就多少会显得有些乏力了。那么,“钱学森之问”已远非教育之问,更大程度上是社会系统之问了。本文试图从政府权力边界的角度切入,对如何回答“钱学森之问”做一些思考。
一、学术职业化程度低:难以培养出杰出人才的一种解释
要讨论“钱学森之问”,可能先要对钱学森先生所说的杰出人才之外延作一个界定。各行各业皆有能称为杰出人才者,但根据当时“钱学森之问”的语境,应该是特指受过学校教育之后的学术人才。2005年,时任国家总理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按照这个问题的逻辑再走下去,我们当然要再接着问:我们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学术人才主要在哪里开展职业生涯?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并无太大争议——国内大学培养的学术人才主要还是在国内尤其是国内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那么,按照这个逻辑走下去的“钱学森之问”就可变成一个界定得更加清晰的问题——国内大学的学术人员为何难以成为杰出人才?
此外,还要对杰出人才之内涵再进行界定。钱老所说的杰出人才,应该是世界级的人才,是大师级的人才,与现在我们国家推行的各种人才计划里的“杰出人才”是不一样的,否则我们的杰出人才早就培养出来了。浏览国内各大学的要闻,各种人才在Nature、Science等世界顶尖期刊发表论文的事迹也常被大幅宣传。若单从学术发表的角度看,杰出人才似乎是一个已得到解决的问题。但这些人才显然还并非属于钱老心目中的杰出人才的范畴,当然也不排除他们最终能成为那种真正意义的杰出人才的可能。中国一直有诺贝尔奖情结,现在我们也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和文学奖了,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足够的底气说,我们已经培养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已经得到解决了。因为纵比民国时期的大师云集、横比欧美等国经常有重大科学发现之举,我们目前的学术人员所取得的成绩依然不容乐观。尤其只是在学术产出数量上高歌猛进,但世界级的学术创新依然匮乏,大师级的人才依然稀缺。
世界级学术创新的匮乏,以及真正的杰出人才的难以出现,仅仅将之归咎于我们的学校教育的失败其实是不合理的。且不说在PISA和TALIS测试中领衔全球的上海中学生和教师,即便是在国内表现平平的中国学子到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校也常表现优异,这起码说明了我们在学校培养阶段也并不见得落后。当然,学校培养的前半程是否落后,因涉及方方面面,并非三言两语能够讲清。而且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正如BBC记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关于中西教育教学模式对比引发的探讨一样,因为涉及不同文化背景,很难说不同模式孰优孰劣。而本文旨在为回答“钱学森之问”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视角:我们难以培养出杰出人才,可能不能只在学校教育这个阶段找原因,而更多需要从学校教育之后的阶段找原因。如果把人才培养比作一场长跑的话,不但需要前半程学校教育阶段的培养,更需要作为后半程的职业生涯的继续培养和成长。也许我们的学术人员培养,在学校教育的前半程没有落后,却输在了在学术职业生涯开始后的后半程,其直接表现就是学术职业化程度偏低。
职业化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其基本指标包括:(1)以一套系统理论为基础;(2)具有为委托人认可的权威;(3)广泛的团体约束和对这些约束的认同;(4)具有一整套规范职业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关系以及与委托人之间相互关系的伦理标准;(5)具有由正式职业协会支撑的职业文化。[3]9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中国日渐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学术系统,学术人员的职业化程度也不断提升,但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职业化程度依然偏低,尤其是在约束认同、伦理标准和职业文化等指标上。学术职业化偏低突出表现为两大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没有建立起高度职业化的体系;另一方面是学术人员面对的纷扰太多。
首先,在国内除了市场化很高的行业之外,其他职业基本都没有建立起高度的职业化体系,即便是国际之间竞争性很大的学术职业和体育竞技类项目。高度职业化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比如在一个高度职业化的竞技体系里,球员只管踢球,不用去考虑薪水能否发放到位;教练只管训练和比赛战术,不用管裁判到底会不会吹黑哨;投资者只管投入和目标考核,不用去干预教练的战术布置……学术职业化也与此类似:有一个专业化的服务系统为学术人员集中精力研究提供各种保障,学术人员只管痴迷于研究兴趣做好研究就好。但目前国内很多大学的情况恰好相反,服务系统变成了管理系统,并为外行管理内行取得了合法性。于是学术研究不但没有办法高度职业化,而且还产生了很多不合理的制约:死板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使得很多学术人员整天盘算着怎么符合财务报销规范而无暇一线科研,连《人民日报》也大声高呼“别把科学家逼成会计”[4];学术人员一年到头面对各种考核填表,不知耗费多少本应用于专心学术的时间……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对着激烈的国际科研竞争,面对着欧美国家那些能够最大化地集中精力去进行学术研究的职业化程度很高的对手,我们的学术人员在时间和精力投入上显然就输了半截。
其次,国内学术人员所面临的纷扰实在太多。一方面,国内很多地方和大学的职称评审条件设置,尽管大多宣称以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为目标,却常常造成了分散学术人员精力的实际效果:如果说教学工作量和科研工作量的要求都是在情理之中,那么职称外语、计算机能力、出国留学、继续教育等各种要求,实在是令人不胜其扰,很多时间都耗在满足这些杂七杂八的评审条件上了。另一方面,如今政府对科学人才越来越重视,各种名目的头衔和奖励越来越多,在一定程度上当然起到了积极激励作用,但很多时候也是对人才做出更有创造性成果的打扰。中国人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政府部门对于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也常常是予以一官半职,至少是学官。表面上是希望人才发挥更大作用,起到领军带头作用,但是事实上对于更需要平心静气做学问的学者,常常使其大大分散精力,整天在各种行政事务中劳心劳力,研究工作甚至还不如前。尤其是我们的奖励常常和待遇对等,将科学创造世俗化。而在美国很多知名大学的学者获得诺贝尔奖,除了诺贝尔奖的奖金之外,并不会享有很多特别的待遇,最多是在校内获得一个永久停车位。相比之下,我们的惯常思维和做法是让各类“高层次人才”的头衔和待遇、资源相匹配,而且很多资源常常是非学术资源,给进一步的学术创新带来纷扰而不是保障。
二、学术职业化程度低的原因:政府权力越界令学术场域难以成形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对于大学以及学术职业的规划都是在国家行动的总体性框架设计下进行的,即“将大学本来属于认识论范畴的学术创新提升到国家行动的高度,通过大学与政治、经济的紧密联姻,构建起中国学术创新的内涵和发展蓝图”[5]。无论是作为上一个发展阶段代表的“985工程”和“211工程”,还是作为新的发展阶段代表的“双一流”建设,都是出于一种“政治论哲学”之目的,将大学发展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代表,并将学术产出作为追赶和发展的最主要行动逻辑。这种体制机制的好处是可以将国家目标、大学组织目标和学术人员个人目标三者统一起来,产生强大激励。但是,其重大缺陷也在于此,即几乎以国家和政府的发展逻辑取代了大学和学术职业自身的发展逻辑,政府权力越界的同时,使得中国大学缺乏自主办学空间,学术场域长期无法成形,并决定了学术职业化长期处于较低程度。
笔者曾经借助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对德国、法国与中国的学术场域作过比较,认为中国学术场域并未成形。[6]因为在布迪厄的场域话语体系中,学术场域是一个独立于外部的小世界,它的所有规则和运行逻辑都从内部生成,场域中最重要的权力是学术共同体内的“科学权力及声望”,是决定参与者的遴选、升等及事业发展的关键权力。学术场域应该是相对独立于权力场域的,有学术场域独有的游戏规则,并且这套游戏规则不可化约为其他不同类型的场域。学术人员可凭借自己所积累的文化资本,按照学术游戏的规则参与竞争,从而获得相应的学术发展和权力位置。因此,以布迪厄对一个场域的定义和标准来看,目前中国学术场域尚未成形,基本上还是作为权力场域的附属,并无独立的游戏规则。无论是政府还是高校,都将学术产出的多寡作为评价发展水平高低的主要指标。因此,大学教师难免沦为学术产品的生产者,成为被评估和被支配的分散个体。大学体系很大程度上只是按照国家政策和政府文件办学,缺乏真正的办学自主权。在这种前提下,不但没有成形的学术场域,甚至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是否存在也存疑。
中国学术场域的这种状况当然有历史与文化的原因,“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发展逻辑和水平,在当前,中国社会由于分化尚不充分,除政治场域(权力场域)外,其他各种场域往往未必成形”[7]。但更为关键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政治权力对于科教文卫等事业的过分嵌入,并直接导致了人才理念的“工具化”和管理机制的“科层化”。因此,中国的公立大学,长期以来是作为“事业单位”的性质而存在,而并不是作为独立的法人机构或者第三部门而存在。这先天地决定了中国大学缺乏真正的学术逻辑,更多是奉行作为“事业单位”的政治逻辑或行政逻辑来开展办学活动。因而,大学的学术人员,更多是在政治或行政权力所指引的方向下开展学术研究,尤其是各个时期的各种国家、省部级课题,基本代表了政治权力对于学术研究的方向掌控,并最大程度地囊括了学术精英们的参与。以社会科学为例,邓正来便曾经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学术自主性的缺乏,从某种角度看乃是政治场域对社会科学场域监督、支配所致,其基本中介是那些并非完全根据社会科学知识的规定性及增长逻辑而建立起来的学术制度;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在社会科学场域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在其研究中与这些并非完善的学术制度之间的“契合”所致。[8]也即政府权力的过度介入使得学术制度成为政治、经济力量影响学术领域的中介。政治力量对学术领域的控制需要一种科层化、量化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因为过于强调规范、标准化乃至量化管制,往往会成为一种对人的行为甚至于精神和思想的规训机制。它尽管有利于一致性和秩序的形成,但这种表面上的无冲突的秩序所带来的是学术人个性的湮没,最终是学术个性的彻底丧失,学术思想和创新的乏力,以及大学整个学术生态环境的恶化。[9]
此外,这种学术治理形态能长期取得成功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政府,但事实上这样的政府又是并不可能存在的。政治逻辑化约为大学内部的运行逻辑,不仅强化了外部对学校的控制,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的垄断,而且最终在微观层面上,左右了大学教师的日常学术生产。其最大的弊病在于,无法建立起一个自由而高度竞争的“活跃的思想市场”[10]260,没有这样的思想市场,自然不具备建立学术职业化体系的基础。即便宣称已经学术职业化了,其实也只是半职业化甚至伪职业化,难以名副其实。因此,在学术职业化程度如此之低的情况下与其他学术职业化程度高的国家的学术人员竞争,当然更多只能依靠规模和体量取胜,在高精尖层面很难占据上风。即便能偶尔有杰出人才冒出,也是各种机缘巧合,属于小概率事件。
三、厘清政府权力边界:杰出人才辈出需要什么样的政府
中山大学原校长黄达人认为:明晰政府和大学的权力边界,可以借鉴负面清单的概念,就是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应以“非禁即入”为原则,在大学自主权方面转变思路,从规定“大学可以做什么”到明确“大学不能做什么”。[11]但事实上,这样的负面清单恐怕很难列出来,尤其是在一些大的前提还没得到基本解决的情况下。在目前这个阶段,解决这些大前提比列出清单更重要,也更现实。笔者认为,重新厘清政府对于学术人才培养和管理的目的、职能和手段这三大问题,政府的权力边界也将会得到基本的厘清,其他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一)重新思考人才培养目的:从“工具”到“人”的转向
在经济学界,张维迎和林毅夫两位经济学家关于产业政策的学术争论持续了多年,张维迎曾重点谈及两者之间的核心分歧在于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讨论体制与战略的问题,实际是在讨论究竟政府是个人实现幸福的工具,还是个人是政府实现某种战略的工具的问题。如果个人可以成为实现政府某种战略的工具,那么实施国家战略存在合理性。反之,如果政府是实现个人幸福的工具,那么就应该保证更多的个人自由,促进市场体系建设,让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12]姑且不论孰是孰非,张维迎所指确实是我们政府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一个习以为常的问题——我们过于强调了人才对于实现政府战略的“工具”价值,却往往忽略了其作为自由发展的“人”的价值。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布鲁贝克也认为,大学在人才培养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13]13。前者趋向于以人的闲逸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后者认为人才培养是为了服务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人才培养尤其是杰出人才培养的实践中,“工具”目的或者说“政治论哲学”目的几乎占据了压倒性。从“教育救国”到“科教强国”,个人长期以来作为政府实现各个时期战略的工具。不可否认,这种目的导向的教育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个人所取得的“成果”累积成为国家与政府的科技实力支撑。但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人”的价值消失了,尽管理论界从未放弃倡导“人”的努力——如“人是教育的出发点”,“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教育的最高的鹄的”[14]等,但在实践层面,人基本都是作为工具而非目的而存在。然而,这么长时间的实践后,有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是:我们的人才作为贡献成果的“工具”,确实产出了大量的成果,但基本没有什么世界级的;而这些年世界级创新成果频出的国家,恰恰是更多尊重“人”的价值和秉持“认识论哲学”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学术人员的好奇心能够达到最大程度的呵护,也能够获得更多自由探索的信任与空间。因此,政府是否愿意自我削权的关键大前提,取决于政府是否开始反思杰出人才培养的目的——是将学术人才视为贡献各种评价指标而存在的“工具”,还是从学术研究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和个人幸福的“人”。
(二)重新定位政府人才管理职能: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
如上文所分析,国内大学的学术人员为何难以成为杰出人才,其内在原因在于学术职业化程度太低。而学术职业化程度太低的外在原因在于政府权力的越界,使得学术场域无法成形。因此淡化权力场域的影响力,使得学术场域得以成形,必须努力推动政府人才管理职能的转变。
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中,认为有一种主宰其他场域的“元场域”,即权力场域。他以同样是中央集权制的法国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相对权力场域而言,其他场域的主宰权力也只是作为“支配阶级中被支配的集团”[15]327而已。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认为,每个场域都规定了各自特有的价值观,拥有各自特有的调控原则,而且各自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这事实上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所主张的“有限政府”是类似的:政府首先应该解决自身职责定位问题,即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一方面抑制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中政府职能不断扩张的冲动,另一方面让社会领域有更多发展空间。我国原有的行政管理模式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政府是“无限政府”“统制政府”,政府职能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对社会和公民进行全方位的控制。我国的人才管理职能的定位,长期以来仍然受到这种传统模式的惯性影响,因此实践工作中广泛存在权力的“越位”和“错位”。
进入新的时期,我国政府对于人才管理显然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不再是以往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命令为主,而是加入了更多市场调控手段,以经济激励为主。这显然具有很大程度的进步,但事实上又并未使得教育和学术场域的独立得到更多的空间,“在最初,教育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被纳入政治范畴;后来,随着市场经济规则的建立与完善,教育又受到经济权力的侵袭和控制,为‘生存’而积极主动地向经济资本靠近和献媚之举日益大行其道并获得了‘合法性’。教育开始拜倒在经济的石榴裙下,大有成为一个经济范畴之势”[7]。如今在中央政府力主“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取消了很多审批权,但在竞争性资源配置上大有此消彼长之势。比如各种各类的人才工程和项目,表面上是增加了资助和奖励,但都通过程序烦琐和强度很大的成果考核来加以控制。于是稍有点“杰出”迹象的人才都会显得非常忙碌,忙于填各种表申报各种项目评各种奖,经济激励的逻辑大行其道,学术逻辑依然黯淡无光。也即在权力场域减弱但经济场域加强的情况下,还是不能保证学术场域按照自身逻辑成形。一个致力于向“有限政府”职能转变的政府,不仅应自觉限制权力场域的影响防止权力滥用,也应自觉收起过度激励的“指挥棒”,这样学术场域才能够遵循其特有的逻辑,并提升此场域中的活动的专业化程度。学术人员也自然会按照科学探究规律来投入学术研究,平心静气做学问。
(三)转变政府的学术管理手段:从“指标”到“契约”
现阶段我国政府对学术的支持投入越来越大,设立了很多“工程”和“项目”,并加以各种“指标”进行考核。但是,世界级的学术创新常常是现有的“指标”设计无法预计得到的。很多发达国家的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支持也设立了很多“项目”,但基本不太会频繁施加各种“指标”考核,而这种看似不问回报的方式常常获得超出预期的收获。比如最近称得上世界级学术创新的事件是美国科学家成功探测到引力波:2016年初,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联合发布了物理领域具有历史意义的公告,宣称人类首次直接探测到了引力波对时空的扰动,这证明了爱因斯坦在一个世纪之前的理论。这项伟大的成就始于30年前美国上马的LIGO项目,而据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介绍:LIGO项目直到3年前还几乎没有任何成果,甚至22年绩效为零,而项目前后总共已投入了将近100亿元。[16]这对于中国科研项目资助来说,根本不可想象。国内的科研资助,更多中短平快的应用型研究项目,对于基础科学研究重视不够。即使重视,也不可能达到这种提供资助却不干预的程度。但基础科学的进步所带来的创新无论对一个国家还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都是惊人的。正如引力波发现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的公开信中所说:“基础科学研究是艰苦的、严谨的和缓慢的,又是震撼性的、革命性的和催化性的。没有基础科学,最好的设想就无法得到改进,‘创新’只能是修修补补。只有基础科学进步,社会也才能进步。”[17]对于绝大部分经费来源都来自于政府的中国科研,相对而言缺乏这样的理念,又长期以“指标”考核作为管理手段,因此很难产出这样的世界级创新成果。
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杰出人才的出现,又常常是和这种世界级创新成果的诞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缔造和成就更多的伟大,政府的学术管理手段必须实现从“指标”到“契约”的转变。与自上而下的单方面的“指标”要求不一样,“契约”是基于双方互相信任基础上的约定。现代契约精神源于西方,19世纪初期的德国柏林大学可以说是教育领域的一个著名“契约”例子。当时洪堡受命组建柏林大学,他认为必须深刻反思当时德国大学训练人才就是为国家服务的培养模式,认为这样的教育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他旗帜鲜明提出应该重构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总的说来,国家绝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挂起钩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职责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18]162他进而指出国家和大学之间建立一种“契约”的共识和关系——“就总体而言,国家决不能要求大学直接地和完全地为国家服务;而应当坚信,只要大学达到了自己的最终目标,它也就实现了,而且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19]当时是19世纪初,在法德战争中德国大败,德国整个知识界为之震惊并深刻反思。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德国政府和社会接受了洪堡的理念,国家尊重科学活动的特性,尽可能不将大学的活动纳入政府的行为系统,尽可能做到不干预。德国高等教育向有国家主义传统,当时德国大学所获得的学术自由,可谓“国家庇护下的学术自由”[20]117,这种难得的“契约”的达成,也源于特定背景下民族精神与学术精神的耦合。但关键是这个“契约”带来的结果是:德国大学凭着不受外界干预的科学研究成为现代大学的典范,德国也因大量高端科研人才的培养和贡献得以复兴,重回强国之列。如今,在各国科研竞争更加激烈的今天,我国政府更需要这种“风物长宜放眼量”的长远目光,以宽容大气的“契约”管理代替斤斤计较的“指标”管理,给予大学和学术工作者充分的信任和空间,让学术人员真正获得“十年磨一剑”的制度环境,让他们在科学世界里全力探索而不是在政府的指令中忽东忽西,才可望获得更多的伟大创新,科教强国之路也将更从容稳当。
[1]卢晓东. 如何破解“钱学森之问”?——兼论创新人才培养与大学教学改革[J]. 中国高校科技,2011,(7).
[2]陶西平. 钱学森之问与基础教育改革[J]. 创新人才教育,2014,(1).
[3]Vollmer Howard M,Mills Donald L. Professionalization[M]. 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Inc.,1966.
[4]赵永新. 别把科学家逼成会计[N]. 人民日报,2015-12-27(11).
[5]徐永. 国家行动下学术创新策略的实践逻辑及其反思——基于大学学术生产的视角[J]. 教育发展研究,2012,(23).
[6]陈先哲,刘皛. 学术生涯:赌博还是游戏?[J]. 复旦教育论坛,2013,(4).
[7]刘生全. 论教育场域[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1).
[8]邓正来. 对知识分子“契合”关系的反思与批判——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再思考[J]. 天津社会科学,2004,(6).
[9]阎光才. 学院人的“癖好”与大学的制度安排[J].高等教育研究,2006,(1).
[10]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 徐尧,李哲民,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11]黄达人. 与其给予,不如放权[N]. 中国教育报,2014-04-21(9).
[12]张维迎. 改革,要从功利主义转向权利优先[N]. 经济观察报,2014-07-14(45).
[13]约翰·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郑继伟,张维平,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4]扈中平.人是教育的出发点[J].教育研究,1989,(8).
[15]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辑出版社,2004.[16]张晔. 基础研究考核猴急不得[N]. 科技日报,2016-03-08(3).
[17]News Office. Letter regarding the first direct detection of gravitational waves[EB/OL].(2016-02-11)[2017-01-01].news.mit.edu/2016/letter-regarding-first-direct-detection-gravitational-waves-0211.
[18]弗·鲍尔生. 德国教育史[M]. 滕大春,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19]威廉·冯·洪堡.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J]. 陈洪捷,译. 高等教育论坛,1987,(1).
[20]周丽华.德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罗雯瑶]
The Government’s Power Boundary and Academic Talents Cultivating
CHEN Xian-zhe
( School of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China )
Why is it difficult for academic staff in domestic universities to be“outstandingones”referred by“The Qian’s doubt”? An important cause is their limited academic professionalism, which mainly results from the“overly broad”of government power, which saps the autonomy in the academia and ignores the academic logic. In a new period of development, with the government’s clarified aims, functions and methods in cultivating and managing talents, power boundaries will be set precisely under the regulation to achieve a mature academia,galaxy of talents, where their professionalism will level up.
power boundary; academic professionalism; academia; talent
G647.1
A
2095-7068(2017)03-0031-07
2017-03-15
10.19563/j.cnki.sdjk.2017.03.005
陈先哲(1980— ),男,广东茂名人,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学术制度与学术职业研究。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5年度一般项目“新常态下中国高等教育转型与秩序建构研究”(项目编号:GD15CJY01)、2015年“广东省培养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文化英才项目(项目编号:201529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