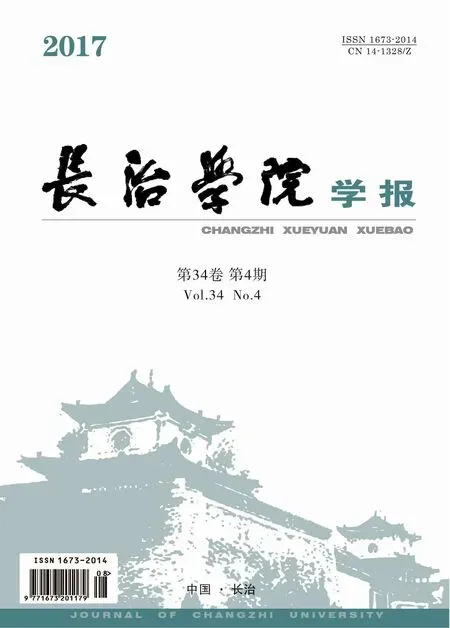福泽谕吉文明论哲学的理论缺陷及现实影响
李 聪,赵本义
(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福泽谕吉文明论哲学的理论缺陷及现实影响
李 聪,赵本义
(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哲学在日本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日本社会看到的多是其积极的启蒙意义,而其诸多理论缺陷却被人为隐藏。对后世的日本社会和国民的历史观造成了极大的误导作用,并导致了日本战后受害者意识普遍的现象,消极影响十分恶劣。因此,全面认识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哲学就显得极为重要。
文明论;受害者意识;战争;国权;民权
一、引言
福泽谕吉是对日本具有重大影响的“启蒙式人物”的代表。在近代日本历史上,他似乎始终扮演着动荡时局中清醒的“正义使者”,时至今日,还依然“闪耀”在日本一万日元纸币之上。其文明论哲学经过后人的完美化“包装”,成为改变近代日本精神风貌的一剂良药。但是,日本如何一步步走向发动侵略战争的深渊,又为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化身为“受害者”去面对历史,个中原因虽纷繁复杂,但骨子里对战争行为的合理化辩解让我们不得不追溯到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哲学。
二、福泽文明论哲学的背景
福泽谕吉的文明论哲学植根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巨变,尤其是与日本一衣带水的我国的遭遇。被动挨打的中国一度让福泽唏嘘不已,起初言语中也多是对中国的同情和对西方列强卑劣行径的愤怒。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沉睡的”亚洲各国逐渐被扯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深渊。地处东亚一隅的岛国日本自然难逃厄运。13年后,“黑船来航”打开了坚锁的日本国门,在幕府统治渐露颓势的内忧外患之下,经历倒幕运动、明治维新等一系列社会运动和改革,不得不奋起直追的日本积极应对着来自世界的变化。相较之下,邻国中国似乎还沉浸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思想和行动上都显得过于迟钝。停滞不前甚至一步步退缩的中国和忍痛前进的日本,这两者对于时局剧烈变化的应对确实迥异。由此,潜藏在日本人心中,企图扭转从古至今中日力量对比不平衡局面的念头借着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之时的混乱聚集、生发并最终付诸行动。福泽的中国观也相应地经历了同情、观望、批判、厌恶等多个阶段。如果说鸦片战争之初的福泽还对中国的遭遇抱有一定的恻隐之心,那么此时的福泽已然变成了曾使其痛恨、畏惧的列强的模仿犯。
三、福泽谕吉文明论哲学的双重标准
在《文明论概略》中他既说“拿起武器杀害界外兄弟,掠夺界外土地,争夺商业利益等等,这决不能说符合宗教的精神。看到这些罪恶,姑且不论死后的裁判如何,就以今生的裁判也是不完善的,这种人应该说是耶稣的罪人。”[1]174之后又说道“杀人和争利虽然为宗教所反对,难免要被认为是教敌,但是,在目前的文明的情况下,也是势非得已……战争是伸张独立国家的权利的手段。”[1]175他一方面倡导要“顺应人民的天性,消除弊害,使全体人民的智德自然发展,使其见解自然达到高尚的地步……人心有了变化,政令法律也有了改革,文明的基础才能建立起来。”[1]14在此,他主张教化民众、伸张民权。另一方面又认为民众智德之进步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国家独立,文明仅仅是国家独立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从而要推进国权,甚至不惜牺牲民权。如此这般前后矛盾的论说不胜枚举,实际上显示了其观点的混乱和伪善。日本著名学者安川寿之辅对此批评到,“福泽所提出的命题和演说,是根据倒退的历史现实主义,即根据现实追随主义和渐进主义,不断追从和追随现实,像变色龙似地变色和变节,由此确立了不修边幅、毫无节操的思想。”[2]306福泽赤裸裸的战争逻辑完全是将文明作为推行侵略战争的借口,在历史风云变幻之际,化身为所谓的启蒙思想家,用文明论哲学为日本对外扩张的军事行为护航甚至可以说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同谋。
四、对“文明”本质的偏颇理解
(一)将文明片面理解为西方工业文明
福泽谕吉所指称的“文明”仅仅是盛极一时的西方工业文明。他断言“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1]11为了接近这样的文明发展水平,日本最终仿效西方列强实施侵略扩张。但是“文明”最早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法语词“c ivilisé”,意为“有教养的”。因此,“文明”从产生之初就被打上了脱离蒙昧的印记,是人类发展到较高程度时才可使用的词汇。它与人类不断求索,积极进取息息相关。从茹毛饮血、衣不蔽体的远古时代发展到当代社会,可以说人类经历了一部超越野蛮,追求文明的进步史。文明并非西方世界工业文明下的极度物化,不是积累的财富越多就越文明,也不是科技越进步就越文明,更不是福泽认为的越接近强者就越文明。不仅如此,凡是追求诸如此类片面的文明反而更易被其掌控乃至异化,成为人类背上的沉重枷锁。实际上,文明应该是一种状态,一种向上奋进的延续,所有这一过程下积累的超越自身过去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等都可以成为文明的表现。只有这样才符合“文明”一词的起源和其蕴含的最初意义。
(二)将战争作为实现文明的一种手段
福泽宣称“没有比对外战争更能激发全国人民之心令国民全体感动的了,……因此当今面对西洋各国,能够激发我国人民报国心的方法,没有比战争更好的了。”[3]133他认为“杀人和争利虽然为宗教所反对,难免要被认为是教敌,但是,在目前的文明情况下,也是势非得已……战争是伸张独立国家权利的手段。”[1]175由此,福泽将战争与获取文明之间,文明与西方强势文明之间完全划上了等号。福泽将侵略战争理解为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赋予侵略战争以实现文明的意义。但是,文明既然是一种动态的过程,那自然并非一种终极目标,更不应该如福泽所言,竟可以通过侵略战争这种本身反文明的极端手段去获取。相反,侵略战争只会摧残人类世世代代来之不易的文明成果,伤害不断创造文明奇迹的人类社会。
(三)将文明与野蛮完全对立
当日本开始用西方列强强加于自身的手段瞄准周边国家之时,福泽便积极发声表示支持,福泽认为“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那么,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1]168在他看来,被动挨打的弱者就是野蛮,主动进攻的强者就是文明。此时的福泽认为被侵略国家的人民都是丑陋和冥顽不灵的,只有用武器去改造他们,才能使他们进步。类似这样的帝国主义逻辑为日本不久之后发动的侵略战争可以说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福泽个人立场的转换映射出日本既善于应变又容易走向极端化的特征,也反映出福泽试图转嫁战争责任的企图,其所谓的文明论哲学使得日本对亚洲的介入言之凿凿。文明从来都不该是唯一的、精准的。以文明和野蛮,进步和落后的“二分法”相区别,这样只会陷入非此即彼,企图用唯一的文明取代异质文明的错误深渊。当代的文明是在新时代背景下要求的文明,它意味着我们要顾及属己文明以外的异质文明,并接纳不同的文明,共同促进文明的多样发展。
(四)视文明为国家独立的手段而非目的
福泽着重说到了国体与文明的关系,宣称“日本人当前的唯一任务就是保卫国体,保卫国体就是不丧失国家的政权。”[1]124他认为“国体并不因文明而受到损害,实际上正是依赖文明而愈益提高。”[1]27并最终得出结论“国家的独立是目的。现阶段我们的文明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1]192在福泽看来,文明从来都不是其本身的目的,而只能是国家独立的手段。由此,文明就被弱化为一种工具。“只是把有助于本国独立的东西,姑且定名为文明。……国家独立也就是文明,没有文明就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1]192这种观点比起审时度势,见风使舵的性质更为明显。到后来发展为鼓励侵略扩张、恃强凌弱的“脱亚入欧”等军国主义思想,之后更以维护“国权”抗衡欧美为名肆意妄为,为日本的战争行为推波助澜,将无数无辜的亚洲人民卷入战争的深渊。
另外,福泽还肯定了保留皇室的积极作用。在它看来“政府的体制只要对国家的文明有利,君主也好,共和也好,不应拘泥名义如何,而应求其实际。……君主政治决定改与不改的标准,只在于它对文明是否有利而已。”[1]32福泽大胆阐述了天皇制的实际作用,“君国并立……维持了我国的政权和促进了我国的文明。”[1]29他认为要学会“去其虚饰迷惑而存其实际效用。”[1]29然而天皇制国家在整个昭和时期不断发酵,愈演愈烈,以致战后天皇逃脱了战争责任的惩罚。作为这场侵略战争背后的核心领导者和精神支柱,天皇的责任本难以推卸。“假使一个以其名义处理日本帝国外交和军政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人,都不为发动和领导这场战争负起应有责任的话,那么,还怎么能指望普通老百姓费心思量这些事情,或者严肃地思考他们自己的个人责任呢?。”[4]9天皇在侵略战争中不仅应该负一定责任而且应该负主要的责任。对天皇的免责,是日本战争责任意识淡薄的重要来源。福泽谕吉从倡导民权到疾呼国权、默许皇室。他这种急功近利式的立场转化既是对文明认识的偏差也是对战争行为的纵容。
五、福泽谕吉文明论哲学在当代面临的问题
站在国家命运的十字路口,日本再次选择了追随强者,甚至成为一个不惜一切“求取文明”的盲从者。福泽行事也无不以西方文明为标准,企图从方方面面全盘吸取西方文明。然而日本社会在近代却逐渐感受到了身份认同的迷惘。“当历史发展到‘泛西方化’时代终结期的20世纪末叶时,非西方世界的人们在经历了全盘西化的迷狂之后,终于发现西方化的道路并不能解决自己国家和地区的根本问题,尤其是不能解决自己文化的精神根基问题。”[5]2此时,福泽谕吉文明论哲学的缺陷便暴露无遗。究其原因,这个在民族根基和西方强势文化之间摇摆、平衡的日本,也会不可避免地遭到这种犹豫的反扑。汤因比在谈到“泛西方化”过程中给非西方世界的人们带来的精神苦恼时说道“事实上,他们忍痛放弃祖辈的生活方式而采取外来的西方的生活方式,这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然而他们却由此不无宽慰地虔信,以如此代价换回的其实只是由于陷入了迫近的西方精神危机所受到的惩罚。”[5]294当文明的冲突越来越表现为精神根底与文化差异的不同。作为弱势一方的东方文明,在近现代面临的不仅是外在的挑战,而更多是自身的定位和归属感的危机。但是绝非一味学习强势文明就能解决自身遇到的一切问题。戴季陶曾说道“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文明的同化性,不能吸收世界的文明,一定不能进步,不能在文化生活上面立足。但是如果没有一种自己保存,自己发展的能力,只能被人同化而不能同化人,也是不能立足的。”[6]17所以福泽设想的全面学习西方文明就能使日本脱离困境的想法不可避免会落空,并且会在之后的发展道路上陷入迷惘和错乱。不论是福泽谕吉还是日本社会,对于本国身份认知的错误所导致的暧昧、纠缠的局面是日本在短时间内快速学习西方文明所付出的相应代价。
六、余论
福泽谕吉文明论哲学的启蒙意义越过历史的长河,在日本民众的心中根深蒂固。由于日本在战后一直企图摆脱所谓的“自虐史观”,甚至不惜扭曲历史,美化侵略行为。福泽的文明论哲学对战争的理论支撑作用在此之下逐渐被人为掩埋。呈现在日本国民和社会面前的只是作为“启蒙思想家”伟大的一面。这般人为的美化蒙蔽了国民的双眼,是日本国家和社会的悲哀。但是时间会证明,一个美化战争的思想家将无法永远保持启蒙家的光明形象,一个不能正视历史的民族终究也是无法前进的。
[1]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安川寿之辅.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解构“丸山谕吉”神话[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
[3]福泽谕吉.通俗民权论.通俗国权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
[4]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M].上海:三联书店,2008.
[5]赵林.告别洪荒——人类文明的演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6]戴季陶.日本论[M].长沙:岳麓书社,2013.
(责任编辑 杨晓娟)
B313
A
1673-2014(2017)04-0001-03
古希腊政治哲学与中国先秦政治哲学的比较研究(12C031)
2017—04—13
李 聪(1993— ),女,陕西西安人,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研究。赵本义(1958— ),男,陕西安康人,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