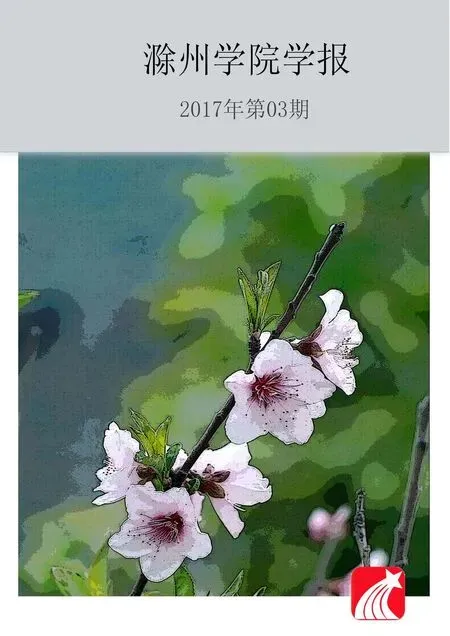近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民族与国家因素
许诺晨
近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民族与国家因素
许诺晨
中国儿童文学诞生在民族危机深重的近代,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国家和民族的宏大命题渗透到原本单纯的文学中,对中国近代儿童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从时代背景、从梁启超到左联、从鲁迅和周作人等关键人物群体,认识民族与国家因素在儿童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
儿童文学;梁启超;左联;鲁迅;周作人
一、时代背景——民族危机下的救亡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面对澎湃逼人的欧风美雨,中华民族处于强大的外部压力之下,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处于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之中,在屈辱中觉醒求索,以求民族的崛起和强大,变法革新,救亡图存以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宰割,民族与国家成为了近代国人建构新国与新民的重要命题[1]。
时代潮流指向了构建民族国家以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路径,而构建新国必须要有新民,文学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启蒙和建构新国民的作用,中国现代文学在内容和创作主题上深受民族与国家因素的影响,作家从不同的角度在文学中参与这一伟大进程。民族和国家的叙事感染着作家,作家也纷纷投身到这一历史洪流之中,围绕着民族与国家这一话题形成了汗牛充栋的文学和经久不衰的创作浪潮,整个近现代文学史洋溢着澎湃的民族国家的想象[2]。
中国的近现代儿童文学,在西风东渐的翻译潮流中诞生,西方儿童文学的大量输入刺激着本土的有心者们,儿童文学意识在晚清出现萌芽[3]。
自梁启超开始,中国知识界就将文学视为宣扬新思想,启迪民智,塑造新国民的一种手段,这不仅和古代中国“文以载道”的传统相因袭,也和西方启蒙主义的影响息息相关。他们对现实的积贫积弱深感痛惜的同时,依然对中华命运抱有坚定信心,把无限的希望寄托在未来的成人——中国少年身上。在这里,儿童——成人——国家未来成为了密不可分的整体,儿童文学被赋予教化儿童成为新民的重大希望,自诞生伊始就被裹挟到严肃而沉重的现实中,承担着教化启迪新民建设新国的重任,彼时的儿童文学题材也多与社会政治,国家历史息息相关,表达的情感也多为慷慨激昂的爱国情感。
二、儿童文学中的现实话题——从梁启超到左联
梁启超作为引入西方思想的急先锋,最早提出了中国少年的说法。1896年梁启超发表《论幼学》,他痛惜中国教育落后,旧式教育只能培养颟顸的守旧士人,而建立新国必须培养新民,培养新民必须要有新的教育,从此中国儿童文学都在努力建构能成为新国民的中国少年形象。1900年,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作《少年中国说》,直接将未来国家命运与少年素质构连,“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4]从此,少年中国和中国少年的想象日益成为一种迅速流通的符号,在中国的知识界广为传播,而其内涵也在层累之下不断扩大。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观一经问世,就得到了知识界和革命群体的积极回应,“少年”一词在清末社会迅速风靡起来,彼时满腔热血,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竞相以中国少年自居。一时之间,少年意气直干云霄,革命浪潮日盛一日。流亡日本的湖南青年杨度做《湖南少年歌》,其中直言“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1902年之“少年中国之革命军”,1910汪精卫发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佳句,少年走向符号化,象征着革命,进步和未来,而真实的少年群体也按照这一想象被建构起来。
梁启超之后的中国知识界依然将民族救亡作为持续的主题,进入30年代,民族危机日甚一日,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的缓慢发展,城市出现了大量无产阶级工人甚至童工,乡村也日益凋敝,人民生活也日益困苦,左翼作家大量出现,在民族话题之外,苦难的社会现实又成为儿童文学构建的新维度。[5]
叶圣陶是20世纪我国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开创者,是童话由模仿向原创过度的火炬手,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叶圣陶的短篇童话集《稻草人》,作为中国第一部原创童话作品。在这一童话集的同名童话《稻草人》里,作者以稻草人的视角,描述了当时中国农民家庭的悲惨生活。稻草人看到了蝗虫吞噬了老农妇的辛勤的劳动成果,看到渔民的孩子在船上又冻又饿,看到走投无路的妇女投河自尽,目睹了这一切不幸的稻草人却无力拯救,他虽有人的意识和观察,却没有人的行为和语言,他只能默默地看待苦难摧毁一个个卑微而又挣扎的人们,看到命运碾过人间而毫无作为。如果他没有感官和意识,他就不会看到听到,也不会难过痛心,但在童话中作者赋予了他这一切又残忍地让他无能为力,最后在内心的焦灼之中,稻草人倒下了,不甘,无奈又痛苦地倒在这经历了太多苦难的土地上。虽然是童话,但写尽了现实,文中的稻草人正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象征,他们有关怀社会的良心和责任感,却又不知所措无力改变,因此遭到巨大的精神焦虑和良心谴责。
在这风雨如晦之时,一批思想左倾的作家如鲁迅,丁玲,茅盾等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左联作家的作品集中表达对黑暗社会的憎恶和对光明正义的追求,对挣扎求生的弱者的悲悯情怀和对不平等社会现象的无情鞭挞。同时,左翼文学又涂抹着浓厚政治色彩,他们的话语总是不离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等名词,呼吁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远景。随着他们大量进入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中也随之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儿童的形象,他们是童工或者仆人,处于社会底层,忍受着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层层盘剥,但同时又不甘堕落,本能的具有反抗精神,具有高度的阶级自觉。在儿童文学中,他们成为左翼作家讴歌的对象,寄托着社会革命和民族救亡的双重希望。
左联刊物《大众文艺》设立《少年大众》专栏,是左联儿童文学的集中地,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其中以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最为引人注目,该作将儿童的幻想世界与苦难深重的现实世界糅合在一起,用童话叙述现实,用现实塑造童话,阶级斗争成为贯彻小说始终的线索,虽是童话却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童话中,同胞兄弟大林和小林因为不同的人生选择,通往了不同的阶级,最终分道扬镳,大林成为富翁的儿子,享受剥削来的荣华富贵而最后流落到孤岛饿死;弟弟小林却被卖进公司当雇工,不堪忍受压迫盘剥奋起反抗,最终成长为成熟的无产阶级,和工人一起反抗资产阶级统治。大林和小林已无一般儿童的纯真天性,更无同胞骨肉之亲,只有赤裸裸的阶级分野和阶级情感。他们成了左联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下的两个符号化的人物,与其说是儿童,不如说是天然对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郭沫若是同期左联中鼎鼎大名的人物,他的童话《一只手》有着更为直接的现实寓意和更为浓厚的政治色彩。《一只手》发表在1928年,正是大革命破灭后的低潮时期,讲述了发生在一个乌托邦——尼尔更达,无产阶级发动革命,成功夺取政权的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小普罗是尼尔更达岛上一个深受剥削的童工,在生产事故中失去了右手。而工厂的资本家却要冷酷无情地抛弃可怜的童工,把他赶出工厂,自生自灭。这样的冷酷无情激起了广大工人的义愤。工人们在英明的领袖克培的带领下发动了暴动,推翻了资本家在尼尔更达的罪恶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府。童话的主人公小普罗以无畏的勇气冲锋在前,用残缺的右手充当武器和阶级敌人搏斗,最终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用童话的方式叙述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全过程,讴歌无产阶级的斗争精神,正是当时作者政治倾向和幻想的清晰投射。童话的标题下有着“献给新时代的小朋友们”的寄语,这确乎是献给未来的无产阶级的儿童文学。而充斥在文中的革命口号,如“反抗一切的资本家”,“杀尽工人的压迫者”等激情呼喊和关于革命道理的通篇陈说,更让我们相信作者写作的对象并不是儿童,不过是假托童话这一不那么敏感醒目的文学形式传递自己的革命激情,避免政治上的危险。
正如外国学者所言,中国儿童文学诞生伊始就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来重塑中国,中国的儿童文学成为成人意识的投影,不是从儿童出发的单纯文学,而是现实政治建构和国民教化的工具。近代以来,儿童文学成为民族国家宏大叙事下的一条支线,这一变迁,意义深远。
三、两种维度——周氏兄弟的儿童文学观
鲁迅和周作人都是鹊起近代文学中的巨匠,周氏兄弟同时也对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有着巨大的贡献和影响,但他们却有着两种大相径庭的儿童文学观。
鲁迅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开拓者之一,1903年开始,鲁迅就翻译了诸多外国科幻小说,后又翻译了《桃色的石》《小彼得》等童话小说。在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中,鲁迅痛斥吃人的旧社会,但对未来还未完全绝望,发出“救救孩子”的疾呼。鲁迅毫无疑问继承了自梁启超起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将儿童看成改变中国命运的最后希望。在《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发表了《孔乙己》《故乡》等描述儿童生活的小说,创造了诸多生动的儿童形象。
鲁迅小说中的成人形象如孔乙己,阿Q,祥林嫂等往往都是惨淡的灰色的身影,集中了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批判,同时在儿童身上,鲁迅又寄托了无限的温情与慈爱,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顺其自然,不打击,不拂他的喜爱”[6],在鲁迅塑造的闰土,双喜,阿发等儿童形象上,可以发现他对儿童天性的爱怜。
1930年代鲁迅翻译了小说《表》,这一苏联现实主义儿童小说的引入,极大的影响着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方向,其体现的关注底层弱势群体的文学精神和日益鼓荡的左翼文学高潮不谋而合,并且共同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转向现实社会问题。鲁迅继承了上一时期在民族和国家框架下进行儿童文学叙述的传统,同时引入了苏联儿童文学,苏联文学模式的引入对中国儿童文学影响深远。
相比鲁迅的沉重严肃,关注宏大命题,周作人关于儿童文学的的三篇重要的著作《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儿童的文学》则主张在自然天性和普世精神的维度上安放儿童文学,关注儿童本体的精神的需要。
周作人是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理论大师,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创立贡献颇多。和他的兄长一样,周作人也从进化论的角度肯定作为后代的儿童要胜过前人,并以此论证了父母子女的之间爱护的天然性以及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批判了中国传统为父母之命从事的愚孝观念。
周作人认为儿童生活固然是未来的成人,但在童年阶段更应当有儿童这一本体的独立存在,而非仅仅作为大人想象的附庸。因此周作人强调儿童文学首先应该满足作为自然人的儿童的需要,然后才考虑其社会影响和教化效果——塑造新国民,灌输国耻教育等[7]。在儿童想象力发展的童年,成人没有权力以“什么神呀上帝呀国家呀”的宏大主题和神圣话语去剥夺儿童自然发展及天真烂漫进行幻想的权利,这一天性发展的权利和衣食住行的物质需求一样不可或缺,周作人反对社会上风行的对儿童的过度期待和在儿童文学中引入国家民族社会等沉重话题,认为这些过早的意识形态宣传是在损害儿童天性和浪费儿童时间。
他翻译的作品如托尔斯泰的《空大鼓》、日本江马修的《小小的一个人》等,现实色彩都较为淡薄,更贴近儿童幻想和纯真情感。
周氏兄弟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认识根本分歧在于两者的立足点不同,鲁迅偏向儿童文学外在的宏大命题,周作人始终立足于儿童内在的自然天性。
纵观近代儿童文学,在沉重的现实危机下,儿童实际已经沦为成人的建构对象,儿童文学受到了成人意志的强烈干扰,越发浓厚的现实意味己经成为童心“不能承受之重”。[8]儿童的地位也诚然不脱国家民族的大语境,然而儿童文学应当首先满足儿童自身的需求,满足儿童的天性和人格的健全发展,儿童当先以为儿童,再为小大人。周氏兄弟分别从现实和人性两个维度进行了儿童文学的的建构[9],在摆脱了民族危机的今天再重新回首近代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历程,仔细考察周氏兄弟不同的儿童文学观,无疑可以获得重要的启示。
[1] 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J].文学评论,2003(l).
[2] 张建青.晚清儿童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之诞生——译介学视野下的晚清儿童文学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8.
[3] 王芙丽.从五四到文革儿童文学中的民族想象[D].济南:山东大学,2010.
[4] 梁启超.近代文学名家诗文选刊梁启超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39.
[5] 李利芳.中国发生期儿童文学理论本土化进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01.
[6] 许广平.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11.
[7] 周作人.阿朋思漫游奇境记[M].//周作人人文类编:上下身.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123.
[8] 刘恋.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构三十年——以十三部讲义为对象的研究[D]. 扬州:扬州大学,2014.
[9] 朱晓进,李玮.语言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形式发展的深度影响[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5.
责任编辑:李应青
I206.6
A
1673-1794(2017)03-0057-03
许诺晨,安徽省文学艺术院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生,研究方向:儿童文学(合肥 230001)。
2017-03-11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