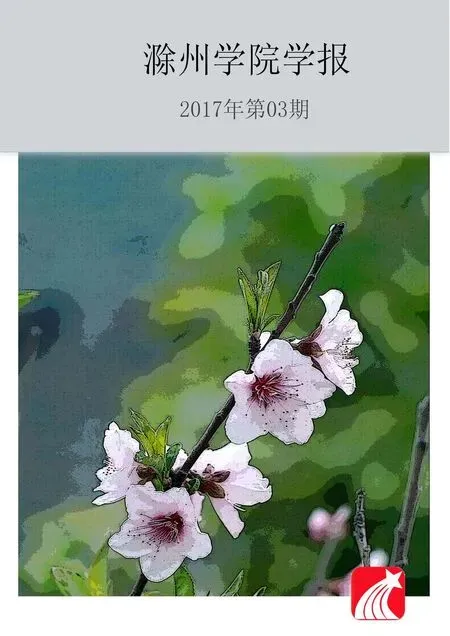清代诗人周懋泰诗歌中的太平天国运动
——以避“寇”诗为中心
余经晓,吴怀东
清代诗人周懋泰诗歌中的太平天国运动
——以避“寇”诗为中心
余经晓,吴怀东
周懋泰,晚清安徽绩溪人士,不但见证了清军与太平军作战,而且将自身“避寇”经历写入诗集《松石斋诗草》与《松石斋诗续》当中。其诗歌真实记录了农民起义在徽州地区的经过,面对战争带来的山河破碎以及家破人亡等残酷现状,诗人写下大量渴望和平,充满仕与隐矛盾的诗歌。对其诗歌进行研究,可一探战争背景下徽州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以及文人心理。
周懋泰;避“寇”诗;太平天国运动;《松石斋诗草》
中国古代社会动荡,战乱频仍。诸侯争斗、藩镇割据以及农民起义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此起彼伏。战争是残酷无情的,一首首描绘战争的诗词,仁人志士写于笔下,感叹于心。晚清江南人士周懋泰,不但见证了清军与太平军作战,而且以切身感受记录了避“寇”期间的所思所感。周懋泰的避“寇”诗在某种程度上说可作为当时历史的补述。对周懋泰避“寇”诗进行研究,把握宏观历史叙述之外战争受难者的亲身经历,揭示太平天国运动给晚清江南人民带来的真实影响。
一、周懋泰及其著述
周懋泰,字阶平,晚号松石老人[1],安徽绩溪县人。生于1827年,卒于1912年,享年86岁。其人生经历丰富:早年经商,壮年弃商从政,先后任屯溪茶局、两淮盐署幕友和北征粮台(1869年改为金陵军需总局)书记,是晚清亦商亦官亦儒的一位较有影响的人物。他不仅著有《松石斋诗草》《松石斋诗续》两本诗集,还著有《松石斋印谱》,在书法、篆刻上面有很深的造诣,在现今《中华书法篆刻大辞典》《中国篆刻大辞典》以及《中国书画艺术辞典·篆刻卷》中也可见他的踪迹。
《松石斋诗草》于清光绪丙申年(1896)排印于梁安,存古今体诗三卷,其中卷一82首,卷二72首,卷三57首,共211首。《松石斋诗续》为自丙申至癸卯得诗,续为三卷,其中卷上51首,卷中62首,卷下80首,共存诗193首。纵观周懋泰404首诗歌,他的诗歌创作从庚申(1860)二月一日写起(时年33岁),一直持续到光绪甲辰年(1904)结束(时年78岁),可见,他的大部分人生都在从事诗歌创作,诗歌内容恰好反映了他一生的出处行藏。他的诗歌内容丰富,不仅包括题画、题壁诗,还有以酬唱、赠答、送别为主的交往诗,感情真挚的伤悼诗,以及其他一些写景抒情诗。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以避“寇”为中心的诗歌恰好描绘了太平军与清军之间的战争,具有相当高的史学价值。
二、诗歌中的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期间,太平军与清军对安徽地区特别是长江两岸地区进行的激烈争夺,给安徽人民生活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周懋泰反映太平天国运动的诗歌多写于其诗歌创作早期,主要集中在《松石斋诗草》前两卷当中。笔者统计,周懋泰直接描写“太平天国运动”或以其为背景的诗歌有110首,约占诗歌总量的1/4,这些诗歌从不同方面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细致的描写或反映,可谓一幅巨大的战争场景画卷,是清代诗歌中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一)直接描写战争时局
周懋泰诗歌中多有直接描写太平天国战争时局的作品,这些诗歌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特点,其多用叙事性手法记录事件发生的经过。如:
收入《贼情汇纂》的《重有感》便直接反映了1860年8月19日太平军从宁国县过来和清军在新安作战占领新安的经过。其诗云:
时维庚申秋,八月日十九。贼从宁国来,直犯从山右。窥伺虽有心,未敢轻攻掊。山势况嵯峨,新安称要口。有明中节公,(谓金正希先生)守此日已久。何来某将军,父书犹在手。地里未深谙,意气欲衡斗。大呼关门开,与贼决胜负。岂知兵未交,尽弃戈矛走。从此失泥丸,偏地皆群丑。因怀古英豪,今人非共偶。
官军退新安,孤城自危急。烽火射山头,杀气蔽原隰。可怜城中人,董逃赋莫及。贼势乘虚来,据城仅六日。如鹊得深巢,如蚁赴荒垤。掳掠尽家有,不复遣余粒。逢人便搜囊,勒索金银亟。或以刀背敲,或以长绳縶。嗟哉何辜惊魂时,战栗杀戮固可悲。焚掠亦可泣,乱后返乡园,蹂躏不堪述。[2](4-5)
民国二十五年李丙麢的《宁国县志》“武僃志”中“兵事”条记载太平军攻打宣城宁国县的真实记录:
“咸丰十年二月初一日,粤匪伪王李世贤由宣城□溪岭入宁国县城,焚掠四出,初三日竄入广德沿途纵火五日始熄。”[3]
又据1997年宁国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宁国县志》中“近代战事”载:
“咸丰十年二月初一日,侍王李世贤、襄王刘官芳经宣城薜溪岭攻克宁国。六月十八日,太平军经胡乐出师丛山关,击退清守军皖南道李元度部。八月太平军与清军战于吴岭(今虹龙),击毙知县李鸿”[4]
再据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平军在安徽的军事斗争》一书中“太平军在安徽地区的重要军事活动年表”记载:
1860年9月26日,辅王杨辅清、侍王李世贤及赖文鸿等军攻克宁国府,击毙清提督周天受、皖南道福咸、宁国知府颜培文等;/10月6日,侍王李世贤军可绩溪;/10月9日,侍王李世贤等军可徽州府;/10月12日,侍王李世贤等军可休宁[5]……
可见,太平军在1860年10月左右的时间内攻克安徽徽州地区的详细记载。周懋泰的这首《重有感》则真实记录了太平军攻宁国县后进而进犯新安的事件经过。“敌军”从宁国来袭,因清军将领指挥不当不战而败,新安拱手让给太平军,进而成为一座孤城。接着诗人描写了太平军在新安境内的暴行:据城六天,太平军们掳尽家财、不遗余粒,逢人就搜刮;诗人用了两个形象性的比喻:“如鹊得深巢”“如蚁赴荒垤”,反映太平军的贪婪残暴;诗人在诗歌中称谓太平军为“贼”“群丑”,可见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
又其《闻官军克复金陵书此志喜》一诗,与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诗云:
一角红旗白下传,万家重睹旧山川。霜戈净洗连朝雨,露布飞题六月天。十载流民归故园,二难功业冠群贤。(谓湘乡相国)朝廷南顾忧方解,更祝兵余大有年。[2]7
诗人自注该诗歌写于“甲子六月十六日”,即清同治三年(1864),诗人听闻清军攻破金陵的事件后而作。据陈作霖《金陵通纪——国朝金陵通纪》“卷四”记载:
“五月,伪天王洪秀全以事急忧惧仰乐死,潜瘗于伪宫中。其子福自称幼主……贼犹保伪天王府,夜半纵火自焚,伪幼主洪因突围走,黄润昌等露立龙山,袁大升等循城南遇逃贼,要击斩数百人,张定魁等追及之湖熟,俘诸略尽,余党挟洪福走广德以去,国荃令闭城救火,获伪王玉玺二金印一萧孚,泗搜获伪王兄洪任达,伪忠王李秀成,几杀贼酉三千余毙,贼十万余,捷闻……”[6]
1864年,曾国藩的湘军攻破南京,远离家乡的诗人闻此消息不禁大喜,抑制不住内心激扬的情感,于是“露布飞题”,感叹持续了十几年的战争终于结束,“兵戈净洗”后,世事归于和平,流浪的人民终于可以“重睹山川”,一直漂泊异乡躲避战乱的诗人终于可以回到他心灵的栖息地。此外,诗人在诗中对破敌的湘军极尽赞美,称赞他们“功业冠群贤”,并对朝廷平叛这场农民起义表示衷心祝贺。由此可见,周懋泰始终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者权威的立场来看待这场农民起义,对太平军的看法未免过于偏激。
除记录战局外,周懋泰诗歌对“太平天国运动”战后惨景的描写更为深入具体,他不仅描写战乱后社会的荒废不堪,而且抒写战争杀戮,妻离子散以及家国之思。
(二)重现战后社会惨景
周懋泰的诗歌多处反映了太平天国运动给社会带来的破坏以及给百姓带来的伤害。其《书事四首》诗云:
几年力竭为筹防,变起须臾势莫当。人尽眼花惊猛虎,厨留角黍饱贪狼。(绩俗以二月二日食粽)连山斥堠空烽火,百里村墟冷夕阳。暂入深林姑避迹,何时重扫旧书堂。
惆怅荒城一弹丸,重遭蹂躏倍凋残。名山古佛皆剜眼,初地头陀亦剖肝。妄想玉鱼搜旧冢,漫思金椀裂新棺。胁从更有诸年少,罗网由来解脱难。
苦雨晓晓碧血流,归途触目总成愁。红颜矢志能完璧,白发龙终概断头。官吏有心斋怨鬼,人家何处认骷髅。绿杨垂地黄鹂啭,添得伤春恨未休。
愁听空山泣杜鹃,关河金鼓尚喧阗。燹余南市成焦土,乱后东邻断暮烟。满架图书皆委地,一庭花月隔遥天。儒生此日无他翼,早罢兵戈大有年。[2]1
这首诗一题四首,内涵丰富。诗人首先描写了战后村落荒废的凄惨景象,用“焦土”“断墓烟”“村墟”反映了战后人民生活无以为继,一片狼藉的悲惨景象。其次,诗人还描写了战争给文物古籍带来的破坏:“古佛”“头陀”“墓冢”向来是让人产生敬畏的事物,但是战争过后,古佛剜眼、头陀剖肝,甚至连人的墓冢棺材都被挖开,只是为了探寻里面有无财宝;“满架图书委地”可看出战乱对古籍的破坏。此外,诗人还描写了战争对普通人民无情的杀戮:“官吏有心斋怨鬼,人家何处认骷髅”——诗人用反衬手法描写内心的悲凉,“人家何处认骷髅”不正表达了对战争的控斥与无奈么!这首七言组诗深刻的揭示出这场本身反封建的农民起义在斗争过程中带给百姓的灾难。
(三)抒写“家破人亡”
安徽江南地区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对太平天国建立革命政权具有重大意义,因而,太平军在安徽的军事斗争持续了十多年之久。战争意味着杀戮、破坏,而百姓面对这一状况只能迁徙、流离躲避。周懋泰诗歌真实的反映了“太平天国运动”给百姓带来亲友分离和背井离乡的痛苦。他从个人角度抒写颠沛流离的诗歌让我们感受到此次农民起义给普通家庭带来的巨大创伤。自1860年战争伊始,周懋泰就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连年战火使周懋泰与朋友多分离,他用诗歌抒发着自己对朋友思念,如其组诗《效五君咏寄怀诸友》中的“一题五首”,作者运用组诗的形式表达对程匊香、胡润生、周懋原、汪澹斋以及养田叔的思念。
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的悲剧,太平军与清军争夺江南地区的斗争致使多少无辜的百姓丧命,家破人亡。从其“伤悼诗”我们可以看到这场战争对生命的践踏。“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周懋泰的亲人朋友也有因战乱逝世的。如其《挽胡子书》诗中“再过高士宅,谁与细论文”化用杜甫《春日忆李白》中“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一句,表达了对逝世朋友的思念,情深意重。又其《闻许瑞园舅兄殁于兰溪诗以代哭》表达了对舅兄的怀念与对往日的追忆。此外,养田叔于辛酉(1861)4月10日在躲避战争途中为寻家人感风寒而死,诗人写《哭叔三首》表达丧亲之悲。
无情的战乱不仅夺走了周懋泰的朋友、舅兄、养田叔,还剥夺了他年轻的发妻。1861年8月6日,他的妻子在避“寇”途中因患微疴逝世,年27岁,诗人更是以悲痛的心情为妻子写下悼亡诗《哭元配许儒人诗》。周懋泰在诗中抒发了对妻子的思念,其内心的痛苦溢于言表。妻子已去,万物犹在,看到“骖鸾”“钗环”,诗人便因相思触目生悲、泪眼婆娑。诗人心中的愁闷与感伤无处可诉,他幻想着妻子有朝一日能够回来,但无奈“返魂无术”,诗人想起妻子在世时曾常伴于荧案边,而今无人伴读,妻子一病便成永诀,似乎身边的一切都挑起诗人脆弱的心弦。诗人在这首诗中不仅表达了自己丧妻的凄苦而且刻画了一个贤良淑德的妻子形象。而后,诗人在七夕日再写《七夕忆亡妻用张船山忆内诗韵》回忆自己妻子。
(四)流落思家之感
周懋泰自1860年以来一直在避“寇”途中,常出入于深山,从《庚申二月初一出城避寇作》到《避寇蒙龙坞将携眷迁歙南水竹坑留别主人》至《经石泉亭小憩》等,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懋泰的避“寇”行迹。“嗟我逢乱世,两度山中过”乃其流落真实写照。因而,“漂泊流浪”以及“思家”无疑成为其诗歌又一主题。
“易洒途边泪,难归梦里家。还闻贫且病,别恨满天涯。”(《与小农兄遇于鱼龙坑道中别后书寄》)真实记录了诗人流落他乡、贫病交加的飘零感,表达出诗人的恋家之情。其《西坡寓斋作》中“有家未可归,乡思深如水”抒发诗人对故乡思念之切,犹如深水。“看人儿女齐争巧,为客蒓鲈总系情”运用“蒓鲈”典故表达了自己的乡思。此外,诗人多用“浮萍”“萍梗”这些意象表达自己居无定所、无家可归的悲惨处境,“光阴容易消千卷,萍梗终难聚百年”(《秋夜与彭焕庭茂才饮酒作》),“跡无定所皆萍梗,交到忘形即弟兄”(《将赴吴城俊夫有诗送行次韵奉酬》)反复表达诗人因避“寇”流浪在外,不得归家的飘零状态。
三、战争背景下的诗人心态
周懋泰作为晚清战争的受害者之一,经历了山河破碎,伊人消亡后,对这场农民起义有着清醒的认识。
(一)渴望和平
其《重有感》就表达了诗人对清军不战而败将新安让给太平军的愤慨。又《有感四首》(其三)“年来军令太从宽,健卒纵横约束难。伐木坟头烧戍火,打鱼溪上佐盘餐。腰悬宝剑游深巷,手挽雕弓猎远峦。毕竟从戎非玩事,须知报国寸心丹。”深刻的揭示了清军平时的放纵行径,对清军军纪散漫,士兵懈怠的状况表示不满和谴责,诗人不仅讽刺了清军的无能而且希望能有真正的人才击退“敌人”。同时,诗人在经历了家破人亡后心里极度渴望和平。“何时青海宇,重入旧烟萝”(《夜宿堨头听雨有感》)、“安得雨连朝,一为兵戈洗。”(《西坡寓斋作》)、“读到新诗怀旧雨,兵戈无处问平安”(《读润生纪难草书此代跋兼寄澹斋》)等诗歌,都明显的表达出诗人对于和平的渴望。
(二)甘于隐遁
连年的战火在周懋泰思想中充斥着仕与隐的矛盾。作为战争的亲历者,周懋泰期待和平,但是他并没有积极的从戎反而渴望归隐。他在诗歌中既感叹生不逢时,“忧国杜陵频寄愁,逢时李蔡早封侯。”又面对现实,感叹“愧我才疏甘隐遁,天涯孰有济时方。”常年的兵燹以及失去亲人的痛苦让诗人对世事、功名失去了勇气,因此,诗人在诗中透露出归隐倾向。
如其诗《荆州草堂题壁》中的“一题三首”,表达了诗人甘于隐遁的思想。其一首诗人描绘一幅美好的桃花源景象:避居于依山傍水的人家,到处都有桑树,鸡犬相闻。俨然一幅与世隔绝的景象;其二首诗人幻想能够驾一叶扁舟,择一片净土享受自然山川的美景;其三首诗人描述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即使没有肉还有韭菜,甚至失去了做官的愿望,“玉带金鱼誓不贪”。又其《书怀四首》,诗人在《书怀四首》中再次营造一种桃花源式的宁静生活,那里没有战争,虽生活贫困,但诗人乐于“躬耕”“学荷锄”,过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由此可见,面对颠沛流离的生活,诗人渴望归隐,希望回归平静,能够过一种普通的生活,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这场看似正义反封建的农民起义在实际斗争当中带给百姓心灵的创伤。
此外,“茫茫天地间,桃源何处是”(《西坡寓斋作》)“解识人生贵适意,浮荣一笑付江流。”(《江上书怀》)“鹿门他日谁偕隐,荧案今宵孰伴吟”(《哭元配许儒人诗》)等诗歌都是作者厌倦尘俗、渴望归隐的旁证。
清代诗人赵翼有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可谓是周懋泰的人生写照。周懋泰作为战乱的亲历者与受害者,他是不幸的,但战乱成就了周懋泰的诗歌,这一点他又是幸运的。从周懋泰的避“寇”诗研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战争给江南人民带来的一定程度上的负面影响——即这场农民起义造成的家破人亡、山河飘零以及给百姓带来的心理阴影是毋庸置疑的。周懋泰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直接受难者,揭示了太平天国运动对百姓造成的危害,有利于我们一探主流历史背景外太平天国运动时江南人民的生活实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周懋泰作为封建文人,他是站在清代统治阶级立场对这场起义在徽州地区造成的影响进行描述,其不仅在诗歌当中称太平军为“群丑”“寇”,而且对这场起义造成的危害进行的过度批判,难免存在文学艺术的夸大性以及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性。因此,我们不能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完全否认这场农民起义。这场农民起义有其正当性与积极性,而周懋泰的诗歌只是作为封建文人的个人观点,不可一概而论。晚清人士周懋泰,尽管其思想中有着隐逸倾向,但是其描写个人以及家庭悲欢离合的诗歌以及记录太平天国运动的诗歌正是这场战争的旁证,具有“史诗”意义。
[1] 绩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绩溪县志[M]合肥:黄山书社,1998:912.
[2] 周懋泰.松石斋诗草[Z].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卷一.
[3] 李丙麢.安徽省宁国县志[Z].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卷十:4.
[4] 宁国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宁国县志[M].北京:三联书店,1997:614.
[5] 安徽省教育厅编.太平军在安徽的军事斗争[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59:37.
[6] 陈作霖.金陵通纪——国朝金陵通纪[Z].清光绪三十三年刊本:卷四.
责任编辑:刘海涛
I207.22
A
1673-1794(2017)03-0068-04
余经晓,安徽大学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唐宋文学;吴怀东,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合肥 230001)。
2016-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