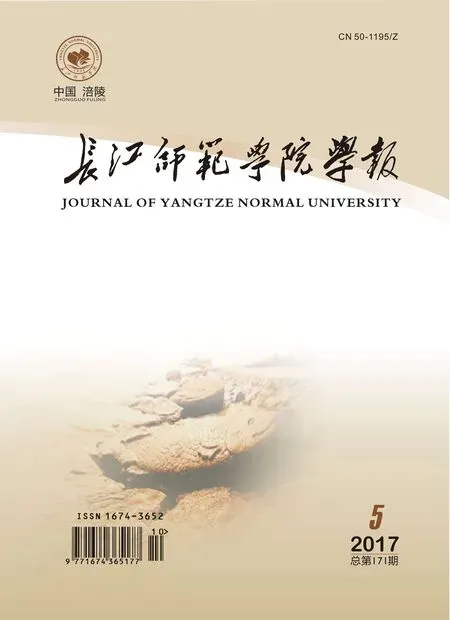多民族文化交融中的阿来创作
——以 《尘埃落定》为例
田晓箐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多民族文化交融中的阿来创作
——以 《尘埃落定》为例
田晓箐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往往受本民族文化和他民族文化的双重影响。作家们在汲取本民族的文化经验进行文本内容构建的同时,也需要吸收他民族的创作经验和文化经验来实现与文本、预想读者之间的三位一体。阿来的长篇小说 《尘埃落定》无论是在语言特色、写作内容上,还是在审美风格上,都具有民族文化交融的特色。这种民族文化交融式的写作一方面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对促进多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以民族文化为背景,将文化功能和美学理想完美结合的写作,不失为保持少数民族文学生命力的重要途径。
阿来;《尘埃落定》;文化交融
阿来出生于四川省西北部阿坝州的马尔康县,这一地区在藏语中被称为“嘉绒”,意思是靠近汉区的农耕山谷,是汉、藏、回等多民族的交界区。因为父亲是回族血统的原因,阿来不是纯粹的藏族血统。这种地域上的边缘化和血统上的混合性使阿来产生了族别上的焦虑:“我们这种人,算什么族呢?虽然在这里生活了几辈人了,真正的当地人把我们当成汉人,而到了真正的汉人地方,我们这种人又成了藏族了。”[1]27民族作家的创作观,往往受到民族文化立场的制约,与扎西达娃、马原等“民族代言”式的写作不同,阿来具有开阔的民族文化观,他的创作往往不受本民族文化的禁锢,而是能在汉藏两种文化的穿梭跳跃中,寻求审美的制高点,以更为全面广阔的文化视角审视多民族文化。他曾表示:“弱势族群的作家,常常会被人强加上一个代言人的角色。这个角色,有时会与个人表达之间,形成非常大的冲突。所以,我想说的是,在这里保持冷静与低调是容易的,真正困难的是,如何保持一种明确的个人立场。”[2]尽管长期以来受多民族文化的影响,阿来还是具有明确的文化立场,那就是不偏不倚,能够站在民族普遍性的立场上,注重“人”这一群体的普遍情感。英国籍印度裔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提出“边缘写作”的概念,认为对跨文化创作的民族作家而言,影响创作的文化有大小之分,主流文化是“大”文化,本民族文化则是“小”文化。对应至阿来的创作,正好相反,“大”文化即汉族文化,藏族文化则是“小”文化。30多年的藏区生活经验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得天独厚的创作题材,藏族文化、创作精神等与汉族主流的创作经验相结合,渗透于他的创作思维、创作视域中,形成了汉藏融汇的创作特色。这种“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3]而又立足本民族文化的文学创作,实质上是汉藏文化交融的结果,对汉藏两种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在提升藏族文化影响力的同时,扩大了汉语的丰富程度和表意空间。
一、语言“陌生化”
语言不仅是人们日常沟通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传播的载体。作家通过语言进行情感表达,语言特色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作家的内心情感世界,而作品语言的形成过程,恰恰同步于作者文化心理建构的过程。阿来这一代藏族知识分子,多是用汉语会话和写作,用藏语进行口头交流。在两种语言之间穿行流浪的独特经验,培养了阿来最初的文学敏感,使他能够以局外人与局中人的双重眼光来感受并观察文化现象,在充分吸收汉藏两种语言养分的前提下进行文学创作。小说 《尘埃落定》的问世,使阿来成为第一位获茅盾文学奖的藏族作家。严家炎评价道:“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颇多通感成分,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出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4]什克洛夫斯基提出“陌生化”理论,旨在将本来熟悉的对象变得陌生起来,使读者在欣赏过程中感受到艺术审美的新颖别致,经过一定的审美过程完成审美感受活动。作为少数民族作家,阿来的作品无论是在写作内容、叙述方法上,还是在语言特色上,都充满异域情调的神秘感和陌生感,《尘埃落定》的语言就具有鲜明的异域“陌生化”色彩。
其一,小说模糊了描写意象的本来面目,通过增加读者的感受难度,延长审美的过程,从而使日常熟悉的意象陌生化,使读者得到全新的体验。作为异族作家,无论在语言技术层面上有多么成熟,都会在文化感受上带有明显的异域情调。小说在遣词造句上往往打破常规,多采用隐喻、怪诞、重复等修辞手法,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文中多次使用比喻修辞,如“喇嘛的泻药使我的肠子唱起歌来了”“那想法就像是泉水上的泡沫一样无声无息地破裂了”“痛苦又一次击中了我。像一只箭从前胸穿进去,在心脏处停留了一阵,又像一只鸟穿出后背,吱吱地叫着,飞走了”“此时此刻的我,不要说脑子,就是血液里,骨头里都充满了爱情的泡泡”[5]200等语句,在这些比喻中,“泻药”使“肚子里唱歌”,“想法”像“泉水上的泡沫”“痛苦”像“箭镞穿胸而过”,“爱情”的感觉则是“骨头里满是泡泡”。其中的喻体“箭镞”“泉水”“骨头”都是藏族生活中常见的意象,作者将“藏式”的喻体搭配汉语的修辞方式来实现本体的表达,将人们现实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赋予生命活力,从而造成了读者对常规常识的偏离,形成语言理解与感受上的陌生感,达到了隐喻修辞的目的。在扩大汉语表意空间的同时,也使民族文化的审美空间提升至新的高度。
其二,小说通过对语言进行创造性的变形,满足读者的期待视野。小说的主人公傻子,是一个“陌生化”的存在,他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问自己“我在哪里?”“我是谁?”傻子的语言具有“傻呆”的特点,他不能组织完整的对话语句,说出的话总是缺少句子成分,却往往具有预见未来的功效,思考“人”这一群体的存在问题,我是谁?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思考与发问,在藏族古老传统而又略带封建色彩的生活中,颇有陌生、怪诞的意味,蕴含了深刻的哲理。作为“集体无意识”中一个独立的自我,傻子所问的问题,是各个民族同胞均需面对的“人”的共性问题,同样的发问贯穿小说始末,引发读者由浅至深的对生命的哲学思考。这种无形中的思考与想象的留白,就拉近了作者和读者的思维之间的距离,产生二者思维上的空间对话的效果。
此外,“行文风格上的且诗且文”[6]58也是汉藏文学交融的重要表现。阿来以诗歌写作起家,因而他的小说语言不乏散文诗的灵动性和诗意性,加之长期以来受中国传统叙事文学“诗性”特征的影响,《尘埃落定》的语言具有抒情小说抒情性的特点。小说中多处“诗意化”的情境描写,给历史题材的小说营造了灵动的诗性境界。小说开篇云:
那是一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她用手指叩响铜盆边沿,随着一声响亮,盆中的牛奶上荡起细密的波纹,鼓荡起嗡嗡的回音在屋子里飞翔。[5]3
“下雪的早晨”“野画眉”“铜盆”“牛奶”这些看似关联生疏的意象,通过诗一般的语言被组合在一起,构成静谧唯美的画面,可谓“诗中有画”。小说相继描写的罂粟遍野、冬日雪景等画面,都是在作家丰富想象和优美修辞的点染下,所营造的宏伟而又精致的历史抒情画卷,使历史叙事作品具有了诗般境界与情怀。
我们知道,藏语以短促、简洁、精炼为主要特点,小说散文诗般的语言,“诗中有画”式的抒情写作,与中国传统抒情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古典传统文学是抒情的文学,自魏晋文学“诗缘情”以来,就主张文学的价值功用在于抒发作者情感,从陆机 《文赋》、刘勰 《文心雕龙》至钟嵘 《诗品》无一例外。苏轼曾在《东坡题跋·书摩诘 〈蓝关烟雨图〉》中评价王维的诗歌:“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意在赞美王维的诗格调高雅,富有诗意的境界。青藏高原的雄伟壮观,天上人间般的美景奠定了阿来小说诗意的抒情格调,藏族土司们的生活起居以及发生在这片神秘土地上的故事就像一首历史的壮丽诗歌,小说中如画般的情境描写,正是这两者的完美结合。藏族学者丹珍草也对此称赞有加:“有着多重文化背景的阿来在叙述中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种开放性、发散式的语言系统,不确定性的汉语叙述在多语混合的宽松空间中游刃自如,使小说语言充满诗意。”[7]毫无疑问,语言“陌生化”带给作者和读者的审美效果是双重的。对作者而言,“陌生化”的叙事可以使作者积极地调动已有的审美意识体验,并且能在头脑中进行审美意象的整合创新,实现思维空间上的“奇异美”。对于读者,在对语言进行咀嚼品味、进行审美的过程中,享受感官上的新鲜感,并使其保持长久的审美注意,扩大审美空间,进而达到提高审美兴趣的效果。
二、民风民俗“兼容化”
丹纳在 《艺术哲学》中指出:“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8]63《尘埃落定》展现了青藏高原上大量的神秘现实,包括土司王朝的生活方式,藏族独特的风土人情,神秘的民间禁忌、巫术、佛法风俗等。从阿来的一系列小说,包括诗歌创作中,可以看出阿来善于从藏族民间风俗中汲取写作营养。“因为在地理上不在藏族文化的中心地带,更因为不懂藏文,不能接触藏语的书面文学,我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的是从藏族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这些东西中有非常强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色彩。所以,那些流传于乡野与百姓口头的故事包含了更多的藏民族本身的思想习惯和审美特征。”[9]291藏族民间口头文学很兴盛,在文字发明之前,藏族文学主要靠口耳传承,民间歌谣即是口头文学的一个重要类型。
作为青藏高原上“地标性”的精神建筑,《尘埃落定》是一部家族、制度的消亡史,也是一部风俗史,各种独特的民间风俗是高原人民历经自然、社会、心理等各方面考验而形成的独特文化现象。小说中多次出现民间歌谣。比如,麦其土司种罂粟的第一年,发生了地动。小孩子们在索郎泽郎的带领下追打到处漫游的蛇,他们走在秋天明净的天空下面,唱到:
牦牛的肉已经献给了神,
牦牛的皮已经裁成了绳,
牦牛缨子似的尾巴,
已经挂到了库茸曼达的鬃毛上,
情义得到报答,坏心将受到惩罚。
妖魔从地上爬了起来,
国王本德死了,
美玉碎了,美玉彻底碎了。[5]59
“我”的侍女桑吉卓玛嫁给银匠后,坐在楼上的栏杆后面绣着花,口里低声哼唱一部叙事长诗里的一个段落:
她的肉,鸟吃了,咯吱,咯吱,
她的血,雨喝了,咕咚,咕咚,
她的骨头,熊啃了,嘎吱,嘎吱,
她的头发,风吹散了,一绺,一绺。[5]100
葬俗文化是藏族民间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葬俗文化是我国各民族共有的文化习俗,藏族的葬俗文化主要包括天葬、水葬和火葬三种主要方式,奶娘德钦莫措夭折的儿子由喇嘛们念了超度经,用牛毛毯子包好,沉入深潭水葬了;战争过后,给阵亡者举行的火葬;麦其土司的大儿子被复仇者杀害后,麦其家族为其举行了隆重的火葬仪式:“火葬地上的大火很旺,燃了整整一个早上。中午时分,骨灰变冷了,收进了坛子里,僧人们吹吹打打,护送着骨灰往庙里走去。骨灰要供养在庙里,接受斋蘸,直到济嘎活佛宣称亡者的灵魂已经完全安定,才能入土安葬。”[5]297
此外,小说中还有“酥油拌洋芋泥”的饮食习俗,“吐口水吓鬼”“禁止捕鱼、食鱼”“禁止杀猴”等民间禁忌习俗。这些民间习俗,与汉族民间习俗有一定的相通性。在现代西部乡土小说中,也不乏这样的民俗描写。以西部乡土作家雪漠为例,在他以河西走廊的大漠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大漠三部曲”中,出现了包括“花儿”“贤孝”为代表的民间表演艺术;以“吐口水”“烧纸钱”“火燎毛病”为代表的鬼魅禁忌风俗,以及以“山芋米拌面”“拌面汤泡馍馍”等为代表的饮食风俗。首先,藏族的民间歌谣和汉族的民间歌谣“花儿”“贤孝”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二者或是由民间故事改编而成,或是即兴而发,有感而作;在形式上都具有对仗、押韵的特点,且都具有情感表达、沟通交流、“谈情说爱”的功能。它们在形式上都是一致的,只是因人们日常生活习惯、行为经验的不同,而产生内容上的差异。其次,藏文化中的“火葬”习俗与汉文化中的“烧纸钱”“火燎毛病”等鬼魅风俗都是人们对“来世转生”、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希冀。此外,在饮食习俗上,两种习俗也是“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藏族生活中的“酥油拌洋芋泥”和汉族的“山芋米拌面”都是以洋芋泥为食材的主要组成部分,加上两个民族特有的“酥油”“面食”混合而成,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诸如此类的民间习俗,都存在某种共同的沟通介质,这种共同性也即两种文化的交汇共同之处。虽然,两种文化在影响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主客关系尚不明确,但相同的风俗在不同民族地域上的扩散和传播,则足以证明文化互相影响以及交融的客观存在性。
三、叙事审美的共通性
小说是一种叙述的艺术,叙述自然也就成为小说的本位特征。叙事文本有3个基本视角:作者的视角、读者的视角和叙述者视角[10]。作者视角指从作者角度对文本的整体建构,读者视角以预想读者为出发点进行文本叙述,叙述者视角则指在文本中完成叙述的叙述者角色。其中,叙述视角与作者视角互相独立,互为补充。《尘埃落定》选取“傻子”这一非常态视角进行叙事,叙述视角是“限知性”的。但“傻子”的傻,又非病理意义上的傻,他“大智若愚”的对所有重大事件的预见性,弥补了正常叙事无法全面顾及、全方位表述的缺憾。从“全知”叙事的角度来讲,这是对鲁迅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视角、贾平凹 《秦腔》中的“疯子”视角、史铁生 《我的丁一之旅》中的“行魂”等叙事视角的继承和发展。它们的共同性,体现在将作者视角和叙述者视角完美结合,拥有“全知性”的叙述视野,将一般叙述所不能覆盖的内容完美地呈现出来。
傻子是麦其土司家的二儿子,在日常生活中具备病理意义上傻子的全部特点,智力和行为上有天生的缺陷,“土司醉酒后有了我,所以,我就只好心甘情愿当一个傻子了”[5]3,“一个月时我坚决不笑。两个月时任何人都不能使我的双眼对任何呼唤做出反应……我一咧嘴,一汪涎水从嘴角掉了下来”[5]5。傻子同时又具有超越时空、预见一切的能力,麦其家的大少爷被复仇者所杀时,“整个官寨像所有人都被杀了一样安静,只有傻子躺在床上大叫起来:‘杀人了!杀手来了!’”[5]293。傻子人物在这种“傻”与“不傻”的性格特征中游移变换,使得傻子这一人物形象具有隐喻意义和哲理意味。
在文本立场上,作者给予傻子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傻子是所有事件的见证者,但又避开了当事人的身份角色,而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重大事件。这样,小说就形成以傻子为中心的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复调性对话。这样的对话方式,使得叙述者与文本之间产生疏离,拉伸了叙述主客体间的空间距离,进而扩大了叙述的张力。重要的是,傻子的双重身份特点与作者个人的双重身份相呼应,二者均具备相似的性格特征、行为方式、敏锐而又矛盾的文化心理等,将文本和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以作者和“傻子”的境遇为典型,影射了数以万计的具有“多民族身份”的“藏族”同胞的命运。
在人物设置层面上,作者围绕傻子这一人物形象,巧妙地设置了包括汉人母亲、黄特派员、叔叔、汉人戏班子里的姑娘等众多人物形象,以及罂粟、快枪、照相机等汉属意象。在血统上,傻子是汉藏混血儿,骨子里带有汉藏文化交融的先天特性。母亲、黄特派员、叔叔等人物是傻子双重文化身份形成的催化剂。汉人母亲总给“我”忽远忽近、熟悉又陌生的感觉,“那天,她又紧紧地捧住我的脑袋,不住地摇晃着说:‘我要教你说汉话,天哪,这么大了,我怎么就想不起要教你学些汉话’”[5]18。叔叔参与内地“白色汉人”和“红色汉人”之间的战争,傻子买飞机支持叔叔,间接参与战争,傻子和叔叔之间以照相机为媒介进行交流。小说中故事情节的展开和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在汉藏文化的不断碰撞中进行的,“我”这一人物形象也在两种文化的交流中日渐丰满。因此,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具有汉藏文化混融的特性。
作者设置“且智且愚”双重性格的“傻子”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具有象征性和隐喻性。庄子认为,完美的人应该具备“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特点。日常生活中的“傻子”基本不具备正常人的行为,在每一次重大事件中,他总会嘀咕一些神神秘秘、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而且事情的结局又总能印证他的“傻话”。傻子是麦其土司走向衰亡的助推者,在傻子“预见性”的安排下,土司制度由兴盛走向衰亡。因此,傻子是土司制度在文化意义上的象征。纵观麦其土司的衰亡以及土司制度逐渐崩溃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外在力量的介入显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引进鸦片种植、进行商贸交易,到梅毒的传染和“红色汉人”的到来,都是土司与汉人之间的直接接触,是汉族文化进入藏族地区的直接表现。文化之间的碰撞向来是利弊共存的,罂粟、快枪、照相机等的传入使藏族人们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全新体验的同时,也遭受了异族文化带来的弊端——各土司之间的争夺愈演愈烈,土司们还染上了梅毒。
毋庸置疑的是,小说叙事带有明显的“汉族经验”,从多个侧面呈现出回归传统叙事的趋势。一方面,“傻子”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性格,与主流文学中的一些人物形象具有同构性,比如前面提到的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贾平凹 《秦腔》中的“疯子”,以及古典小说 《红楼梦》中林黛玉、贾宝玉的人物形象,都具有双重性格。作家们通过双重性格深化了人物的心理刻画,丰富了小说的人物性格类型,使得小说展示出无与伦比的丰富内涵,同时也体现出历史现实、社会现实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对于人物而言,两种性格相互制约、相互平衡,是儒家中庸文化之美的体现。另一方面是在叙述的过程中,为了突出中心事件而相对淡化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不仅 《尘埃落定》如此,在创作小说 《天火》时,为了突出“天火”这一中心事件,作者改变了以往的叙事方法,主要突出“森林大火”这一事件而相对淡化了对人物的描写塑造,这种拟以回归传统叙事的方法,明显是受了古典小说的影响。
四、结 语
为了创作,阿来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外国名著,多次徜徉于中国古典小说的海洋,从中汲取经验。“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11]的独特身份,使他将藏族人对生命的特定感知转换为汉语的审美表达。诚如作者所言:“我可以说,作为一个写作者已经成功地把一种非汉语的感受融入了汉语。这种异质文化的东西,日积月累,也就成为汉语的一种审美经验,被复制、被传播。这样,在悄无声息中,汉语的感受功能、汉语经验性的表达就得到了扩展。”[12]209-220可以说,阿来的小说,无论是 《尘埃落定》《空山》,还是 《格萨尔王传》都在叙述内容、语言特色、叙述方法上,成为“扩大汉语感性丰富程度”的重要实践,作品里的丰富多彩的藏文化因子,随着作品的传播,在潜移默化中对汉族文化产生了影响,不仅丰富了汉语的感受功能,扩展了汉语经验性的表达,而且影响了汉族人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虽然在整个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两种文化博弈连连,争论不断,但从整体上说,藏族文化还是以积极的姿态参与整个互动过程的。
诚然,汉藏文化之间的这种交融是双向共存的。汉族文化在藏化的过程中,自身受到冲击,以非显性的方式保存下来,同样在无形中影响着藏族人们的生活。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文本中的汉语审美表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藏族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尤其是在经济、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区域政治、经济之间的交流,无疑为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便利条件。
毫无疑问,阿来的小说是多民族文化融合写作的范本,是促进民族文化交融的中介和载体,对促进多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重要的是,透过这种“异质文化”写作,阿来想表达或告诉人们的恰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共性,即“人”的群体文化的共性——吸收先进、互相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文化功能和美学理想完美结合,以地域文化作为背景进行创作,不失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保持生命活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1]阿来.大地的阶梯[M]//阿来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27.
[2]阿来,陈祖君.文学应如何寻求“大声音”[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5(2):260-273.
[3]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N].中国文化报,2001-05-10(3).
[4]严家炎.尘埃落定:丰厚的文化底蕴[N].人民日报,2000-11-11(6).
[5]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00.
[6]马丽华.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58.
[7]丹珍草.“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尘埃落定》的多文化混合语境[J].民族文学研究,2008(4):67-72.
[8]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63.
[9]阿来.就这样日益丰盈[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291.
[10]王富仁.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3):1-36.
[11]阿来,姜广平.“我是一个藏族人,用汉语写作”[J].西湖,2011(6):88-95.
[12]阿来.汉语:多元文化共建的公共语言——在中韩作家对话会上的演讲[M]//看见.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
I206.7
A
1674-3652(2017)05-0102-05
2017-06-17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11&ZD113)。
田晓箐,女,甘肃张掖人,主要从事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志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