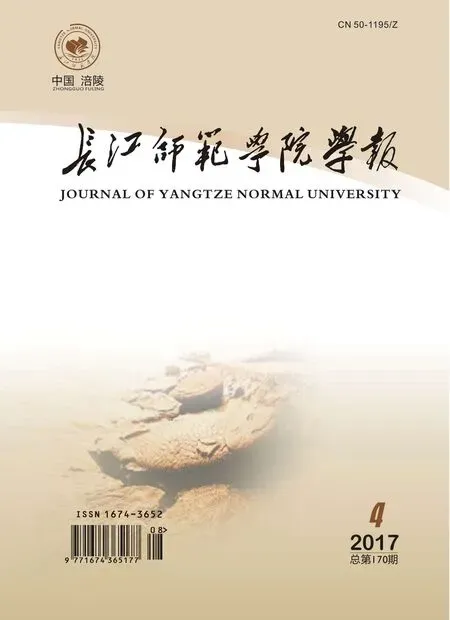司空图“意境说”美学价值论
郎江涛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司空图“意境说”美学价值论
郎江涛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中华名族历来偏重形象这一审美趣味,“意境说”就是这一审美趣味的理论体现。在“意境说”的发展过程中,唐代诗人司空图全面深刻地阐释了“意境说”的本质特征:“思与境偕”“妙造自然”“味外之旨”“象外之象”。自唐以后,司空图的“意境说”从宋到清都不断有人给予新的阐释,足见其影响之深远。尽管司空图“意境说”的美学价值是多方面的,但若从它自身的独特特点以及它对后人的影响来看,司空图“意境说”的美学价值主要集中体现在3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神形”美学思想、完善了中国古典诗歌接受美学思想、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审美移情思想。
“意境说”;本质特征;美学价值
一、前言
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前期,“意”和“象”是两个不同的审美范畴,但从魏晋南北朝中叶以后,刘勰(约465-520年)首次把“意”和“象”合成了一个审美范畴——“意象”。在刘勰看来,“意象”是创作之首,如他所说:“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1]249到了唐代,经王昌龄(约698-757年)、皎然(中唐诗僧,生卒年不详)、刘禹锡(772-842年)、司空图(837-908年)的不懈努力,最终形成了“境”的审美范畴。从词语的使用上讲,王昌龄是把“意”与“境”合起来使用的第一人。在王昌龄看来,“境”体现“意”,是“象”与“心”的契合,如他所说:“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挈之,深穿其境。如登高山绝项,下临万象,如在掌中。以此见象,心中了见。”[2]41继王昌龄之后,皎然、刘禹锡对“境”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他们看来,“境”的本质在于“象外”,如皎然在《诗评》中说:“或曰:诗不要苦思,苦思则丧于天真。此甚不然。固当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趣,写真奥之思。夫希世之珍,必出骊龙之颔,况通幽名变之文哉!”[3]268又如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纪》中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象,工于诗者能之……诗者其文章之蕴邪?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4]68继皎然、刘禹锡之后,司空图提出了自己的“意境说”。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司空图从“思与境偕”“妙造自然”“味外之旨”“象外之象”4个方面揭示了诗歌审美创造和审美欣赏的基本问题,从而使中国“意境”理论趋于成熟。
自唐以后,历代都有人不断丰富和发展司空图的“意境说”。例如宋代苏轼(1037-1101年)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元代王若虚(1174-1243年)认为“三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明代画家王履(1332-不详)提出“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明清画家石涛(约1642-1717)提出“法于何立?立于一画”;近代王国维(1877-1927年)提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可见,司空图的“意境说”对唐以后中国“意境”理论的影响是深远的。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意境”理论经历了“意”—“象”—“意象”—“境”—“意境”的发展历程,其理论建构的最终完善者是唐代的司空图。自此以后,司空图的“意境说”从宋代一直到清代都不断得到新的阐释和发展。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很有必要对司空图“意境说”的主要美学价值作一定程度的探讨,以便对中国“意境”理论的发展、本质特征、文化价值等相关的问题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同时对学界的“表现论”与“抒情论”也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二、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神形美学思想
在司空图看来,“道”决定“意境”,亦即没有“道”,“意境”就不会存在。因此,在《二十四诗品》中,司空图常用“真”“真体”“真宰”“浑”“气”“自然”等概念来指“道”。这个“道”就是宇宙的本体和生命,亦即老子的“道”。在以“道”为自己立论的基础上,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形容》中指出:“俱似大道,妙契同尘。离形得似,庶几斯人。”[5]36这里,司空图明确提出“离形得似”的主张。这里的“离形,不求貌同;得似正由神合”[5]37。因而,“离形得似”的意思是不求形同,而求神同,亦即以神为主。在《二十四诗品·雄浑》中,司空图又指出:“超以象外,得其环中。”[5]3这句话的意思是“一方面超出乎迹象之外,纯以空运,一方面适得环中之妙,仍不失乎其中,道即是所谓‘返虚入浑’”[5]4。值得一提的是,“得其环中”出自于庄子的“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6]62。我们知道,老子的“道”是“有”与“无”、“虚”与“实”的统一;而庄子的“象罔”是“象征有形和无形、虚和实的结合”[3]130。由此看来,司空图的“离形得似”强调的是“有”与“无”、“虚”与“实”的统一,突出的是以神为主的思想。
在继承老子、庄子思想的基础上,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出了“味外之旨”,如他所说:“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復以全美为上,即知味外之旨矣。”[5]48不仅如此,司空图还在《与极浦书》中提出了“象外之外”,如他所说:“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然题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5]52在司空图看来,“意境”应突出“味外之旨”中的“旨”以及“象外之象”中的第二个“象”。从审美主体的角度看,“味外之旨”和“象外之象”突出的审美主体应是欣赏者,而不是创造者。“味外之旨”让欣赏者品原诗潜在的意味,在司空图看来,“味外之旨”是最美的,故因欣赏者不同,原诗所品出的意味也不一样。“象外之象”给欣赏者更大的想象空间,让虚的“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欣赏者的脑海里,从而让欣赏者欣赏到更生动形象的画面。从神与形的角度看,“味外之旨”和“象外之象”则揭示了神外有神、形外有形以及神外有形、形外有神;也就是说,在神形关系上强调了神形的无限互延性。正是这种神形的无限互延性突出了司空图“意境说”的精妙之处。
在神与形的关系问题上,司空图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离形得似”。从思想来源上讲,司空图的“离形得似”继承了老子、庄子的“有”与“无”以及“虚”与“实”相统一的思想,突出了以神为主。从审美层面上看,司空图的“离形得似”突出了两个主体的统一:创造主体与欣赏主体的统一,其“象外之象”和“味外之旨”强调神形的无限互延性,从而发展了中国古典神形美学思想。
三、完善了中国古典诗歌接受美学思想
司空图的“意境说”在审美创造方面突出的是审美主体的能动性,但司空图认为审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受“境”的限制。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司空图说:“王生寓居其间,浸渍益久,五言所得,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5]50司空图在这里提出了“思与境偕”的观点。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文学创作的生命在于真实,只有创作意图和艺术想象与“境”融合为一体,作品才具有生命力。在司空图看来,创作主体只有做到“思与境偕”,才能“妙造自然”。在《二十四诗品·精神》中,他说:“碧山人来,清酒深杯。生气远出,不着死灰。妙造自然,伊谁与哉。”[5]24在《二十四诗品·缜密》中,他说:“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5]26可见,司空图认为诗的意境既来自自然,又超出自然,它是经诗人创造的第二个自然;同时,造的关键在于“妙”和“奇”。
在探讨“思与境偕”与“妙造自然”的基础上,司空图还从审美欣赏的角度提出了“味外之旨”与“象外之象”。“味”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老子的《道德经》。在该书中,老子从悟道的角度分别在第十二章、第三十五章、第六十三章提到“味”。在老子看来,最大的“味”是“无味”,即“味无味”[7]293。在诗歌美学中,钟嵘(468-518年)最早提出这一概念。在《诗品》中,钟嵘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也。”[4]70这里,钟嵘把“滋味”看成是诗歌的审美内容。在唐代,对“味”论述最精辟的是司空图。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中用江岭之南的人吃醋和盐与中原人吃醋和盐的不同味感来说明“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徜复以全美为上,即知味外之旨矣”[5]48。这里,“味外之旨”指的是诗境中需靠读者自己发掘的潜在意味。按司空图的意思,诗的意境是内在的实和外在的虚构成,即诗内之象与诗内之味的统一,诗外之象与诗外之味的统一,这两个统一揭示了审美创造与审美欣赏的统一。
美学意义上的“象外”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南朝谢赫(479-502年)的《古画品录》,文云:“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3]268-269谢赫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画家不应受具体事物形状所限制,而要突破具体的物象,才能让欣赏者感受艺术的魅力之所在。在司空图以前,皎然和刘禹锡都提到过“象外”,如皎然说过“采奇于象外”[3]268,刘禹锡讲过“境生于象外”[4]68,但司空图所说的“象外之象”是“象外”有“象”;换句话说,“象”是实体存在的,而“象外之象”是虚的,但能引起欣赏者的不同想象。“象外之象”中第一个“象”决定第二个“象”,而第二个“象”则拓展第一个“象”,如司空图说:“超以象外,得其环中。”[5]3也即在神与形的关系上,要离形得神,从而让欣赏者感受艺术之美。
司空图从审美创造和审美欣赏的角度创造性地提出了“思与境偕”“妙造自然”“味外之旨”“象外之象”。这4个方面共同揭示了创作者和欣赏者平等的审美主体地位,从而转换了中国古典诗歌美学审美视角,即不单一地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来谈审美接受问题,而是把创作者和欣赏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突出了平等的审美主体地位。他的“味外之旨”“象外之象”强调欣赏者的感悟,从而打破了“文本神圣性”的观念,确立了文本开放性的思想,即欣赏者要超越文本本身的形象和情志。可见,司空图的“意境说”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古典诗歌接受美学思想,从而从理论上驳斥了那种认为“中国接受美学思想”是从西方引进的观点。
四、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审美移情思想
中国美学学科体系下的“移情论”虽来自西方,但有关审美移情的思想在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早就存在。庄子在《秋水篇》中用自己“出游从容”而感“乐”的经验来推测鱼是否感到“乐”,把自己“乐”的心境外射到鱼身上,庄子的这种心理活动就是移情。“这种现象是很原始的、普遍的。我国古代语文的生长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移情原则进行的,特别是文字的引申义。我国古代诗歌的生长和发展也是如此,特别是‘托物见志’的‘兴’。”[8]584-585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指出:“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1]250刘勰在这里对创作中的移情作了高度的总结,亦即客体对象的主体化、主体情感的客体化,用朱光潜的话说,就是“由物及我”与“由我及物”。
司空图的“意境说”从审美创造和审美欣赏两个角度丰富了中国古典审美移情思想。从审美创造的角度看,“思与境偕”“妙造自然”揭示的是创作者的审美移情问题。在司空图看来,情感投射是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所崇尚的,即“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5]50。这里的“思与境偕”其实指的是审美观照中审美主体的“心”与“境”的契合;也就是说,审美主体要进行自己情感的投射。司空图认为诗人只有把握住了自己的情感投射,才能“碧山人来,清酒生杯。生气远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谁与裁”[5]24。这里的“妙造自然”强调的是造出自然之生命;也就是说,这个自然已融入了诗人的情感,实现了“思与境偕”。可见,司空图在审美创造上主张诗人要投射自己的情感,亦即移情,但司空图对审美创造者的移情作了一定的限制,即“思与境偕”;也就是说,审美创造者的移情必须与“境”契合。在司空图看来,审美创造者只有“思与境偕”,才能“妙造自然”,从而体现作品的真实性。
从审美欣赏的角度看,“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揭示的是欣赏者的审美移情问题。在司空图看来,“味外之旨”最能体现诗歌之美。同时,司空图还认为,好的诗歌应是“象外”有“象”,即“象外之象”。司空图认为“象外之象”中的第二个“象”是虚的,它只存现在欣赏者的脑海里,但这两个“象”之间的关系应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5]3。也就是说,第一个“象”规范、制约着第二个“象”;可见,司空图认为诗歌欣赏者应进行情感的投射才能品味“味外之旨”、把握“象外之象”,从而获得美的享受,如他所说:“情性所至,妙不自寻。”[5]34
司空图的“意境”说从审美创造和审美欣赏两个方面揭示了创造者和欣赏者的移情问题。从司空图对“味外之旨”和“象外之象”的具体阐述来看,欣赏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创造者,故创造者和欣赏者的情感投射过程是一样的,即“由物及我”“由我及物”“物我合一”。值得一提的是,司空图对诗歌意境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他的《二十四诗品》《与李生论诗书》《与王驾评诗书》《与极浦谈诗书》等中,但《二十四诗品》则集中突出了司空图的移情思想,它反复强调虚静的心态,如“素处以默,妙机其微”(《冲淡》)[5]5、“虚伫神素,脱然畦封”(《高古》)[5]11、“体素储洁,乘月返真”(《洗炼》)[5]14、“绝伫灵素,少回清真”(《形容》)[5]36等。这正如朱光潜所说:“最典型的运用移情作用的例是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以及在南宋盛行的咏物词。”[8]585可见,司空图的“意境说”从创造者和欣赏者两个方面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审美移情思想。
五、结语
中国“意境”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其主要经历了“意”—“象”—“意象”—“境”—“意境”的发展脉络。王昌龄、皎然、刘禹锡在中国“意境”理论的建构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促使中国独特的“意境”理论成熟的却是司空图。与其他理论一样,司空图的“意境说”带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具体而言,司空图的“意境说”体现了老庄思想的真谛,强调“有与无”以及“虚与实”的高度统一,主张审美主体以“思与境偕”为根本、以“妙造自然”为创作目的、以“味外之旨”与“象外之象”为审美欣赏途径。正是这些特点使司空图的“意境说”不断被后人赋予新的阐释,从而使它具有巨大的美学价值。虽然司空图“意境说”的美学价值是多方面的,但如我们从它自身的独特特点以及它对后人的影响来看,司空图“意境说”的美学价值主要集中体现在3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神形美学思想、完善了中国古典诗歌接受美学思想、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审美移情思想。
[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李珍华.王昌龄研究[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
[3]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中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5]司空图,等.诗品集解续诗品注[M].郭绍虞,集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6]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2009.
[8]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志 洪]
B241
A
1674-3652(2017)04-0100-04
2017-04-06
郎江涛,男,重庆丰都人。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和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与审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