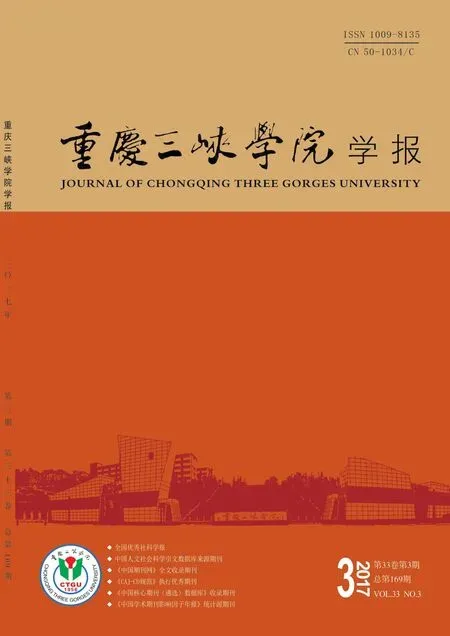论汉语修辞学体系的建立
——《文心雕龙》的修辞学研究
陈会兵 孙 婷 刘文亚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重庆 404020)
论汉语修辞学体系的建立
——《文心雕龙》的修辞学研究
陈会兵 孙 婷 刘文亚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重庆 404020)
《文心雕龙》不仅是我国第一部体大思精、震古铄今的文艺理论和文章创作论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汉语修辞的理论著作,其修辞理论、辞格研究和修辞实践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初步建立起汉语修辞学的理论体系。《文心雕龙》开了汉语修辞学系统研究的先河。
《文心雕龙》;修辞理论;辞格研究;修辞实践;修辞学体系的建立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章创作论中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备的一部杰作,震古铄今,它对我国传统文学研究的贡献可谓首屈一指,历来备受推崇,对此书的整理、研究成为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一门显学——“龙学”。同时它又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全面论述汉语修辞学的理论著作,标志着汉语修辞学体系的建立。作为一个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理论家,刘勰的文学思想和修辞研究都深深地打上了儒家学说的烙印,但又能突破某些儒学正统观念,他的文学思想、修辞学观念和具体的修辞学研究都继承、总结并发展了儒家经典的文学观和修辞观[1]。
在中国修辞学史上,《文心雕龙》主要继承了孔子“文采”“尚巧”的修辞学说,兼采儒家经典和诸子著作“质”“文”辩证的修辞观念,总结前代经典著作的修辞理论、实践和方法,对传统的遣词、炼句、裁章、谋篇等主要修辞内容,特别是文学语言的修辞,均有精湛论述。其中《神思》《体性》《风骨》《情采》《熔裁》《声律》《章句》诸篇从一般修辞理论、修辞的作用和效果、字词的选择、章句的组织、声律的配合、语言的风格等方面(即后世所谓“消极的修辞”)全面具体论述了汉语修辞理论;《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等篇则总结了先秦以来儒家经典、诸子著作以及诗歌文赋的具体修辞手法和实践(即后世所谓“积极的修辞”)并给予理论的提升;著作本身的语言也对我国六朝以前的修辞方法兼收并蓄,可以说是刘勰修辞观念的具体体现和修辞理论的具体运用,反映了六朝时期文学艺术的自觉和“唯美”的时代精神[2]。
通过这些理论探讨和修辞实践,《文心雕龙》初步建立起了汉语修辞学的理论格局,跟其文学理论和文章创作论一样,完成了中国传统语言学中空前的系统的修辞学理论构架,指导着后世诗歌文赋和各种体裁文章的语言修辞,并给予汉语修辞学的进一步发展以启迪。本文试从修辞理论、辞格研究、修辞实践三个方面探讨《文心雕龙》的修辞学研究,恳请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一、修辞理论
我国先秦时期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就十分重视语言的运用,他们在许多著作和文章中对汉语修辞进行了经典性的论述,如《尚书》:“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易经》:“辨物正言,断词则备”;《诗经·淇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又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论语·颜渊》:“子贡曰:‘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礼记·表记》说“情欲信,辞欲巧”;《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等,成为汉语修辞学的发端[3]。这些著作和文章本身对汉语修辞也身体力行,成为后世文章的修辞典范(见《文心雕龙》的《原道》《征圣》《宗经》等篇)。刘勰《文心雕龙》批判地继承了先秦经典和诸子著作的修辞观念,结合后世人们对修辞的认识和自己的研究,建立了汉语修辞的一般理论体系。《神思》《体性》《风骨》《情采》《熔裁》《声律》《章句》等篇集中探讨汉语修辞问题,对汉语修辞的作用、修辞的方法等修辞理论的重要问题进行了集大成式的研究,还有许多其他见解散见于别的篇章,这些论述是对前代及当时语言修辞的总结和发展,这也是前无古人的,在修辞学上的地位无与伦比。
在文采与质实的关系上,刘勰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尽善尽美”(《论语·八佾》)、“文质彬彬”(《论语·雍也》)的文质论。《文心雕龙·情采》进一步主张“文附质”“质待文”,明确指出了文章内容决定修辞形式,修辞形式要为文章内容服务,要求情采相称,他说:“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原也。”提倡“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认为“联辞结采”的目的是“将欲明理”,文章要以“述志为本”。如果“繁采寡情”,则“味之必厌”。处理文章文质关系要“文不灭质,博不溺心”,这样才能做到“雕琢其章,彬彬君子”。《文心雕龙》本身就是一部“剖情析采”(《序志》)的伟大理论著作。具体说来,语言修辞应从形态、声音、性情三个方面入手,他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广泛精研前代著作,分辨源流正邪,“亦可以驭文采矣”。刘勰要求文章既要内容丰富真诚,又要文辞美妙优雅,这是执笔作文的金科玉律,所谓“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征圣》)。
语言修辞一个重要方面是锤炼字、词、句、段和剪裁篇章。《练字》论述选字、择字问题,即选择最恰当的字眼来表情达意,使文章更加精美。要做到“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用词问题(即字义),要求不用偏僻字,少用偏旁相同的字,要权衡一个字重复出现,这主要是从文章的内容考虑,同时也考虑了文章的形式;一个是书法问题(即字形),要使文章书写出来以后有视觉上的美感,不能单调重复。除此以外,刘勰还告诫运用语言不可沿讹求奇,如对“别风淮雨”的论述。
《章句》:“夫人之立言,因字(词)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明确指出字(词)是篇、章、句的“本”,是语言和文学的基础和根本,句、章、篇则是字(词)生出的“末”,“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语言的正确使用必须做到字、句、篇、章不妄、无玷、无疵。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文章修辞的根本要求:“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刘勰在本篇还进一步通过分析“兮”字探讨了虚字“无益文义”(即没有词汇意义,“益”应理解为“增加”,而不是“有益、无益”)的本质,通过分析虚字在文章中“发端”“札句”“送末”等位置探讨了虚字的“弥缝文体”“外字难谬”的语法作用和修辞作用,在汉语史上影响深远。同时这也是我国最早的一篇文法、修辞结合论[4]。
《熔裁》对剪裁篇章有精到的论述:“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蹊要所司,职在熔裁,櫽括情理,矫揉文采也。”写作文章,布局谋篇的关键在于熔意裁辞,矫正文章情理上的偏差,修剪文辞上的毛病。“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词谓之裁。”熔裁文章情理和文辞首先要确定三个标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其次要讨论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若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非夫熔裁,何以行之乎。”熔意裁辞要达到“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的境界。刘勰对锤炼词句、剪裁篇章的精到论述对今天我们运用语言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充分运用汉语声律来增强文章的语音美是汉语修辞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运用语音来增强语言和文章的美感是魏晋六朝的时代风气。《声律》篇从声律的产生、声律与音乐的关系、声律在语言中的运用、声律对文章的重要修辞作用等问题给予了充分的论述,是对六朝时期我国音韵学研究的理论总结,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限于论题和篇幅,兹不详述,参见拙文《〈文心雕龙〉的语言学研究》)。同时也将声律理论运用到文章创作中。语音对文章的修辞作用不容忽视,《神思》:“循声律以定墨。”《声律》:“音以律文,其可忽哉。”“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机杼,吐纳律吕,唇吻而已。”这是说人的语言是构成文章的关键,是表达思想的机关;吐辞发音要符合音律,要调节唇吻等发音器官。《声律》论述利用语音进行修辞就要做到声韵调配合,刘勰称:“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离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声调的飞沉(高低升降)与双声叠韵必须“辘轳交往,逆鳞相比”,“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这样才能达到“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的语音效果。语音在语言运用上还要注意两点:“异声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和”与“韵”有显著的不同:一是求异,一是求和;两者又有相通之处:异中求和,同中求韵,以此构成完整和谐的统一体,构成优美的声律。对当时两大不同的文体“文”与“笔”在语音修辞上的运用也进行了比较,认为“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写作无韵之“笔”容易工巧,但要使音调和谐(异声相从)最困难;写作有韵之“文”难以精工,然而压韵(同声相应)却很容易。刘勰还从反面指出,文章违反“声律”要求,必然导致“文家之吃”,就会“吃文为患”。六朝声律理论的研究及运用于诗文创作,为六朝骈文的盛行和唐代“一代之文学”——律诗的鼎盛打下了基础,这是语音修辞对诗文发展重大影响的一个结果,刘勰《文心雕龙》的推动功不可没。
《风骨》《体性》等篇集中论述了文章的艺术风格,但是语言风格是形成文章艺术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作家的语言风格又主要体现在修辞上,因而它们也是修辞论著。《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苑: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章之鸣凤也。”“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或巧意,危败亦多。”“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这些论述阐明了艺术风格、语言风格对于文章和作家的极端重要性。《体性》篇则具体总结了文章的艺术风格:“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如前所述,语言的风格是形成文章艺术风格的主要因素,作家的语言风格又主要体现在修辞上,因而,这些艺术风格同时也是作家通过修辞而得到的语言风格。
二、辞格研究
修辞格的使用是语言修辞的主要内容之一,陈望道在他的《修辞学发凡》里将这种有意识使用的特殊修辞方式称为“积极的修辞”。一般认为,对修辞格的全面研究始于宋代陈騤的《文则》,但是,就事实而言,《文心雕龙》首开辞格全面研究的先河。《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等辞格专论总结了先秦至齐梁时期儒家经典、诸子著作以及诗歌文赋具体的积极的修辞手法和实践并给予理论的提升。只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这是学术发展的规律。刘勰的时代,人们对修辞格的认识可能还相当粗疏,许多人们经常使用的修辞手法(即“积极的修辞”)在当时并没有总结为特殊的修辞方式(即辞格),后世才确定为“积极的修辞”,这是当时人们认识水平的限制。另外,《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它侧重论述原理、原则性问题,要求其理论具有“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跨越前哲的系统性,对细枝末节不做过多追究。因而,刘勰有意识地在《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等篇里详细讨论了当时“骈文”常用的一些修辞格,而其他一些修辞格则散见于其他篇章之中。但这些讨论并不是零散的,而是深入、系统、全面的。
《丽辞》篇论述对偶修辞格。丽者,俪也,两个结构比较一致,词义、音律上下相对的一组(两个或两个以上)句子就是丽辞。刘勰将对偶句式分为四种:言对、事对、正对、反对,前两种是从内容上划分,后两种对形式也有考虑,虽不及陈騤《文则》和现在人们给对偶句式的分类精细,但他首开根据内容和形式给对偶句分类并进行深入研究的先河;总结对偶的方式则有“句句相衔”“字字相俪”“宛转相承”“隔行悬合”等等,这些对偶句式“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丽辞》篇还讨论了这四种对偶句的修辞运用和效果,认为“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通过举例说明用得不好的对偶句为“句之骈枝”,一意重出,即后人所谓“合掌”;要求属对优劣相配,“务在允当”。六朝骈文盛行,《文心雕龙》受时风影响,也多用偶句,但他并不排斥单行奇句,认为“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相反,“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聩耳目”,这也是刘勰对六朝绮靡文风、片面追求对偶形式的匡正。
《比兴》借助《诗经》的“六义”讲解比兴,“比兴”之义,历来人们认识分歧,有人认为是“诗体”,有人认为是“诗法”。但是细按文意,我们认为在刘勰的观念中,比与兴在语言的运用上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都是指比喻。“‘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义。”所谓“比”就是“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兴”要“起情”“拟义”,指的就是有譬喻作用的起语。比较而言,“比显而兴隐”。“比兴”的作用是“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比喻的方式则是“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比喻的运用要做到“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若比喻用得不恰当则“刻鹄类骛,则无所取焉”。
《夸饰》一篇论述夸张的修辞手法。普通语言的运用,常常会出现“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而运用夸张的修辞手法,则可以做到“形器易写,壮词可以喻其真”。尽管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却可以描摹事物的真实情状,“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刘勰还简要地论述了夸饰的发展,认为“自天地以降,夸饰恒存”,“大圣所录,以垂宪章”,“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修辞运用夸饰,则“莫不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夸饰运用得当,能抓住要领,读者的共鸣就会蜂拥而起;夸饰运用得不好,即“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运用夸饰的修辞手法基本原则是要做到“使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亦可谓之懿也”。
《事类》:“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例,援古以证今者也。”事类就是引用古事古语来论证支持作者自己的观点。这一修辞手法历来受到人们普遍的重视,所谓“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用人若己,古来无懵”。“引成辞”“举人事”的主要作用是“明理”“征义”,其主要方法和修辞特点则有“重言”“缀采”“起兴”“节缩”。经籍深富,文采浩瀚,人人都可以从中吸取营养,为我所用。然而,要恰当地引用事类,就必须要有渊博的学识,多识古人、古事、古语,即所谓“宗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才能做到“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用典不能“引事乖谬”,否则就会“虽千载而为瑕”。《事类》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篇全面研究“事类”辞格的专论,全篇几乎无一字不是谈引用辞格。
除上述辞格专论外,《练字》《谐隐》中论述了“隐语”“谜语”等辞格,认为好的隐语应该“义欲婉而正,辞欲隐而显”,贵在“理周要务”。《物色》篇讨论了“摹状”“复迭”等辞格:“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所举例子,都是身兼“摹状”“复迭”两种辞格。
刘勰还特别注意文字书写书法的美感作用,《练字》篇认为字形对于修辞的作用与语音对于修辞的作用同样重要,即所谓“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矣”,这是从听觉上和视觉上追求语言的美感。为了追求文章的字形和书写美,刘勰提出“缀字属篇,必须练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要求文章不用诡异的字,相同偏旁部首的字应尽量避免连用,如果实在不可避免,一句之中可用三个联边的字(即“半字同文者”),要权衡重出的字(即“同字相犯”),但是“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这是与刘勰形式服从内容的正确认识一致的,还要注意调整单复(即“字形肥瘠”,笔画多少),不能“瘠字累句”,也不能“肥字积文”,字形的肥瘠要相间,做到“参伍单复,磊落如珠”。只有这样才能在文章书写上给人以视觉享受。我们知道东汉发明了纸张,魏晋之际,书法大家、书法理论相继出现,当时的书籍主要靠手抄,为追求美感,人们必须注意书法和汉字的结构。刘勰要求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除了要考虑文章本身内容和形式的美感以外,还要注意文字书写书法的美观,也就是要求文章写作要声音美、视觉美、感觉美(内容美),在可能的条件下,无一不美。这是一般研究语言文学的理论家不大注意的,不管这种要求是否合理,但它体现了六朝“唯美”的时代风气和刘勰的修辞思想。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应用,书籍文章在文字书写上千篇一律,后世人们也就不再考虑文字书写书法的美感作用了。
三、修辞实践
刘勰是文章学和文学理论大师,也是语言学和修辞学大师,其《文心雕龙》可谓一部语言和修辞宝典。《宗经》篇阐述了刘勰修辞的总标准,他说:“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他将儒家经典视为“群言之祖”和文章之祖,是汉语修辞的楷模,认为“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若征圣宗经以立言,“则文其庶矣”。而对那些不合经典的“纬书”,尽管从内容上斥为“乖道谬典”,但在形式上却赞誉其“词富膏腴”,认为“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辨纬》),体现了刘勰的儒家正统观念及对这种正统观念的某种超越。
刘勰的修辞要求体现在《附会》中:“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刘勰在此尽管说的是“才童学文”,但是,任何人写文章道理都是一样,都要“附词会义”即炼字选词、联句成章来表情达意。他认为写作文章除了必须有“情志”“事义”(思想内容)外,还要讲究“辞采”“宫商”(艺术形式、语言美感),要从文章内容和形式等几个方面来品评文章有无毛病,存优去劣,做到恰到好处,这是构思作文的一般规律。明确指出了汉语修辞的主要内容,包括文章内容和形式的诸多方面(与今天人们一般认为修辞只讲究语言形式有区别,但笔者认为如此则更科学)。《文心雕龙》的语言运用体现了刘勰的修辞主张。
《文心雕龙》还总结了不同文体、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修辞实践。在其 20篇文体论中分别论述了每一种文体的语言运用、修辞准则和技巧(篇幅所限,兹不赘述),《定势》简要概述了一些文体的修辞标准:“是以括囊杂体,功在诠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表明修辞手法的运用不是千篇一律的,应该随势而变,适应文体和内容的需要。《才略》品评上古至刘勰当时作者的文学创作,对各时代的作家作品的语言和修辞也做了简要总结,如:“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辞令华采,可略而详也。虞夏文章……辞义温雅……商周之世……文亦足师……春秋大夫,则修辞骋会……”等等,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修辞面貌;又“魏文之采,洋洋清绮……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等等,表现了不同作家的修辞风格,在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上全面概括考察汉语修辞的总体情况。这些不同时代、不同作家在修辞上各有特色,造成了他们不同的艺术风格。《时序》篇可以说是一篇简略文学史,文学、语言、修辞三位一体,文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语言和修辞的发展,或者说语言和修辞的发展是文学形式发展的标志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说,《时序》篇又可以说是一篇修辞风格简史,正所谓“蔚映十代,辞采九变……质文沿时,崇替在选”。
《指瑕》从反面论述修辞失当的教训,概括地说,修辞瑕疵主要有六类:一、文义失当之瑕;二、比拟不类之瑕;三、字义依稀之瑕;四、语音犯忌之瑕;五、掠人美词之瑕;六、注解谬误之瑕。认为“古来文才,异世争驱: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纤密;而虑动难圆,鲜无瑕病”。具体举出曹植、左思、潘岳的措词不当,崔瑗、向秀的文章比拟不类,这些人文采风流,但在修辞的时候也还存在着一些严重毛病,说明运用修辞必须认真严谨,否则将“斯言一玷,千载弗化”;运用修辞的瑕疵除上述毛病以外,还有用词“依希其旨”,“逐奇失正”,造成词义不明确;“比语求蚩,反语取瑕”,即用谐音字和字词的反切来挑毛病,这是六朝文士卖弄声律的不良后果;刘勰还特别指出修辞(包括文章)贵在独创,反对抄袭剽窃,他说:“制同他文,理宜删革。若掠人美辞,以为己力,宝玉大弓,终非其有。全写则揭箧,傍采则探囊。然世远者太轻(轻薄无德),时同者为尤矣。”这给“文抄公”们敲响了警钟。
《知音》确立了判断修辞效果的标准:“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词,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与《指瑕》篇一起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修辞的原则和要求。
尽管《文心雕龙》是一部理论著作,不能很好地体现刘勰的修辞实践,但它的语言仍极有美感,富有形象性。首先就整部著作的结构来看,《文心雕龙》像一座宫殿,外表规模宏大、金碧辉煌,内部奇珍异宝、流光溢彩。全书自序一篇,总论五篇,文体论二十篇,创作论十九篇,批评论五篇,共同构成一个完整有机而且自足的理论体系;分开来看,五十篇论著又可分别独立,每篇集中论述一个问题。这样环环相扣,珠联璧合,共同支撑起《文心雕龙》的理论大厦,反映出他对整部著作布局谋篇的匠心。
文章句式整齐,几乎全用对偶句,但又根据表达的需要,不完全拘泥于严整的对偶句,读起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富有节奏感、音乐美。字词锤炼,词义句义高度浓缩,巧妙化用前人事迹和言论,内容丰富而又韵味悠长,语言典雅含蓄,又富有说服力;有意识地选用色彩鲜明、形象突出的词语,词句的声律和谐,广泛运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词语,合理利用汉语四声,使文章如行云流水。长句短句、肯定句否定句、主动句被动句、常式句变式句、奇句偶句、单句复句等等各种句式交错使用,服从表达的要求,不拘一格,灵活多变,构成摇曳多姿的视觉、听觉和感觉形象。常见的修辞手法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等在全书几乎俯拾皆是,婉曲、排比、对比、设问、反问、摹状、复迭等后世常用的修辞手法也几乎都能找到,而且运用得恰到好处。总之,《文心雕龙》的语言修辞实践已经涉及到后世修辞的方方面面,是刘勰语言学和修辞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和实际运用,也是汉语语言学和修辞学的典范著作。
四、结 语
魏晋六朝是我国文学艺术的自觉时代,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在这个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各自脱离其他门类开始独立成为一个学科。汉语修辞学体系的建立可谓生逢其时。三曹、七子、陆机、挚虞、李充、钟嵘、萧统等文学家开始了对文学理论和文章创作理论自觉的探讨,成就引人注目,尽管他们的研究“各照隅隙,鲜观衢路……并未能振叶而寻根,观澜而索源”,但他们都在各自的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理论研究无一例外都必须建立在科学的语言研究和修辞研究的基础之上,他们对文学、语言、修辞的研究为《文心雕龙》的全面研究作了铺垫、准备了条件。
《文心雕龙》在汉语修辞学研究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其修辞学理论、辞格研究、修辞实践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已经全面建立起了汉语修辞学的理论体系,直到今天,汉语修辞和修辞学研究,仍然没有超出这个理论框架。可能由于其震古铄今、光辉灿烂的文学理论和文章创作理论的成就遮掩了其语言学和修辞学的价值,一直以来人们对《文心雕龙》的语言学和修辞学成就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上述有关汉语修辞的问题在文学理论家的心目中又都往往视为艺术表现手法,大多从文艺美学的角度而不从语言角度进行分析研究,这是令人遗憾的。
文学理论、语言研究、修辞研究三位一体、密不可分,《文心雕龙》在建立起它的文学理论和文章创作论体系的同时,也建立起了它的语言学和修辞学的理论体系。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文心雕龙》的每一个篇章都论述了语言和修辞问题,这是应该引起语言研究者注意的。
研究《文心雕龙》的修辞学,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古时期汉语和汉语修辞的现状和成就,了解汉语和汉语修辞的历史和发展。如果没有对《文心雕龙》的语言学和修辞学全面深入的研究,这将是“龙学”研究的严重缺陷,这样建立起来的汉语语言学史和汉语修辞学史,也是很不全面的。
[1]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2] 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
[3] 陈会兵.儒家经典和诸子著作的语言学思想[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3(4):61-65.
[4] 陈会兵.虚词在先秦诗歌里的修辞作用[J].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3(4):39-41.
[5] 李裕政.文笔之辨研究述略[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2):43-46.
[6] 论《文心雕龙》的生命化批评[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S1):77-78.
(责任编辑:郑宗荣)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hetoric System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Rhetoric Theory Study of Wen Xin Diao Long
CHEN Huibing SUN Ting LIU Wenya
(College of Arts,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4020, China)
Wen Xin Diao Long is not only the first classical book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ssay writing in China, but also the initial book on Chinese rhetoric theory. Its rhetoric theory, researches of figures of speech, and practices of Chinese rhetoric are all the symbols of that era. It was this book that first constructed the rhetoric system of Chinese language as well as set a pattern for figures of speech researches.
Wen Xin Diao Long; rhetoric theory; figures of speech research; practice of rhetoric; construction of rhetoric system
H15
A
1009-8135(2017)03-0060-07
2017-02-28
陈会兵(1967—),男,重庆奉节人,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汉语史和古典文献。
孙 婷(1993—),女,重庆云阳人,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在读硕士生。
刘文亚(1986—),女,河南邓州人,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在读硕士生。
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类课程‘3+1’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142024);重庆三峡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应用技术大学转型条件下汉语类课程教学内容、模式的改革与实践”(GJ15070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