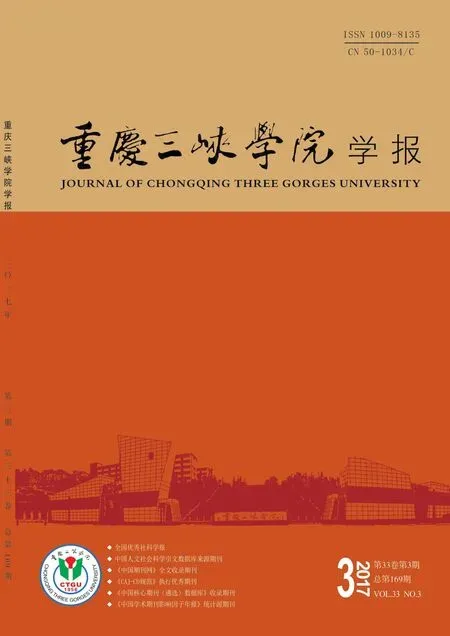朱大枬新诗观念探究
——以佚作《读〈蕙的风〉》《诗的意境》为中心
李朝平周长慧
(1.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重庆 404020)
(2.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241)
朱大枬新诗观念探究
——以佚作《读〈蕙的风〉》《诗的意境》为中心
李朝平1,2周长慧1
(1.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重庆 404020)
(2.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241)
1920年代初汪静之《蕙的风》曾引发一场著名的文艺论战,朱大枬《读〈蕙的风〉》亦参与其间,却长期被遗忘。文章在还原历史现场、钩沉佚文的同时,以《读〈蕙的风〉》和《诗的意境》为中心,重点探究了朱大枬的新诗观念。其本位主义文学立场、古典与现代交融的新诗本质观、有机谐和的美学观与诗性语言观以及主张新诗小说化、戏剧化的技法论自成体系、颇具特色,是对新诗理论的重要补充。
朱大枬;佚文;《蕙的风》论争;新诗观念
如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朱大枬 24岁便已陨落,成为新月派又一位英年早逝的诗人,此后长期被埋没。作为《晨报•诗镌》上的重要诗人之一,其诗曾被朱自清列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中,可谓一时之选。诗风幽晦玄妙,是前期新月诗派中最富现代主义气息的诗人。朱大枬文学兴趣广泛,举凡新诗、小说、杂文、翻译等皆有尝试及创获,论诗亦颇具心得。目前共辑得诗论若干,它们散布于民国报刊间,迄今无人问津[1]。其中《读〈蕙的风〉》最能体现其诗歌理念,它既是书评,又关涉一场文艺论战,其理论光华也因这次论战而闪现。
一、一场文艺论战的潜在参与
《蕙的风》是湖畔派诗人汪静之1922年8月出版的一部个人诗集。因新诗诞生不久,当时个人诗集不多见,仅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及郭沫若的《女神》等几部,故《蕙的风》之印行可谓文坛盛事。周作人亲笔封面题字在前,朱自清、胡适、刘延陵等名家作序殿后。胡适盛赞其诗具有“新鲜风味”,驱散了初期新诗中“旧诗词的鬼影”。但两个月后却遭到其同乡——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的严厉批评,在《读了汪静之君〈蕙的风〉以后》中,他秉持“温柔敦厚”“蕴蓄雅致”的诗学观念,从读者接受角度指责汪诗“堕落轻薄”“纤巧”,会产生道德上的弊害。他说:“这种兽性冲动的话,只令读者觉其肉麻;血气方刚的读者看了,又受一番诱惑。可怜不知加添了多少青年男女的罪恶。天真烂漫的年青人们还以为‘文人无行’是常事,是荣耀的事;不然《蕙的风》集子里何以尽载些这样的诗,还有中学的教员,新诗的努力者,大学的教授,全国景仰的学者,替他做序呢?辩护呢?”[2]234-243在论诗的同时,胡梦华还顺带批评了几位序作者。这篇文章很快便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文艺论争。针对胡梦华的保守立场,事隔一周,章洪熙率先发难:“诗是一件事,道德又是一件事;诗只有好不好,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诗是情的流露,也无所谓道德不道德。”[3]114曦洁则着力驳斥其“模仿”说,而力陈创造之于诗的重要性[4]124-126。于守璐在与胡梦华的往复辩论中,所持观点与章、曦基本一致[5]116-118,145-150。几乎与章洪熙同时,周作人在《晨报副刊》“文艺谈”中发表了《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他引经据典地论证伟大作家笔下不乏性爱描写,描写性爱并非不道德,而“凭了道德或法律的神圣的名去干涉艺术,都是法利赛人的行为”[6]。鲁迅在静观这场论战后,对胡梦华开始“不以为然”起来,他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中写道:“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7]宗白华则以“纯洁天真,活泼乐生的少年气象”[8]151-153来礼赞他。
综观这场绵延近三月的文艺论争,新文学的重要开拓者鲁迅、周作人等悉数登场,胡适和刘延陵也间接卷入其中。在这场车轮战中,双方实力悬殊,胡梦华几成孤军奋战之势,四面楚歌。虽然胡梦华一再申明自己并非“中庸道德家”,但在关于旧道德与新文学关系的焦点论争中,他还是被视作方巾气息浓郁的道学家典型,成为众矢之的。众所周知,在新文学发轫期,曾有过几次著名的新旧文学论战,如与林纾的论战,与学衡派、甲寅派的论战等。与之相较,《蕙的风》触发的论战虽规模较小,但性质如一,都是在为新文学鸣锣开道、扫清障碍。在浓烈硝烟中,多了几分意气用事,少了些许平和理性。但每个历史时刻总会有那么一两位清醒者,他们往往能做出更为客观理性的评判。在1923年1月,朱大枬便扮演了如是角色。历史地看,他也应是这场论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史学家们似乎早已将他忘却,即便搜罗备至的《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也不见《读〈蕙的风〉》之踪影。
《读〈蕙的风〉》作于1923年1月27日,临近论战尾声。从时间上看,朱大枬似乎具备通观全局、横评各方的优势,但事实上,囿于各种条件,当时他可能并未充分掌握各方论辩资料,其批评的对象仅限于《蕙的风》及书前几则序言,且主要是胡适的序。他说:“老人常说颓唐的话,小孩常说毫无禁忌的话,不假思索的话;老人的精神是衰颓的,小孩的精神是天真的,活泼的。《蕙的风》的幼稚风味,不是天真的活泼的风味,只是胡说的风味。总而言之,别人批评《蕙的风》的好处,只有新鲜和幼稚两种风味,但是他的这两种风味我都不取啊!”这段文字旨在批评胡适对汪静之“稚气”“新鲜”诗风的推崇,胡适的原话是:“他的诗有时未免有些稚气,然而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况且稚气总是充满着一种新鲜风味,往往有我们自命‘老气’的人万想不到的新鲜风味。”又比如:“对于汪静之的诗,我确以为有不道德的嫌疑。”这也是对胡适观点“成见是人人都不能免的;也许有人觉得静之的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的回应。《读〈蕙的风〉》中的辩驳大约仅此两处,而更多笔墨则是倾注在诗歌本身的品评上。纵然旨在单纯发表自我感悟,但也已不自觉地卷入了这场论战,与上述诸家构成了事实上的潜在对话关系。
二、朱大枬的新诗观念
那么,朱大枬与上述诸家究竟构成了怎样的对话关系呢?其诗歌观念有无卓越特异之处呢?通过对《读〈蕙的风〉》及《诗的意境》的具体分析便可获知一二。
(一)本位主义文学立场
《蕙的风》中情诗占绝对比重,胡梦华统统将其视作“淫业底广告”,主张“要于抒写恋爱之中,而勿为反善德的论调,以致破坏人性的天真,引导人走上罪恶之路”。他从情诗联想到的是道德教化,认为这些“露骨”的描写会诲淫诲盗,诱导血气未定的青年犯罪,进而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体现了注重伦理效果,以温柔敦厚为主旨的传统诗教观念。也正因如此,在当时他被当作保守势力群起而攻之。同样批评《蕙的风》中的情诗,与胡梦华的伦理学进路不同,朱大枬则是从题材角度予以评判:“诗是抒情的文学,这是人人所能承认的。但是这个‘情’是泛言情感的情,并不是专属爱情的情,更不是专指男女间爱情的情。读汪静之的诗以后,看他诗里所描写的差不多尽是男女间恋爱的事情,不然便隐藏着恋爱的意思。就看描写几件无生命的东西,也要把他们当作人们的男女一般,互相的爱着,拥着,吻着……”他认为情感具有广域性,“不是专指男女间爱情”。换言之,举凡亲情、友情及国家民族情感等皆应囊括其中。虽然追求恋爱自由是挣脱传统礼教束缚的表现,也具有个性解放的意义;长期被抑制的情欲在一朝释放后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势必起到摧枯拉朽的作用。然而,题材的单调总会给人以“重复的厌烦”之感,且会在自我封闭中与现实脱节、与民众隔膜。所以,主张拓宽文学题材领域的实质是期待青年作家能从儿女私情中挣脱出来、从象牙塔中走出来,将目光投向广阔的社会现实,从而创作出更具现实意义、更忠实于人生的作品。朱大枬说:“现在的新诗却多以两性的恋爱为材料,不过在《蕙的风》里,尤其描写得多罢了。”五四前后,文学重心曾一度向爱情倾斜,不特新诗如此。茅盾对1921年4—6月的创作情况进行统计后发现:在120多篇小说和戏剧中,“描写男女恋爱的小说占了百分之九十八”。他不无忧虑地感叹道:“一般青年对于社会上各种问题还不能提起精神注意……而只有跟着性欲本能而来的又是切身的恋爱问题能刺激他们……特流于强烈的享乐主义的倾向。”[9]这也应和着朱大枬的感叹:“然而这种‘接吻的文学’究竟有什么意思?”
可见,同样是评价汪静之的情诗,朱大枬刻意于诗歌题材的拓展以及诗人情怀、抱负的扩大,而不是如胡梦华一般倚重伦理道德尺度。所以,他认为“诗的好坏不能以道德不道德来判定,不道德的诗也有称得起好诗的”。基于文学本位立场,他将以善为宗旨的道德和以美为鹄的的文学截然分开,凸显文学的独立性。这与章洪熙的论调不谋而合:“诗是一件事,道德又是一件事;诗只有好不好,没有什么道德不道德。”这种超功利的文学理念除得益于道家美学观外,更多受惠于西方。自康德提出“审美无利害”观念后,西方便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审美为核心、强调文艺独立自足性的理论潮流。当这股潮流经王国维等人引入中土后,便在众声喧哗的多元格局中潜滋暗长,影响了不少后之来者,朱大枬、章洪熙应是其中之一。
胡适显然也不接受人们对《蕙的风》的道德宣判,但其出发点、立场与朱大枬一致吗?他在序言中写道:“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成见是最容易错误的,道德的观念是容易变迁的。”[10]14胡适秉持一贯的进化论思想,认为道德循时而变、古今各异。人们若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指斥新诗,便是“错误的”“成见”。换言之,看待汪静之的这类情诗,须换用一套现代的伦理道德眼光。很明显,胡适的论点并非建立在文学与道德的分离上,而是基于二者的统一。这便是他与朱大枬的和而不同处,朱大枬秉持的是一种主张文学独立的近代观念,与儒家诗教及实用主义文学观相去甚远。
(二)古典与现代交融的新诗本质观
早在他登上诗坛的几年前,新诗的革新运动便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当时的先驱者意识到,因受谨严格律的束缚,旧诗已无法容纳现代“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更无法发挥反抗封建思想、塑造现代人生、参与时代变革的作用。于是,从形式与内容的互动关系出发,胡适等人便以“诗体的解放”为突破口,吹响了诗界革命的号角,甚至提出了“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应当说,对于新诗的发展而言,形式的革新(自由体取代格律体)包括语言载体的革新(白话取代文言)固然是十分重要的,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作诗如作文”的主张会模糊诗与散文之间的文类界限,进而弱化新诗特质。早期白话诗虽顺应了时代需求,增强了社会介入力,但诗质稀薄、想象贫弱、情感苍白又成为先天痼疾。许多诗只是散文的分行书写而已。“作诗如作文”的策略在推进诗歌革新的同时也埋下了诸多隐患,那些隐患甚至是解构性的。对新诗特质的漠视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时人无疑有所警惕,如康白情在《新诗底我见》中说:“诗和散文,本没有什么形式的分别,不过主情为诗底特质。”[11]他将“主情”视作新诗特质所在。纵然如此,却未能匡救时弊,枯燥说理、冷漠写实的作品如雨后春笋,就连他自己的诗作亦未能幸免,饱受后世诟病。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以及文学本位主义立场,有感于白话诗草创期的艺术失范,朱大枬才在《读〈蕙的风〉》和《诗的意境》中陈述了他对新诗本质的看法。类似于康白情,他也认为“诗是抒情的文学”和“主观的文学”,即“抒情”并非一种泛泛的表达方式,而是文类区分的重要标尺。但他的论述更为精细:“诗里切不可闯入文的意境,我们很讨厌旧诗里面的甚么咏史诗,颂圣诗,说理诗,应酬诗,当然是用文的意境作诗的缘故;他们若能老老实实的写成散文,也自有他的地位。”诗职司抒情,而“咏史”“说理”“应酬”等则为散文专属。诗须谨守诗与散文之间的文类规范,不可越界,否则会导致非诗化。以情感为中心的诗歌观念是人本主义与个性主义思潮的产物,正如林以亮在《诗与情感》中所言:“拿情感在诗中所发生的作用,估计得这么高和重要,甚至认为没有情感就不是诗,还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盛行以后的事。”[12]78换言之,朱大枬的诗学观念深受西方濡染。不过,当时鼓吹“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成员也是“情感至上主义者”,郭沫若认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为诗。”[13]60创造社的理论旗手成仿吾更是理直气壮地宣称:“文学是直诉于我们的感情,而不是刺激我们的理智的创造,文艺的玩赏是感情与感情的融洽,而不是理智与理智的折冲;文学的目的是对于一种心或物的现象之情感的传达,而不是关于他的理智的报告。”[14]69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西方影响,朱大枬的诗歌本质观都具有现代气韵,当然也有对“诗缘情”传统的遥远致意。但朱大枬并未止步于此,他认为仅凭抽象的情感还难以确保诗意的生成,必须将“抽象的情感用具体表现出来”,因为“诗重具体而忌抽象”。这就切中了诗歌乃至文学重形象的本质,同时也体现了意象主义和浪漫主义诗学的有机结合。论及朱大枬对古典诗学的传承,最明显莫过于他在《诗的意境》中所持论调:“我想情和景是融化的调和的在诗的意境内。作诗要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无情感的写景诗便呆板了而不流动,无景物的抒情诗容易失之于太主观而不真切。”“意境”“情景交融”均属古典诗论术语,而朱大枬却充分运用这些术语来界定、品鉴新诗。与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姿态不同,朱大枬采取了一种更为客观稳健的方式对待古典文化。因此,有理由认为朱大枬的“抒情”与“意境”并重的诗歌本质观确是中西融会的产物。
(三)有机谐和的美学观与诗性语言观
五四前后,外文入诗为一时之尚,大家争相尝试。如朱自清的《睡吧,小小的人》、郭沫若《天狗》《雪朝》《无烟煤》《三个泛神论者》、王独清的《我从cafe中出来》等或多或少都嵌入了外国字。汪静之《蕙的风》也存在类似情形。朱大枬对这种语言夹杂的状况颇不赞成,在《读〈蕙的风〉》中进行了批评。其实,朱大枬一直都很关注这个现象,对汪静之的批评仅为发端。几个月后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杂感《新“某生”体》,专门抨击用外国字代替“本名”的行为,并戏称为“新某生体”。此文旋即招致梁实秋的驳斥,于是,一场笔战拉开了帷幕。双方各有支持者,蹇先艾、赵景深及郑兆松等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间,纷纷著文彼此攻伐[1]。因前后两事颇具内在关联,故可将它们合而观之,以探其文艺主张。
首先,从声音层面出发,他认为外文入诗会破坏诗歌的乐感。“因为诗是可歌的,假设中间夹有外国字,我们能够歌唱么?就是能歌唱,歌唱起来能够悦耳么?”朱大枬比较注重诗歌的整体音韵效果,这种有机观念近于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的论调:“诗的语言是一种声音的言说,是为了特别的美学目的而组织起来的。”[15]43他不仅要求诗歌能唱,而且还要“悦耳”。但若诗中嵌进了外文,两类文字的错杂就会破坏自然、谐和的整体效果。他曾明确推崇“自然的音节”,十分歆羡康白情《疑问》中“滴滴清泉”的调子。为实现整体谐和,他甚至将字词的推敲与布置推向极致,颇具苦吟色彩。如其名篇《笑》:“赤霞纱里跳着一炷笑/……翠羽湖里摇着一朵笑/……青铜鞘里跃着一柄笑”,几乎无一字可更易。汉字的运用尚如此讲究,何况外文了。在他看来,外文入诗势必破坏作品的有机性与统一感。因此,反对外文入诗便体现了他自然谐和与有机统一并重的诗歌观念。
其次,从艺术表现力角度出发,他认为外国字嵌入作品会使文学的“具体性”受损。“文艺作者的任务,是不是要予读者以极明确的观感?是不是要把他所描写的极灵活的表现在纸上?若然,‘新某生体’的作品这两点是否尽做了?M,P,S,T能否极明确活现的告诉读者这篇小说里面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前已述及,朱大枬一直主张“诗重具体而忌抽象”。经由对“诗”及“小说”的体察,一项文学通则呼之欲出。朱大枬认为若用外文字母来替换“本名”,就会缺乏“明确的观感”和“灵活的表现”,显得特别抽象,连切实之感都无法产生,遑论意义的生成或联想。因为文学作品中的地名、人名等并非纯粹的指称代号,而是附着了特定的意涵和功用。所以有人说:“人物的命名应该是作家艺术构思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刻划人物形象的正当的艺术手段。”[16]比如曹雪芹笔下的贾雨村、甄士隐,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夏瑜等便是明证。深一层看,文学作品中的命名因受文学语言机制的规约,应当具备文学语言的基本特性。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科学语言的重要区别便在于它的非指称性,按照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的说法,文学语言与其他语言并无质的不同,它是“诗式功能居于主导,就是排除或抑低指称功能的结果”。而“‘诗式功能’即信息指向自身”[17]169-170,托马舍夫斯基说得更明确:“在日常生活中,词语通常是传递消息的手段,即具有交际功能……文学作品则不然……比起日常实用语言来,它更加重视表现本身。”[18]83“M,P,S,T”只是一组信码,仅能起到信息区分的作用,还不具备“表现本身”的功能,故属非文学语言,毫无文学性可言。这才是朱大枬否定用外文字母替代本名之深意。据此反观,我们发现朱大枬是在竭力捍卫语言的文学性,以便尽量增强作品的文学浓度。而这种以文学性为主导的语言观正是所谓的诗性语言观。
(四)主张新诗小说化、戏剧化的技法论
虽然在新诗草创期便已出现小说入诗、戏剧入诗的情形,比如胡适《人力车夫》、刘半农《卖萝卜人》以及戴季陶《懒惰》等,但综观1923年以前的诗论,尚无人对此进行理论探索,朱大枬的垦拓行为便难能可贵了。朱大枬在《读〈蕙的风〉》中写道:“从前有句话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我以为诗中也有小说,像杜甫的《上山采蘼芜》和《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和《新丰折臂翁》都可以说是很好的短篇小说。”然后具体评点了汪静之的《我俩》,认为该诗“也带点小说的写法”,并与徐振亚的《燕雁离魂记》进行了情节对照。由上述引文可知,朱大枬是从诗画关系展开论述的。“诗中有画”侧重于诗歌的画面效果,属意象营构范畴,主要包括设色与构图两方面,如康白情的《江南》:“只是雪不大了,/颜色还染得鲜艳。/赭白的山,/油碧的水,/佛头青的胡豆。”这是一节标准的绘景诗,远近层次分明、颜色搭配清新,读之若身临其境,但视觉性、空间性与静态性在赋予诗歌以质感的同时也有其鞭长莫及处,当诗人欲呈现更加生动直观的情境或处理叙事类题材时,仅凭画面感便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而小说或戏剧方式的运用能在画面感之外增添听觉性、时间性及动态性元素。这类叙事性元素的融入在拓展诗歌表现空间的同时也能极大提升诗歌的表现力,尤能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即以朱大枬评点的《我俩》而论,这首诗讲述了一对男女青年自由婚恋的失败。读者既能看到他们嬉戏、亲昵的画面,又能听闻二人情意缠绵的对白,伴随情节发展的还有人物的心理景深。笔触诗意斑斓、形象栩栩如生、命运历历在目,较之单纯的画面呈现,自然更能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这种以诗意和情感为旨归、以对白和情节为手腕的技巧正是朱大枬所谓的“小说的写法”。
单就对白而论,其实,对白不唯小说独具,更为戏剧之长。因此,对白到底还是一种戏剧性手法。就诗论诗,对白也并非叙事诗专属,在现代派诗中它又是营造“戏剧性处境”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开风气者有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艾略特等。影响所及,在中国,历经20年代闻一多、徐志摩的尝试,30年代卞之琳的推波助澜,到了40年代,九叶诗人已将其发扬光大,并结出了理论硕果——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不过,同样采用戏剧化对白形式,以“戏剧性处境”为核心的诗歌往往追求“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19],与叙事诗所要达到的艺术效果不同。虽然朱大枬对上述方面仅点到即止,但无论从叙事诗还是从“戏剧性处境”的角度考量,他所关切的以对白和情节为中心的“小说的写法”在现代新诗理论上都具有一定的垦拓意义。
三、结 语
20世纪20年代初,围绕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曾展开的这场文艺论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参战各方文字后来基本收入了王训昭辑录的《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唯独不见朱大枬《读〈蕙的风〉》。与其余诸家取径不同,《读〈蕙的风〉》突破了文学与道德的论辩焦点,不一味吹捧或鞭笞,而是基于文学本位立场衍生出独特的新诗本质观、语言观和技法论,在一个系统性框架中参与对话。相对而言,《读〈蕙的风〉》的论析显得更为客观理性、立场更为纯正地道、视野更为宽广宏阔,某些理论主张甚至还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而《诗的意境》是其姊妹篇,彼此支援,相互阐发。因此,二者俱为新诗理论史上的重要佚文,值得充分重视。
[1] 李朝平.新月派诗人朱大枬生平及著译简表[J].新文学史料,2016(3):191-199.
[2] 胡梦华,吴淑贞.表现的鉴赏[M].上海:现代书局,1928.
[3] 章洪熙.《蕙的风》与道德问题——问胡梦华君[M]//王训昭.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4] 曦洁.诗的模仿的问题[G]//王训昭.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5] 于守璐.与胡梦华讨论新诗,答胡梦华君——关于《蕙的风的批评》[G]//王训昭.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6] 作人.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N].晨报副刊,1922-11-1.
[7] 风声.反对“含泪”的批评家[N].晨报副刊,1922-11-17.
[8] 宗白华.《蕙的风》的赞扬者[G]//王训昭.湖畔诗社评论资料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9] 郎损.评四五六月的创作[J].小说月报,1921(8):1-4.
[10] 胡适.胡序.汪静之.蕙的风[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
[11] 康白情.新诗底我见(有引)[J].少年中国,1920(9):2.
[12] 林以亮.诗与情感[M].台北:大林出版社,1982.
[13] 郭沫若.论诗三札[M]//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14] 成仿吾.诗之防御战[M]//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15] 汪正龙.西方形式美学问题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6] 傅继馥.《红楼梦》人物命名的艺术[J].红楼梦学刊,1980(2):221.
[17] 赵毅衡.《语言学与诗学》编者按[M]//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18] 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艺术语与实用语[G]//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19] 袁可嘉.新诗戏剧化[J].诗创造,1948(12):3.
[20] 鄢冬.当代诗歌情感空间的两种表征范式[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5(1):142-146.
(责任编辑:郑宗荣)
附:朱大枬佚文辑录
读《蕙的风》①载1923年2月10日《爝火》第1期,署名一苇,标题后括号内所标文体为“批评”。
诗的革命到现在不过才四年的功夫,成绩却很可观了。个人的诗集——据我所知道的——已经出版了七种,就是《尝试集》《冬夜》《草儿》《女神》《蕙的风》《将来之花园》《红蔷薇》。其余如像《雪朝》和《湖畔》,前者是朱自清……等八人的诗集,后者是修人……等四人的诗集。选集的诗有《新诗年选》和《新诗三百首》二种。关于诗的杂志,有中华书局出版的《诗》一种。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如许的成绩,我们先不必问他的本质如何;只就这一点看来,中国文学界的新诗坛已经很可乐观的了。
诗是主观的文学,批评也是主观的作品;加以我学问的肤浅,识见的薄弱,不知道要弄出许多的错误来。所以我不敢轻易说这篇就是批评,只把他当做读后的感想,或者还能见谅于读者罢。
诗是抒情的文学,这是人人所能承认的。但是这个“情”是泛言情感的情,并不是专属爱情的情,更不是专指男女间爱情的情。读了汪静之的诗以后,看他诗里所描写的差不多尽是男女间恋爱的事情;不然便隐藏着恋爱的意思。就看描写几件无生命的东西,也要把他们当作人们的男女一般,互相的爱着,拥着,吻着……。像下面的一首诗:
浪儿张开他底手腕,/一叠一叠滚滚地拥挤着,/搂着沙儿怪亲密地吻着。/……/他抱着那靠近沙边的小石塔,/更亲密地用力接吻了。②因版面所限,原分行排列的诗句改用分隔符间断。下同。
偶然用拟人的方法,把诗那样地描写出来,本不足奇怪。不过不论一个什么风景,一个什么东西,一到他的眼里,做出来的诗就都是那样描写。不道德的嫌疑,固然可以说没有,重复的厌烦已经给与读者了。
我有一个诙谐的譬喻,读汪静之的诗好像在看外国爱情片的电影,时常看着在拥抱,也时常看着在接吻。我又记得有一个故事:“有一个腐败的老学究,一天带着他的夫人到影戏场去看电影,每看到两个人——一男一女——拥抱着在接吻的时候,他就急忙用手把伊的眼睛遮住。伊看了没有好久的功夫,眼睛却被遮住了十余次了。”我们虽不至于像老学究那样顽固,也不必像他那样顽固;然而这种“接吻的文学”究竟有什么意思?
我推测汪静之的心理,一定以为做诗除了描写恋爱,就没有好材料;除了接吻,就不足表示恋爱。下面我还抄他几处,来证明他诗集里描写接吻的繁多。
我吻了我手上的影。(《竹影》)我每每乘无人看见,/偷与你亲吻。(《我俩》)那夜的亲吻异常甜蜜!/到于今还甜蜜!/哦!到死后还甜蜜呵!(我俩)我底歌吻着伊,/我底歌吻着我。(《愉快底歌》)琴声恋着红叶,/亲了个永久甜蜜的嘴。(《恋爱的甜蜜》)你知道我在接吻你赠我的诗么?/知道我把你的诗咬了几句吃到了心里了么?(《别情》)我昨夜梦着和你亲嘴,/甜蜜不过的嘴啊!/醒来却不有你底嘴了;/望你把你梦中的那花苞似的嘴寄来吧。(《别情》)后来一飞飞到初开的花里,/他和花蕊接吻十分和畅。(《蝶儿与玫瑰》)他俩情投意合,/紧抱尽情甜蜜地接吻。(《乐园》)湖儿充满热烈的爱,/……/与他不息地接吻着。(《微笑的西湖》)露水与你接吻,/你脸上就透出了新胭脂了。(《微笑的西湖》)喜时没有你吻着了。(《送你去后》)
上面所引的,描写景物的也有,因人而及于物的也有,纯粹描写人的也有。只要读过一到,就都能辨认出来,所以我也不细细的分明述说了。
D字样的月儿独自来拜访/我逛着S形的草路。(《西湖杂诗》十五)
外国字入诗,在近来很盛行的。郭沫若的诗常常有英国字。这件事情我不很赞成,因为诗不是专给又懂中文又懂外国文的人看的,假若不懂外国文的人看了,看到外国字的地方,他怎能读得下去?既不能读下去,看到外国字的地方,又怎能领略得其中的意味呢?用外国文字母入诗,比较还要好点,因为像上面的D和S两个字母,跟中国卐字的意思差不多。——这个卐字本来也不是中国原有的字,也是由外国流传来呢。——虽是不懂外国文的人也还看得下去,意义却也揣想得出来,所以比较可用;却是还不能放情地唱啊,所以也不可随意乱用。非到描写极困难,或无法描写的时候,才借来补救。其实用外国字入诗,并不是表示自己的兼通中西,只是显出自己的能力不济;不能用本国的文字表现出来,才借外国文来掩饰。
用外国文入诗也不是绝对禁止的,不过当我们要用外国文入诗之前,先要问问自己:这首诗里有用外国文的必要么?能不能够用本国字代替他(它)?用了本国字来代替,是不是不恰当?若是可以用很恰当的本国字来代替,就不必用外国文了。若是实在寻不着相当的本国字,那只好用外国文。但不可直接写入行里,因为诗是可歌的,假设中间夹有外国字,我们能够歌唱么?就是能歌唱,歌唱起来能够悦耳么?还有那不认识外国字的人,又待怎样呢?用外国文入诗,最好翻译出他的意义,或读音,把原字用夹注号附在后面,或者用星点把原字写在那首诗的后面;对于读者的诵读或歌唱既没有妨碍,作者自己的意思也不至于有丝毫走失了。
D和S读音都很简单,所以插在中文里还勉强可以读下去,只是对于不识洋字的有点不便罢了。
从前有句话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我以为诗中也有小说,像杜甫的《上山采蘼芜》和《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和《新丰折臂翁》都可以说是很好的短篇小说。像《蕙的风》里《我俩》一首,也带点小说的写法。
我生平最不能忘的一次——/我年十五你十三,——/你底姆妈微笑对你说:/“我的娇娇,今夜和哥哥同睡眠。”/那时你还不懂得什么,/我俩只互相受着影响罢了。/……(《我俩》)
后面描写他们八字的不合,婚姻的失败,越发像是小说。我记得在《快活》里看见有一篇长篇哀情小说,似乎是叫做《燕雁离魂记》,中间也写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只差没有亲吻,异常甜蜜的亲吻。我不想蝴蝶式小说家的心理,却与这新诗人不谋而合。
《西湖小诗》觉得幼稚一点,却也诚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有点新鲜风味。一共分十七首,大都是用拟人法描写。
娇艳的春光映近灵隐寺,/和尚们压死的爱情,/于今压不住而沸着了:/悔煞不该出家啊!(《西湖小诗十一》)
这首诗不知道果然道破了灵隐寺僧人的心理没有,不然汪静之还有一个捏造和污蔑的罪名,或者也应该得一个太武断的责罚。但说谎是道学老夫子深恶痛绝的事情,在诗人却是一种很普通不足为怪的常事;就是武断也是诗人所不能免。所以我读了这首诗,总不觉得他说诳,也不觉得他武断;只觉得他一语道破了僧人无意识的生活,说得很是痛快。只是过于浮露点,不能算很含蓄的小诗。
汪静之的短诗顶短有一句一首的,像下面的四首:
偏偏不许我没有烦闷的长夜啊!(《长夜》)不息地燃烧着的相思啊!(《在相思里》三)朝阳里骄傲地愤怒地放着奇香之花啊。(《欣羡》)用热泪洒活暴徒底良心呀。(《孤傲的小草》)
现在的新诗与旧诗不同的地方,最显著的可以说是不押韵。须知道无韵并不是新诗的好处。胡适他们也常常说过,新诗虽然是没①原文如此,此处疑缺一“韵”字。诗,也要有自然的音节。像康白情的诗:
滴滴清泉,/听听他滴的是什么调子。(《疑问》)
这首诗里“泉”字和“子”字并不押韵,但读起来音节是怎样的谐和?知道这首诗的好处,就知道自然音节在新诗里的重要。上面这首短诗,虽然很短,却也有两句,所以能够有自然的音节;一句一首的诗,读着总难有好联(“联”应为“听”)的调子。
诗要有很复杂的情感,一句的诗怎能尽致的描写出来?把很复杂的情感硬要缩短装成一句,岂不太牵强了,像《欣羡》一首读着就觉得有点局促。
再看他有三首结尾都是“啊”字,一首结尾是“呀”字,看来好像是举的文法里惊叹句子的例一样。
新诗方实行的时候,多是以劳动问题阶级制度……为材料,像胡适之刘半农和沈尹默的《人力车夫》,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学徒苦》……都是。现在的新诗却多以两性的恋爱为材料,不过在《蕙的风》里,尤其描写得多罢了。所以我们从前所赞赏的古诗,多是《卖炭翁》《石壕吏》《兵车行》……诸首。直到现在,这种趋向还尚未泯没;但是将来我们所崇拜的古诗,一定会改变的。这种变革是好是坏,我不敢说。不过这种情形若给那些头脑冬烘的顽固先生知道,一定要摇头摆脑地叹道:“世风不古,……先王之道不存。……诗尚诲淫。哀哉!”
对于汪静之的诗,我确以为有不道德的嫌疑。不过诗的好坏不能以道德不道德来判定,不道德的诗也有称得起好诗的;我这里是谈诗,不是评人,所以关于道德不道德的问题,也不多谈了。汪静之的情诗里面却也有好诗,但是有些太亵,有些太泛,有些太露,很完美的诗却也少得很。像第二首《定情花》的确是一首仔细斟酌过的诗,写情也还写得恰到好处;不像《我俩》的狂浪,《窗外一瞥》的肤浅,《祷告》的秽亵。
我每夜临睡时,/跪向挂在帐上的“白莲图”说:/白莲姊姊啊!/当我梦中和我底爱人欢会时,/请你吐洗清香薰着我俩罢。(《祷告》)
“欢会”二字固然能当着“很欢喜地会着”讲,不过这两个字普通的讲法是怎样,读着总有点肉麻。
伊底情丝和我的,/织成快乐的幕了;/把它当遮拦,/谢绝人间的苦恼。(《谢绝》)
这首诗简短而含蓄,抽象的情感用具体表现出来,所以狠(“狠”应为“很”)好。
《蕙的风》里也有写劳动问题及阶级制度的诗。
辛苦的轿夫搬运着上等人,/抬得汗流气喘了。/沿路都是叫化子的悲痛之呼声,/我底听觉实在不忍领受呀!/上等人瞥也懒瞥他们一瞥,/只不过丢些铜钱罢了。/我探探袋里还有几个大,/不由得不掬给了他们。/我又问问自己底心:/这就算你发慈善心么?/就算是你救苦命么?/你想用钱驱逐他们勿来扰你么?/你想买他们勿做厌耳之声么?/他们明天又没饭吃了,/你天天有的供给他们么?/无量数的苦百姓,/你能去了他们个个底苦么?/你肯牺牲你底必须——非裕余——的一切么?/这一问问得我好不难过!/我底眼痴呆呆地起来了,/脚慢钝钝地起来了。(《西湖杂诗九》)
这首诗就是抽象的事实用抽象的手腕描写出来。前半“搬运”“领受”几字,还用得不错。中间一共就有七八个抽象的问题,所以不能够深刻地感动读者。
下面一首也是写劳动的,但是写法却又不同了。这首的前半还是写的事实,固然是用具体的描写;后半写的是抽象的感想,也是具体地很委婉地描写出来。
暴雨密密地,/向着田中的农夫打击。/他劳得遍身是汗,/淋漓得雨和汗都分不出。/我特为他祈祷://上帝呀!请你降福给他——/你给他的雨点汗滴,/请变为珍珠的米粒给他!(《暴雨》)
读完这首诗与前首诗比较,究竟哪首感人些呢?哪首感人深刻些?
总起来说,《蕙的风》里也有几首好诗,但是有些作品太幼稚,有些太秽亵,有些太浮泛,有些太肤浅,有些太平庸,有些太神秘,除了很多的糟粕,精华实在很少。但是那些不好的诗,不是因为他①原文如此,本文后面几个“他”皆为“它”之误。太长了;长诗也有好的,像《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等诗,谁不承认他是好诗呢?也不是因为他太短了,像康白情“滴滴的清泉……”一首我也很喜欢读他;也不是因为他是呻吟宛转的情诗,像朱淑真的《生查子》爱读的人也很多。
过火的食物吃了不消化,像太煅炼很了的律诗,就使人不能十分了解;没熟的食物又不中吃,汪静之的诗很多的人读了要皱眉的。《蕙的风》里面的新鲜风味还是太生了点;倘能再等些时日,等蕙儿长成熟点后,那时的《蕙的风》或者还要比现在芳香些罢!
老人常说颓唐的话,小孩常说毫无禁忌的话,不加思索的话;老人的精神是衰颓的,小孩的精神是天真的,活泼的。《蕙的风》的幼稚风味,不是天真的活泼的风味,只是糊(“糊”应为“胡”)说的风味。
总而言之,别人批评《蕙的风》的好处,只有新鲜和幼稚两种风味,但是他的这两种风味我都不取啊!
十二,一,十七。
诗的意境①载1923年《巴县留京学生会会报》创刊号,署名朱大枬。
我们若要寻找出来诗和散文最确定最妥当的分别,就是在他(“他”应为“它”)意境;尤其是白话的散文诗。但是常有人嘲笑:白话诗是分行写的白话文。这个有趣的疑难竟使我们莫赞一辞,最后的解答大概都是说到他们的意境上面。这个答复的确比较要算是圆满的了。
我们知道画中有诗,其实文中也有诗,所谓文中有诗是说散文里面有诗的意境。我读爱罗先珂的童话如像《鱼的悲哀》,安徒生的《丑鸭》,还有王尔德孟代等童话作家的著作,都觉得里面含有优美的诗意的成分。在文学作品的地位上,我们只就意境而论,诗和童话要算最接近的了。但是诗里切不可闯入文的意境,我们很讨厌旧诗里面的甚么咏史诗,颂圣诗,说理诗,应酬诗,当然是用文的意境作诗的缘故;他们若能老老实实的写成散文,也自有他的地位。可惜他们太不替自己和读者体谅了,必要使自己丢丑!这个丢丑只是丢在脑筋清楚的读者之前,太侥幸了。——读者皱眉掩鼻而后已。若要举例,俭(“检”应为“简”)直举不胜举,读者若不嫌手酸,也可以翻出几十百首来。现在我有了一件最好的回赠:这类的诗可以说是挤成了五言或七言,四句或八句的散文。其实白话诗里面也有这类的作品,或许更多。因为白话诗更容易犯这种弊病。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尤甚。
胡适批评《冬夜》,说他“妄想兼差做哲学家”,是他作品的失败的一层原因。我在我的《冬夜读后的话》里面也说过:“……喜说哲理也是抽象写法的一种表现,所以谈哲理的诗也不能成好诗;《冬夜》里谈哲理的诗最多,这也是《冬夜》最大的一个污点。”
诗重具体而忌抽象。所以俞平伯的哲理诗只好说是说理文。在《冬夜草儿评论》里面,梁实秋批评《草儿》说里面有些是游记,有些是格言,有些是演说辞。游记,格言,演说辞都是文不是诗,但是要把他写成分行加上一个诗的头衔,于是就变成诗不诗,文不文的“二不相”了。这也无怪会引起白话诗是分行写的散文的论调。
有人说过只有写景诗和抒情诗才算是诗,这话也确有存在的理由。但是我想情和景是融化的调和的在诗的意境内。作诗要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无情感的写景诗便呆板了而不流动,无景物的抒情诗容易失之于太主观而不真切。
我们读诗常感着一种阔放的心情。如:
“坐久了,/推窗看海罢!/将无限感慨,/都付与天际微波。”——冰心《繁星》
“……放翁胸次谁能测,万里秋空未是宽。”——陆游
有时我们又得着一种闲适的情趣。如:
“春无踪迹谁知?除非问取黄鹂。百啭无人能解,因风吹过蔷薇。”——黄庭坚《晚春》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李白《山中问答》
“夜深了,屋子静了,鸟巢都盛些美睡。”——泰戈尔诗
有时我们的心中起一种深刻的悲哀,或同情的烦恼的反应。如:
“莫问是在纳霞堡或在巴比伦,/莫问杯中的是苦汁或是芳醇,/生命的酒浆滴滴地浸漏不已,生命的绿叶叶叶地飘堕不停。”——莪默伽亚谟诗。
A Study on Modern New Poetry Concept of Danan Zhu: Based on the Lost Articles Reading ‘Hui De Feng’ and Poetry-Conception
LI Chaoping1,2Zhou Changhui1
(1. College of Arts,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4020, China)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Hui De Feng written by Jingzhi Wang in 1920’s triggered a firestorm artistic debate. Reading ‘Hui De Feng’ written by Danan Zhu was involved in the debate, but it was long forgotte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Zhu’s modern new poetry concept based on the lost articles Reading ‘Hui De Feng’ and Poetry-concep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restored historical scenes and collected lost material. Zhu’s ideas of literature theories are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the modern new poetry theory, such as selfish departmentalism literature standpoint, the modern new poetry essence of blending the classical and the modern, harmonious aesthetic point of view, poetic quality language view, and his equal proposals of novelistic poetry and dramatic poetry, etc.
Danan Zhu;debate of Hui De Feng ;modern new poetry concept
I206.6
A
1009-8135(2017)03-0050-10
2017-03-09
李朝平(1980—),男,四川安岳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重庆三峡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周长慧(1981—),女,湖北恩施人,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职员,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渝籍新月派诗人朱大枬作品辑佚及特质研究”(14SKL0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