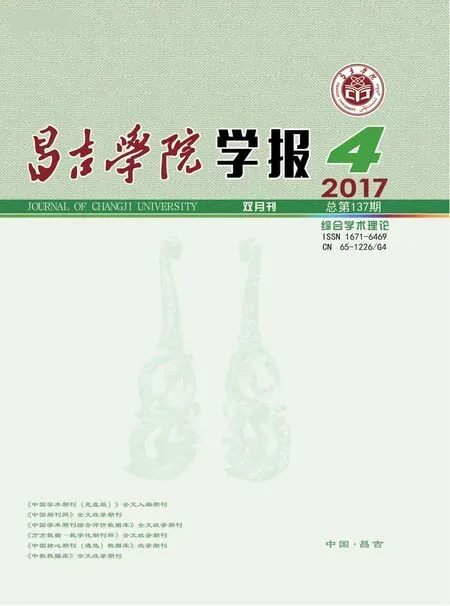张爱玲小说中母女之间代际关系的异化现象
艾安琪 胡明贵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张爱玲小说中母女之间代际关系的异化现象
艾安琪 胡明贵*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母女关系的描写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她一反传统母女关系那种“慈母爱女”形象,刻画了一种另类的残缺而畸形的母女关系。张爱玲对传统慈母形象的改写及母女矛盾的揭示主要原因是文化环境的影响:一方面父权宗法制社会的道德规范、文化习俗渗透到女性的文化心理中,使母亲成为父权制的“帮凶”;另一方面父权社会对女性经济和欲望的剥夺压制,使母亲囿于金钱和情欲之中无法自拔,导致母女关系扭曲和变形。本文从这两方面对母女关系异化的原因进行分析,探讨男权社会和封建文化对女性身心的摧残。
张爱玲;小说;母女关系;异化
“张爱玲的世界毕竟是一个女人的,关于女人的世界”[1]252,她塑造了许多鲜明的女性形象来揭示男权制社会下的女性悲剧命运,同时反思、自审女性的精神缺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女性审美世界。母女关系的描写是张爱玲小说中的一个重要叙事环节,它不同于以往的小说和谐的母女描写,在她的笔下,母亲不再是高尚圣洁的慈爱形象,而是一种阴暗扭曲、自私病态的化身,母亲和女儿之间充满了疏离、矛盾和冲突。
一、父权专制教化下的母女关系异化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母亲不再是无私、慈爱的伟大形象,而是自私、冷漠的面孔,母女之间的关系常呈现出紧张冷漠的状态。我们看不到母亲的无私奉献和对儿女们的呵护,而是看到一些母亲的自私和残忍。母女关系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母女之间在价值观念等方面产生了差异和对立,这种差异、对立被玛格丽特·米德称之为“代际关系”,即代与代之间的矛盾、冲突,产生这种代际关系的原因则是由于文化环境的影响。“在母女关系中,女儿的成长变化在父权社会中要与父权发生冲突和争斗,在冲突和争斗中母女关系也会随着冲突和斗争矛盾的大小发生变化。”[2]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造就的。这也就是说女性是被一定的要求和标准来规范和制约的,母亲形象正是在这种文化机制下被男权社会等级化和物质化,失去了母亲应有的人性和女性文化内涵,成为“父权意志的执行者和代言人”[3]2。因此在女儿受到父权的迫害而向母亲寻求帮助时,“由于受父权专制文化的压迫和教化”,母亲这个本该庇护女儿的角色却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了父权的‘帮凶’”,甚至是“父权专制在家庭中的主要执行者”[4]12。这必然导致母女之间的疏离,二者之间曾经和谐融洽的关系必然会产生变形和异化。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离婚后寄居在娘家,兄嫂把她的钱财搜刮一空,还想逼她回婆家守寡守节,以借此摆脱她这个“累赘”。流苏受了兄嫂的委屈来母亲跟前哭诉,想寻求母亲的安慰和支持时,白老太太却站在家中男性的立场上替她的儿子说话:“你知道,各人有各人的难处......支持这个家,可不容易!种种地方你得体谅他们一点......”[5]121此时的流苏还对母亲抱有一丝希望,希望母亲能为自己考虑,但白老太太却摆明了立场说:“你跟着我,总不是长久之计,倒是回去是正经。”[6]121这几句话,终于让白流苏意识到“她所祈求的母亲与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7]123白老太太对流苏的婚事漠不关心,实际上是怕儿子怪罪她心疼女儿,她这种对女儿不幸遭遇的漠视及对儿子的畏惧心理,在以父权为中心的宗法制社会里根本不足为奇。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男性为本位的文化,在这种文化里,男女之间有着截然相反的社会地位:男人是家庭的主人,生活中的主宰者;女人是家庭的奴仆,男子的附庸。在这个由男性为主导与统治的家里,家中的财产和经济大权掌握在儿子手中,白老太太虽然是家中的长辈但也必须要依附于儿子才能生活。而且“重男轻女”的思想一直都是男权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女性长期被男权文化所匡范,在这些男权观念潜移默化的作用下,女性在心理上也逐渐认同和顺从这种男权意识,并将之当做生存的原则。白老太太正是这样一个奉行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旧时代女性,在她的心中相比起自己的儿子来,流苏作为一个已经嫁出去的女儿当然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在流苏被兄长驱逐出门的时候,她的母亲出于自己生存的考虑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选择了站在儿子的一边,牺牲女儿的幸福来巩固封建家族,成为了父权制的执行者和“帮凶”。
《半生缘》里顾曼桢的母亲顾太太也是这样一个冷酷自私的母亲。在男权社会里,女人作为个体的独立人格是不存在的,她们被当做是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封建家长式的‘母亲’并非母亲,而是父权意志的化身”[9]19。由于曼桢的父亲去世,姐姐曼璐不得不靠出卖肉体帮母亲挣钱养家糊口,但她却得不到母亲的安慰,母亲劝慰的话从来搔不到痒处,常常还使她啼笑皆非。作为母亲她对曼桢姐妹来说几乎是没有爱的,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使她将母爱大部分放在了儿子身上。社会是男性的社会,没有了丈夫就只能在往后的生活中依附儿子生存,在顾太太的观念中母亲和儿子才是一家人,女儿终归是要嫁出去的,嫁出去的女儿就如同泼出去的水,不再是娘家人了。所以顾太太可以心安理得地用女儿出卖肉体换来的钱去经营儿子的家,却从未考虑过女儿的出路,即使有对女儿婚姻的关心,也只是建立在是否会对家里的经济有所帮助的基础上。后来曼璐嫁给了祝鸿才却无法生育,为此顾太太提出了“借腹生子”的建议,这种建议的提出表明顾太太认为女性为男性传宗接代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祝鸿才在曼丽的帮助下占有了曼桢,并将她软禁在家中达一年之久,本该救女儿脱离苦海的顾太太却对曼桢的悲惨遭遇视而不见,甚至将曼桢给男友沈世钧的信交给了曼璐,做了断送女儿一生幸福的帮凶。顾太太做出这种决定,除了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还有对女性应该臣服于男权统治下的认同,这样一个自私、冷酷且残忍的母亲形象被张爱玲赤裸裸地展示在了我们面前。最终顾太太与曼桢之间的关系也只剩下了恨意和冷漠,这种母女关系的异化正体现了父权专制文化中男尊女卑等封建观念对女性的摧残和伤害以及对母女感情的无声蚕食。
宗法制父权社会的文化赋予了母亲父权代言人的身份,尤其在父亲缺席的家庭中,母亲更是有着最高权力的封建家长,是宗法父亲的化身。作为一家之长的母亲在自觉不自觉中认同强势的父权文化并以此来统治家庭确立家长权威,这样一种母亲实际上已经被父权观念和生存需求所扭曲。《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虽与葛薇龙是姑侄关系,但她实际上充当了葛薇龙养母的角色,她也是一个完全被男权社会所同化的女性,被异化的封建家长。梁太太在年轻时嫁给了一个老富豪为的是换取金钱,然而等到丈夫死了她的青春也消逝了,于是她就利用分来的遗产利用一切来弥补自己的情欲。梁太太在掌握了家里的经济大权后,由于被男权文化所同化,她也想成为像男人那样让别人依附于自己的人,她利用对金钱的支配权成为家里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家长,这一权力也使她由受害者变为加害者去支配和奴役他人。梁太太有着强烈的权力掌控欲望,意图对葛薇龙等人的命运进行全盘操控,且不允许任何人违抗她的意愿。睇睇因为不听她的话偷偷去找乔琪乔她就将睇睇赶了出去,她甚至利用这一权力来迫使亲侄女葛薇龙心甘情愿地堕落,为她去勾引男人。在梁太太的心中没有亲情只有自己的利益,她可以为了自身的利益毫不留情地去牺牲任何人,哪怕是自己的亲侄女。从她第一次答应资助葛薇龙,到最后劝说乔琪乔娶了葛薇龙说的那番话,都表明她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考虑,在她眼里葛薇龙不再是她的亲人,而是她勾引年轻男孩子的工具。葛薇龙的堕落除了受到梁太太给予的物质诱惑外,其实更在于她对梁太太生活模式和是非观念的潜在认同,她也想获得那种绝对掌控权力。在梁太太的影响和控制下,葛薇龙也走上了梁太太的老路,最终成为梁太太权力欲望的牺牲品。张爱玲通过讲述葛薇龙和梁太太这一对“母女”之间的矛盾冲突,展现了“封建家长制权力机制是如何通过制度化的家,将异质的他者——女人改造成同质者的。”[9]197
二、金钱诱惑和欲望禁锢下母女关系的异化
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生存权力和欲望的剥夺压抑也是导致母女关系扭曲和变形的一个直接原因。在这个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权的时代里,“不论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贫困母亲,还是寄生在封建大家庭的母亲,都面临着或隐或显的生存威胁。母亲的生存焦虑扭曲遮掩了母亲对女儿的庇护和爱,迫使其以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呈现。”[10]17《花凋》里川嫦的母亲郑夫人仅仅因为怕丈夫知道自己有私房钱,就置重病的女儿于不顾,任由女儿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死去。当生存的困境出现时,母亲却选择了金钱,母女间的脉脉温情也就不复存在,这是多么可悲而残酷的一件事,神圣的母爱被淹没在了金钱的欲望之中。《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则是父权对女性的压制摧残导致母亲这一角色心理扭曲变形的极致。封建宗法制压抑女性身心所造成的母性消解,最集中的体现在了她的身上。曹七巧本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后来被贪图钱财的哥哥卖给姜家,嫁给了姜家患病的二少爷,开始了无爱无性的生活,卑微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使她成为了情欲和金钱的牺牲品。她在姜家处处遭受奚落,连那些下人都瞧不起她,如此种种遭遇都是因为她娘家没有钱,这是她对金钱有着强烈占有欲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七巧作为一个有着正常生理需求的女人,当她无法在自己丈夫身上得到满足时,必然会渴望像三少爷那样身体健全的人,但是她没有得到,爱欲得不到满足导致了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在这种畸形生活影响下,她的内心变得极度扭曲疯狂,最后为了守住牺牲自己的青春和爱情换来的金钱,她给自己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在她的儿女长大之后,曹七巧和女儿长安之间的矛盾冲突更是体现了一个完全丧失母性的丑陋母亲形象。曹七巧对儿女的婚事进行百般阻挠,她害怕女儿会伙同他人来夺走她用青春和一生幸福换来的金钱,她不允许任何人觊觎她的金钱。七巧经常对长安进行冷嘲热讽或直接破口谩骂,使长安长期受到母亲的羞辱,也因此让长安觉得没脸再去见老师同学而辍学了。长安对母亲的这种控制欲有过抗衡,但七巧却因为这种抗衡变得更加疯狂。后来长安交了一个男朋友童世舫,出于性变态的心理和对女儿可能获得幸福的潜在的仇视嫉妒心理,曹七巧为了拆散女儿的婚事将童世舫请到家中做客,故意向他透露长安有抽大烟的习惯:“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这孩子就苦在先天不足,下地就得给她喷烟……戒戒抽抽,也有十年了。”[11]186简单的几句话就将长安的终身幸福断送了。作为母亲的曹七巧完全失去了与女儿之间血浓于水的亲情,她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父权社会中的参与者,母性在曹七巧这里完全消失。在她的眼中女儿不再是女儿,而是一个与她对立的女人,她自己的情欲得不到满足,也见不得自己的女儿得到幸福,她想掌控女儿的命运,让女儿变成和自己一样的人。而长安在母亲的强势威压之下,渐渐放弃了反抗,长安的那点独立精神最终被消磨殆尽,完全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她的言谈举止越来越像她的母亲了”[12]175。
另一个与曹七巧有着相似经历的是《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蜜秋儿太太,她与曹七巧的共同之处都在于通过扼杀女儿的幸福生活来满足自己变态的心理需求。“女权主义认为,母亲或成年女性的心灵,尤其是感情生活、性本能方面所受的压抑,会形成她们的根本性压抑,即心灵的一种基因性变异,并且会将变异的阴影,转嫁到别人,尤其是子女身上。”[13]在以男权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中,性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标准。不管是在婚前还是在婚后男人可以享受纯粹的性,而女性却必须保有童贞,在日后的婚姻生活中也必须服从于自己的丈夫;男人可以三妻四妾,而女人若是偷情却会面临被抛弃甚至是死亡的威胁;男人丧偶之后可以再娶,而女人丧偶之后却必须为死去的丈夫守寡守节,这样的一些封建传统观念严重压抑和禁锢了女性的精神。小说中靡丽笙一句“连我们所读的报纸,也要经我母亲检查才让我们看的”[14]49,就道出了蜜秋儿太太对女儿教育的阴谋。蜜秋儿太太常年守寡,也让女儿们陪她一起过这种修女式的生活,在抚养和教育女儿的过程中,她故意忽略了对女儿们“性”的教育,也不让女儿们接触“性”方面的知识,通过严格的家教把她们培养成了纯洁无知的人,明知女儿新婚之夜要经历什么却不向女儿透露半分。女儿们将丈夫当成流氓,使他们名誉扫地甚至为此丢失性命时,蜜秋儿太太明知其无辜,却偏偏什么都不说,不动声色地扼杀了无辜的男性,葬送了女儿的幸福。在她的眼中,“女儿既是自己的复制,又是另外一个人;她既对女儿有过度的亲爱,又怀有敌意;她将自己的命运又缚在女儿身上;这是对自己女性命运的骄傲的申张,却也是为自己向它的报复。”[15]42在蜜秋儿太太的畸形教育之下,她的两个女儿——靡丽笙和愫细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帮凶。而蜜秋儿太太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她常年守寡致使心中的欲望得不到发泄,情欲得不到满足,极端压抑之下而导致心灵变异。她自己没有幸福的婚姻生活就对女儿进行摧残,也不想让她们的婚姻生活得到幸福,这种扭曲变态的心理其实反映了封建传统守节观念对女性精神意识的残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封建传统文化中,谈性是一种禁忌,认为男女之间的性爱是丑恶的,是为了传宗接代不得已而为之的,应该尽量压抑和回避。蜜秋儿太太被这种观念浸染,禁锢自己欲望的同时也要禁锢女儿们的欲望,阻止她们获得“性”方面的知识,使这种“性罪恶”的思想逐渐在她们心中根深蒂固,最终导致了两个女儿的婚姻悲剧。
三、结语
张爱玲塑造了这一系列的非常态的母亲形象,一反传统文学中母亲的美好柔和,将在父权宗法制社会中被压迫的母亲的阴暗一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揭开了掩盖在脉脉温情下真实的母女关系。在父权社会秩序下,母亲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情欲需求而吞食女儿的幸福,母女关系被男权文化、金钱、欲望所异化而变得残缺畸形、冷漠疏离,在这种冷酷无情的变异关系中,不管是女儿还是母亲,她们的人性最终都被摧残以致扭曲,这一切都是拜父权宗法制所赐。在经济、人格毫无独立性可言的男权社会里,她们只能自私地为自己的生存焦虑而丧失母性,被畸形情欲支配而逐渐泯灭母女亲情。张爱玲“对男权规范的母亲角色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母女关系的否定,而是通过对被男权文化和现实功利所腐蚀伤害的母女关系的审视”,揭露封建宗法制度对女性身心和母女关系的破坏,是父权制社会秩序对女性生存和欲望的压抑,导致了母女之间关系的冲突和紧张,并呼唤至爱亲情,“重建被父权制所放逐和割裂的母女关系”[16]21。
[1][8]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2][4][10][16]邢海霞.讴歌、颠覆与理想化——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母女关系[D].河南大学,2010.
[3]刘媛媛.她视界·现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探析[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5][6][7][11][12][14]张爱玲.花凋[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
[9]邵迎建.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张爱玲的文学[M].上海:三联书店,1998.
[13]黎荔.中国现代文学女性观之母女关系研究[J].东南学术,2015,(06):231-237.
[15]西蒙娜·德·波伏娃.女人是什么[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I246
A
1671-6469(2017)-04-0036-05
2017-03-26
艾安琪(1991-),女,汉族,湖北荆门人,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胡明贵(1965-),男,安徽马鞍山人,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女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