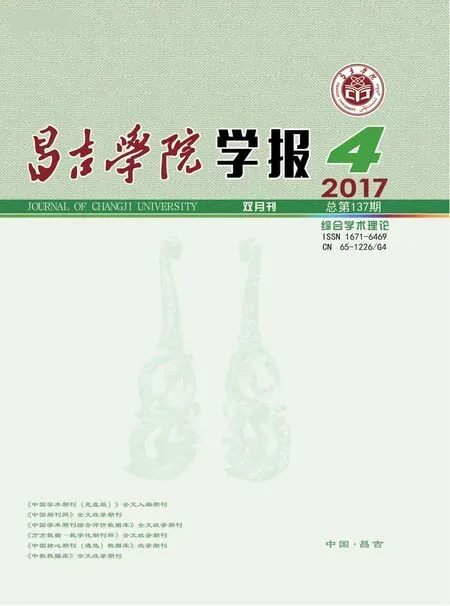“母亲”的叙事功能及无母的隐喻
——《望春风》中的缺席者研究
高慧雯 汪 杨
(安徽大学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母亲”的叙事功能及无母的隐喻
——《望春风》中的缺席者研究
高慧雯 汪 杨*
(安徽大学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在新作《望春风》中,格非延续了其在小说中设置缺席者的写作方式。在小说叙事效果上,“母亲”章珠作为小说中的缺席者承担了营造神秘气氛、为展现乡村人情提供背景、推动情节发展的叙事功能。此外,“无母”所致的个体自我认同的缺失与寻觅,母亲无法回归所隐喻的希望的遥不可及,母亲所代表的虚妄和春琴所代表的希望之间的摇摆,更使得小说在展现乡土人事之外,呈现出更深层次的主题。
缺席;母亲;主题
从《迷舟》《青黄》等颇具先锋意味的小说到保存乡村记忆的新作《望春风》,格非的作品中出现了一类独特的形象——缺席者,这类缺席者往往不在叙事现场,其形象有待填空。这类形象以悬置的空缺来推动小说的发展,并为小说营造了神秘的氛围。[1]《望春风》中缺席者是叙述者赵伯渝的母亲章珠。在赵伯渝不满周岁时,他母亲就离开了儒里赵村,在赵伯渝成长过程中,母亲一直是缺席者,一直到母亲去世他们都未相见。
一、缺席者“母亲”所承担的叙事功能
(一)作为谜团和解谜者的“母亲”
在小说第一章“妈妈”一节中,缺席者的形象开始以空白—谜团—猜谜的模式呈现。在赵伯渝的童年时代,缺席的母亲对于他来说是不可知的。在前两章中,母亲的身世、父母离婚的真相、母亲的离开原因和去向以谜团的形式被抛了出来。作为当事人的父亲赵云仙保持缄默,其他人物则跳出来发声,龙英、老福奶奶、婶子、梅芳、赵宝明、赵同彬、冯金宝,这些人对“母亲”的态度和说法因个人经验的带入而显得不甚可靠。个人化的讲述往往难以摆脱价值判断的偏见,对于同一个事件,不同的讲述者会有不同的答案,“本事是不可被复述的”[2],不同版本的讲述看似逼近真相,却可能因为还原“本事”这一行为的不可能而滑向不可认识的虚空。在猜谜的过程中,小说呈现出的是众说纷纭的杂乱,事件的真相显得影影绰绰。作为谜团出现的母亲为小说营造了一种扑朔迷离的叙事效果。关于母亲的种种传言,以及由叙述者“我”在讲述时通过预述手法故意抛出的悬念,都起到了吸引读者,增强读者的阅读体验的作用。
谜团的存在使得小说的叙述摇曳多姿,充满了神秘气氛,这种先锋技法的使用在调动读者积极性,增强可读性的同时,容易指向命运的不可知,叙述的不可靠的主题,这是转型后的格非所要避免的。因此,《望春风》中的谜团是有答案的,格非在保证小说叙事技法的高妙的同时,努力给读者一个关于真相的解释。随着叙述的层层展开,母亲这一形象在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口头回忆或猜测中被描绘出轮廓。小说中作为谜团的母亲,同时也担任了解谜者的角色。在第三章“余闻”中,母亲以信件的方式为自己的形象填空。在母亲留下的遗物里,她用十四本硬面笔记簿记载了七百六十余封写给儿子的信。从这些信件中,赵伯渝了解到了母亲一生的忧郁与痛苦,而父亲死亡的真相也从母亲的忏悔中浮出水面。母亲以不在场的形式完成了小说中重要的解谜过程,这一解谜行为的存在使得作品避免了流于形式实验之嫌。
(二)作为叙事背景的“母亲”
借助“母亲”这一缺席者的设置,格非实现了展现父爱和乡村人情的意图。
“母亲”的缺席为父爱的表现提供了一个聚焦的舞台。因为母亲的缺席,父亲兼任了母亲的角色,他在生活中竭力照顾儿子,并教他识人,传授他生存智慧。在《望春风》的创作中,正是因为母亲的不在场,才使得父亲这一形象的塑造更为有力。母亲的隐去,将默默无闻的父爱推到前台。父爱是格非在小说中所绘的一抹暖色,他有意将其个人的生命体验加入到小说中,通过细节描写来表现父爱的深情脉脉,更以母亲的缺席来凸显父亲这一形象及父爱的主题。
“母亲”的缺席也为其他人物的形象补充提供了机会。在“母亲”缺席的背景下,王曼卿在“我”梦见母亲后暗自哭泣时对“我”的关怀和温柔举动,体现出了她人格中的慈爱温善一面。春琴在“我”父亲死后对失怙的“我”频频关照,不仅刻画了她的性格和为人,更为后文埋下了感情线索。婶子临终前对于私吞“母亲”礼物一事而感到愧疚,这一情节的设置在刻画母爱以补全“母亲”形象的同时,也对原本悭吝刻薄的婶子的形象做了补充。通过各种形式的形象补充,格非在小说中展现了人性的多个侧面,呈现出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于《望春风》这部承载了他故土情结的小说,格非不愿在其中表现出绝对的善恶,他对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处理,体现了他尝试理解每一个普通人的努力。
(三)作为命运推手的“母亲”
格非虽然设定了“母亲”的缺席状态,但并未使其仅仅成为一个背景。要在二十三万字的作品里描绘一个村庄五十年来的流变,叙事节奏的控制是必须的。“母亲”这一角色发挥着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她的两个举动加速了小说的叙事节奏,决定了叙述者赵伯渝生命中的两大转折。
其一,母亲的举报让赵伯渝进入“无父”的状态。出于自保的考虑,母亲在慌乱之下交出了一封有关父亲当年加入的特务组织的情况的举报信,这封信让赵伯渝失去了父亲赵云仙,他因此更加期盼母亲的回归。母亲的这一举动所导致的赵云仙的死亡进而改善了赵伯渝和春琴之间的关系。春琴对失怙的赵伯渝由冷漠和敌视的态度变为关怀备至,为他们后文在便通庵共度余生埋下了情感线索。其二,母亲的召唤让赵伯渝离开了故乡,使其有了之后拉开距离后的恋乡。母亲要接他去南京同住,作为叙述者的赵伯渝有了离开故乡的理由,在他告别儒里赵村来到邗桥镇之前,他感受到了对村庄的依恋。结果是,与母亲见面落空,得知母亲死讯的他变成了孤身一人的状态。在无父无母的情况下,曾经生活过的村庄成了他想要回归的温暖巢穴。这一情节的设置是为了更好的展现恋乡的主题,母亲则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一环。
从缺席者“母亲”所起到的营造神秘气氛、为展现乡村人情提供背景、推动情节发展三方面作用来看,格非设置“母亲”这一缺席者形象便于他更好地叙事,这是作家在叙事上所采用的巧妙方式。格非虽然在《望春风》中安排了“母亲”的不在场,但从情节设置上对其进行了形象补全,并使之尽可能地可信。因此,与格非小说中的其他缺席者所呈现出的残缺未定不同,“母亲”这一缺席者并未指向虚空和不可知,在拼合和补缀中这一形象逐渐明晰,补全母亲形象的这一努力和作者在小说中表现的父爱和乡村人情都体现了格非在小说创作上的转型,他开始变得温情。
二、“母亲”缺席所隐含的主题
从表面来看,《望春风》的创作基于格非的童年经验,是对逝去家园和记忆中人事的记录,但是作家的写作绝不会只是描摹现实、为乡村立传。小说结尾处颇具诗意写道“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将会突然出现在明丽的春光里,沿着风渠岸边的千年古道,远远地向我走来。”[3]393,小说以假想母亲重回故乡这一场景作为终结。这意味着,作为缺席者的“母亲”在承担小说叙事功能之外,更指涉了小说的深层次主题。
(一)自我认同的缺失与寻觅
母亲离开村庄意味着赵伯渝被抛弃,他的性格和命运与母亲的缺席存在密切的联系。在承担小说叙述者功能的同时,赵伯渝也是文本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将他零碎讲述的有关自己的生平事迹全部勾连整合之后,这一人物的性格表现为自卑、怯懦。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为母亲所特别钟爱的孩子,一生都有身为征服者的感觉。”[4]赵礼平与赵伯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婶子对儿子的溺爱使赵礼平成为一个征服者。对比之下,赵伯渝在婚配、离异及工作上都显得被动,他对一切表现得都无所谓。缺失母爱的赵伯渝是一个懦弱的被动者形象。在拉康的心理学分析理论中,母亲在婴儿最初身份的建立中起着第一“他者”的作用。母亲是婴儿形成最初自我意识和开始身份构建的基础,母亲的缺席无疑会对赵伯渝主体身份的构建产生负面影响,“像我这样一个人,似乎不配有更好的命运。”[5]196,从他的自白中即可看出他自我认同的缺失。
得不到母爱的怨念以及对母爱的渴求是赵伯渝成长过程中隐秘的伤痛。过早离开的母亲没有给赵伯渝留下任何印象,对他而言,母亲的音容是空白的,这一空白有待填补。小说以梦境中出现的母亲形象的影影绰绰来反映他内心对空白的恐惧和填补的渴望。他曾在梦里以王曼卿、孙耀庭前妻的形象来想象母亲,这意味着他在潜意识里一直在追寻母亲。“母亲”是一个与人类的心理与命运相关的原型因素。寻找母亲意味着对自我的寻找,意味着身份的认同和定位。赵伯渝一生也未与母亲相见,从两地分离到生死相隔,他的寻找最后仍然扑空,母亲留下的遗物只能做缅怀之用,寻母无望最终指向的是自我认知的迷茫。
(二)希望的遥不可及
母亲的缺席埋下了回归的希望,在赵伯渝寻找母亲的过程中,期望母亲的回归是他生存下去的动力之一。小说中,母亲的回归与春风的意象相连。老福奶奶说母亲在春风中回来,在父亲离世以后,盼望母亲出现成为赵伯渝生活的最大动力。“我的母亲还在,她活在一个我所不知道的地方。说不定哪天,当大雁北还,燕塘边的野蔷薇花开出成片白色和粉色的花朵,在温暖的春风里,我的母亲就会回来。”[6]329就连唐文宽愚弄赵伯渝时,也会编织一个母亲会在春天回到村子里来的故事。
弗洛姆指出,对婴幼儿而言,“母亲就是温暖和食物,就是满足和安全的快感”[7]。春风、河岸、野蔷薇花这些意象多次出现,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明媚之景。尽管赵伯渝对母亲的缺席抱有怨恨,但在他想象母亲的时候,“母亲”意味着希望和美好,代表生命的希望,孕育新的未来。她像春风一样能够唤醒万物,使大地复苏。母亲这一形象虽寄托了赵伯渝对美好的向往之情,但最终指向的是美好的失落。在第二章末尾,母亲突然派人来接赵伯渝,他将要进城,将要和已成为高官家属的母亲见面。他的人生在父亲离世后有了新的可能,他还因此娶上了之前高攀不上的雪兰。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他的极大的好运,但几个月后,他得到的却是母亲早已去世的消息,他从希望跌入绝望。这一情节的安排所隐喻的是:“母亲”看似带来了希望,而最终这希望是不可及的,留下的只是更深的悲怆而已。
在赵伯渝假想的场景里,春风意味着母亲的回归,而在赵伯渝的幼时梦境里,母亲的话语和面容都被四月的熏风吹散了去,这一梦境早已隐喻了母亲回归的不可能。直到母亲去世,母子俩不能相见已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在春风里,母亲不会回归。就连他所怀念的故土,也被终结在一个细雨迷蒙的春天。最终,缺席的“母亲”和“春风”指向的是美好而虚妄的幻想,《望春风》中的春风终是可望不可及。
(三)希望与虚妄的摇摆
如果说,母亲是握不住的春风,那么春琴则是格非在小说中留下的可触及的希望。因为母亲的缺席,在父亲赵云仙离世后,春琴实际上担任的是赵伯渝母亲的角色。在潜意识里,缺少母亲关爱的赵伯渝将春琴作为移情对象,对赵伯渝而言,春琴是一个替代式的母亲,她兼具“母亲”和“情人”的双重身份特征。所以在多年以后他们成为夫妻并且交合时,他才会“带着对禁忌、罪恶乃至天谴的恐惧”[8]378-379而噙满泪水。
将春琴的名字拆分来看,“春”字对应的是篇名《望春风》中的“春”,寓意万物复苏,重新开始,而“琴”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意象,在小说中与琴有着密切关系的是遗老赵孟舒,琴字指涉的是古风犹存的儒里赵村,也就是格非所要纪念的故乡。春琴合二为一,蕴含的是对于故乡的希望。小说的结尾处,由春琴提出了百十年后出现一个大村子的憧憬。
与缺席的母亲带来的不可实现的希望不同,春琴在小说中给赵伯渝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希望。因为春琴,失去父亲的少年赵伯渝得到庇护,失去故乡的老年赵伯渝老有所依。兜兜转转,他们最后回到了便通庵,用油灯照明,用茅草生火,以塘水灌园,以井水煮饭,回到了童年时代所过的日子。小说最后,他们夫妻二人回半塘扫墓的情景与小说开头父亲赵云仙带赵伯渝去半塘将春琴说给德正为妻的情景形成了一个回环式的结构,同样是岩溶般的火球,同样是一寸寸变高的身影。格非以春琴这一人物设置完成了他关于时间机器的构思,在小说最后,人物得以“重返时间黑暗的心脏”[9]366。
这样的希望也许是不持久的,赵伯渝和春琴难以成为新村庄的始祖,他们面临着无父、无母、无后的断裂。春琴是有后的,但是格非设置了这样一个情节——春琴儿媳夏桂秋不能生育,这一安排指向的是“无后”的隐喻。由此体现了作家内心的矛盾状态以及在此状态下文本呈现出的一个矛盾——希望与虚妄的摇摆。春琴象征着故乡的希望,但是到了小说的结尾,他们都已年过半百,赵伯渝五十二岁,春琴五十七岁。他们除了等死还有可能生育下一代吗?也许有,也许没有吧。格非设置他们的交合情节除了引出赵伯渝对春琴的隐秘情感以外,也许还暗示着下一代的可能性。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他们只能短暂地在乌托邦里停留,最后走向死亡。所以,赵伯渝最后给出的答案是假如,这个假如里还包括了他早已去世的母亲的回归。母亲已经离世这一事实注定了结尾处的美好向往不可能实现。格非知道尸首不能开花,但他不愿意走向绝望,他仍要在小说中留下一些可能性,希望与虚妄的摇摆之间,是理性和情感的碰撞。
继最终指向绝望的《江南三部曲》之后,格非尝试着做了一些改变,于是新作《望春风》有了一个温暖而富有诗意的结尾。不管是格非还是书中的叙述者赵伯渝,他们都清楚:现代化进程中乡土的覆灭是难以逆转的。结尾处,格非引用了《荒原》里的诗句来表达清醒者的苦涩。但赵伯渝最终没有将“不可能”说出口,也没有像《祝福》中的启蒙知识分子“我”一样给祥林嫂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他选择了用“假如”的句式留下希望。如果希望最终指向的是虚妄,我们还需要希望吗,文学还需要希望吗?格非通过缺席的母亲和作为替代式母亲的春琴为赵伯渝提供的希望告诉我们,即使是不可能实现的希望,也能给人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物理性的时间不会重回,只会义无反顾地向前,将停滞与回望的人抛弃在时间幽暗的河流里。而文学提供给我们重回时间怀抱的时光机器,这就是文学的意义所在。
[1]张霞.迷失在时间中的“缺席者”——论格非小说的时间与人物设置[J].东岳论丛,2011,(06):121-124.
[2]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26.
[3][5][6][8][9]格非.望春风[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4](奥)弗洛伊德.张唤民,陈伟奇译.弗洛伊德论美文选[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3.
[7](奥)弗洛姆.爱的艺术[M].陈维纲,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44.
I206.7
A
1671-6469(2017)-04-0041-04
2017-05-22
高慧雯(1993-),女,湖南邵阳人,安徽大学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研究。
汪杨(1980-),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