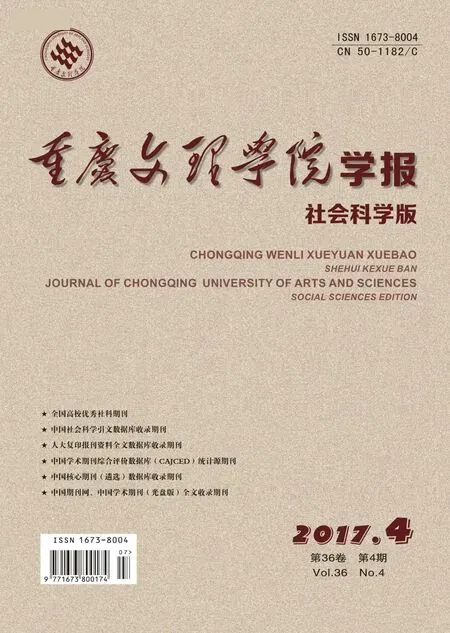欲望的叫嚣
——读苏童小说《黄雀记》
王凤语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欲望的叫嚣
——读苏童小说《黄雀记》
王凤语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欲望是苏童小说不可缺少的关键词,在长篇小说《黄雀记》中,作者再一次将我们带回了他所熟悉的“香椿树街”,为我们展示了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时代巨变之中,三位主人公保润、仙女和柳生,以及香椿树街居民在欲望叫嚣中的沉沦、挣扎和救赎。大时代的激变给人性之弱点以发酵的土壤,青春期的反叛又做了罪恶的推手,香椿树街的欲望图景是丰富多样的。欲望是人之本性,但欲望一旦膨胀,命运就会给人以无情的惩罚。三位主人公的救赎无望说明了灵魂安放之艰难,这既是命运给生命的无法承受之重,也显示了作者对于出路的无力找寻。
欲望;绳子;罪与罚;魂
苏童作为20世纪80年代成名的作家,早期以中短篇小说闻名,与马原、余华和格非等人被归为先锋派小说家之列,后转向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黄雀记》讲述了保润、仙女和柳生三人20多年的命运纠葛。大时代的激变背景加上人性中难以抑制的弱点,使得所有的罪恶都悄然萌生,在南方的潮湿阴郁中不断发酵,而罪恶与审判的绳索将三个少年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使他们难以挣脱。
一、《黄雀记》中的欲望世情图
欲望一词最早来源于11世纪末的拉丁文,原意是指“对缺乏者的抱憾”,可分为愿望、要求、想望、肉欲、性欲和所想望等东西。它的基本成分是需要和占有。欲望也成为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古今中外的作家们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或隐晦或直接地表达着人类的欲望,剖析人性中最为隐秘的幽深之地。苏童历来很重视这一话语的表达,他的小说基本上都与欲望相关。《妻妾成群》里的几位姨太太争风吃醋,想尽各种办法来得到陈佐千的宠爱。《米》就描写了一个关于人的基本需要与人性之间冲突的故事,关于欲望,关于痛苦,关于轮回,作者用欲望来建构五龙的一生。《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的陈宝年,更是因为最简单的生理欲望而开启了自己的逃亡之旅,进而改写了枫杨树镇的历史,带动了一个行业的发展。
同样,在《黄雀记》里,作者又把我们带回他所熟悉的“香椿树街”,讲述南方湿润小城中的隐秘欲望。
王德威曾经说过“南方的南方,是欲望的幽谷,是死亡的深渊……在那个世界里,耽美倦怠的男人任由家业江山倾圮,美丽阴柔的女子追求无以名状的欲望”[1]。苏童这一次又把故事的开端落在他所擅长的青少年成长主题,如同《伞》和《独立纵队》中的少年一样,作者将一场命运的纠葛放在青少年那懵懂又不可遏制的茫然情欲之下,探寻人性悖论之中不可摆脱的原罪。
在开篇“保润的春天”一章中,青春期的冲动和爱意都将从春天这个季节萌发,“这是一个意外的春天。意外从照片开始,结局却混沌不明”[2]8。对于保润、柳生和仙女,这都是一场不知名的意外,欲望的种子在春天生根发芽,结局指向虚无与沉沦。祖父为了维持自己死后的尊严,每年都要去照相馆拍一张照作为遗照,保润在一次替祖父去照相馆拿照片的过程中无意看到了一名少女的照片,和祖父一样,他自己也丢了魂。在井亭医院,保润邂逅了仙女,朦胧的爱欲在体内发酵,他开始思念她。柳生的出现和诱惑,使保润的懵懂爱意进一步发酵,也一步步被命运的绳索套牢。捆人是保润的拿手绝活,也是他彰显权力和控制欲望的诉诸途径。保润鲁莽强势且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尊心,他有着强烈的征服欲,即使在梦里也不允许别人的挑衅。他的眼神凶恶,王德基的女儿将其比喻为“探照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像一条绳子一样对别人进行审视和宣判。正是这种人性中的主导因素,使得保润在约会仙女邀请其跳小拉不成之后,将其捆绑在水塔之中,引发了后来柳生的犯罪,使保润做了替罪羊。
如果说保润代表的是青春荷尔蒙的欲望的话,那么柳生的行为代表的则是原欲。“原欲(Libido)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解,就是人的基本欲望‘爱的本能’,它蕴藏在‘本我’中,是生命能量之源的核心力量,是人类生命活动最原始的内驱动力和终极原因。尽管弗洛伊德声称‘原欲’是比‘性欲’包含更广的生理机能——‘爱的本能’,实际上二者在他那里并没有多大的区分。”[3]《米》中的五龙面对来自大城市的诱惑,无法抑制自己的欲望,丧失了理智从而疯狂地占有女性。《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的杨宝年从妻子身上得不到满足,从而离开家庭。同样在《黄雀记》中,柳生在面对被捆绑的仙女时,出于欲望,出于冲动,犯下了要让三个人用一生偿还的罪恶。柳生对仙女的感情与保润有所不同,保润对仙女是真正的喜欢,而柳生则是纯粹的生理冲动。由于原欲的膨胀,给柳生的精神生活加了一层枷锁,他的快乐充满了假象,不论时间过了多久,那两只当年目睹真相的乌鸦,还依然栖息在水塔顶上,不停地鸣叫,提醒着他曾有过不可磨灭的罪恶。
葛红兵曾说“苏童以天才的悟性,打破了20世纪主宰中国文坛的启蒙主义文学语式关于时间的叙述图式。他对时间的非线性认识,对事物轮换、人事反复的体验,使他更能深入中国人的性与命的深处,挖掘那具有民族史志色彩的人性蕴含”[4]。苏童历来对那种宏大的历史叙事不感兴趣,他善于解构历史,将历史的完整性打破,转而突出在历史河流中流淌着的个体生命的自由姿态,用他们的生存图式来表现历史,表现片段化的细节真实,展示在时代洪流中最为真实的人性。《黄雀记》中的文本时间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绵到20世纪末,这近2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变化最为剧烈的时间段。改革的浪潮使国民在欲望的洪流中被冲刷得迷失了自我,群体性的惶惑和精神紊乱成为时代的病象。然而不论精神是多么逼仄,追求欲望的脚步却从未停歇。在小说的开头,香椿树街的全民掘金行动似乎在诉说着随着代表上一代历史的祖父丢了魂之后,香椿树街的居民也开始丢魂了。马师傅的精品服装店开张,马师母举止投足间的精于算计,郑老板因一夜暴富无所适从而引发的妄想症,邵兰英用钱财买通关系使柳生免去了十年的牢狱之灾,还有从昔日的古镇变为现在买春天堂的枫林镇,苏童用看似平淡化的叙事随意点拨与历史有关的语境,探寻人性中最为真切的部分。仙女作为小说的主角之一,在出场时就显示出对于金钱和虚荣的渴望。因为柳生的小恩小惠而对其唯唯诺诺,称其为“老大”,在与保润的第一次约会中表现出对物质的渴求,欲望的种子深深埋藏在仙女的人性之中。数年后仙女化身为白小姐,堕落于风月场所,辗转于各色男性,无所顾忌地消耗着自己的青春,沦为“花瓶”。虽然这一部分的描写过于滥俗,遭到很多读者和评论家的批评,但就其根源来说,人物的这一身份转换与人物本身的特性相吻合,也较具有说服力。
二、欲望膨胀的结果:罪与罚
《黄雀记》中的各色人物在各自的欲望中沉沦,或贪欲,或性欲,或权欲,欲望萌生的枝丫有千万种,而沉沦后的道路却只有一条,那就是惩罚。苏童曾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来描述这部小说,欲望可以引发罪恶,罪恶的绳索在伤害他人或自己后又紧紧地捆绑着每一个人。
1.“欲”与“狱”
苏童的小说表现的是一个又一个“欲”与“狱”的故事,欲望带来的是身体或精神之“狱”。《妻妾成群》中的颂莲、梅珊和卓云,想尽办法来得到陈佐千的宠爱,填补自己空虚的身体和精神,梅珊的惨死,颂莲发疯印证了命运对她们的惩罚。《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陈宝年的大儿子狗崽纵欲后因伤寒病而死,陈宝年寻欢作乐后遭人暗算,“狱”与罚无时无刻不在体现着它们的规则。到了《黄雀记》这里,“欲”与“狱”的关系则更为隐秘和错综。
当青春的反叛迷茫和忧郁感伤与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相遇时,个体的彷徨与世界之恶是如此尖锐。保润对仙女的青春期懵懂爱意是真切的,18岁的少年对异性和爱情的欲望在春天一再萌芽,涨势汹汹。仙女与别的男孩在冰场上滑旱冰的快乐情景使他激愤不已,他带着怒火去仙女家讨债,却在她的窗户外开始思念她。还有那些绚烂的在现实中实现不了的梦境,都如同兔笼上的粉色新型标牌一样温柔炙热,缓缓地在诉说着“我爱你”。所以当仙女在水塔中报复性的无理要求和拒绝跳小拉的打击一起袭来时,爱与恨的交织占据了他的理智,他用铁链捆绑了仙女。这一捆绑换来的是十年的冤屈。不仅使保润身体被“狱”,失去了人身自由,并且使他的精神世界被仇恨所占据。当他出狱后误以为白小姐和柳生在一起苟且,自己受到了愚弄,罪恶之火再次喷发,最终使他杀了柳生,自己也再次入狱,走向毁灭。
柳生的一场冲动的欲望改变了三个人的命运,他想要洗刷自己的罪孽却由于自身的弱点和命运的羁绊,始终得不到救赎。柳生深知自己的过错,变得谦卑世故,对白小姐唯命是从,替她买枪,帮她讨债,即使是出了车祸断了几根肋骨也毫无怨言。他替代保润照顾祖父,给保润出谋划策。然而他看似没有得到身体的禁锢,却在精神上受着折磨,精神之“狱”将他牢牢困住。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并没有交代那张暴露柳生罪恶的纸条来源于谁手,是命运还是那只看不见的黄雀,作者并未给出答案。它或许也在暗示柳生的结局:得不到救赎,抹不掉罪恶,为自己的过错付出生命的代价。
仙女的拜金使她在物欲横流中丧失理智,因为金钱的收买而诬陷保润,摇身一变为白小姐时又在灯红酒绿中迷失了自己,用自己的身体担当筹码换取物质利益。最后一个个喜欢过她的男人都离她而去,她也在生下代表耻辱与愤怒的怒婴后消失,最终走向虚无。
小说中的其他人也在演绎着“欲”与“狱”,罪与罚的交响曲。保润的父母卖掉祖父的床,把他的房间租出去换得金钱,对上一代的不孝和对下一代教育的偏颇使整个家庭蒙受灾难。邵兰英用钱财买通关系侮辱法律的公正却使自己晚年承受丧子之痛。命运的绳索不会放弃对每一个有罪之人的审判。
2.绳子——罪与罚的物化形式
苏童历来是塑造意象的好手,各种看似寻常的事物在他的笔下都能被赋予各式各样的意味,王干在他的《在意象的河流里沉浮》中认为“苏童的小说是具有鲜明个性的意象小说”[5]。米、河流、兔子和白马等都在他的小说中具有深刻的寓意。绳子这一意象曾出现在他的小说《把你的脚捆起来》和《我的帝王之家》之中。在《黄雀记》中,绳子作为中心意象,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首先绳子是欲望与罪恶的实现手段。和柳生相比,保润在香椿树街上显得特别普通,他唯一的绝活就是用绳子捆人,把住在井亭医院的祖父像狗一样进行捆绑,民主结、法制结,各种花样在祖父身上轮番上演,祖父不仅失去了自由还丢失了尊严。“那堆绿白相间的绳子正在柳生的胳膊上晃荡,一圈白色的诱惑,套着一圈绿色的邪恶,一圈绿色的邪恶,套着一圈白色的虚无。”[2]45当控制欲遭遇青春期的荷尔蒙时,便使保润失去理智了。水塔的链条厚重又刺骨,它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缠绕的不仅是仙女的身体,更是三个人的命运。就连他的复仇也离不开绳子:在柳生的婚礼上,他用绳子捆绑新娘,与众人发生争执,最终保润拿刀捅死了柳生。
再者绳子代表的是对有罪之人的惩罚。“他看见了十八岁的保润,身上穿着旧时代风格的米黄色夹克,手里转动着一条长长的绳子,保润说进来,柳生你进来,我们好好谈谈。”[2]137对柳生来说,保润和仙女是他的梦魇,当他每以为自己已经摆脱那个犯罪青春的噩梦时,保润的绳子总是不时地冒出来抽打他的灵魂。他看似是一个成功者,“下海”创业,左右逢源寻求商机,与成年后的保润和仙女和平相处,但内心的阴影却一直不曾散去。“你不在,我的魂就在,你回来了,我的魂就丢了。”仙女和保润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对他来说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可以随时引爆他的生活。年少的罪恶使他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但无论他怎样赎罪,怎样挣扎,命运的绳索却还是把他越捆越牢。最后保润带着绳索出现在他的新婚之夜上,结束了这场解不开的纠葛,也许只有死亡能使他真正卸下精神的枷锁,实现永恒的救赎与自由。
小说中,对郑老板遭到惩罚的部分描写得尤为精彩,这里的绳子是作为审判者的角色而出现的,“白色的尼龙绳子来了。绿色的尼龙绳子来了……郑老板在沙发上看电视,要上厕所了,脚往沙发下一探,探到的是那根冰冷的金属绳,他当场喊起了救命,喊了几声便休克了”[2]167。如果说柳生、保润代表的是与自身命运抗争的人,那么以郑老板为代表的则是被利益蒙蔽身心、丢失善良本性的欲望者形象。柳生的母亲邵兰英、保润的母亲栗宝珍又何尝不是这样。栗宝珍家破人亡,邵兰英晚年丧子,郑老板年纪轻轻就患上疾病整天生活在心惊胆战之中,绳索是公正的,它总是能够在不经意间做出最终的判决,无人可以幸免,无人可以逃脱。
三、“灵魂无处安放”——作者在欲望面前的救赎困境
“生活仍在演进,时代步伐的每一个阶段正在制造着香椿树街的新内容,但灵魂依然是我们的人生难题。”[6]保润为了自己青春期的冲动而失去了十年的自由,心灵被仇恨所占据,就在他的善良天性再一次战胜人性的缺陷,决定放下仇恨,与生活握手言和时,命运又再一次将他摧毁。柳生多年的自我救赎也最终无果,正如苏童所言,“柳生不是拉斯科尔尼科夫,无宗教信仰,无抽象的思考习惯和能力,他是以人情世故对待一切的,包括赎罪”[7]。他以为自己改过自新是个好人了,然而菩萨面前的一张暴露真相纸条可以瞬间把他打回罪恶的原形。同样,仙女在欲望的河流中也没有突围成功,她在金钱的幻象中无法自拔,自己却浑然不觉。尽管她在庞太太的斥责中终于懂得自我审视,妄图在河流中洗涤掉自己的肮脏,然而诞下的那个红脸婴儿永不停歇的恸哭仿佛在提醒着仙女,她曾有过的羞耻终究无法洗脱且不能被遗忘。
每个人都是不彻底的人,他们在欲望中沉沦,在沉沦中得不到救赎。文中的人物好像都在逃,逃离困境,逃离自己不想面对的生活难题,祖父一次又一次从井亭医院逃回家,柳生在探望保润时在监狱门口仓皇逃出,仙女逃出噩梦般的香椿树街……然而他们又在逃亡中受到新的诱惑,在逃亡中继续沉沦,逃来逃去始终逃不出命运这双无情的大手。小说的结尾,祖父抱着怒婴坐在水塔之外等待仙女的归来,水塔作为罪恶的发生地点,祖父作为引出故事的开端,一切仿佛回到了原点,生命就是一场轮回。
文中的庞太太手中的《圣经》只是惊鸿一瞥便匆匆退场,水塔中的菩萨金像也没能真正使有罪之人的灵魂得到救赎和安放,以个人一己之力的挣扎无法突破生命的困境,宗教信仰依然不能拯救不安的灵魂。苏童也没能给出一条很好的出路,他只好又把这一切最终归结为他善于把玩的宿命论,就像萨特说:“一切存在都是偶然的,人生也是偶然的、无所谓的、没有根据的,这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8]所有的矛盾,所有的罪恶,都是不经意的,所有的困惑也可以在命运之手下趋于虚无,像那只黄雀,看不见,摸不着,无法把握。个体如何在欲望和惶惑中突出重围,得到平和快乐,罪恶的灵魂如何才能得到救赎,难道只有像文中的祖父那样失魂进入生命的无意识状态才能得到安宁?作者在文本中并没有给出很好的答案。
四、结语
正如苏童在《寻找灯绳》中说道:“小说是一座巨大的迷宫,我和所有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小心翼翼地摸索,所有的努力似乎就是在黑暗中寻找一根灯绳,企望有灿烂的光明在刹那间照亮你的小说以及整个生命。”[9]在《黄雀记》中,作者在时代变迁中为我们展示了香椿树街上各种各样的人生图景,发现了人性中黑暗和幽微的部分,对欲望和罪恶进行毫不留情地剖白,然而在探求如何救赎灵魂和寻找灯绳的旅程中,苏童要走的路还很长。
[1] 王德威.南方的堕落与诱惑[J].读书,1998(4):70-80.
[2] 苏童.黄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3] 王昕.苏童小说的原欲意识[J].现代语文,2006(3):68-69.
[4] 葛红兵.苏童的意象主义写作[J].社会科学,2003(2):107-113.
[5] 王干,费振钟.苏童:在意象的河流里沉浮[J].上海文学,1988(8):73-76.
[6] 程得培.捆绑之后——《黄雀记》及阐释中的苏童[J].当代文坛,2014(4):19-30.
[7] 傅小平,苏童.充满敬意地书写“孤独”[N].文学报,2013-7-25(3).
[8] 萨特.厌恶及其他[M].郑永慧,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65:230-231.
[9] 苏童.寻找灯绳[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116.
责任编辑:罗清恋
Desire of Shouting——Reading Su Tong Novel“Yellowbird”
WANG Fengyu
(Liberal Arts,Anhui University College,Hefei Anhui 230000,China)
Desire is the indispensable key word in Su Tong’s novels.In the novel “The Yellowbird”,the author brought us back once again his familiar“Xiangchunshu Street”,telling to us the ups and downs,fighting and salvation in the desire of shouting of the three main characters,Baorun,Xiannv and Liusheng,and the residents in the street,under the great change from the 1980s to the new centuries of 2000.The great changes of era provide the conditions of people’s growing weakness,and prompt the rebellion of youth age,in which the desire of the Xiangchuanshu Street is diversified.Desire is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s,but if it expands,the fate will bring punishment to the people.The salvation of three main characters tells the difficulties of peace soul, which is the unbearable weight of life brought by the fate,and also shows the weak pursuit of the author.
desire;the rope;crime and punishment;soul
I206.7
A
1673-8004(2017)04-0044-05
10.19493/j.cnki.issn1673-8004.2017.04.007
2017-05-09
王凤语(1993— ),女,安徽淮南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