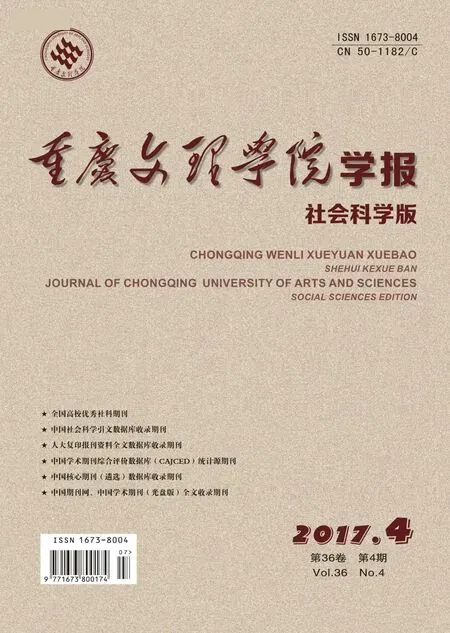川端康成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李鹏飞
(内蒙古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10)
川端康成小说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李鹏飞
(内蒙古科技大学 文法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010)
川端康成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出生态原则和女性原则相结合的创作倾向。他笔下的自然随处可见、千变万化、充溢着灵性,随着作品情节及主人公的感情波澜而变化,自然与人情完美地结合。他笔下的女性集卑微与圣洁于一体,既有早期的蕴含男性文化标记的传统女性形象,又有中后期的女性意识觉醒的追求个性独立的新女性形象。川端康成还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出发对现代文明进行了批判。他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形成与传统文化——“万物有灵观”“万物有生观”和母性文化等思想,以及他对现实生活的忧虑紧密相连。川端康成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念对我们当代生活有重要的启示和情感抚慰作用。
川端康成;生态原则;女性原则;天人合一;整体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前沿的文化和文学批评流派于20世纪90年代受到世人的瞩目。该流派是在环境恶化危机四伏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人类对女性问题和环境问题的重新审视与定位。川端康成虽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一位男性作家,却超前性地在其小说创作中从整体主义思想出发,表现出“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观,表现出对环境问题与女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与当下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不谋而合。本文拟用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分析川端康成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自然观念以及二者完美的依附关系,探究内在的成因,以及对我们的启示。
一、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是当代西方由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汇流而成的主动适应社会变革需求的文化思潮。”[1]这一思潮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繁盛于90年代。生态主义者主张为生物圈中各机体及存在物争取生存的空间,繁荣及展现自身的价值权利。女性主义者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力求争取同男性一样享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相同权利。女性主义者致力于妇女解放,生态主义者专注解决环境危机。表面上看,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毫无关联,而事实上却存在着内在指向的一致性,正如著名的生态女性主义研究者斯普瑞特耐克(C.Spretnak)指出的那样:“西方文化中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性的关系。”[2]女性与自然同处男性文化体制中被压迫者的地位,类似的生存境遇、相同的文化根源使得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在20世纪后期的工业化时代合流形成生态女性主义。
在人类早期,自然曾经是人类敬畏和膜拜的对象,但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自然逐渐为人类所熟知,并成为人类征服和无情攫取的对象。在人类看来,自然存在的价值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深层生态主义者突破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模式,倡导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的新型生态观。生态女性主义者在肯定深层生态主义者观点的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社会学上的缺陷。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女性与自然联系紧密且经常被相互指代和象征:西方古代文学中的神灵都是自然界中某种物象的化身,且女性居多。发展到后来,人类习惯将孕育万物的自然称为“自然母亲”,由此可见,女性与自然不仅渊源极深而且俱属弱势的集合概念。在此基础上,生态女性主义者对深层生态主义者所反对的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人类”构成机制进行了重新思考,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质就是“男性中心主义”,而这恰恰又是父权制文化的产物,这正是造成女性与自然受压迫的共同文化根源。因此,生态女性主义的矛头不仅指向人类对自然的攫取和破坏,而且直指男权社会下男性对女性生存空间的打压。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虽然发端于政治运动,但却在文学艺术领域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温床,为文学创作、文学鉴赏提供了新的文化语境。
二、川端康成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徜徉于川端康成的小说世界,我们认为其中蕴含着深深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在这些小说中,作者敏锐地捕捉到生活于大自然之中的人,尤其是具有自然人性的女性。她们是大自然的精灵,是大自然的女儿。值得注意的是,川端康成笔下的自然不仅仅是喜爱和赞美,而且是出自内心的崇拜和信仰,“以感恩之心体悟着自然与人合而为一的美感,追求着人与自然共荣共生、和谐相处的美好境界”[3]。同时,川端康成以此为出发点对工业文明带给自然的灾难性恶果表示不满和厌恶,对女性的悲惨境遇给予深切的同情,这显然是一种生态女性主义的意识。
(一)“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意识
人与自然本是共生共荣的,是休戚与共和谐一体的,人从本质上不是自然万物的主人和守护者,而是自然万物中的一分子。川端康成正是这样认识的,他心怀感激、热爱之情注视自然、接触自然和捕捉自然,将自己全部的身心融入自然之中,亲身感受谛听着大自然的倾诉,就像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在川端康成的小说中,随处都是日本岛国所特有的自然美景,他笔下的自然千姿百态令人应接不暇。从静态的角度看,川端康成几乎把自己生活中所见到的所有自然景观写入自己的作品中,如:天上的日、月、星辰、白云、暮霭、疾风、细雨、雪花和冰雹,地上的溪流、草原、雪山、松林、大江、大洋、温泉、樱花、球虫和落叶等,各种自然景物应有尽有。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川端康成笔下的自然景物不是呆板的,而是充满盎然生机千变万化的。如《雪国》中,“云雾缭绕,背阴的山峦和朝阳的山峦重叠在一起,向阳和背阳不断地变化着,现出一派苍凉的景象”。随着云雾的变化,连绵的山峦也在瞬息间千变万化,仿佛生命的轮回。这就是神秘的大自然,这就是自然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这也就是生命的意义。
川端康成笔下的自然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并且与人心意相通,很好地实现了“天人合一”的美好愿望。川端赋予自然以人的情感,人与自然在这里完全融为一体。如《古都》中一处描写千重子和真一在观赏樱树时的文字:“仔细一看,它确实是女性化了呀!”“不论是垂下的细枝,还是花儿,都使人感到十分温柔和轻盈……我过去从没想到樱花竟然会这般女性化。”作者赋予樱花以女性的形态和情感,这种描写不是简单的拟人化手法,而是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去审视自然,作者情不自禁地将眼中的樱花看成是一位体态婀娜、柔情款款的少女,此时人与自然融为一体难以分辨。大自然中的山川草木、宇宙万物在川端康成看来都鲜活而富有生命。又如川端康成在《我在美丽的日本》一文中,开篇便引用了道元禅师的一首和歌,“冬月拨云相伴随,更怜风雪浸月身”,这首诗表面是在写冬月、风雪,感激深夜冬月的相伴之情,而实际上是写人与自然的相融,“亲密到把看月的我变为月,被我看的月变为我,而没入大自然之中,同大自然融为一体”[4]。与自然万物亲近是日本的传统,但也可见川端康成的灵魂深处潜藏着“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意识。
(二)由男性文化标记下的女性观向“生态女性观”的嬗变
川端康成“生态女性观”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经历了由前期的男性中心主义到后期的女性崇拜的转变过程。
1.川端康成早期小说中的男性文化标记
首先,在川端康成的早期小说中,男性主人公虽然处于配角地位,但在小说中高高在上很有优越感,女性处于屈辱的地位,默默地接受来自男性的同情与爱怜。《伊豆的舞女》中的“我”是在大学读书的青年学生,接受着高等教育见过世面,属于社会中的优越群体,而“我”钟情的舞女则身处社会底层,混迹于巡回演出艺人团体。在当时,巡回艺人与乞丐被视为一类人。尽管小说处处流露出“我”对舞女的倾慕,但字里行间的性别歧视又极为抢眼,舞女在举手投足间显出身份的卑微。舞女与“我”初次偶遇时,舞女见到刚刚爬到山顶的“我”时,“马上让出自己的坐垫,把它翻过来,推到了一旁”,而“我”只是“噢”了一声就在这张坐垫上坐下,“我”从衣兜里掏出一支香烟,舞女随即将同伴身边的烟灰缸推到我跟前,我却没有表示任何谢意。“我”与舞女素不相识,却理所当然地接受舞女为我提供的便利。接下来“我”提出与巡回艺人结伴而行,舞女与“我”初次搭讪时有点紧张并且脸颊绯红。这些细节虽然表明了年轻舞女的羞涩,但也反映了“我”在舞女面前的优越感。“我”和舞女相伴行走于一条险峻的乡间小径上时,“她走在我身后,保持不到两米的距离。她不想缩短间隔,也不愿拉开距离”[4],短短两米的距离却显现出男女主人公之间身份地位的差别。在喝山泉水时,姑娘们站立在泉水周围,只等“我”喝完以后,她们才喝,在她们看来,在女人后面喝,不干净。女性的精神深处浸润着男性文化的价值观念,女性在循着男性文化的轨迹前行,男性在俯视着女性的同时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女性的服侍。
其次,在川端康成早期的小说中,男性中心的色彩极为明显,男性的自私与不负责任充斥于作品之中,女性成为男性文化的牺牲者,女性的痴情、宽容与忍耐被视为美德。《千鹤》中的菊治是个养尊处优具有虚无思想的青年。在他的思想深处既无伦理道德,又无做人的起码底线,任由情欲的支配,寡廉鲜耻形同畜生。太田夫人是菊治亡父的情妇,与菊治相差20岁左右,却与菊治发生关系。这种罪恶的结合据太田夫人讲,是由于她意识的恍惚,沉溺于情欲所造成的罪孽。之后她服药自杀。太田夫人的死似乎与菊治没有关系,非但毫无责任,而且俨然还是受害者。而事实上,菊治恰恰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他的行为上愧于父亲,下害死了太田夫人。而菊治的责任在作品中被撇得一干二净,所有的过错都归结在太田夫人身上。太田夫人作为父亲和儿子的情人,备受蹂躏,其地位不仅可悲,还要承受所有的罪责。太田夫人是沉浸于男权文化的迷恋者和牺牲者。太田夫人死后,菊治又与太田夫人的女儿文子发生了关系。文子原本极力反对母亲与菊治的交往,但在母亲死后完全改变了这种看法,不但认可了母亲的行为,而且由衷地赞叹了母亲的美。文子认识的变化体现了对男权文化的认同,男性对女性的欺凌就这样在世世代代延续,遭受践踏任人欺凌却默默承受的女性在男权文化语境下被奉为美德的化身。
2.川端康成后期小说的女性主义意识
二战后随着日本女权运动的逐渐展开,女性意识开始逐渐觉醒,传统女性观受到质疑,这些文化思潮的风起云涌多少影响了川端康成的文学创作。如《山音》《睡美人》中表现的母性救赎意识,《舞姬》《东京人》塑造的一些具有个性独立意识的新女性形象。女性主义意识的显现显示了父权文化的衰落。
首先,川端康成后期文学作品中流露出了对女性的崇拜,有着强烈的母性救赎意识。在川端康成后期的文学作品中,男性中心视角开始移位,女性地位开始上升。男性力量的孱弱渴望母性力量的拯救。《睡美人》这部小说创作于1960年,作品讲述了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江口来“睡美人旅馆”与服药沉睡中的少女同榻而眠的故事。丧失了性能力的江口面对赤裸的充满蓬勃青春气息和活力的少女思绪纷飞,“其中有着性的陶醉,更有着青春与衰老,美与丑、生与死的强烈对比和反差”[5]。表面上看小说描写了老人的垂暮之歌,而事实上该小说有着深刻的寓意。江口是位处于风烛残年的丧失了性能力的行将就木的男性,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怀恋着昔日男性中心的时光,存有对女性征服的心态,只可惜这种征服只能存在于幻想中罢了,他代表了二战后日本社会男性主体地位的颠覆以及父权制文化的衰落。熟睡中的女性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与男性主人公丑陋的外表衰老的容颜形成鲜明的对比,她们均匀的呼吸、安详的表情、无视男性主人公的存在,寓意着对男权社会的排斥、女性意识的萌动。此外,在这部作品中还潜藏着女性救赎意识,作品中的江口老人老朽不堪,缺乏生命的激情与活力,生命的本能受到压抑,内心充满了恐惧、不安、惆怅、孤独和失落,渴望在精神上得到解脱和救赎。“而女性作为生命的起源,代表着人类生命,是支撑和激发人类的生命之力,并成为人的精神救赎之力。”[6]正如川端康成所说:“儿童和女性与自然一样常常是有生命力的明镜,是新的清泉。”江口老人正是希望在与少女的肌肤接触中得到心灵的抚慰,获取生命的力量,获得精神的解脱和救赎。
其次,川端康成后期的文学作品塑造了很多女性意识觉醒、追求个性独立的新女性形象。他们有意在家庭中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执意挣脱男权中心社会所赋予女性的“家庭”“婚姻”的枷锁,渴望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坐标。二战后,随着日本法西斯的覆灭,日本传统的封建意识形态失去了存在的根基。随着西方各种妇女解放思潮的涌入,日本女性开始着手重拾自己的社会属性,探寻自己的人生价值。妇女开始尝试着走出男性的阴霾,抛开家庭的羁绊,去投身于广袤的社会生活。《舞姬》中的波子就是一个具有很强事业心的新型女性形象。由于战争的缘故,波子失去了自己的舞蹈艺术梦想,战后她把自己全部的对舞蹈的热爱放在了对女儿品子的培养上,希望女儿成为一名优秀的芭蕾舞演员,以延续自己年轻时的梦想。热衷于舞蹈事业的波子,不仅享受着舞蹈给她带来的精神愉悦,而且在舞蹈中找寻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山音》中的池田和娟子也是具有新思想的新型女性代表。战后,池田与娟子都成了所谓的战争寡妇。按照当时的习俗,她们可以选择留在夫家或选择再嫁,可她俩却选择了一条自我奋斗自我独立的道路。池田成了一名家庭教师,娟子成了一名服装设计师,虽然自我奋斗的道路上充满了艰辛和苦涩,但收获了从未享受过的自由。她们可以自由地思考,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她们也有重新组建家庭的想法,但却不首先考虑依赖男人,而是追求平等基础上的婚姻。
(三)从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出发对现代文明的批判
生态女性主义是在兼顾女性和生态原则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倡导关爱、公正和平等的伦理价值,强调所有生命形式之间的相互关联,赞同生态文化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反对一切形式的剥削与压迫,主张必要的社会变革。”[7]在这一原则支配下,生态系统将呈现出和谐性、整体性和可持续性。川端康成在感受人与自然交融的同时,也深感现代文明的发展对女性和自然的戕害,对此他感到十分痛心和忧虑。
川端康成本是一位男权意识非常突出的作家,但二战后随着民主主义思想的传入,女性有了选举权,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开展,传统的女性观日渐受到人们的质疑。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使得川端康成的女性观也在逐渐发生变化,由早期的将女性视为男性欣赏和寄托的对象,转为对女性的正面歌颂与赞美,开始涉足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权益和女性独立方面的思考和探索。如《日兮月兮》中的道子,在战后毅然离开禁锢扼杀过自己青春的丈夫,选择与情人绀野私奔,结束了在她看来地狱般的生活。之后由于情人的懦弱无法给她带来真正的幸福,她再次选择了离开,然后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作品中的道子虽然没有找到一条独立生存的道路,但毕竟在爱情面前有了选择的权利,一扫传统女性的恭顺忍耐的“美德”。川端康成在批判男性文化体制对女性人身自由束缚的同时,也期待女性能够获得同男性一样的自由。类似的新型女性形象在川端康成后期的小说中还有很多,如《舞姬》中的波子、《东京人》中的朝子和《山音》中的菊子。
川端康成在关注女性的同时也在审视日渐枯竭的自然。自然与女性一样,也是生命的赋予者和象征者。自然本有强大的繁殖能力,但由于以男性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资源的毁灭性开采,使得我们人类赖以世代繁衍生息的地球不堪重负,气候变暖、物种消失、资源枯竭和乱砍滥伐等现象触目惊心。在《古都》中苗子就曾感慨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在这个世界上,要是没有人类,也就不会有京都这个城市。这一带就可能成为自然森林,或者草原荒野,说不定还是野鹿和山猪的天地呢。人类干么要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这是多么可怕啊,人类……”[4]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被打破,身为女性的苗子在感叹自己悲惨命运的同时,也在感叹被人类破坏的自然,自然与女性的命运何尝不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呢?
三、川端康成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形成的原因及对我们的启示
(一)川端康成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形成的原因
首先,川端康成是一位坚守日本传统文化、致力于表现日本民族性格、展示日本美的作家。川端康成本人也承认,要做一个日本式的作家,写出真正日本式的东西。
1.受日本传统的“万物有灵观”和“万物有生观”思想的影响
日本人受到美丽岛国自然环境的恩惠和培育,对自然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切感。在他们看来自然万物与人类一样有着鲜活的生命,具有强盛的生殖力。这种思想可以最早追溯到日本民族早期的神话中。日本神话起初是自然神话,在日本民族的先民看来,自然不仅与人一样拥有生命,而且更为神秘。《古事记》《日本书纪》中就记载有许多自然神话的故事。同样,早在日本绳文时期的陶器上也刻有植物的花纹,以此表现对植物生命的信仰。日本先民这些对自然万物的认识体现了他们朴素的人生观:“既不把人的存在当作世界的中心,而把外在世界当作无生命的素材或工具,也不单纯地认为只有人才拥有情感和精神,而是把自然与人看作同体的、同情同构的:自然就是看得见的精神,精神则是看不见的自然。”[8]可见,日本早期对自然的认识与我们今天的生态主义学者所倡导的整体主义思想是相通的。
2.受日本传统母性文化的影响
日本是一个充满母性文化传统的国家,这种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早期的创世神话。据《古事记》记载,伊邪那歧和伊邪那美二兄妹是日本最早出现的神。兄妹二人奉天神的命令从天而降,兄妹结合产下山川岛屿、花草树木及主宰万事万物的天照大神——天阳女神和八百万神。其中天照大神是万物的主宰,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了类似古希腊神话中宙斯的角色。与古希腊神话不同的是,日本的天照大神是位女性。由此以后,天照大神成为日本国民心中神圣慈祥的母亲,这也形成了日本早期女性崇拜的文化心理。事实上,日本神话中反映的女性崇拜心理也反映了日本漫长的母系社会的真实情形。由于自然环境和诸多历史原因,日本经历了漫长的母系社会,那是一个绝对女性中心的世界,女性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注重女性血缘谱系的传承而淡化男性的存在。这种女性中心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奴隶社会后期。之后,由于外来文化传入,特别是中国的儒家思想文化的传入,日本传统的女性崇拜观念开始淡化,终被男尊女卑的男性文化所取代。从“女性崇拜”时代到“女性失落”时代,一方面集体意识中经历了对女性的遗忘、怀疑和指责,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放眼望去都是对女性的玩弄和蔑视;另一方面集体无意识中还潜藏着对母性的留恋和追忆,反映到文学中就是对女性的赞美和崇拜。由此可见,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对女性怀有敬畏和蔑视的二重心理。
3.川端康成的生态女性意识也源于对现实生活的忧虑
尽管日本民族是一个对自然怀有特殊感情的民族,但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不断加快,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自然还是惨遭人类的破坏。尽管二战后日本的女性地位有了一些改观,但放眼整个日本社会,对女性的轻蔑和不屑依然是社会的主流认识。以男性为主导的人类社会对自然的无情攫取和对女性的压迫在20世纪后期的日本愈演愈烈。残酷的现实触动着川端康成敏锐的神经,使得作家重新思考和梳理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等诸多现实问题,在创作中贯穿着生态女性主义的理念。
(二)川端康成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对我们当代生活的启示
川端康成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在环境恶化、男女比例失衡和价值观念缺失的时代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去反省和深思。
首先,从“整体主义思想”出发兼顾人类发展和环境保护,重塑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的关系。长久以来,西方传统文化中的认识误区割裂了人与自然、科学与价值的统一,造成了人类与自然的对立。这种狭隘的认识使得人类只顾追求眼前的利益,忽视人类的长久利益,盲目地破坏生态平衡,浪费自然资源。这种主客对立的认识思想在破坏环境伤害自然的同时,实际上最终还要损害人类自身的利益。生态女性主义的观念正是对这一思想的反拨和纠正。生态女性主义从整体主义思想出发,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人类对女性的压制这两个问题,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实质是指男性中心主义)在作怪,主张推翻男性主导的陈旧文化模式,建立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和谐、包容、平等和共生共荣的关系,这样才有利于地球上一切生命物种的健康、可持续地发展。因此,川端康成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念对我们当代生活有重要的启示和警示作用。
其次,川端康成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既可净化心灵也可陶冶情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又是一个各种文化思潮泛滥的时代,面对残酷的竞争与淘汰,在欲望与利益的诱惑下,读者的审美观难免会出现偏差,甚至扭曲。而川端康成的生态女性主义审美观念将读者的审美视野引向生机盎然的自然和秀美多姿的女性,引导读者重温女性与自然的完美交融,感受人与自然的亲密无间,从而净化人的心灵,培养人爱护自然、保护环境的生态观念。
川端康成小说创作中所蕴含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为当代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素材,也为当代生态女性主义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1] 关春玲.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1996(2):25-30.
[2] 查伦·斯普瑞特奈克.生态女权主义建设性的重大贡献[J].秦喜清,译.国外社会科学,1997(6):62-65.
[3] 王艳凤.论川端康成散文创作的生态审美意识[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83-88.
[4] 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小说选[M].叶渭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5] 王向远.东方文学史通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6] 邓桂英.女性·爱·救赎·回归——从《山音》看川端康成的女性崇拜观念[J].船山学刊,2009(4):223-226.
[7] 李鹭,殷杰.生态女性主义的科学观[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1):60-65.
[8] 邱紫华.东方美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责任编辑:罗清恋
Interpretation of Eco-feminism in the Novels of Kawabata Yasunari
LI Pengfei
(School of Humanities&Law,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Technology,Baotou Neimenggu 014010,China)
The novel creating of Kawabata Yasunari shows the tendency of combination of ecological principle and feminine principle.The nature in his works is everywhere,ever-changing,and full of intelligence,changing with plot and emotional fluctuation of the main characters,perfect combination of nature and humanity.The female in his works combine the humble with the purity, in which there are traditional female image marked by the male culture in the early period,and also there are new female image with the feminine consciousness awakening pursuing the individual independence.Starting with the eco-feminism,Kawabata Yasunari criticized the modern culture.The formation of his eco-feminism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ulture,such as the idea that everything has spirit and life,and the concern of modern life.His eco-feminism consciousness has inspirations and mental comfort on the modern life.
Kawabata Yasunari;ecological principle;feminine principle;the unity of heaven and people;collectivism
J905
A
1673-8004(2017)04-0049-06
10.19493/j.cnki.issn1673-8004.2017.04.008
2017-03-06
李鹏飞(1978— ),男,内蒙古包头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日文学及文化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