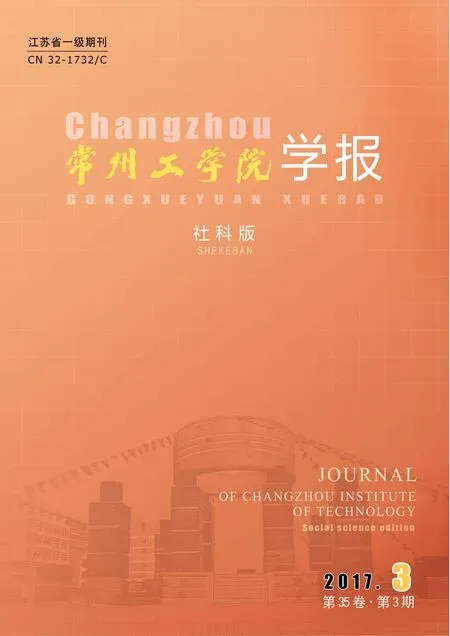“无名女人”的神话原型阐释
金婕煜,丛佳红
(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无名女人”的神话原型阐释
金婕煜,丛佳红
(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作为近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批评理论,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为文学的创作、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文章借助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剖析汤亭亭作品《女勇士》中的“无名女人”,阐述了替罪羊、夜莺及美狄亚这三个原型与“无名女人”之间的联系,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学是移位的神话”。
神话原型批评;《女勇士》;替罪羊;夜莺;美狄亚
作为近代西方文学批评史上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批评学派,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得益于文化人类学、运用心理学及象征哲学的发展[1-2]。通常情况下,我们将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发展历程分为三阶段,主要代表人物分别为: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卡尔·荣格及诺思罗普·弗莱。其中,弗莱作为该理论研究方面的集大成者,在其著作《批评的剖析》中强调神话是所有文学模式的原型,从神的诞生、历险、胜利、受难、死亡直到复活,包含了文学所涵盖的一切故事[3]。因此,作者们往往会基于某些特定的神话来创作文学作品,这也使得文学作品间可能存在共通性。但在创作时,原型也会被加工,出现移位、变形,所以文学又被称作“移位的神话”[4]。
无名姑姑出自华裔女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女勇士》。全书的第一章节主要讲述了作者姑姑的悲惨遭遇。在那个生活困苦的年代,姑姑因婚后与人通奸而受到了来自村民及家人的惩罚,最终在猪圈中分娩产子并选择同孩子一道投井而亡,自此成为家中不能提及姓名的“无名女人”。细考文中对无名姑姑的种种描写,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所蕴含的神话色彩。汤亭亭突破了文学创作中对原型的单一运用,独具匠心地将三种神话原型进行演变使其与东方文化融合,创作出了一个具有“三面特性”的无名姑姑。本文拟从神话原型批评的角度入手,着重探讨无名姑姑与替罪羊、夜莺及美狄亚这三个原型的相似性,从而进一步剖析该章节的思想内涵。
一、坠入渊薮的替罪羊
替罪羊的原型最早在《旧约》中有所提及。《旧约·创世纪》第22章描述,为检验亚伯拉罕的忠诚,上帝命他将自己的儿子带到约定的山头并把儿子作为燔祭。遵照上帝的指示,亚伯拉罕果真将自己的儿子带到了上帝所指示的地方。就在他要动手杀子的时候,上帝感受到了他的忠诚,从天而降制止了这场悲剧的发生。与此同时,一只公羊恰巧在附近出现,亚伯拉罕便将这只公羊杀死,代替他的儿子作为祭品,献给了上帝。自此之后,羊便常常被人们当作替罪之物,久而久之便产生了替罪羊的说法。
在汤亭亭的描述中,无名姑姑无疑是封建礼教的替罪羊。人类学家勒内·吉尔拉认为,人们在选择替罪羊时,女人、儿童和老人等弱者最易被选中[5]。身负父权制社会强加于女性的枷锁,无名姑姑这个可怜的弱女子在婚姻与爱情面前显得既无助又无畏。婚后不久,丈夫便离家赶往美国,留下她一人面对着前路的坎坷,维系着脆弱的婚姻,时间久了,她甚至连丈夫的模样都记不清了,只得靠临行前的一张黑白照片来极力回忆[6]5。然而,在这样一场令人唏嘘的婚姻背后,是什么原因让她违背“三从四德”的教诲,选择与人通奸呢?正如汤亭亭在书中所推测的那样,她或许是遭人恐吓被迫和他发生了关系[6]5,或许她真的爱上了某个人,他多情的目光、柔和的声音、缓慢的步子,无一不在牵引着她离家[6]7。但无论是哪种推测都没能改变她替罪羊的命运。
倘若无名姑姑真的是遭到胁迫而不得不与他人发生关系,那她便是真正意义上的受害者。可不幸的是,在一切发生后,她非但没能得到大众的同情,反而沦为了封建礼教的替罪羊。生活在父权制社会下的人们崇尚“男性至上”,这迫使女人有时候不得不去承担男人所犯下的罪责。无名姑姑也是这样,在她通奸的行为被村民们发现后,没有人关心与她发生关系的男人到底是谁,大家只是一股脑地将所有怨气都撒在她一人身上。“在孩子出生的夜里,村民们袭击了她家,一开始是扔污泥和石块,紧接着便开始杀牲口,将血涂抹在墙壁上,而后便是将家中的厨房和无名姑姑的房间一并毁掉,最终离开的时候也不忘从牲口上割下几块肉,拿走没被砸坏的碗和撕烂的衣服。”[6]3汤亭亭在书中将村民们的愤懑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也让我们不禁去同情她的这位无名姑姑,如果这种假设真的成立,那村民们的暴行和家人的指责便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另一种假设就是无名姑姑真的爱上了某个人,自愿与其发生关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段不被大众接受的感情或许就成了她不幸人生中最突如其来的幸运。相较于恋爱自由的当今社会,无名姑姑生活在一个婚姻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时代。作为家中的独生女,父母把她送到丈夫家后,就将财产分割给了其他几位兄弟,指望她能在婆家遵循传统的方式生活[6]6。可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丈夫又长年累月在异国务工,她的生活又怎会幸福?因此,她或许就这样爱上了别人,只能通过这种不被大众接受的方式来维系彼此间的情感。可封建礼教下的社会又怎能容得下她的错爱?正如书中所写的那样,“通奸在正常年景或许只是一种错误,但在村民们闹荒凉的时候就成了一种罪过”[6]11。封建礼教下的迂腐思想和贫穷社会总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罪与罚,这也使得饱受压迫的人们党同伐异,寻求宣泄情绪的出口。因此,在这种环境下,无论哪种假设是真的,无名姑姑都不会为社会所同情,都要有人牺牲,只是这次她不幸沦为坠入渊薮的替罪羊罢了。
二、摆脱桎梏的夜莺
菲勒美拉又被称为夜莺,其原型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神话中。她是雅典国王潘底翁的小女儿,姐姐普鲁丝妮是色雷斯国王泰诺斯的妻子。远离故土多年后,普鲁丝妮十分挂念远在家乡的妹妹菲勒美拉,于是便请求泰诺斯将妹妹接来与她团聚。可在返程的路上,泰诺斯却因嫉妒菲勒美拉的美貌而心生歹意,割掉了她的舌头并将她囚禁在一间茅屋内。事后,泰诺斯欺骗妻子说妹妹在返程途中身亡,但在多年后普鲁丝妮发现了真相。得知真相的普鲁丝妮赶忙救出了菲勒美拉。为了复仇,姐妹俩杀死了泰诺斯的儿子,泰诺斯也因此要与她俩大战一场。最后,众神为了阻止这场恶斗,就将泰诺斯和普鲁丝妮分别变为了戴胜鸟和麻雀,同时,菲勒美拉也恢复了她的声音,但自此之后她便化身为一只夜莺,只能在寂静的夜晚诉说着自己的苦楚[7]。
在无名姑姑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她与菲勒美拉这个原型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她们都有姣好的容貌,只是这出众的外貌却让她们沦为罹难者。根据汤亭亭的描述,我们可以体会到无名姑姑在村里与众不同。“所有已婚妇女都将头发剪短,垂在耳边,或者紧紧地梳成发髻,拢在耳后……”[6]7,而婚后的无名姑姑却不同于村上的其他人,她对自己的外表尤为上心,会去揣测对方的喜好,而不时地改变搭配的颜色和款式,也会将自己的头发梳成“别具一格的发髻”[6]7。不仅如此,对于自己外貌上的一点瑕疵她也无法容忍,“拔汗毛、挖雀斑”[6]8,她尽其所能地展现出她所有的美。只可惜她的美却没能给她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村民们的注目,其他男人的觊觎,都加剧了她的不幸。虽然神话中并没有对菲勒美拉的外貌作详细的描述,但从泰诺斯的嫉妒心以及他后续的行为来看,菲勒美拉也具有出众的外貌。此外,无名姑姑在遭遇上也同被割舌的菲勒美拉极为相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无名姑姑的故事可以算是菲勒美拉神话的移位叙述。尽管她并没有真正被割去舌头,但她却仿佛被人扼住了咽喉而不得发声。在整个章节中,充斥着村民的责骂和家人的责怪,但作为主人公的无名姑姑却没有一句独白。这种巧妙的布局并非偶然,而是为了凸显妇女在传统父权制社会下话语权的丧失。在欧洲近代早期,人类学家就已指出,女人相较于男人而言处在社会的较低层次。在自然与文化二元对立的假设下,自然与女人联系在一起,文化与男人联系在一起,也正因如此,女性在文化、社会的各项等级秩序中才会处在一个较低的位置[8]。传统父权制下的女人更是如此,男人主宰着社会和女人,整个社会都尊崇“男权至上”“三从四德”等思想。但不同于其他墨守成规的传统妇女,无论是菲勒美拉还是无名姑姑,她们都并没有因为外界的胁迫而选择沉默不语,即使被割去了舌头、扼住了咽喉,她们也在试图用自己“女勇士”一般的行为来打破沉寂。如同菲勒美拉不懈的反抗那般,无名姑姑的通奸行为可以说是对父权制社会的公然挑战。此外,在故事的结尾,无名姑姑选择了投井而亡,这更是一种菲勒美拉般的复仇。菲勒美拉通过杀死泰诺斯之子来发泄自己的怒火,激起对方的愤怒与悲痛,而无名姑姑偏偏选择了投井的自杀方式,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她的复仇之心。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水鬼”有一种畏惧之心,认为溺水而亡的人的灵魂会徘徊在水边,等待着下一个落水者来当自己的替死鬼[9]。无名姑姑生前无力去抵抗那些夜袭家中的村民,但是她却用自己的死来实现了复仇。在那个贫困的年代,作为一个饱受压迫的妇女,无名姑姑选择在人们赖以生存的井水中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她所能做出的最直接的报复行为。因此,在她选择结束生命的时候,她就宛若神话中摆脱桎梏的夜莺,只是自此之后她无法像菲勒美拉那样在静谧的夜晚诉说自己的苦楚,只能静静地待在井底。
三、敢于反抗的美狄亚
在古希腊神话中,美狄亚也被称为绝望的复仇女神。她本是科尔喀斯国的公主,却与前来盗取金羊毛的伊阿宋一见钟情,之后她便毫不犹豫地帮助自己心爱的人获取金羊毛,甚至不惜与父亲反目,同时还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多年以后,就在美狄亚年老色衰之时,伊阿宋却为了王位而弃她不顾,迎娶了柯林斯国的公主。直到这时,深受爱情蛊惑的美狄亚才如梦初醒。最终,心灰意冷的她杀死了柯林斯国的公主和自己的两个儿子,而伊阿宋也在对美狄亚的仇恨中拔剑自刎[10]。
除上文所提及的替罪羊和夜莺这两个原型之外,我们也能从无名姑姑身上挖掘出她与美狄亚的相似之处,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她们的杀子行为。通过比较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主人公们的杀子行为往往都是一种无奈之举。无名姑姑同美狄亚一样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美狄亚先后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和柯林斯国的公主,因此她的孩子注定要活在复仇的阴影下。同样,无名姑姑的通奸行为被视为那个年代不可饶恕的罪行,她的孩子也必然会因为母亲的过错而在日后承受村民的指指点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两位母亲别无选择,只能亲手结束自己孩子的生命。除了美狄亚与无名姑姑,我们会发现杀子这种行为在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无论是歌德的《浮士德》、乔治·艾略特的《亚当·比德》,还是托尼·莫里森的《宠儿》都出现了母亲杀子的情节[11]。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行为也可视为一种女性意识觉醒的标志,不堪长期压迫的女性,终于化身为具有反抗精神的复仇者,只是这样悲凉的复仇方式着实让人感到心酸。
四、结语
作为《女勇士》中的典型人物之一,无名姑姑这一形象的塑造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弗莱关于“文学是‘移位神话’”的说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该作品的成功离不开汤亭亭华裔作家的身份。汤亭亭作为第二代美籍华裔,清贫的童年生活、母亲娓娓道来的神话故事以及西方圣经文化的灌输,都对她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位西方评论家曾说:“没有一部文学经典作品仅仅是由于它巧妙或写得不错而流芳百世的,它必须有几分普遍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可能含有原型的成分。”[12]正因如此,《女勇士》中的无名姑姑这一形象才能在诸多女性角色中脱颖而出,成为读者心中真正的“女勇士”。
[1]杜志卿,张燕.《秀拉》:一种神话原型的解读[J].当代外国文学,2004(2):80-88.
[2]王萃萃.土地原型与诗性文化[D].南昌:南昌大学,2008:2.
[3]黄明嘉.寻觅莱茵河底的“宝物”:伯尔小说的神话原型蠡测[J].外国文学评论,1998(1):80-86.
[4]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M].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8-10.
[5]勒内·吉拉尔.替罪羊[M].冯寿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23.
[6]汤亭亭.女勇士[M].李剑波,陆承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7]NORTHROP F,JAY M.Biblical and classical myths:the mythological framework of western culture[M].Toronto Buffalo London: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04:312.
[8]卡洛琳·麦茜特.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M].吴国盛,吴小英,曹南燕,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159.
[9]鲁春林.现代美国的神话 文化融合的桥梁:汤亭亭小说《女勇士》的原型解读[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9:13.
[10]杜翠琴.试论美狄亚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及意义[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S1):169-171.
[11]杨慧.西方“美狄亚”与中国“杀子”、“弃妇”叙事比较研究[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36-139.
[12]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厄尔·雷伯尔,李·莫根.文学批评方法手册[M].姚锦清,黄虹炜,叶宪,等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241.
责任编辑:赵 青
10.3969/j.issn.1673-0887.2017.03.003
2017-03-24
金婕煜(1994— ),女,硕士研究生。
I106 4
A
1673-0887(2017)03-0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