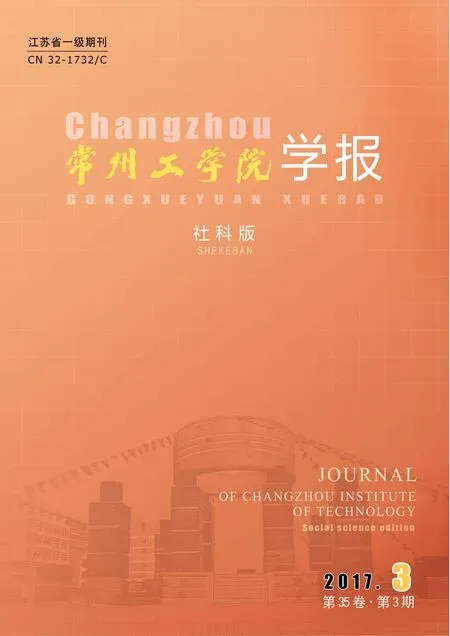唐寅诗歌与明中叶吴中独抒情怀之文学思潮
姚瑶
(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400700)
唐寅诗歌与明中叶吴中独抒情怀之文学思潮
姚瑶
(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400700)
唐寅以其一生行藏和体悟所创作的诗歌,充分表现了其奋发情怀、生命情怀、失落情怀、及时行乐情怀、隐逸情怀和宗教情怀,呈现出独抒情怀的文学风貌。这一文学风貌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明中叶吴中独抒情怀之文学思潮的体现。此种文学思潮与前七子复古思潮差不多处于相同时段,却又相对独立于复古思潮而存在,它产生于明中叶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之下,代表人物众多,影响广泛而深远。
唐寅;诗歌;独抒情怀;文学思潮
有明一代,整体而言,复古思潮占据文坛主体地位。复古诗风自明初以来就存在,宋濂即提出过复古主张。到了明中期,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两代皇帝重用“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文学也被三位馆阁大臣统治。他们继承了六朝遗风,倡导平正典丽的文风,文坛出现了千篇一律的“台阁体”。当时,由李东阳领导的茶陵派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旨在纠正台阁文风。其后,又有前七子,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抨击台阁文风。明中期还有高扬唐宋八大家旗帜的唐宋派发出了复古的弦音,提倡唐宋文风,强调文以明道。可见到了明中期,复古思潮笼罩了当时的文坛。但是在复古主潮之外,重视独抒情怀的文学思潮却在吴中地区悄然展开。“这一发生于吴中的文学思潮,没有形成明确的团体,没有公推的领袖人物,只是由于趣味的相近而形成思潮。但是它影响广泛而深远。”[1]3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有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徵明等。其中,又以唐寅的诗歌创作最能体现自适狂放、独抒情怀的文学风貌。
一、唐寅诗歌中独抒情怀的文学风貌
唐寅,字伯虎,后改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等,苏州吴县人。生于明成化六年(1470年),卒于明嘉靖二年(1523年),明中期著名诗人、书画家。诗文上,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绘画上,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又称“明四家”。唐寅才华横溢,自诩“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可是,这样一位文坛奇才却命途多舛,其人品诗文在当时以及后世的主流文化中都没受到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唐寅的诗歌创作体现了一种重视独抒个人情怀的文学思想与观念,同时,他也以其创作实践,推动了吴中独抒情怀之文学思潮的发展。
(一)奋发情怀
唐寅自幼聪明伶俐,少年时即有才名。早年的他充满侠骨壮心,表现出奋发向上的情怀。他幻想自己成为汉唐边塞抗敌的侠客、将领,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如《侠客》:“侠客重功名,西北请专征。惯战弓刀捷,酬知性命轻。孟公好惊坐,郭解始横行。相将李都尉,一夜出平城。”[2]9像陈遵那样的侠客仅凭名声便可以让人震惊,像郭解那样的侠客行动起来更是无所顾忌,他们身上投射了诗人的理想与追求。又如“功成筑京观,万里血糊涂”(《出塞二首》(其二))[2]8,豪情万丈,慷慨激昂。在《紫骝马》一诗中,诗人借紫骝马诉说了“阴山烽火急,展策愿超骧”[2]8的愿望,名为写马,实为喻人,“展策”“超骧”正是他要在国家需要之时一展雄才的自况。
与其他文人士子一样,唐寅也有求取功名之心。如《夜读》:“夜来欹枕细思量,独对残灯漏夜长。深虑鬓毛随世白,不知腰带几时黄。人言死后还三跳,我要生前做一场。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2]87“人言死后还三跳,我要生前做一场”是唐寅备战科举的宣言,也体现了他希望通过科举取士成就一番事业的奋发情怀。
据《明史·文苑传二》记载:“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性颖利……举弘治十一年乡试第一,座主梁储奇其文,还朝示学士程敏政,敏政亦奇之。”[3]唐寅才华横溢,人以为奇,乡试第一,春风得意,名震江南。他踌躇满志,蟾宫折桂似乎指日可得。他在《领解后谢主司》一诗中云:“壮心未肯逐樵渔,泰运咸思备扫除;剑责百金方折阅,玉遭三黜忽沽诸。红绫敢望明年饼,黄绢深惭此日书;三策举场非古赋,上天何以得吹嘘。”[2]58此时,唐寅满怀信心,期待着会试夺魁那一天的到来。进京之后,唐寅不断受到追捧与瞩目,据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载:“至京,六如文誉籍甚,公卿造请者阗咽街巷……是时都人属目者已众矣。”[4]唐寅自己也表示:“若肆目五山,总辔辽野,横披六合,纵驰八极。无事悼情,慷慨然诺。壮气云蒸,列志风合。戮长猊,令赤海。断修蛇,使丹岳。功成事遂,身毙名立。斯亦人士之一快,而寅之素斯也!”(《上吴天官书》)[2]219由此,可以窥见唐寅当时的年少疏狂和目空一切的豪情,其建功立业、奋发作为的情怀跃然纸上。
(二)生命情怀
弘治七年(1494年),唐寅25岁,父广德殁,妹、母、妻亦相继而逝。其后弘治十二年(1499年),好友文徵明之父文林(唐寅常随其游宴)卒于温州任所。亲近之人相继离世,唐寅在精神上遭受到沉重的打击,他深感死生无常,对生命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在《与文徵明书》中他曾写道:“不幸多故,哀乱相寻,父母妻子,蹑踵而殁,丧车屡驾,黄口嗷嗷。”[2]221《白发》《伤内》两首诗最能表现他的生命情怀,前者哀父母,后者悲亡妻,感情深挚而自然。《白发》诗云:“清朝搅明镜,元首有华然。怆然百感兴,雨泣忽成悲。忧思固逾度,荣卫岂及哀。夭寿不疑天,功名须壮时。凉风中夜发,皓月经天驰。君子重言行,努力以自私。”[2]11《伤内》又云:“凄凄白露零,百卉谢芬芳。槿花易衰谢,桂枝就销亡。迷途无往驾,款款何从将?晓月丽尘梁,白日照春阳。抚景念畴昔,肝裂魂飘扬。”[2]13二诗感怀生命寿夭无常,一切皆流,无物常住,逝者如斯,世人都只是暂时寄居在天地之间的过客而已,一如苏轼曾经悲叹:“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5]147抚今追昔,感怀生命,不禁肝肠寸断。
死生无常,不知何时即走向死亡,这样看来,人生是极其短暂的,唐寅在诗歌中也写了他对生命短暂的哲学思考。如《七十词》:“人年七十古稀,我年七十为奇。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中间只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算来只有二十五年在世,受尽多少奔波烦恼。”[2]31用明白如话的语言,道出生命“只有二十五年”的严酷事实,揭示出了人生苦短的真谛,而这期间又要经受无尽的烦恼与奔忙,着实引人深思,发人深省。相似的还有《和沈石田落花诗三十首》(其十九):“万紫千红莫谩夸,今朝粉蝶过邻家。昭君偏遇毛延寿,炀帝难留张丽华。深院青春空白锁,平原红日又西斜。小桥流水闲村落,不见啼莺有吠蛙。”[2]69表达了对韶华易逝、生命短暂的无奈之感。
生命短暂,死生无常,领悟至此,已极易产生人生如梦的幻灭感,东坡即有词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5]93看过了生死寿夭,经历了悲欢离合,唐寅对生命、对人生有了更深切的体悟,发出了“人生水上泡”“铅华梦一场”“浮世真成梦”的感慨,人生如水中月、镜中花,如梦似幻,似假还真,虚无缥缈,捉摸不定,这种浮生若梦的幻灭感成为了唐寅生命情怀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唐寅之生命情怀并没有止于浮生若梦的感慨,而是在他死前得到了升华,达到了超越生死的境界。在《伯虎绝笔》中云:“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无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飘流在异乡。”[2]159唐寅从宇宙本体论的意义上来理解人生,理解生命,无限感慨。平生万般烦忧磨难,最终皆为怡然的达观所稀释,就连地府也无所畏惧,把死亡当成又一次不经意的自我放逐,如此高超的人生玄思,正是唐寅生命情怀的终极体现。
(三)失落情怀
唐寅以其绝世之才华,应天府试举第一,却在弘治十二年(1499年)的入京会试中陷入了科场舞弊案而终身遭到废放,当时之惨状,在《与文徵明书》中表现得非常彻底:“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诏狱。身贵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涕泗横集,而后昆山焚如,玉石皆毁;下流难处,众恶所归……海内遂以寅为不齿之士,握拳张胆,若赴仇敌。知与不知,毕指而唾,辱亦甚矣!”[2]222本该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6],却不料锒铛入狱,身被刑具,还要面对胥吏审问呵斥,遭受世人的指责唾骂。从众人交相称赞的风流才子,沦落为海内不齿的阶下囚徒,人生际遇的巨大落差给唐寅带来沉重的打击。加之父母亲友相继逝世,还有“僮奴据案;夫妻反目;旧有狞狗,当户而噬”(《与文徵明书》)[2]222,妻子与他吵闹,僮仆对他无礼,就连家中的看家狗也似乎染上了人间的势利,对他狂吠不已。此时唐寅之心情,岂一个痛字了得!因此,他的诗歌中也表现出情感的失落,呈现出一种失落情怀,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怀才不遇之叹。唐寅胸怀奇才,自诩“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但得不到赏识与重用,祝允明在为他写的墓志铭中即道“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摈”[2]548。他坎坷一生,贫困凄苦。正如韩昌黎曾经感慨“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7],这可以说是对唐寅一生的最好注解。唐寅也企盼着能遇见自己的伯乐。如《和沈石田落花诗三十首》(其一)中的“六如偈送钱塘妾,八斗才逢洛水神;多少好花空落尽,不曾遇着赏花人”[2]65,《和沈石田落花诗三十首》(其十二)中的“花开共赏物华新,花谢同悲行迹尘;可惜错抛倾国色,无缘逢着买金人”[2]68,《山家见菊》中的“可惜国香人不识,却教开向野翁家”[2]91。他以花自喻,期盼能遇着赏花人、买金人、识香人,却终究一人花开,一人花落,无人问津。怀才不遇、不为人知、命途多舛的失落与无奈尽寓其中。此外,唐寅在诗中也曾直抒胸臆,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如《赠徐昌国》中写道:“书籍不如钱一囊,少年何苦擅文章。十年掩骭青衫敞,八口啼饥白稻荒。”[2]60生计艰难、落魄困窘的境地更加剧了诗人的不遇之叹。
其次是壮志难酬之感。唐寅科场一案,海内尽知,人人皆以为不齿。唐寅求取功名、建功立业的梦想破灭,仕途断绝,可谓壮志难酬空遗恨。《又漫兴十首》集中表现了其壮志难酬之感,选录如下:
此生甘分老吴阊,宠辱都无剩有狂。秋榜才名标第一,春风弦管醉千场。跏趺说法蒲团软,鞋袜寻芳杏酪香。只此便为吾事了,孔明何必起南阳!(其二)
久遭名累怨青衿,不变贫交托素歆。去日苦多休检历,知音谅少莫修琴。平康驴背驮残醉,谷雨花坛费朗吟。老向酒杯棋局畔,此生甘分不甘心。(其三)
落魄迂疏自可怜,棋为日月酒为年。苏秦抖颊犹存舌,赵壹探事囊没钱。满腹有文难骂鬼,措身无地反忧天。多愁多感多伤寿,且酌深怀看月圆。(其七)[2]83-84
诸葛孔明“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8],一生怀抱着兴复汉室的雄心壮志,六出祁山,以图统一天下,却不幸病死军中,遗恨千古;苏秦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列国,成功组建六国联盟,合纵抗秦,却不料联盟破裂,秦一统天下,他被车裂而亡;赵壹刚正不阿,不愿同流合污,多次受到排挤和迫害,几致于死,“思飞不得,欲鸣不可”(《穷鸟赋》)[9],正是其困窘之态。此三者,皆为壮志未酬之人,唐寅借此表达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愤与感叹。纵使秋榜才名第一,满腹才华,也难实现一己之志,如此这般,怎能让人心甘?“此生甘分不甘心”,体现出诗人壮志难酬的沉痛之感。
最后是对世道人心的失望之情。由于科场舞弊案,唐寅饱受世人的唾弃与指责,夫妻反目,僮仆无礼,一生坎坷,看尽世态炎凉,这在其诗作中常有体现。诸如“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秋风纨扇图》)[2]157,“莫言四海皆兄弟,骨肉而今冷眼看”(《题败荷脊令图》)[2]147,“暗笑无情牙齿冷,熟看人事眼睛酸”(《和雪中书怀》)[2]77,“贪利图名满世间”(《警世八首》其六)[2]95。在《怡古歌》中说得更为明白:“人心不古今非昨,大雅所以久不作;宣尼叹生觚不觚,良为真纯日雕琢。大禹宝鼎沉泥沙,宣王石鼓已剥落;世间耳目狃时俗,闻见安能免龌龊?”[2]35通过古今之对比,凸显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态。诗人在失意之后历尽沧桑,才会对世态炎凉有如此深切的体悟。题名怡古,是因为古之真纯而今之龌龊,诗人对世道人心失望至极,不得不转向古代寻求心灵的寄托。
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说唐寅“才情绝胜,失意后所作,多凄咽感叹之旨,往往使人欲歇欲绝,真一代之异才也”[10],可谓是对此类诗作的准确评价。
(四)及时行乐情怀
既然生命苦短,仕进无门,那么,人生应该怎样度过才有意义?——唯有活在当下,尽情享受人世的欢乐。唐寅开始了放浪形骸、狂歌痛饮、及时行乐的生活。表面看来这似乎有些颓唐堕落,但骨子里,与其说是享受,勿宁说是一种苦闷的追求。怀瑾握瑜,却无处施展自己的才华,失去了人生的终极目标与追求,只能紧紧抓住现世的享乐,使青春与才华在花酒中耗费。这样看来,唐寅及时行乐情怀的产生,亦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悲剧。
唐寅及时行乐情怀的产生与当时吴中市民关注自我、及时享乐的社会风气也有很大的关系。《五杂组》中记载:“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11]《寓圃杂记》也说:“吴中素号繁华……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12]可见吴地市民追求声色享受的生活情趣十分普遍。
在这种背景下,唐寅的众多诗作中均明显地传达出一种及时行乐的情怀。如“烹鲜热酒招知己,沧浪迭唱仍扣舷。醉来举盏酹明月,自谓此乐能通仙”(《咏渔家乐》)[2]35,“昨日醉连今日醉,试灯风接落灯风。苦拈险韵邀僧和,暖簇熏笼与妓烘”(《新春作》)[2]90,“年老少年都不管,且将诗酒醉花前”(《老少年》)[2]147,“相逢且相乐,不惜解罗襟”(《听弹琴瑟》)[2]40,“请君与我舞且歌,生死寿夭皆由他”(《闲中歌》)[2]30,“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五十自寿》)[2]79,“头插花枝手把杯,听罢歌童看舞女”(《默坐自省歌》))[2]24……饮宴赋诗,狎妓纵情,笑舞狂歌,诗酒风流,放浪形骸之外,寄情八荒之表。功名利禄皆弃之不问,唐寅活得潇洒,自在。在狂放适意的生活里纵情地享受心灵的自由与快乐。沉迷于狂醉之中,行乐于酒边樽前,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慰藉人生的苦闷与烦忧,亦不枉费短暂的一生。其乐中有悲,名为行乐,实为掩悲,乐有多深,悲即有多重,不能不令人叹惋。
(五)隐逸情怀
吴中素有隐逸的传统,前人已有论及,祝允明《金孟愚先生家传》后题词对此也有论述:“吴最多隐君子……有名隐而专与世事者,赵同鲁与哲,顾亮亦然,而金孟愚乃略同之。”[13]372元明之际的隐逸之士多集中于东南,而又以吴中的隐逸之士声名最盛。吴中隐逸之士的生活方式,一般都不会是全然地去绝尘俗,而是大隐隐于市,心隐而身不隐,在市井而离俗。他们大多居于市井之间,而不是隐匿于深山丛林,且并没有完全脱离自己的家庭及与俗世的一些交际活动。不同于世人的是,他们的心灵是离俗隐逸的。作为吴中之人,唐寅自然而然地受到此种隐逸传统的影响,在历经了理想失落、人生坎坷、世事沧桑之后,隐逸也成为他心灵的依托。通过对自然世界的心灵观照,达到忘却失落、忘却感慨的目的。唐寅此类题材的诗有三种。
一是歌咏前代隐者,表达自己隐逸的愿望。如《题画渊明卷二首》其一:“满地风霜菊绽金,醉来还弄不弦琴。南山多少悠然意,千载无人会此心。”[2]124其二:“五柳先生日醉眠,客来清赏榻无毡。酒资尽在东篱下,散贮黄金百斛钱。”[2]125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14]的隐者形象早已深入人心,通过对他的咏叹,诗人抒发了自己愿像陶渊明一样返归自然,悠然自得,享受静谧自由生活的隐逸愿望。类似的,在《题辋川》中有“高隐不求轩冕贵,且将踪迹寄烟萝”[2]98诗句,通过歌咏隐居辋川的王维,表现出诗人绝意仕途、寻求隐逸的情怀。
二是刻画当代隐者式的形象,表达自己对隐逸的向往。在七言古诗《烟波钓叟歌》中,开篇即谈到“太湖三万六千顷,渺渺茫茫浸天影”[2]34,以烟波浩荡的太湖为背景,塑造了一位“不知朝市有公侯,只识烟波好风景”[2]34的八十钓叟形象。这位浪迹江湖的老渔翁远离市井,蔑视公卿,敝屣功名,狂傲洒脱,大有隐逸之度与仙人之风,无疑是唐寅所追求的理想隐者的化身。所以在诗的后半部分,他干脆写自己也驾舟追逐渔翁于江湖之上,并称“我曹亦是豪饮客,萍水相逢话识荆”[2]34。两人情趣相投,并游太湖,饮酒赋诗,逸兴遄飞。最终诗人的形象与老渔翁的形象融为一体,这首诗成为了唐寅隐逸情怀的真实写照。与此诗相媲美的是《渔樵问答歌》[2]33,这首七言古诗通过对渔翁和樵夫两个隐者式的形象的刻画,表达了诗人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三是描摹自己桃花源式的生活,表现自我的隐逸情怀。弘治十八年(1505年),唐寅36岁,在城北桃花坞筑桃花庵别业,自号“桃花庵主”。正如祝允明所言,“治圃舍北桃花坞,日般饮其中,客来便共饮,去不问,醉便颓寝”[2]548,于鲜花盛开的私人别业中,邀请二三好友同来饮酒赋诗,挥毫作画,兴尽而归,潇洒自在,过着桃花源式的隐逸生活。吴国富在其《论唐寅适志姑苏隐游的市俗性》中认为唐寅在姑苏城隐游具有世俗性,并对其意义进行了评述——“唐寅改变了传统隐士自闭于山林或者田园孤芳自赏、只求精神自慰的老套路”,而是“居于姑苏城的一隅,却游于四方,以市井文人的身份在苏州过着一种桃花般热闹的世俗生活”[15]175。桃花庵是唐寅的隐逸世界,它自成一方天地,在市井而又超俗。唐寅遨游于此间,自由而快乐,恍如世外桃源之遗民。如《把酒对月歌》:“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2]22唐寅仰慕谪仙、酒仙、诗仙李白,自称“桃花仙”,虽然没有李白那样得到皇帝征诏的经历,但也有他那种豪放不羁的禀性,“不上长安”倒也乐得自在,在姑苏城外的桃花庵中对月赏花,饮酒自乐,呈现出潇洒闲适的隐逸情怀。同样的,七言古诗《桃花庵歌》也展示了唐寅的隐逸情怀。此诗前八句写诗人于桃花庵中半醉半醒、似仙非仙的隐居生活,后十二句写他在荣华富贵与闲居山林之间做出的冷静思考和明智选择,“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2]21,在二者的鲜明对比中,更显示出唐寅对隐逸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六)宗教情怀
宗教是解脱生命苦痛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唐寅几经沉浮,看透了世事险恶,人生虚幻,故寄情于宗教,寻求解脱。晚年唐寅自号“逃禅仙吏”,意为逃遁入禅,从禅定和禅悦中获得人生的自在和解脱。更常自称“六如居士”,居士是在家修佛修道者,“六如”源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16]此间之梦、幻、泡、影、露、电,便是“六如”,比喻世间诸法皆空,是佛教思想的体现。体现唐寅宗教情怀的诗作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寄情于寺院。唐寅一生游历了诸多名寺,如《与朱彦明诸子同游保叔寺》[2]52中的保叔寺,《登法华寺山顶》[2]20中的法华寺,还有《嗅花观音》中的天台山国清寺等等。游历寺庙的经历坚定了他逃禅入佛的决心,其宗教情怀也于此类诗作中自然流露出来。
其二,阐释佛道之理。唐寅对佛道之理的领悟非常有见地。他认为寻仙问佛就是为了自我解脱,如《醉时歌》:“几番死兮几番活,大梦无凭闲聒聒;都是自家心念生,无念无生即解脱。”[2]25“翻身跳出断肠坑,生灭灭兮寂灭乐。”[2]26在《解惑歌》中,他认为世人纷纷学仙求佛,追求长生富贵或来世幸福,皆是痴愚之想,所以他要“漫作长歌解其惑”[2]26,认为无论是学仙还是求佛,皆须根于本心,不作外求,“神仙福地是蓬莱,释迦天宫号兜率;不在西天与东海,只在人心方咫尺”[2]27。这种佛理应求之于本心的观点,正切合《坛经》所云“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17],讲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修之法。唐寅对这一内涵的理解,可谓抓住了禅宗的要旨。
唐寅诗歌中所呈现出的奋发情怀、生命情怀、失落情怀、及时行乐情怀、隐逸情怀、宗教情怀大体构成了其诗歌独抒情怀的文学风貌。作为一名吴中诗人,唐寅诗歌受到了明中叶吴中独抒情怀之文学思潮的影响,与此同时,他的诗歌创作又推动了吴中独抒情怀文学思潮的发展。
二、明中叶吴中独抒情怀之文学思潮及其兴起原因
明中叶,以前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的创作成为诗坛上的主流,而与前七子复古文学思潮差不多同时存在的是吴中独抒情怀的文学思潮。这股文学思潮“不是一种普遍的文学趋向,它是一种文人的生活风尚、文化风尚和文化趣味、人格理想……像唐寅,像文徵明,像祝允明他们这种,缘情尚趣,追求自适与狂放。呈现出相对独立的文学风貌,更为鲜明的非正统文化色彩”[18]。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论及唐寅等吴中诗人时也说:“其作风别成一派,不受何、李的影响,他们以抒写性情为第一义,每伤绮靡……在群趋于虚伪的拟古运动之际而有他们的挺生于其间,实在可算是沙漠中的绿洲。”[19]
罗宗强将明中叶受吴中独抒情怀文学思潮影响的文人士子大体划分为三类:“完全没有入仕经历的”,如沈周、朱存理等;“屡试不第,由于某种原因短暂入仕、入幕的”,如唐寅、祝允明、文徵明等;“在官任职的”,如顾璘等[1]347。他们没有提出明确的、系统的文学理论主张,他们的文学思想倾向主要通过文学创作表现出来。而他们的文学创作均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一种重视独抒个人情怀的文学思想观念,呈现出独抒情怀的文学风貌。
如沈周《市隐》一诗:“莫言嘉遁独终南,即此城中住亦甘。浩荡阖门心自静,滑稽玩世估仍堪。壶公溷世无人识,周令移文好自惭。酷爱林泉图上见,生憎官府酒边谈。经车过马常无数,扫地焚香日再三……”[20]具体描绘了自己的隐居状态,表现出隐逸的情怀。诗名即为“市隐”,说明自己即使居于城市,依然心隐而离俗。祝允明在《春日醉卧戏效太白》中,以李白式的奇思妙想,书写独自饮酒的乐趣,表现了行乐的情怀,“携手观大鸿,高揖辞虞唐。人生若无梦,终世无鸿荒”[13]67,更是展现了其逍遥、自由的心态。《哭子畏二首》(其二)中写唐寅风流倜傥的“狂士”风貌,而在“万妄安能灭一真”[13]183的反问中为身怀奇才却连遭不幸的好友鸣不平,表现出失落的情怀。文徵明个性温文尔雅,因而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以比较温和的方式独抒情怀。在《月夜登阊门西虹桥,与子重同赋》中,企图超越那“带城灯火千家市,极目帆樯万里船”[21]65的繁华世俗,追求温雅宁静的境界,流露出隐居林泉的隐逸情怀。《感怀》一诗,抒发诗人“老去入樊笼”[21]147的苦闷心情,梦想如同那泛舟五湖的范蠡一样,功成身隐。其他代表人物如朱存理、杨循吉、都穆等人的创作,均能独抒情怀,张扬个性,表现真情。
明中叶吴中独抒情怀之文学思潮之兴起,与当时独特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在政治上,明前期统治者竭力加强专制集权,大兴文字狱,但经由“土木之变”,国势由盛转衰,宦官长期干政,边境局势动荡。统治阶级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有所削弱,明初建立起来的严格的等级制度也有所松动。经济上,明中叶,尽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居于统治地位,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商业贸易繁荣。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在此基础之上,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社会上,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壮大,社会风尚和思想观念开始发生转变,民风日趋重利尚俗,人们的个体意识开始觉醒,弘扬个性、肯定人的正常欲望,成为相当普遍的社会思潮。而吴中独抒情怀的文学思潮,可以说就是这种追求个体意识、力图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社会思潮在文学中的反映。
三、明中叶吴中独抒情怀文学思潮之影响
以唐寅等人为代表的明中叶吴中独抒情怀之文学思潮,余韵悠长,影响深远。从微观上看,它具体地体现在唐寅等吴地文士的创作实践中,使其呈现出独抒情怀的文学风貌。而从宏观上分析,则可分为两个向度。在横向上,与前七子等所倡导的复古思潮相比较,吴中独抒情怀之文学思潮是相对独立的。但是,二者大体处于差不多相同的时段,又共处于明王朝这一大的空间背景之中,不可能完全隔绝,互不影响。事实上,明中叶吴中独抒情怀之文学思潮与前七子复古思潮是存在一定程度的交互影响的,这可以通过史料来证明。在正德、嘉靖之间,吴中独抒情怀文学思潮的一些代表人物开始转向对复古的尊信,其中又以徐祯卿表现得最为明显。一般认为他的变化是在认识李梦阳之后,后来他还成为了前七子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尤其是他“悔其少作”的行为,充分证明了复古思潮对吴中文人的影响。同样的,今天人们所见到的后七子身上的一些有别于其前代的特征,有些与时代的变迁有关,有些则是受到来自外部诸思想潮流的影响而调整的结果,其中吴中独抒情怀的文学思潮对复古思潮的影响是显然存在的。在纵向上,明中叶吴中独抒情怀之文学思潮上承元末明初以杨维桢为代表的尊情抑理的思潮,下启晚明以李贽、袁宏道等人为代表的文学解放思潮。李贽绝假纯真的“童心说”,强调表现个体的真实感情与愿望,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说,重视对性灵的抒发,从二者中均能看见吴中独抒情怀的文学思潮的影子。而这其中,表现最明显的是公安派的袁宏道,他在任吴县县令期间,受到了吴中文学的直接影响,除了结交了一大批吴中文士之外,他还以很大的热情评点了唐寅的诗文集并为之作序。如他评《默坐自省歌》为“说尽假道学”[2]24,评《送王履约会试》为“自在”[2]41,在他所作的序言中也说:“余为吴令,虽不同时,是亦当写治生帖子者矣。”[2]532这种尊情抑理、自由自在、独抒情怀的精神,正是晚明独抒性灵的文学思潮的渊源之一。再往后,公安派后嗣如钱谦益等在诗歌领域倡导性灵,也与其所从出的吴中系脉有密切的关系,这在纵向上是一个影响的衍生系统。
综上所述,明中叶吴中独抒情怀之文学思潮与前七子复古思潮差不多处于相同时段,却又相对独立于复古思潮而存在。此一文学思潮没有形成明确的团体,没有提出系统的文学理论主张,但通过以唐寅等人为代表的吴中文士的文学创作实践表现出来。它兴起于明中叶独特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之下,涌现出众多著名的文人士子,余韵绵长,影响广泛而深远。
[1]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唐寅.唐寅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3]张廷玉.明史:第五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6:4169.
[4]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97:133.
[5]苏轼.苏轼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6]华忱之,喻学才.孟郊诗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54.
[7]韩愈.韩愈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36.
[8]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92.
[9]范晔.后汉书:卷八十[M].长沙:岳麓书社,2009:893.
[10]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六[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229.
[11]谢肇淛.五杂组:卷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98.
[12]王锜.寓圃杂记: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4:42.
[13]祝允明.怀星堂集[M].孙宝,校注.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
[14]陶渊明.陶渊明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63.
[15]吴国富.论唐寅适志姑苏隐游的市俗性[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2):174-175.
[16]金刚经[M].田茂志,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117.
[17]坛经:付嘱品第十[M].尚荣,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204.
[18]郭英德.明清文学史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6-97.
[19]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926.
[20]沈周.石田诗选:卷七[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661.
[21]文徵明.甫田集[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赵 青
10.3969/j.issn.1673-0887.2017.03.005
2016-10-23
姚瑶(1993— ),女,硕士研究生。
I207.22
A
1673-0887(2017)03-0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