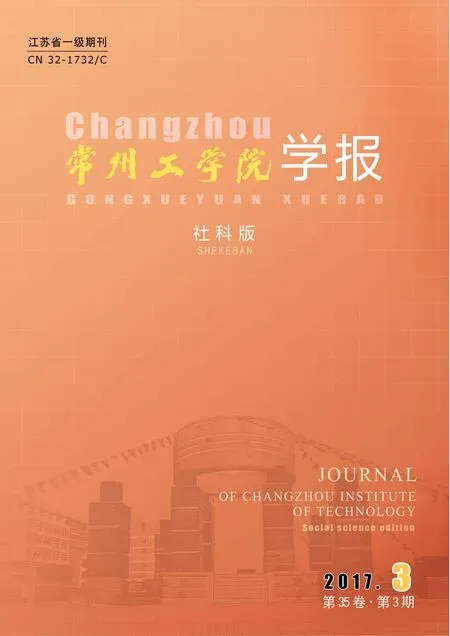白茆山歌“情歌”与《诗经》对比研究
王文意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无锡214122)
白茆山歌“情歌”与《诗经》对比研究
王文意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无锡214122)
情歌类白茆山歌是2002年版《中国·白茆山歌集》中除《时政歌》之外最多的山歌,也是如今当地人认为的占据最主要地位的一类山歌。文章将山歌集中的情歌分为五类,并对其中两类——求之不得式和两情相悦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列举和分析。通过这两类情歌与《诗经》中情歌的对比研究,发现前后两者存在着明显的传承关系,这对“白茆山歌·情歌”的保护和对《诗经》中情歌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白茆山歌;情歌;《诗经》;求之不得;两情相悦
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愫,《诗经》开卷的第一篇就是歌咏爱情的《关雎》。在先秦以至后代的各类诗歌集中,收录情歌的数量一直相当可观。就现存白茆山歌而言,按照当地人的说法,绝大多数都是情歌。在2002年版的《中国·白茆山歌集》中,《情歌》收录了120首,远远多于《劳动歌》《仪式歌》《传说故事歌》等的数量,仅次于《时政歌》。既然在数量上有充分的优势,对情歌的古今对比研究也应当比其他题材歌谣的研究更加深入,更加透彻。在此,笔者将古今情歌大致分为五类:求之不得式、两情相悦式、私定终身式、思妇式、弃妇式。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将重点对求之不得式和两情相悦式两类进行研究。
一、求之不得式
爱情始于一方对另一方的追求,多数表现为男子对女子的追求。追求的过程是艰辛而痛苦的,尤其是长期追求而“求之不得”的感觉,更是让人备受煎熬。反映这一题材的歌谣自古就有,最著名的就是《诗经·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1]133“求之不得”这一成语正出于此。白茆山歌中,也有大量反映这一题材的作品。《十八岁姐妮上高桥》里有“后生家看见一思痨”[2]79之句,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1]133异曲同工,都描写了男人追求女人过程中相思成疾的情景。
以“求之不得”为主题的歌谣,常常与水有关。河流是天然的屏障,常常会给人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感觉。男子在追求女子的过程中,也会出现这种感觉。当两种感觉契合的时候,水就成了一切阻隔的象征。无论是作本体还是作喻体,水都是求之不得式爱情诗中不可或缺的意象。尤其在江南水乡白茆,水本来就是生活中常见之物,当地人更是喜欢以水入情诗。《中国·白茆山歌集》里收录了一首《隔河看见好姐妮》:“隔河看见好姐妮,眉毛弯弯像吾妻,陌陌生生搭嫩勿好话,冷水里调浆米麦生。”[2]90歌谣中的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是初次相见,彼此并不认识,男子便对女子一见钟情。但是这位男主人公十分害羞,不好意思上前搭话,隔着一条河水,望着伊人却不能触及。这就是《诗经·蒹葭》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1]157的感觉。无论是“溯洄从之”还是“溯游从之”,男子都追不上女子,“道阻且长”不可怕,可怕的是“宛在水中央”。在白茆山歌集中,还有《隔河看见好后生》《隔河看见好姣娘》《隔泾看见好娘娘》等作品,从主题到内容都大同小异,多数为男追女,也有部分女追男,以四句式居多。每首歌谣的开头都有固定的格式,为“隔河看见好××”,“××”处分别填上姐妮、后生、姣娘等,唯有《隔泾看见好娘娘》是“隔泾”,不是“隔河”。
《诗经》中的《汉广》与《河广》篇名相近,但内容相差很大。《汉广》里有“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1]134这样的句子,主题比较鲜明,属于男子思恋女子之作,部分段落与《关雎》几乎异篇同调。“汉”“江”是指汉水和长江,男主人公隔着汉水、长江,苦苦追求女主人公而不得,这与白茆山歌以水入情歌的主题正好吻合。与《汉广》相比,《河广》的情感表达显得有些模糊,“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1]145,既可理解为思乡之作,亦可理解为怀人之作。按照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里的解释,将其称为怀人之情诗也未为不可:“跂以望宋,觉洋洋者若不能容刀①、可以苇杭。此如《郑风·搴裳》中‘子惠思我’,则溱、洧可‘搴裳’而‘涉’,西洋诗中情人赴幽期,则海峡可泳而度,不惜跃入(leap′d lively in)层波怒浪。”[3]164如果《河广》被定性为情诗的话,那么《汉广》与其正好可以一南一北相互照应,一个属于长江流域,一个属于黄河流域。由此推广开来,可以说,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也无论是长江流域的先民还是黄河流域的先民,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隔水咏情”的传统。无论是茫茫的河水、江水、汉水、溱水、洧水,还是《关雎》《蒹葭》中不知名的小河,都和白茆塘水一样,构成了自先秦至今至少已有三千年的共同情愫。那是一种从古老年代走来发自人类本性的情愫——对爱情的追求、对美丽异性的向往、对繁衍生息的渴望。水作为一个永恒不绝的意象,无论是真实存在还是仅仅“打个比方”,都不可否认地成为了隔绝有情人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这样的屏障是苦恋的象征,也是无奈的象征。
二、两情相悦式
与“求之不得”的苦恋相比,“两情相悦”往往是幸福的。这种类型的歌谣在白茆山歌集和《诗经》中都比较常见,有一定的比对研究价值。
男子与女子两厢生发感情之后,便开始出现彼此赞美的言辞,要么是男方夸女方长得漂亮,要么是女方夸男方长得英俊。有些歌谣侧重于“夸赞”,然后才是两情相悦;有些歌谣侧重于“两情相悦”,突出表现男女双方的如胶似漆,赞美之词只是糅合其中,不作特别突出。除了彼此欣赏之外,男女恋人之间还常常会打情骂俏。这种打情骂俏式的情歌,有时会比相互唱颂歌式的情歌更能反映出男女主人公之间真挚的感情。把两情相悦式情歌大致分为彼此欣赏和打情骂俏两类,会发现无论是题材上的横向对比还是古今时空上的纵向对比,这一系列情歌都能表现出一致性、连贯性和传承性。
(一)彼此欣赏
白茆山歌《桥边阿姐水磨刀》唱道:“摇到桥就唱桥,桥边上阿姐水磨刀。郎看阿姐磨刀嫩勿要磨碎手,姐看郎来嫩勿要船碰桥。”[2]76这首歌谣的后两句“郎看阿姐”和“姐看郎来”形象地表现了“阿姐”和“郎”之间的深情。“郎”笑话“阿姐”磨刀时一直盯着自己看,叫她当心别磨伤了手;“阿姐”也同样笑话“郎”摇橹时一直盯着自己看,叫他当心别让船撞到桥上。表面上看是嘲笑彼此,实际上正描摹了男女恋人之间彼此爱慕、彼此欣赏的心理状态。另一则白茆山歌《姐勒看郎针戳手》里也有类似的句子:“姐勒看郎针戳手,郎勒看姐船要横。”[2]76就这两句而言,仅是把“刀”换成了“针”,可以算出自同一个模板。
在《诗经》中,也有大量以欣赏异性为题材的作品。但与现存白茆山歌不同的是,当时的“欣赏”主要是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而不是彼此交互式的欣赏。“女追男”的作品在《诗经》中并非没有,但女子对男子的欣赏,主要是出于对男子德才、衣饰的欣赏,赤裸裸描写男色的作品很难见到。但男性欣赏女性时,大多就是直接描写女人的美貌、身材等。这种把女性作为审美对象的作品,不仅是出于对“情”的描写,也是出于对“色”的赞美。这类题材的作品对后世梁陈宫体诗、唐末五代花间词的繁荣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卫风·硕人》是《诗经》中描写女子美貌描写得最成功的一首作品,其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1]144之句,已经成了对女子容貌的最高赞美。后世《红楼梦》中对林黛玉的外貌描写与此有一定的传承关系:“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4]到了白茆山歌中,就成了《姐妮生得十哟哟》里的“姐妮生得头哟哟,金丝头发菜油浇,哎嗨哟,金丝头发菜油浇”[2]86。从“头哟哟”一直唱到“十哟哟”,不厌其烦。《十把拗勺》也是同样的风格,从“小姐妮打扮头拗勺”[2]87一直唱到“姐妮打扮十拗勺”[2]87。从第五段开始,省去“小”字,其余起句格式不变。纵观这四首诗歌,后两者显然比前两者土俗了很多。白茆山歌创作得无论如何出色,终究属于当代民间俗文学,终究敌不过经过三千年积淀的文学经典。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四首诗歌的主题都是对女子美丽容貌的赞美。
就《诗经》而言,除了最经典的《硕人》之外,还有《有女同车》《月出》《东方之日》等篇目,也以竭尽歌颂的笔调描写了女人美丽的容颜。其中《东方之日》最为笼统,只有“彼姝者子”[1]151之句,未细致刻画女子的模样。《月出》则借月色渲染氛围、营造意境,侧面突出美人之美。《有女同车》则写得稍微细致一些,将女子的容貌比作“舜华”“舜英”,而且在赞美女子容貌的同时还赞美了她的佩玉,颇有爱屋及乌之意。白茆山歌集里的《湖边莲莲自田田》有与之神似的句子:“姐要晚妆,湖水好像镜子样。我一头撒网,一头看你俏容颜。”[2]125先用一个比喻,表现湖水之静。再用极静之湖水,衬托容颜之“俏”。间接手法,与《月出》同工;比喻方式,与《有女同车》神似。
彼此欣赏的男女恋人,会在爱情的行进过程中出现许多甜蜜的情景,这种甜蜜的恩爱场景,在《诗经》和白茆歌谣中都能有所呈现。白茆山歌《郎盘犁头妹盘针》:“郎盘犁头妹盘针,犁快针飞两情真,一个犁头播片云,一个绣花表心真。”[2]100男子盘犁,女子盘针,是典型的男耕女织的传统农业社会的写照。这几句诗的时代感是非常弱的,最早可用来形容春秋战国时期②,最晚可以用来形容今天的一些闭塞农村。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是一种脆弱的经济形式,也是一种最容易生发浪漫爱情的经济形式。在男耕女织的生活状态下,男女都不会受到外界纷繁世界的干扰,而是醉心于小小的二人世界。女子醉心于欣赏男子盘犁时的动作,男子也醉心于欣赏女子盘针时的姿态。在这种状态下写出的情诗,是最唯美的情诗,也是最不能模仿的情诗——在这类情诗中,有一种现代城市居民永远无法还原的纯净感。那样的爱情,与金钱名利完全没有关系,仅仅是因为有爱,所以要在一起。《郑风·野有蔓草》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情愫:“野有蔓草,零露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1]150爱情的生发,成了一件很简单的事,男女双方没有问是否门当户对,也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仅仅是因为伊人很美、邂逅很美,就可以“适我愿”了。“适我愿”之简单,居然可以连话都不用说就直接对对方作出满意的评价。沉溺在爱情中的人,可以忽略整个世界,眼里只有对方。这时的对方,是最美丽的艺术品,怎么欣赏都欣赏不够。这种视恋人为一切的情愫,和男耕女织生活方式所表现出来的情愫是一致的。无论过了多少年,痴情的男女都会保留这份情愫。这是上天创造人类时为繁衍种群而赋予的永恒的天性,这种天性不会因时空的变迁而有所改变。
对伊人的欣赏,有时还会体现在爱屋及乌上。上文提到的《有女同车》,由喜欢车上的女子转化为喜欢女子身上的玉佩。因为喜欢那个女子,所以连玉佩发出的声音也觉得动听。在《邶风·静女》篇中,这种爱屋及乌之意表现得更为明显:“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1]141荑草,按照《管锥编》的说法,即为茅草[3]148。茅草是极为卑贱之物,却能被恋爱中的男子视作至宝,可以想见他对女子的深情已经到了不可自拔的地步了。白茆山歌《小妹妹家中有根藤》表达的同样是爱屋及乌的感情:“小妹妹家中有根藤,送给哥哥做根橹绷绳。济手推出金鸡叫,顺手召回凤凰声。”[2]99小小的一根藤,竟然可以唤出金鸡和凤凰的叫声,仅仅因为它是小妹妹家里的。对于“哥哥”来说,只要是“妹妹”家里的,无论是多么粗陋的物品,都是无价之宝。白茆山歌里的这根“藤”与《诗经》中的那根“荑草”,都是极低贱之物,却因爱情所托而成了无价之宝。把爱人之物视作无价之宝的爱屋及乌式的传统,从先秦的邶国到现代的白茆,都不曾断绝过。欣赏爱人之物,实质上是欣赏爱人。有时是为了使爱的表达更加委婉,有时则真的只是一种恋物癖。当对一个人的爱深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算是再卑贱的物品,只要与所爱之人有关,都会被痴情的人当作无价之宝来珍藏。《诗经》中表现出来的恋物作风,在白茆山歌集里也能找到标志性的对应传承作品。
(二)打情骂俏
男女情侣表达爱的方式是多样的,有时通过赞美,有时通过调侃。赞美过多,难免有互相吹捧的感觉,会显得不真实。调侃式的爱情往往会比欣赏式的爱情更能反映出男女双方的真情。在白茆农村,劳动人民也没有多么高的文学素养,他们创作的山歌往往耿直而缺少文学性的修饰。从审美的角度说,白茆人民无论多么努力炼字,都不可能使山歌具备比《诗经》还强的审美属性。与经过三千年历史积淀的《诗经》相比,白茆山歌是“俗”,不是“雅”。也正是因其“俗”,白茆山歌更能适应俗文学的要求,更能通过最直白的文字表达最真挚的感情。在口语化的戏谑式的文学作品中,白茆人民表现出的真情完全可以像《诗经》一样真切地打动人心。
情侣们情到深处,就不再只局限于彼此欣赏、互相赞美,而是开始打情骂俏。打情骂俏表现的是另一种形式的甜蜜,也是两情相悦的一种,只不过这种相悦是通过相反的方式表达出来罢了。将先秦时人们打情骂俏的歌谣与现当代白茆人民打情骂俏的歌谣进行比对研究,会发现这种“打情骂俏”的传统是任何时空下都不会改变的永恒恋爱模式。
所谓的打情骂俏,常常表现为明里贬低对方,暗里夸赞对方;明里讨厌对方,暗里喜欢对方。白茆山歌《郎唱山歌顺风飘》唱道:“郎唱山歌顺风飘,下风头阿姐立勿牢。连喊三声郎啊、郎啊,嫩勿要唱,再唱山歌奴晕倒。”[2]73郎的山歌已经让阿姐沉醉到站不住脚的地步了,阿姐却口是心非地劝郎不要唱,说再唱自己就要晕倒了。实际上是动听得让人要晕倒,却装出一副难听得让人要晕倒的模样。阿姐不好意思直接说郎歌声的动听,就用相反的口吻说歌声难听,用“立勿牢”之句表明歌声震撼力之大。《郎唱山歌响铜铃(之一)》《郎唱山歌响铜铃(之二)》和《郎唱山歌响铜铃(之三)》都有相类似的段落,大意都是说,女子听男子唱歌入了迷,于是打碎了名贵的碗,既而痛骂“郎”是害人精。明明是被男子的歌声所吸引,却因碗被打碎之事抱怨男子是害人精,这是典型的明贬实褒手法。女子不好意思直接夸赞男子的歌声多么动听,而是通过碗打碎之事旁敲侧击地表达对男子歌声的喜爱——表面上骂得越凶、贬得越低,内心的爱也就越深。
《诗经·郑风·山有扶苏》中有类似的句子“不见子都,乃见狂且”[1]149、“不见子充,乃见狡童”[1]149。子都、子充都是著名的美男子。诗中的女主人公表面上是抱怨男主人公不如子都、子充,只是个“狂小子”,实际上是暗里表达对男子的喜爱。《诗经·郑风·搴裳》将男主人公称为“狂童”,并用了两个“狂童之狂也且”[1]149。表面上看,“狂童之狂也且”[1]149这样的句子表达的是对男主人公的抱怨乃至责骂,实际上,这是一种典型的打情骂俏行为。《诗经·郑风·搴裳》里抱怨男主人公不搴着衣裳涉过溱水洧水来看自己和白茆山歌《郎唱山歌顺风飘》里抱怨男主人公唱歌“难听”要让自己晕倒,同属于女主人含蓄地表达对男主人公爱慕之情的手法。女性在恋爱中出于天生的被动和害羞,她们不敢正面直接地去追求喜欢的男子,而是通过明贬实褒的方法引起男子的注意,希望藉此获得男子的好感。《诗经·郑风·溱洧》中的打情骂俏则显得更高级也更直白一些,“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1]151。什么叫“伊其相谑”?《诗经今注》把“谑”解释为“开玩笑”[5]。笔者认为,“伊其相谑”可以直译成“互相调戏”或意译成“互相打情骂俏”。这种“调戏”和“打情骂俏”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侮辱。后半句的“赠之以芍药”说明了这一点——虽然至情流露,却不失庄重。
打情骂俏式的情歌,首先是建立在两情相悦上的。因为两情相悦,所以才会打情骂俏。男子喜欢女子,所以要对女子唱歌;女子喜欢男子,所以会站不住脚要晕倒。《诗经》里青年男女的相互责骂,表现的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明贬实褒的恋爱模式。由于女性常常在恋爱中处于被动方和弱势方,所以明贬实褒的技巧更多情况下是由女主人公来呈现的。这样的呈现,往往是出现于男主人公主动追求之后。男子追求女子,女子欲答应又不好意思直接答应,于是就出现了这一系列暗藏喜爱于明的厌恶中的情感表达方式。《郎唱山歌响铜铃》从“之一”到“之三”都反映出了女子欲主动又不敢主动的复杂心理。《搴裳》中的女主人公明明是思念男子至极欲主动“搴裳”去见男子,却表现出对男子不及时“搴裳”来看自己的抱怨,这种心思与《郎唱山歌响铜铃》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溱洧》,则是一种更高形式的打情骂俏,由于男女主人公都在现场,所以这种“调情”也更直接、更露骨。但即使如此,女主人公依然尽量保持着矜持、被动,在整个过程中不失礼、不失庄重。
从先秦的“诗经时代”到今天再到遥远的未来,爱情都不会成为过去式。无论社会形态发生怎样的改变,男女在恋爱过程中依然会在总体上长期处于“男子主动、女子被动”的状态。当恋人双方对上眼的时候,女子往往会出于矜持而对男子做出一些打情骂俏的举动,有时男子也会有一定的打情骂俏式的回应。这样的爱情,是真挚而质朴的爱情,是当代信息社会中很难体会到的爱情。白茆山歌因其传统属性,与先秦古谣不存在根本性的断裂,因此在情歌上依然保留着人类最原始最单纯的情愫。
三、结语
笔者将《中国·白茆山歌集》中的情歌大致分为了五类:求之不得式、两情相悦式、私定终身式、思妇式和弃妇式。本文重点选取了前两类情歌,与《诗经》中相同或相似题材的情歌进行了对比研究,并发掘了人类三千年来在爱情方面从未改变过的某些情愫。在男子追求女子的过程中,会有求之不得的艰辛;追到之后,又会有彼此欣赏和打情骂俏的甜蜜。“求之不得,寤寐思服”[1]133,是单相思之人最大的痛苦。当单相思变成“双相思”之后,爱情就会成为互相的欣赏或互相的调侃。在恋人眼中,对方永远是完美的,因此才会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1]144这样唯美的诗句。情到深处,便不再互相吹捧,而是“伊其相谑”[1]151。白茆山歌在文学审美方面不敢比肩古老的《诗经》,“姐妮生得头哟哟,金丝头发菜油浇”[2]86这样土俗的句子也不太可能流传千古,但白茆山歌所表达的人类在爱情面前的美好痴念不逊于《诗经》。从古至今,对爱的追求和对美的追求是不会改变的。白茆山歌对《诗经》的传承,是恋爱模式的传承,也是人类美好天性的传承。
注释:
①刀者,舠也,指小船。
②铁犁牛耕技术始于春秋战国时期。
[1]四书五经[M].张彩梅,舒琴,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
[2]江苏省常熟市文化局,江苏省常熟市文化馆.中国·白茆山歌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
[3]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7.
[4]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35.
[5]诗经今注[M].高亨,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27.
责任编辑:庄亚华
10.3969/j.issn.1673-0887.2017.03.008
2016-11-08
王文意(1994— ),男,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2016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610295062)
I0-03
A
1673-0887(2017)03-003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