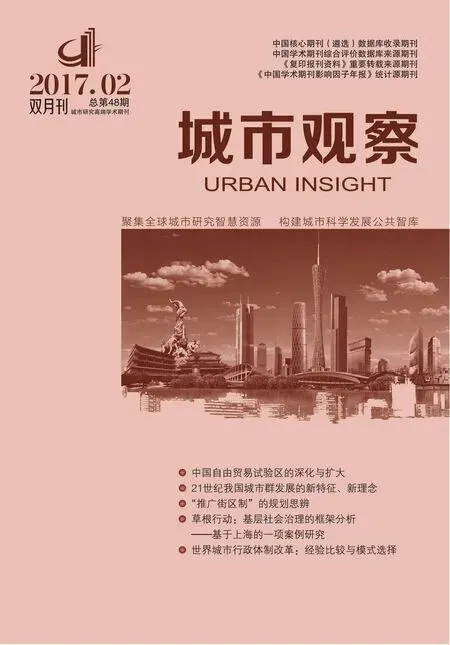草根行动:基层社会治理的框架分析
——基于上海的一项案例研究
◎ 杨秀菊 刘中起
草根行动:基层社会治理的框架分析
——基于上海的一项案例研究
◎ 杨秀菊 刘中起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开始了重大的变革,单位制解体,社区制逐渐建立,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陌生人社会”使得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难以产生,这是中国新型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社区参与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呈现出一种国家治理需要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居民的行动逻辑与行动策略以及政府与居民的互动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何借力创新社会治理激发基层活力的时代背景,通过构织基层组织网络的框架扩散将宏大的基层社会治理与普通居民的日常草根实践加以勾连?基于上海的一项社区治理案例分析试图展示这一基层社会治理的框架整合模型及其草根行动的内在逻辑。
草根行动 基层治理 框架分析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Goffman于上世纪70年代提出“框架”(Frame)概念,指“使个体能够定位、感知、识别和标记在生活空间和更广泛的世界中所发生的世界的理解图式”(Goffman,1974)①,它“赋予事件和事情以意义,从而发挥着将体验组织化并引领行动的功能”(Benford & Snow,2000)。框架建构论②中的“框架建构”(Framing),表示用一个概念框架去塑造和建构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解读这样一种行为和过程③。框架分析体现了社会运动理论的“文化或建构主义转向”(Melucci,1988;Touraine,1981;Della Porta& Diani,1999),它强调有别于实体性资源的观念和话语在集体行动中的关键作用,力图论述社会运动组织是如何通过社会互动和意义的生产,从而获取其他行动者对其目标的主观认同和行动参与。后来经由甘姆森(Gamson,1975)、D. A.斯诺和本福德(Snow et a.l,1986; Snow &Benford,1988、1992)等学者的理论拓荒,框架分析,与基于理性选择和组织理论发展出来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等理论一起,共同丰富了对现代社会中集体行动和动员机制的认识④。
框架分析将“集体行动框架”(collective action frames)作为独立的影响因素,这一点与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其他理论范式不同,它不仅指涉个体的认知过程,而且能在情境互动中生成事件或文本的组织理念,这种组织理念通过刻意强调事件的某个面向及象征意义,有助于在动员过程中转换和锁定某种社会价值,进而影响人们的行动取向。具体而言,框架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核心任务:对某种事件或社会问题的诊断;关于所诊断问题的解决之道的陈述和提议;对参与集体行动的呼吁或论证(Snow& Benford,1988:199;Benford & Snow,2000)。鉴于受众和其他行动者在诠释事件时,也会加入自己的解释框架并组建事件的另类意义。因此,社会运动组织需要通过框架的策略性互动,尤其是“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 process)来连接与公众以及其他潜在参与者的信念或价值观,以产生共鸣并激发行动上的支持。联结点和共鸣越多,参与者就越能认同其诉求,追随其行动(Williams& Kubal,1999)。在这个意义上,框架分析就是对框架整合过程的分析,它契合了克兰德曼斯(Klandermans,1988)所谓的“共识动员”⑤(consensus mobilization)。
在框架整合的过程中,动员主体所嵌入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意义重大,在某种意义上,框架化过程和动员网络的形态扩展相伴相生。社会运动理论中的网络分析已经指出了社会网络的重要性,而且指出了不同的动员网络会对运动的结果和产出带来影响(Snoweta.l,1980; Gould,1991;McAdam& Paulsen,199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开始了重大的变革,单位制解体,社区制逐渐建立,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政府和居委会应成为公共物品的重要提供者,但它们均存在角色迷失的现象⑥,尤其是居委会出现了严重的行政化倾向,使基层社会自治形式化。其他的社区自治组织又尚未出现,从而出现了社区公共事务自治主体严重缺乏的局面。不仅如此,“陌生人社会”使得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难以产生,这是中国新型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⑦。上海作为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社区,其新兴的商品房居住模式中,由于居民和居委会组织的相对微弱的利益关联,由此使得动员性参与(mobilized participation)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成为必然。如何通过有效的框架整合与草根行动让更多的居民参与到基层的公共事务已经成为当前社区建设的重要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居委会主导的这种基层社会动员的具体过程中,行动主体如何通过微观的框架整合模式将宏大的基层社会治理与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加以勾连?本文的案例分析试图展示这一框架整合的微观机制及草根行动的内在逻辑。
一、行动:上海“GREEN HOUSEWIFE”草根治理实践
“GREEN HOUSEWIFE”草根治理案例源自上海市徐汇区凌云街道的梅陇三村社区,该社区位于上海市西南端,建成于1990年,共有3个自然小区、2369户人家、6500余居民,以动迁安置为主,小区规模较大、设施较为陈旧、人员结构繁杂、居民诉求多样。该社区曾是远近闻名的“垃圾村”。居民区党总支敏锐地捕捉到居民的兴趣点和需求点,以当今社会共同关注、人人皆可参与的“绿色、健康、低碳、环保”生活作为草根自治行动的切入点,逐步引导、培育、扶持“GREEN HOUSEWIFE”居民自治组织不断成长壮大,最终成为基层社会自治工作的中坚力量,小区面貌也焕然一新,成为名副其实的“花园村”,目前正在全力营造低碳环保社区。“GREEN HOUSEWIFE”居民自治组织的孵化和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并逐步逐层加以推进和深化⑧。
(一)绿色生活理念先行,培育草根自治意识
由废旧塑料和利乐包装作原料制作而成的简捷、坚固的长凳——凌云社区学校内一张概念型的环保“世博椅”, 吸引住了梅陇三村几位家庭主妇的目光,她们惊叹于变废为宝的神奇力量,被绿色环保的生活理念深深折服——“我们是不是也能做点什么?”于是,她们主动请缨,并得到党总支立即回应。2011年初,在党总支的推介和组织下,由10多名家庭主妇组成的“GREEN HOUSEWIFE”低碳环保自治行动小组应运而生。2012年—2013年期间,参与垃圾减量回收活动的居民超过了19,270户次,实现生活源头垃圾减量(包括可再生废弃物和废旧衣物)超过了45吨。
(二)家庭团队志愿行动,丰富草根自治项目
垃圾减量回收活动初见成效后,2012年初,一条讯息传到小区:市妇联联手环保公益组织正筹划开展一项以“美好家园绿色生活”为主题的“家庭阳台一平米小菜园”种植活动。为了让更多的居民融入小区建设,营造“熟人社会”,党总支抓住这一契机,使种植活动落户三村,活动计划也随之出台,先由“GREEN HOUSEWIFE”和小区花卉小组成员组成的核心团队试种。“GREEN HOUSEWIFE”工作室也实现了华丽转身,“上海徐汇区凌云‘GREEN HOUSEWIFE’环境保护指导中心”正式注册成为民间公益组织。随着“家庭阳台一平米小菜园”活动项目的成效逐步呈现,以“绿色环保”为主题的一个个活动项目——“GREEN HOUSEWIFE家庭微绿地”、“GREEN HOUSEWIFE家庭有机芽菜种植”等也不断地推陈出新,并逐步推广辐射开来。截止2013年10月底,“GREEN HOUSEWIFE”志愿者人数多达5000多名,参与“一平米小菜园”的居民超过了7780户。
(三)公益项目议事平台,构建草根自治网络
随着“家庭阳台一平米小菜园”种植活动、“爱心编结”⑨向贫困儿童捐毛衣活动等一个个项目的推出,小区志愿者队伍日趋庞大,居民对小区事务越发热心,一人有难、众人相帮的场景也时常发生,“小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自治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党总支见时机成熟,酝酿产生了“GREEN HOUSEWIFE”议事会。以议事会为枢纽,以“绿色环保”理念为抓手,党总支和居委通过“GREEN HOUSEWIFE、我当家”行动小组旗下的老年读报组、侨联小区合唱队、花卉兴趣小组、凌梅梅艺术团、夕阳互帮服务队,以及“GREEN HOUSEWIFE”工作室旗下的低碳环保宣传队、垃圾减量活动组、环保创意设计组、社情民意联络团等团队和组织,引导居民融入小区“大家庭”,参加居代会、小区事务联席会、听证会、妇女代表会等自治会议,让居民在社情民意交流平台、小区需求受理平台、小区矛盾调解平台、小区问题处理平台等自治载体上发挥重要作用。
二、进程:草根社会治理的框架整合模型
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推进依赖于草根行动参与者的公共性发育与框架整合策略。D.A. Snow& Benford认为“框架”来源于共享的个体经历。同时,要成功动员参与者,动员者就需要在框架过程中细分并运作三项任务:用来找寻问题和确认目标的“诊断性框架”(diagnostic framing),用以提供解决问题方案和建议的“策略性框架”(prognostic framing)以及用以论证行动合理性的“动机框架”(motivational framing)。对于框架性整合来说,框架与更大尺度的信仰系统的关系以及框架与参与者的互联性(interrelatedness)也极为关键:越强的互联性便越可以放大框架的动员效能⑩。这意味着,一旦框架具有这些规范特征,并且能够按照如上原则得以建构,社会运动组织就可以通过框架整合来实HOUSEWIFE”治理案例的运作过程中,这一框架整合机制又是如何得以体现的呢?
(一)诊断性框架:草根社会治理难题的回应与解决
“诊断性框架”的第一步即是确认问题和行动目标的存在。为了提高集体动员的水平,社会运动必须增强人们的“问题意识”,将那些集体行动所关心的事物和现实变成人们意识中的“问题”。梅陇三村社区是20世纪90年代初建造的老小区,原来是出了名的脏乱差,大家都叫它垃圾三村。居民的心情自然不会好,埋怨、吵架是常有的事。居委会作为基层组织,人手少事务多,在巨大的压力下一直寻求突破传统的基层社会管理方式,希望通过草根行动让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从而改变社区的基本面貌⑫。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是,政府单一的行政资源已越来越力不从心了,而小区居民的自治理念、自治能力还都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状况下,居民自治团体的作用就显得尤其重要。怎样有效调动居民积极性参与社区治理,去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这一层面难以解决的事情呢,作为街道、居委会政府基层单位应怎样去培育和扶持居民自治组织?如何寻找到使政府意愿同居民意愿能达成一致的“契合点”,实现双赢的基层社会治理发展模式,应是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之所在⑬。梅陇三村正是通过对草根社会治理难题的有效回应,实现了对基层社区的“诊断性框架”整合。随着我国城市社区的分化与利益关系的调整,基层社会面临的任务与问题发生了新的转变,由此凸显出既有社区治理结现既定的目标⑪。那么,在上海“GREEN构的限度,包括社区利益多元化与表达机制单一化之间的张力、基层社会矛盾尖锐化与协调机制的有限性以及业主委员会等新社区治理主体的出现等。社区利益的多元化和基层社会矛盾的复杂化,凸显既有社区治理结构的失效,即社区居委会作为定位于社区居民开展自治的组织,无法涵盖和包容日趋分化的多元社区利益,以及错综复杂的基层社会利益矛盾。由此,从构建基层社会和谐稳定出发,需要充分发挥政党、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及基层社会草根组织等多元参与,尤其是发挥基层群众社团组织在基层社会动员中的框架整合效能,推动社区公共事务走向基层社会自治,从而实现社区治理结构新的转型⑭。
(二)策略性框架:基层社会草根自治网络的构建与运作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区营造受到国家与社会双重力量的作用,同时因为社区内房产的商品属性,市场逐渐成为创造基层社会动员话语的重要来源。要想使基层社会动员具有蓬勃生命力,动员话语的选择既需要契合国家最新的政策,寻找到法理上的合法性,也需要考量社区居民已有的草根“文本”,回归到社区居民最熟悉的日常生活和认知框架中,进行创造性思维⑮。梅陇三村抓住居民的需求点和兴趣点,以“绿色、健康、低碳、环保”作为草根文化的切入点,引导、培育、扶持本土化的“GREEN HOUSEWIFE”草根自治组织逐步成长,并基于“GREEN HOUSEWIFE”效应全面构织基层社会自治网络,从而成功通过绿色环保主题和自治策略的转换将基层治理的组织目标和价值与动员对象的利益和情感联系起来,实现了基层社会动员的“策略性框架”整合。Snow等指出了社会运动组织的网络对于社会运动动员的重要性⑯,即如果社会中存在着一些相互支持的动员组织的话,社会动员的水平必然会提升,那么社区参与中,如果基层社会其他组织能够积极配合居委会的行动,必然能够改善当前的主体间性状况,提升居民社区参与率⑰。
在草根治理的基本网络结构中,“关键群体”与行动精英对于治理的参与深度与行动有效性至关重要。Oliver等人(1985)通过对社会运动中“关键群体”(critical mass)的研究发现,作为一种动员网络,“关键群体”能够在其他人不愿意加入的情况下也有旨趣进行动员,并且付出必要的社会成本(Marwell &Oliver,1993)。“关键群体”形成了一个互相勾连的集团,而其他的参与者则依附于这一高密度的积极分子网络⑱。凌云“GREEN HOUSEWIFE”正是通过一批关键性的行动小组群体全面构织基层社会的草根自治网络,从而实现基层社会动员的策略性整合行动,包括“互助,共商共议共治”的民主自治小组管理网络;以“合作,宣传教育提升”的小区自我教育平台等,尤其是以“GREEN HOUSEWIFE”行动小组和“GREEN HOUSEWIFE”工作室为主的关键行动群体,通过“GREEN HOUSEWIFE”行动小组旗下的老年读报组、侨联小区合唱队、花卉兴趣小组、凌梅梅艺术团、夕阳互帮服务队,“GREEN HOUSEWIFE”工作室旗下的低碳环保宣传队、垃圾减量活动组、环保创意设计组、零积分卡兑换点、社情民意联络团组织的辐射性系列活动,逐步地让居民从小家庭融入到小区“大家庭”,进而增强了“大家庭”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形成了由居委会支撑、“GREEN HOUSEWIFE议事会”主导、居民自我教育和民主互助管理稳步前行的小区自治动员网络⑲。涂尔干将由人们的相似性所产生的社会成员平均集体信仰和集体感情的总和称为“集体意识”——“如果人们相互结成一个共同体,并在其中感受到了某种信念或感情,那么这种信念和感情会给人们带来强大的力量”⑳。通过“GREEN HOUSEWIFE”议事会,居委会通过18名志愿者骨干成员网络在培育基层社会自治和社区认同上成功实现了“策略性框架”动员。一方面,居民在自治管理中备感珍惜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增强了对小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即涂尔干所谓的一种“集体意识”,进而形成了约束自己行为的责任感,以此实现小区的草根治理。另一方面,“GREEN HOUSEWIFE”议事会的草根自治网络以及小区自助、互助服务体系,都是基于居民对小区集体观念树立的前提下形成的,并且网络化管理与组团式服务又成为培育社区价值和公共利益观念的重要途径。
(三)动机性框架:基层社会草根需求的激发与对接
社会运动进行框架建构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们加入社会运动,但“诊断性框架”和“策略性框架”均不足以实现这个目的,因为接受某种信仰与愿意为这个信仰而采取实际行动,是既相联系又不完全等同的两件事——这正是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以及资源动员论和政治过程论反复强调的观点。因此,社会运动必须在“诊断性框架”和“策略性框架”之外提供一个动机性框架——让人们能够产生参加集体行动的动机。Benford (1993b)发现,为了说服人们采取实际行动,社会运动往往会从四个方面对诊断出的问题进行进一步阐述:一是问题的严重性(severity);二是采取行动的紧迫性(urgency);三是采取行动的有效性(efficacy),即让人相信只要按照运动的要求采取行动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四是行动在道德上的适当性(propriety),即鼓吹采取运动所要求的行动是每个人的道德义务㉑。动员结构一般包括集体行动产生过程中的核心行动者和行动策略。在刘能的解释框架中,动员结构变量是集体行动产生的核心变量之一。“集体行动所需的共同意识的形成需要动员,集体行动所需的资源和成员也同样需要动员。”㉒但在中国现实情境下,“不利的政治机遇结构”、主要精英知识分子的角色形象和角色意识的变迁使社区公共事务治理集体行动面临着积极分子供给不足的困境㉓,而“陌生人世界”则阻碍信任、社会网络的构建和参与意识的提高,造成社会资本不足,再加上社会流动性的加快,使基层社会动员网络构建更加困难。因此,社区公共事务的集体治理需要核心行动者采取一定的行动策略构建或激活社区的草根社会资本㉔,使得基层社会动员最终形成其发生的动机性框架。梅陇三村居民委员会根据小区的特点,把自治工作的突破口和重心放在女性居民上——最初由老年协会的负责人方翠英倡议,小区里自发组织起一支以“GREEN HOUSEWIFE”为主题的低碳环保行动小组,在居委会的引导、支持下成立了议事会,并有序组织、开展起一系列小区自治管理的工作㉕。回顾总结该项活动,其一大创新点是:活动的组织和发动是从家庭的领导人——女性居民开始,以女性为主导带动家庭,由激活家庭到激活小区,进而辐射更多草根居民,通过制造呼应社区生活共同主题和基层社会草根特征的动员话语,利用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需求以及共享的基层社会草根文化,通过集体认同感的激发,塑造基层社会情感与社区意识㉖,从而将大量潜在的社区行动者——草根志愿者家庭成员动员起来,形成基层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集体行动效应。
传统经济学认为个体的理性将导致集体的非理性,采取行动策略的主要目的则是将个体的理性转化为集体的理性选择。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㉗的行动策略,是将人的理性极端化,忽略了人的情感。在社区治理中,居民出于理性计算可能会选择“搭便车”,但他们作为社区共同体中的一员,容易受积极或消极情感的驱动而改变自己的理性计算水平。因此,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策略主要是通过改变社区居民的信任、信念和基层社会草根网络㉘,培育他们的积极情感,如提高集体行动的信息透明度、让居民体会到集体行动的成果等,进而改变其“搭便车”的理性计算,实现集体理性。尤其是对于“陌生人社会”的社区来说,构建这种网络的一个现实途径是组织形式多样的社区活动,并使其制度化和常态化,以此增强社区草根成员的归属感㉙。凌云“GREEN HOUSEWIFE”案例正是从社区情感角度展示了基层社会动员的动机性框架即是基于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与草根实践,“低碳环保”这一基层社会公共需求通过核心行动者方阿姨的引领动员,很快成为居民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和公共议题,使得环保行动理念在小区内广泛传播,再经由大量的社区公益行动营造“熟人”网络,从而使社区的草根社会资本得以迅速增长。
三、策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草根议题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做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继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尤其是要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㉚。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居民对城市生活的追求日益呈现多样化、复杂化和个性化的特征,这一变化对基层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和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Snow & Benford提出的“框架扩散”(frame diffusion)过程认为,在推进公共治理的进程中,各个社会运动或社会运动组织的框架建构活动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彼此互动的。这种互动也不是只有对立和竞争,而是同时存在合作、借鉴和吸收。框架扩散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在一个运动周期内,由先驱运动所创造的主框架会对后续社会运动的框架建构产生剧烈影响;二是在同一时期并存的多个运动有可能相互合作或影响,形成一个共享的主框架;三是同一时期并存的多个运动即使未形成一个共享的主框架,也会吸收其他框架的思想和元素,融入自己的框架。“主框架”往往是在一定时空内发生的诸多社会运动的共同主题, 它体现了一个时期主要的意识形态思潮。在社会运动史上,有影响的主框架曾经多次出现。比如,美国民权运动创造的“权利框架”,后来就被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印第安人等社会群体发起的社会运动所采用㉛,大家纷纷在“维护公民权利”这个大框架下建构符合本运动的框架。主框架对后续社会运动的影响有多种方式。一是为后续社会运动创造一套“解读戏码”(repertoire of interpretations),即创造一套现成的解读社会现实的模式,借助这套模式所提供的观点、概念、命题和语言等,后续的社会运动可以较为便利地对社会现实进行解读,从而更快更好地建构出符合本运动的框架㉜;二是先驱社会运动并不直接为后续社会运动提供框架或意义元素,而是以自己的框架建构为其他社会运动的框架建构开创一个政治机会空间,使它们能够发生和存在㉝。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市化与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推进,社会结构的加速分化使得单位共同体日趋式微,如何重建社区、重构适应城乡居民多元化需求的新的共同体成为基层政府面临的新挑战。从滕尼斯到鲍曼,“‘共同体’意味着的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㉞。正因为如此,自90 年代以来一项旨在改革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社会工程——社区建设运动的兴起带来了社区研究的复兴,显然这构成了基层社会动员的主框架范畴。政府和学界为基层社会建设提供了理论和制度框架,但现实中形成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社区还需通过居民的基层社会参与和日常草根实践来认识㉟。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由社区参与和基层社会自治方面的制度建构转向居民的社区意识和参与行为(王思斌,1991;马卫红等, 2000;孙柏瑛等,2001;徐庆文,2001;王小章、冯婷,2004;张宝峰,2005)。
回溯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草根动员,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一种地方性权威式动员——这一动员模式是在总体性社会解体的背景下适应城市社会变迁的一种新型的权力技术,既运用原有行政组织网络的强大动员力量,又借用某些非正式因素,将社区居民纳入社区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之中。因为在改革以前的总体性社会中,由于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不对称,单纯依靠行政系统难以实现对资源的总体性控制,群众草根动员就成为党和政府实现治理目标的重要手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单位制的瓦解和市场机制的确立使资源分配渠道呈现多元化,居委会手中所掌握的体制内的资源又十分有限,由此改变了组织化动员得以存在的根基。市场观念的渗透、传统意识形态的弱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劝说、教育等参与式动员策略的效力下降。而党和国家强调稳定的新型治理理念也使他们抛弃了具有破坏性的运动式动员的手段㊱。由此,基层社会动员的草根机制、方法需要借力社会体制改革以寻求新的“主框架”得以支持、扩散。
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明确要求“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㊲。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把社区治理写入党的纲领性文献,进一步指明了社区建设的方向、原则和任务,这在某种意义上为推进新形势下基层社会动员的框架整合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依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㊳。可见,创新社会治理、激发基层活力是新时期基层社会动员“框架扩散”的时代命题。2014年上海市委“一号课题”重要成果——《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健全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议题和自治项目形成机制,引导居民全程参与社区自治事务”㊴。正是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这一时代“主框架”的影响下,梅陇三村党总支以“GREEN HOUSEWIFE”公益项目推广活动为平台,将“绿色环保家园”这一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草根议题作为新时期特大城市社区建设的框架整合策略,不失时机地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引导居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培育社区公共精神与草根意识上,通过构织基层群众草根自治组织网络实现了基层社会动员的框架整合。
四、结论与讨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而基层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精细化和共建共享治理格局形成的重要场域,承担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实践与社会行动方略,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伟大中国梦这一治理主框架的重要整合路径。自滕尼斯以来,西方社区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在个人至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社会,一群陌生人如何超越个体私利形成具有集体责任感和归属感的社区?经典社区研究——人类生态学、社会系统与结构功能主义以及社会互动论分别从空间竞争、价值共识和符号互动的角度解释了社区的形成和整合机制(Stoneall,1983;Poplin,1979;Lyo n,1987)。这些解释都只强调了社区的某个方面:地域、共同联系和互动。随着现代社会空间改造步伐加快、价值日趋多元化和人际疏离加剧,这些经典理论在解释社区形成机制方面已显出不足。社区研究的最新进展——社区形成过程研究将参与视为社区形成的核心机制,从动态的视角揭示了草根社区形成的具体过程㊵。
社区认同感的形成、社区意义的建构以及市民在空间政治博弈和社会改造过程中主体性的生长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通过参与保护生活空间的文化特质和集体记忆的过程而实现的㊶,而基层社会参与的内在动力从某种意义上正在凸显基层动员的框架整合路径与草根行动效应。有学者将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比作一种化学反应过程——“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共同需求以及居民的情感和理性,就如同化学方程式中的反应物,动员结构为反应发生的催化剂,制度为反应发生的附加条件,而集体行动则是反应的生成物。只把反应物放在一起,反应难以发生或者极其缓慢,但是当加入催化剂时,反应会加速,而制度使该反应持续发生。也就是说,在基层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仅有社区居民的共同需求、情感与理性很难自发地产生集体行动,在核心行动者采取行动策略动员潜在参与者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情况下,集体行动才较易发生,其中动员结构是通过作用于潜在参与者的情感和理性使其加入集体行动。另外,该集体行动是可循环的,前期集体行动产生的结果——制度,又反过来指导和形塑人们的行为,使集体行动持续有效地运行”㊷。
当代中国社区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讲仍然主要由政府推动与主导,在社区建设的发展目标、结构构造、功能设计与运作机制等方面,都呈现出“行政性推进”与“社会化参与”两个基本方向的互动。由此,政府主导推动社区建设的过程,并不单纯是一个孤立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性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有意识的探索性的发育草根社区的客观过程,包括社区各类社会化组织的逐步发育和形成、公众对社区活动参与的不断扩大、基层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样化以及社区成员的社会化联系和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等㊸。大量基层社会草根组织网络生成与运作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社区的核心行动者框架动员与草根行动的整合过程——如同凌云“GREEN HOUSEWIFE”的环保实践逻辑。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凌云“GREEN HOUSEWIFE”的顺利推进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其核心行动者尚艳华的框架动员。Kuhnert认为,在研究集体行动过程中必须关注企业家个体的角色、动机和能力㊹。尚艳华之所以成为上海“GREEN HOUSEWIFE”的核心行动者,与其具备相应的角色资格、动机和能力是分不开的。在担任上海“GREEN HOUSEWIFE”环境保护指导中心负责人之前,尚艳华就有多年的农场锻炼经历,也曾是某国企组织科的干部,加之梅陇三村党总支书记的特殊身份以及她本人善于洞察政策机会的能力,使得上海“GREEN HOUSEWIFE”在基层社会动员中实现了有效的框架整合与草根行动效应。这一经验也许对于中国未来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战略要求,而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关键在一定意义上即是要廓清国家和社会的分界,对于基层政府而言,应为社会主体预留充分的自治空间,为基层民众提供参与公共决策与草根治理的平台和机会,提高公众社区参与的水平,构建基层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沟通机制㊺。可以说,上海“GREEN HOUSEWIFE”这一基层社会治理的框架整合案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中央社会治理创新的最好回应,也是推进基层公共精神发育提升基层草根治理能力的重要探索。
注释:
①参见Goffman,Erving.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1974.
②从学术源流和谱系的角度说,认知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出自组织动员研究,和理性分析论一脉相承。这样,运动参加者的主体意识得到了理性的诠释,而不只是当作情感的破坏性宣泄。同时,认知框架分析不是理性行为理论的简单延伸,因为这一概念实际上不得不超越理性分析模式,强化情感和文化分析的领域。可以说,认知框架分析正是要在理性的认知分析和非理性的分析(心理、情感)间建立起某种联系。社会运动认知框架( frame)使群众激情( emo tion)及其向集体行动的转化,得到了理论上的表达。参见Nick Crossley,Making Sense of Social Movements,Open University Press,Buckingham,2002:136.
③在Snow看来,框架对于人类的认知和行动具有三个功能:聚焦、连接和转变。参见Benford,Robert D. and A. Snow. 2000. “Framing Process and Social Movements: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611-639;Snow,David A. 2004a. “Framing Process,Ideology,and Discursive Fields. ” PP. 380-412 i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edited by D. A.Snow,S. A. Soule,and H. Kriesi. Malden,MA: Blackwell Pub.PP384-385
④参见McAdam,Doug, John D.McCarthy, and MayerN. Zald. (eds. ). 1996.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Movemen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刘春荣.选举动员的框架整合——银杏居委会换届选举个案研究.社会,2010(1).
⑤在Klandermans看来,集体行动的社会建构过程可分为“公众话语和集体身份”、“说服性沟通”(Persuasive Communication)以及“意识提升”三个层次来讨论。“框架配合”(Framing Alignment)、“共识动员”(Consensus Mobilization)和“目标与手段包装”(Packaging of Goals and Means)等策略的主要目的是令行动所代表的理念能与社会的核心价值联系起来。参见Klandermans,Bert & Sidney Tarrow 1988,Mobilization into Social Movements: Synthesizing European and American APProaches. in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eds. ) by Bert Klandermans,Hanspeter Kriesi & Sidney Tarrow.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vol. 1. Greenwich,Conn.:JAI;刘春荣.选举动员的框架整合——银杏居委会换届选举个案研究.社会,2010(1).
⑥陈天祥,杨婷.城市社区治理:角色迷失及其根源——以H 市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3).
⑦陈天祥,叶彩永.新型城市社区公共事务集体治理的逻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⑧2014年6月,“GREEN HOUSEWIFE”家庭可再生废弃物回收志愿者服务团队被中宣部授予全国最美人物之“节约之星”称号;2014年12月,《“GREEN HOUSEWIFE”居民自治组织的发展历程》获得上海社会建设十大创新项目。参见《新民晚报》,2014.12.30;凌云街道党工委:《从“垃圾三村”到“花园三村”的蜕变——“GREEN HOUSEWIFE”居民自治组织的发展历程》,中共徐汇区委党建网。
⑨爱心编结社前身是“GREEN HOUSEWIFE编结聊吧”,最初是由喜欢编织毛衣的阿姨们汇聚活动的场所,她们一边编织毛线,一边聊聊家长里短,献爱心和民意收集两不误,聊吧的召集人经常把收集到的社情民意汇总到“GREEN HOUSEWIFE议事会”,而梅陇三村党总支则通过聊吧向居民开展一些宣传发动工作,效果出乎意外的好。当然,“编结聊吧”爱心行动主要是为小区的独居老人义务编织毛衣、围巾、手套等过冬衣物,三年时间里,总共向老人们赠送了200多件过冬衣物。2012年秋冬时节,“GREEN HOUSEWIFE编结聊吧”升级成为“GREEN HOUSEWIFE爱心编结社”,人数也增加到了70多位,“GREEN HOUSEWIFE”团队编制的爱心衣物达1800多件(套)。参见凌云街道党工委:《从“垃圾三村”到“花园三村”的蜕变——“GREEN HOUSEWIFE”居民自治组织的发展历程》,中共徐汇区委党建网。
⑩Snow, D.A., & Benford, R.D.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1988,(1),PP197- 219.
⑫韩狄明,陈彬.梅陇三村社区自治的经验与启示.检察风云——社会治理理论专刊,2015(1).
⑬居民自治必须先凝聚人心.检察风云——社会治理理论专刊,2015(1).
⑭刘中起.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构筑与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基于上海市G社区的案例分析.城市观察, 2012(2).
⑮范斌,赵欣.结构、组织与话语:社区动员的三维整合.学术界,2012(8).
⑯Snow, D., et al. Social met words and social movements: A micro structural approach to differential recruitment. Americans Sociological Review,1980,(45)
⑰王冠.动员式参与与主体间性:居委会的社区参与策略考察.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
⑱正是这样的网络层层递进地揭开了集体行动的帷幕,并生产出集体福利。由此,框架化过程有赖于特定的动员网络结构的形成。动员主体的跨越制度边界的、散布性的结构特征,可以扩展动员幅度,更好地综合各种竞争性的解释话语,从而更容易达成共识并实现框架整合。参见Kim, Hyojoung and Peter S. Bearman. 1997./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MovementParticipation.0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70-93;刘春荣.选举动员的框架整合——银杏居委会换届选举个案研究.社会,2010(1).
⑲凌燕.“GREEN HOUSEWIFE”以绿色先行,探索居民自治模式.检察风云——社会治理理论专刊, 2015(1).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闲书的阅读,没有压力,没有强迫,没有功利,纯粹是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所以往往更能引领自己寻找到自己的真正擅长,真正打开属于自己天赋的灵田。很多人在人生路的中途又独辟蹊径,答案正在这里。一个农民成了作家,一个医生成了诗人,一个教师成了画家,不都是因为他们横向的寻找吗?
⑳参见Durkheim, Emile,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Trans. by W.D. Halls. London: Macmillan,1984.
㉑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19-220.
㉒曾鹏,罗观翠.集体行动何以可能? ——关于集体行动动力机制的文献综述.开放时代,2006(1).
㉓刘能.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开放时代, 2004(4).
㉔陈天祥,叶彩永.新型城市社区公共事务集体治理的逻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㉕韩狄明,陈彬.梅陇三村社区自治的经验与启示.检察风云——社会治理理论专刊,2015(1).
㉖范斌,赵欣.结构、组织与话语:社区动员的三维整合.学术界,2012(8).
㉗因为“公共物品一旦存在,每个社会成员不管是否对这一物品产生做过贡献,都能享受这一物品所带来的好处。公共物品的这一特性决定了当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想为获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时,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能让别人去为达到该目标而努力,而自己则坐享其成”。所以必须运用选择性激励手段去促进所有利益相关社区居民的参与,选择性激励是某些社区居民如果不参与则会失去某些东西,唯有如此,才能使理性的个体积极地参与到社区建设中。参见赵鼎新:《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王冠:《动员式参与与主体间性:居委会的社区参与策略考察》,《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㉘帕特南( Putnam) 认为:公民参与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在一个共同体中,这类网络越密,其公民就越有可能为了共同利益进行合作,而这网络指的是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参见:[美]罗伯特D.帕特南著,王列、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 现代意大利公民传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页;陈天祥、叶彩永:《新型城市社区公共事务集体治理的逻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㉙李妮.社区社会资本与社区自治的关联及其发展.重庆社会科学,2008(10).
㉚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 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人民日报,2016,10,13.
㉛Snow, D.A. and R.D. Benford. Master Frames and Cycles of Protest, 1992,Pp. 133-155 in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ited by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P148
㉜Mooney, Patrick H. & Scott A. Hunt. “A Repertoire of Interpretations: Master Frames and Ideological Continuity in U.S.Agrarian Mobilization.”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 37,1996,PP177-197
㉝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230-231.
㉞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3.
㉟杨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国究.社会学研究,2007(4).
㊱杨敏.公民参与、群众参与与社区参与.社会,2005(5).
㊲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
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
㊴参见《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2014年12月31日.
㊵杨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国究.社会学研究,2007(4).
㊶夏铸九等.朝向市民城市:台北大理街社区运动.台湾社会研究,2002(46);庄雅仲.五饼二鱼:小区运动与都市生活.社会学研究,2005(2).
㊷陈天祥,叶彩永.新型城市社区公共事务集体治理的逻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㊸徐中振,徐珂.走向社区治理.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1);刘中起.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构筑与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基于上海市G社区的案例分析.城市观察,2012(2).
㊹Stephan Kuhner,“An Evolution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 Schumpeterian Entrepreneurship for the 侨Common Good”,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1( 12) ,PP 13—29
㊺李树忠.全面认识基层治理法治化.光明日报,2014-11-8.
Framework Analysis of Grass-root Socia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Yang Xiuju, Liu Zhongqi
The institution of grass-root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has undergone substantial changes since the 1990s following the collapse of the unit system and the gradual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ty system. The supplying mechanism of public goods has also been changed. The real plight facing the new type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China is that the existence of the strangers’ society makes collective actions such as self-governance never an easy task. Meanwhil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urban communities, to some extent, resembles more of a topdow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logic and strategies of people’s actions manifes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so ar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its people. It is worth studying that in such a time when the grass-root activity is motivated by innov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what can be done to join together the massive subject of grass-root governance and the everyday practice of the general public through organization network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he paper is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
grass-root action; social governance; framework analysis
C916
10.3969/j.issn.1674-7178.2017.02.009
杨秀菊,上海徐汇区委党校、徐汇区行政学院教师。刘中起,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卢小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集体行动的内在认同机制及其消解策略研究”(项目号:13BSH03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8批面上资助项目(项目号:2015M58027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