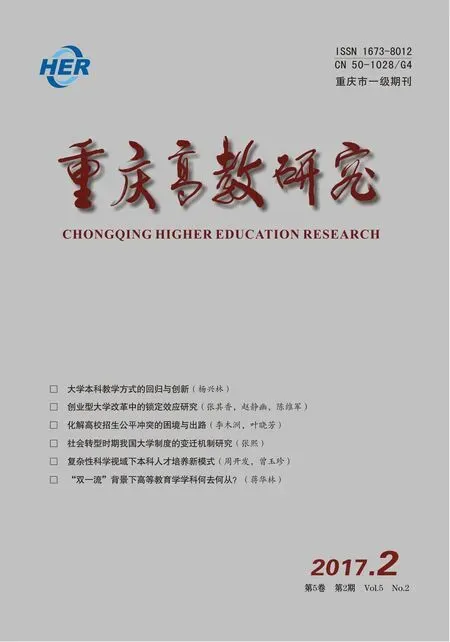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大学制度的变迁机制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与反思
张 熙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专题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大学制度的变迁机制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与反思
张 熙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关注焦点。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研究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大学制度的变迁机制,在分析宏观制度因素与路径依赖模式的同时,关键还在于把握历史制度主义近年来的理论反思与发展趋势,探讨制度场域中的权力关系、思想观念和行为互动对于制度渐进性变迁的影响,从而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制度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转型时期我国高校制度变迁主要受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与内部动力因素的驱动,表现为渐进型的双重变迁。一方面,制度环境中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心理是大学制度变迁的外部结构性要素,其推动力主要体现在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变迁。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场域中的权力结构、制度观念和行为者互动是大学制度诱致性变迁的内部动力,在未来将更为深刻地影响大学制度的持续变迁。
历史制度主义;大学制度变迁;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大学制度问题逐渐引起中国高等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并成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重要命题。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出台和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试点工作的开展,近年来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探讨将相关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目前,学术界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已有相当多的积累并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初步形成了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多学科范式。有学者认为,相关研究应加强对本国高校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分析和基于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1],因为就其本身而言,现代大学制度并非是抽象的价值理念或泛化的制度框架,而是世界各国大学在其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且不断演变的制度体系。对于中国大学而言,如何基于本国国情与大学发展历程来探究我国大学制度的变迁机制,不仅是高等教育制度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对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理性构建也具有积极意义。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探索开始于清末民初,新中国成立之后经历了较为剧烈的变革。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正经历着全面而深刻的社会转型,国内高校则在相对稳定的内外部环境下不断改革与发展。因此,笔者以改革开放后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重新探索为逻辑起点,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并结合其理论反思与发展趋势来剖析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大学制度的变迁机制。
一、理论反思与分析框架的重构
作为新制度主义中的重要流派之一,历史制度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受到西方学术界特别是政治制度研究者的关注。由于受到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旧制度主义传统的影响[2],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主要体现在它的结构观与历史观上。在其结构观中,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影响制度的宏观因素,特别是国家的政治体制对于公共政策和其他制度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极为重视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在其历史观中,历史制度主义注重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强调制度发展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重大事件以及偶然性因素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3]。
相较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的特点在于其分析并不是基于一个特定的理论前提或假设,而是从具体国家或地区的历史脉络中寻找制度演变的线索,这使得其关于制度的国别研究与比较研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进而成为当代重大问题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早期的历史制度主义十分强调环境改变、路径依赖和偶然性事件对制度的影响,认为制度经历激进变革后会长期处于稳定状态。制度发展所遵循的是路径依赖的逻辑,直到下一次激进变革的到来,也就是所谓的“断裂均衡”模式。在这种逻辑下,它虽然能够恰当地解释制度的稳定性以及剧烈变迁的原因,但无法很好地解释制度渐进型变迁的机制与可能性,而后者对我国当下的大学制度改革与设计恰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近年来,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开始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来探讨高等教育领域的制度变革。笔者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传统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的局限性很明显地反映在国内相关研究中,多数论文仅停留在对历史脉络的梳理和对路径依赖的分析上,关于制度变迁的研究也只是对变迁类型的介绍或对断裂均衡模式的演绎,缺乏对制度变迁机制的合理性解释,而就此做出的改革推论在逻辑上也难以自圆其说。
近年来,通过关注制度结构性要素间的冲突和矛盾以及新的组合来解释制度变迁,已成为历史制度主义发展的新趋向。特别是渐进性制度变迁最终导致制度根本性变迁的可能性,已引起制度研究者的关注[4]67-68。历史制度主义在对自身进行深入反思的基础上借鉴了其他制度理论流派的主张,它认为制度是由多样的、异质性的要素或逻辑构成的复合体,而这些要素之间的互动将会导致制度的不断变迁[5]。因此,历史制度主义没有停留在外部结构变量和路径依赖的分析层面,其关注重点转向了制度变迁的内部因素,开始积极运用权力结构、思想理念、行为互动等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来分析制度变革的内在机制,希望提出更为有效的分析框架。因此,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剖析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演变,除了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外部制度环境中的结构性要素以外,还需要对影响大学制度渐进性变迁的内部变量进行研究。
二、社会转型期大学制度的发展与沿革
(一)高等教育秩序整顿与恢复(1978—1985年)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性转折点。但由于“文革”十年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严重破坏,这一阶段高等教育领域的主要任务是恢复与调整。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国家在高校招生制度、发展规划和领导体制方面做了一些探索。高校在读学生数量迅速增加,基本上满足了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1978年,教育部在1961年《高教六十条》的基础上颁布了《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规定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实际上确立了党委在学校重大问题决策中的核心地位。1979年,中共中央修订并颁布了《关于加强高等教育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决定(试行草案)》,重新确立了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体制。虽然我国高等教育的秩序得以较快恢复,但就高等学校的办学和管理体制而言,这一时期实行的依然是“国家包办、统一计划、高度集权、条块分割、统招统配”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模式。地方政府和高校基本没有管理权力可言,社会和个人也没有机会参与高校的办学和管理事务。
(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探索(1985—1992年)
这一时期是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教育等各个领域启动改革与探索发展的新时期。随着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科技和教育体制的改革成为国家发展中的战略性任务。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相继颁布,尤其是后者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来讲,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以权力下放、理顺中央与地方职权关系、实行党政分开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为重要内容。从1985年到1992年,中央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教育发展规划、学位与专业审批、保送生制度、毕业生分配、高校领导干部任免、机构设置和社会力量办学等一系列具体政策。这实际上为之后20年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80年代中期,高校内部涌现了一批具有改革精神的大学领导者和改革典型案例,如武汉大学的教育教学改革、上海交通大学的管理体制改革、深圳大学的办学体制改革等。此外,不少高校也尝试实行了以校长负责制推动大学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然而,受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影响,国内的学潮运动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对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负面效应,部分高校改革的成果没能得以持续和扩大。虽然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大方向已经确定,但国家本位的集权模式依然占据主导地位。
(三)高等教育稳步发展中的制度变革(1992—1998年)
90年代初,我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再次加快,也使很多领域的思想观念得到进一步解放。1993年颁布的《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要实现中央与地方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管理体制,并逐步建立国家规划与宏观管理、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新体制。《意见》还提出了在招生和就业体制方面的改革目标,如扩大自费生比例并逐步实行多数毕业生面向市场自主择业。此外,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1994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指出高等教育要走以内涵发展为主的道路,使规模更加适当,结构更加合理,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这是该阶段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特点。相比之前,这一时期政府下放权力的速度加快,高校自主权有所扩大,社会和个人获得了之前没有的一些教育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我国大学治理由国家本位开始向市场本位转型。就高校内部管理体制而言,随着90年代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学术权力得到张扬,其主要标志是高校普遍设立了学术委员会和学科发展委员会等机构。教授和一般教师在学科和专业规划、学位授予、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科学研究等方面已获得较大权限。但与高校内部行政权力相比,学术权力相对较弱且缺乏独立性,常常是行政权力主导着学术权力。此外,学生权力微不足道,学生组织和团体只是行政权力的附属或受其委托从事学生管理工作[6]。
(四)高等教育加速发展与深化制度改革(1998—2010年)
21世纪前后,在“高等教育强国”理念的指导下,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与战略规划。在整体规模快速提升的同时,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速度也在加快。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不但明确了高校的法人地位,还进一步规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与高校的权责关系,同时鼓励社会和公民依法办学,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高等教育法》还对高校的内部管理体制、办学自主权以及高等教育的投入与保障等问题做了明确规定。我国在法律和政策文本上进入了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实质性阶段,高等教育权力的下放速度也超过了以往。然而,我国大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如规模快速增长与教育质量保障之间的矛盾、高校盲目趋同性发展而欠缺办学特色、大学日益行政化与官僚化等问题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较为全面地阐释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完善大学治理结构”。在这之后,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与未来发展方向的现代大学制度的探索成了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中的热点问题,也是我国今后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任务。
(五)全面深化改革与现代大学制度的推进(2010—)
近年来,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在推动高等教育外部制度环境与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同时,也促进了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方面,政府加快了向地方和高校下放权力的步伐,强调政府角色与职能的转变,提出构建政府、大学、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新型关系;另一方面,政府和高校都意识到,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需要进一步明确各利益主体的权责关系,不断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与相关制度建设。由此,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意见》和《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等指导文件,旨在扩大和落实高校在招生考试与录取、教学与科研、学科专业设置与调整、人事制度管理、财政经费管理、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自主权。政府在加大放权力度的同时,更加强调对高等教育进行宏观管理,提出综合运用法律、政策、规划、财政、指导标准和信息服务等,把该放的放开,把该管的管住。此外,教育部还相继出台了《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普通高等学校理事会规程(试行)》《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等重要文件,对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深化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相关原则做了进一步的制度安排。在政府部门的推动下,部分高校在大学章程建设、理事会制度、人事制度、学术评价机制、考试招生制度、研究生培养模式、学部制、教师专业发展、产学研合作和创新创业教育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已进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
三、大学制度渐进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由历史梳理可以看出,转型时期我国大学制度主要是一种局部替换式的渐进式变革。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为特点,在制度发展中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历史制度主义认为,现有制度不仅造成了社会集团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7],而且还具有使这种不平等关系继续下去的倾向,过去的制度安排和权力关系会制约未来制度选择的路径[8]。当一种制度被选择之后,它本身会产生自我捍卫和强化的机制,使得扭转和退出这种制度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制度陷入一种“被锁定”的路径依赖之中。制度场域中存在的权力秩序、学习效应、协同效应和适应性预期是造成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
(一)权力分配的非对称性
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政治权力分配的非对称性是产生报酬递增的一个原因[4]28-29。由于政治权威倾向于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强化自身地位进而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在集体行动、制度演变、权力行使和社会解释的过程中都存在自我增强的倾向。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制度的变迁,由于初始权力关系的极端不对称,权力的主导者并不愿意主动放弃既有权力和利益,加之历史上两次盲目放权造成的混乱,政府始终在权衡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利弊关系,因此在给高校放权上一直比较谨慎,诸如学科和专业设置、考试招生、重大人事任免等重要权力至今仍未全部下放。此外,由于政府、大学以及社会的角色关系和权力边界未能厘清,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和功能还需不断完善,因此政府主导的放权路径和资源二次分配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导致高校内部行政化趋势的加强[9],这也是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学习效应
改革开放后,政府、大学和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议题。我国在1950年借鉴苏联模式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利用有限的资源发展高等教育,按照国家现实需求培养各行业的专门人才。但与此同时,这也加强了国家对大学办学政治方向的引导和思想控制。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政策基本上恢复了建国初期集权式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学习和复制的行为,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秩序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路径依赖效应也阻碍了大学制度的变革。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之后,我国“高等教育强国”的学习对象开始向欧美等发达国家转向,高等教育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转变,但由于国情体制和学习对象的先后顺序,使得转型期中国大学的改革既呈现出路径依赖的色彩又有路径替代的趋向。
(三)协同性效应
由于相关主体已经被深深地嵌入旧制度的模板之中,已有的正式规则会导致一系列非正式约束的产生[10]111-113,这种各安其分的协同效应使得制度变革十分困难。在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过程中,虽然政府不断出台相关政策,但由于政策实施和操作中的问题,地方政府与高校感受到的制度变迁的压力较小。地方政府要推行大学制度改革,既要考虑与其他地方政府的协同性问题,也要考虑与上级部门的利益协调与政治支持等因素[11]。就高校内部而言,一方面,以党政机构主导的制度变革在推动外部制度变革中力量有限;另一方面,大学内部学术和学生权力不足使得制度创新缺乏自下而上的内生动力。此外,由于制度变革要支付“实施成本”“退出成本”和“摩擦成本”等多重成本[11],所以各主体间相互观望与“搭便车”成为一种较为稳妥的选择。因此,随着制度环境和权力结构的改变,在固有路径之外更需要探索制度变迁的其他动力机制。
(四)适应性预期
当一种制度框架经过充分的制度化过程而被固定下来之后,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预期,尤其当这种制度仍能使多数利益主体受益并可以通过制度微调来适应环境时,人们对这项制度的预期往往倾向于保留和维持[10]23-25。例如,我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一直以来不乏批评甚至废弃之声,政府也不断地进行高考制度改革与调整,但其作为一种符合中国国情且较为公平的教育考试制度还是被保留了下来。改革开放后,高考制度客观上使政府、社会和个人都获得了收益,特别是平民阶层因此得到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总体上有利于社会公平与稳定。因此,政府、高校和社会对高考制度的正向功能持有基本的共识。这样一项重要制度的变革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和高昂成本使得政府、高校和社会都对改革慎之又慎,所以近年来的高考改革依然遵循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逻辑。
四、大学制度变迁的外部制度环境
(一)国家政治体制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高校外部资源配置主要由政府调控,社会力量无法有效参与大学治理,大学也难以面向社会筹措办学资源。此外,高等教育相关法律体系建设十分滞后,大学办学的主体地位和自治权力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使得高校党政机构实际上成了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附属。大学管理中的诸多事务均需要获得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高校缺乏独立自主的行动能力与改革创新的驱动力。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两个主要目标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旨在改变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各个领域过度集权的旧体制,教育领域的变革也基本遵循国家宏观体制改革的逻辑。回顾转型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现代大学制度的探索,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生成与变迁主要依靠政府主导下的制度供给模式,与同时期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密切的联系,而制度环境的改变往往为大学的改革提供了契机与先导。有学者认为,现代大学制度是大学在逐步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国家现代化进程具有高度一致性,大学要获得制度环境的合法性支持,其行动必须要在国家制度框架的范围内并受其约束。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与变迁受到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权力文化向法律文化转型等深层次的社会背景因素的影响与规制。因此,就其总体发展趋势而言,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是我国大学自主权逐步得以扩大的时期,也是我国大学治理从行政主导逐渐走向法人治理模式的过程[11]。
(二)社会经济水平
在历史制度主义的结构变量分析中,社会经济水平和思想观念分布是其考察的核心要素。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经济资源有限,国家只能通过行政命令和计划式管理来规范高等教育的秩序。近30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大学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资源支撑,中国逐渐具备了建设一流大学的外部条件。然而,仅靠资源堆积和行政指令无法发挥大学的主动性与创造力,更别奢谈建设真正的一流大学。因此,建立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现代大学制度就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大学教育已不再局限于为某些传统行业培养专门人才。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型使大学的科研和社会服务职能逐渐凸显,高校办学既要符合自身特色和定位,又要面向市场进行调节。这都客观上要求高校要相对独立地履行各项职能,而政府则更多地通过宏观调控而非直接行政干预来管理大学。此外,社会成员的选择和利益也出现了巨大的分化,政府、大学、社会和个人等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取向。这就需要打破以往政府绝对主导的大学管理体制,建立一种能够协调不同利益群体诉求的现代大学制度。
(三)意识形态与文化心理
从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来看,首先,“高等教育强国”是改革开放后政府推动大学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正向功能[12]。由于结构(制度)对功能的决定作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便成为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理想的重要载体。其次,国家在推动大学发展时的主要原则是坚持办学的社会主义方向,在改革过程中还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一方面,政府期望大学在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为国家做出贡献,因而给予高校一定的办学自主权;另一方面,政府又要防止激进变革可能导致的秩序失控,避免自由主义思潮泛滥。此外,较之改革开放前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绝对主导的话语体系,近30年来中国大学出于学术本位思想而要求自主和自治的呼声越发突出,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的探讨和争论可以看作是大学主体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一。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社会和个体思想观念的变化。一方面,大学已不再是世人眼中远离尘嚣并带有神秘感的象牙塔。另一方面,伴随大学的“世俗化”和“去魅化”而来的是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诉求的凸显和“大学共治”思想的萌发。因此,构建一种基于本国国情又能够包容各种思想观念的制度体系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时代要求。
五、制度渐进型变迁的内部动力机制
近年来,历史制度主义在坚持自身特点的前提下,适当借鉴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利益算计”模式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文化认知”层面的分析思路。首先,历史制度主义十分重视现有制度中的权力结构与关系对行动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制度对行动者进行约束的同时,又给予行动者机会和资源。此外,为了合理地解释制度约束下行动者的偏好形成与行为选择,历史制度主义还十分关注制度理念的建构对于行动选择的塑造作用。因此,探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大学制度的变迁机制,除了路径依赖和外部制度环境外,还需要从制度场域中的权力结构与关系、制度观念和行为互动这3个方面进行研究。
(一)权力结构关系
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环境的改变和相关政策出台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合法性与外部条件。政府不断下放权力使制度场域中的权力结构发生改变,这种变化对制度的渐进型变迁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实际上,现代大学制度的发展就是高等教育内外部各种权力间不断进行博弈、重新组合和寻求平衡的过程。因此,如何在国家控制与高校自治、大学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大学自主办学与社会参与监督之间建立符合国情的权力关系模式就显得十分重要。有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高等院校、社会和个人等相关主体间的权力结构与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高等教育正从政府高度集权型向政府适度主导型转变,提出在中国现实体制下未来的理想模式应当是向高校适度主导型转变[13]。笔者认为,目前政府主导的大学制度变革虽说还存在许多不足,但仍是在整体制度约束下的一种较为理性的选择,只不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国民素质的提高,可以逐步向高校主导型转变,使政府、高校和社会的权力结构进一步趋向于合理。与此同时,还需要明确各权力主体的角色与职能,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和制度框架。随着政府权力的下放和外部权力结构趋向稳定,高校内部权力关系与治理结构变革对于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重要性将更为突出[14],学校内部的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力之间的互动与利益博弈将推动大学制度的持续变迁。
(二)制度理念与话语
我国高等教育界普遍认为,现代大学制度不仅是一套规范性的制度框架,更代表着一种现代大学的制度文化与价值追求。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此类主题进行了诸多讨论,政府文件和带有官方色彩的著述中也不乏相关表述,这其中既有共通性的认识,也有异质性的见解。这一方面展示了相关制度观念的丰富性,另一面也反映出场域中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的作用。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如何对理念要素进行重组和运用以及谁的理念体系将会反映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取决于持有不同理念的众多集团中拥有权力和资源较多的一方。按照这种观点,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过程也是相关理念和意识形态重新组合与诠释的过程,能够影响政策和制度的精英集团通过引入、选择、诠释、整合和执行理念来推动政策变迁。例如,学术精英团体努力将现代大学制度的理念框架化甚至范式化,通过对现实的批判与反思以及对国外大学制度的借鉴与比较,力图将制度变迁引向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方向。相对而言,政府则更倾向于从本国政治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出发,以国家本位的立场对各种观念和声音进行辨识与取舍。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讨论经历了从借鉴国外大学制度理念到强调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体系的过程。这反映出场域中相关的制度观念是不同权力主体基于特定的制度背景和目标策略所进行的理念建构,而这种观念性的转变将对制度的发展与变迁产生重要影响。
(三)行动主体的互动
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场域中的行为主体不断增多,其行为模式与互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高等教育中行动者似乎只有政府和大学,其互动方式主要是国家颁布政策法规,大学被动执行或消极反馈。随着制度环境和管理体制的变革,一方面,政府在尝试调整和转变职能,加强对高等教育的宏观引导和监督问责,尝试减少过多的行政干预。另一方面,国内不少高校进行了内部机构与管理体制改革,出现了一些被政府和社会所关注的改革个案或群体典型。如北京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南方科技大学的自主招生和去行政化改革、部分高校的本科生通识教育与培养模式改革、大学的学部制与书院制改革等都是高校运用自主权力进行的积极探索。此外,部分具有影响力的高校领导和学者利用体制渠道,如人大、政协提案和专家咨询委员会向政府部门建言献策,部分人直接参与相关政策与规划的制定,还有近几年“高校智库”的建设与发展,这些都是大学组织试图以“知识动员”的方式来影响和改变制度环境的重要表现。与此同时,社会和个人参与高等教育的积极性以及权利与问责意识逐步增强,新闻媒体、用人单位、校友代表、家长和学生对于大学制度的变革将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无论是政府还是高校,面对来自社会的质疑和诉求都无法再保持沉默,如何回应外界关切,协调多方关系,为高校发展集思广益,都需要一种更为合理的大学制度框架。
六、结语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回顾与分析,笔者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社会转型时期我国高校制度变迁主要受外部制度环境的影响与内部动力因素的驱动,表现为渐进型的双重变迁。一方面,制度环境中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心理是大学制度变迁的外部结构性要素,其推动力主要体现在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变迁。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场域中的权力结构、制度观念和行为者互动不仅是大学制度诱致性变迁的内部动力,在未来还将更为深刻地影响大学制度的持续变迁。因此,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与反思,理解和把握转型时期我国大学制度的变迁机制,不仅具有学术上的探讨价值,也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理性设计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首先,重大历史事件和国家决策往往成为制度变革的先导并为其创造条件。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应抓住“历史关键点”,特别是抓住当前深化改革的契机以推进制度完善进程。第二,由于制度环境中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和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的成效也依赖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以及社会文化和国民素质的提高。第三,高等教育制度场域中的权力结构与关系的改变是大学制度变迁的重要条件,除了政府放权之外,未来应通过加强法律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相关主体权责与行为界限,建立权力负面清单制度。第四,思想观念在现代大学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基于本国国情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理念与话语体系,凝聚利益相关群体的改革共识,有利于更好地引领大学制度向前发展。第五,促进高等教育利益相关方的良性互动,除了转变政府职能以外,还应当推动高校内部民主管理模式的创新,更好地发挥基层学术组织的作用,引导学生和社会各界积极有序参与大学事务。这些都会对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变革产生积极且深远的影响。
[1] 李连梅.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脉络、指向与展望[J].高校教育管理,2015,9(4):114-119.
[2] 何俊志.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J].国外社会科学,2002(5):25-33.
[3] 刘圣中.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的比较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92-107.
[4] 河连燮.制度分析——理论与争议[M].刘秀峰,柴宝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5] LIEBERMAN R C.Ideas,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order explaining political change[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2(4):697-712.
[6] 黄红卫.我国公立高校权力冲突与协调的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09:2.
[7] 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70-83.
[8] KNIGHT J.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27-30.
[9] 钟秉林.关于大学“去行政化”几个重要问题的探析[J].中国高等教育,2010(9):4-7.
[10]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11]罗红艳.我国公立大学治理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4(3):16-21.
[12]王洪才.中国大学模式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建构[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35-40.
[13]林荣日.制度变迁中的权力博弈——以转型期中国高等教育制度为研究重点[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352-366.
[14]龚怡祖.大学治理结构: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石[J].教育研究,2009(6):22-26.
(责任编辑 吴朝平 冯 帆)
Study of the Change Mechanism of Chinese University Institutions in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ZHANG Xi
(Faculty of Edu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With the advance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capability,the building of modern university institution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domestic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the change mechanism of Chinese modern universities has been studied.Meanwhile,while analyzing the factor of macro system and dependent mode of path,the key is to understand the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nd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recent years,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more powerful systematic analysis framework.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the change of Chinese university institutions mainly is affected by the environment of external system and driven by the internal motive factors,which displays the gradual double change.On the one hand,the political system reform,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are the external structural factors for the change of university institution,and the driving force is mainly dominated by the government’s compulsive change.On the other hand,the power structure,system concept and the interaction of behaviors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are not only the internal power to induce the change of university institutions,but also profoundly affecting the constant change of university institutions in Chin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change of university institutions;higher education;institutional reform
G647
A
1673-8012(2017)02-0048-09
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17.02.007
2015-12-18
张熙(1986—),男,四川达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大学组织与治理及高等教育制度理论研究。
张熙.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大学制度的变迁机制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与反思[J].重庆高教研究,2017,5(2):48-56.
format: ZHANG Xi.Study of the change mechanism of Chineseuniversity institutions in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based onthe analysis and reflection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J.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20175(2):4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