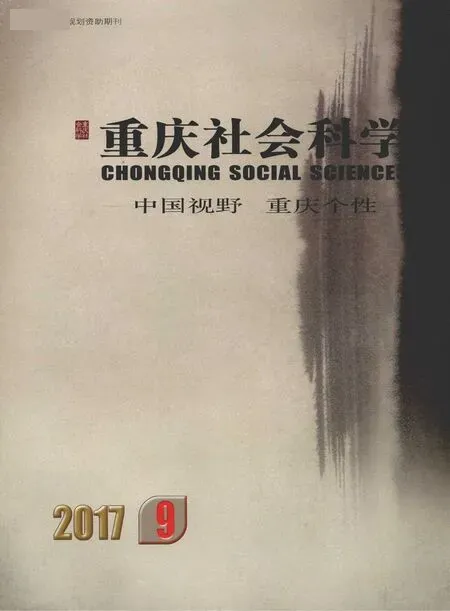法院调解社会化的制度重构*
曾令健
法院调解社会化的制度重构*
曾令健
民众参与司法调解是中国司法的关键问题。至于法院调解社会化的形式,道路选择仍是根本问题。制度重构的分析重心及切入点应是那些影响或支配制度构造、发展面向的思路与框架。在法院调解回归解纷机制属性之后,可将委托调解作为制度重构的主线,并坚持规范化、组织化发展面向。依循渐进式改革观,可选择从公权合作型委托调解迈向国家—社会互动型委托调解的制度重构“三阶段”说。
法院调解 社会化 制度重构 渐进性 “三阶段”说
民众如何更好地参与司法调解是中国司法的一个关键问题。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在司法调解……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以“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法院调解社会化是民众参与司法调解的核心路径。历部 《民事诉讼法》(1982年、1991年、2012年修正)均规定法院邀请调解,2004年《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不仅细化邀请调解,还“创设”委托调解,尔后一系列司法解释均不同程度涉及法院调解社会化之制度安排。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再度强调整合力量、助推法院调解、促进纠纷解决的纠纷解决观念与制度建设思想。
2016年司法解释旨在引导、规范委托调解(即“特邀调解”),但目前尚不能据此断言委托调解为法院调解社会化惟一形式。一是迄今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表达此种观点。二是司法解释也没否定邀请调解。相反,第17条给邀请调解保留了空间:“特邀调解员为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可以邀请对达成调解协议有帮助的人员参与调解。”三是司法解释不是法律,而民诉法对社会化形式的表述较为粗疏,具有倡导性、促进性立法之意味。
就法院调解社会化形式而言,道路选择仍是一个根本问题。这里拟从制度重构的立场入手,反思作为原则的法院调解,倡导以委托调解为主线的发展定位及规范化、组织化的发展面向,并基于渐进改革理念提出制度重构 “三阶段”设想。
一、制度重构:态度与立场
首先,制度设计尤其对程序事宜作制度安排,大抵“仁智相见”。如调解期限设为10天,抑或20天,还是30天,不同期限设置间并无本质区别,或均可以充足理由证成该种设置之必要及可行。关键问题是,相关理论证成与逻辑自洽分析常常无法被证伪。凡不能被证伪的命题皆需小心对待。此意义上,这些具体以至琐碎的制度安排通常重要却未必关乎宏旨。
其次,对于具体制度尤其邀请调解与委托调解之不足、缺陷,既有成果已有不同程度的涉及①依照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委托调解达成的协议的司法确认,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办理。此处将受理作为诉讼系属的起算点,立案之前包括审查起诉阶段的委托调解则被等同于人民调解。围绕该种委托调解之协议确认还有一系文章,如王亚新:《诉调对接和对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法律适用》2010年第6期;潘剑锋:《论司法确认》,《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范愉:《诉讼与非诉讼程序衔接的若干问题——以〈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切入点》,《法律适用》2011年第9期;向国慧:《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完善与发展——结合〈民事诉讼法〉修改的思考》,《法律适用》2011年第5期。2016年特邀调解的司法解释又尝试“委派”与“委托”的二元划分来寻求解决办法。,[1][2][3][4][5]对此不予赘述,尽管这些是制度重构的智识参考。
第三,制度建构在某种程度上是研究的较高层次。一方面,笔者主张坚持“问题出发型研究策略”,强调“问题中心”、关注“中国问题”、注重“理论关怀”,以法律实践为切入点,从而提炼、验证、回应、修正法学理论,从繁复、琐碎、庞杂的法律实践中抽勒出具有学术生命力与理论张力的问题,遂分析之。这可避免学术研究与立法工作的混淆。学术之核心要义在于实现知识增量、追求理论贡献,所谓的“一切为了思想”,应尽可能避免出现法学研究之 “环大会堂现象”。[6]学者之使命在于提出有批判力、洞察力的命题,如果可能则建构具有思想深度的理论体系,而非“立法草案”的执笔者。另一方面,从立法论视角研究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并应在理论探讨之深度及广度达至相当程度后方宜进行。这是理论成果的现实转换。当学术界尚未对法院调解社会化完成有针对性、深入的研究之前,任何期图提供一整套通盘制度设计的想法,往往是学者的某种学术激情。充分、透彻的理论证成以及“理论—实践”之反复应照、修正及耦合,是制度设计及其研究的前提性工作。②此方面的经典性、深入人心的例证无疑是200年前围绕德国民法典编纂展开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学术论战。其中,萨维尼旗帜鲜明地主张,法乃“民族精神”之体现,非立法者可任意创造,也非纯粹的理性产物,法典编纂依赖诸多主、客观条件。其中,法学研究与法典编纂也有重要关联。详见:(德)弗里德尼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场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
最后,研究重心与分析的切入点应当置于那些可能影响或支配制度构造、发展面向的基本思路与主体框架。在理论层面,这类研究可保持论述的学理性,不会陷入一般、琐碎的制度细节;在实践层面,这类研究可能影响、决定制度命运,并不同程度地影响具体制度设计。支撑某项制度、引领制度重构的思路与原则,以及依循这些思路、原则而建构的基本框架最能发挥“提纲擎领、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功效。
二、一项原则的反思:作为解纷方式的法院调解
在相当长时期内,法院调解被视为一项民事诉讼基本原则,这也是诉讼法学界主流看法。实践中更是以司法实务基本原则对待,但制度实践的后果是“调解审判化”与“审判调解化”之共生。反思调解原则关乎法院调解社会化之正当性及制度重构。由于调解与审判的本质区别,所以二者共存于同一审判结构往往影响司法活动的依法、依程序开展。如果将调解视作基本原则,则可以适用于诉讼任何阶段。因为基本原则的含义在于其对民事诉讼之立法及司法的全过程具有指导意义,且贯穿诉讼始终,并对诉讼产生根本影响。众所周知,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有其独特发展历程,是不同时期相对复杂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文化综合作用的产物。尽管立法视其为基本原则,但显而易见的是,法院调解更多是一种纠纷解决机制或案件处理方式,不具备指导诉讼的功能。制度缘起及其发展也表明,法院调解与仲裁、私力救济等一样,只是纠纷解决机制而已。即使不说法院调解与审判截然不同、“水火不容”,但二者确是两套解纷机制。
法院调解回归纠纷解决机制有利于法院调解社会化的制度重构。其一,在逻辑上,重构或修正诉讼原则将涉及整个诉讼机制,工作之巨可想而知。事实上,法院调解不对整个诉讼活动产生指导作用,也不是立法的基本出发点。此意义上,法院调解社会化的制度重构不牵涉基本原则,也不影响整个诉讼架构及程式。这个制度重构仅是“局部战斗”。其二,视法院调解为一种与审判、仲裁、和解、私力救济等并列的解纷机制,使得建构一套体现公力救济与社会型救济相衔接、互动的解纷机制名正言顺。否则,一个诉讼基本原则何以与作为解纷方式的审判衔接、互动。凡说衔接与互动,各者在逻辑上应具有同质性、相似性。狭义的司法权为一种判断权,这主要针对裁判者的功能而言,与调解者促进合意的功能定位相距甚殊。将两种在纠纷应对时拥有不同处理思路的解纷方式组合起来,这无疑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系统论在法院调解制度改革中的运用,而法院调解社会化正是此种努力。当然,从世界范围来看,也不应截然绝裂调解与审判,忌将二者全然对立,毕竟司法权内涵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即使极不明显。在奉行法治主义传统的国度,调解(包括和解)也越来越为司法程序、法官所认同、接受,并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既有司法理念及模式。①美国学者Marc Galanter对美国民事审判所作的法律社会学考察表明,美国的诉讼案件数以及审判结案的案件数在相当长时期呈下降之势,且调解、和解等纠纷解决方式业已为司法所接受,并重塑着美国司法的格局。 详见:Marc Galanter, “A Settlement Judge,not a Trail Judge:Judicial Medi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Vol.12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1~18(1985);Marc Galanter,“The Emergence of the Judge as a Mediator in Civil Cases”,Vol.69 Judicature 257~62(1986);Marc Galanter,“The Vanishing Trial:An Examination of Trials and Related Matters in Federal and State Courts”,Vol.1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459~570(2004)。
三、法院调解社会化的定位:以委托调解为主线
调解具有一副反程序的外观,而法院调解社会化之实践更是将其演绎到极致。但法院调解及其社会化的形式外观不应成为制度实践中随意、拖沓、冒进等行为之借口。作为一种解纷方式,法院调解社会化应具有明确、恰当的定位。依“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可将委托调解分情况界定:首先,在参与的非司法力量不具有足够充分、显著的社会属性时,这种制度安排属于国家权力的统一行使及其引发的分工、配合;其次,当社会属性较明显的调解组织参与司法调解时,国家与社会之二元互动论可能成立,但这种情景下的委托调解亦未能构成一个具有独立品格与特有属性的解纷领域。总言之,当下委托调解实践实为一种斑驳、交杂的纠纷解决多元主义的体现,透露着不尽相同的制度意涵。这是基于当下集中型权力体制展开的分析。无论社会转型的进程及结果如何,委托调解中透露出的注重社会力量与法院力量的交接、互动、协作,以及适当加大社会力量的调解权重,都是些富有价值的启发。故而,将法院调解社会化界定为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共存的纠纷解决方式,具有广袤的制度发展空间与旺盛的理论生命力。
对法院调解社会化的结构定位,不仅利于指引制度重构的方向,且有助于扭转当下司务中的问题。法院调解社会化之所以如火如荼,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关制度及实践契合 “司法能动”、“大调解”诸潮流。在这些浪潮中,司法突破被动、消极等传统特征,于是乎“作为法庭的街道”成为了当下司法的一道景观:法院常常超越司法被动与消极性原则,针对纠纷、主动出去、尽快入手、及早解决,以达到纠纷解决之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①该项研究表明,对于劳动争议类纠纷,如果劳动者通过集会、游行表达诉求,法院、政府等会主动与之接洽并寻求解决之道,而党政方面也常常会指示政府部门主持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调解;前述情形不仅与现行纠纷解决程序规定大相径庭(在一起个案中,聚众上街的劳动者们甚至可以不经过劳动争议仲裁程序,而由法院工作人员在集会现场为其办理诉讼案件的受理手续,从而绕开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以便“便捷地”、“高效地”维护其权益;或重复查封、冻结企业之设备、账户,通过给“企业施加更多的压力”,从而使劳动者在调解中处于有利地位),且此类集体维权行动的效果往往较劳动者各自依程序寻求权利救济要方便、快捷、有效得多。关键之问题在于,法院会主动迎合这些纠纷。详见:Yang Su,Xin He, “Streetas Courtroom:State Accommodation of Labor Protest in South China”,Vol.44 Law and Society Review 157~84(2010).法院调解社会化正好“大展身手”,许多案例可以佐证。当这些做法遭遇 “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就彻底解决”的社会心理,从长远而言,不仅无助于纠纷解决,还将与法秩序发生冲突。笔者认为,即便在“能动司法”、“大调解”的潮流中,法院既不能发挥主导作用,更不宜充当“排头兵”。②有研究对法院在“大调解”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本土实践进行过反思,也认为法院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很难真正地扮演起“大调解”中的主导角色。详见:王禄生:《地位与策略:“大调解”中的人民法院》,《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6期。同理,法院调解社会化应是一种相对温和、持久的制度实践,应定位为常规性解纷机制,而非应急性解纷手段。此外,明确法院调解社会化的结构定位可避免“程序倒流”。该现象一定程度上透露出制度的命运:在集中型权力体制之下,制度极可能被选择性适用,且常常可能“变脸”,以满足即时性需要。在此意义上讲,对法院调解社会化的结构性定位不是限制其功能发挥,而是对制度良性运作的一种保护。
四、制度发展面向:规范化、组织化
长远而言,法院调解社会化应当坚持规范化、组织化的道路,但不一定需要遵循专业化的发展方向。规范化几乎是所有制度建构、改革的一个方向,法院调解社会化的规范化重在强调对法院调解社会化的具体制度予以明确、细化。所谓法院调解社会化之组织化,即通过设置机构、厘定规程,使法院调解社会化更加具体、明确、易操作。从广义上讲,组织化可以划归规范化的范畴。组织化视角对于法院调解社会化的制度重构具有重要意义。从既有实践来看,委托调解的组织化程度最高,仍需加强规范化建设;邀请调解与人民陪审员参与法院调解的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几乎依附于法官以及常规的司法活动,其社会化属性相对较弱。这种比较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规范化、组织化重构法院调解社会化时可能不得不直面的抉择。
另外,作为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场域,法院调解社会化的性质就决定着,专业化或者说职业化不是主要发展面向。从理论上讲,如果受托组织实施市场化运作,也可能引发专业化、职业化的法院调解社会化形式。这将面临两个问题:其一,只有在市场化极度发达的社会,这种理念才有付诸实践之可能;其二,市场化运行中的“利益追逐”与纠纷解决中的“公正执法”可能会发生冲突。君不见,许多公用企业在市场化运行之后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问题,何况是作为社会秩序维系手段的纠纷解决权?当然,有一种限制“恣意”、“不公”的力量来自于当事人对调解的决定权。姑且搁置专业化、职业化不表,法院调解社会化不仅不排斤专业技术人员的参与,且作为重要的纠纷解决资源,专业技术力量应当被规范化、组织化地吸引至法院调解社会化之中。
五、制度重构的渐进性思路
制度重构应当坚持渐进式改革,一步步展开、勿急勿躁,以减少剧烈的制度变革可能诱发的社会“阵痛”。但凡具有成文法传统的制度体系,往往具有强烈的变革色彩。①一些杰出的比较法成果可以充分地说明此问题。相当意义上讲,1804年《法国民法典》是“法国大革命精神的一个产物,这场革命旨在消灭往昔的封建制度,并在其废墟上培植财产、契约自由、家庭以及家庭财产继承方面的自然法价。1789年后的年代里所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事件对于该法典的形成极为重要。”[(德)K·茨威格特 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米健、高鸿钧、贺卫方译,潘汉典校订,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4页]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总被视作脱离罗马日尔曼法系所构成的另外一个法系,“在苏联……自1917年革命以来,一种独具一格的法发展了起来”。法典制订也具有政权更迭的表征功能。“自从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以来完成了大量的法典制订工作,特别是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南斯拉夫这样一些以前不曾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法的统一的国家。”[(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28、228~229页]维阿克曾言:“法典编纂的目的,是通过体系性的和包罗万象的新秩序对社会进行总括性设计。”[Franz Wieacher,Privat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1.Aufl.,1952,S.197(2.Aufl.,1967,S.323)。 转引自(日)大木雅夫:《比较法》,范愉译,朱景文校,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 154 页(注 5)]成文法传统正是中国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便如此,仍有渐进式改革的空间。事实上,这种渐进式变革的法制变迁对于中国而言并不陌生,甚至可从当下制度变迁中找寻例证。比如我国民诉法规定的社会化形式是邀请调解,但司法解释对其阐释时,一种将法院调解案件托付与非司法力量的做法也悄然成形,并在“横空出世”后“迅速窜红”,且少了邀请调解在条文中长达数十年的“沉默”、“潜伏”、“蛰伏”。当然,委托调解还是一宗尚未事功的制度改革,但其借助司法实践土壤得以“生根发芽”并“笜壮成长”。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司法实践是制度变革包括法院调解社会化制度重构的滋生地,②中国司法改革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往往改革的思想(或者说思想渊源)来自高层,而具体的制度探索与实践则源于地方的能动与突破。这方面例证可谓不胜枚举,如20世纪后期的“一步到庭”之庭审制度改革,如21世纪初期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如是等等。这也为制度重构的渐进式改革提供了可能。
在渐进式变革中,成文法传统本身也能为这种温和、有序的改革创新提供制度性的“庇护空间”。如自上而下地推进法院调解社会化改革,应有序、克制、温和、渐进、分步骤地重构,如“通过试点推进重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代中国法院调解社会化必须正视社会力量的解纷能力有限,“多快好省”的思路极可能酿成“欲速则不达”的苦果。渐进式变革方可避免社会力量之“力有不逮”。最为重要的是,无论如何论证司法权与调解权,在既有司法框架下推行规范化、组织化的法院调解社会化,最终都将触及将纠纷调解权分割、让渡给社会调解组织的敏感一刻。对于尚需在权力架构中努力争取话语权的法院系统而言,这无疑需要顽强的毅力与极大的勇气。故而,渐进式制度重构之路就益发紧要。
六、制度重筑的“三阶段”构想
对制度重构的立场和观点做一个概括式描述:在渐进式制度重构过程中,贯彻规范化、组织化的制度发展面向,并将法院调解社会化定位为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交接、互动的作用场。为实现该企画,大抵可将制度重构的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依次推进。
第一个阶段,慎用法院邀请调解并逐步减少其适用比重,同时将委托调解作为法院调解社会化的一种主要形式。虽从公开报道看,邀请调解的适用频率高、成功率高,但田野调查表明,该制度既缺乏运行动力,也容易偏离司法运行规律,还与规范化、组织化的制度发展方向相悖。相比而言,委托调解应作为制度重构的主要方向,故第一个阶段应调适二者的比重,为进一步重构打好基础。虽然现行立法并未对委托调解予以正名,但不损及制度重构的可行性。一个便利的例证是,法院委托调解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是重要、正式的诉讼与非诉讼之衔接制度,或有近似的制度安排。如中国台湾地区的“法院移付调解”,即法院或法官将进入诉讼系属的案件委托给乡镇市调解委员会。[7]该种制度例可为制度重构提供信心。
第二个阶段,除家事纠纷等特定案件之外,①特定案件的范围依凭两种方式予以限定:其一,列举特定案件类型,如家事纠纷、邻里纠纷、房屋租赁纠纷、劳务纠纷、劳动合同纠纷及其他案情简单且法律关系明确的案件(如在交通肇事案件中,由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事实认定和责任划分有极大帮助,同时又由行政诉讼处理事故责任认定分歧,故便于开展和解工作);其二,将纠纷与普通民众生活存在相当程度的关联性作概括标准,在具体处理则由法官裁定。通过列举与确立标准相结合的方式,对诉讼和解之案件范围予以必要限定。可将调解从诉讼中予以剥离且以诉讼上之和解替代现行法院调解制度,同时加大法院委托调解的建设及适用力度。如条件成熟,则以诉讼上之和解彻底取代法院调解。至此,法院邀请调解以及人民陪审员参与法院调解这两种情形从制度层面而言几乎不存在,而法院委托调解虽然名义上可称为法院调解,其实后者业已为诉讼上之和解取代之后,故而,此时的法院委托调解实际上已经无形中转变身份,成为一种典型的法院附设调解,成为坚持法治中心主义的诉讼活动之补充性机制。该阶段是改革中最为艰巨的一环,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环。这样一种法治中心主义的诉讼活动与委托调解的交相辉映在世界范围内有其成功范例,纵然个中经由的路径不同。通常认为,1976年庞德会议(Pound Conference)上有学者提出“多门法院”(Multi-Door Courthouse)观念,将小案子从法院移至社区法律中心。[8]1980年代末,Marc Galanter指出,美国民事诉讼的惟法治中心主义观被“捅破”,和解被接纳。[9]1998年《ADR法》鼓励每个地区法院设置ADR项目。不限于美国,调解以及附设性调解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纠纷解决方式中最具活力与魅力的制度。②调解在一些国家的实践及发展趋势,可参阅(澳)娜嘉·亚历山大主编:《全球调解趋势》,王福华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
第三个阶段,从公权合作型委托调解迈向国家—社会互动型委托调解。当下法院委托调解更多属于行政力量与司法力量的结合、协作。这于发挥社会力量之解纷潜能并无多少助益。当然,这与当下社会自身能量有限存在莫大关系。毕竟相当长时期内“传统的社会自生功能几乎被完全铲除了。于是,使社会自组织程度骤然下降到一个空间的低点,所以我们对于‘自生社会’的良性机能只能越来越陌生”。[10]故而,在社会转型期,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在培育、吸纳、开发纠纷解决的社会资源方面仍大有可为。通过政府力量的推动,完全有可能打造出真正具有民间属性的社会纠纷解决组织。③应该说,缘于社会转型出自总体性社会之故,当下诸多所谓的民间性解纷机制都存在属性不明确尤其民间性成色不足的问题,如仲裁、人民调解等。可参阅汪祖兴:《仲裁机构民间化的境遇及改革要略》,《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汪祖兴:《中国仲裁制度的境遇及改革要略》,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38~143页;范愉:《〈人民调解法〉:让人民调解回归民间》,《中国法律》2010年第6期。不仅培育社会力量对于委托调解意义重大,且社会力量的增强对社会自身应对纠纷解决也有重要意义,惟如此,司法才可能成为终局性解纷机制。笔者认为,高度发达的司法体系并不意味受理案件数或处理案件数多,甚至不一定是司法效率最高的法院,也不大可能是人案“剪刀差”的法院。司法系统之发达甚至不完全在于司法系统本身,而在于社会自身的纠纷解决能力。如果社会型救济体系足够发达,则有限的司法负载便可引领社会规范的运作,实现社会正义的生成。
这种社会型救济与司法救济之互助、共济局面在美国有所体现。研究显示,联邦法院受理案件数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降幅达60%;民事结案率下降,1962年11.5%,2002年1.8%;州法院类似。[11]这很大程度上利益于法院附设ADR(包括法院附设调解)的开展。当大量纠纷通过社会型救济甚至私力救济予以解决,①关于现代美国社会中的私力救济,可参阅(美)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美)唐纳德·布莱克:《正义的纯粹社会学》,徐昕、田璐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美)唐纳德·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美)唐纳德·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法院可抽出足够的人、财、物来“作好”判决,从而树立行为规范、引导社会风气、维系社会秩序。②除费斯教授之外,还有很多学者纠纷对被体制化、大规模地予以非讼化处理表示担忧。如Hazel G.Genn,Judging Civil Jus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Elizabeth G.Thornburg, “Saving Civil Justice”,Vol.85 Tulane Law Review 247 (2010);Edward J.Bergman,John G.Bickerman,eds.,Court-Annexed Mediation:Critical Perpectives on Selected State and Federal Programs, (Silver Spring:Pike&Fischer,1998)。司法ADR对提升司法体系的形象、助长司法体系的权威可谓功不可没。因此,培育、吸纳、开发纠纷解决的社会资源,实现从公权合作型委托调解迈向国家—社会互动型委托调解,是法院调解社会化制度重构中最重要的环节。
[1]李浩:《法院协助调解机制研究》,《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第62~70页
[2]李浩:《委托调解若干问题研究——对四个基层人民法院委托调解的初步考察》,《法商研究》2008年第1期,第133~140页
[3]李浩:《调解的比较优势与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第19~27页
[4]肖建国:《司法ADR建构中的委托调解制度研究——以中国法院的当代实践为中心》,《法学评论》2009年第3期,第135~144页
[5]范愉:《诉前调解与法院的社会责任——从司法社会化到司法能动主义》,《法律适用》2007年第11期,第2~7页
[6]陈瑞华:《论法学研究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13~116、177~179 页
[7]范愉:《诉讼与非诉讼程序衔接的若干问题——以〈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切入点》,《法律适用》2011年9期,第30~34页
[8](美)詹姆斯·E.麦圭尔 陈子豪 吴瑞卿:《和为贵:美国调解与替代诉讼纠纷解决方案》,法律出版社,2011 年,第 11~12 页
[9]Marc Galanter,“The Emergence of the Judge as a Mediator in Civil Cases”,Vol.69 Judicature 257~62(1986)
[10]王毅:《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困难、可能与路径选择》,载资中筠:《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94页
[11]Marc Galanter, “The Vanishing Trial:An Examination of Trials and Related Matters in Federal and State Courts”,Vol.1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459~570(2004)
I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 towards Socialization of Judicial Mediation
Zeng Lingjian
It’s vital for the masses to participate in judicial mediation,as to chinese judicature,and the path of judicial mediation is also a fundamental issue.Frankly,the essential respects and the breakthrough points of i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 should be ideals and frames which are dominating the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Recognizing judicial mediation as one of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s,we should fouce on court-entrusted mediation,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standardiza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it.Following the reformism of progressivity,the hypothesis named Three-Stage Development Strategy can be employed to make the court-entrusted mediation tranfromed from Public Powers’Cooperation to State-Society Interaction.
judicial mediation,socialization,institutional reconstruction,progressivity,Three-Stage development Strategy
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仲裁学院 重庆 401120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合作主义视野中城镇基层纠纷解决实证研究”(批准号:13XFX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