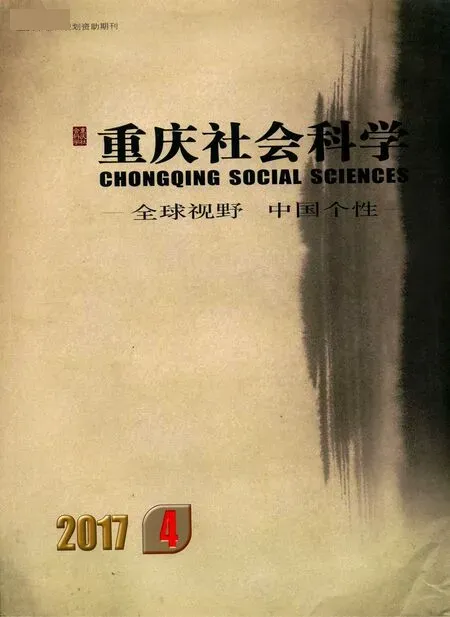新能人治村的操作机理与地域特征*
李 宽
新能人治村的操作机理与地域特征*
李 宽
苏南地区的村庄治理模式可以用新能人治村来概括。与原来的治理模式相比,当前的能人治村呈现出三个新特点:在产生的方式上,采取乡镇政府选拔和村民选举相结合,更加注重组织的培养;在行为目标上,追求集体利益的最大化,更加注重公共需求;在能力要求上,由经营型向管理型转变,更加强调守业能力。这些新特征的出现,与当地实行以招商引资为主的发展方式、以村级为核心的集体经济、土地管理的规范化和松散的社会结构有关,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征。
社会治理创新 社区建设 “三农”问题
对我国农村治理主体的探讨经历了由士绅向地方精英的拓展,形成了基层治理研究的“士绅”模式和“地方精英”模式。士绅模式认为基层的治理主要由依靠科举制度出身的官员、士大夫及其家族来完成,在家国同构的框架下,由他们保持着信息的沟通,主导着地方秩序。随着科举制度的衰落和对日常生活研究的深入,士绅模式逐渐被地方精英模式所取代。地方精英的涉及面更加广泛,只要是在某方面比较出众、有一定的号召力就可被认为是精英。在基层治理中,大致可分为依靠体制性资源的政治精英、在市场中取得成功的经济精英和在村庄生活中具有影响力的民间权威(李猛,1995)。在当前的形势下,经济精英在村庄的治理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一些人将经济精英主导的村庄治理称为“能人治村”。这些村庄主要分布在沿海发达地区,那些在经济领域获得成功的个人逐渐步入村庄政治领域,承担起了治理责任。这批人走向村庄治理的核心与“双强双带”政策有关,也契合了普通群众发家致富的期盼。[1]
对于能人治村的效果,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对能人治村给予积极评价,肯定他们所作出的贡献。能人在村庄中发挥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将个人的经验、关系和资金等资源奉献出来,对村庄进行经营,促进集体经济的发展;二是在村庄中实行民主基础上的权威政治,实现精英主导与群众参与的有效结合;三是改善村庄社会面貌,恢复村庄的秩序和活力。这种认识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概括了能人对村庄带来的有益影响。[2][3][4][5]从表面上看,在能人的带领下,村庄确实发生了许多可喜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升。另一种是从村庄内部结构的视角指出能人治村的消极影响。在经济方面,认为这些经济能人确实将自己的资源用于村庄,让村庄的经济获得了发展,但是自己从中获取得更多,有侵吞集体资产的嫌疑;在政治参与方面,则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使普通村民被边缘化,导致村民参与村庄政治的积极性降低;三是在社会层面,主导了人际交往规则变迁,让村庄的人情出现异化。[6][7][8][9]10]他们更加喜欢将这些经济精英称为 “富人”,而不是“能人”。
上述认识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对能人治村的理解,也从侧面表达了对村庄治理的期待,希望经济精英们既有很强的个人能力,又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学者们对于这些能人在市场中所获得的能力并不怀疑,比较担心的是他们如何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上述研究调查的区域集中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浙东地区,如果将此问题放在其他地区进行考察,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同时,相关的分析也只是集中在村庄的层面,而对乡镇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较少。若是拓展对此问题的研究,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一、“新能人治村”的特征
苏南地区的新能人治村有着比较显著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干部的产生方式、行为目标和能力要求方面,与原来的能人有较大的不同。
(一)村干部由选拔与选举相结合产生
在苏南地区,村干部在选拔与选举相结合的方式下产生,不同于其他地区仅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选举是从村庄民主的角度来理解,表达了村民的意愿,考察了干部们的群众基础。选拔则体现了乡镇政府的意志,显示上级对村干部的认可程度。乡镇政府的选拔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稳健的晋升制度,内含着对村干部不断进行培养的意味。在成为村里的主要负责人之前,村干部要经过组织长期的考察、培养和多个岗位的历练,获得一致的认可之后,才能走上比较重要的工作岗位。比如,许多村的支部书记都是从生产队长开始做起,历任民兵连长、会计、村委会副主任、主任,最后才成为真正的“当家人”。当前,村民小组逐渐弱化,村民小组长只是负责具体的联络工作。村委会工作人员的选拔主要来自企业、联防队和个体户。有能力和意愿到村委会工作只是前提条件,至于能否到村委会工作还要看相应的考试和考察情况,而不是村民的选举。即便能够到到村委会工作,也不是直接被选举为村委会委员,而是要从一般的办事员开始做起,在身份上是临时性聘用人员或社区工作者。只有工作比较出色,积累了相应的工作经验,达到了相应的要求,才有可能被提名为村委会委员候选人。
从上述村干部产生的过程可以看出,乡镇政府在其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村民的选举只是作为民意参考。即便某个人具有很强的能力和较好的民意基础,也不大可能仅通过选举的方式就当选为村干部,乡镇政府或选举委员会的提名才是所要过的第一道关。这也并不意味着乡镇政府通过行政消解了自治,提名的干部一定能够当选,而是将村干部的产生作为一个培养的过程。村干部的能力不只是依靠自己在市场经济中获得,更多的是依靠组织的培养。经过长期的考察和培养之后,才可能成为村干部。如果某人的能力、民意基础太差,乡镇政府也不会让其担任重要的职务。
(二)以集体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目标
苏南地区村干部以集体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目标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让集体经济获得发展。让集体经济获得发展,主要来自于乡镇政府的要求。只有当集体经济发展之后,乡镇的财力才会得到保障,各项工作才容易开展。因此,能否发展集体经济成为上级对其考核的重要指标,并且这个指标很容易量化。没有集体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他们的晋升,在这个评价体系中也就没有太多的地位。集体经济的发展与个人的进步紧密相关。
二是维护村庄的合理秩序。秩序对村庄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公共品”。形成合理的公共秩序,就要求村干部们行事公允,获得大多数村民的认可。如果村干部们不能做到这些,就可能让村民们产生反感,在村庄选举和日常治理中就会表现出来。尽管在干部的产生中组织的意图占了较大的比重,但是村民的认可也同样重要。在选举过程中,村民即便是不投反对票,也可以弃权的方式表达无声的抗议。村民对秩序不合理的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日常治理中的不配合,让村干部的工作无法开展。在取消农业税费之后,村干部与村民的互动很大部分落在了惠民政策的落实上。当前,这些政策不只是简单地发钱、发物,还涉及众多公共工程的修建。当村民不认可村干部的行为时,就会认为这些工程不是为自己带来便利,而是损害自己的利益。这样一来,就使得村庄的整体利益受损,影响了村庄的治理。为了落实各项工作、获得村民的认可,村干部们必须维护村庄的合理秩序。
三是对村民的生活进行托底保障。课题组在苏南地区调查时,有两个比较明显的感受:一是村庄的上访户比较少;二是村庄贫困人口得到了比较多的照顾。在村庄中上访户比较少,一方面说明边缘人群比较少,大部分人还参与着村庄的政治、社会生活,没有被“甩出去”。另一方面,则说明村庄的照顾比较周到,没有让村民产生太多的不满。如果村干部的行为明显超越了某些界限,让村民们产生意见,那么就会冒出上访户来,利用各种机会来反对村干部,干扰村干部的正常工作。村庄除了对残疾人和符合条件的癌症患者两类人群进行照顾外,还会评选出若干个低保边缘户,即家庭比较困难或患重大疾病,但不能列入低保户的家庭进行帮扶。尽管帮扶的金额不是很大,但尽量地将符合条件的村民纳入进去,至少可以让村民获得心理上的安慰。在村庄中没有边缘人的出现或者说极少,也是集体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这说明,将公共资源用在托底保障,在发挥个人积极性的前提下,尚保留着平均分配的传统,而不是唯个人能力论。
(三)由经营型向管理型转变
经营型能人多产生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经营好集体资源,让集体经济获得更快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产生了大量的“老板书记”。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村支书将村庄当成企业来经营,自己扮演着“老板”的角色。将村庄的发展当成事业来做,虽然自己的获利不多,但是村庄得到了发展,自己收获了荣誉和成就感。二是让“老板”来当村支书。当村干部就要有带领大家致富的能力。也许,有些人的思想非常端正、作风也比较正派,而且还很勤劳,执行上级的政策不折不扣,但缺乏把握市场的能力,这也不适合担任新时期的领路人。三是做了一段时间的村支书之后,掌握了许多的资源,自己去办公司、当“老板”。这三类人的特点比较明显,第一类是自己没有公司,将村庄当成自己的公司,有能力无私心;第二类是先“老板”后村支书,在有了能力之后,经过组织的培养才成为村支书,为村集体作贡献;第三类是组织培养过程中,发生了一定的异化,有了能力之后,没有完全地用在集体上,而是为自己谋取利益。这三种类型的美誉度逐渐降低,村民们对第三类书记的意见较大,其存在会影响乡村治理的秩序。
当前,农村中更加需要管理型的村干部来“守业”,对创业型村干部的要求在降低。管理型村干部所面临的主要工作有三个:一是管理集体资产,实现保值、增值。二是协调处理各种村庄中的矛盾,保持社会的稳定。当前,处于社会矛盾的突发期,社会问题逐渐增多,维稳的任务落到了基层社区之中。相应的工作必须由村干部来完成,将矛盾和问题及时地化解。三是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完成对村民的服务工作。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政府对村民有许多的补贴和服务,需要村干部进行配合,将其传达给村民。同时,还有许多的创建活动,如新农村建设、环境综合整治、房屋拆迁等,需要村干部进行落实。这类工作需要用心去做,不断将任务进行细化,而不需要冒太大的风险,比较平稳。
上述三个特点所产生的基础还是能人治村,只是与既有的模式稍有不同而已。尽管乡镇政府在其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他们还是村庄的一员,尚未进入正式的科层体制,还可以在村民自治的框架下进行讨论。
二、“新能人治村”的基础
苏南地区的村庄治理以新能人治村的形态呈现,与其他地区有较大的不同。这种形态的出现与以政府为主的招商引资发展模式、以村级为核心的集体所有制、土地管理的规范化和比较松散的社会结构有关。
(一)招商引资为主的发展模式
苏南地区的集体经济发展比较早,也拥有着比较深厚的集体主义传统。改革开放后,虽然引进了大量的外资,发展了招商引资经济,但并没有削弱集体的力量,只是改变了发挥作用的形式。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任务和压力在政府,但是土地以生产队或村民小组为基础。这就意味着若要发展经济,必须对土地进行强有力的控制,只有掌握了土地资源,才能获得发展的主导权。我国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在此关系中,土地属于集体,但又不明确为哪个具体的层级。三级所有本身就不排除公社或者乡镇政府对土地利益的支配和占有。从基层政府的角度来讲,有着明确的将土地权力上收的冲动,但又不能完全上收,而让自己陷入无尽的纷扰之中,成为实际的管理者。因此,本地的集体所有制更多体现在村级层级,但乡镇政府会进行有效管理。村民小组层级基本上被虚化了,不再成为一级核算单位。
招商经济在较大程度上需要下级的配合,如果没有相互之间的良好配合,就不能将土地资源效用充分发挥。政府只有发展的任务,但没有发展的资源,因而必须牢牢控制住村干部的任命,如此方能控制资源的分配,比如土地的开发和资金的使用。这就决定了本地更需要以选拔的方式来产生干部,而不是以个人为主的竞选。即便是竞选,个人也没有太多的资源,不可能影响村庄政治。因为发展的不是民营经济,所以,大部分人没有多少资金,这些企业家也没有进入村庄政治的欲望。为了让这些村干部们承担起发展的职责,政府也就肩负着对干部进行遴选和培养的责任。只有让这些干部们从基层做起,在不同的岗位上进行历练,他们才能够知晓各方面的情况,能够掌握住大局,将一个村庄发展、经营好,实现集体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二)以村级为核心的集体所有制
以村级为核心的集体所有制对村干部的行为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不能让自己的财富增长过快,侵吞集体的财产;二是必须将经营所得的收入全部用在集体方面,对村民进行照顾,保障村庄的公平秩序。以村级为核心的集体所有制要求村干部们将集体利益放在首位,而不能过多地追求个人的私利。村干部们过多地追求自己的私利,不在经营和管理方面用力,就达不到上级的要求,不能实现发展的目标,也会遭到村民的指责。
以村级为核心的集体所有制,使得村集体拥有大量的可支配收入,并在村庄内进行分配。集体收入的存在为照顾村民生活、提供相应的保障奠定了经济基础和道义基础。既然收入属于集体,那么就应该让集体成员进行分享,对弱势群体进行照顾。如果弱化集体的所有权,强化村民的承包权和经营权,那么集体就没有收入,或者说收入极少,结果是富了个人、穷了集体。如果说集体的核心是村民小组一级,那么村级的收入就较为有限,支配能力会大大下降,在村庄内部的统筹变得不大可能。若将实际的支配权放在村民小组一级,多数情况会演变为本组内部的共有制,而不是公有制,会将集体收益均分掉,而不是用在发展上或对贫弱群体进行适当的照顾。以村级为核心的集体所有制为村干部们追求集体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基础保障和制约性条件。
(三)土地管理的规范化
经营型能人产生的重要条件是村庄拥有可以让其进行经营的土地资源。在管理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村庄享有较大的自主开发权。交通便利、条件优越的村庄,在头脑灵活的村干部带领下,将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用地,获得较多的增值收益。当时的经营主要是利用集体的土地兴办集体企业,或者建设厂房进行出租,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经营型能人有经济头脑、风险意识和品牌意识,通过在市场中搏击,获得了市场机会。在市场经济的初期需要这种干部的存在,对村庄进行良好的经营。
2005年之后,土地管理逐渐规范和严格起来,发展的主导权逐渐上收到了政府手中,发展的模式转变为以工业区、开发区为载体,而不再是村庄中的企业集中区。同时,在乡镇企业改革之后,村庄不再直接经营企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规模进行了锁定,不再可能进行大面积扩展,依靠土地的扩张进行发展的模式终结。现在,则是进行招商引资,提供土地或者厂房的租赁,发展的最大可能性就是实现既有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这也就使得村干部具有浓厚的职业经理人色彩,主要对以村为主的企业集中区进行管理,为企业提供服务。他们要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对集体资产进行有效的管理,对厂房进行适当的翻修,并选择合理的出租方式,对村干部的经营性能力的要求在降低。能否实现集体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是对当前干部最大的考验。
能人的类型与经济发展的模式紧密相关。原来的集体经济多是实体经济,而现在则是租赁经济,从地产、房产中获得更高的收益。对于经营性活动来说,很难进行监督,在某些时刻需要给予他们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可是,管理性活动则不然,可以对其进行有效监控。因此,也就产生了由经营型向管理型能人的转变,他们都是村庄中的能力出众者,但侧重点有所不同。
(四)较为松散的社会结构
本地的村庄治理中呈现前述特征也与比较松散的村庄社会结构有关。松散的村庄社会结构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血缘关系比较松散,没有形成紧密的“自己人”认同;二是经济关系比较松散,没有形成紧密的利益结合体。由于近代以来的战乱,苏南地区移民较多,没有形成紧密的血缘共同体。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本地发展的是集体经济和招商经济,居民以在工厂中上班者居多,难以与企业经营者结成紧密的关系参与到村庄政治中来。这就使得苏南地区的派性政治色彩比较弱,没有办法形成对立的派系。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村庄政治比较平淡,没有太多的曲折和故事。
村干部不依靠派性政治选举而产生,也就决定了他们与普通村民之间的距离基本相等,私人逻辑运作的空间比较小。[11]他们成为村干部不是依靠某个人的支持,而是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那么,他们工作的目标就是要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而不是为某个人负责。为了大局着想,村干部们会坚持比较一致的原则,获得大家的认可。当坚持了原则之后,干部就有了说服村民的底气,村民也没有反驳的理由。这也就在客观上造成了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能人治村新特征的出现是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之上的,经济发展模式、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土地管理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对村庄的治理结构有重要的影响。
三、结论与讨论
新能人治村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外部条件才会产生。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就是本地集体经济的发展,土地控制在村级。在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自然会产生与乡镇政府的紧密关系。乡镇政府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对村庄进行控制,最为明显和有效的手段就是影响村干部的产生和工作方式。这种控制不只是表现在选拔上,还体现在对村干部的培养方面。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直接选举出来的是已经在市场经济中拥有较强能力的人,而在集体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则要通过不断历练和培养才能成为真正的当家人。当然,村庄的社会结构和土地管理的规范化也会对村干部的行为逻辑产生较大的影响。
新能人治村是苏南地区村庄治理的突出特征,远比其他地区表现得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地区没有能人治村,或者说该地区的能人就不存在问题。在集体经济发展初期,由于监管不到位,出现了村干部侵吞集体财产的事件,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村民的反感。这种现象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客观原因。政府为了发展经济,鼓励村干部们租赁土地或厂房带头致富,并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来落实。在土地的租赁效益尚未显现出来之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当情况发生变化后,就成为了村庄分化的基础,村干部成为比较富裕的阶层。随着能人由经营型向管理型的转变和相关制度的完善,新上任的干部基本上不存在相关的问题,村庄治理也逐渐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从全国的范围来看,乡村治理逐渐走向规范化,科层制的色彩逐渐增强,只是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在苏南地区,行政化是通过将村庄的精英吸纳进入体制实现的;在浙北地区则是将政府的工作人员派驻到农村去,实现联村干部的常态化,对村干部进行经常性的督促和指导。随着土地“三权分置”的实施,集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强,乡镇政府也在利用这个契机,重振农村的集体经济。当然,相应的管理制度也会更加严格,对村干部的能力和素质亦提出了新的要求。
[1]刘炳香 韩宏亮:《能人治村: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选择》,《理论学刊》2007年第8期,第33页
[2]卢福营:《经济能人治村: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学术月刊》2011年第10期,第23页
[3]卢福营:《论经济能人主导的村庄经营性管理》,《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78页
[4]王金红:《村民自治与广东农村治理模式的发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53页
[5]施从美:《江苏“富人治村”现象观察》,《唯实》2013年第6期,第45页
[6]贺雪峰:《论富人治村》,《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2期,第111页
[7]欧阳静:《富人治村与乡镇治理逻辑》,《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44页
[8]余彪:《公私不分:富人治村的实践逻辑》,《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第17页
[9]魏程琳 徐嘉鸿:《富人治村:探索中国基层政治的变迁逻辑》,《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8页
[10]郑风田:《富人治村的“美”与“险”》,《人民论坛》2010年第2期,第4页
[11]赵晓峰:《公私定律:村庄视阈中的国家政权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Governing Villages by the New Generation of Able Men
Li Kuan
The village governance model can be summarized by the new able people government in Sunan aera.Compared with the original governance model,there are three new features:in the way,it takes the township government selection and villagers election combination,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organizational training;in the behavioral goals,they pursuit the maximization collective interests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public demand;in the capacity requirements,it transforms the management to the administration and more emphasis on business ability.The emergence of these new features,with the local implementation of investment-based development approach to the village as the core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land management standardization and loose social structure,with distinct geographical and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innov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community-building,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countryside and farmers”
上海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 上海 200233
*该标题为《重庆社会科学》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新能人治村:苏南地区的村庄治理》。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研究——聚焦人口流入型地区”(批准号:15ZDC028)。感谢谭林丽、陈锋、刘向东、王子愿、卢青青、江亚洲、朱爱和孙自然等在调查过程中给予的指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