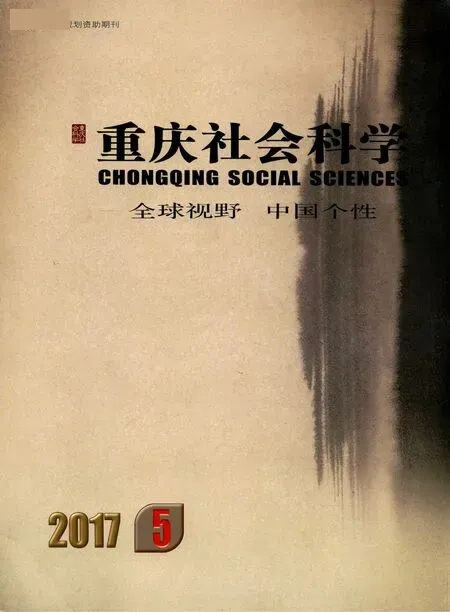供给侧改革理论回溯与展望
胡洪彬
供给侧改革理论回溯与展望
胡洪彬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是完善供需结构、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在要求,对推进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强化社会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具有重要价值。供给侧改革提出以来,国内学界对其展开了持续性探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相关研究在理论体系建构、微观实证调查、横向比较分析和学科交叉参与等方面有待完善。今后,学界要进一步强化和明确对供给侧改革理论研究的“深度”、实证调查的“力度”、多学科参与的“协同度”及同域外相关理论和经验的“关联度”。
政府作为 供给侧改革理论 全面深化改革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应对经济新常态的过程中,强调要通过“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达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标。在此基础上,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命题,要求“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此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进一步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案进行了研究,为强化和提升我国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指明了方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提出以来,学界给予了高度关注,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研究迅速成为学界热点。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界定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对其内涵作出科学界定和把握。综合学界近期的理论分析,其观点可大致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一元核心论”。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主要从“供给侧”的主体视角出发对其概念作出界定,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领域的宏观管理存在明显区别,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界定必须把握其内在核心。如王小广认为,新常态下我国结构性问题主要集中在供给领域,这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将重点聚焦在供给体制这一核心层面上,同时也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是宏观调控的全面改革,而是关键领域的重点突破。他认为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宏观管理体制变革是对这一概念的曲解和误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抓住深化供给体制改革的关键与核心,通过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达到释放改革红利和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目标。[1]
二是“三元化解论”。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主要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视角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作出界定,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直指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难题,其根本目标在于发展生产力。如黄群慧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鲜明的问题指向,即通过改革进行结构性调整,以增强供给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因此,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必须遵循“问题—原因—对策”的“三段论”线性化解逻辑。他认为,我国经济问题主要是高端与有效供给不足,而其根源在于供给结构难以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相应的对策只能是通过体制改革进行结构调整,以达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针对全要素生产率低下问题,在把握供给和需求结构不相适应根源的基础上,对其作出结构性调整的体制和机制性改革。[2]
三是“四元要素论”。持这类观点的学者立足于供给侧内在要素的微观视角对其概念进行界定,认为要科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要前提是对供给侧的结构性要素作出解析,这是使供给适应需求的必要前提。如李翀把影响经济发展的供给侧因素,具体概括为经济结构调整、人力资源供给、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四大方面。他认为,这四大要素对化解我国经济难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对这四大要素进行细化改革,以实现资源配置过程的科学化,为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通过对其要素的整合,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变投资驱动为效率驱动,以达到创造新增长动力的目标。[3]
四是“五元任务论”。持这类观点的学者主要从国家战略决策的视角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出解析,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分析当下经济形势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对其界定必须以满足国家发展要求和战略任务为旨归。如赵宇认为,党中央作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主要在于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五大任务,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加以明确的。中央的决策不仅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了方向,同时也赋予了这一概念以丰富内涵,即基于做好降低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防范金融风险、化解库存和补短板五大任务,着力提升供给体系的效率和质量,为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奠定根基。[4]由上可见,针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界定,学者们因解读视角不同,导致其得出的定义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我们认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作出科学界定,不应仅停留在对经济体制考察的现实性维度上,不能忽视经济结构本身的系统性和发展性,还应在理论分析上夯实其合法性根基,这是科学全面把握其概念内涵的必然要求,也即唯有在实现对概念本身的动态与静态分析、历史与现实考察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其价值、动因和体系等作出全面的阐释,才能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作出更加科学的界定。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与动因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及演变都是在其独特背景下一系列相关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同样也不例外。学界普遍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是当前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如崔军等指出的,当前我国经济整体状况良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基础条件没有改变,但短期内经济低迷的外部压力依然存在,尤其是“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档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影响加剧”,导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5]另一方面,经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一直较为迟缓,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化,甚至出现长期停滞的危机,也使得“世界经济对中国发展带来的边际带动力正在减弱”,尤其是以往“中国经济发展借助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战略机遇期基本结束”,面对中国进出口增幅的明显下降,外需对经济拉动作用减弱,外汇储备下降过快等不利局面,客观上对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提出了现实呼唤”。[6]
基于这一背景,学界从更加具体的层面上探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外动因,相关观点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需求不足论”
该类观点着重从 “需求侧”的角度作出论证。如杨春学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是以需求为主导进行展开的,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也主要基于消费和投资因素进行评估,通过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对总需求进行干预,并以此来抚平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这一政策虽带来了短期扩张,但也导致了对宽松政策下的“需求依赖症”,造成资源和环境的浪费和破坏,而且在总需求政策的指导下,我国第二产业已渐趋饱和,大量资源开始涌向第三产业,但目前第三产业主要以低端服务业为主,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随着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从“结构性增速”向“结构性减速”的转变,其需求量必将难以有效提升。他们认为,经济新常态下需求不足的困局,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现实需求。[7]
(二)“产能过剩论”
该类观点着重从 “供给侧”的角度作出论证。如胡荣涛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绝非单纯的“消费者需求不足”,而是“部分行业产出供给量超出了市场的实际需求量”,导致了生产能力的过剩。尤其是部分产业因缺乏规划而盲目发展,导致市场难以完全消化。我国经济发展中产能过剩的形成,表面上看是固定资产投资失误所致,但其深层原因是长期“粗放型增长方式、僵化的体制机制”带来的恶果。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带来了投资规模过大、过长的现实弊端,也使企业本身养成了难以满足的“投资饥渴症”,而长期僵化的体制机制则进一步使企业形成了“对投资的等、靠、要依赖心理”,这亦构成了我国投资效益差和产能过剩的重要根源。他认为,要化解与消除产能过剩的现象,迫切需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摆在首要位置,以在优化投资结构的过程中,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升级。[8]
(三)“结构失衡论”
该类观点着重从“供需两侧”的角度作出论证。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因为 “产能过剩”和 “需求政策”,而应基于结构性的角度对其作出分析和评判,因此可视为对前述观点的理论深化。如贾康等便立足供需结构的双边视角,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因归结为 “供给侧和需求侧不相匹配”,并指出“供给侧改革绝非排斥需求侧的优化努力”,而是要结合“供需两端”的结构作出系统性的安排。[9]徐宏潇结合需求满足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了供给结构的失衡问题,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两大结构性失衡;在生产力层面上是低端产品供给过剩,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在生产关系层面上是低效制度供给过剩,高端优质制度供给存在不足。正是这一结构失衡,导致供需之间的矛盾难以化解,并对生产力的发展形成现实制约,同时也构成了当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层根源。[10]
(四)“国际压力论”
该类观点着重从全球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角度作出论证。如王一鸣等人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困局,根本上源自于结构性改革的迟缓。尤其是近年来国际分工结构开始发生改变,传统的欧美发达国家纷纷从信贷消费模式转向再工业化战略,而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迫于压力也开始着力延伸产业链,以提高产品附加值,并凭借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抢占国际市场。面对普遍的发展难题,世界各国都力求通过结构性调整来提升自我优势,争取更有利的国际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要提升我国国际竞争优势,就必须把结构性改革摆在突出位置上,尤其是随着国内要素成本不断提升,我国的传统优势正在逐步减弱,面对“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双重压力,唯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可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也是我国适应全球经济形势和国际分工格局的紧迫要求。[11]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与争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为学界相关学理分析提出了现实要求,一些学者试图通过确立其内在的理论基础,为其顺利推进提供“合法性”依据,这是目前该领域争议较多的一个方面。综合而言,这些争论主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否可以“西方溯源”的解读展开。从西方渊源论支持者的角度看,“萨伊定律”、“供给学派”、“新自由主义”等是构成其论证的主要依据。如有学者将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为“现阶段萨伊定律在我国的新内涵”[12]。有学者认为,作为供给学派典型实践的“里根经济学”对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淖”具有积极意义,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背后就是供给学派”[13]。此外还有学者试图在新自由主义那里寻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依据,将市场化视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认为国有企业是导致“无效供给”的根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让市场成为真正的主体”。[14]
针对学界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西方渊源论断,一些学者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林毅夫看来,中外之间面临着不同的发展任务,每个国家的发展都有其特殊性,我国经济政策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同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存在差异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 “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套我国的问题”,必然“带来很大的误读”。[15]胡若痴指出,西方的供给学派的背景是经济滞涨现象,而我国当下的经济问题在于通货紧缩和结构失衡,而且供给学派的政策目标是私有化,而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公有制的主体性,因此西方的理论并不适合中国国情,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应以西方理论为指导,尤其“应谨防新自由主义的误导”[16]。刘元春对西方理论的局限性作出了分析,他认为,不仅供给学派开出的削减福利与减税药方难以解决中国问题,而且包括 “萨伊定律”,以西方发展经济学为核心的各类结构主义等均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并同我国“完善市场机制和实现均衡发展的改革目标相冲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桎梏”[17]。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基础的交锋和论争,推进了学界相关层面认知的科学化和理性化,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逐渐转向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中探求答案,从而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基础的确立上形成了更加科学的认知模式,相关论点可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马原论”
“马原论”主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相关原理展开论证。如任保平等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针对我国经济结构与生产问题而进行的改革,根本目标在于通过“促进社会分工的深化”,“培育新的发展动力”。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为依据。[18]许梦博等则认为,当下我国经济问题的实质是供给侧问题引发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的不平衡,要科学加以化解就必须重新回到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进行解读。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分析了两大部类的平衡关系,其不仅直指供给侧的问题核心,而且对经济运行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联系亦能作出解释,从而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更为深刻的理论证明。[19]
(二)“中特论”
“中特论”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理论体系的角度展开进行论证。如肖林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是基于当下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对“改革实践的综合性创新”,本质上属于我国经济在新时期背景下的调整和探索过程,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其完善化的理论体系建构,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提供最为科学化的理论指导。[20]刘凤义也持有同类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秉持的以人为本原则、共享发展原则和公有主体原则等,构成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然指向。[21]此外,有些学者从更为具体性的理论视角作出了分析,如王廷惠等就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角度进行论证,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唯此才能在深化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扩大有效供给,并最终达到提升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根本目标。[22]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价值取向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攻坚战”,其必将推动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学界对此亦作出了积极呼应。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价值取向,学界虽存在观点碰撞,但大都给出了积极评价。
(一)经济价值:完善供需结构,推进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二)社会价值:强化社会建设,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发展
盖逸馨认为,社会建设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根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宏观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不仅为社会生产力提升提供了新路径,而且也在客观上进一步增强了我国“社会建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凸显了我国社会建设“扭住关键,精准发力,严明责任,狠抓落实”进行深化改革的全新走向。在其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对于社会建设体系的完善,社会秩序、社会建设成果的创建和提升等意义重大,能够为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提供积极帮助。[26]方辉振等则认为,经济发展新常态同样给我国城镇化过程带来了新的态势,这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也必然会对城镇化的推进带来新的影响。新型城镇化作为我国当下的社会发展战略选择,标志着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全体居民现代化建设成果的共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成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环节,其有助于解决好其中的“人、地、钱”的供给问题,为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创造良好条件。[27]
(三)理论价值:深化理论创新,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卫兴华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核心,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得出的科学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应用于我国发展实践,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理论成果。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历史演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类新问题和新矛盾又不断产生。我们党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深刻把握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客观规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断前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经济术语”的提出,就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重大理论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提高供给体系的效率和质量,这是中央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大创新,也是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发展”。[28]
(四)政治价值:强化简政放权,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诚如汪玉凯所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政府改革”,其“关键在于政府”。[29]娄成武(2016)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将对推进政府简政放权产生积极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该目标的实现必然要求政府在降低行政成本的基础上,着力处理好同市场、社会的关系,也即要求其必须把积极做好简政放权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上。石瑛(2017)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落实到政府职能的转变上。她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象上属于经济领域,但根本上在于政府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必然要求政府释放更多的政策红利,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不断提升施政透明度,以增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这些都必然要求政府在治理中积极实现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
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障碍
现阶段,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绝非易事,其必然要遭遇重重的困难和障碍。通过对学界已有观点的考察,这些障碍和难点可以从改革的主体、客体和过程三大层面作出归纳和阐释。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性障碍:从“认知滞后”到“本领恐慌”
改革作为对旧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局部性或整体性调整,是在一定主体的引导和推动下展开的社会实践。所谓改革主体,即改革的实际引导者和推进者,是“有目的地扬弃旧制度、构建新制度的组织和个人”[30]。改革能否成功,关键是改革主体是否形成前瞻性的认知结构和能力水平。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中,目前这两方面均有待进一步强化。一方面,对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些地方改革引导者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贾康(2016)将其概括为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界定为新的“计划经济”,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理解为实行需求紧缩,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释为对“里根经济学”的“中国化”,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标签式新概念任意应用四大方面。廖清成等(2016)则认为,一些领导干部在实践中要么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沿袭旧的改革内容和模式,对改革的内涵和逻辑存在误读和误解;要么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化为生产高质量商品,对改革的重点和动力进行误导和误判。在其看来,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体的这些认识误区,构成了影响改革进程的制约因素。
另一方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部分改革主体亦面临一定程度上“本领恐慌”的尴尬境地。对此,郑京平(2016)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政府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紧密相关,但受部分治理主体能力和本领不足的掣肘,各级政府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还面临诸多难题亟待破解,如一些领域的垄断问题依然较为严重,市场上假冒伪劣等行为未得到有效遏制,部门之间推诿扯皮、设租寻租等。张彬等(2016)认为,改革主体的能力不足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沉溺于过去的老方法来发展经济,对新常态下如何基于供给侧角度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以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尚未完全“破题”。二是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在政府治理和经济发展各领域的应用不断普及,也给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部分基层干部因欠缺专业知识而陷入被动和茫然。可以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是“老办法不灵了”,“新方法又未掌握”,改革主体能力建设层面的问题,构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障碍。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体性障碍:从“要素残缺”到“利益困局”
改革的客体即改革主体实施改革针对的客观对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调整结构、促进要素最优化配置的治理实践,涉及资本、制度和技术创新等多重要素,这些要素在实质上构成了改革的根本性对象。在当下转型期,这些客体还一定程度上存在“残缺不全”的不良境况。刘志彪(2016)对此作出了阐释,如在资本领域,面临着投资效率不足的现实境况,“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阻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在技术领域,则面临着如何激励社会主体“将资源转向自主创新的问题”;而一些关键领域的制度创新,也存在“只闻其声、未见有真动静”的现实窘况,这些客体性要素的残缺构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张卓元(2016)进一步分析了其内在根源,将利益关系调整视为客体性障碍的重要内因,指出随着当下改革进入深水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必将带来较大的利益调整,结果导致 “一些部门利益受损”,特别是部分行业“高收入、高福利者的利益丧失”或“失去种种优惠”,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既得利益群体必然会采取各种方法对改革进行干扰和阻挠,使改革难以推进甚至“举步维艰”。因此,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前行,着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和困局是必然选择。
Energy Management Strategy for Electric Ships with Hybrid Energy Source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性障碍:从“风险叠加”到“监管缺位”
除了在主客体层面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障碍之外,近年来学界也从改革过程的动态视角进行解析。张杰等(2016)认为,正是基于改革客体层面上的“利益冲突”,导致了各类可能性风险的产生,如“债务风险及可能诱发的金融风险”、“失业风险及可能诱发的安全风险”以及 “产业风险及官员怠政行为可能诱发的经济波动风险”等,进而给改革过程带来了“延误或扭曲”。刘安长(2016)则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风险具体划分为 “减税降负中的财政收支风险”、“去产能过程中的失业风险”、“短期内的经济下行风险”、“金融风险”、“政府的过度干预风险”和“改革与调控的混淆风险”等六大层面,其也将这些风险视为改革的不利因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各类风险的叠加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导性根源还在于相关层面的监督没有及时跟上。对此,陆岷峰等(2017)基于化解金融风险的角度指出,金融监管模式的完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化解产能过剩风险的必要前提,但一些机构目前很大程度上还秉持着“谁的孩子谁抱走”的监管原则,给相关层面留下了不可忽视的监管空白,其结果必然是对金融风险难以形成有效监测,在阻碍金融市场良性发展的同时,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提升带来现实制约。
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路径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价值取向和现实障碍,学界也对其未来的科学路径进行了探索与建构。概而言之,可从五重向度作出分析和归纳。
(一)在改革起点上,主张转变和形成科学的思维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科学推进供给侧改革实践,改革主导者和参与者实现相关理念的更新是首要前提。厉以宁(2017)就将理念的转变和创新视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指出一方面企业家要着力改变过去固步自封的经营理念,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关注消费变化”,从而“准确把握结构性调整的方向”。另一方面则要积极树立创新理念,以保持旺盛的创新精神,确保自身跟上时代步伐。乔洪武等(2016)认为,理念更新与否是考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成功的重要变量,其从更为深层次的经济伦理视角,阐释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相关理念的应然转变方向,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主体要积极变革角色伦理观,改变单纯追求GDP的片面政绩观;社会主体要积极转变就业伦理观,通过树立自食其力的价值观,形成崇尚自力更生的行为准则;企业主体要变革致富观,摆脱以往崇尚“快富”、“暴富”的不良社会心理,逐渐树立起“平稳致富”的经济伦理观,由此三方面的理念转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奠定科学的思想根基。
(二)在改革主体上,主张建构和形成科学的治理模式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作为根本性引导主体责任巨大,其必须不断促进自身治理模式走向科学化。对此,吴敬琏(2016)认为,各级政府必须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两个层面,如在“组织融资”、“操办项目”和确立“技术路线”等层面,政府机构要善于“有所不为”,而对“公共产品”、“经济环境”和“社会保障”等层面则要做到“有所为”。在他看来,政府明确定位是其形成科学治理模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学迈进的首要前提。姚洋(2016)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了政府治理方向,但这绝不意味着政府就限定于供给侧一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一个长期的过程,“绝不能忘记短期的需求管理”。当下我国经济的发展问题既是长期的供给问题,又有短期的需求问题,尤其是包括消费和投资等的需求在当下依旧较为欠缺。这决定了新常态下要推进经济实现科学发展,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就应基于宏观经济短期平衡的要求,建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短期需求管理相结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唯有实现二者之间治理政策的紧密结合,才能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科学的保障体系。
(三)在改革对象上,主张把科技创新摆在突出位置上
从矫正要素配置模式,到产业和投资结构的优化,再到有效经济总量和人民生活品质的最终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象虽涉及方方面面,但其中的关键与核心还在于科技创新。李稻葵(2015)就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向,“就是运用最新的科技手段改造生产结构”,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看,即运用“最新的科学技术去改造生产关系”。尤其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生产关系如果跟不上互联网发展的技术要求,则必将成为阻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障碍。赵志耘(2016)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要素的质量水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依赖科技创新。当下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其深层次根源说到底还是在于科技创新的乏力和不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已构成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掣肘”,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在于“通过科技创新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抓住了科学创新这一根本对象,就抓住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牛鼻子”。
(四)在改革过程上,主张以完善的法制体系进行保障
法律和制度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要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沿着科学的方向和目标实现持续化迈进,就必须建构相应的法制体系进行保驾护航。在公丕祥(2016)看来,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构成了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逻辑标志,同时也“蕴含着深刻的法治逻辑”。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唯有以法治方式对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进行巩固,才能形成“激发创新精神的法治激励机制”;唯有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所需的法律机制,才能“有效维护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唯有对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权责范围依法作出划定,才能实现对良好发展环境的营造,并推动供给侧革命实现纵深化发展。任保平从四个方面具体构建了供给侧改革的制度保障体系,具体而言:一要建构科学的政府官员考核制度,核心是将质量效益、民生改善和文化建设等列为考核内容;二要建构科学的行业准入制度,以改变政府对资源的过度控制;三要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四要推进财税体制、价格体制和教育体制等的联动化,以形成供给侧改革的宽松环境。[31]
(五)在改革视野上,主张科学吸收和借鉴域外先进实践经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新常态而进行的战略创新,同时也是为适应当下全球经济形势作出的主动抉择,应树立全球视野,在实践层面上借鉴域外先进经验。程恩富等(2016)指出,当下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展开的,期间机械化、智能化的双重嵌入给改革本身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复杂格局,而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领跑者的德国则具有先进和成熟的转型经验,因此,积极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德国相关经验和“关键共性技术”,对创新我国制造业供给体系,将我国建设成为世界制造强国是有积极意义的。[54]赵景峰(2016)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世界经济运行中并非个案”,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借此走出危机,如英国就通过缩减财政补贴等途径来减少财政支出,而美国则放宽了政府对天然气、交通和银行业等的管制和准入,其均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有效提升。科学借鉴国际经验,可以给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辅助效应,确保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实现双重提升。
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展望
基于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的回顾分析,可知目前学界在该领域的探索上已取得一定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极大提升了各界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知水平,而且也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强化供给的有效性和灵活性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学理根基。但学界对该领域有针对性分析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尤其从整体性和全面性的角度而言,学界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还存在一些现实缺憾,亟需作出完善和补充。
第一,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分析较为粗浅。综观学界已有成果,不难发现当下的关注重心主要还是集中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动因及意义等层面,对一些重大理论议题依旧缺乏权威性界定,如有关中国情境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的全面性把握,有关中国模式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建构等,目前学界显然观点不一且欠缺深度,亟需从更加权威性的角度对其作出分析。
第二,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横向比较分析有待进一步科学化。如对于国外相关理论和经验,有的学者认为其不符合我国国情,应加以否定和批判,有的学者则认为可以进行吸收和借鉴。二者之间到底存在何种程度上的关联性,学界需要作出更加科学化的阐释。
第三,微观层面的实证分析有待加强。已有的研究无论是在问题的研判还是具体的路径建构上,都主要基于宏观政策层面作出分析,从市场主体的微观视角进行的实证调查相对不足,而这一层面的研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可或缺。
第四,亟需拓宽学科参与面。经济学、管理学等是当下学界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导学科,而从其他学科的视角开展的研究,如基于法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视角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还不多见,显然,这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性和科学性认识体系的形成是不利的。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在我国这样的大国深化改革“绝非易事”,改革的“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改革要有序推进,对改革的认识和研究首先就必须体现出科学性和前瞻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例外。基于对上文的分析,这里认为当下学界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应重点在以下四个“度”上作出进一步突破。
第一,在研究内容上,要进一步强化供给侧改革体系研究的理论“深度”。一方面要对我国情境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外延及其内在规律作出更加精确化的阐释和界定,其中既要着力在我国国情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脉络中提炼和挖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要义,又要结合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客观实际和发展布局,对中国模式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运行规律作出探究。另一方面更要立足于建构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和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高度,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价值定位、独特性质、基本原则、运作逻辑和目标取向等层面入手,着力建构和形成中国特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方位理论体系,从而更好地发挥改革理论对改革实践的科学指引作用。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微观层面的调查“力度”。调查研究是获得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唯有通过对改革对象具体状况、基本诉求和发展动态的调查分析,才能为改革的深化带来更加科学化的指导效应。当下我国的改革事业已经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必定会存在内部的利益冲突和博弈。在这种情况下,要确保各项具体的改革政策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研究者必须以更加积极的热情投入到调研环节中去,以客观务实的态度对政府和市场主体的相关诉求作出全面深刻的摸查和评估,进而才能提出更富建设性和针对性的改革建议。这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体系建构的内在诉求,又是有效规避改革风险的重要保障。
第三,在研究视野上,要进一步厘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域外相关理论和经验的 “关联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建构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除了要着力在纵向的改革历史进程中挖掘资源外,还要善于从横向角度上对其同域外理论和经验的关联性作出正确厘定。我们认为对其应作出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一方面,对于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等相关西方经济学流派及相关理论体系,必须明确其无论在诞生背景还是阶级属性和建构目标上,都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存在本质性区别。对于这些西式理论,学界在对其进行研究和分析上应保持高度警惕,绝不能生搬硬套将其同我国改革实际进行对接,以免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推进产生误导。另一方面也必须明确中外理论的差异性,并不代表域外实践经验就毫无价值。对西方理论体系的“戒备”,也绝不意味着改革大业就要“闭门造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在坚持理论自信的基础上树立全球眼光,从纯粹技术理性的角度对西方的先进经验作出萃取和借鉴,这也是使我国改革少走弯路的应然选择。
第四,在研究力量上,要进一步提升多学科交叉切入开展研究的“协同度”。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少学者认为,其必然牵涉政府治理、制度完善和观念意识等层面的内容。这事实上也在客观上表明要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更加全面的认知体系,在理论研究上不应仅仅局限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范畴内,而应把拓展学科参与面摆在突出位置上,通过积极借鉴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等角度作出分析和探究,由此才能在更好发挥各研究智库“外脑”作用的过程中,为解决好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供坚实的指导。
[1]王小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内涵、理论源流和时代使命》,《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 2期,第 82~87页
[2]黄群慧:《论中国工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9期,第5~23页
[3]李翀:《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政策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年第1期,第 9~18页
[4]赵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党的文献》2017 年第 1 期,第 50~57 页
[5]崔军 张雅璇:《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动因及助力的财政政策探析》,《财政监督》2016年第9期,第 12~14 页
[6]张慧莲:《国际经济深度调整对中国的影响及对策》,《经济纵横》2016 年第 3 期,第 101~110 页
[7]杨春学 杨新铭:《供给侧改革逻辑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6年第4期,第 48~58 页
[8]胡荣涛:《产能过剩形成原因与化解的供给侧因素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16年第2期,第5~9 页
[9]贾康 张斌:《供给侧改革:现实挑战、国际经验借鉴与路径选择》,《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4期,第5~9页
[10]徐宏潇:《双重结构失衡困境与破解路径探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16年第6期,第171~175页
[11]王一鸣 陈昌盛 李承健:《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民日报》2016年3月29日
[12]黄剑:《论创新驱动理念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第12~17 页
[13]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经济问题》2016年第5期,第12~17页
[14]朱海就:《供给侧改革关键是市场化》,《深圳特区报》2016年1月12日
[15]林毅夫:《供给侧改革的短期冲击与问题研究》,《河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 1期,第 2~4页
[16]胡若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谨防新自由主义的误导》,《红旗文稿》2016年第14期,第22~23 页
[17]刘元春:《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理论导报》2016 年第 3 期,第 16~19 页
[18][31]张如意 任保平:《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人文杂志》2016年第6期,第20~25 页
[19]许梦博 李世斌:《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 4期,第 43~50页
[20]肖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逻辑》,《科学发展》2016年第3期,第5~14页
[21]刘凤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向》,《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 2期,第 211~214页
[22]王廷惠 黄晓凤:《以“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供给侧结构改革》,《光明日报》2016年1月2日
[23]胡鞍钢 周绍杰 任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17~22 页
[24]徐光远 李鹏飞 焦颖:《供给侧改革的历史来源与现实意义》,《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 3期,第 15~23页
[25]吴群 侯祥鹏:《供给侧改革中企业降成本的现实意义与路径选择》,《现代经济探讨》2016年第6期,第15~19页
[26]盖逸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社会建设的意义及影响》,《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2期,第 108~111页
[27]方辉振 董若愚:《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新型城镇化》,《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 4期,第 57~62页
[28]卫兴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金融评论》2016年第 5期,第 1~5页
[29]汪玉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政府改革》,《中国经贸导刊》2016年第13期,第48~49页
[30]周荣华:《改革主体与改革动力生成》,《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23~29 页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the Supply-side Reform
Hu Hongbin
The reform of the supply-side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perfecting the supply and demand structure and adapting to the new normal for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which is of great value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our government functions,strengthe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perfec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ince the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has been put forward,domestic scholars have carried out continuous research,and achieved some research results,but the related research needs to be perfected i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construction,the micro empirical investigation,the horizontal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participation.In the future,the academic community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and clarify the“depth” of the theory of supply side reform,the “strength” of th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the “synergy degree” of multi-disciplinary participation and the “correlation degree” of the related theory and experience.
government action,supply-side reform theory,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