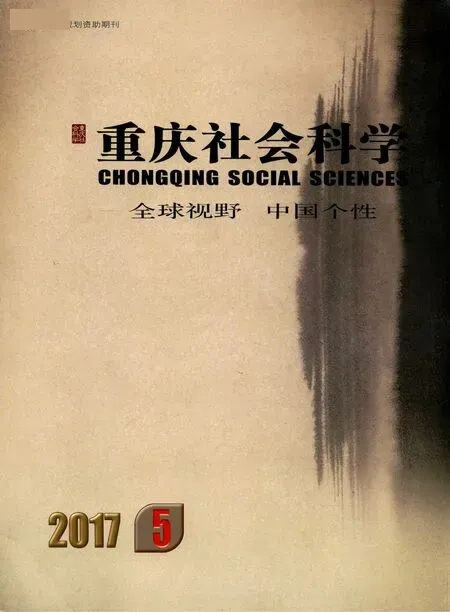“互联网+社区养老”的运行困境摆脱*
屈 贞
“互联网+社区养老”的运行困境摆脱*
屈 贞
“互联网+社区养老”是典型的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型养老模式。其在实践运行过程遭遇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提供者“错位”与“缺位”并存;生产者高度依赖政府扶持与服务内容单一并存;消费者养老需求多元与有效参与不足并存;评估者评估主体单一与评估流于形式并存。探索构建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协同联动机制,有效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是实现“互联网+社区养老”持续有效运行的可能方案。
“互联网+社区养老”社区治理 养老产业
作者单位中共长沙市委党校政治与领导科学教研部 湖南长沙 410004
随着老年人口规模的增加、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以及老年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我国社会养老负担日益加重,在当前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社区养老因其便利性、舒适性、经济性、安全性等相对性优势,成为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但事实上,我国养老服务“供给侧”始终存在重机构养老、轻居家养老的误区,造成社区养老服务平台重视和利用不够,社区养老服务面临着需求剧增与养老服务供给总量不足、养老服务需求多元与供给结构性失衡的低效甚至无效供给困境。为破除困境,我国多地开始借助信息技术的发展打造社区养老服务升级版,展开了“虚拟养老院”的探索。2015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联合下发通知,提出在养老领域推进“互联网+”行动,此后多地再一次展开对“互联网+养老”模式的探索。由于社区养老是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对“互联网+社区养老”模式的探索也成为“互联网+养老”模式探索的主体部分。不可否认,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互联网+社区养老”的价值与功能都保持较高的认可度,但是也不乏对 “互联网+社区养老”可能遭遇的“技术性难题”和运行困境的担忧。而实践情形也表明,“互联网+社区养老”在一些地方确实面临着“需求低、供给少、利用低”的难题,有研究者通过对武汉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系统“一键通”使用情况的统计调查后发现,汉阳区某社区近200名65岁以上老人认为需要配置一键通手机的有61人,不需要的有132人,实际需求为31.6%,对比已发放的手机“一键通”数据,真正参与这项服务的居民仅占1/4。[1]实际上,“互联网+社区养老”在实践运行中遭遇的困境并非仅止于此,那么“互联网+社区养老”在实践运行中到底会遭遇哪些困境呢?考虑到“互联网+社区养老”模式对于缓解我国日益加重的社会养老负担意义重大,展开对“互联网+社区养老”模式实践运行困境的细致挖掘以及寻求破解方案,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互联网+社区养老”:分析视角的选择
作为一种新生的养老服务供给理念与方式,“互联网+社区养老”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可能遭遇一系列困境是处于理论预期范围之内的事情。虽然“互联网+社区养老”模式还处于初期探索阶段,但已有不少研究者对其实践运行困境有了事实性的把握。问题在于,由于研究者依持的群体价值与利益关怀不同,研究立场分散与多元,使得当前对“互联网+社区养老”实践运行困境的挖掘与呈现相对较为零散,因此,有必要以一种更客观、更包容的宽阔立场来挖掘“互联网+社区养老”的实践运行困境。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事实上,“互联网+社区养老”在实践运行中之所以会遭遇困境,也与“互联网+社区养老”运行中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的考量与行为选择有关,他们的考量与行为选择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互联网+社区养老”模式的实践运行样态。利益相关者理论,缘起于西方学者对企业股东利益最大化经营目标的反思,由斯坦福研究院于1963年首次提出。1965年,美国学者Ansoff最早将该词引入管理学界和经济学界,此后随着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将利益相关者理论运用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研究中。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其一,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挖掘 “互联网+社区养老”的实践运行困境是一条可行路径;其二,既然此前由于研究立场的分散造成对 “互联网+社区养老”实践运行困境的挖掘与呈现相对较为零散,因此选定利益相关者视角之后,分析的关键就在于找准找全“互联网+社区养老”实践运行中的“利益相关者”。
“互联网+社区养老”是一个内容复杂、涉及部门较多的综合体系,其理论内涵可以界定为“以 ‘互联网+社区养老’平台为载体的合作治理”,其核心特征是整合资源、集成功能、能力合作与无缝对接,即通过“互联网+社区养老”信息中心成功搭建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一体化”运作平台,从而破解传统社区养老服务的资源匮乏和方式失灵的困境。在“互联网+社区养老”服务供给模式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多元主体包括四大类:供给者(政府)、生产者(承接信息平台搭建项目的社会组织或养老企业、加盟企业、一线工作者)、消费者 (享受服务的老人和家属)、评估者四类主体。在各地实践中,承接项目的社会组织既有非营利组织,又有私营企业。评估者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信息平台运营商对加盟服务商相关服务供给方面的评估;二是由地方政府主管部门、街道、社区居委会相关负责人员联合对“互联网+社区养老”平台社会化运营成效进行的评估。整体而言,“互联网+社区养老”的运行逻辑为:提供者(政府)引导扶持主要生产者(平台运营商)搭建信息化平台;平台运营商广泛吸纳优质服务商加盟,满足社区老人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需求;政府一方面通过建设补贴、运营补贴、为高龄“三无”老人购买信息平台服务等“补供方”的方式扶持平台运营商,一方面给老人发放服务补贴,即“补需方”的方式激励老年人无偿或低偿购买相关服务;老人的积极参与产生规模效应,各生产者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促使其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吸引更多老年人参与消费,由此逐渐形成良性循环。
二、“互联网+社区养老”的运行困境:利益相关者分析
基于对公共服务“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社会失灵”的基本认知,“互联网+社区养老”供给模式的初衷旨在依托“互联网+”信息平台实现多主体的有效合作,通过平台社会化运营、引入竞争机制提升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质量和效率。但实践中由于各主体角色不清、权责划分不明,“互联网+社区养老”运行面临实践梗阻。
(一)提供者——“错位”与“缺位”并存
科学定位政府引导者、扶持者、规范者及监督者角色,是推进“互联网+社区养老”服务合作供给模式的基础。但实践中,政府“错位”与“缺位”并存。主要表现在:
第一,政府角色“错位”,将引导者、扶持者变成了包揽者。在“互联网+社区养老”发展初期,政府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引导资金消除投资者疑虑,发挥好引导者与扶持者的角色是其职责所在,但政府的有效推动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大包大揽”。当前各地探索的主要模式是政府强力推动,在这种行政主导模式下,短期内效果明显,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同时带来了财政投入的捉襟见肘、平台经营商的过渡依赖、社会参与度低、运行的不可持续等问题。
第二,政府“规范者”、“监督者”角色“缺位”。发展规划的制定、标准的出台、有效的规制和科学的监督是“互联网+社区养老”得以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但当前有关“互联网+社区养老”方面的政策制度设计与安排并不多见,仅有的一些以“通知”、“意见”等形式分散在相关政策文件中,只具指导性,实践性不强,对行业健康发展的激励约束性不够,造成一些地方实践探索中空有其名。
(二)生产者——高度依赖政府扶持与服务内容单一并存
在多元主体合作供给的 “互联网+社区养老”模式运行中,寻找到合适的服务生产者是保障“互联网+社区养老”模式可持续运营的关键,西方国家的经验是通过构建一个适度竞争的养老服务市场以筛选服务承接者,但我国目前缺乏这一制度土壤。现实中,平台主运营商、加盟企业、一线工作者作为主要服务生产者,普遍不同程度地存在供给目标异化或(和)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服务递送的效果并不理想。
一是承接者(平台运营商)先天不足。在“互联网+社区养老”社会化运营中,作为委托方的地方政府往往基于养老服务组织或养老企业数量少、服务能力不足、服务质量无保障等现实风险,而更乐于寻求或支持自己培育的内生性社会组织或域内的养老企业作为承接者,并通过提供财政补贴和相关辅助服务扶持其发展。这样,一方面造成平台运营商的先天不足,一方面也因其对政府扶持与资源的强依赖,造成其供给目标的异化,倾向于瞄准政府偏好,而缺乏对老人切实需求的回应。
二是加盟企业积极性不够。给加盟企业带来合理的盈利是保障企业积极参与的前提,但现实中由于处于探索初期,市场覆盖面窄,除了政府购买服务的部分老人,一般老年人购买有偿的养老服务需求不足,理想状态的规模效应难以实现,加上老人作为特殊服务群体,往往在上门服务时还面临信任缺失、高风险等因素制约,加盟企业积极性不高,变动频繁。
三是一线工作者专业化服务能力有待提升。在“互联网+社区养老”模式中,信息技术只是提高服务效率的工具,养老服务的核心始终是人对人的服务。因此,一线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专业技能直接关系到服务品质,也关系到老年人对“互联网+养老服务”这一新模式的认可度。现阶段,一线养老服务人员面临年龄偏大、薪酬待遇低、流动性大等系列问题。
(三)消费者——养老需求多元与有效参与不足并存
老人参与不足、覆盖面窄是“互联网+社区养老”模式发展面临的重要阻碍。目前我国各地的实践中,主要覆盖的是缺乏生活自理能力、高龄、“三无”等政府购买服务的特殊老人,有偿购买平台养老服务的老年人并不多。老人参与不足的原因是多元的:一是百姓传统的“重积累、轻消费,重子孙、轻自身,重物质生存、轻精神享受”消费观念根深蒂固。二是老年人的消费能力相对较低,有效需求不足。三是由于缺乏扎实的需求调研和恰当的需求表达途径使得服务内容不能契合服务需求。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显示:2015年,城乡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项目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上门看病、上门做家务和康复护理,其比例分别是38.1%、12.1%、11.3%,其他需求依次是:心理咨询或聊天解闷服务为10.6%,健康教育服务为10.3%,日间照料服务为9.4%,助餐服务为8.5%,助浴服务为4.5%,老年辅具用品租赁服务为3.7%。①《三部门发布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成果》, http://www.cncaprc.gov.cn/contents/2/177118.html,2016-10-09。目前,平台提供的服务主要是家政便民类和主动问候类服务。服务内容的形式化与空泛化使得社区中的多数老人并没有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依赖感就更无从谈起。四是宣传推广不到位,老人对新事物接受慢加上服务模式不成熟等造成现阶段老年人对信息平台服务的不信任和消费顾虑,信息化产品的市场氛围、意识还没有培养起来。
(四)评估者——评估主体单一与评估流于形式并存
评估是“互联网+社区养老”多元主体合作运行中非常重要的环节,科学有效的评估一方面能避免多元主体合作可能产生的公共伦理缺失,减少因寻租、合谋造成的腐败,减少私人部门因寻利动机在供给中的取巧规避,保障服务的公益性和公平性[3];另一方面通过定期考核评估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奖励和扶持的依据,可以提高市场和社会组织参与的积极性,提升服务质量,让老人享受到合适、满意的服务。实践中,由于“互联网+社区养老”作为一种新的养老模式正处于摸索阶段,评估工作的组织一定程度上是作为提供者的政府在负责主导,这造成运行中面临诸多困扰:一是就评估主体来说,当前考核监管和评估的工作主要是由政府部门或服务机构自行进行,行政色彩较浓,缺少居民评估、专业评估和社会的有效监管,造成评估结果缺乏真实性和客观性,有的地方虽然实行第三方评估,但流于形式。二是就评估指标来说,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可量化的评估标准和规范。评估指标的不完善往往造成实践的迷失,致使现实操作中将大量资金投入有形、看得见的硬件设施设备建设而忽略了服务项目的拓展与挖掘、服务人员技能培养等软件方面的提升,结果出现信息服务中心闲置,没有老人参与的窘况,在社会上也造成“形象工程”的负面评价。三是就评估对象来说,评估对象比较单一。主要是对承接者平台运营商、加盟企业、一线服务人员的考核,缺乏对政府推进“互联网+社区养老”社会化运营成效的评估、政府购买高龄困难老人服务成效的评估,对老人的需求评估也重视不够。
三、破解“互联网+社区养老”困境:联动机制构建
增强相关利益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是推动“互联网+社区养老”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立足供给者、生产者、消费者、监督者四类主体,构建“互联网+社区养老”联动机制(见图一,下页)。
(一)构建提供者(政府)“对上回应+对下负责”相结合的供给动力机制
在“互联网+社区养老”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模式中,理顺主体间关系、实现各主体间的良性互动是其有效运行的前提。养老服务属于准公共产品,在发展初期,政府承担着核心供给主体的角色,提升政府自身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激励和监督政府形成良善的供给意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追溯政府动力之源是避免政府基于部门利益或私人利益行事,取得良好的供给绩效的前提。[4]那么,基层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养老服务供给意愿、供给动力、供给目标如何形成?在政府层级体制和层级分工之下,政府的供给动力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自上而下的养老服务供给的任务指派,即中央负责制定大政方针确定总目标,各级政府之间进行层层的任务分解和指派,由此实现政府养老服务供给动力的逐层传递;二是自上而下的绩效考核压力带来的政治激励效应。自上而下的动力之源造成实践中各级政府对上级指标的积极回应和对民众需求的回应不足,造成了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供给中的结构性失衡[5],也造成了“互联网+社区养老”模式运行中“服务需求低、供给少、利用低”的现实困境。因此,迫切需要构建起生产者(政府)“对上回应+对下负责”相结合的供给动力机制。

图一 利益相关者逻辑下“互联网+社区养老”模式联动机制构建框架
1.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健全机制,强化政府的公共责任意识,进而引导政府成为公共利益的忠实维护者、民众需求的满足者、“对上回应+对下负责”的兼顾者。一是改革对政府养老服务部门绩效考核中的上级政府单一考核主体模式,增加老人、家属以及广大社会公众的参与,并占有一定的权重,从而约束政府供给行为。如在“互联网+社区养老”模式中,可以借助信息化平台老人评价、老人需求表达等相关功能设置的完善,借助基于政务云大数据平台的信息互联共享等技术优化手段,实时了解养老服务消费者的诉求和反馈,避免以往评估中出现的“走形式”和“技术处理”问题,真正发挥出考核对政府供给养老服务行为的约束作用。二是将公众的评估结果作为政府及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晋升的重要依据,从而破解自上而下的供给动力传递与自下而上服务需求传递之间的“逆层级化”现象[6],提升政府对老人服务需求的回应性,使服务供给更加有效和精准。
2.健全多元监督机制
加强监督是约束政府行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保护公众利益的有效途径。一是提升行政监管能力。各级民政部门要加强对养老服务探索的指导、监督和管理,相关部门要依照职责分工对养老服务实施监管,从而对养老服务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经办机构协调管理行为等进行全面监督、检查和评议,多方协作形成合力,确保事有人管、责有人负。二是加强社会监督。发挥行业监督、公民个人监督和媒体舆论监督等方面的作用,通过监督倒逼政府加强信息公开力度、完善招标竞标程序、细化相关规则标准,为“互联网+社区养老”模式发展营造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三是畅通投诉渠道,建立养老服务举报和投诉制度。
(二)构建生产者市场准入与扶持激励机制
生产者能否提供保质保量的符合老人诉求的养老服务是推进“互联网+社区养老”模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加大扶持力度、培育强大的生产者联盟是当务之急。
1.健全公平参与机制
公平的参与机制是挑选到合格合作伙伴的前提,合格的合作伙伴是确保“互联网+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精准匹配、优质保量的基础。一些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基于部门利益或个人私利的非规范化操作,一方面造成社会资本因缺乏有效、合理的介入途径而面临进入壁垒;另一方面也造成目前养老服务业发展中的 “马太效应”,即进入的社会资本越少,越无法形成竞争,进而形成垄断,更加丧失改进服务的动力,最后影响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因此,一方面要健全信息公开机制、多元主体参与机制,通过一定的程序和准则疏通社会组织的参与渠道、参与方式,保障广大社会组织的参与权利,从而扩大参与规模,实现适度竞争格局。另一方面,要建立全程监督机制,贯穿供给主体的选择、供给过程的管理、合同的执行、供给效果的评估等各个环节,营造公开、透明、规范的社会发展环境。
2.健全扶持激励机制
针对“互联网+社区养老”服务供给中服务承接者发展资金不足、规模小、内部自主性差、人才匮乏、社会公信力不足,加盟企业“有利上无利让”,一线服务人员招不进留不住、专业技能缺乏等现实,须进一步完善参与支持系统。第一,优化政府职能,加强顶层设计,营造健康有序的服务发展环境。第二,制定系统的扶持政策,通过完善土地、财税、购买服务、水电气优惠等政策,通过整合审批流程简化相关手续,通过明确相关补贴待遇条件及验收标准等相关政策的落实给市场明晰的预期,提高资本进入意愿。第三,政府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建议设立互联网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专项基金,发挥其对社会资本的撬动作用;同时拓宽养老服务企业融资渠道,减轻前期投入带来的资金沉淀问题,缓解资金流转压力。第四,针对养老服务行业的高风险性,建议政府扶持“互联网+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购买综合责任保险,提高生产者抵御意外风险及善后处置能力,减少社会资本进入顾虑。
3.健全人才培养机制
一线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和服务能力是体现其专业化服务水准的一扇窗口。一是注重发展养老服务职业教育。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职业技术学院家政学、老年服务相关专业的示范引领作用,优先支持和推进现代养老服务业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另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社会福利机构、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建立社区养老服务研发和实训基地,设立与养老服务相关的专业和培训项目。二是通过免费培训、发放入职补贴、补助社会保险金、建立动态岗位津贴、公平职称评审、养老服务表彰等政策、资金支持,提高养老服务行业的岗位吸引力。三是制定并实行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认证和常态考核制度。一方面落实新人入职培训上岗制度,所有新员工都要接受系统培训和试用期,经修满学分和考核合格后方可正式上岗;另一方面信息中心应定期对所有员工进行业务技能和文明服务考核,考核结果直接与晋职提升、岗位调整、奖金福利挂钩,将定期性、持续性、系统性、专业性培训列为重点工作内容之一。四是积极与人社部门对接,在社区(村)设置养老公益性岗位。
(三)构建消费者需求表达与广泛参与机制
针对运行中的老人参与不足、覆盖面狭窄、老人知晓率低、老人购买意愿不强、购买能力不足的现实,民政部门需切实找准“互联网+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点、关键制约点。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实现老人有效参与,进而扩大服务覆盖面。
1.健全需求调研机制
第一,通过扎实的调研“摸清基础情况、摸清市场需求、摸清建设成效”,建议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协助“互联网+社区养老”信息平台在辖区内开展系统的需求摸底调研,具体可采用上门询问、电话采访、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调研对象包括政府保障对象、离退休老干部、自费人群、咨询用户等群体。围绕需求进一步拓宽养老服务项目开发的广度和深度,分层分类满足老年人在娱乐、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使服务更加精准、更接地气。第二,建议进行科学抽样调研,从而客观了解老年人对信息化养老的认知、使用情况和服务满意度。具体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对智能化养老的认识、设备使用、服务模式、收费标准、政府职能以及个人建议和意见等。在充分调研基础上,科学分析和客观会诊存在的问题,从而做到有的放矢。
2.健全宣传推广机制
针对受传统消费观念影响制约,老人对新模式不知晓、不了解、不信任等问题,政府应加大对“互联网+社区养老”服务的宣传与推广力度。建议列出宣传推广专项费用,多方式营造“互联网+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的环境氛围。一是引导和鼓励老年人树立合理购买养老服务的健康养老观念、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消费理念,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质;二是广泛宣传敬老、养老、爱老、助老、孝老传统美德,鼓励子女和家人在孝敬老人方面适当消费,培育家庭成员形成“互联网+社区养老”服务消费新模式;三是通过街道、社区与信息平台合作开展 “互联网+社区养老”服务模式的入户宣传和指导工作,通过张贴海报、发放宣传黄页、定期组织信息化养老服务使用方法培训等方式,努力做到人人知晓、人人会用,进而达到大多数老年人认可与接受 “互联网+社区养老”服务的目的。
3.健全财政补贴机制
针对老人消费能力不足问题,一是建议政府优化财政补贴结构,实行“补供方”与“补需方”相结合,适度放宽或者加大老年人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补贴政策,降低老人享受服务的补贴门槛,加大对老人的服务补贴力度,适当倾斜失能老年人的补贴额度。二是建立与“物价消费指数”变化相适应的养老服务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通过财政投入引导老年人的有效需求释放。
(四)构建评估者“需求评估+过程评估+效果评估”全程评估机制
针对当前社会组织评估工作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评估机构独立性不强、专业化水平不高和评估结果运用不充分等问题,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估机制,既为“互联网+养老服务”健康发展提供明确导向,又为多元主体有效合作提供必要的监管与约束。
1.健全多元评估机制
第一,丰富评估内容,既要涵盖老人需求评估、养老服务供给质量评估、老人满意度评估,又要对“互联网+社区养老”扶持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政府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效益,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机制运行成效,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养老服务成效等方面进行有效评估。第二,实现评估主体多元化。改变当前“互联网+社区养老”信息平台运营商自我评估和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评估模式,搭建起“政府部门+行业协会+服务机构+服务对象及其家属+社会媒体”的多元化评估主体模式。第三,建立完整、科学、合理的考评指标体评,注重评估指标的可操作性。第四,注重评估结果的权威性。评估结果的权威性要基于评估结果的反馈与应用,不能为评估而评估,评估结果出来后向社会及时公布。政府要将评估结果作为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招投标以及退出的重要依据,通过优胜劣汰、动态管理,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及其家属的消费利益。
2.健全第三方评估机制
第三方评估是保障养老服务合作供给绩效的关键环节,是测定养老服务绩效的最为有效的监督手段,其形式通常包括独立第三方评估和委托第三方评估,即通过具有权威性的专业性中间机构或组织,由其制定一系列标准来对业内各组织进行评定,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果和报告。第三方评估作为一种必要而有效的外部制衡机制,弥补了传统的政府自我评估的缺陷,显著提高了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针对部分地方第三方评估形式化的问题,一方面要建立第三方监管准入、评估、考核、裁定等系列监管体系,规范养老市场,确保服务效益;另一方面要建立第三方评估资金保障机制,不断拓展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资金来源渠道,积极争取财政部门的支持,将第三方评估经费纳入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经费或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四、结论与展望
“互联网+社区养老”作为现代科技与养老服务有机结合的新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发挥政府机制主导作用的同时,适当地引入市场机制、社会机制和公民参与机制,力求实现全社会养老服务资源、服务方式、服务渠道的调配、整合与共享,实现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高效化、便捷化、智能化。从发展趋向看,随着新一代老年人教育水平的持续提升,以及接受新事物及运用信息技术能力的逐步增强,“互联网+社区养老”的发展与普及乃大势所趋。从发展阶段看,目前的“互联网+社区养老”模式处于从概念走向现实的探索起步阶段,虽然国家的倡导、各地的探索为推进“互联网+社区养老”打下了基础,但其成长和发展还受制于诸多条件:第一,“互联网+社区养老”模式的发展目前还处于 “零敲碎打”、“各自为政”阶段,须加强顶层设计,使其发展有立法、规划有统筹、资金有保障、管理有归口、执行有力度。第二,观念上的重硬件轻软件,重行政轻市场,重线上平台搭建轻线下服务支撑,使得“互联网+社区养老”的推广面临着诸多问题和阻碍。各相关主体对这一新模式的关注与热情差别较大,虽然政府积极推进,少数企业也踊跃进入,着力于布局其集团下养老服务产业链,但整个社会的关注度还不太集中,尤其是作为消费者的老人对这一创新模式的认可度还较为有限,市场尚未成型,观察者比参与者多,老人更愿意用实际感受、实在的成效去判断、支持和参与到这一新模式中来。当前“互联网+社区养老”的发展不可完全由政府主导推行,需坚持科学规划、先行先试、逐步扩大的建设方针。第三,“互联网+社区养老”模式的发展须秉持政府主导、政社合作、全民参与理念,合理界定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和个人在养老服务供给中的职责定位,充分激发各方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整合各方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形成相关主体有效参与、相互协作和互惠共生的合作机制,是“互联网+社区养老”模式发展的关键。
[1]毛羽 李冬玲:《基于UTAUT模型的智慧养老用户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以武汉市“一键通”为例》,《电子政务》2015年第11期,第99~106 页
[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2页
[3]夏志强付亚南:《公共服务多元主体合作供给模式的缺陷与治理》,《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39~45页
[4]吕普生:《政府主导型复合供给:纯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的可行性选择》,《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69~76页
[5][6]鲁迎春:《政府供给养老服务的动力机制研究》,《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1期,第 110~114页
Getting Rid of Operation Difficulties of Internet plus Community Pension
Qu Zhen
“Internet plus community pension” is a typical top-down government-directed pension model.The main practical dilemmas are as follows:At the provider level,“dislocation” and “absence” coexist; At the producer level,highly relying on Government support and the content of the service is single;At the consumer level,multiple pension needs and insufficient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coexist and at the assessment level,the assessment subject is not diverse enough and the assessment process has no real meaning;Building collaborative linkage mechanism of the stakeholders and arousing their enthusiasm is the feasible plan for achieving continued effective running of“Internet plus community pension”.
Internet Plus Community Pension,community governance,endowment industry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湖南省推进‘互联网+社区养老’模式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批准号:16YBA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