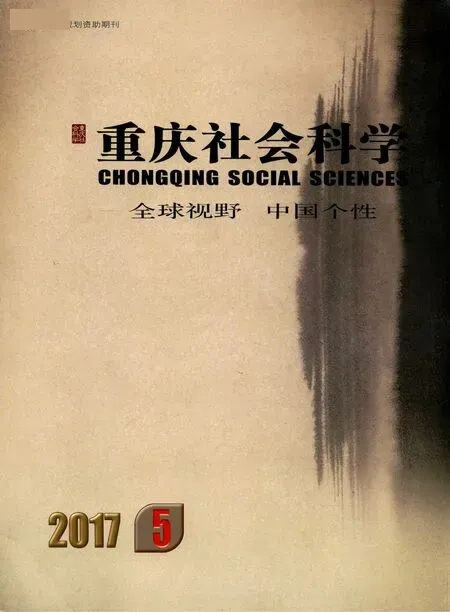手机APP与现实生活场景化
宋树萍
手机APP与现实生活场景化
宋树萍
随着手机功能的智能化发展,手机APP所带来的虚拟社会场景越来越多样化,使得手机社交场景、消费场景与现实场景之间不断融合,线上与线下的完美结合不断改善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场景。APP场景与现实场景的重合产生出新的社会场景,使得人们之间的信息传播越来越被场景化,主要包括自我意识的场景化、人际互动的场景化、群体空间的场景化。
手机APP移动互联 互联网思维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山东济南 250000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手机成为连接网络与现实的重要枢纽。移动互联时代场景变得多元化,设备变得智能化,社交变得多样化,数据变得公开化,这些变化与手机APP关联密切。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的应用功能越来越广,各种APP的出现使得手机功能几乎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几乎都可以借助手机APP来完成。手机APP的出现重构出一个虚拟的掌中世界,使得社会场景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手机软件在为用户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在影响人们头脑中对世界认知的固有场景。
一、手机APP:与手机共进退的“掌中世界”
(一)第一代模拟移动通讯手机:“大哥大”时代
摩托罗拉3200是进入我国的第一款手机,被人们称为“大哥大”。“大哥大”是手机的始祖,砖头大小的体积价格高达数万元,使得“大哥大”在当时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在那个时代,“大哥大”没有复杂的功能,只有单纯的通讯功能,恰恰就是这一功能将人与人沟通的距离缩短到拇指与按键之间,移动手机不仅改变了人际交流的时空距离,还将通话场景从室内解放出来,使得人们能够从固定的空间走到自由的空间,这一变革改变了人们对于距离的初始界定,由手机带来的“掌中世界”便从这里起源。虽然当时还没有形成各色各样的手机APP,但 “大哥大”作为一种原始手机模型为手机APP的发展提供了沃土,后来手机APP便随着手机功能的多样化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二)GSM网络时代:APP的初步发展
GSM(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是全球移动通信系统的简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2G通讯系统。1995年,爱立信生产的GH337是第一款进入中国大陆的GSM手机。2G时代的手机与“大哥大”时代相比,其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可以发送文字、图像、传真,还增加了音乐、蓝牙、闹铃、游戏、摄影摄像、收音机等具有复杂功能的APP,而且还可以连接到Internet上。手机APP在2G时代迅猛发展起来,手机的功能的翻新不断超乎人们的想象,以致每隔几年用户都想换一部新手机。手机功能的不断丰富意味着手机APP在不断发展创新,也意味着由手机带来的“掌中世界”越来越丰富多彩。随着后来3G、4G网络的发展,2017年被GSM运营商确定为关闭GSM网络的年份。随着时代的发展,落后的技术势必被新技术所取代,新技术势必带来新变革。
(三)智能手机时代:APP拼凑的“掌中世界”
从1973年库帕发明手机至今,虽仅有40多年的发展历史,但手机的功能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速度越来越快,功能越来越多,样式越来越轻巧,作用越来越大。如今随便找一款智能手机,打开手机自带的应用商店,随便搜索一个词便有相应的APP出现,手机APP涉及的功能领域之广、内容之多,似乎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霍华德·加德纳与凯蒂·戴维斯在《APP一代:网络化传播的新时代》中曾提到:“APP可以满足人们的任何需求,若有人需要一种APP,这个APP马上就会被设计出来。”[1]可以想象一下现代年轻人一天的活动:早上被手机闹铃叫醒,洗刷时间打开手机音乐;出门找“滴滴打车”,或者打开“369出行”查找公交车,或者打开地图查找路线,或者打开单车APP寻找共享单车;用餐时间打开外卖APP订餐;休息时间打开手机,或者聊天,或者游戏,或者刷资讯,或者网购,或者自拍等;晚上下班回家打开视频软件看个综艺或者网剧,跟朋友聊聊微信;连每天步行的步数都会有数据记录。手机几乎记录了人们每天的行为活动,如今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也几乎离不开手机,可以说智能手机通过各种功能的APP为人们拼凑出了一个丰富的“掌中世界”。
二、手机APP:重构的虚拟社会场景
“场景”的概念原本是指一种物理空间,后来梅罗维茨将对媒介的探讨同与地点有关的场景的探讨联系起来,提出了“作为信息系统的场景”的概念。[2]随着手机功能的智能化与多样化发展,手机APP所带来的虚拟社会场景越来越多样化,使得手机社交场景、消费场景与现实场景之间不断融合,线上与线下的完美结合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场景。
(一)“小应用”与“大世界”
手机应用程序看似只是手机页面上一个简单的图标,打开后呈献给用户的却是一个个内容丰富的“拟态世界”,这些小应用在网络与现实之间搭建起桥梁,成为一种新型的生活工具。李普曼曾提出过“拟态环境”的概念,他认为,“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了一个拟态环境”[3]。如今手机APP所提供的“拟态世界”就类似于李普曼的“拟态环境”,它以现实生活为选材,将现实中人们最常见的场景搬运到手机网络,向人们展示了全新的场景链接。手机APP的便捷化与简易化使用户的需求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满足,人们在满足于手机APP应用功能的同时,也在无形中被手机APP所带来的 “拟态世界”影响着头脑中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于是,由“小应用”所带来的场景世界,在慢慢地影响着人们的“大世界”。
(二)无形的界限与无形的场景
在电子媒介出现之前,场景通常是根据有形的地点中的行为来定义的。劳伦斯·佩尔温曾定义场景为“一个特定的地方,在大多数情况下包括特定的人、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活动”。电子媒介出现之后,“作为信息系统的场景”登上舞台,物理场景与媒介场景为人们共同提供了两种不同的交往场所与社会信息传播平台。移动互联时代,手机媒体逐渐超越PC终端成为主流媒体,手机APP的多样化将手机虚拟场景分解成众多的APP场景,不同的APP场景之间形成了一种无形的界限,这些界限看不见、摸不着,将APP场景分隔成一个个无形的场景,原有的社会场景在APP时代再一次被革新。场景不仅涵盖了物理场景、电子场景、媒介场景等,还有众多无形的手机APP场景。
(三)单一场景与多元场景
电子媒介出现之前,在印刷场景中完成阅读最好是单独一个人在一个安静的空间,书写需要在有纸、笔、书桌的特定环境,并排除其他活动。而手机互联时代,单一场景的缺陷早已被新场景所弥补,新场景不仅可以进行场景的重叠使用,还能将各个独立的场景融合到一起,包括各种APP场景之间的融合,以及网络场景与现实场景的融合。随着媒介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场景也不断地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变化。APP场景时代,场景更加丰富多彩,每一种APP都是一个无形的虚拟场景。任何使用某种APP的人都存在于手机APP场景与现实物理场景之中,而且一个人可以同时使用多种APP,例如:晚上下班回家,一边跟朋友微信聊天,一边刷着微博热门,一边听着喜爱的音乐。也就是说,人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场景中而能够运筹帷幄,单一场景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手机APP所带来的多元场景满足了人们对场景的需求欲望。
(四)业余化生产与消遣式消费
手机APP时代进一步为人们扫除了语言表达的旧障碍,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发表自由言论,职业记者、职业摄影师、职业媒体人在人人都是“自媒体”时代已不再是稀缺人才,拿起手机人人都是摄影师,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专业化生产逐渐向去专业化、业余化生产靠拢,业余化也随着手机功能的不断提高而变得专业化。手机APP所带来的这种业余化信息生产场景,使得“拟态环境”更具有可选择性与可创造性。以往的信息场景是通过专业媒体的筛选而呈现的信息环境,如今的信息场景成为受众自我选择与自我消遣的场景。丰富的信息从四面八方涌来,人们可以择其感兴趣者而阅读之,在上班路上、公交车上、沙发上、厕所里,任何场所都可以拿着手机躲在自己的手机场景中,使信息消费变成了一种消遣式消费的过程。
三、手机APP场景:新时代的新变革
(一)从线上到线下——支付场景的变革
自2015年开始,移动支付方式开始渗透到线下支付,各大商场、超市等纷纷使用支付宝或微信的扫码支付功能来辅助经营。到2017年,移动支付方式的线下支付功能已经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
支付宝APP以理财功能出身,2015年春节成功与央视春晚合作,“摇红包”功能深入人心;2016年春节的“集福”活动一推出,支付宝添加好友的功能便迅速火热起来,支付宝红包再一次红遍全国,支付宝开始身兼理财与社交两种身份;2017年春节的“扫福”活动依然是全民大行动,“蚂蚁森林”通过线下支付收集能量的应用更是成功捕获用户的好奇心。微信APP以社交功能出身,2014年下半年,微信开发出钱包功能,可以绑定银行卡,好友之间可以进行转账,后来又开发出互发红包功能,如今微信不仅仅是一个社交软件,还涵盖了工作、购物、支付、理财、阅读等多种功能。从支付宝与微信的发展来看,社交与支付成功满足了用户的使用心理,成为两大发展趋势。如今支付宝与微信的支付功能逐渐从线上转移到线下,各个超市、商店,不论店铺大小几乎都可以使用微信与支付宝进行线下转账支付,支付宝与微信支付场景的成功建立,改变了原来线下支付场景,对着二维码扫一扫,方便又快捷,不一样的支付场景给人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场景体验。
(二)自我包装与自我把关——社交场景的变革
《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6年,网民在手机端最常使用的APP是即时通信。调查显示,79.6%的网民最常使用的APP是微信;其次为QQ,占比为60.0%;淘宝、手机百度、支付宝分列第三、四、五位,占比分别为24.1%、15.3%和14.4%。[4]手机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社交环境,而且改变着人们的社交习惯。
霍华德·加德纳与凯蒂·戴维斯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表明,年轻人会精心地为自己打造一种被他人认可的、完美无暇的网上形象,手机社交媒体的虚拟性与自主选择性特点允许人们精心设计一种合适的自我形象,具体通过对个人信息进行优化处理、取长避短、刻意夸大或者完全忽略来实现。手机社交APP充分赋予人们以空间与方法来创造一个自认为心中完美的形象,将精心包装过的自我形象在手机社交媒体平台上尽情表演。手机社交APP不仅给用户提供了表演的舞台与道具,而且还给“表演者”带来观众,人们在手机社交平台上相互观看并相互回应。社会学家戈夫曼提出的著名 “戏剧理论”认为任何人在某个环境中的行为都可以分为“后区”或后台行为,以及“前台”或台上行为。在戈夫曼的理论中所指的环境为物理环境,与手机社交媒体的虚拟场景不同,但在手机社交媒体中“后区”与“前台”的说法依然适用,手机社交场景就像一个网络舞台,人们可以拿起手机站在后台来“操控”在前台表演的自己。手机社交媒体逐渐使专业化的 “把关人”形象个人化,信息呈现演变为个人对个人信息的选择与加工,与以往专业化的大众传播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手机社交媒体盛行的时代,手机社交场景不仅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工具,还是一个能够进行自我包装、自我价值实现的新场景。
(三)从手动到遥控——遥控APP改变家居场景
在物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智能家居应用是物联网技术的实际应用,人们可以通过手中的移动终端设备,实现实时家电控制,成功地将现实与虚拟融合。智能家居系统由智能控制终端、智能家电设备和智能家居网关组成,其中,智能控制终端便是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充当遥控器的作用,从当前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来看,手机终端设备是最便利、最实用的“遥控器”。
目前由手机APP遥控的家居用品已经普遍存在,例如自动遥控窗帘、手机远程遥控智能插座、手机遥控无线摄像监控、数字电视手机遥控APP、遥控智能插座灯泡、手机遥控智能热水器等,越来越多的生活用品可以实现智能遥控功能。早年麦克卢汉就曾提出过“媒介即人的延伸”的观点。他认为,任何媒介都是人的感觉和感官的扩展或延伸。而如今手机APP的遥控功能不仅延伸了人的感官系统,而且延长了人手的长度,缩短了时空距离,在户外就能随心所欲地控制家居用品。手机遥控APP改变了家居生活场景,使得现实生活在拇指间变得方便快捷,物联网时代已经到来。
四、手机APP场景:生活环境的场景化
移动互联时代人与设备的高度融合打破了常规的场景界限。梅罗维茨在其著作《消失的地域》中就曾提到:“由于接触地点的新规则,将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场景融合在一起,许多旧的行为模式开始无法维持,物质接触新规则的变化导致了新的‘中区’行为的形成。”[5]于是,新的行为模式伴随着新媒介的发展而出现,对手机和手机APP功能的依赖都是人们新行为模式的表现。APP场景与现实场景的重合产生出新的社会场景,使得人们之间的信息传播越来越被场景化,场景化的表现可以从自我、人际与群体三个不同层次来论述。
一是自我意识的场景化。自我意识的呈现是人内传播的内在表现,人内传播一般是指个人通过接收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的过程。随着信息化时代与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场景被 “刻录”到手机APP中,或者越来越多的生活场景需要手机APP的辅助,人们接触的APP时间越长、内容越多,人的自我意识就越来越被手机APP场景所改变。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其在社会化成长的过程中对世界的认知与阐释在自身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一定的框架,而手机APP的场景使用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人们头脑中认知世界的框架,人们的自我意识被逐渐场景化。
二是人际互动的场景化。手机社交APP为人际传播搭建了一个新场景,在这样一个“掌中场景”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手机社交APP将人际传播的场景转移到手机中,文字、表情、语音、图片、视频的多形式交流比面对面交流更加丰富多样。人际传播是两个个体系统组成的新的信息传播系统。在移动互联时代,人际传播不再单纯是两个个体系统之间的交流,个体与个体进行交流的过程中可以置身于多个APP场景或多个媒体场景中,不再只是两个行为主体之间的信息活动,还包括来自各个信息场景的信息传播。手机社交APP将人际传播从单一场景变为多元场景,简单的个体传播关系越来越被场景化。
三是群体空间的场景化。社会学家岩原勉将群体定义为“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属感,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杂个人的集合体”,包括家庭、学校、企业、团体等。QQ群、微信群、朋友圈等群体社交场景的建立,为群体成员构建了一个新的交流场景,在这个场景中,任何人都不会缺席,不管你身在何地,只要拿起手机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谈论与接收信息,省去了构建同一个物理空间的繁琐,缩小了群体之间的时空距离。在群体社交场景中,身体虽然不在场,但意识都会在群体公共场景中,正所谓“身体的缺场,意识的在场”,“虽然行动者的社会身份、尤其身体在某种程度上缺席了,但是,行动者的社会身份和身体又通过对自身表征的多媒体符号化实现了对网络时空的在场,这就是网络社会运动的第三种机制——行动者的“符号性在场”。[6]
[1](美)霍华德·加德纳 凯蒂·戴维斯:《APP一代:网络化科学的新时代》,李一飞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
[2][5](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7年1月
[6]苏涛:《缺席的在场:网络社会运动的时空逻辑》,《当代传播》2013 年第 1 期,第 23~26 页
Mobile Phone APP and Scenarization of Real Life
Song Shuping
With the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mobile phone functions,the virtual social scene brought by mobile application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which leading to the continuous integration among the mobile social scene,consumption scene and the realistic scene.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continues to improve and have an impact on people's life scenes.The overlapping of the APP scene and the realistic scene produces a new social scene,making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ople increasingly being scenarized,which include the scenes of self-awareness,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and group space.
Mobile phone APP,mobile interrelation,internet thin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