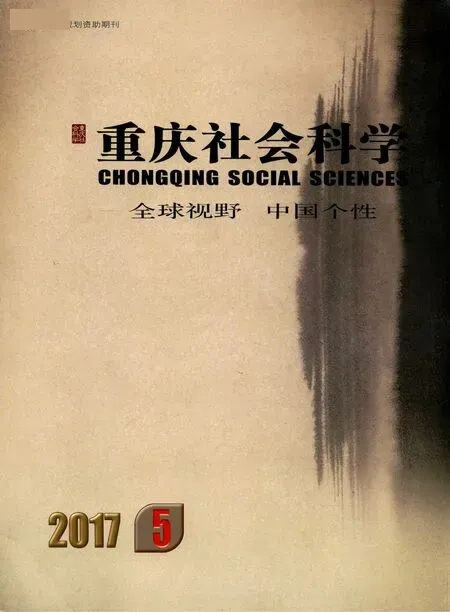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模式与实践*
方晓彤
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模式与实践*
方晓彤
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不仅是我国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关乎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全局。伴随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政策实践,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形成了多种创新性的建设模式,比较典型的有政府主导、精英引导、市场驱动等模式。这些实践模式,有效地提升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更好地满足了农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应理性地评估每种模式的价值,实现多元动力的有效组合,再造一种更有效率、更具活力的复合型文化发展模式。
农村公共文化 文化事业 文化产业
作者单位兰州城市学院商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农村文化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文化是一种以乡村社会为生成背景、以农村群众为主体的文化形式。 农村文化表达的是农民的心灵世界、人格特征及文明开化程度。长期以来,以农民为主体的自然经济、以农耕为主体的生活方式,使传统中国社会形成了“伦理型”文化特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伦理、交换原则、资本逻辑渗透到乡村社会,农村群众的文化心理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逐渐向积极、主动、进取、理性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新的“文化规范”、“文化理性”。这种文化精神,既蕴含着独立、自主、自律等主体性追求,又包含着平等、理性、民主等价值规范。在现代文明的熏陶下,农村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激荡中呈现出较为普遍的“二元结构”,即形成了进取性与保守性、开放性与封闭性、流动性与凝固性错综结合的复合体。农村文化的这种特质,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制约。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我国在农村文化建设上存在着“附属论”、“靠后论”、“代价论”等认识,导致农村文化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建设,公益性文化事业明显滞后于经营性文化产业。“附属论”是指用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功利观点来衡量文化事业,导致农村文化建设的泛商业化。“靠后论”强调经济发展之于文化建设的优先性,认为经济发展是文化建设的基础。“代价论”则认为牺牲文化建设是加快发展农村经济所必需付出的一种代价。这些认识上的偏差甚至错误,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导致精神文明建设明显滞后于物质文明建设;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则阻碍了脱贫致富的进程,形成“经济贫困”与“文化贫困”的恶性循环。特别是市场经济资本逻辑的过度张扬,引发农村公益性文化活动的萎缩,商业性文化得以大肆扩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公益性文化的社会教化责任,一些农村地区文化建设出现“逆流”。
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变迁过程。农村社会的现代化,绝不仅是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的物质富裕,还包括农村的社会进步和农民的精神富裕。推动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和文明进步,需要审视农村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和紧迫性,并将其放在“五个建设”战略格局中来考量。在“五个建设”的宏观视野下,农村社会的文化生态令人担忧:以伦理本位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逐渐消退,以感官娱乐为内容的大众文化勃然兴起,以政治认同为目的的主导文化面临挑战,农村社会呈现出多元文化混存的局面,农村文化在传统与新潮互悖的迷惘中选择。针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滞后和困局,我国将农村文化建设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进行部署,推出了一系列有关农村文化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的政策,旨在促进农村文化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公共文化建设至关重要,因为它担负着核心价值引领和公共需求满足的任务,关乎农民的文化权益保障和国家的文化整合。
二、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实践模式
在国家公共文化政策的驱动下,各地组织实施了多项文化建设工程及常设性的文化活动,扩大了公共文化服务的领域,丰富了基层公共文化的内涵,并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实践中创造出多种模式。结合各地实践经验及其主导性特征,这里从理论上将其归纳为“政府主导”、“精英引导”、“市场驱动”三种模式。
(一)“政府主导+社会协同”模式
农村公共文化是一种社会公共产品,理应由政府来提供,政府要发挥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充当起新农村文化建设领航者的角色。中央明确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任务,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把握方向,制定政策,整合力量,营造环境,切实担负起领导责任。”[1]政府拥有巨大的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民众信任资源,能够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长期以来在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设了相对完善的公共文化设施,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促进了人民群众文化权利的实现。政府主导模式,是基于政府在公共文化建设中的目标地位和职能界定,在实践中形成的一种注重政府在资金、政策、管理等方面的主导作用的文化建设模式,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政府主导文化建设,以县、乡、村文化阵地建设为基础,构建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平台。近年来,甘肃临泽县按照“完善县一级、巩固乡一级、发展村一级、延伸社一级、辐射户一级”的文化发展思路,积极进行政策规划,不断加大财政投入,改善了县级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的设施条件,加强了“三馆”的规范化建设,推动其开展经常性的群众文化服务活动。同时,着力推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建设,全县7个乡镇已全部建成高标准的乡镇综合文化站;在行政村一级,建成农家书屋71个、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村级服务点71家、村级文化体育健身广场64个。[2]目前,临泽县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已初具规模,在基层公共文化建设中,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活动中心扮演着引导者、组织者的角色。
第二,文化活动形式以政府组织的“文化下乡”活动为主。政府组织把农村短缺的、农民群众喜爱的文化内容与文化服务送到农村,包括电影、戏剧、图书、影碟、文化科技、医疗卫生信息等,也包括为农民提供文化服务的设备,如流动舞台车、流动售书车、电影放映机等。2010年,湖南澧县组织县文化局、司法局、科技局、计生局、卫生局等单位,在澧县澧南镇开展了送文化、送图书、送法律、送科技、送医疗“五下乡”活动。澧县文化局组织的澧州大鼓《查家底》、小品《包箱里的风波》以及戏曲、歌舞表演等精彩节目,受到了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澧县图书馆为农家书屋和农民群众赠送的图书、图书借阅卡受到了群众的好评。通过“五下乡”活动,农民群众文化、科学、卫生、法律素质得到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生活质量得到提高。①《澧县县委、县政府组织文化下乡惠民演出活动》,http://www.hnqyg.com/a/zh/2010/0611/1065.html,2010-06-11。
第三,社会参与多以社区、村组、社团、自然人等为主体,形成一定的社会文化网络。采取由政府牵头主办文化活动、文化项目,社会各单位积极承办的形式,集结各方面的力量和优势配合政府办好农村文化。在公共文化建设中,深圳市宝安区制定了扶持和促进社会文化组织发展的政策,对活力强、影响大的优秀社会文化组织和民间文艺团体,在文化项目开发和文艺精品生产等方面给予资助和奖励,充分调动社会办文化的积极性。政府主导下的乡村“文化大院”是这一模式的创新形式。内蒙古九原区从2003年开始“文化大院”创建以来,已有“歌舞大院”、“剪纸大院”、“秧歌大院”等40多个基层文化户在开展活动。文化大院是以农家小院为活动场所,以每个村的文艺、文化爱好者和拥有活动设施、设备的农户为组织者和参与者,自发组成的文化社团。他们利用农闲时间,经常开展文化活动。文化大院积极鼓励支持广大农民以自己的庭院为阵地,就地参与庭院文化建设,就地享受文化生活,最大限度拉近文化与农民群众的距离,使广大农民既成为庭院文化的参与者,又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使农民群众真正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人。[3]
(二)“精英引导+社团推动”模式
社会学理论表明,无论是野蛮社会,还是文明社会,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精英和民众两个群体,他们在意识、能力、权力与价值追求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在我国农村社会,乡村精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群体。乡村精英是那些在乡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方面具有较高地位,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和社会威望,能够对乡村的事务和发展有一定支配能力的人。就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而言,散布于广大农村的“民间艺人”和“文化能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其艺术养分直接来自于农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相通性,在民间文化的传承和新农村文化建设中起着骨干和桥梁作用。这种以“民间艺人”和“文化能人”等乡村精英主导农村文化发展主流、社区整合民间资源为基础的农村文化发展模式,可称为“精英引导”模式,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第一,乡村精英协同、主导农村文化的发展走向。乡村精英在文化发展方向的确定、文化重大决策的启动和文化活动的策划等方面发挥着规范、引导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精英体现的是农村文化特质中代表社区、村落主流文化的先进因子,农村文化精英人物是农村文化的传播者和倡导者。湖北宜昌三峡地区有个民间说唱艺人刘德方,能讲400多个民间故事,会唱几十首山歌民调,会表演一批花鼓戏和皮影戏剧目,会唱多部长篇丧鼓词,被专家评价为“目前三峡地区最具活力的民间故事家和民间艺术家”。为发挥民间艺人在文化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当地成立了“刘德方民间艺术团”,开展经常性的民间文学演唱活动,并在活动中关注农民文化骨干的挖掘和培养,培养了新一代民间文化传承人。[4]
第二,文化建设突出民间文化的传承和乡土特色的发扬。在陕甘地区的自乐班中,出现了一批农村文化的带头人。这些热心民间文艺活动的中老年人,腾出自己的房子,作为文艺活动场所,集资“凑份子”购买演出服装、道具,长年举办活动,农民活动农民办,用市场运作手段来办,使农村文艺活动富有生命力。在陕西眉县青化乡,当地村民集资组建了“大秦战鼓社”等自乐班组织,这种组织“小型多样”,活动以戏曲、歌舞、社火、快板等为主,农闲时自娱自乐,节庆日在周边村镇表演,很受群众欢迎。浙江开化县华埠镇注重挖掘民间文化,把已经失传和面临失传的民间表演艺术,如锣鼓队、秧歌舞、腰鼓舞、旱船、布龙、竹马舞等通过整理和恢复全部展现出来,保持了文化建设的乡土特色,促进了民间文化的多样性发展。甘肃河西地区到处都有农民自发组织的剧团、戏社并常年活动在乡村,使传统的民间文化得到传承。位于临夏、甘南交界处的莲花山民间花儿会,由于民间精英自觉组织,规模一年超过一年,吸引周边数万农民前来参加,活跃了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兰州市永登县苦水的“高高跷”社火享有盛名,当地青年农民每年都筹划组织 “高高跷”社火表演,使这种民间技艺得以发扬和传承。[5]
第三,政府适度的引导和扶持发挥着重要作用。山东省昌邑市不断加大对基层文艺组织的扶持力度,注重提高农村各类文艺骨干的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极大地满足了农村群众不同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目前该市85%的村(社区)拥有文艺队伍,庄户剧团、秧歌队、合唱团等群众性文化团体总数达500余支,农村文化能人300余人,每年自发演出达1万余场。全市乡村形成文明和谐的社会新风尚。[6]山东省临清市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中,注重挖掘乡土文艺人才的潜力和乡村独特的文化底蕴。通过政策帮扶,指导部分村庄成立了京剧戏迷协会、文艺俱乐部、农民诗书画协会等民间组织,利用农闲开展书画展示、文艺节目创作、文艺汇演等一系列活动。为给乡土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们结合村庄文化大院建设,将小广场、小戏台等文体设施纳入政府文化设施建设之列。①《临清民间艺人扛起文化龙头》,http://www.lcxw.cn/news/liaocheng/xianyu/20120824/253113.html,2012-08-24。同时,通过举办乡土人才培训班、文艺工作者下乡指导等形式,鼓励农民以身边人、身边事为素材,创作演出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讴歌农村变化,教育感化群众。
(三)“市场驱动+村企共建”模式
公共服务市场化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核心主题,其基本思路是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将原由政府承担的部分公共职能推向市场,通过充分发挥市场优化配置公共资源的作用,达到改善和提升公共服务的目的。适应公共文化建设的需要,我国一些地方政府逐渐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维中跳出来,尝试通过市场机制为文化建设募集资金、资源并创新其运作方式,“文企联办”、“公办民营”等市场化的运作模式逐渐发展起来。吉林长春市采取文企联办、民办公助、公办民营等方式,引导国有企业和民营资本积极参与到文化活动中。福建省长乐市积极探索文企联办、市场运作的文化建设路子,探索以民间资本“入股”方式发展农村公共文化,从而形成了形式多样的“民资文化”格局。概括而言,“市场驱动”模式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第一,依托企业投资和集体投资,创新文化投入机制。一是依托当地大型企业和企业集群兴办农村文化。由于筹资渠道便利,此类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具有规模大、设施全、层次高等特点,多集中在城郊和开发区的周边,基本形成了文化生态园区,以河北省武安市东山文化公园和霸州市王疙瘩村的农民公园为典型。公园内设有剧场、图书室、各类球场、农民健身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等,各类文体活动常年不断,且活动内容较为丰富,村民们可以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体生活。二是依靠集体力量投资农村文化建设。这一类型主要集中在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以河北省辛集市的都大营村、新垒头村为典型。都大营村投资60万元建设的村民文化活动中心,每天都有村民舞会和文体活动,周围十里八乡的农民都来这里参加活动,成了当地一大亮点。文化活动还成了村“两委”与村民沟通村情、共谋发展的有效载体。[7]
第二,尝试市场化运作,创新公益文化运营模式。文化事业的繁荣离不开市场,也要在市场中找到自身的适当位置和生长点。目前,文化事业单位改革试点中的一些市场化运作,已经取得骄人的成绩,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就是一个予人启发的例子。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自1996年以来,摆脱了长期以来束缚文化馆发展的桎梏和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经营观念,经历了馆长聘任、全员聘任,引进机制、改变格局,开放办馆、多元发展等三个阶段,进入到全面建设现代化文化馆的新阶段。①《略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http://www.ccmedu.com/bbs4_4573.html。兰州市在2005年举行了第三届文化项目推介会,把兰州各类文化活动和建设项目面向社会整体推介,为企业和社会各界关注文化、参与文化建设搭建服务平台,借助市场机制对城乡文化资源进行整合运作,为构建高层次的“文化圈”提供了动力支持。通过市场化运作和创新公益文化运营模式,项目推介会成为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生产主体、发展资金、消费受众等各种要素整合配置的基础平台。
第三,政府创造环境,为“民资文化”发展助力。将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起来,在坚持公益性前提的情况下实现有限的市场化,是公共文化建设的路径之一。政府需要适应这一发展要求,出台推动“民资文化”健康发展的相关政策,在企业赞助、社会赠与、社会投资等方面,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在文化活动场地、场所的建设用地等方面,给予相应的灵活政策;在农村文化骨干人才的培养和专门人才的文化支农方面,提供相应的扶持政策。2002年以来,福建省长乐市投资建成人民会堂、博物馆、图书文献中心、金源科技大厦、广播电视中心、新华书店、会堂广场等多处基础设施,为民资文化实体创造环境,提供演出的舞台。每天清晨和傍晚,人民会堂广场、南山公园、郑和公园周边地区,遍布数十个大小不等的扇子舞、彩带舞、民俗舞方阵,都充满欢声笑语。同时,该市还坚持为民资实体“充电”、为书屋送图书、为放映队送电影拷贝、为演出户送精品小戏等活动。[8]
三、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模式的检视与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经济、社会变迁的过程伴随着传统文化的扬弃、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孕育和形成。在这一社会转型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时期,坚持文化秩序建构的社会主义方向,全面推进具有全民性和健康文化价值导向性的公共文化建设是必然的选择。然而,考察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的态势,农村文化发展滞后是一个典型问题,尤其是公共文化建设更是滞后,存在着三个“不适应”:与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不适应,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不适应,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不适应。
近年来,在国家文化政策的驱动下,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并探索形成了一些创新模式,有效地提高了当地公共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更好地保障了农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了农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但如果过分强调这些实践模式的纯粹性,往往又会使其自身缺陷得以放大:政府主导模式如果过分强调政府的主导地位,就可能忽略农村文化建设的主体——农民的文化权益和文化需求;精英引导模式如果过分依赖于少数精英人物,就可能漠视民众作为农村文化建设主体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民众在文化建设和文化生活中的选择权、参与权和创造权,不符合现代文化民主化发展的趋势;市场驱动模式如果过度渲染市场化的发展取向,过度张扬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可能导致文化发展的商业思维和文化商业化的泛滥,削弱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性和社会公益性特征,就可能对人文精神和文化品位构成潜在威胁。
新农村公共文化的发展繁荣,需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通过文化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综合多种文化发展要素,吸纳各种发展模式优势,实现多元发展动力的有效组合和良性互动。[9]
为此,需要在借鉴吸纳各种实践模式优点的基础上,探索一种更富活力、更有效率的文化发展模式,这种新型的公共文化发展模式应该注重以下方面:一是明确文化发展的基本宗旨,将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包括享受权、参与权、选择权、创造权等)作为公共文化发展的基本目标;尊重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话语权”,使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植根于民众,发挥民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二是发挥政府在促进“文化民生”与“文化民主”中的关键性作用,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辩证统一,切实履行政府的文化管理与文化服务职能,通过战略规划、政策支持和舆论引导,保证社会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维护社会文化秩序,优化社会文化生态。三是发挥文化精英在艺术创作、文化创新等方面的作用,鼓励专业文艺工作者深入农村基层体验农村生活,鼓励他们创作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改善民间艺人生存与发展环境,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壮大民间文艺团体,发挥它们在优秀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创新、公共文化的生产供给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四是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实现文化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确立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利用市场的竞争激励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形成规范有序的竞争网络,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在此过程中,应强化政府对市场化的管理能力,增强政府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管理责任,保持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伦理意义。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人民日报》2006年1月13日
[2]马钰良:《临泽逐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张掖日报》2012年6月19日
[3]阿勒得尔图:《包头市九原区引导扶持文化大院建设》,《中国文化报》2010年5月19日
[4][5]黄永林:《要重视民间文化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光明日报》2006年5月15日
[6]代选庆 李生涛 李洪帅:《昌邑民生为本谱写文明和谐乐章》,《潍坊日报》2012年1月29日
[7]聂辰席:《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新模式——河北省发展“民资文化”的调查》,《党建》2007年第8期,第 38~39页
[8]蔡小伟余荣华:《小城大“文”章——福建长乐公共文化建设纪事》,《人民日报》2007年7月22日
[9]金民卿:《构建多种文化发展模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8日
Model and Practice of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Fang Xiaoto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is not only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but also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new rural construction,which is related to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rural social modernization.In the process of policy practice on rural public cultural construction,some places explore various innovative construction model,more typical model including government led,elite guidance,market driven model.These practices have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grass-root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and better meet the diverse cultural needs of the farmers.We should rationally evaluate the value of each model;realize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multiple forces,and rebuild a more efficient,more dynamic compound pattern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rural public culture,cultural undertakings,culture industry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北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批准号:11XZZ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