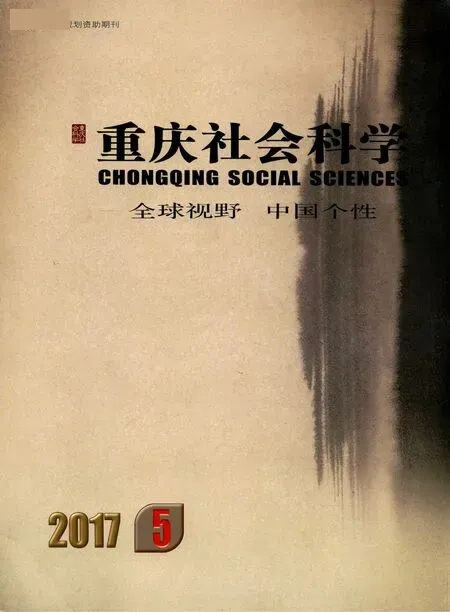空间结构、时间叙事与乡村生活变迁
房静静 袁同凯
空间结构、时间叙事与乡村生活变迁
房静静 袁同凯
空间与时间作为民众生活的基础,记录、规约、承载、驱动着人的活动。以古村落的空间演变为例,从不同的空间格局中去描述时间叙事在空间中的排列。一方面意在确定空间结构要素对行为产生影响而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试图表明在不同的空间演变状况下,时间作为一种社会建构,得到了截然不同的构想。“时间焦虑”、“时间慌”、“乡村记忆”、“乡愁情结”并不仅仅是因为社会的快速变革所引起的文化恐慌,而是面临社会转型所引起的群体心理失衡。
新型城镇化 社会变革 社会治理创新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天津 300350
20世纪80年代,空间与时间被纳入社会分析的中心。关于空间的研究理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空间与社会关系、空间与社会结构、空间与社会意义。社会结构与社会意义在“空间”中互动,确立了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并使之具体化。由此,空间性将社会生活置于一个活跃的竞技场中。然而,时间是多维的,这种多维的深刻性在于勾连各种观念或文化的时间共存在同一时空场合中,从而造成了现实表达与呈现的复杂化。“空间”与“时间”的关系问题骤然“升温”,并成为构建和评判社会的重要维度。如在现象学中,“空间性”与“时间性”的概念意指空间与时间对主体来说何以成为空间或时间。我国传统社会的基础是乡土社会,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村庄的自然空间有着明确的边界及较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多以农为生,聚族而居,在这一空间中生活的人们的时间建构多与主体日常生活体验不可分离。当时代的变迁在不经意间将传统社会链条打断时,社会就会发生深刻的空间转换,改变的政治—经济实践和文化实践决定了时空领域内人们社会互动模式的性质。因此,我们在了解社会如何建构其空间时,实际上也在了解其如何建构其时间观。
一、空间结构与时间:理论谱系
(一)关于“空间结构”的理论阐释
空间要素在古典社会学家的分析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中,土地作为一种具体的空间形态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工具和结果,并且凭借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开拓了世界市场,让整个世界卷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中。[1]涂尔干则认为:“图腾崇拜和宗教仪式中的空间安排折射出主导性的社会组织模式。”[2]这种关于空间实质是“物质”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后来学者对空间结构的分析。如现代社会学中,戈夫曼使用“前台”、“后台”、“局外区域”等一系列概念,来探讨空间区域的制度化特征,并开启了研究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互动关系的先河。[3]关于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互动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布迪厄的 “场域—惯习”理论、吉登斯的“时空压缩理论”、爱德华·索贾的 “社会空间辩证理论”。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将整个世界划分为无数的小世界,每一个小世界即场域中均有自己独特的实践逻辑,场域中的社会成员秉持着与之相适应的惯习。[4]吉登斯在解读结构以及结构和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时,实现了对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融入,并把时间和空间放在社会结构的终极性要素的位置上。[5]而爱德华·索贾的“社会空间辩证理论”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们创造和改变着社会空间,二是他们也被自己所生活和工作的空间以不同的方式所支配。但是空间结构不仅仅是社会行动表现自身的竞技场,且是带有各种目的或所谓的“计划”的目的性存在。
在此基础上,这里将空间结构划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以“再生产”为目的的空间结构,以列斐伏尔为代表。他认为:“社会生产关系仅就其在空间中存在而言才具有社会存在;社会生产关系在生产空间的同时将自身投射到空间中,将自身铭刻进空间。否则,社会生产关系就仍然停留在‘纯粹的’抽象中,也就是在表象和意识形态中。”[6]索贾则提出:“空间是由社会生产的,而且如同社会本身一样,既以各种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形式存在,也以个体与群体两者之间的一套关系,即社会生活本身的一种具体化与媒质而存在。”[7]因此,空间结构和空间关系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物质形式,整个社会生产出了一个空间,在空间中,生产关系的维持变得具有决定性,而技术和生产力则达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水平。空间性、社会再生产、生产关系的相互关联成为“空间结构”建构的核心。
二是以秩序、纪律等权力分配为目的的空间结构,以福柯为代表。他认为:“一种完整的历史,需要描述诸种空间,因为各种空间同时又是各种权力的历史。”福柯从空间中发现了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提出了一种关于“权力运作基础的空间”,即“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8]。他在紧抱历史的同时,给历史增添了关键性的联结,即空间、权力和知识之间的联系,由此,它们一起构成了空间结构的具体方面。
三是从个体角度讨论空间结构,以梅洛·庞蒂和海德格尔的思想为哲学基础的战后现象学场所论,针对工业化和都市化所造成的空间异化进行了批判,它所关注的是日常生活空间形式的一部分。在现象学派的视野里,现代主义空间观把空间当作社会变革的手段,而人被当成被动的存在者。如梅洛·庞蒂构想了一个关于身体、世界、知觉、时间、空间的相当复杂的协同构造进程,即“身体图型”,并将其解释为一种管理、协调和支配身体与空间交互构造的运作机制。[9]这可看作一种对空间异化的回应,但他采用“隐喻的身体”来探索日益复杂和分化的世界。
总之,空间结构既产生于空间的再生产,同时又是权力、知识、日常实践活动等诸种结合体的具体表达,且是具有交互作用的各种因素和影响的一种历史整体,即“有组织的空间结构,并不是一种独立结构,有其自身自主的构建和转型法则,它表征了各种一般生产关系的一种业已得到辩证解释的成分”[10]。
(二)关于“时间”的理论阐释
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文献中仍然缺少对时间的关注,原因就在于社会学所强调的是秩序、稳定和状态问题,而忽视了冲突、变迁和过程的问题。关于“时间”的研究可归纳为三个方面:时间内涵、时间意义、时间分类。
一是时间内涵。古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最先强调“时间”是一种集体现象,并把它看作集体意识的产物,是集体表征的主题。[11]而埃利亚斯将“时间”定义为表示某种关系的符号,由人群,亦即一群具有记忆和综合的现成生物性能力的生物,在两个或数个事件过程之间所成立的关系,而其中一个过程则标准化成另一个事件过程的参考框架或基准。[12]休伯特则把“时间”界定为一种象征结构,这种结构通过时间的节奏来再现社会组织。[13]可见,对时间概念的表达无论是持续时间,还是对时间的标记,都是关于社会活动或者集体的成就。在此基础上,现代社会学转向从社会意义上对时间进行划分,并在反思中提出了诸如 “社会时间”、“时间观”等相关意涵。
二是时间意义。爱德华·索贾指出:“个体能理解自己的经验,而且只有通过对自己所处历史时期的定位来判定自己的命运,即只有通过对自己环境中所有其他个体的认识,他才能把握自己在人生中的各种机遇。”[14]刘易斯·科塞则提出时间研究旨趣在于:“当我们在社交聚会上讲述过去的事情时,会把那些事件置于社会背景中。因为相关事件只有被置于社会时间而不是纯粹的历法时间之中才能获得意义。”[15]其实,对时间意义的表达无法与社会活动发生的空间相分离,而将现象或事件放置于一种时间序列,对每一位理论家来说变得更具有意味和更能说明问题。然而,“时间意义”本身可能微不足道,各种时间在社会中的划分则构成了一组刺激物,推动我们在时间中前行。
三是时间分类。古尔维奇将个体的、群体的和文化的层次当作社会结构理论的最普遍区分,并把这种区分作为社会时间类型学的出发点,由此区分了社会时间的三种形态:自我时间、互动时间和循环时间。[16]对社会时间多重性的划分表明了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中诸要素之间的因果联系。史坦利·柯恩则将时间分为“私人时间”和“社会时间”。如在前工业时代,几乎所有工匠都自己经营生意,在他们自己家里,用自己的工具,根据自己的时间,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完成自己的工作;工业化的到来,则造成了工作时间的刚性化。时间由松散而多变的模式开始转向时间安排紧凑。[17]因此,时间开始变成有价值的东西,并获得了一种商品的意向。时间的商品化意向则又进一步促使人们从“时间观”方面来反思时间,如罗斯·科塞认为时间观是一个社会中各种价值观的整合部分,个体要根据与其共享价值观的群体来确定现在和未来的行动方向。
概而言之,时间以社会学的建构将自己表征为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具体化存在,并被置于社会互动过程中,作为建构人社会意义的另一种形式和每一社会中制度和组织的组成部分。但我们从中获得的启示在于社会学的时间研究所强调的是社会事件、社会变迁、社会进程与时间的复杂动态关系,以及社会生活在时间的演进过程中,以什么样的生产方式来表现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三)“空间”与“时间”的关系
通过对空间结构和时间的解读可以发现,空间与时间在社会中一起运作,并与社会再生产的过程相关联,然而任何过程都可以视为一种历史性过程,都是在时间流中展开的社会呈现,即社会是由时间、空间和社会行动三个基本向度组成的复合体。涂尔干指出,“空间和时间都是社会构造”;在此基础上,不同的社会产生性质不同的时空观。而时空独特的表现形式会引导时空实践,时空实践反过来又会维护社会秩序。[18]如在再生产意义的空间结构里,生产关系和生产时间变得具有决定性,并以生产时间体制的形式映射到空间形式和空间战略中,成为资本积累的积极要素;而在权力分配的空间结构里,时间是以一种使人的行动和计划的合理性成为可能的机制而发挥作用,并与社会制度的理性化相结合,成为植根于社会的一种同质的、连续的时空观。当从个体意义上来理解时空观时,我们意在通过个体对日常生活的重要时刻、微观层面个体生命历程的时间表达,来探讨空间结构所传达的社会、文化价值。总之,一个社会空间结构的分配,表明了不同的角色、行为的范围和这个社会秩序下的权力路径;而作出不同的社会行为和不同的关联方式的时间和地点,则传达了清晰的社会信息。可见,每个社会结构都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社会再生产的目标,来建构关于时空的客观概念,并根据那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下面以山东雄崖所村为例,分析其空间结构与时间秩序的再造方式。
二、空间演变与时间叙事:以雄崖所古村落为例
空间是通过物来彰显其自身的存在的,没有物或物质,空间就无从具体化。以山东海防古村落雄崖所为出发点,源于其空间形态经过三次空间实践,呈现三个层次的意象:一是“守御千户所”,即明清军事防御占支配地位时期的特色建筑和庙宇,二是历史转变层面的改造和建设的空间,三是古村落保护战略空间。以古村落的空间演变为例,从不同的空间格局中去描述时间叙事在空间中的排列,意在确定空间结构要素对行为产生影响而使之发生改变。
(一)军事防御空间与时间叙事
明代防卫海疆的主要措施是在沿海府州县和沿海重要之地建卫、所,筑城堡、墩台,守以重兵。“雄崖守御千户所”的设立就是在这个大格局下应运而生的。城设四门,并于沿海一线设立椴村、王骞、王家山、公平山、望山、青山、米粟山、北渐山、陷牛山、朱皋、白马岛共11座烽火墩堡。[19]城门、烽火墩堡是具有特色的空间要素,其军事特性贯穿并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得当时的社会生活有组织地进入支配与服从、中心与边缘的多层结构中。据《即墨县志》载:“雄崖守御千户所设正千户两员,副千户两员,百户五员,吏目一员。共有京操军春戍250名、秋戍319名,守城军51名,屯田军77名。”[20]此时明朝对“卫所”采取的是“屯田制”和“军户世袭制”政策。仿照历史上的屯田制,雄崖守御千户所又于沿海分设八个军屯,由屯田军驻防;而屯田是朝廷分封给千户和百户的,由他们驻领,皆为世袭;屯田则分配给军户耕种。军屯中的每位军士授田五十亩,称为一份。耕种临近所城土地的军户,还兼有守城的职责,他们三分守城,七分种地。清雍正十二年,雄崖所裁并归即墨县,屯田归公,原来的军户成了民户,就地居住,分给土地耕种。[21]
土地作为空间的重要作用开始显现,农业生产对土地的依附和农耕制度的年度周期制约使民户的生存空间相对固定在一定区域。在特定的时空制度下,“卫所”职能逐渐转变,使得聚落住民由先前基于军事目的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步向普通的大众化生产生活方式转变,聚落内部也相应出现了更多世俗功能的建筑和设施。据记载,雄崖所城内外共有庙宇13座,其中,城内有关帝庙、天齐庙、观音殿、城隍庙、三官庙、先农坛、九神庙。而这些庙宇以其独特的象征意蕴,映射了空间中人们的时间感。如三官庙,殿内有天官、地官、水官。相传,天官能赐福,地官能赦罪,水官能解厄。在天旱时,人们到三官庙求雨,三官因与百姓荣辱祸福密切相关,备受崇拜。先农坛则供奉着先农、司农、司蔷,正月十一逢会,人们燃纸烧香,磕头膜拜,祈求丰年。九神庙作用则在于每遇洪涝、旱灾、病疫,人们前来祭祀,祈求消灾祛难。[22]在调研过程中,据一位87岁的老人讲,“这些庙宇在当年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早晨和晚间的钟声、鼓声、诵经声朗朗入耳,逢年过节灯火通明、香烟缭绕”。
杨庆堃指出:“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寺院、祠堂和拜神的地方,寺院、神坛散落于各处,举目皆是,表明宗教在中国社会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他们代表了一个社会实在的象征。”[23]而笔者通过对军事防御空间生成机制的串联,发现在由“军户”沿革为“村民”的过程中,个体自我时间被嵌入在一种超验的时间之中,人们在心理上更多地是依靠神灵来舒缓心中紧张。在与传统农业生活的不断磨合中,形成表达独特地方化意义的生产时间、作息时间,“以农为本”、农事节律成为时间安排的轴心。
(二)改造建设空间与时间叙事
1960年,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明确指出:以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所有,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这样,绝大部分土地无偿转归为生产大队所有,由生产大队统一使用,少量归公社一级所有,生产小队没有土地。据《雄崖所建置沿革志》载,1956年4月,即墨、即东两县合并为即墨县,雄崖所隶属的区、乡和人民公社名称多变。1961年,雄崖所属丰城人民公社,以城中十字大街的东西大街为界,划分成南雄崖所和北雄崖所两个行政村。[24]而原来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13座庙宇也大多被拆除,城内庙宇或被改为生产大队办公室,或成为居民住宅。可见,空间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而以“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为主题的空间构造赋予社会层面什么样的时间观呢?这里以案例进行呈现。
案例1:陆某,女,1944年生。当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忙时节,四五点钟就走,一直干到中午12点回家。你家里有老人的,有公公婆婆在家给做熟饭,你可以吃现成的,还能休息一会儿。当时我1966年12月嫁过来的时候,公公刚于一个月前去世,家里也没有婆婆,我得回来现做饭,还得照顾孩子。匆匆忙忙回来做熟吃完了,小队一吹哨,麻溜就得走,去晚了要挨罚。
案例2:黄某,女,1942年生。我们这代人基本上都有三四个孩子,即便拖着好几个孩子,为了不耽误挣工分,也设法克服困难去出工。孩子刚会走那工夫,我就把他带上,一天都不耽误的。
在访谈中,他们反复念叨的主题就是:“那会队长说了算,叫你去你不得不去”,“你要不去劳动就罚你,扣你工分”。此时,以“生产队长”为影像的时间观描绘了“先集体、后个人”的时间安排策略。然而,这种强有力的时间结构,是由当时政府确定并支配的时间体系所构建的,且空间结构在制度安排上配合了这种时间政治。因此,时间作为一种社会建构,被社会制度、社会习惯和人际互动所巩固,并形成体制。
(三)生态保护空间与时间叙事
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土地开始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号角吹响中国大地。1982年国家公布首批24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986年,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提到了保护“历史村落”的概念。雄崖所古城被青岛市人民政府命名为 “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成为山东省仅有的两处之一。而城内各种庙宇,如观音殿、玉皇庙开始重修。伴随现代化进程,曾经被视为封建迷信而遭到批判的民间信仰仪式也一度参与到国家活动中,调研中一份关于“雄崖所古城玉皇庙会”的宣传单显示其主办单位为丰城镇人民政府,承办单位为雄崖所村民委员会。上边标有:“玉皇帝赐福:吉祥如意;凡捐资贰千元以上者均赠玉皇庙开光金如意宝葫芦壹尊。”同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乡村工业渐趋渗入古村。据调查,村里现有项链厂、个人养猪场、海参养殖场等,农业劳动者变成了工人。在此过程中,这种由工业发展而导致的群体性时间较之以往发生很大改变,我们仍以相关案例为证。
案例3:韩某,女,1964年生。1986年结婚,1987年我生完第一个孩子后,在家里边绣花(一种手工活)边看孩子,孩子照顾得无微不至;90年代,1994年左右,给别人养鱼,别人给工钱,一年给千儿八百的;1997年生完第二个孩子后,就把孩子放在家里,去厂子干活了,主要是去当时的冷库;干到2003年,孩子六岁的时候,孩子的姥姥说孩子自己待在家,万一出点事咋办,得好好照顾小孩。于是开始在家做手工零工,挂项链的勾子,一年赚3700~3800元,干了两年。后来去城里陆续做保姆,在村里项链厂上班,现在在镇上一家纺织品厂,每天早上6∶50走,晚上有时候加班到9点。
案例4:李某,男,1963年生,瓦匠。1985年在邻村做工的时候认识了现在的媳妇,女方家不愿意,嫌我家穷。我俩去东北干了一年烧瓦,赚了2000多元,回来后给丈人家送去聘礼才结了婚。结婚后,一直干瓦匠,胶州、崂山、即墨,足迹遍青岛各地。时间主要集中在干活上,每天差不多赚200~300元。为儿子在即墨买了房子,娶妻生子。
在访谈中,韩某一直讲,“要不是因为自己小女儿在上大学,我才不去干这份工呢,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到村里厂子上班,虽然钱少一点,但是起码中午和下午还有一个小时可以回家来,现在这个时间太赶了”。李某常说的是,“一天不干,少赚300元”。可见,时间在此已经获得了一种商品的意象,并被感知为确定的时间间隔;而工业生产的时间结构急需时间的这种线性模式,于是人们开始寻求遭遇工业时间的同时,保持私人主观时间的可能性。
大卫·哈维认为:“我们可以主张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概念必须通过物质实践与过程创造出来,而这些实践与过程再生产了社会生活,时间与空间不能脱离社会行为来理解。”[25]因此,我们对古村落的研究不应仅仅关注其空间演变的特征,还应致力于探究空间构造对不同类型时间的建构,即带有不同目的的空间结构对时间的生产、管制和规训。就社会背景来说,上述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主体之间的互动构成了时间的意义。然而,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空间结构与时间设置是最能体现人类本质特征的符号表述。我们可以透过时间叙事来理解社会的运作、国家的权力实践以及意识形态的推广;反过来,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亦能很好地认识时间本身及其变迁。
三、古村落的社会时间变迁
就空间而言,雄崖所古村落经历了由军事防御为目的到以改造建设为主,最后重新实现“回归乡土记忆”的空间实践;而从时间来看,村落空间同样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时间,像空间一样,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深刻的过程或结构。而人类生活是与作为一种在象征的意义上形成的环境而获得意义的自然和符号实在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唯有将时间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群体生活习惯等社会性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刻理解乡土社会的变迁。这里从主体—自我时间、互动—组织时间、私人—工业时间三个角度来分析。
第一,主体—自我时间。梅洛·庞蒂认为:“我的身体拥有时间,它使一个过去和一个将来为一个现在而存在,它不是一个物体,它创造时间而不是承受时间。因此每一个身体都有它自己的时间,有它的节奏和周期,通过这种运动和行为,它又把这种时间性扩散到围绕在它周围的知觉场中。”[26]海德格尔则指出:“出现在孤独的自我体验当中的时间,可称为自我时间。它是以被记起的过去、被体验的现在和被想象的未来这种形态而投射在存在之上;所以一个人所具有的体验的类型,它们的时间上的接近,以及它们立体的形态确保每个人的自我时间感是独特的。”[27]在雄崖所最初的军事防御空间中,居民由军户转变为民户,人们在特定的环境中形成了自身的日常惯习,如根据农事进程从事社交、信仰等社会活动,感知大自然周期对生存的意义,与祖先发生情感与精神上的关联。自我的这些实践和观念渐形成了一系列地方性时间机制,进而建构出村落的民俗、岁时、节日、仪式等时间概念。总体来说,传统乡村民众时间是以主体—自我时间为主,此时的时间是特定社会中的人们创制出来的时间。
第二,互动—组织时间。社会时间的一个关键的结构特征在于所有社会行动都是在时间上顺应更大的社会行动;因此,不仅自我时间被嵌入到互动时间结构之内,而且二者又被嵌入到社会制度的宏观层次的时间秩序之中。此时的社会时间被解释为在互动过程中建构起来的人的意义的另一种形式,是每一社会中的制度和组织的组成部分。[28]在雄崖所改造建设的空间中,个人劳动时间、休息时间被“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机制协调组织起来,个人劳动价值被生产小队长以“工分”的形式给出特定评价和赋予意义;在我们描述的这种时间之中,制度组织时间是完全优先于个体时间的。上述“黄某谈到回家吃完饭,队长一吹哨,就得麻溜走”,可见占据权力位置的人把自身确立为时间资源的控制者。但是当组织对时间的规训使社会成员感到压力时,必然引起人们迫切想摆脱现实权威的宰制的愿望,由此来自日常制度时间的变革势在必行。
第三,私人—工业时间。工业化的到来,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工作时间的刚性化。即在工业社会,职业规划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机器体系的速度所支配的。劳动被按区域大量而精细地分布在空间和时间之中,并且要求根据预先确定的时间间隔来对活动进行一种小心翼翼的协调,而且会把机器时间越来越细的限制强加给人们。因此,根据把时间当作商品的现代观念,工作时间虽被视作私人时间的一部分,但因雇主购买了雇员的时间,从而把它转变成了工业时间。[29]雄崖所最后过渡到古村落保护空间,但是工业力量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结构,深刻影响着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如今的古村落,人与土地之间的自然乡土关系已渐渐疏离,经济链接方式渗入肌理。村中除了老人还心系土地,遵循着传统的农业生态时间,青壮年劳力的时间安排已与自然现象没有什么关系,一种高度精确化的工业时间笼罩在具体时空中。正如索罗金所言,“人类生活原本就是通过带有自身的动机和目的的不同活动来竞争时间的过程”[30]。
因此,在不同的空间演变状况下,时间作为一种社会建构,一种用于定位的符号手段,得到了截然不同的构想。阿尔都塞指出,每一个结构层面可能包含不同的历史时间。我们应该赋予每一层一个特定的时间,即相对自主、相对独立于其他层面的时间。[31]然而,每一个结构层面同时还拥有特定的地理空间,在以下论述中笔者将围绕空间结构的不同层面来探讨与时间的关系。
四、时间变迁的空间结构要素分析
(一)空间文化与时间
黄应贵指出,空间应该被视为文化习惯,包括文化的分类观念与个人的实践。他还强调,不同空间建构是由人的活动与物质基础的相互结合运作的结果。文化在空间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指,文化是空间变迁中的重要建构力量。当空间被赋予某种文化意义时,便会有特别的象征意义。[32]时间是人们最为平凡和显著的日常生活特征。要了解一个文化如何建构其历史时,不可能不先了解它们如何建构他们的时间观念。戈夫曼曾将日常比作剧场,方法是观察在这个空间里人们时间上的表演。他因此认为,“任何个体都身处多重时空中。”[33]笔者通过雄崖所空间的转换,展示了不同的时间价值。最初人们的时间价值建立在农业的再生产上,人们通过在空间中设置一些固定或临时的象征物,如庙宇,空间经由祭祀的圣化后,世俗空间转化为神圣空间,便有了仪式时间和世俗时间的划分,并由此衍生出与自然时序有关的社会活动,如农历正月初八玉皇庙祭祀、二月初二祭神、三月初九祭山仪式等。此时,时间以个体时间为主,并嵌入到超越时空界限的仪式关联上。
(二)空间权力与时间
当一个地点在一组既定的历史环境下生成时,权力关系就成为社会结构的核心。一切权力关系最终都不能够与行动和日常实践的领域相分离,不能与具体时空中对行动者直接或间接控制相分离。[34]大卫·哈维认为:“空间和时间实践在社会事物中从来都不是中立的,他们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因此,支配空间的优势始终是阶级斗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35]而笔者所述的“互动—制度时间”的一个关键性结构特征就在于国家借助权力为个人铺设了一条时间轨道,个人从这一轨道出发,形成恰当的时间表,但个人时间表的设置在时间上是顺应更大的社会行动的。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设置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化的制度,空间和时间在此都显示出不可让渡性,充分体现了国家权威。而最初之“大跃进”到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国家以“社”为基层控制单位,其根本目的在于以一种社会行动的次序,使地方社会的建构空间按照社会时间的制约,有计划地开展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对抗私有制的计划。因此,正如布里奇曼所说:“当事件性质变化时,我们用来指定某一事件发生在某一时间的方法也会发生变化。因此,时间会以不同的外观出现。”[36]
(三)空间经济与时间
列斐伏尔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划,倾向于成为空间的规划,人们现在通过生产空间来逐利。空间成为利益争夺的焦点,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生产力和产物之中。[37]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被空间所压制,并被化约为空间的界限。如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区分通常与时间的持久性有关,那些占据中心的人把自身确立为一些资源的控制者,因此时间上的领先因素已经对空间中的突出位置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38]当前我国乡村正在经历巨变,既包括物质生产方式层面,又包括社会结构层面,而最为本质的变迁则发生在时间价值体系层面。以雄崖所村为例,随着传统处境由以往 “匮乏经济”转变为“丰裕经济”,人们对金钱的欲望也由“知足”变为“不知足”。而市场通过金钱这一稀缺媒介创造了时间的紧缺,并通过所需要的工作时间与金钱的交换关系来安排时间。由此,原先与农业生产密切联系的、伸缩性强的传统时间随着生产的工业化,开始出现时间分层,即工业组织时间优先于互动时间,而互动时间又优先于主体—自我时间。人们日常生活现状也只有以节假日为标志得以调剂,且对大多数进城做工的人来说,一般不会有礼拜日,除了国庆、春节等法定假日外,他们一般被牢牢拴在岗位上。于是,在被卷入工业时间的同时,人们产生了将私人时间从工业时间中分离出来的愿望。在调研中,我们时常听到做工回来的人们对于以往“下地”回来后一起玩耍的眷恋。总之,现在时间的匮乏状态与各种时间矛盾纠结在一起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处境应该得到社会的重视。
五、结语
费孝通认为:“中国现代的社会变迁,重要的还是被社会的和技术的要素所引起的。社会的要素是指人和人的关系;技术的要素是指人和自然关系中人的一方面。”[39]即隐藏在现代性里的是空间结构的深刻构筑和时间嵌入层面的多样化。和空间一样,时间也被纳入各种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战略中,记录、规约、承载、驱动着人的活动。然而,空间因行为而兴,自然也因行为的缺失而废。时间在空间叙事中,曾依赖于一系列象征物、符号、仪式行为,表述意义、展现价值、表达情感。但在现代社会,随着人们工作日程安排加快,以及城镇化的加速,人们的时间日趋被国家经济的结构性变化所改造。时间的文化价值虽然很久以前已被写就,但是面对社会变迁,其意义究竟栖居何处值得思考。毕竟,现代人对时间的追忆,“时间焦虑”“时间慌”“乡村记忆”“乡愁情结”并不仅仅是因为社会的快速变革所引起的文化恐慌,而是面临社会转型所引起的群体心理失衡。所以,以何种方式发挥时间在社会生活中的心理调节意义,从而满足社会、群体、个人的需要,使三者相处和谐,发挥其在社会中的“安全阀”作用,是建设美丽新乡村的题中应有之义。
[1][3]景天魁:《时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2](美)L.A.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4]陈占江:《空间认同与社会秩序》,《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3期,第122页
[5](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
[6][34][38]德雷克·格利高里 约翰·厄里:《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7][8][10][14](美)W.苏爱德华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4年
[9]刘胜利:《身体、空间与科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
[11]Durkheim,E..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Glencoe Free Press,1975.
[12](德)诺伯特·埃利亚斯:《论时间》,群学出版社,2013年
[13]方向红:《时间与存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商务印书馆,2014年
[15](美)刘易斯·科塞:《时间观与社会结构》,载《时间社会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16]Gurvitch,G..The Spectrum of Social Time.Dortrecht Reidel,1964.
[17](美)史坦利·柯恩:《时间与长期服刑的囚犯》,载《时间社会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18](美)大卫·哈维:《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载《都市空间与文化想象》,三联书店,2008年
[19](清)姚梦白:《雄崖所建制沿革志》,藏于即墨市档案馆
[20][21][22][24]孙铸:《凤凰·雄崖:历史资源荟萃》,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
[23]金耀基 范丽珠:《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社会》2007 年第 1 期,第 1~13 页
[25]Harvey,David.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Oxford Blackwell,1990:p.204.
[26]张尧均:《隐喻的身体: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年
[27](英)约翰·哈萨德:《时间社会学》,朱江文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8]Gurvitch Georges.The Spectrum of Social Time.Dortrecht Reidel,1964.
[29]Soule,G..What Automation Does to Human Beings.London:Sidguick&Jackson,1956.
[30]Sorokin,P.A..Sociocultural Causality,Space,Time.Russel&Russel,1943:p.209.
[31]Althusser,L.and Balibar,E..Reading Capital.London,1970:p.99.
[32]黄应贵:《空间、力与社会》,《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 3期,第 12~15页
[33]Goffman,Erving.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New York:The Overlook Press.1959:p.106.
[35](美)戴准·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商务印书馆,2013年
[36]Bridgman,P..The Concept of Time,Scientific Monthly,1932:p.97.
[37]Lefebvre,H.Space Product and Use Value,in Freiberg,J.W.(ed),Critical Sociology:European Perspective.New York:Irving,1979.
[39]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Spatial Structure,Time Narrative and Rural Life Change
Fang Jingjing Yuan Tongkai
As the basis of people’s lives,space and time record,stature,carry and drive people’s activities.Take an example of 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ancient village,we attempt to describe the time narrative arrangement in space from different spatial patterns.On the one hand,it is intended to define that the spatial structure elements have an impact on the behavior.On the other hand,the author tries to show that time as a social construction,has been conceived differently in the situation of different spatial evolution. “Time anxiety”, “time panic”, “rural memory”,“nostalgia complex” are not just because of cultural panic caused by the rapid changes in society;but the group mental imbalance in the fac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new urbanization,social change,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