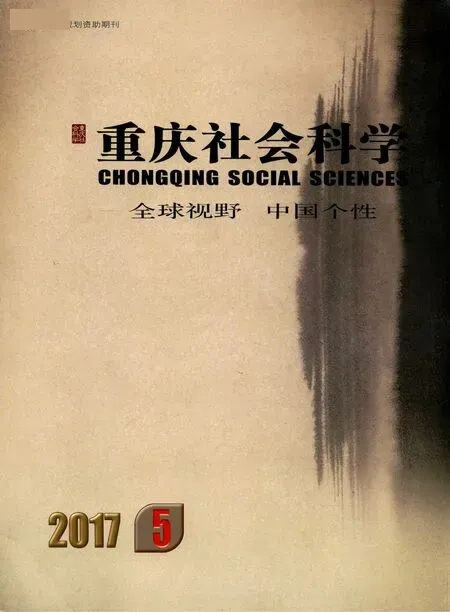新型城镇化背景的人口迁徙趋向*
李宝芳
新型城镇化背景的人口迁徙趋向*
李宝芳
近年来人口流动迁移研究议题不断丰富,主要包括人口流动迁移的新特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展望未来,流动人口的治理与服务仍有探寻的空间,具体包括流动人口治理与服务的细化研究;面向家庭的流动人口公共服务政策体系研究;多元的流动人口服务治理政策体系研究。
新型城镇化 人口流动 社会治理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天津 300191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口大规模的流动迁移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人口现象之一。这一重要人口现象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目前,关于人口流动迁移研究已形成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并存、研究议题丰富且不断增多的局面。近年来,除流动因素、流动与经济发展、流动人口生存状况等传统的研究领域外,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关于人口流动迁移重点关注和研究的议题主要包括人口流动迁移新特征、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等方面。
一、人口流动迁移的新特点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人口流动迁移呈现出新特点,总体流动规模减缓,流向出现多元化。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也由以男性为主向性别均衡转变,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体,年龄老化趋势明显。与此同时,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显现,更多的流动人口开始举家外出。
(一)人口流动迁移出现新趋向
当前经济进入新常态,人口流动迁移出现新趋向,人口在区域和城乡间迁移流动规模减缓,城镇化趋势变缓。分析原因发现,除了全国经济增速变缓之外,还有一些重要原因包括农村经济效益趋好、进城机会成本有所提高、城市的包容性差以及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等。[1]虽然人口流动迁移规模减缓,但是随着城市内部迁移呈增加趋势,农业劳动效率的持续提高,流动人口整体规模和强度还有着比较大的上升空间。只是仍有一些因素可能导致未来我国人口流动迁移的不确定性,增强流动迁移人口规模增长的波动。一是新常态下的经济形势和结构调整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的波动。二是流动人口大量集聚的特大城市正在通过划定城市空间增长边界和人口规模上限、提高落户门槛、疏解中低端产业等诸多政策遏制流动人口的快速增长。三是近年来随着各级政府的积极引导,人口主要流出地的城市工商业和村镇企业开始快速发展,不仅带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在本地就业,而且有可能推动回流人员在老家长期居留。[2]
东南沿海地区作为流动人口主要目的地的趋势不会改变,但是当前人口流动不再是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大规模单向流动,而是进入全国各地区之间多边流动的人口再分布均衡阶段[3],尤其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有所增强。[4]如2015年重庆市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0~2015年,来自市外的流动人口规模从94.5万人增至150.2万人,增长了58.9%。[5]随着“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推进,依托省会城市的中西部城市群有望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极,在产业集群发展和吸纳人口集聚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流动人口特征出现新变化
最初的流动人口以男性为主,大多数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以下,但现在流动人口特征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性别趋于均衡,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劳动人口主体,数量达到1亿左右。2015年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3年,2013年这一数字是9.2年。[6]高中以上阶段受教育者已成为每年新增流动人口的主要来源。流动人口中,年龄在40岁以上的占比持续提高,原因之一是流动人口中的农民工开始逐渐老化。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50岁以上的农民工数量高达4967万人,占比17.9%,分别比2010年增加了1352万人和3.6个百分点。[7]原因之二是,人口流动的家庭化带动随迁老人数量快速增长。
(三)流动人口家庭化成为趋势
“十二五”时期,举家外出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比例持续快速提高,家庭化迁移成为人口流动迁移的主体模式。新生代流动人口表现更为突出,近90%的已婚新生代流动人口是夫妻双方一起流动,与配偶、子女共同流动的约占60%,越来越多的流动家庭开始携带老人流动。迁移家庭而不仅仅是流动个体将成为未来我国社会政策的主要着力点。研究发现,劳动者性别、婚姻、年龄等个人特征,家庭规模、家庭总收入、平均年龄、子女数量等家庭因素和社会结构因素等都对家庭化迁移的发生具有显著的影响。[8][9]从流出地的视角展开分析则发现,农地流转会对家庭化流动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10]也有些研究指出,家庭化迁移存在职业、区域、时间和序列差异。如从事自我雇用的流动人口会更倾向于举家迁移。[11]东部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跨省流动者中,家庭规模最小、代数最少、结构最简单,中部地区和跨县流动者的家庭规模最大、代数最多、家庭结构更复杂、子女更易与父母团聚。家庭团聚的门槛因各地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而不同。[12]流动人口外出后平均约三年接来一批亲属。随着时间的推进,流动人口家庭团聚速度不断加快。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一次性迁入的可能性越小,但是接第二批、第三批亲属的可能性增大,它们的间隔时间缩短。[13]家庭迁移呈现出先夫妻、后子女的序列。[14]
二、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流动人口问题的关键,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都关注到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异质性,流动人口因性别、职业、收入不同而导致融合程度存在差异。社会资本、流动距离、居留意愿、流入地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就业等多个层面的因素都会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产生影响。近期一些特殊群体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流动老人的社会融合等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一)社会融合的具体差异与因素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已经成为共识,而且也已具备基本条件。虽然关于社会融合的概念和测量有所差异,但都认同社会融合是多维和复杂的,主要集中于社会、经济、文化几个方面。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具体差异,已有研究揭示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收入等的流动人口融合的异质性。如低端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显著低于城镇流动人口,而高端农民工则显著高于城镇流动人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度显著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已婚、受教育程度较高、拥有现代型社会资本的农民工城市融合度更高。省级大城市和县级小城市农民工的融合度显著高于地级中等城市的农民工。[15]两性间的社会融合度也有显著不同,有些研究认为总体而言,女性的社会融合度要高于男性。[16][17]即使相同性别的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也会因自身技能的差异而在融合度上存在区别。[18]
在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因素中,已有研究对个体特征、社会资本、流动距离、居留意愿、流入地层面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就业及基本社会保障等多个层面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19][20][21],研究日益宽泛和细化。现实中,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确实受诸多因素影响,但是如果面面俱到地进行各项指标的探讨,则会导致相应的对策无的放矢,所以在影响因素分析中应该更加聚焦,着重指出主要的影响因素,这样研究结论才会更有针对性和现实价值。
(二)特殊群体的社会融合
流动人口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内部结构复杂的社会群体。在不同子群体内部,他们的社会融合程度是有所差异的。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流动人口的子群体即一些特殊群体的社会融合情况,包括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流动老人的社会融合等。
1.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1000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已经在数量上超过世居少数民族,但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为语言沟通障碍、受教育水平较低、偏见,存在边缘化和低端就业现象,尚未实现行为融入。研究表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呈现流动群体“内卷化”特征[22][23][24],这主要是居住区间“孤岛化”、社会交往“内卷化”、就业形态“单一化”以及情感支持“族内化”不断强化的结果。[25]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进程滞后于全国,但流动规模和参与率快速提高,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重会进一步上升,民族多元性将在城市地区日益显现。[26]
2.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
“六普”数据显示,城镇流动儿童规模已经增长到2880万人,占全部儿童的比例为10.3%。这一群体的社会融合同样存在着危机。一是“照看者”在流动儿童的文化认知发展中呈现功能性缺位;二是流动儿童的同伴交流作为其消解文化障碍的有效途径呈现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三是间断式社会环境中所蕴含的文化落差强化了该群体的“同一性混乱”心理危机。[27]这种原因的造成与户籍制度、社会接纳、流动儿童个性心理、家庭环境的亲密度和适应性紧密相关。[28]而具体的社区生活经历、家庭经济社会地位和教育方式、学校类别等方面也是影响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重要因素。[29]社会融合具有一定的可塑性,但也具有代际的传承性。[30]流动会改善部分儿童的心理健康,但并不适用于全部流动儿童。流动儿童城市社会融合的根本障碍体现为教育困境,包括学前教育困境、义务教育过程中的困境及升学困境。[31]
3.流动老人的社会融合
对流动老人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流动老人的定义、迁移的特点、目的及社会保障等方面。老年人口流动主要以家庭团聚、为子女照料家务为目的。孟向京将流动老人定义为没有办理户口迁移,居住在外地的60岁以上男性、55岁以上女性人口。[32]对流动老人社会融合的研究则主要探讨其融合现状及面临的困境。大多数研究都认为,老年人的个人因素、代际关系、社会资本影响着他们的融合过程与结果[33],所以流动老人的适应及融合过程和程度有所差异。流动老人的社会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政府在户籍、社保、医保等制度方面的完善,还需要社区提供交流与关怀的平台以及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
三、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和内在规定。在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研究热点。刘英杰指出,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经济发展有很大贡献,流动人口公共服务是属地化管理的重要内容,流入地政府有解决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地方政府应该承担主要职责而不是依靠转移支付。蔡昉也认为农民工在大城市创造了社会财富、缴纳了税费,大城市有义务为农民工解决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关信平认为,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问题,途径之一是要加快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使全国城乡和各个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趋于一致。[34]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层面仍存在诸多不均等现象,其原因涉及理念、财政、机制、法制等多方面。有学者指出,从建设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视角来看,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公共服务普遍化、差异化、合理化、整合化、持续化等五个方面。[35]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流动人口的融合与发展,需要在充分认识问题及原因的基础上,通过理念谋发展、机制助发展、财政促发展、法制保发展,促进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之间、流动人口与政府之间、流动人口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谐。
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学界对流动人口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虽然流动人口的新增生育数量可能相对有限,但由于流动育龄妇女有可能会在流入地区,特别是东部的城镇地区进行生育,所以妇幼、孕产等医疗卫生资源本就紧张的东部城镇地区将会面临更大压力。学界在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的内涵、发展逻辑、测量评价、财政转移支付、市场化供给、筹资机制及创新服务模式、建立评估指标体系方面都有探讨(赵红等,2010;陆亚芳,2015;段丁强等,2016)。但是关于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对未婚流动育龄妇女及男性流动人口研究少;实证性研究分析少;不同地区间比较性研究少;流动人口需求角度研究少等。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加强对未婚流动育龄妇女及男性流动人口的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研究。
四、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有效应对人口大规模流动,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将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置于社会治理视域下进行考量。学界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治理有了更多的关注,认识到当前流动人口治理正经历深刻的双重转型,一是代际更替带来的群体特征大转变,表现为第二代流动人口的权利意识增强、权利诉求增多及抗争能力提高;二是政府治理的行为逻辑从管控向服务与治理兼顾转变。双重转型造成了双重张力:一是流动人口的需求与社会治理体制回应之间的张力,二是治理理念、管理体制与工作机制之间的张力(唐有财,2015)。具体而言,流动人口长期存在与当前流动人口治理的策略与效果相偏离,流动人口秩序整合遭遇多重困境,流动人口诉求的多元化与政府服务的统一性存在矛盾。流动人口秩序构建应以流动人口的群体特征为基础,以我国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为方向,依托流动人口的权利赋予、服务保障等手段,构建流动人口治理的综合体系 (江立华、张红霞,2015)。研究者分别从制度层面、体制层面提出构建治理新模式。如唐有财指出要构建“治理理念-管理体制-工作机制-流动人口需求”的四位一体框架。既注重赋予和增强流动人口的社会权利,又强调提升以政府为核心的各类社会主体的治理能力(唐有财,2015)。王永志(2015)则从制度层面对其重新进行建构,加强顶层设计和创新,建立健全各项制度。陈捷(2016)指出,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趋势在主体、客体、机制三方面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管治”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因此,需要从主体、客体、机制三方面推进城市社会流动人口社会治理的创新和转型。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必须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社会流动人口治理体制。李程伟(2016)则认为,应该探索社区包容性治理新方式。
五、结论与展望
综观近年来人口流动迁移研究的主要议题可以发现,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人口流动迁移也呈现出新的趋势,相关研究议题亦不断变化和丰富。除前文所述主要议题之外,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落地实施,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议题,如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与生育间隔的探讨。展望未来,在流动人口治理与服务体系方面仍有较大的探寻空间,具体包括如下方面。
一是流动人口治理与服务的细化研究。在有关流动人口治理与服务研究中,现有文献主要是通过分析现有政策、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措施进行研究,研究模式较为单一,而且主要是从定性角度出发,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对流动人口治理与服务体系进行定量研究,对其进行成本分析。
二是面向家庭的流动人口公共服务政策体系研究。近些年,人口流动越来越呈现家庭化的特点。流动人口公共服务需要尽快实现由个体向家庭的转变,必须将流动家庭作为服务对象,制定流动家庭发展的扶持战略和公共服务政策体系。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的不断增强,流动儿童和流动老人的数量不断增多,这两类群体将成为流动人口家庭发展中重要的关注点。因此,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也需要与时俱进,尤其对流动儿童、流动老人的需求与服务需要应给予更多关注与探讨。
三是多元的流动人口服务治理政策体系研究。由于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特大城市实行严格的人口调控政策等,未来人口流动可能会出现更频繁的波动,结构模式趋于复杂化,因而需要建立更加多元和富有弹性的流动人口服务治理政策体系,这也需要研究者给予更多的关注,给出更具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1]陈志光 李华香 李善同:《“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与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101~110页
[2][5][6][7][26]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中国人口出版社,2016 年,第 4、6、56~57、9、10 页
[3]曾相嵛 赵彦云 贺飞燕:《中国人口的多边流动与再分布均衡》,《调研世界》2015年第10期,第 7~11 页
[4]翟振武 杨凡:《中国人口均衡发展的状况与分析》,《人口与计划生育》2010年第8期,第11~12 页
[8]崇维祥 杨书胜:《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影响因素分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第 105~113 页
[9]王文刚等:《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特征与影响机理》,《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 1期,第 137~145页
[10]李龙 宋月萍:《农地流转对家庭化流动的影响——来自流出地的证据》,《公共管理学报》2016年第 2期,第 76~83页
[11]周敏慧 魏国学:《自我雇用与已婚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基于6省12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4年第3期,第 106~111 页
[12]杨菊华 陈传波:《流动家庭的现状与特征分析》,《人口学刊》2013 年第 5 期,第 48~62 页
[13]侯佳伟:《人口流动家庭化过程和个体影响因素研究》,《人口研究》2009年第1期,第55~61页
[14]吴帆:《中国流动人口家庭的迁移序列及其政策含义》,《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 4期,第 103~110页
[15]王震:《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兼与城镇流动人口的比较》,《劳动经济研究》2015年第2期,第41~61页
[16]陈湘满 翟晓叶:《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湖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西北人口》2013年第6期,第106~110页
[17]杨倩倩:《性别视角下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研究》,载于《城市社会学辑刊·2015》,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114~130页
[18]谢桂华:《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第103~124 页
[19]潘泽泉 林婷婷:《劳动时间、社会交往与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研究——基于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15年第 3期,第 108~115页
[20]张宏如 李群:《员工帮助计划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模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还是心理资本》,《管理世界》2015年第 6期,第180~181 页
[21]金昱彤:《社会支持与青年农民工社区融入——基于全国六城市的调查与分析》,《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35~39 页
[22][25]黎明泽:《浅论城市融入过程中的社会认同“内卷化”——以沿海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例》,《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 31~35 页
[23]肖昕茹:《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现状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1 期,第 60~65 页
[24]肖锐:《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境况及变化趋势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49~55页
[27]庄曦:《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融合问题及路径探析》,《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第140~146 页
[28]巩在暖 刘永功:《农村流动儿童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 82~87 页
[29]王毅杰 史晓浩:《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融合:理论与现实》,《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6期,第 97~103页
[30]周皓:《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代际传承》,《中国人口科学》2012年第1期,第70~81页
[31]徐丽敏:《农民工子女在城市教育过程中的社会融合研究》,《学术论坛》2010年第1期,第197~201 页
[32]孟向京等:《北京市流动老年人口特征及成因分析》,《人口研究》2004 年第 6 期,第 53~59 页
[33]刘亚娜:《社区视角下老漂族社会融合困境及对策——基于北京社区“北漂老人”的质性研究》,《社会保障研究》2016 年第 4 期,第 34~43 页
[34]关信平:《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的实质及相关政策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第 70~76 页
[35]宋连胜 金月华:《论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探索》2016年第2期,第123~127 页
[36]李晓霞:《融合与发展: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思考》,《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2 期,第 110~116 页
Migration Tendency in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Li Baofang
In recent years,population migration issues have continued to enrich.There are four main issues including new features of migration,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social governanc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there are some researching space in the governance and servic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The first is the refining research on the governance and service of migration.The second is to study of the family oriented policy system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The third is to research on diversified policy system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governance.
new urbanization,population mobility,social governance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研究”(批准号:15CRK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