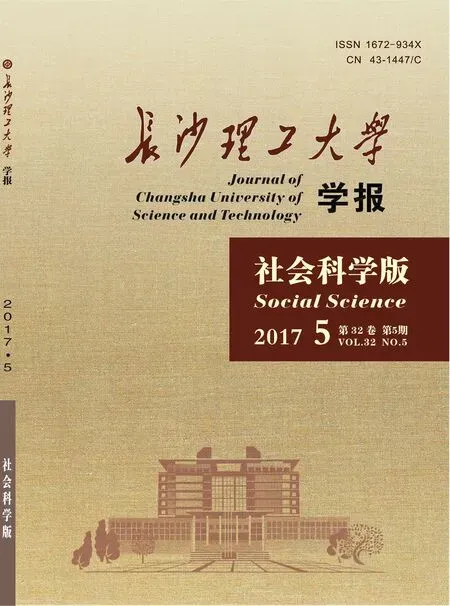德国古典道德-政治哲学的启蒙精神
赵敦华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德国古典道德-政治哲学的启蒙精神
赵敦华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文章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对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启蒙性质的论述,分别考察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着重说明了康德政治哲学中实践、经验的、实用的特征,费希特关于民族自由的法则和人类自由精神的论述,以及黑格尔辩证的法权体系。
法国大革命;启蒙;政治共同体;民族精神
Key words:French revolution;enlightenment;political community;spirit of nations
一
马克思恩格斯首次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政治意义作了富有洞察力而又易遭误解的评论。《神圣家族》的“政治自由主义”一节把德国自由主义的根源追溯到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马克思说:“18世纪末德国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经过历史上最大一次革命跃居统治地位,并且夺得了欧洲大陆;……但软弱无力的德国市民只有‘善良意志’,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康德的这个善良意志完全符合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他们的小眼小孔的利益始终不能发展成为一个阶级的共同的民族的利益……一方面是德国市民的现实的地方的、省区的偏狭性,另一方面是他们的世界主义的自夸。总之,自宗教改革以来,德国的发展就具有了小资产阶级的性质。”[1](P211-212)
“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规定和道德假设。因此当这种强有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以恐怖统治和无耻的资产阶级钻营的形态出现的时候,德国的小资产阶级就在这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面前畏缩倒退了。”[1](P213-214)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比较了法德两国启蒙哲学的不同: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溃的前导。法国人同全部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在国外,在荷兰或英国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都可能进巴士底狱。相反,德国人是一些教授,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笨拙枯燥的语言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人物的自由派,不正是最激烈地反对这种使头脑混乱的哲学吗[2](P214-215)?
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而自由派的反对是错的。他说:“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推翻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2](P215)
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洞察力在于发现了法国和德国哲学同属于启蒙主义的思想政治运动。在这一点上,他们坚持和发扬了黑格尔的启蒙观。黑格尔说:“世界历史的这一伟大的时代(其最内在的本质将在世界历史里得到理解),只有日耳曼民族和法兰西这两个民族参加了,尽管它们是相互反对的,或正因为它们是相互反对的……这个原则在德国是作为思想、精神、概念,在法国是在现实界中汹涌出来的。这个原则出现在德国,显得是一种外部环境的暴力和对这种暴力的反动。”[3]
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把法德两国启蒙哲学的对立归结为反官方与官方、公开抨击与隐晦思辨、法国资产阶级的自觉革命与德国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贫乏之间的对立。他们承认黑格尔辩证法具有革命性质,尽管采取了“头脚颠倒”的“神秘主义”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的评论是否招致多少误解,这里姑且不论。20世纪政治哲学确确实实充满马克思恩格斯提到的那些偏见和误解。西方现代的“自由派”如同恩格斯年代那样,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隐藏或表达着极权主义的秘密,他们要克服或超越德国启蒙代表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形态。而哈贝马斯、罗尔斯等自由主义巨擘却从康德的政治哲学中吸收丰富的理论资源,对黑格尔的“国家主义”和形而上学却报以微词。保守主义或国家主义者如同当年普鲁士官方那样认可黑格尔的法哲学。然而,无论哪一个阵营,都没有把德国古典哲学当作与此前社会契约论和此后“现代性批判”同等重要的政治哲学。国内情况大体如此。除了贺麟在抗战时期提倡德国三大哲人抗御国难的精神,对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康德的批判哲学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对其中政治哲学的评述流离在西方政治哲学主流之外。
针对各种偏见误解所带来的忽视,我们对德国古典政治哲学的性质能够给出以下几个大致限定:首先,从康德的政治哲学延续至费希特和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其实质上并不反映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冲突,只不过是德国启蒙运动在不同阶段的时代精神精华的表现;其次,康德的政治哲学思想也不单纯是其纯粹理性在道德哲学领域的推论和实践,同时带有着回应现实政治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意向,因此也是实践、经验的、实用的知识;再次,费希特的自我并非拘囿于纯粹思想上的一种规定,或者是单纯的道德假设,还表现为实现民族自由的法则,因此也呈现为彰显人类自由精神的运动;最后,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也并非是隐藏的,或者说是“神秘主义”,其实质上是法权体系的一种辩证推演以及论证的过程。
两组患者均严格控制饮食,合理运动。对照组给予二甲双胍治疗。用药方法:每天3次,每次0.5g,餐前服用。观察组患者给予瑞格列奈联合二甲双胍治疗。用药方法:二甲双胍同对照组。瑞格列奈:餐前30min服用,起始量每次0.5mg,最大量每次2mg,每天2次,根据患者血糖水平调整。两组均连续治疗3个月。
二
1798年,康德说:“我们在自己这个时代目睹了一个富有才智的民族进行的革命,这场革命可能会成功或失败;它可能会如此充满了不幸和暴行,以至于一个思维健全的人如果会希望第二次从事时成功地完成革命的话,就绝不会以这样的代价来进行这场试验。”[4](P82)
此前的《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1787)中,康德自觉地将“革命”概念应用在了理论知识的身上,同年的《学院之争》论及“形而上学革命”和“道德实践革命”。与1871年所说的“真正的批判时代”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法庭”相比,“革命”的思想用宗教哲学、法哲学、实用人类学、人类历史、国际关系等社会历史内容充实和展开了道德实践的纯粹理性。康德的一生都在维护着其平民哲学家的使命感,其思想所关注的都是人的平等、尊严和自由这些基本问题,并且将如何能够过一种善的生活来设定为哲学的最高目的。批判哲学防止未经理性自由和公开检验的独断思想的专横,把个人的意志自由和自律作为善的生活的合理保障。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后,康德越发认识到,自由不仅在个人内心,也是外部自由和社会权利,个人自由和道德自律的实现有赖于公正的秩序、法权制度和国际和平,人的至善不是道德公设,而在自然历史合目的之进步。康德高度评价启蒙的社会进步作用。启蒙不但为人们“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带来了开明的政治保障,而且正在和将要创制“由源于契约的理念所产生的、一个民族的一切法权立法都必须建立于其上的惟一宪政——就是共和制的宪政”[5](P355)。
康德还说:“建立一种完善的公民宪政的问题,取决于一种合法的外部国际关系的问题,而且没有这种关系就不能得到解决;而‘国际法权应当建立在自由国家的一种联盟之上’。”[5](P31,359)无需多言,康德政治哲学的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政治远见为现代世界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三
以卢梭和康德的平等自由为基础,把康德的理性存在者转变为自由意志的行动者,把道德自律转变为无条件的普遍法则,不受现存秩序的妨碍,而是一切法律和政治的合法性依据。费希特早期政治哲学比康德激进,被指控为“民主主义者”或“雅各宾党人”。
费希特的知识学虽然按照康德体系包括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个部分,但试图克服康德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分离,强调实践哲学的优先性,哲学家是这样一种人,他们自觉地意识到自我存在于行动,并且要将行动施行于感性世界。在此意义上,“知识学应当是人的精神的一部实用的历史”[6]。
费希特在1796-1789年的《自然法权基础》和《伦理学体系》著作中说明“人”作为理性存在者是类概念:“人(所有真正的有限的存在者)只有在人群中间才成为人”;“个人的概念是不可能想象的,相反地,人的概念是类概念”[7](P296,297)。个人在自由是相互承认、相互尊重的主体间关系:“每个人都应当用他人的自由的可能性来限制自己的自由”。从交互主体的概念出发,费希特演绎出“法权”和“义务”相对应的法权关系:“按照法权规律,这个人可以做不损害其他人权利的一切事情”[7](P355,364);按照伦理原则,“永远按照对于你的职责的最佳信念去行动”[8]。法权体系是带有强制性的共同体概念:这个概念是必然的,而这个必然性迫使我们双方都遵守这个概念及其必然的结论:我们双方通过我们的实存而相互结合、相互约束[7](P306)。
法权共同体是感性世界的国家。费希特设计的国家也是康德式共和宪政政体,但个人受到国家强制权力的更多限制。费希特把财产权当作首要的自然权利,前提他们靠劳动生存。他认为:“所有合理的国家宪法的原则是每个人都必须能够靠自己的劳动生存。”[7](P472)失去财产权的穷人虽然有权要求国家资助,但前提是证明他的劳动仍不能维持生活,还要接受国家对他财产管理的监督。黑格尔称费希特的设计是“警察国家”。不过,费希特承认人民主权,国家权力来自人民依据契约转交的权利,行政权受独立的民选机构监察权的制约。
1800年之后,在抗争法国入侵的环境里,费希特论证民族国家是理性要求的“与外国隔离的贸易机体”和“与外国隔离的法律的和政治的机体”[9]。费希特唤起德意志民族主义,强调德意志民族是说同一语言的“命运共同体”,德语把“民族的感性生活和超感觉的精神概括为一个整体”,是“由一种最初由天然力量迸发出来的时候就一直活生生的语言”。在说这个语言的民族中,“精神影响着着生命”,“广大民众都是可以教育的”[10]。费希特不像康德那样相信人的道德和理性的平等,没有理性“私人运用”和“公开运用”的区分。他赋予学者以教育民众、通过发展科学、艺术和宗教把精神文化带入公共生活的使命。费希特倡导民族主义不是德国人的狭隘利益,而是通向人类完善的途径,与世界精神的进程相一致。他的政治哲学表达了启蒙的时代精神和德国统一的民族精神。
四
黑格尔经历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时代和普鲁士王国崛起的过程。青年黑格尔是法国大革命的同情者,中年是拿破仑的支持者,而老年是对一个完成了的时代的全面反思。黑格尔在1820年版的《法哲学原理》序言结尾处说道:“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自身之后,才会出现……当哲学把它的灰色描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青,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11](P13,14)
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与康德和费希特的差别并不像他经常强调的那样大,他的优势在于处在一个时代的终点,把其他启蒙学者反映的这个时代的精神建成一个辩证体系。他用辩证法的范畴分析和推理,把他们和其他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哲学组建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描述的自由意志的主体在自己创造的法权制度中实现自身的过程,这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抽象到具体、从外在经由内在到内外统一、从客观经由主观到主客观统一、从普遍性经由特殊性到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单一性的辩证发展过程。法哲学的辩证法不等于历史辩证法,如黑格尔所说:“一系列定在形态的实际出现在时间上的次序,一部分跟概念逻辑的次序是互有出入的。比如,我们不能说,在家庭出现以前就已经有所有权存在;但尽管这样,所有权必须放在家庭之前论述。……现实的东西、概念的形态虽然在现实世界本身中是首先存在的,但是我们仍把它放在后面作为下一步骤来处理。”[11](P40)
在各种法权制度中,只有市民社会和君主立宪制国家是现代的形态,所有权的自由和家庭的自主婚姻只有在市民社会才被实现,而道德自由和市民社会的福利只有在现代国家中才是具体自由。“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两章是黑格尔法哲学最有创意而又最有争议的部分。
在启蒙学者中,只有黑格尔注意到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哲学内涵,并用辩证法阐述市民社会的个体、习俗、经济体系、等级区分和政治结构的本质。与康德简略提到的“公民社会”相比,黑格尔的理论更充实、具体、全面,至今看来也不过时。自由主义者常质疑黑格尔为什么认为市民社会必然过渡到一个强权的政治国家。黑格尔的理由不只是逻辑范畴的推演,而且以经验观察和分析为事实根据。他看到市民社会自身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是奢侈与贫困的无限分化:“一方面穷奢极侈,另一方面贫病交迫,道德败坏”,“怎么解决贫困,是推动现代社会并使它感到苦恼的一个重要问题。”[11]P(209,245)无论是费希特设计的国家监督下的救济,还是海外移民,都不能对贫困问题进行解决。贫困化将三个等级中的许多人打入社会的底层,从而成了同业公会没有办法照顾的“贫民”或者“贱民”,这些人同“劳动阶级”一起构成了“群众和群氓”,一有风吹草动,很容易成为“暴民”。黑格尔说:“国家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中介关系”;如果没有国家制度的中介,“专制国家只有君主和人民”,或者是“暴君总是姑息人民而只是拿他周围的人来出气”,或者是将导致“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的暴民骚动[11](P322-323)。黑格尔似乎说,只有通过政治国家,才能解决贫困化造成的少数人暴政或多数人暴力政治后果,因而也能保障和发展伦理家庭和市民社会已经获得的个人权利和自由。
启蒙学者大多主张民主制或共和制及立法权、行政权和监督权的分立和平衡,而黑格尔提出的设想是要实行君主立宪制,并且要实现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统一。就此看来,黑格尔的主张似乎是一种倒退。实际上,《法哲学原理》论述的君主立宪制,18世纪出现在英国、荷兰,19世纪被更多民族国家所采纳。黑格尔对国家制度的设计把各国现存制度的优点综合在一起,试图使德国的世袭王权与法国中央集权的行政权和英国两院制的立法权达到“有机统一”。需提醒的是,普鲁士王国当时远不是君主立宪制,黑格尔的设计对德国具有超前意义。
直到“铁血宰相”俾斯麦上台执政的时候,德国才在他的领导之下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家,并且建立了在中央集权体系之下的官僚体制以及帝国议会。但“第二帝国”由于受到王权专制以及容克贵族的军国主义的影响,逐渐地走向了自我毁灭。其在1918年的败局,似乎是证实了马克思1842年对德国“立宪君主制这个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12]的批判。但这笔坏账不应该记在黑格尔头上。
马克思在1844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对它的批判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13]。而在1859年又说,对黑格尔所概括的“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1](P32)。笔者认为,在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吸收这个问题上,承认它比否定它对于我们会有更大的收益。只要把“密纳发的猫头鹰”的黄昏反思转变为“高卢雄鸡的高鸣”宣告的新的大革命,把市民社会中的劳动群众和贫民转变为无产阶级,把普遍等级集中体现的“国家的意识和最高的修养”[11](P315)转变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把国家的强制权力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把黑格尔对市民社会“需要的体系”的概括转变为使用黑格尔逻辑学把握和分析更加丰富经济学和社会学材料的《资本论》体系,那么从康德开始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政治哲学顺理成章地转变为马克思的学说。当然,这只是一条简明扼要的线索,需要大量的文本材料和论证这些环节复杂的转变。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240.
[4][德]康德.康德著作集(第7卷)[M].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82.
[5][德]康德.康德著作集(第8卷)[M].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6][德]费希特.费希特著作选集(第1卷)[M].梁志学,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638.
[7][德]费希特.费希特著作选集(第2卷)[M].梁志学,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8][德]费希特.费希特著作选集(第3卷)[M].梁志学,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60.
[9][德]费希特.费希特著作选集(第4卷)[M].梁志学,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88.
[10][德]费希特.费希特著作选集(第5卷)[M].梁志学,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12,314.
[1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
Enlightenment Spirit of Classic Moral-Political Philosophy in German
ZHAO Dun-hu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B516
A
1672-934X(2017)05-0032-05
10.16573/j.cnki.1672-934x.2017.05.005
2017-07-28
赵敦华(1949-),男,江苏南通人,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