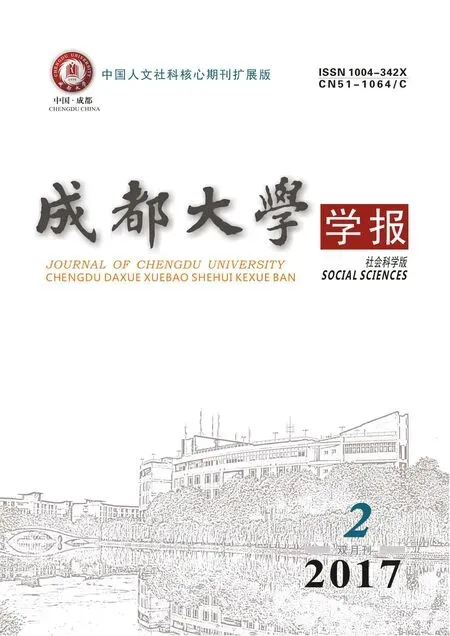我国史学与文学典籍外译历史与现状*
季红琴 龙佳仪
(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14)
·文艺论丛·
我国史学与文学典籍外译历史与现状*
季红琴 龙佳仪
(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14)
文化典籍具有深刻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外译对象在选择性中体现丰富性。史学典籍外译逐渐向纵深方向发展,文学典籍外译则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典籍外译在曲折性中体现发展性。文化典籍外译主要由汉语翻译人才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将包括儒学经典、佛教文献、史学典籍以及文学著作等在内的文化典籍,译介到诸如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德国等其他多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翻译活动。本文中将以我国史学典籍以及文学典籍为重点,通过横向及纵向的对比研究,进一步分析文化典籍外译的历史及现状,为我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提供有力依据。
史学典籍;文学典籍;外译
我国文化典籍文本丰富,覆盖面广,形式多样,外译历史悠久,译本丰富,翻译主体亦具时代特征。我国文化典籍外译主要围绕以下几类作品展开: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家哲学经典,以佛教经书为主的宗教文献,以《史记》、《汉书》为重点的历史文献,以经典小说和诗歌为主的文学著作。《我国文化典籍外译历史与现状(上)》对前两类著作的外译进行了总结和梳理,本文将围绕后两类著作的外译与传播展开论述。
一、以《史记》、《汉书》为重点的史学典籍外译
我国史书卷帙浩如烟海,编排体例十分丰富,包括编年体、纪传体、国别体以及纪事本末体等。在西晋荀勖等人所编目录书《中经新簿》中开始将史书独列为四部之一,自此史部自成一类,数量之多、流布之广,已在各类典籍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多样性和连续性成为我国史籍的重要特征。[1]
《史记》名列“二十四史”之首,由西汉杰出史学家司马迁创作,被史学家奉为典范。它在史学上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编撰体例,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根据马祖毅、任荣珍(2003)以及李秀英(2006)记载,19世纪中期,奥地利汉学家先驱菲茨迈耶(August Pfizmaier,1808-1887)把《史记》24卷译成德文,零散地发表在《维也纳科学院会议报告》上,这是对《史记》最早的德文译介。1895至1905年间,由巴黎拉鲁斯出版社出版的汉学家沙畹博士(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1865-1918)译注的5卷本《史记》译本,是法国最早大规模译介《史记》的成果。1969年巴黎梅森内夫出版社再版沙畹的《史记》译本并增加一卷,该书后来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性著作选集·中国系列丛书”。1960年,美国的华兹生(巴顿·华兹生Burton Watson,1925-)以《司马迁:历史学家的神圣职责》和《历史学家的撰史方式》为题翻译的《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三代世表》的序、《大宛列传》等,收入“亚洲文明导论”丛书中的《中国传统之本源》一辑,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辑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性著作选集·中国系列丛书”。到目前为止,华兹生已翻译《史记》130卷中的80卷,他的译本是《史记》已经出版的译本中最为完整的英文译本。其译本侧重文学内涵,面向读者,堪称杰出的文学译著。[2][3]
除此之外,还有前苏联帕纳秀克(В.А.Панасюк,1924-1990)的俄文译本,维雅特金与塔斯金合译的俄文《史记》,两译本分别于1956与1975年出版。匈牙利汉学家杜克义(Ferenc Tøkei,1930-)编译了《史记》的节选。据有关资料显示,越南也翻译过《史记》,但详情无从考证。20世纪末以后,《史记》在西方的流传从最初的译介逐渐向纵深的专题研究方向发展,这些译介和研究让西方认识到了《史记》是一部史学价值和文学审美融为一体的不朽著作。《汉书》是中国古代官修正史的典范,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创立有着重大贡献。
然而与《史记》外译传播命运不同的是,《汉书》尚无全译本,目前仅出版过一些节译本,且大多为英译本。《汉书》最早的英译本出自英国汉学家、伦敦会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他是西方最早对《汉书》进行研究并取得成果的汉学家之一,其翻译内容主要集中在汉代民族政策和对外关系。他编译的《汉匈关系史·〈汉书〉》卷94于1873年连载于《上海晚邮》上,次年《〈汉书〉中的民族信息》一书由伦敦人类学会出版。
1938-1955年间,美国汉学家德效骞(Homer Hasenpflug Dubs,1892-1969)译注的《〈汉书〉注译》三卷,包括《帝王本纪:〈汉书〉》卷1至卷12的内容,由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韦弗利出版社出版,这是西方选译《汉书》篇目较多的英文译本。该版本译风严谨,注释和考证都很翔实、严谨,属于学术研究型的典范译本。随后美国汉学家华兹生的《古代中国的朝臣与庶民:班固〈汉书〉选译》于1974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于1977年再版。华译《汉书》章节较为完整,依照原作,风格简约,可读性强。但该本更大意义在于,仅除刘若愚在1967年出版的《中国游侠骑士》节译过《汉书》卷92《游侠传》外,其所译介基本上为首译。在翻译史上,华氏对《汉书》的译介有筚路蓝缕之功。
而俄译本的《汉书》数量较多,所知即有10种。首位译介《汉书》的俄国人是比丘林(尼基塔·雅科夫列维奇·比丘林,1777-1853),他所译《匈奴列传》(《前汉书》第94卷上和下)于十月革命后载入了《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集》。此外,俄译本内容较多的有两种,即斯捷普金娜等译的《前汉书选》,载《东方古代史文选》(1936年),以及波兹德涅耶娃(1908-1974)译的《前汉书选》,于1950年载《世界古代史文选》第1卷。
《史记》和《汉书》对中国历史上各族间历史文化认同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反映了中华民族“通"的历史面貌与恢弘气象,《汉书》则凭借其第一部断代纪传体的地位成为历代纪传体皇朝史的楷模。这两部巨著的译介,大大推动了西方社会对书中所记载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制度及对外关系的研究。
除了《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的外译,也有不少其他体例的史籍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而被译介成各国语言。编年体是中国最古老的史书体裁,作为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著作,《左传》被西方汉学家看作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西方将《左传》翻译成英文的汉学家主要有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和美国的华兹生。1861至1872年间,香港伦敦传道会印刷出版的理雅各的《中国经典》包含《春秋》和《左传》的全译本。1989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华兹生翻译的《〈左传〉:中国最古老的叙事史选篇》。除此之外,还有德国汉学家鲍吾刚(Wolfgang Bauer,1930-1997)于1959年出版了《〈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与谷梁传》。俄国汉学家波兹涅耶娃选译过《春秋》、《左传》及《战国策》等书,1963年,司徒卢威(P.B.Struve)和列德尔摘选了各译本的片段收录于《东方古代史文选》。这在俄国是第一次全面译介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后来甚至有东欧国家的汉学家间接从俄文译本来阅读这些中国文化典籍。
法国传教士冯秉正(Moyriac de MAILL,1669-1748)于康熙年间来到中国,主要从事中国历朝兴亡史的研究。他于1777年至1785年在巴黎出版了《中国通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吉朋曾把这部书放在仅次于李维的《古罗马史》的重要地位,后者也曾在欧洲思想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此外,还有美籍华人方志彤(Achilles Fang,1910-1995)英译过《资治通鉴》。在日本,京都大学的兴膳宏与东北大学的川合康三共译著了《隋书·经籍志》刊载于《中国文学报》。在德国,白乐日翻译的《隋书·食货志》曾获法国巴黎科学院的“儒莲奖”,所译的《隋书·刑法志》也受到欧美学者的广泛好评。
二、以经典小说和诗歌为主的文学典籍外译
文学典籍是指我国经典文学作品、文献的总称,包括汉语文学作品,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并不涉及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文学典籍中,经典小说相对于经典诗歌、经典散文、经典戏剧而言,泰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1828-1893)认为,其是“比真的面貌还要有神气、有活力、有生气"的一种艺术样式,虽是发展和成熟最晚的一种艺术样式,但它却是异军突起,独领风骚。[4]
中国经典小说的对外译介是从当时被誉为“欧洲汉学中心"的法国开始并形成高潮的。最先在法国译介的我国经典小说是《今古奇观》里的三个短篇,即《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狠仆告主》、《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由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Francois-Xavierd' Entrecolles,1662-1741)翻译,收在杜赫德编的《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到20世纪,《今古奇观》中的短篇仍有人续译。首先介绍到法国的经典长篇小说是《好逑传》,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两种法译本:其一是根据英国德庇时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的英译本转译的重译本,1828年出版,译者名不详。其二是于1842年出版,居耶尔·达海所译的版本。18世纪初至19世纪中期正是欧洲对中国文化兴趣高涨之时,《好逑传》的英译本出版后,引发了西方翻译出版《好逑传》的热潮,它被迅速地转译为法、德、荷等多种语言,它们大抵继承了《好逑传》英译本的翻译和编排体例,进而形成了由序言、正文、注释和附录组成的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的翻译范式。20世纪上半叶,法国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译介,处于低潮。此后经过了战火的洗礼,以及文学交流的恢复与发展,195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决议,选择东方国家文化名著编成“东方知识丛书"。将《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儒林外史》、《唐人传奇》、《聊斋志异》等系列典籍约请专家翻译,由巴黎最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出版。1981年,伽利玛七星文库推出的一百二十回全译本《红楼梦》,震动了当时法国的文学界和汉学界,受到了欧洲的热烈欢迎,经典小说译介可谓盛况空前。古典小说在西方大面积地被译介,而作为我国文学典籍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典诗歌,自然也受到翻译界的重视。我国古代诗歌早在史前时期的口头创作中就已经产生,早期的诗歌大多都是四言诗,《诗经》就是第一本四言诗的诗歌总集。汉代诗歌作为诗经的传承,出现了形式比较自由的民歌,并形成了汉代的“乐府诗"。魏晋南北朝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重要阶段,诗歌形式丰富多样。到了唐代,诗歌进入全面繁荣的高峰,涌现出许多伟大的诗人和优秀的作品。[1]
我国文学最初是以诗歌的形式传入英国,传播历史已逾400年。1589年英国人在其《诗艺》中介绍了中国古典诗歌格律,算是中国文学传入英国的开始。法国读者最初接触到中国诗歌的是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1666-1736)所译的《诗经》中的8首,1736年收入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有关《诗经》的翻译,在介绍《四书》、《五经》的译介时(见上)[5]曾提到,兹不再述。
而《楚辞》中的《离骚》最初是由帕尔克(E.H.Parker,1849-1926)翻译,并于1879年发表在香港出版的英文杂志《中国评论》上。1895年,理雅各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27卷上发表了《“离骚"诗及其作者》。他的译文相较于帕尔克,要精确得多。然而译介《楚辞》最有成就的当数亚瑟·韦利(ArthurWaley,1888-1966),他翻译过《风赋》(英译《雄风和雌风》)和《登徒子好色赋》(英译《登徒子》),1955年又推出了《九歌:中国古代巫术研究》,由热心介绍中国文学的阿伦与昂汶公司出版。他英译的《九歌》为九篇(没包括《国殇》和《礼魂》),每篇除了译文外,还包括补注和若干附录。继韦利之后,系统译介《楚辞》的是他的学生戴维·霍克斯(David Hawks,1923-2009)。
最早向西方介绍唐诗的是法国汉学家、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1718-1793),由他所编译的《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或《北京耶稣会士杂记》16卷,于1776年至1814年陆续出版。该书第四、五卷集中介绍了唐诗和李白、杜甫。1862年,巴黎阿米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译著《唐诗选》,每个重要诗人都附有简介,每首诗都有详细注释。序言里详述了中国诗歌艺术从《诗经》到唐诗所经历的变化发展,并对中国唐诗作了高度评价。这本书于1977年再版,被出版商评价为“重要的,最好的中国诗歌的法文译著”。1962年,巴黎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由汉学家戴密微(Paul Demieville,1894-1979)主持编译的《中国古诗选》,该书翻译了从《诗经》到清诗204位诗人的诗共374首。译述工作从1954年到1957年共持续了四年时间,动员了多位汉学家的力量。这部巨著集法译中国古诗之大成,把法国汉学界译介中国古典诗词推向了高潮。
以美国译介唐诗为例,以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著《华夏集》和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1874-1925)的《松花笺》开其端,亚利桑那大学中文系教授在“泰恩世界名作丛书"中又推出唐代诗人专辑,现已出版的就有杜甫、柳宗元、元稹、李贺、孟浩然、王昌龄、王维等人的专辑。到本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遂成为西方世界唐诗研究中心。此外日本小火田熏良译《李白诗集》,德国海尔曼译《中国古今抒情诗选》,澳大利亚以及苏俄、意大利、拉美、韩国等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对中国经典诗歌有不一的翻译作品,都可见中国古诗在海外汉学界乃至翻译界的风行。
文学典籍译介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近几个世纪以来我国古代文学典籍在西方广泛传播,这有助于让西方读者能更直观地了解中国文化,纠正了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这对中国文学经典、对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甚至对汉学研究都有积极意义。
三、汉籍外译现状
汉语典籍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精髓的载体,其外译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在国家层面上,在20世纪末投入经费立项启动了“大中华文库”翻译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是列入国家规划的重大出版工程,并得到国家财政的支持。这一工程,被官方认为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的中国古籍整理和翻译的重大文化工程,也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工程。[6]近年来,典籍外译的学术关注度有了大幅增长,相关论文的发表率也有所提升。尽管这些文章讨论的意图、侧重点不尽相同,学术含量不一,但反映出典籍外译在国内翻译界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随着我国典籍外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发展,范围与视角出现了新的进展和趋势,根据陈莉(2014)总结,这种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论文数量稳中有升,尤其是近三年论文发表量较前几年有大幅提升;(2)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典籍英译本研究、运用翻译理论研究典籍英译时间问题、典籍英译的标准、原则及策略研究。然而,事实上汉文化典籍仍然鲜为世界所知。“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7]由此可见,让我国文化典籍走出去并非易事,典籍外译事业仍面临巨大挑战。叶慧君、陈双新(2015)的研究表明,在典籍外译过程中,出现了典籍文献术语外译及相关研究不平衡的现象,主要体现在:(1)文化术语翻译研究与典籍翻译研究之间的不平衡,前者的关注度与研究成果大大少于后者;(2)术语来源选择不平衡;(3)外译目标语语种不平衡;(4)文化术语翻译研究本身的不平衡。[8]因此,有关部门亟待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展开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实现中国文化典籍“走出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四、结语
我国文化经过长期积淀,博大精深,史学典籍外译与研究呈现纵深方向发展的态势,而文学典籍对欧洲文学开始阶段的发展,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近年来,典籍外译在国内翻译界研究视角出现了新进展,关注度也有所上升。尽管如此,我国典籍外译仍处于不容乐观的境地,需要各界加大对其的支持,以推动我国传统文化的繁荣复兴。
[1]李致忠,周少川,张木早.中国典籍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李秀英.《史记》在西方译介与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4).
[3]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修订本)[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4]宋丽娟,孙逊.“中学西传”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翻译——以英语世界为中心[J].中国社会科学,2009(6).
[5]季红琴.我国文化典籍外译历史与现状(上)[J].外语学刊,2014(2).
[6]周新凯,许钧.中国文化价值观与中华文化典籍外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5).
[7]陈莉.回顾与反思:国内典籍英译十年研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4(3).
[8]叶慧君,陈双新.典籍文献术语外译研究现状及思考[J].河北大学学报,2015(3).
(责任编辑:刘晓红)
2016-05-10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典籍翻译与中华文化传播中的战略研究(12CGJ020)”;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典籍翻译外国读者接受调查研究”(14YBA003);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我国文化典籍外译与传播实证研究”(15A010)的阶段性成果。
季红琴(1979-),女,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龙佳仪(1993-),女,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H059
A
1004-342(2017)02-8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