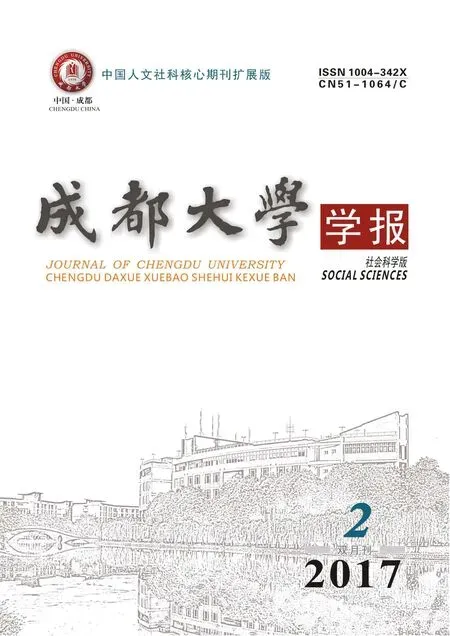巴金、靳以怀人散文对照谈*
石 健
(玉溪师范学院 文学院, 云南 玉溪 653100)
·文艺论丛·
巴金、靳以怀人散文对照谈*
石 健
(玉溪师范学院 文学院, 云南 玉溪 653100)
巴金与靳以在抗战爆发以后,都曾写下大量悼念亡友的回忆性散文。巴金的作品,强调了亡友对自身的切实帮助,充满浓重的感伤格调,以及强烈的忏悔意识,在自我透视中,不乏对人类终极命运等问题的思考。这些作品与巴金对于无政府主义信仰的改变,具有直接的关联。靳以则别有幽怀,即在悼念友人的过程中,充分宣扬了个人的文学观念,传递出符合时代主潮的最强音。怀人散文的鲜明反差,折射出二人创作的不同取向。对巴金、靳以的这些作品予以辨析,可以匡正以往的一些不确评价。
巴金;靳以;怀人散文;自我透视;文学观念
1930年代,巴金、靳以在共同编辑著名文学期刊,如《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丛》等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人在文学观念上有很多共通之处,即都强调文学为人生服务,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并且自觉地以平民本位自居,甚为反感学院派文人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的浮泛之风。在抗战爆发后的散文中,怀念逝去的友人,同时成为二人创作的重要主题。这些作品亦有相通之处,如评价亡友的价值标准,就是看其是否纯洁朴实、踏实稳重。那些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的人,往往会赢得他们的特别赞许。他们所推崇的人格,都较为符合传统儒家文化讲气节、重操守以及仁义为怀、安贫乐道的道德观念。这与巴金、靳以本人立身行事的价值观念,是完全吻合的。在抗战时期,这样高尚的品性,也为中华民族所特别需要。不过,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巴金、靳以对亡友的悼念,会有不同维度的表现。通过细致解读巴金、靳以的怀人散文,可以管中窥豹,探询这对老朋友不同的创作取向。
一、巴金:伤悼与忏悔中的自我透视
(一)怀友与自剖的双重呈现
巴金在《纪念友人世弥》中,对于作家罗淑的回忆,更正了罗淑在别人眼中只是贤妻良母的形象,而格外强调了其作为社会革命斗士的色彩。同时,还写出了罗淑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及善于为朋友排忧解难的能力。而对于巴金本人,文本中的罗淑,似乎更像是精神导师:
这三四年来,我在生活里、事业上遇到各种麻烦,我缺乏忍耐,不能从容地应付一切,常常让自己沉溺在苦恼中间。朋友不宽恕我,敌人不放松我。我不能严格地改正错误,我反而让自己陷在绝望的心境中。好几次我带着气愤到她那里倾诉,她仔细地开导我,安慰我,甚至指责我的缺点。她知道我的弱点、我的苦恼和我的渴望。但是她绝不姑息她的友人。我是在朋友们的督责下成长起来的。她便是那许多朋友中间给了我帮助最大的一位。[1]473
熟悉巴金作品及其为人的读者, 当不会把这样的文字,仅仅视为单纯悼念逝者的溢美之词。因为巴金在多篇作品中,反复渲染过这样的个人感受,即他一直在作家与改造现实的行动者之间痛苦徘徊。此外,巴金总是以固守己见的姿态,参与各种文坛论战。来自方方面面的不理解和攻讦,的确时常令其苦恼。正因如此,在巴金的生命中,一直把朋友看得极为重要,友情也因之构成他创作的重要母题之一。“你留下了这么深的敬爱在我们中间,我们失去了你这样一个连锁,可是我们已经坚实地团结起来。”[1]474巴金特别看重罗淑在朋友中间的“连锁”作用,也正源于他对友情的格外重视。
在《怀念》集的其他作品中,巴金几乎都把逝去的朋友描述为像罗淑那样,即对自己的人生给予了切实的帮助,甚至对自己的思想予以了深刻启迪。所以,巴金怀人散文的典型特点,就是以浓郁的抒情方式,对逝者予以无尽的哀悼和无限崇敬的赞美。《悼范兄》一文,在对科学家、教育家陈范予的缅怀中,巴金突出了其人格的魅力,如这样描写陈范予饱受病痛折磨而不屈服,“你以一种超人的力量平静地吞食了那一切难忍的病痛,将它们化作生命的甘泉而吐出来。难道世间还有比这更强健的人?还有比这更美丽的生命的表现?”[1]480巴金还讲述了陈范予切实的工作作风与科学的思维方式对自己的影响:“靠着你,我多知道一些事情,我知道怎样节制我的幻想,不让夸张的梦景迷住了我的眼睛。”[1]476并在结尾饱含深情地写道:“我想起了一颗死去的星。星早已不存在于宇宙间了,但是它的光芒在若干年后才达到地球,而且照耀在地球上。范兄,你就是这样的一颗星,你的光现在还亮在我的眼前,它在给我照路!”[1]483
在《怀陆圣泉》中,巴金同样以充满诗意的笔触,高度赞美作家陆蠡:“有时候等着我们的还是一个上海的寒夜,但我的心总是很暖和,我仿佛听完了一曲贝多芬的交响乐,因为我总是和一个崇高的灵魂接触了。”[1]535陆蠡于1942年在上海被日本侵略者杀害,巴金虽未得到陆蠡明确的死讯,但已然能够猜测到其落入虎口后凶多吉少的命运,不过他仍在文中深情地呼唤老友的归来,也相信所有爱理想、爱正义的读者,与自己的期待一致:“要是他们有一天读到圣泉的书,知道圣泉的为人,明白他的爱和恨,那么他们会爱他敬他,他们会跟着我们呼唤他,呼唤他回来,呼唤那个昙花一现的崇高的心灵重回人间。”[1]537也正因对朋友的敬重、对友情的珍惜,巴金的怀人散文都写得甚为哀痛,语气沉重,声声带泪,字字滴血。
值得注意的是,巴金的怀人散文,还不时流露出很强烈的悔意,即对在逝者生前没有更好地珍视友情的追悔。《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是怀念作家缪崇群的,巴金像描述与罗淑的交往那样,道出了自己在烦恼之中,格外需要对方友情的心声:“这时候我多么需要友情的安慰和鼓舞。我想找个机会去你那里同你畅谈一两个整夜,因为在朋友中你是比较了解我而又愿意听我发牢骚的人,正如你自己所说,你‘一直在系念着’我,而且恐怕再也没有像你这样系念着朋友的人。”[1]500-501而在听闻对方的死讯时,对于没有珍惜友情的哀痛,溢于言表:
只有在这时候我才知道我的损失是多么地大。我失去了一些永远找不回来的东西,一些我应该珍惜却没有好好珍惜的东西,在我们相识的十四年中间,我不知错过了多少次和你相聚、和你通信的机会。我没有好好地认识你的纯白的心灵,我也没有尽我的力帮助你跟疾病、跟困苦挣扎,我也没有尽我的力帮助你安排一个较好的生活,我给你的只是一些空话,一些不能实现的希望。一直到你死,我没有能给你一点安慰,减轻你一些寂寞和痛苦。作为一个朋友,我辜负了你的信任了。[1]502-503
还有一些忏悔性的文字,是不能与危难中的友人共患难而引发的:“你们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不设法透出来一点消息?或者你们真的不存在了?或者真的陷在了敌人的手里?……我想呼唤你们,尤其是你。……但是这次我却安居在这里,对你甚至无法伸出一只救援的手。”[1]487(《怀念》)甚至,有的篇章为自己还苟活于人间而自责:“我想到伴着你的一片黄沙、一堆山影和几颗枯树,心隐隐地发痛了。原谅我这个自私的人,我独自享受了温暖的灯光和热腾腾的浓茶。”[1]495(《纪念憾翁》)应该说,在那样人人自危的艰难岁月,如此自我责难,是有些过苛了。不过应注意到,这样真诚的忏悔情结,也是巴金写作特有的品质。作家在与朋友的交往中,时时反思自己的不足,毕竟有助于达到“事事反求诸己”、“吾日三省吾身”的人生境界。这对于一个长期缺乏宗教忏悔情结的人文环境,不失为有益的弥补。越发浓重的忏悔意识,也无疑帮助巴金提升了创作的境界。他在新时期推出的具有重大影响的《随想录》,就是其一生忏悔意识的结晶。
(二)追悼背后的深层原因
巴金还在深挚的友情书写中,感同身受地借亡友透视了自身。《写给彦兄》在悼念作家鲁彦时,指出了其作品曾对自己的影响:“那种热烈的人道主义的气息,那种对于社会的不义的控诉,震撼了我的年轻的心。”[1]496在肯定了鲁彦以其不肯屈服的个性,像一个勇敢的战士之外,从他人的角度指出他也存在缺点,不过马上就笔锋一转,既对鲁彦予以理解之同情,又流露出自我的悔恨:“不管他看重你的好处,或者注意你的缺点。你两样都有,因为你是一个人。而且我们谁又没有更多的缺点呢?况且作为一个十几年的朋友,我在你的苦难中给过你够多的助力么?我分尝过你些许的痛苦么?”随后道出了这样的心声:“彦兄,我不是在为你哭,我是在哭自己。我那时就想到在你身上也活着我一部分活动、快乐的岁月,它们快要跟着你死去了。”[1]498这里,既有对朋友的伤悼,更以一种镜像化的方式,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剖析。巴金创作所一直秉承的,不正是根深蒂固的人道主义精神吗?巴金所给人的永恒印象,又何尝不是对社会不义发出激烈控诉的文坛斗士?而在战火中颠沛流离、饱经苦难,更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巴金在为逝去的友人悲悼,同时也悲悼着自己。巴金的友情书写,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众所周知,巴金曾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早年作品经常出现这样的话:“我不怕,我有信仰!”信仰之所以支撑着他不竭的创作,“唯一的原因就是他相信他的安那其主义的理想‘胚芽’,将来必定会成长壮大,只要是符合人性的思想,总有一天定会成为社会的现实。”[2]然而,无政府主义以其激进的反传统色彩,对于美好人间乐园的建构,经过现实的检验,备显乌托邦色彩。也正因如此,早期巴金作品一方面在充满理想主义的人物身上,对人类未来寄予热切希望,另一方面却多以悲惨的结局收场,笼罩着阴郁、颓废的气息。“抗战爆发后的巴金积极投入到反法西斯主义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开始淡化他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是因为他看到法西斯主义比传统主义更具有毁灭人类的危险性。”[3]如果说,时代风云促使巴金对以往的信仰有所反省,在不可缺少的心灵家园寻觅中,他则时时需要同道的指引、友情的浸润。所以,在他的怀人散文中,总是满溢着浓浓的友情和深深的感伤。
抗战的爆发,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分水岭。许多个体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死亡”不可避免地成了作家创作中的一个核心词汇。在战乱中面对死亡、体验死亡,使巴金增加了对于死亡的深切理解。他在锥心刺骨地悼念友人的过程中,不但传递出人间的至爱情怀,大大摆脱了凌空蹈虚的所谓信仰,对现实生活有了深切的思考,还强化了对于人的命运问题的深入探寻。他的怀人散文,不但表现出对于侵略战争轻易剥夺人生命权利的痛恨,还表现出个体生命在战争时代的脆弱,以及人类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荒诞感。通过怀人散文,也可以折射出巴金创作所发生的蜕变:他在抗战爆发后的作品,既切近现实人生,又增添了建基于人性体验之上的深刻哲思,早期那种朦胧而虚无的理想主义色彩则渐趋消散。
二、靳以:品文与论世里的激切呼声
(一)自身观念的充分折射
靳以在创作初期,曾以浓重感伤色彩的爱情小说为文坛所瞩目。巴金对于友情的看重,在靳以的怀人散文中也有体现。但是除却沉痛的伤悼与缅怀色彩之外,更能看出靳以与巴金不同的重心所在。如果说,巴金在《写给彦兄》中只是隐微地从亡友那里,找到文学创作的共鸣。靳以的独特之处则在于,他总是在悼念朋友的过程中,倾向于充分表露自己的文学观以及人生观。
同巴金类似的是,在靳以的《悼罗淑》中,也把同罗淑的友谊,建立在其对自身个性的体察之上。比如,靳以说自己不善于和陌生人尤其是女性打交道,但是与罗淑一见如故,这就强化了同逝者的同道之感和真挚友谊。不过,如果说,巴金从敬仰的角度描述他个人的一些弱点,以及罗淑对其的精神指引,靳以则运用了一种相对平视的方法来书写逝者。比如,写到他在给罗淑的作品《生人妻》提修改意见时,罗淑表现出了羞赧、谦逊、感激的态度。“那不是因为受了别人空妄的阿谀,那是因为一个苦心的创作者作品中的心血不曾被人忽略时所应有的衷心的喜悦。”[4]331尽管这里并无对于《生人妻》的具体评价,但是可以清晰地看到靳以在怀人散文中,喜欢谈论作品与创作的倾向,这在其他作品中,则有更为鲜明的呈现。
在《忆崇群》中,靳以在回忆与悼念亡友之外,同样添加了对于文艺的探讨。很有意味的是,此文用了很大篇幅,提及他本人的散文集《人世百图》:
为着使它犀锐,为着使人看不出是我的作品,我把笔调整个改换了。说是《人世百图》,所写的题目无非是禽兽们,在那中间巧妙地寄托我的憎恨和喜悦。为了时时不使我的文笔显露出来,我写得很吃力,有时好像我必需忘掉我自己才能下笔。可是这却没有逃过他的眼睛,在信中告诉我知道是我写的,而且表达出他的说不出的喜爱。[5]129
平心而论,《人世百图》的题旨相当明显,以种种动物比附丑恶的人类,意象显豁,语调夸张,并非佳作。可是,这里明显看到靳以的自负,而且对缪崇群对自己作品的赞赏也欣然接受,由此强化了二人由文坛知音而生发的友情。
至于《忆陆蠡》,更可看出靳以与巴金相较,其怀人散文别有幽怀的一面。靳以在颠沛流离的途中,不断把长篇《前夕》寄往陆蠡坚守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前夕》在上海出版后,敌人把宣传抗日的《前夕》与其他进步书籍,共抄走了两卡车。陆蠡以其大无畏的正义感,去与敌人交涉,结果惨遭毒手,再也没有回来。巴金、靳以对此过程都有记述。不过,巴金在《怀陆圣泉》中,着重刻画了陆蠡高尚的灵魂,并深情地呼唤老友归来。靳以在《忆陆蠡》中,也有这样的表达,但是同时用了很大的篇幅,交代了自己写作《前夕》的经过。其中有对写作艰苦环境的描绘,更有无比钟情于《前夕》的表述:“每次上过课,我的身心都陷在疲惫之中,唯一能解救我的,还是我的长篇。那才是我心中愿意做的事,一切对于人生的喜怒哀乐,都装在里面了,我也正像活在那中间的一个人物,我不是旁观,我简直分享他们的感情。”[5]133并写出了对自己作品满意的内在原因:“我也相信我的作品,没有一点违背人民的愿望和利益。”[5]134耐人寻味的是,靳以并没有对陆蠡之死流露任何的愧疚。
尽管靳以不能承担罪责,也无法扭转好友的命运,但陆蠡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并最终被折磨致死,与靳以还是有关联的。试想一下,巴金在面对与己相关的好友悲剧时,又会作何处理?按照他在怀人散文中所体现出的深重的忏悔情结,想必一定会对好友的不幸表现出深深的愧疚之情。
(二)激进的文学主潮追随者
以巴金的一贯立场来要求靳以,也许有些过苛,不过从中却能看出二人文学观念的重大分途。以往研究经常将靳以与巴金相提并论,比如有论者这样比较二人:“巴金热烈,常常发出激越的吐诉,而靳以则偏于冷静,更宜于娓娓地倾谈。这后一种个性形之于文字,则是那一派优雅恬澹。”进而如此概述靳以的小说风格:“这是一个平凡的小说家。……他的形象世界没有恶的极致,也没有善的极致,却有契诃夫式的柔和的忧郁。这种美学风格无疑反映着作者对生活的理解,——理解也那么平凡。”[6]实际上,与这种“平凡化”解读恰恰相反,与巴金相比,靳以始终是一个更为关注并充分介入现实的作家。并且,随着靳以在四十年代以后越发激进,他创作中的人情因素也越发稀薄。其鲜明的表征就是,只要不符合历史潮流的人物,都该被时代所无情地淘汰。在这样的主题异常显豁的《前夕》的结尾,黄俭之、黄静宜等人在出走途中,因沉河而遇难,就是这种单线历史进化论的鲜明图解。而巴金,也与以上论述并不完全一致:通过对于人道主义精神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于人生体验的淬炼,他在20世纪40年代完成了个人创作的蜕变,推出了《憩园》、《寒夜》等深沉凝练的优秀作品。同巴金相比,靳以的创作在抗战爆发后,则越发乏力。总之,通过二人的怀人散文,可以折射出他们对于人道精神、人生体验的不同理解。也许,正是这方面的差别,对于两人的创作走向,乃至总体艺术成就,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靳以与巴金的另一重要区别还在于,他不像巴金那样,在强调朋友对其人生提供重要帮助的前提下,对逝者夸赞、溢美成分较多,而是在自身的人生观乃至文学观的视野中,来对朋友予以态度明确的评价,有时甚至不惜予以尖锐的批评,即便是亲密的师友。比如对亦师亦友的郑振铎,靳以在《不是悲伤的时候》中,曾从知己的角度予以评价:“在是非善恶之间,他反应得很敏锐,也很强烈;任何时候从他的脸上就一直可以望到心底,他掩不住心底的快乐和愤怒,虚情假义简直和他没有一点关联。”[4]537不过,他同时一再书写与郑振铎的多次争论,还对郑振铎交友眼光不准、在抗战期间长期蛰伏有所颓唐等,都予以严正的批评。再如,靳以这样回忆大学时期所尊敬的老师孙寒冰:
当我离开大学以后,我们就相隔得极远了,在空间的距离和精神上,也许那完全出于误解或是他那永远向着善良一面的天性,他的一些言论使我不能同意,就为了他那和什么样的人都能相处或是放大别人一星的善性掩盖其余的恶点的个性,就极容易地把自己陷入使别人不能了解的地步。那时候我们无从相见,我想如果能见得,我一定会向他剀切说明的。[4]323
(《孙寒冰先生》)
可见,凡涉及到他所认为的原则和立场问题,主要体现于是否追求进步,及对人性善恶的看法时,靳以都会直言不讳。这与巴金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靳以直爽耿介的性格,固然可以强化其创作个性,其旗帜鲜明的倾向,也可以作为巴金悼念亡友时难免给人夸张印象的一种矫正。不过,靳以对于自身的立场,往往缺乏反思,这也是他与充满自剖意识的巴金相比,在文学旅途中十分匮乏的一个重要因素。
作为著名的进步作家,抗战期间任教于迁到重庆的复旦大学的靳以,在文学青年中有很大影响。文学编辑与教授的身份,使其在很长时间都扮演了文学指导者的角色。作为靳以的学生,束衣人是一位左倾倾向很明显的文艺青年,因受反动势力迫害而罹难。在《怀念衣人》中,靳以透露了自己对这位当时较有影响的青年评论家的深刻影响:“衣人说过我是他在大学里给他最大影响的人……我说的话是多的,可是向他们许多人,也许他从那里得到一些意义;此外就是当我看过他的稿子,我的意见总是很详细地说出来。”在此文中,靳以还肯定了束衣人辛勤的创作态度:“别人也许看到天才的光耀,我看到的是汗和血的结晶,那光辉不是属于一个天才的,是属于一个辛勤的苦作的人。”[5]137这与靳以本人追求如实描画人生、不凌空蹈虚的文学观念,是完全一致的。
束衣人的文学评论充满激进的色彩,如以“文学必须着眼于现实斗争”的基调,来评价萧红的《呼兰河传》,认为萧红与现实斗争脱了节,这对她来讲是一个悲剧。这样的观点,作为老师的靳以,已经先于束衣人表达过了。他在重庆期间曾与端木蕻良、萧红比邻(端木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在《悼萧红和满红》中,他对早逝的萧红表达了沉痛的心情。与束衣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靳以并没有从文学本体方面对萧红的创作做具体评价,而是对萧红不幸的感情生活影响到她的才华发挥表示慨叹:“我们并不只做无为的哀伤,因为我们也了解生命不必吝惜,但是生命的虚掷是可惜。”[5]126同时,他对萧红遇人不淑流露出惋惜与激愤的情绪,尤其对端木蕻良表达出强烈的反感,如认为萧红的文章,“不是那写什么花絮之类的人所配说的。”并且认为,端木是“一个自私的人”,“他自视甚高,抹却一切人的存在,虽在文章中也还显得有茫昧的理想,可是完全过着为自己打算的生活。”[5]125
靳以对端木的评价引人沉思。端木的贵族艺术家作派,在当时的确显得相当另类,不过,对于靳以来讲,对端木的评价仍旧延续了他自己写作中的套路,即以人品论文品,而且最终的着眼点还在他所最厌憎的人性弱点——自私自利。所谓“花絮之类”,显然指端木的作品《新都花絮》,这一描写家境优越的女性在战时生活中的活动尤其是微妙心境的作品,与靳以“以文学作为时代号角”的观念当然不符。虽然靳以没有对萧红的作品做评述,但对于其人生悲剧的看法,仍可以看出他将个人生活态度与人生经历,视为影响作家创作的重要因素。
从靳以的怀人散文中,无不可以看到,他始终念兹在兹于对文学观与人生观的阐发。从对自己艺术上并不出色的作品《人世百图》与《前夕》的喜爱,可以看到靳以鲜明的文学观念,即强调明确的主题的确立,以及真实情感的倾泻。而在悼念逝者的时候,他执着于探讨对方人生观对文学创作、生活态度的影响。这都可以看出,靳以把文学与现实紧密结合的观念,折射出与时代主潮十分契合的强烈的文学功用论。
总的来看,巴金的怀人散文,常常以炽热的情怀,诉说着友情的重要性。在如泣如诉的叙写中,渗透着浓郁的悲伤格调和自身的忏悔意识。而靳以的怀人散文,则充分融入了文学为人生服务的文学理念,凸显出与时代文学主潮密切配合的激进色彩。二人在怀人散文中的分化,也可以在现实中显现出来。靳以于1959年去逝,巴金在《哭靳以》中写道:“这些年总是你走在我的前面,你的声音比我的响亮,你的热情煽旺我的心灵之火,你的爽朗的笑音增加我前进的勇气。”[7]确实,靳以在建国前后追求进步的心声颇为急切,并且对好友提出了相同的要求,甚至为巴金跟不上形势而对其颇有怨言。[8]这与其在怀人散文中的书写,是完全一致的。通过巴金、靳以的怀人散文,以及他们与时代的关联,还可以对他们的创作旅程做进一步的透视。巴金和靳以都曾以个性色彩强烈的作品为文坛所瞩目。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作品,以其充满激情的青春特征,具有强烈的时代鼓动性,但是也存在文学性欠缺的问题;靳以的早期小说作品,虽然也有极端情绪化的色彩,但是由于没有忽视对艺术的探求,所以也有一些足以传世的精品。而在此后的创作中,巴金没有彻底为文学主潮所裹挟,一直坚持人性与艺术的探索,非但在20世纪40年代不断写出小说精品,晚年还推出了振聋发聩的充满反思色彩与人性深度的《随想录》。靳以则渐渐在追随文学主潮中,泯灭了宝贵的创作个性。探讨两位挚友文学旅程的重大分化,对于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何以易于迷失自我,当不无启示意义。
[1]巴金.《巴金全集》(第十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2]汪应果.巴金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41.
[3]耿传明.来自“别一世界”的启示——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与乌托邦心态[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225.
[4]靳以.靳以选集(第五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4.
[5]靳以.靳以散文小说集(上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6]赵园.艰难的选择[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80.
[7]巴金.哭靳以[J].人民文学,1959(12):58.
[8]石健.靳以与巴金的分途——从两篇白俄小说谈起[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5):95-98.
(责任编辑:刘晓红)
2016-02-26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巴金、靳以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15Z174)的阶段性成果。
石 健(1970-),男,玉溪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I207.6
A
1004-342(2017)02-9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