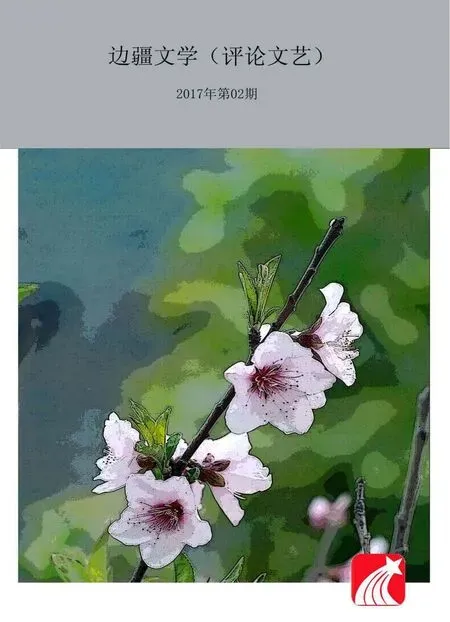我看李更
董宏猷
争鸣广场
我看李更
董宏猷
·主持人语·
本期争鸣栏目所发《我看李更》一文,不无新意。作者认为,批评家、“文坛冷枪手”李更,一直以“文化晃晃”自居。其实,从他自觉不自觉地充当“文坛冷枪手”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再是“晃晃”了,也就是说,“文化晃晃”恰恰是“文化晃晃”李更的终结。因为李更已经有了自己的“位置”:不仅仅是“文坛冷枪手”,而是肩负了文化使命的火炬手与掘进工。李更始终是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不为流俗所淹没的、具有叛逆精神的、始终没有停息过自己的追求的单纯而阳光的作家和思想者。本文作者对李更的深度解析,不仅指出其特立独行的种种优点,也深入分析其不自信、精神上的自卑等毛病,对其矛盾心态有鞭辟入里的分析,更肯定了李更作为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编辑、杂文作家和思想者的价值和意义。(冉隆中)
关于李更,要说的空间似乎不多了。自从他戴上了两顶桂冠——“文坛冷枪手”和“文化晃晃”——之后,他便成了两顶桂冠的品牌代言人了。尤其是“文化晃晃”一说,经朱健国对他进行访谈,并发表《“晃晃文化”与“文人喜剧”》一文后,“晃晃”这一武汉街头的俗语便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某一类人的代名词,“文化晃晃”或“晃晃文化”也成为社会学和文化史上的一个新的发现,成为解剖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一个切入点和一扇窗口。而李更本人,自然是成为一个活的标本,或者注脚,而载入史册了。
平心而论,这两顶桂冠对于李更来说,应该是形象的,准确的,它们至少概括了李更生命历程中的某个阶段,艺术创造的某些特点。尤其是“文化晃晃”,既是李更的自我认同,自我发现,自省与反思,更是他和朱健国共同创造的一个社会学的新名词。这样的创造,不能不说是一种贡献。至少在武汉,“武汉晃晃”迅速地泛化扩张,我在网上不但发现了“武汉晃晃”的同名长篇小说,而且发现了以“武汉晃晃”命名的公司。其经营方式竟然与李更的“文坛冷枪”极其相似,那就是对武汉的餐饮业进行“冷枪手”似的评点。这样一来,“晃晃”便成为武汉这座城市的文化特征之一。
既然是发现和创造,既然是贡献,李朱二人的有关论述在这样一本书的序言中概括提及,我想是必要的。
李更说:没有理想,不能够作战到底的、找不到自己固定位置的人,就叫晃晃。这个新方言现在已延伸到了武汉的各行各业,社会盲流都叫晃晃,在单位时没有正经工作的人也叫晃晃。
李更说:“晃晃”的理念是我现在才考究成熟的,实际上,“晃晃”的精神现象是早就有的。我不知道你读过索尔·贝娄的书没有?贝娄一家也属于晃晃,1924年他九岁时,全家移民美国,在芝加哥定居,1935年,他又转学到伊利诺斯州的埃文斯顿,1937年,又跑到麦迪逊,然后进入谋生阶段,始终在到处晃。贝娄走上文坛的第一部作品是《晃来晃去的人》。是一本日记体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等待应征入伍的犹太青年,叫约瑟夫,我始终认定这就是贝娄本人的内心写照。约瑟夫辞去工作,依靠妻子养活,妄想享受一下个人自由。但是征召书迟迟不来,他整天晃来晃去,无所事事,生活反而越来越空虚,精神也越来越苦闷。他企图在这个混乱、荒诞的世界上寻找“自由”,但这种“自由”反而成了他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他痛感“我们所追求的世界,永远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我们所期望的世界,永远不是我们所得到的世界”。最后只得要求立即入伍,屈服于“荒诞的现实”。后来,贝娄的小说一直是以表达知识分子的晃晃心态作为自己文学的用功点。
李更说:现在的晃晃具有城市盲流的心态,他们自己是带菌者,对一切污染有着天然的抵抗力和融合性。我们不能说他们没有理想或者失去信仰,准确一点说,他们也许骨子里曾经有过使命感,但现实离他们的设想距离太远,他们自感自己的能力承受不了那样的抱负,只好用调侃、嘲笑的心态为自己减压。所以他们普遍抱着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心态,活着,活下去,看看这个世界到底会变成什么样?
李更说:文化晃晃一般都没有吃饭的困难,即如卡夫卡那样不容于社会的人,还可以安于一个谋生的小职员位置。文化晃晃的位置是一种精神属性。
朱健国则说:李更颇忏悔、颇自知之明地称自己只是一个“文化晃晃”——始终在文化圈中晃来晃去,却又一直未能坚守一个高大目标,攻下一个独特行当。他发现,武汉麻将场上的“打晃晃”现象,早已扩大到各行各业,如今中国的“晃晃”太多了。这使我顿生“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些年我们总在大谈新时代的“浮躁病”,却无人捕捉一典型现象一言而蔽之;而今李更所概括的“晃晃现象”,实在是形神兼备地说透了“浮躁”。
朱健国发现:可以说中国现在有几类晃晃——有一种是“航道之内的晃晃”,这种晃晃虽然也在晃,但还未离谱,比方一个作家,他虽然没有始终坚持写高尚理想的小说,有时媚俗写点低级情趣招徕读者,但他终究没有向权势献殷勤,向金钱卖身;有一种是“越过底线的晃晃”,他曾经写过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但受不住种种诱惑,一忽而为政治制造“阳谋”,一忽而为大款制造神像,完全丢失了人格;有一种是“伪晃晃”,他从来就没有真正有理想,从来就没有写出一篇好文章,从来就只想用文学当敲门砖,他虽然在写文章和做生意之间晃荡,但却一直躺在市侩的茶馆里没有动。准确地说,他们只是在文痞与奸商之间“换位思考”。
请原谅我在这里大段地引用了李更和朱健国关于“晃晃”和“文化晃晃”的原汁原味的论述。因为这样的引用能更直接地表达他们思想的原义。故意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弯子,现在,可以直接表述我的观点了:
第一、“文化晃晃”的发现和探寻,是李更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拐点。从“晃晃”到“文化晃晃”的延伸,是从原义到引伸义的过程,从社会层面到人文、精神、信仰层面的过程。同时,也是李更自我寻找、自我反思、自我定位、自我救赎的过程。也就是说,“文化晃晃”的发现和探寻,对于李更来说,无异于一次振聋发聩、醍醐灌顶的精神涅槃。他从解剖自己出发——即朱健国所说的“忏悔”;我所认为的对鲁迅先生“严于解剖自己”精神的继承——进而发现了中国人(不仅仅是武汉人)的“国民性”尤其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巨大的精神缺失:“找不着北”。或者说,缺乏独立人格、独立思想和文化担当的勇气。“晃晃”这样一种状态,既是没有根基,没有立场,没有自我,没有主见,随波逐流,随遇而安,又是徘徊,犹豫,探寻,求索。心有不甘却又无力回天;精神想自由独立却又被现实和物质所压迫不得不为生计而“晃晃”……其间的苦闷、孤独、矛盾、挣扎、无奈和痛苦,无法言说。
第二、“文化晃晃”的发现,以及对其精神历程的探寻,其实是与“五四”精神的一次对接。李更谈到了贝娄,认为他就是一个“文化晃晃”。其实,在历史的转型期,尤其是剧烈的转型和震荡期,先驱者精神上处于“晃晃”状态,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先驱者,不也曾处于“彷徨”的状态吗?鲁迅的痛苦、彷徨、惆怅,显示了他在历史巨变中的悲悯情怀,反思精神。他着眼于对国民性的解剖,“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他的“晃晃”,是想为拯救这样沉默的灵魂寻找出路。因此,彷徨与呐喊,反思与拯救,尤其是文化拯救与灵魂拯救,便成为“五四”精神重要的进行曲。中国的“文革”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中,均是剧烈的前无古人的地覆天翻的大动荡、大变革,大转型,这样的历史巨变,产生“文化晃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这个社会的敏感者、先知者和思想者不甘沉沦、不甘物化、苦闷彷徨、反思探寻的痛苦的求索状态。朱健国之所以对李更的自嘲感兴趣,也是敏锐地感受到了“文化晃晃”这样一个词汇,似乎可以概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这一命题的提出,实际上也就同时提出了文化拯救与灵魂拯救的启蒙课题。
第三、李更说自己是一个“文化晃晃”,并且由此生发开去,最初恐怕是感性的,自嘲的,甚至是策略性的。李更反复提到了“位置”的重要,包括谋生的位置,社会的位置,文坛的位置,等等,我们不难揣测到,在李更的心目中,或者潜意识中,是有一个与“晃晃”相对应的“位置”的。从他对以往经历的自嘲和自省,以及所举的例子看来,最初,他是将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的人,称之为“晃晃”的。与这样的“晃晃”相对应的“位置”,是稳定的单位,稳定的经济收入,是计划经济内的,是体制内的。后来,他又将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沉浮的文化人,即没有公司、工作室等经济实体,仅凭策划大型活动,以创意为谋生手段的文化人,称之为“文化晃晃”,与之相对应的“位置”,是固定的经营形态,稳定的经营方向和经营项目,且有一定成就的文化人。再后来,主要是出于对自身状态的剖析――有固定的工作岗位、工资收入,但却在单位内部被疏离、被边缘化,身有位置而心无所依,于是不得不处于“晃晃”状态。这时的“晃晃”,已经是衣食无忧但却失去现实生活中的“位置”的“文化晃晃”。身在红尘心却在彷徨晃晃,这时的“位置”,已经上升到了形而上,即精神、思想和信仰的层面,身在形而下沉浮,心却在形而上求索。如果这样的分析可以成立,那么,我便感觉到,李更对于“位置”是相当的敏感和在意的。他曾经多次毫不留情地剖析过自己的父亲,一个工人出身的作家,突然就在省作协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是,成也“位置”,败也“位置”,最终被“位置”所累。李更的深刻和可爱、可贵,就在于他敢于拿自己,甚至是自己的父亲开刀,以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语)。但我们也感觉到,李更对于“位置”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这里所说的“位置”,与其说是主流的,中心的,不如说是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群体、某一个文学圈、文化圈、思想圈内,被承认的,被关注的,哪怕被视为另类,视为异端,但在这另类和异端内,也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和话语权的。如果这样的分析也成立,那么,我们将看到一个有趣而严肃的现象:即使是像李更这样,从青年时代,从改革开放的初期,从思想解放的年代,一直是以先锋姿态、现代派姿态出现的文化人,在其思想谱系中,仍然深深浸润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对于“名”,是相当重视的。“名正而言顺”,“名不正而言不顺”。而在“名”的内核中,“位置”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这样的分析继续成立,那么,我们就可以体味到李更为什么会自嘲,为什么会以调侃的口吻来反思:那是一种没有位置、或者有了位置却仍然没有位置的彷徨、郁闷、乃至隐藏很深的不平与自卑。这样的情绪,是与一个文化精英、思想先锋却深陷珠海这样的市场经济漩涡中的曲折人生分不开的。马克思说过:“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存,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存,不仅包括我实现着什么自由,而且也包括我在自由地实现自由”。(马克思《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77页)。正因为有了这样巨大的反差,又经历了灵与肉的洗礼与涅槃,李更才从形而下而飞升起来,发现了这个时代巨大的黑洞。“文化晃晃”是李更的不幸,却又是他的幸运。虽然他只是发现了现象,提出了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感性的分析。
第四、现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李更从发现、提出“文化晃晃”这一命题的那一刻起,从他自觉不自觉地充当“文坛冷枪手”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再是“晃晃”了,也就是说,“文化晃晃”恰恰是“文化晃晃”李更的终结。因为李更已经有了自己的“位置”:不仅仅是“文坛冷枪手”,而是肩负了文化使命的火炬手与掘进工。前面已经说过了,李更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个非常具有使命感的热血青年。在我的心目中,李更始终是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不为流俗所淹没的具有叛逆精神的始终没有停息过自己的追求的单纯而阳光的作家和思想者。李更当然有自己的毛病,在我看来,他最大的毛病倒不是“晃晃”,而是不自信,是精神上的自卑,同时,对于“晃晃”状态的自恋。他心怀大志,富有才华,广交天下俊杰,敢于“冷枪”在手。但是,他总是不自信于自己已有的“位置”,于是,才以“晃晃”或者“文化晃晃”自嘲和自慰。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的确影响了李更审美(审丑)视点的聚焦,文化事业的开掘,精神世界的升华。但是,从他拿起杂文和随笔这个武器起,他就从一个“愤青”和“先锋诗人”,逐渐成长为一个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文化编辑、杂文作家和思想者。尤其是他重返编辑岗位,他所主持的文化名人的访谈,以及他所创作的杂文随笔,逐渐成为南中国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这样的风景由于不再晃动,而愈来愈清晰。这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个可喜的渐进与崛起。
最后,我想说的,便是李更这个人以及自选集本身了。“晃晃”李更,出版的作品,都送过我了。非常抱歉,至今我还没有看到李更自选集的具体篇目。对其自选集作品的艺术评价,看来是出书以后的事情了。李更兴趣广泛,是个才子。各种文体,均有涉猎。我读他的作品,除了青锋凌厉,畅快淋漓,便是杂花生树,满眼斑斓。这样一个自选集,应该是他对过去的一个总结。总结也是一种聚焦。对于李更来说,是个大好事。我真诚的希望在自选集之后,李更能够甩掉“文化晃晃”的桂冠和包袱,看准目标,轻装上阵。说老实话,当炉火正红、铸剑正酣、腾飞在即,再以“文化晃晃”自嘲或者自诩,我觉得是不合适的了。李更不是、也不应该仅仅是“文化晃晃”的标本和注脚。中国的作家太多,但是,中国的李更太少。中国不缺少一两个狗屁作家,但是,绝对缺少敢于揭穿皇帝和群臣、百姓没有穿“新衣”的“热枪手”和思想者。这是我对李更热切的期待,也是历史给予李更的机遇和热切期待。
(作者系武汉市作家协会主席)
责任编辑:杨 林

姚黄魏紫 国画 杨跃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