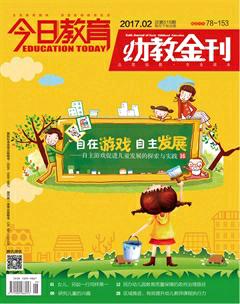儿童与哲学
胡福贞
“儿童”与“哲学”并置,总会使人感觉到明显张力。长期以来,这种并置也确实常被视为悖论。因为既有哲学中没有儿童和儿童的声音;既有儿童生活里也没有哲学和哲学的教育。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哲学家马修斯(出版了被誉为儿童哲学三部曲的《哲学与幼童》(1980)、《与小孩对话》及《童年哲学》(1994))、李普曼(被誉为“儿童哲学之父”)、夏普等开始倡导并大力推行儿童哲学教育之后,并置张力虽有所松动和缓和,但文化影响仍式微。迄今为止,在儿童日常生活和教育实践里,“哲学”与“儿童”仍不太相干,两者关系仍未理顺。“哲学”依然更多被视为关乎高深玄妙主题的理性活动,只有少数“术业有专攻者”能为;而“儿童”也仍多被认为“懵懂无知”“理性未发”且“以感觉形象思维为主”,不能也不适合做“严格的”“批判性的”哲学思考。事实上,“儿童哲学”作为尚未确立起自身合法性的学科,至今在定位上也仍摇摆不定,或指称“关于儿童的哲学”(Philosophy about/of Child),服膺于既有哲学框架和研究范式,关注以儿童为对象的思辨研究;或指称“儿童的哲学”(Childrens Philosophy),聚焦于儿童思考的哲学兴味、方式和效果;或指称“为了儿童的哲学”(Philosophy for Children),致力于对儿童进行哲学教育,尤其是逻辑思维训练。
应对哲学与儿童关系——同时也是定义“儿童哲学”/“儿童哲学教育”——的前提性条件在于明确回答“哲学是什么?”“儿童是谁/什么?”以及“教育是什么?”据我所知,在当下这仍是最想当然、最富争议的基本问题之一,本文暂不卷入这种争论中。
在教育世界,把儿童与哲学放在一起,至少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着三种明显不同的关系类型:其一是哲学本位的关系观。这主要是以哲学之思看待儿童,依循既有哲学范式分析儿童以及审查儿童是否具有进入哲学世界的资格,通常聚焦于儿童地位的依附性和儿童哲学思考的不可能性。其二是儿童本位的关系观。主要是以儿童之在来审视逻辑思辨哲学的局限性与生存/生活哲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以此肯定儿童存在的哲学意蕴,通常聚焦于儿童特质中的游戏性和审美性。其三是教育本位的关系观。强调以教育整合与平衡之道来把握哲学与儿童的关系。既有儿童哲学教育的整合性活动中,高度重视师生对话和共同建构哲学探究共同体,以此发现、阐释并引发、维持和提升儿童思维品质和生活形态的自为性和超越性。
上述三种关系类型彼此定位迥异、内容各有侧重,并在不同文化时期活跃程度不一,尤其在教育世界里受重视的情况很不一样。这与不同历史文化时期的儿童观密切关联,更由不同时代儿童所处的实际境遇决定。
其实,三者本无高下之分。尤其在当代,基于人类文明既有成果和儿童发展境遇,“于宇宙中定位儿童、提升儿童幸福”的社会述求已日益显现,迫切需要在看到上述三者定位不同和层次差别的同时,注重并达成彼此间的平衡和整合。若用一句话来概括,儿童与哲学关系的“整合实践之道”意味着:依循哲学既有规范的技术理路,儿童成为自主的探究者,在教育支持下获得有意义的和谐发展。具体体现在实践路径上则是一体观下的“分而治之”。即以完整的儿童和儿童的完整生活世界来观照和遵循“哲学”“儿童”和“教育”的既有边界——要言之,“哲学”作为“一门批判的技术和艺术”“儿童”作为“逐步被纳入既有(成人)世界的不成熟的人”“教育”作为“有目的有计划地促进个体身心发展的社会活动”——终而至于儿童有意义的和谐发展。此中,在实践中,“整合”一词意味着综合、平衡与全面的同时也超越其上,成为了某种直觉经验式存在。也就是说,儿童与哲学关系的“整合实践之道”既需要尊重并恪守哲学作为“科学的科学”的本有规定,用严肃、规范、理性的逻辑技术来专门对待并精微探究儿童、训练儿童思维能力;同时也意味着儿童作为哲学活动主体,精神世界里呈现出的哲学兴味、哲学思维和表达的合法性地位和发展述求。进而要求当代社会要逐步确立起儿童哲学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平衡好儿童与成人、技术和存在的关系,尊重并理解儿童的哲学兴味(敬畏),关爱并丰富儿童的精神空间(原点),引导和促进儿童的哲学探究(对话),规范儿童的理性思维(逻辑),从而切实提升人类的幸福。
追根溯源,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儿童与哲学的关系状况从根本上取决于哲学的发展状况。人类文化思想史中,除以哲学方式看待儿童外,还有科学的和宗教的方式。从根本上说,区别于宗教诉诸信仰和神启、科学取决于实证和客观的确定性,哲学在寻求确定性的同时,也因反思性和批判性超越着确定性,从而哲学一直“在路上”。体现在对儿童的认识上,长期以来,哲学就以一种“严格的理性思维方式”和根植于惊讶和质疑的“思考的艺术”,既把“缺乏理性的”儿童排除在哲学活动之外,同时又以“小大人”或动植物的简单比附否定了儿童特质和儿童主题的合法性。尤其当哲学缩减为“批判的思考方式”或“推论的理论”时,哲学与儿童的关系极有可能就是疏离乃至对立的:凡是哲学的必不属于儿童,凡是儿童的必与哲学无关。
当然这只是哲学与儿童关系发展史中的一段(不要太乐观,这段历史仍很鲜活地活跃在众多现实场域并发挥着关键性的影响作用)。人类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哲学自身的理性诉求和反思特质使得它不断超越自身。姑且不论自卢梭(被誉为“儿童的发现者”)以降,儿童特性在哲学中被以各种面貌呈现(在人性讨论的框架中,从“神的人”中的“纯善性”/“邪恶性”,“自然人”中的“自然性”,“理性人”中的“非理性/无意识性”,“经济人”中的“游戏性”,再到“游戏人”中的“审美性”),“儿童”(童年)已被视为独立的重要主题,获得了哲学家们日益严肃的专门对待。尤其在当代,当经院哲学日益陷入“危机”、哲学概念日益沦为哲学工作者们自娱自乐的学术方言时,儿童哲学的兴起成为了“拯救哲学危机”的重要现象,哲学与儿童的关系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并因此改变着哲学世界本身。
一方面,哲学以其固有的理性方式、更加精微地审视儿童主题(包括儿童参与哲学的现象),不断调整着立场(从“宇宙本位”到“成人本位”再到“儿童本位”)、视角(从忽/无视、俯视、仰视到对视)和框架(从“欲望克制”“逻辑规范”到“爱智慧”),从而不断深化着儿童阐释系统。當然,这也是“哲学本质上是哲学史”的意蕴所在。当讨论儿童观从“小动物”“小大人”“家国财产”到“儿童是成人之父”“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时,我们同时就需要明白为什么要从一种儿童观过渡到另一种儿童观,这些过渡是如何实现的。
另一方面,哲学世界向儿童敞开大门,把儿童纳入到哲学活动主体队伍中来,从而改变了以往哲学世界中儿童缺席和失语的霸权状态。而一旦儿童成为哲学活动主体、尤其是当儿童本位观得以确立后,哲学就不再限于“以概念和原理等理性方式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以及“对真理以及真理在生活中的恰当应用的满怀激情的探寻”,只是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沉思或学术活动,来构建伟大思想体系/思潮(当然这始终是哲学最富有特色的根本任务)。它必须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和存在状态以及对此的确认和反思,哲学开始充满鲜活的生命意义和生活味道。此时,与其说是哲学发现并提升了儿童,莫如说是儿童拯救和拓展了哲学。
因此,即使相当一部分成年人(和哲学家)还停留在“儿童既令人惊讶地像我们,又令人惊讶地不像我们”的慨叹中,儿童却一如以往,始终在用他天然的好奇、热情、专注和自由,天马行空地探究着这个世界,浑然忘机地在事实与反事实之间想象、推理和判断,并且保持着令人惊讶的平衡和适应。即使用最严格的哲学精神来审视儿童,他们都堪称“哲学家”。而且,“小孩子应该比较可能称为好哲学家,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概念。而这是哲学家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小孩子眼中所见的乃是世界的原貌,他不会再添加任何的东西”(贾德,《苏菲的世界》)。在这里,贾德强调了儿童作为好哲学家“向世界敞亮”的开放状态,但我觉得这还不够。从根本上讲,“好的哲学家”更意味着“整合实践之道”的契合,是那些能以整全平衡的方式做哲学的人,是在生活中充分活现哲学品质与状态的人,与要么相信哲学只是一种专门技术性科学、要么相信哲学影响广阔无边的人们是对立的,因而从结果看,“好哲学”当然也与意见多少无关。
儿童就是以其所是充分彰显着好的哲学家的独特魅力:充沛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天马行空的想象与设计、浑然忘机的游戏和生活、不拘形式的提问与表达……哲学世界也正因为儿童的存在与表达,回归并彰显“爱智慧”的本性,成为每个人(当然也包括儿童)尽可能明智、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