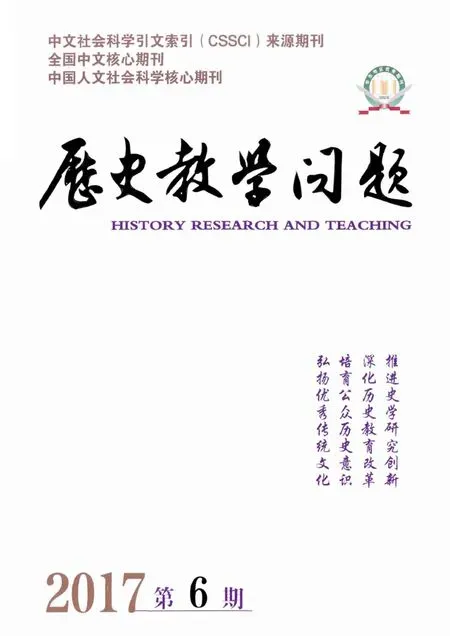观其会通:吕思勉的近代史研究
裘陈江
吕思勉是当代史学大家,一生撰有多部中国通史和断代史,被奉为会通实践“新史学”旨趣的代表。①王家范:《吕思勉与“新史学”》,《史林》2008年第1期。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吕氏通史著作也颇多赞美之词,称其“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为新式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纪元。②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1-82页。吕先生撰写中国通史,多贯通至写作的当下,因此又被称为全通史。③张耕华:《吕思勉〈中国史〉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页。同时他还有以断代史集合为大通史的计划,在谈到断代史的便利时,吕先生说:“断代为史,亦有数便,前朝后代,虽不能凡事截然划为鸿沟,然由衰乱以至承平,事势自亦为一大变,据此分划,不可谓全然无理,一也;纪述当朝,势不能无所隐讳,并有不敢形诸笔墨者,革易以后,讳忌全除,而前朝是非之真,亦惟此时知之最审,过此则又或湮晦矣,史料之搜辑亦然,二也。”④吕思勉:《史通评》,收入《吕思勉全集》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33页。由第二点反推可知,吕先生是深知“当代史”难作的,但仍留下了大量的近代史文字。2016年《吕思勉全集》整理出版,该集对于吕氏文字搜罗详备,故此前虽然学界已有关于其近代史书写的讨论出现,⑤赵庆云:《吕思勉的中国近代史书写》,《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1期,该文对于吕思勉近代史研究的学术特点和贡献多有发掘。但范围仍以《吕著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八种》等近代史专著为限,因此本文以最新版《吕思勉全集》为范围,希望对吕氏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一番全局的介绍,并探讨其学术特点与贡献。
一、作品介绍
吕先生治学不以专门家自居,更不是所谓近代史专家,但却留下了多部近代史专著。后人曾以《吕著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八种》为名结集出版,盛行一时。⑥《吕著中国近代史》最早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初版印行,其中包括《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世史前编》《中国近百年史概说》(全集版改名为《中国近百年史概论》)《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日俄战争》五种。2008年,《吕思勉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汇总印行时,又以《中国近代史八种》为名,在前述《吕著中国近代史》的基础上加入了《中国近百年史补编》(全集版恢复旧名为《初级中学适用本国史补充读本》)《国耻小史》和《近代史表解》三种。据收录各书的内容可知,《中国近代史讲义》和《中国近世史前编》均是吕先生在光华大学为讲授中国近代史所编写的讲义。前者以明代中后期中西交通作为起点,并概述清代盛衰简况,其主体则是以道光年间的中外交涉开始,讲到民国成立为止。最后各设两章综论民国以来的内政和外交,将时段延续到了北伐后全国短暂统一。《中国近世史前编》叙述的起点与前书相同,而以太平天国和捻军结束为止,将其视为“汉族的光复运动”。该书宝贵之处在开首两章综论“近世史的性质”和“入近世期以前中国的情形”部分,且书中不时加以按语,多隽语妙笔,启发良多。《中国近百年史概论》是抗战期间吕先生到常州乡下的中学任教时所用的通俗讲稿,时段从明末到北伐胜利。《日俄战争》1928年收入商务印书馆“新时代史地丛书”初版印行,是中国学界有关日俄战争“最早的研究性著作”。《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以文化史的写作方式,主体原是《中国社会史》中商业、财产、征榷、官制、选举、刑法各章的近代部分。《近代史表解》大约写于1952年,是吕先生建国后结合政治学习和教学实践,参考他自己多年搜辑的近代史素材撰写而成。《中国近百年史补编》,原名《初级中学适用本国史补充读本》,1946年5月由上海中学生书局出版,时段自“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以后。《国耻小史》是早年在中华书局任编辑时撰写的一种文史通俗读物,1917年2月收入中华书局“通俗教育”丛书初版发行。该书用直白的语言,详细叙述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并检讨了清政府在外交中的种种失误。
此外,最为重要的便是通史中的近代史部分,如前所言,吕氏所撰通史多将时间直接贯通至写作的当下,因此有一部分近代史的研究,便是中国通史的后半段内容。在吕先生早期参与编写的两种小学历史教材《高等小学校用·新法历史参考书》和《高等小学校用·新式历史教授书》中,①两本教材分别收于《吕思勉全集》,第22、23册。因为考虑到是小学用书,故以收录重要专题和人物事件为体裁,其中已包括近代的部分。而正式的通史则必须从《白话本国史》说起,②《白话本国史》,《吕思勉全集》第1册。这是吕先生第一部通史著作,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其中的近代史部分,可以说是后来诸多吕氏近代史著作的母版,篇幅和内容相对而言也最为丰满。只是该书绪论中有关近代史的分期与正文目录不符,略嫌体例不纯。“绪论”中原为第五篇“最近世史”,作为“近世史”的延续,时段“从西力东渐到现在”。而正文中实为第四篇“近世史”上中下三部中的下部,共有五章,时段从第一章的“中西交涉的初期”,即明末西学东渐,到第四章“清朝覆亡和民国的兴起”。而因为该书体例关系,在第五章又综论“明清两代的政治和社会”。后续几章从武昌起义开始到其写作当下,则被定为“现代史”。
此后,在其他通史类的中学教材中,也多有近代史的论说留存其中。吕先生一生编写中小学历史教材十来种,其中相对重要而近代史篇幅较为丰满还有数种。如《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③《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吕思勉全集》第20册。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将前一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中绪论与正文目录不符之处加以统一,将近代史的内容主要放入“最近世史”之中,时段以明末“西力之东渐”为引子,从鸦片战争到“民国十一年六月为止”。而细目与《白话本国史》基本一致,内容可说是《白话本国史》的简版。该书最有趣的是吕先生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教授理念,他认为:“这部书,虽系从上古编起,依次而下,然而我很希望用他的人,从最近世史授起——最近世史授完后,接受那一编,可以斟酌情形而定,不必有画一的办法。因为最近世的事和眼前生活较切近,学生容易了解,且容易有兴味。在理论上言,读后代史,必须探其原于古,方能真实了解。在事实上言,读古代史,正须有后代的史事,为之对照,乃觉容易了解。”④同上,第13页。我们无从知晓当时使用这本教材的教师是否按照这种方法实行教学,也无从知道教学效果如何,但可以看出吕先生对于历史教学的独特看法,以及古今贯通的史观。这个观点在《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的例言中也再次得到重申,而这本教材后来曾以《中国史》为名单独出版,也是吕著中国通史系列中篇幅较为完善的一种,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其余如1935年出版的《初级中学适用·本国史补充读本》和《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1937年的《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更简要的如抗战时期在常州教学使用的《本国史(元至民国)》和《本国史复习大略》,都是在中学教材的通史叙述下包含了近代史这个时段。而较为特殊的是在抗战“孤岛”时期所作的《吕著中国通史》,这是为了大学教学需要而编写,上下编分别于1940和1944年出版。其中近代部分内容不多,一部分穿插于上编的文化史中,可与《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参看。下编的最后五章,内容从“中西初期的交涉”到“革命途中的中国”,文字精炼,但相对而言篇幅较小。
在这部分的近代史书写中,可以注意的是吕先生采用的近代史分期方法。有关分期的问题,吕氏在《白话本国史》绪论中,直言只是为了“研究上的便利”。不过在民国时期,史学界关于近代史的分期出现过两种主要的不同看法。1945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就注意到了这一情况:“第一种认为新航路发见以来,世界的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然有不同的地方,是为中古史与近世史的分界;这时期历史孕育出未来的局势,每以民族的思想为其演变的原动力;故近世史的范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来的历史,无论中国与西方皆系如此:此派可以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世史》为代表。第二种则认为在新航路发现的时候,欧洲仅产生了商业革命,明季以来,中国虽与西方接触,但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其后欧洲产生了工业革命,中国与西方发生新的关系,以中国言方系近代史的开始:此派可以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①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83页。由此结合吕先生的近代史作品,可知其采用的分期方法更接近于第一种,非如第二种那般界线分明。
近代有关中国历史的分期,很大程度上借鉴自日本人桑原骘藏《东洋史要》等著作,以上史、中史、近古、近世四期的分法,②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1页。近代史的出现,则是在古史分期框架下出现的新问题。吕先生的通史大体也是延续前面这种线性分期的思路,这从他采用“最近世史”这种提法便可看出,③《白话本国史》绪论和《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目录均采用这一分期名称。可视作是贯通的意图,也可说是便利研究。不过吕先生认为近代中国毕竟与前代差异巨大,他曾就中国文化的演变轨迹,将其分为三个大的时期:1.中国文化独立发展时期;2.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时期;3.中国文化受欧洲影响时期。其中第三期指的就是近几百年来的历史,“欧洲人因为生产的方法改变了,使经济的情形大为改变。其结果,连社会的组织亦受其影响,而引起大改革的动机,其影响亦及于中国”,从此“交通无法阻止”,且“时时在改变之中了”。④《中国近世史前编》,《吕思勉全集》第13册,第125页。以明末西学东渐作为近代史起点的分期中,吕先生还对重要的时间节点作了一些细分。他主张这一期历史还可以分为两个“小期”,五口通商是前后两期的分界线:前一期西力虽已东渐,但“一切保守其旧样子”;后一期“外力深入,不容我不感觉,不容我不起变化”。⑤《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第四章《本国史时期的划分》,《吕思勉全集》第20册,第188页。而若以中国的反抗着眼,则又可分为:“一自欧人东来,至清末各国竞划势力范围止,此为中国受外力压迫之时代;一自戊戌变政起,讫于现在,此则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也。”⑥《中国近代史讲义》绪论,《吕思勉全集》第13册,第6页。此说另见《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吕思勉全集》第20册,第13页。由此可见,吕先生采用的分期方法并不是一个固定僵硬的模型,而是在讨论具体问题和编排不同教材时,采取变通的手段。当然不可避免的是,由于“当代史”的敏感,吕先生的写作还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例如民国时期教育部规定“民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单列为现代史”,⑦张耕华:《吕思勉〈中国史〉导读》,第5页。建国后官方和主流断定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史开端等等。不过吕先生往往只是在学术讨论的前提下,尽量作出变通,决不违背学术求真的根本。
二、吕氏近代史研究特点
五四之后,随着思想解放,尤其是古史辨运动搅动了整个古史研究界,疑古、考古、释古等各家各说迭出。⑧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收入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64页。同时也伴随诸多新史料的发现,使得古史研究成为显学。⑨顾颉刚1945年在《当代中国史学》中提出:“最近二十多年来古史的研究,可说是当代史学研究的核心之一。”见该书第122页。但也有学者开始关注近代史的史料搜集和研究,1930年,同样是古史辨领军人物的顾颉刚曾致书罗家伦,感慨“青年学子喜治古史,而不喜治近代史”,因而鼓励罗氏从事于近代史的鼓吹和研究方法的探讨。①罗久芳、罗久蓉编辑校注:《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第384页。顾颉刚还曾说过:“史学本来以现代为重要”,见《当代中国史学》开篇首页。罗家伦是五四新人中最早关注近代史料整理和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之一,早在1928年,他留学归国后不久就有两篇关于近代史研究计划和设想的文字,并与顾颉刚多有交流。②1928年,罗家伦致信顾颉刚,该信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为题发表在《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年第2卷第14期。另有演讲录一份《怎么研究中国近代史》,刊于《燕京大学校刊》1928年第9期。到1931年,罗家伦又写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这篇纲领式的文章,提出近代史研究的必要性,以及在当时少被重视等问题。深究其中原因,罗氏认为:“第一是因为学者的好古心,觉得材料愈古的愈可尊重(不可一概而论,有许多真正的古史学家,并不忽视近代史的重要)。第二点是因为恐怕时代愈近,个人的好恶愈难避免,深怕不能成为信史。第三点,是因为恐怕许多材料不能公开,将来发见,以后他人要来重写,自己的著作不能成为定史。”③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1年第2卷第1期。该文也曾作为郭廷以1940年主编出版的《近代中国史·第一册》的引论。就罗氏所提第一点而言,吕思勉先生恰是这样一位重视近代史的“真正的古史专家”。④吕思勉在《中国近代史讲义》绪论中讲:“历史知识信莫贵于现世。”又讲:“然事之真相难穷,而人之知识有限,就凡人识力所及,原因结果,要不能无亲疏之分,然则举吾侪认为与现在有直接关系之事,搜集而研究之,夫固未为不可也。所谓近世史者,其义如此。”见《吕思勉全集》第13册,第6页。
吕先生曾讲过:“史事后先一贯,强分朝代,本如抽刀断流。”⑤《史通评》,《吕思勉全集》第17册,第232页。吕思勉在《中国近代史讲义》绪论中也讲:“史事前后相因,又彼此皆有关系,欲强分之,正如抽刀断流,不可得断一事也。”见《吕思勉全集》第13册,第6页。他很多近代史的论述,均是中国通史和通史教科书的延续部分,正可见其对历史通贯性的重视。例如,在《吕著中国通史》上编讨论清末以来地方“尾大不掉,行政粗疏”的问题时,他便从元代设立行省制度说起,认为其中症结在于行省制度导致地方一直过于庞大无伦,且明清两代虽略有析分,但区域一直未能改革。而这个问题延续到民国,又因为辛亥革命中各省纷纷以独立的方式完成光复,所以即使民初“裁兵议起,又改称督理或督办军务善后事宜,然其尾大不掉如故”。⑥《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全集》第2册,第83-84、86页。在《中国近百年史概论》讨论近代南方人才辈出,带动社会变动的现象时,吕先生便从历史上中国北中南三带的变动差异说起:“中国地分南北中三带,北带本为政治之重心,然遭异族之蹂躏,又水利不修,生业憔悴,在近代,文化反较落后。中带是五胡乱华以来,即为中国文化之保存者,又为全国产业之重心,然其发展,偏重产业、文化方面,政治上、军事上之力量不足。惟南带地势崎岖,交通不便,发达较迟,故社会之矛盾不深,其民气最为朴实强毅。近代对外之交通,西南最早,故其渐染新文化亦较早。”⑦《中国近百年史概论》,《吕思勉全集》第13册,第210页。因此,如太平天国的平民起义以及士人阶层中康梁的改革派和孙中山的革命派均起于南方。从这段议论可以看出,吕先生不仅史识通贯,且视野极为宏大。正如在《中国近代史讲义》正文开讲“中西交通之始”时,首先便从自古中国通向欧洲的海陆通道开始,宛如一幅以欧亚大陆为中心的地图缓缓在读者眼前展开。⑧《中国近代史讲义》,《吕思勉全集》第13册,第7页。这种宏观的视角,多见于吕氏其他通史和教材之中。其对于历史宏观叙事的把握,不仅为研究者提示门径,同时为基础教育也指出方法。如吕先生在《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中便认为:“初中学生读历史,实在只要知道一个轮廓,过求详细,反要连轮廓而丧失掉的。”这种对包含历史时空观念的轮廓的强调,也可以为当今历史教学者鉴。
在吕氏近代史的文字中,不仅可以看到其读史的体会,更有阅世的经验。这一点尤其可以反映在其对史料的搜集和积累上面。据吕先生自述,他在甲午战后便有读报的习惯。由现存大量的剪报资料可知,他对于平时身边报刊史料的搜集是时刻在意的,如庚子、壬寅两年的日记中,便每天都有报章的摘录。日记中还存录了大量报刊上的物价史料等,可惜原有剪报在抗战中亡佚了。⑨李永圻、张耕华编撰:《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6-69、74-75页。日记中尚有诸多物价史料,更是吕先生亲历所记。此外,吕先生自己还撰有大量有关近代史的研究和时论文章,兼具研究与史料价值。如《三十年来之出版界》和《追论五十年来之报章杂志》二文,①《论学丛稿》上,《吕思勉全集》第11册,第331页;《论学丛稿》下,《吕思勉全集》第12册,第815页。对于晚清以来报章杂志和相应人物的流变及作用梳理得十分清晰,且加以个人的感观经历,因此多有洞见卓识。在《追论》一文中,吕氏论及辛亥革命后的言论界情况,认为国体虽更,但“言论界之势力,一时仍操诸旧人物之手,以新起者多浅薄无足观也”。这里的旧人物指的是康梁这样的老新党,但他认为其“针砭时弊之作,可谓深切著明。然时社会之机运,方当舍旧谋新,而二人皆以旧观念相箴规,欲释其新而反之于旧,故其机卒不相契”。因此到二次革命后,言论界更加死气沉沉,惟有《新青年》稍留一线生机,为五四运动后的新契机埋下种子。但随着五四以后杂志日多,而势力分散,此后再无言论界的重心了。吕氏将民国伊始到五四运动这段较受忽视的言论界动向描画生动,展现这个过渡阶段的实情和意义。②《论学丛稿》下,《吕思勉全集》第12册,第816-817页。吕先生对于当下史料的重视,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敏锐感和责任感,也可看出其读史阅世的精神,借用克罗齐的话,真正达到了“历史和生活的统一”。③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页。
余 论
前揭罗家伦1930年初系统讨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论文中,他还提出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中须注意“连续性与交互性”这两个要点。连续性实则就是通贯性,就交互性而言,罗家伦认为:“中国近代史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而且是一个最有趣味的对象。”④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1年第2卷第1期。其中原因当然就是近代开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趋紧密,且无日不处于变化影响之中。若将这两点对应到吕思勉的近代史研究中,也都可以一一吻合。吕先生在《史籍与史学》中就讲:“史学者,合众事而观其会通,以得社会进化之公例者也。”⑤《史籍与史学》,《吕思勉全集》第18册,第9页。其中“观其会通”四字,1934年吕先生还作为题词,专门赠送给《光华年刊》。若将这“会通”二字拆开理解,也正是交互性和连续性的意思。
另外可注意的是,吕先生一生治学服膺梁启超及其“新史学”,因此他在《现代史学家的宗旨》一文中说过:“现代史学上的格言,是‘求状况非求事实’。”“求状况的格言,是‘重常人,重常事’,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这种历史眼光,一方面是史学方法层面强调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另一方面,实为平民的眼光,强调一种群体的历史。具体如《中国近世史前编》中,吕先生对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毁灭大量文物一事,就表达了独到的看法。他认为:“(一)文化的进退,视乎其社会的情状,是否安和,物质所表现的文明,实在其次。(二)即舍此弗论,以现在文化的状态,虽有宝物,亦必不能终守。此岂独今日为然?亦岂独中国为然?(三)所谓有关文化的建筑品物,一方面固然代表学术技艺,一方面也代表奢侈的生活。后者固绝不足取,即前者,就已往的社会论,并不过一部分人能参与此等工作,大多数人都是被摈于其外的。今后社会的组织果能改变,合全社会人而从事于此,已往的成绩又何足道?所以有关文化的建筑品物等,能保存固当尽力保存,如其失之,亦无足深惜。”⑥《中国近世史前编》,《吕思勉全集》第13册,第159页。这段话展现了吕先生对于一般社会情状安和与否的关照,以及站在全社会大多数人立场之上的态度,二者都是注重“民史”的眼光下必然产生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