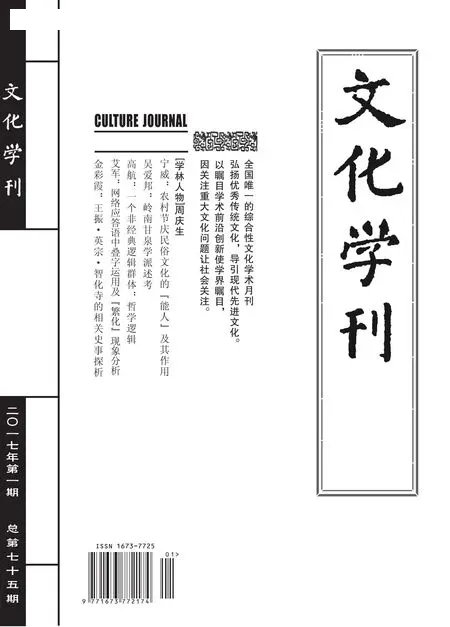《所罗门之歌》中异化现象的研究
王 滢
(滨州学院,山东 滨州 256600)
【文学评论】
《所罗门之歌》中异化现象的研究
王 滢
(滨州学院,山东 滨州 256600)
本文以埃里希·弗洛姆的异化理论为基础,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阐述《所罗门之歌》中主人公奶娃所经历的痛苦和随之而来的异化以及为找回自我所做的努力,旨在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和莫里森对于人性的关怀。
异化理论;《所罗门之歌》;自我
《所罗门之歌》是托尼·莫里森的第三部小说,主要讲述了奶娃回家乡寻找金子却一步步发现自己家族历史的经历。小说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女性主义、神话原型等方面对小说进行了阐释,但很少从异化角度对它做深入、全面地分析。本文基于弗洛姆的异化理论,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小说中的异化主题进行分析,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加清晰理解莫里森作品主题的新视角,同时也是对《所罗门之歌》研究的补充。
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艾里希·弗洛姆结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研究社会的异化现象,以此审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异化及人性扭曲的病态现象,分析人们陷入异化的原因。黑人北上之后,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但心理异化现象却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众多黑人作家对这一群体的关注点,也是本文探讨《所罗门之歌》这部作品中的原因。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奶娃的异化,即人的自我疏离、人与他人的疏离和人与自然的疏离,展现了生活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黑人所遭受的异化。
一、主人公异化的主要表现
(一)人的自我疏离
对于主人公奶娃而言,他的生活可以说是没有目标,也没有意义。他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不满,两条腿也长短不一,身体缺乏一种整体感和协调感。在生活中,奶娃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时才感觉到真实的存在,体现了人的异化与失落。[1]面对白人主流社会,他感到茫然,甚至迷失自己。为了让奶娃在政治上觉醒,好友吉他给予引导,但奶娃却始终默然。他对跟种族有关的政治问题毫无兴趣,甚至“七天”组织的暴力谋杀也没能警醒他。这些情节都表现了奶娃与自我的分离。[2]
(二)人与他人的疏离
个人的行为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将导致个人无法认定身份,同时失去社会认同感,产生各个方面的冲突及焦虑,最终异化于他人和社会。奶娃出生在一个富裕的黑人家庭,与其他黑人不同,所以尽管家里有很多黑人租客,但奶娃却都跟他们毫无交集;在奶娃的家中没有任何亲情和温暖,家庭成员之间从来没有推心置腹的交流过,甚至姐姐恋爱的事情都无人知晓。这便促使他形成了自私、无情的性格。小说有描写奶娃对着姐姐丽娜小便的场景,这反映出他对女性的藐视。奶娃和哈格尔相恋14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奶娃对她感到厌烦,他随意抛弃哈格尔就像吐掉口香糖一样,间接导致了哈格尔的死亡。[3]
(三)人与自然的疏离
在黑人的观念中,人和自然是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整体。自然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资源,而且也是全人类的精神家园,它具有治愈人类心灵的功能。人与自然之间的分离将导致黑人的无根感,并使黑人变成没有身份和文化的孤儿般的民族。奶娃的异化就部分源自于他对自然界的陌生和远离。在小说中,奶娃对周围的自然景物毫不留心,对姑姑派拉特咀嚼松针感到惊讶,对南方故乡同伴的亲近自然感到无所适从。这一切,都使得奶娃无法从自然之中获得生存技能和精神养分,更谈不上继承黑人传统文化。
二、异化原因
本文从探讨奶娃异化的表现出发,进而分析根源,探索消除异化的经历和最终的觉悟。身处一个金钱至上、物质主义盛行的社会,黑人身份、家庭关系都是引起异化的原因。
(一)物质主义的盛行
弗洛姆认为,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的巨大精神压力与痛苦。物质越来越成为人无法掌控的力量,影响、支配、占据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人甚至沦为了物质的奴隶。物欲横流的社会使人彼此间变得猜疑与虚伪,人们之间的关系都打上了功利的烙印。对于人们来说,被抽空了社会价值观的心灵变得越发空虚、孤独与无力,从而“异化”了内心世界。
金钱至上观念深深地植入奶娃的脑中,而传统的价值观、亲情观与社会责任感则被金钱贪欲吞噬。在这种被金钱观包围的意识形态下,在他与别人之间形成自私、虚伪、排斥与冷漠的异化关系就势在必然。小说中,奶娃给哈加尔送圣诞礼物就充分体现了异化。他准备了一沓钱作为礼物,准备以此结束这段感情。奶娃一方面沉溺于对物质的追求,另一方面又觉得精神上的需求无法在这个社会中得到满足,越来越感觉生命的无意义。
(二)黑人身份
在美国,黑人不仅承受着白人的歧视,而且还需忍受自己人的冷漠。美国黑人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之间本来可以坚守自我,互相帮助,共同努力走出困境。但在面对自己的困境和别人的无助时,他们毫无反应、甚至相互欺侮,试图从同伴的痛苦中获得满足。由此可以轻易看到美国黑人的生活困境及精神荒原。
因为出生在黑人家庭,奶娃无法摆脱白人社会对他及家人的歧视与压迫,残酷的现实让他感受到无助和无奈。他要持续忍受“身份危机”的折磨,体会不到生活的意义和努力的价值。于是他开始鄙视和厌恶真实的自我,完全不能忍受自己在社会上的无能,最终促使他走向了极端,走向了自我异化。
(三)家庭关系
美国黑人远离非洲文化,又受到白人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影响,所以他们在北上之后在心理和行为上产生了诸多变化,导致许多家庭不幸福、婚姻不和谐。梅肯与露丝两人正是如此,夫妻之间没有互相爱戴,互相关心,取而代之的是漠然和相互鞭打。梅肯对地位和财富过于痴迷,也导致其教育子女以财富的占有为目的。他教导儿子奶娃对黑人施加更严厉的剥削和压迫。他的女儿去上大学不是本着提高自身素质的目的,而是为了提升资本以钓“金龟婿”。作为丈夫,梅肯不能承担相应的责任;作为父亲,他也是失败的,儿子奶娃也深受其影响养成了不尊重女性、始乱终弃的性格。母亲露丝给予孩子的仅仅是哺乳喂养。对于奶娃而言,家庭不再是幸福的港湾,父母也不再是孩子的保护神。父亲给孩子带来了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母亲根本不去了解孩子,对孩子的痛苦无能为力甚至是漠不关心。母爱的缺失使奶娃极其缺乏安全感,对女性充满了不信任,进而失去了爱的能力。[4]这也是他远离人群和社会的重要原因。
三、走出异化的途径——精神复苏
彼拉特是奶娃回归路上的指路明灯,她母亲般地给予了奶娃爱和精神力量。彼拉特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奶娃,她对黑人历史的讲述激发了奶娃对祖先的崇拜,使奶娃有了归属感,使其人性开始复苏。在彼拉特的影响下,奶娃抛弃了拜金主义,接受了黑人信仰,了解了黑人文化和历史,对民族身份有了自豪感和认同感,学会了责任和担当,精神也得到了升华。
主人公大多数在发现自身处于异化状态时会抵制与逃离,整个人物形象也会随异化而变得进步与完善。为了摆脱他人的控制以及异化的环境,更重要的是为了寻找家族丢失的一袋金子,奶娃踏上了回家乡的路。[5]但这场旅行却演变成了一场寻找自我的征程。
奶娃人格独立及精神解放主要体现在其狩猎时进行的观察和独立思考的行为上。奶娃开始直视这个世界,直面自己,在思索中为自己和他人定位。他开始从自己经历的种种苦难中意识到别人存在的价值,意识到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意识到给别人带来的痛苦。他第一次认识到自己应对家人负有的责任,也第一次意识到母亲和哈加尔都是受害者。此时的奶娃已经能够坦然接受一切。于是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逐渐改变了一些生活行为,在姑妈派拉特被吉他射杀的时候获得了新生,摆脱了异化。[6]
四、结语
主人公奶娃,从迷失的浪子到找回自我的寻根人,从在北方时的他者到在南方时的自我,从麻木到热情,从消极避世到积极融入自己的群体,他经历了复杂的心理斗争和艰辛的探寻路程,最终寻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1][美]托尼·英里森.所罗门之歌[M].胡允桓,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36-48.
[2]唐红梅.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托妮·莫里森小说创作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00-105.
[3]章汝雯.托妮·莫里森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89.
[4]朱荣杰.伤痛与弥合:托妮·莫里森小说母爱主题的文化研究[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36.
[5]弗洛姆.“资本主义下的异化问题”[J].哲学译从,1981.(4):68-75.
[6]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64.
【责任编辑:王 崇】
I712.074
A
1673-7725(2017)01-0075-03
2016-10-20
本文系2015年度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西方现代文学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研究”(项目编号:1506084)的研究成果;2015年度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新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西方现代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015SD0109A)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王滢(1981-),女,山东夏津人,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