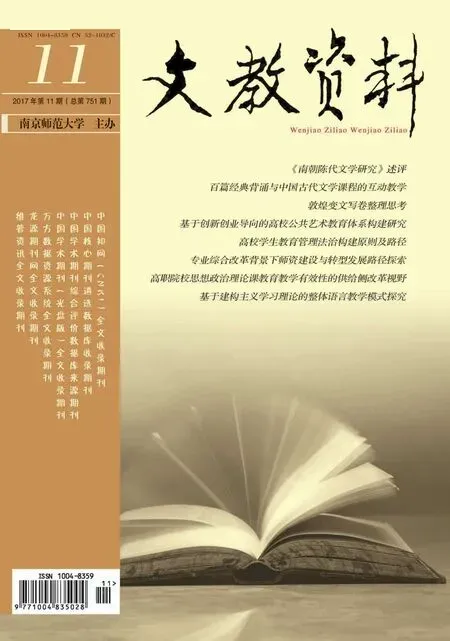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韵致、道心与仙人形象略论
袁俊伟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韵致、道心与仙人形象略论
袁俊伟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晚唐司空图有《二十四诗品》,以诗论诗,对后世诗学风格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并且为后世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其中一些诗学概念进行提取式分析,希图理解《二十四诗品》韵外之致的美学理想、道法自然的精神主旨及饶有意味的仙人形象。
司空图 《二十四诗品》 韵致 道心 仙人形象
晚唐司空图有《二十四诗品》,以诗论诗,品诗之味,超然于尘。搁在当时诗论上以明道衰微,绮伤渐起为主流的乱世里,算是一股美学上的清流。晚唐诗潮文论大抵有几派,“一是主张缘情绮丽文学,寓感伤于风情之中,寄性灵于华艳之间,以杜甫、李商隐为代表。二是提倡隐逸冲淡文学,系忧愤于山水田园之作,含怒骂于江湖隐逸之篇,以皮日休、陆龟蒙为代表。三是宣扬纵情声色的闺阁香艳文学,以韩偓、欧阳炯为代表。四则是追求超逸的诗味诗美,潜心艺术意境的创造,便以司空图为代表”[1]。
一、韵外之致的美学理想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连同其诗论文章,诸如《与李生论诗书》、《与王驾评诗书》、《与极浦书》、《题柳柳州集后续》等,还有其诗歌作品,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生机流动的美学生态体系,尽管《四库全书总目》说《诗品》:“所列诸体毕备,不主一格。”[2]但于此之外,则更有其美学偏向,即以王维等人为标举,追求淡泊隐逸的生活,崇尚自然冲和的诗风。其美学内涵概要地说,是以道心充诗心,用意境铺诗意,融景象于诗境,借味致论诗品,从而提出了他最核心的诗学理想范畴,即“韵外之致”。“韵外之致”具体特征有二。一者,“近而不浮,远而不尽”,是其最明显的感触体征。前者是一种浑成之美,艺术形象必须饱满而充实,后者是情趣韵味的委婉与醇厚。此中可见于其《与李生论诗书》中一句:“噫,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3]二者,“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以传统文论中的景、象而论,更重于由内象内景而生出的外象外景,其与“韵外之致”所并趋,可见于《与极浦书》,其借戴叔伦之言,曰:“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 ”[4]
除此,在“四外”的美学范畴中,“味外之旨”算是“韵外之致”的一种比喻补充,而且以诗味论诗品,算是对于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中关于诗味与趣味的一种发展。见于其《与李生论诗书》,“文之难,而诗之难又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5]。于此可知,醇美难得,味外之旨更是诗之真品。而且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又以味蕾况诗人,并且都是将他韵外之致诗学理想发挥得最完备的两位,即诗风禅淡澄迥的王维与韦应物,其中足见他的诗学指向,“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左丞苏州趣味澄,若清沇之贯达。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焉。元、白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公巨源,亦各有胜会。阆仙东野、刘得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6]。且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又提出了他“思与境偕”的艺术方法,见于“今王生者,寓居其间,浸渍益久,五言所得,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7]。前者主内在之感怀,后者主外在之景象,可谓“融情入景,则寄托遥深,不着迹象,寄意于象,则情韵吞吐,含而不露”[8]。
二、道法自然之精神主旨
整部《二十四诗品》便是用道家自然之道一以贯之,应当是一种血脉的维系。道在文本中常与诸多拟道之词通用,譬如“真”、“素”、“天”、“神”、“自然”等,所以又给道赋予了多样性的形态,算是道的一系列丰富性内涵阐释。简单梳理一下,直接言“道”的有《自然》中“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委曲》中“道不自器,与之圆方”,《实境》中“忽逢幽人,如见道心”;《悲慨》中“大道日往,若为雄才”;《形容》中“俱似大道,妙契同尘”;《超诣》中“少有道契,终与俗违”。其余“真”、“素”、“自然”等更是比比皆是,无须一一列举。司空图言道,便是在追求那种与道相契的境界,由道契心,便是老庄的“致虚极,守静笃”,“心斋”、“坐忘”,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司空图有一首《自诫》,“众人皆察察,我自独昏昏。取训于老氏,大辩若纳言”。他是一种独昏昏的状态,更是出自“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道德经》第二十章)自此点明了道的不可名状,即“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且“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第一章)清人袁枚在《续诗品序》中,又把司空图这种道心引起的道之意境称之为“妙境”,而且古人提笔,多爱引之有出处,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几乎篇篇有老庄之言,如《流动》中“超超神明,返返冥无”,《超诣》中“如将白云,清风与归”,“诵之思之,其音愈希”,所引之多,不可枚举。
道心是血脉所在,亦铸骨骼。倘若从《二十四诗品》的结构布局来看,自可管窥出天地大化之道,道家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所以,《诗品》中以道心为原点,先是生出了《雄浑》和《冲淡》二品,可以看作阴阳二道,其实这也是中国文论中以阴阳划分风格的一种潜体系所在,由 《易经》生发,经过千万年的文论发展,清人姚鼐更是有了阴阳刚柔二体之说。道是流动不息的,讲求周行而不殆,天地万物是一个循环往复、大化流衍的过程。《诗品》既以《雄浑》为首后,又以《流动》作尾,形成了一个圆形的回环结构。其他二十一品,可自由组合,共二十四品,又同中国自古有的二十四节气相吻合。这种本文结构其实多有学者言说,“《雄浑》为《流动》之端,《流动》为《雄浑》之符,中间诸品皆《雄浑》之所生,《流动》之所行也。不求其端,而但其流动,其文与诗,有不落空滑者几希”。还有一位杨廷芝直接说:“是无极而太极也。 ”[9]
三、饶有意味的仙人形象
《二十四诗品》中多出现人物形象,更是符合多道家的仙人形象,可看作骨血的熔铸,此处可略作辑取。《纤秾》中有“窈窕深谷,时见美人”,此中美人非俗艳可比,她从深谷走出,处处“采采流水,蓬蓬远春”,可以看作道家春季里的时令之神。《高古》中有“畸人乘真,手把芙蓉”,畸人就是有道之人,出自“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者也”。(《庄子·大宗师》)而且其能“泛彼浩劫,窅然空踪”,可见早就超脱人世间了。《典雅》中有“坐中佳士,左右修竹”,他们可以看作魏晋竹林中的出世之流。《洗练》中有“载瞻星辰,载歌幽人”,他们“体素储洁,乘月反真”更是出自“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庄子·外篇·刻意》)《清奇》中“可人如玉,步屧寻幽”取自晋朝玄学家卫瓘的掌故。《实境》中有“忽逢幽人,如见道心”,这个幽人更是毋庸置疑成道了。《飘逸》中尚有“高人惠中,令色氤氲”,又是一个可御风蓬叶的道人。如此种种,皆可见道家以道化人之色彩。
饶有趣味的仙人形象镀上了道家文化的色彩,自然体现出了一种道家的人格精神境界,概括而言就是超绝于世、冲和平淡的人格境界。神仙都是世人所化,世人有了道心,如《实境》中“如见道心”,继而与天地自然相契,便是做到了道契,如《超诣》中“少有道契,终与俗违”,如此这般便可谓仙人了。故而这些饶有意味的仙人形象之所以能够体现出道家人格精神,莫非是其拥有了一颗道心。他的诸多诗歌都直言道心,《即事》二首之一有“茶爽添诗句,天清莹道心”,《白菊杂诗》中有“黄昏寒立更披襟,露抱清香悦道心”。这里的道心莫非就是一颗诗心?以道契诗,道就入了诗人的生命,成就了一种人格精神境界,从而可以捕捉到一种他于诗境中所追求的生命体验,“研昏炼爽,戛魄凄肌。神而不知,知而难状”。 (《诗赋赞》)
除却完备且体现道家精神人格外,仙人形象还为我们铺陈开一片道家独有的空灵诗境来,即所谓的“妙境”或者“道境”,他们飘然于二十四种诗境之中,我们看到了“窈窕深谷”里的美人,感受到了那种万物复苏时“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的生机盎然之境,又看到了“修竹坐中”中的佳士,感受到了只有陶渊明笔下才会出现的淡远悠然之境。这些仙家诗境便是司空图所追求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美学理想,余音绕梁,耐人寻味。我们自然可以悟到,这些形象其实都是诗人走进了诗境里,“直致所得,以格自奇”(《与李生论诗书》)、“俱道适往, 著手成春”(《自然》),从而塑造了理想的人格形象,幻化了妙造诗境,由人及诗,由诗入境,由境及人,诗人与诗境浑然天成,物我合一。
总而言之,司空图诗学思想源起,更是“韵外之致”的思想之源,即道心所在。在《与李生论诗书》之最后,有“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10]。算是点出了味外之旨所在,即“全美为工”,味之全,在于无味,即真味、素味,全美即本真之美,有了本真,方才有了其醇美者之所在。本真一词,更是其诗心所在,道心所寄,本真来自于自然之道,道家最讲自然,司空图整个诗学也是从道家老庄哲学里演化而来,稍杂佛家空相之说。既然道心为道家之心,那么司空图的诗学之境,也就是道家纯真素朴、超逸玄远之境,其不可言说,只道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德经》第四十一章)
[1]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40.
[2][清]永瑢,纪昀,编.四库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85:1781.
[3][4][5][6][7][8][10][唐]司空图,著.罗鼎中,注.二十四诗品[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98,99,98,99,99,15,98.
[9]孙联奎,杨廷芝.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M].济南:齐鲁书社,198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