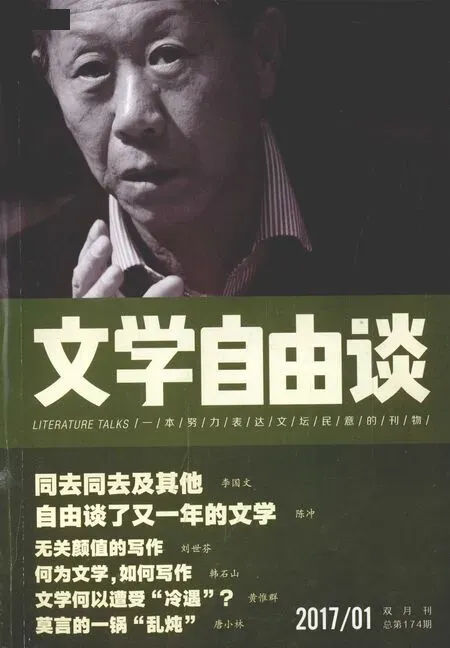妄分轩轾的“危险”
陈歆耕
妄分轩轾的“危险”
陈歆耕
2016 年,中国学界的压轴之作问世,这是一部向莎士比亚与汤显祖致敬的最为厚重的理论建构。
四百年前 (公元 1616 年), 人类星空有两颗璀璨的巨星陨落。他们分属东西方,然而都是文学史上不朽的巨子。穿越数个世纪,人们仍然在剧院和书籍中享受他们的精神创造。 在此刻,想起他们纪念他们品味他们,是出自我们内心的自然生发,而非某个外力需要来擦拭遮蔽着他们的尘埃。对他们的记忆,不需要人为地唤醒。 他们穿过岁月和种种“偏见”,仍活在当下。
就在此刻,评论家李建军先生用一部 30 多万字的专著——《并世双星: 莎士比亚与汤显祖》(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6年 10 月版)——来品评他们的艺术成就和内蕴, 无疑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我有幸成为这部书的首批读者。当然,我也毫不讳言初获新书的担心,担心这部出版社“命题”的书,它进入我们视野的理由仅仅是“纪念”。 读毕全书,我的“担心”被惊喜所取代。 建军先生在这部书中倾注全部心力,挥洒才情,使得这部理论专著成为他多年阅读思考、文学批评积累的一次爆发和飞跃。这部书是理论的,但表达却又是充满激情和诗意的,新见迭出,文采斐然,文气贯通——犹如瀑布,飞流直泻。 即便是望理论而生畏的阅读者,也可以如同进剧院欣赏《罗密欧与朱丽叶》和《牡丹亭》一样,轻松地跟随他一起,进入两位巨星的精神世界。
读此著,最让我受到启发的是,作者提出了一个学界未强烈意识到的重大问题;这是不同语言在转译过程中无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即不同语种之间转译的困境。 因为不同地域、民族创造的不同语言,其中都会蕴含着该民族独有的遗传密码、人文信息、表述方式。 有些语言表达在本民族人民中,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更何况用另一种语言来传递。因此,无论英译汉,还是汉译英,在转译过程中都必然会产生信息损耗的状况。作者特别强调了汉语言文学作品转译成其他文字的难度。 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语言,都表现出对翻译的反抗和不服从的姿态……深蕴在文学语言深处的美感和诗性意味,很难被翻译和转化到另一种语言中去。作为一种‘深度语言’,汉语对翻译的抵抗性似乎更强。”由此带来的状况是,我们在读他国翻译过来的著作,以及他国读者读汉语文学作品,之间有无法消解的“隔”。莎士比亚与汤显祖都是伟大的剧作家,但在世界范围的影响或有强弱,其中就有翻译带来的障碍。 无法想象,汤显祖那些典雅、细腻、深刻,充满馥郁诗性的文字,翻译成英文该如何表述。 “若如玉茗四梦’,其文字之佳,直是赵璧随珠,一语一字,皆耐人寻味。 ”吴梅《顾曲尘谈》)如此充满“微意象”的文字,如何译成其他语种而不失其味?
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坦然地面对包括汤显祖这样的中国最为经典的作家的作品,为何很难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建军先生提醒学界:“我们无须为如何帮他‘走出去’而煞费心思和焦虑不安。”我想接着说的是,一个中国作家的文学成就,恐怕也不能用能否“走出去”来衡量。他的文学成就所抵达的高度,完全取决于他在本国人民心中的认同度。经过翻译的文本,往往与它的原貌大相径庭;它们是经过不同语言再创造的文本。 因而,一个好的翻译,可以把三流作家翻译成一流作家;同样,一个差的翻译,也可能把一流作家翻译成三流作家。莎士比亚在汉语世界的影响力,得益于朱生豪先生精彩的译文;那么,谁能担当英语世界的汤显祖的“朱生豪”呢? 由此想到,我们的文化自信,似乎也无须建构在汉语言文学作品在世界范围的接受度上。赛珍珠曾经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高度赞誉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是世界上最好的小说。她的评价之所以有说服力,是因为她曾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能够深刻领会汉语言文字的魅力;同时,她又是谙熟英语的美国作家。
这样一个基本认知,成为建军先生构建《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理论框架的基石。在品评这两位巨星的文学成就时,他时分时合,对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特征及与创作、命运、生活的关联,对他们的戏剧文本蕴含的深刻的思想内容、精神向度、美学理念,对他们塑造人物的不同技艺,对他们伟大的人格形象,都进行了精到的评析。他不断地寻找,不断地开掘,不断地发现,然后对他们的共同点和异质点,进行客观的鉴赏和论说,却绝少如某些学者那样,在他们之间妄分轩轾。 论异同,却不论高下。 “兰有秀兮菊有芳”,他们都是人世间绝佳的风景。 对两座耸立在不同地域的山峰,褒贬失当,则陷虚妄。难能可贵的是,建军先生在品评他们的文学成就时,既对他们的艺术高度给予充分阐释,同时也客观地综述了他们在不同疆域引发的巨大争议。面对争议,作者用现代学者的眼光,对其争议的核心焦点进行了深度剖析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引我深思的是,两位大师级的作家、学者,曾对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有过极为尖刻乃至否定性的批评——在托尔斯泰眼中,“不仅不能把莎士比亚看作伟大的、天才的作家,甚至不能看作最平常的文人。”“莎士比亚享有的无可争辩的天才的伟大作家的声望,以及他迫使当代作家向他效颦,迫使读者和观众歪曲了自己的审美的和伦理的见解,在他的作品中寻找不存在的优点,像所有的谎言一样,是巨大的祸害。”写过《宋元戏曲史》的王国维先生,对汤显祖也作出类似的批评,他认为,戏曲在“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汤氏才思,诚一时之隽;然较之元人,显有人工与自然之别。故余谓北剧南戏限于元代,非过为苛论也。”面对类似对两位伟大戏剧家的尖刻批评,同样也曾尖刻批评过许多当代名家的建军先生,则显得雍容大度和理智客观。 他不是简单地为莎、汤回护,而是深入分析批评者的美学思想和趣味,以及由此产生的偏见”。对“偏见”,他有态度,却也不过多辩驳,而是综述各家观点,让读者去做延伸思考。
托尔斯泰和王国维对两位同样是大师级戏剧家的严苛批评,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作家有三六九等,批评家也有三六九等。 当一位顶级的批评家批评一位作家时,作家应会想到,相比较那些三流批评家的廉价表扬,能够享受他的批评,其实应该感到荣幸;因为进入他的视野也是需要“门槛”的。
在品读本著时,我的思维也不断地被撞出火花。我不断地在书的页边写下自己的感受,有些感受是可以另行撰文,独立成篇的。 建军先生的评析,有时也有我并不认同的“偏见”,但我愿意享受一部充满卓见但也不乏“偏见”的让人提神的好书,而不会让时光耗费在那些通篇皆正确“废话”的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