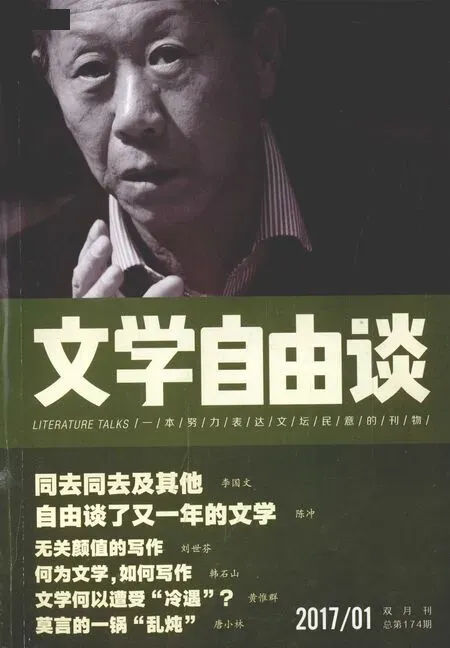也论“他妈的!”
王澄霞
也论“他妈的!”
王澄霞
时至今日,无论是谁,只要读过鲁迅先生的《论“他妈的!”》一文,怕是没有不为先生的见人所未见、人所未发而抚掌叫绝的罢;本人当年读来自然也曾如此。“国骂”一词在此文中一经先生造出,至今广为沿用且无可替代者,足见这篇文章影响之深远。
先生在文章中对 “他妈的” 词义的考订与阐释自是妙不可言。 他告诉我等,此语本是缩略语,前后已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 虽然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中国人使用起“国骂”来大多并不缩略,而且用“对称”,还要加上主语,即“我—动—你妈的—名”),但是对于外国人来说,倘若不如此阐释一番怕真是难懂;因为据先生接下来的考据,世界上其他各国多没有这等精彩而恶毒的骂法,可见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
至于这“国骂”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处,先生遍查典籍,竟也仍是茫然,只是从《广弘明集》中邢子才的几句话中寻得一点消息。据文章所引, 邢子才 “以为妇人不可保, 谓元景曰:‘卿何必姓王? ’元景变色。 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 能保五世耶? ’”这话用在这里十分费解,先生也未作阐明。 考邢子才此语原意,即妇女很容易受到性侵,一旦被人“他妈的”了,其子孙就难保家族血统的纯正,或者说其家族血统就被“他妈的”者所占据,先生认为这就是国骂“他妈的”的思想渊源。只是在一般人看来,先生这番考据,弯子未免绕得太大,而且也未必十分准确。中国人之“他妈的”,其本意是将这举动视为对女人的侵害与凌辱;倘若这女人又是对方的老母,自然侮辱尤甚,而于改变对方血统则没有多少考虑和期望。 谓予不信,且看其他类似用法——当时的“你姊姊的”和当下的时髦用语“你妹”,显然都是意在凌辱对方,因为即使“动”了对方的姊姊妹妹,与对方的血统其实并无甚牵连。还有更恶毒的骂法“动—你祖宗八代”,连对象的性别都已无足轻重。倘若仍不信,中国北方还有骂“你大爷”的,连对方男性亲属也可凌辱一番,至于如何“动”人家大爷,根本不予考虑,因为关键就是这一个“动词”解气。
更有趣的是,这个“他妈的”的用法还不断泛化。虽然这动作本是男人的行为,但是这说法连女人也乐于使用。一些妇女常常不让须眉,“国骂”屡屡不绝于口,甚至骂起自己的子女来也不时蹦出一个,完全想不到这“他妈”正是她自己。 推而广之,这“国骂”还可以用之于非人类,正如鲁迅先生文中所述,连骂拉车的骡子也可以用一句“你姊姊的”,此外还有“他妈的这鬼天气”等等,可见这“国骂”旨在凌辱对方而泄愤,与改变对方的血统实在不太相干。
然而不知何故,先生却坚信这“他妈的”是意在改变对方血统,进而引申到阶级斗争学说方面去,认为:“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华胄世业,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个酒囊饭袋,也还是不失为清品。 ……庶民中纵有俊才,也不能和大姓比并。 ”“要攻击高门大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 ”于是在先生眼里,“他妈的”就成了被压迫的庶民阶级反抗贵族阶级的斗争武器了——虽然先生也认为这种战略有些卑劣。 对于先生这番理论分析,现今读来,私下却不免有些疑惑。既然先生遍搜典籍也未能考据出“他妈的”源自何典,又何以断定此乃晋朝被压迫的庶民对高门大族的反抗?再者,诚如先生所言, 在中国,“他妈的” 广泛使用于下层民众的相互之间,所骂不分贵贱,乃至不分人畜,何以知之独独攻击晋朝“坚固的旧堡垒”,抑或瞄准金元的暴发户?再说了,豪门望族与被压迫的庶民固然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也不否认这两个阶级之间会有斗争,但是总不至于这两个阶级的人们,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表现为阶级对立,就连人人都有的出汗也要区分出香汗臭汗这种阶级差别来,又何必出于阶级立场,硬要将这庶民阶级的“他妈的”提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上去呢?
其实,这“国骂”的文化内涵实在丰富,先生的文章确乎有所未及,若说起来却也很是有趣。 这“国骂”尽管出言粗鲁,但考其实质,说的却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即男女交合。 这阴阳交合本是天地间至大至伟的事;夸赞人家婚姻美满,谓之“天作之合”,这“合”字本也是指男女交合,引申为婚配。先生在《狗·猫·鼠》一文就曾说过,迎亲的队伍招摇过市,其实就是一个性交广告。 可是为什么“他妈的”所表示的男女交合,却具有如此强烈的恶意呢? 看起来原因很明白,因为这种交合不是两情相悦,而是违背女性意愿的强行施暴。
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在所有并非强行施暴的男女交合关系中,仍然普遍存在“女性吃亏论”,就是女人只要给人家做老婆,横竖都是吃亏,总是男人占了便宜。 这种“女性吃亏论”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
这种“女性吃亏论”究竟有何道理? 为什么男人女人都这么认为?若是细细追究起来,其间还是有些道理的。远在人类尚未出现之前的动物世界里,雄性总是求偶行为的发动者,雌性则是雄性追逐、争夺、获取、占有的对象。 对于雄性的性行为,雌性只能顺从与接受,若是不从,雄性往往暴力相向,如果反抗激烈,甚至会被咬杀。人类社会本来就是从动物世界演化而来,动物世界性活动中的不平等状况也自然延伸到人类社会中来。尤其是进入父权制社会以后,这种不平等的性关系演化为不平等的婚姻关系,被以文化制度、意识形态的方式固定下来,并且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三从四德”“七出之条”“贞节牌坊” 等等就是最明显的表现。男女两性的性交配形式虽然始终与动物相同,但其背后却增加了无限复杂的社会文化制约。
两性关系的这种不平等状态,都是起始于男女交合,由“他妈的”那一个动作所导致:就是那么被“动作”了一下,女人从此就不得不“三从四德”了。即使在婚姻之外的两性地位中,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也比比皆是。 女人一旦被“动”之后立刻大贬身价;男人稍微牛了一点,就与女人计较起个“处女膜”来,而何时有人计较过男人的 “处男皮”? (就连这个词也是此刻生造出来的。 )女人与男人在“性权利”上的差异就是这么大。 女人怎么不是吃了这个“动作”的亏? 这便是“国骂”中所包含的“女性吃亏论”的真正由来。
然而时代终究不同了。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女性的政治经济地位不断提高,束缚女性的重重枷锁不断解除,两性关系中的不平等状态也在不断改变,因而女性吃亏的观念也开始淡化。 这一点在“国骂”上也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女诗人于秀华的一句“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惊动了文坛,继而女作家六六推出电视剧新作《女不强大天不容》,并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睡过的男人都是我愿意睡的”——这下语义明确了:这些女人不再是“被男人睡”,而是要主动地去“睡男人”。 这或许表明女人们在性活动中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主体地位开始确立,不再是那个动作的对象,而是那个动作的发出者了。这也可以算是社会上男女平等指数大幅提高的表征,只是这种表征实在有些不雅罢了——这当然不是反对男女平等,而是讲究文明。
——重返“五四”之一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