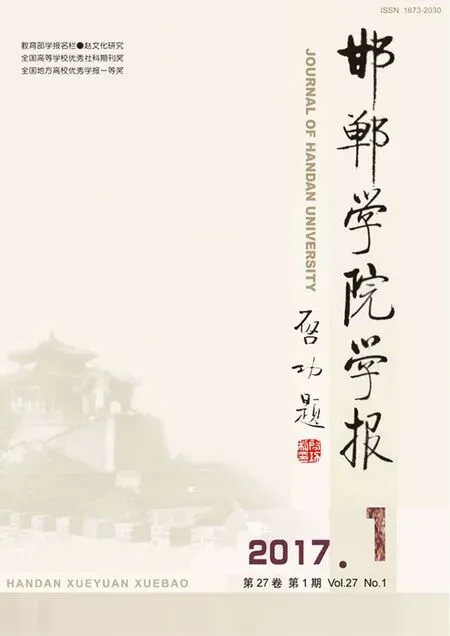著名藏书家韦力先生访谈录
贾建钢
著名藏书家韦力先生访谈录
贾建钢
(邯郸学院学报编辑部,河北邯郸 056005)
韦力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古籍文献收藏家,版本目录学家和文化学者。韦先生从事古籍收藏和研究30多年,在古籍收藏与拍卖、古籍版本鉴定、古籍目录研究、古籍文化理论与著述等诸多领域卓有建树。至今他已撰写古籍文献研究论文80余篇,论著、编著20余部,曾获文津图书奖等,影响颇著。2016年12月17日,笔者很荣幸地对韦力先生进行了独家学术访谈,韦力回顾了他30多年来的古籍收藏与文化研究的心路历程,着重阐述了他的系列文化寻踪类著作的理论思考与写作建构、古代藏书楼的文化意蕴及其深刻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对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教学等等新领域的独特思索、古籍文献著录方式的思考与实践、芷兰斋书跋的研究写作以及将要进行的研究计划等等问题,以飨学界。
韦力;古籍收藏;古籍拍卖;版本著录研究;文化寻踪;学术访谈
在当今古籍收藏与研究界,韦力先生集古籍收藏家、文献学家、版本目录学家、文化学者、作家于一身,被称为“又读又研究”的“国内最大的藏书家”。韦力先生古书收藏30多年,他凭藉个人之力,所藏四部齐备,7大系列书藏,宋元明清各代版本古籍7万余册,碑拓2千余种,他的“西苑书楼”与“芷兰斋”为国内古籍收藏与研究界所熟知。
韦力先生藏书宏富,学识渊雅,勤于研读,藏著兼善,取得了一系列收藏与著述成就。截至2016年,韦力先生发表了各类研究文章80余篇,已出版《批校本》《书目答问汇校》《芷兰斋书跋(初、续、三、四集)》《古书收藏》《鲁迅古籍藏书漫谈》《鲁迅藏书志(古籍之部)》《中国古籍拍卖述评》《失书记·得书记》《古书之媒》《古书之美》《古书之爱》《书楼寻踪》《书魂寻踪》《觅宗记》等古籍文献、拍卖与文化研究著作,主编《古书题跋丛刊》《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补编》等大型文献资料著作。面对韦力先生这样的收藏大家,他的学术研究与文化寻访体系庞大,建构精深,行文娓娓而谈,为古旧书籍收藏传统与当代人文传播的融合做出了重大贡献。2016年12月17日,笔者很荣幸地对韦力先生进行了独家学术访谈,韦力先生回顾了他30多年来的古籍收藏与文化研究的心路历程,着重阐述了他的系列文化寻踪类著作的理论思考与写作建构、古代藏书楼的文化意蕴及其深刻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对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教学等等新领域的独特思索、古籍文献著录方式的思考与实践、芷兰斋书跋的研究写作以及将要进行的研究计划等等问题,以飨学界。
贾建钢:韦力先生您好,很高兴能有机会向您当面请教关于藏书与古书研究的一些问题,也希望能与大家一起分享您这么多年来坚持思考与写作的体悟。首先向您请教,这个山西碑刻拓片的边栏是什么形制,我发现好多刻石都有类似的边栏?
韦力:一般说来,带边栏的拓片基本上是为了制作成册碑帖时的方便。当然,我的所指乃是有规律的、一块一块的分割线,大多这种制作方式,其目的是为了便于装订成册时的折叠整齐。所以说,您的这种拓片有可能当初刻制时就是为了捶拓成册,所以您的这张碑帖虽然仅有一页,但我的看法,这可能是某个套帖中的一张。当然这种说法也不绝对,有的单碑也会刻制花边,因此说,您拿来的这张拓片,是单石还是套帖中的零种,这要查证后才能做出结论。
由此可以展开一个话题,那就是拓片根据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就拓片而言,古人最初的目的是将这些刻在石头上的文字拓下来,以便于学习书法。大概到了宋代之后,人们用碑刻来收集文字,比如欧阳修、赵明诚等等才开始着力搜集。而这种收集的目的已经脱离开了学习书法的概念,其着眼点乃是搜集古代的文献,尤其是古代名人文集中失收的文章,因为古人大多数是请名家来写碑文,而碑文原本就是文集中的一部分。但出于某种原因,有时名家文集中并没有收录这些碑文,而从古代的刻石拓片中即可找到这种有价值的文献,这就正如您带来的这张拓片。因为您已经告诉我,这张拓片中所刻的诗在《全宋诗》中未曾收录,所以今天的这张拓片就是古人收集拓片目的的一个很好例证。
当然了,古人文集中有时候不把碑文和墓志铭收进去,也是有意而为之。因为在古代,请名家写碑文,要付很大一笔钱,如果正赶上某位名人这个时候缺钱花,为了挣笔润,也会接一些不该接的活儿,同时在文字上也有不少溢美之词,这样的碑文被称之为“谀墓”。虽然有些碑文乃是谀辞,带有阿谀奉承的文笔,但是从史料角度来看,里面又涉及很多人物关系,虽然为了捧人,但基本事实还是可靠的,因是同代人所写,准确度就比较高,因此史料价值就比较大。
我们再从书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书体变化在唐代基本完结了。从唐代以后人们使用的书体主要是八大字体的变体,八大书体就是现代人总结的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魏碑,其他的书体都是它们变体而已,因此唐以后在字体上已经无所突破了。这就产生一个结果,唐以后的碑拓就没有人收集了,因为书体的变化到此完结。也正因如此,很多人认为唐之后的碑刻就不足为道了,当然这是从书法上来说。
对于拓片的收藏,在乾嘉之后又有一个新的高潮,人们从这些拓片中开始找文献和记载线索。中国人强调正经正史,其实每一个时代的正史很多都是官修的,说到底是皇家史,这对整个历史面貌来说显然是以偏概全的,而正史就是这样记载的,与正史关系不大的人物及其事迹就不在其中记录。但是人们发现碑刻上面却较多地记载了正史中从没提到的人物和事迹。乾嘉时代的学者们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于是,碑刻的资料价值受到足够的重视。就像王羲之的书法,它的内容大家都很熟悉了,也基本没有研究的必要。反倒是一些不常见的碑刻,突然间会发现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并且还能纠正正史上的一些错误,甚至可以校改正史等等。比如《疑年录》的出现,它其实就是来考证每一个人的生卒年等内容,这是古人特别关注的,因为生卒年确定之后,你会发现,历史上的许多传说就突然靠不住了。这样古人就开始关注碑刻的重要性了。
再后来,人们又从美学角度来关注六朝时期的造像,虽然当时人开凿这些造像是从信仰角度着眼,然而这些造像却能以具像的方式来反应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还有一类刻石名为摩崖,就是在稍显平坦的崖壁上直接刊刻文字,而这类文字主要是为了记录一段历史史实,用古人的说法,这是载事。另外,古器物也被古人制作成了拓片,比如古权、古尺等等,这些拓片可以来考证古代度量衡的变化。
总之,从大类来分,古代的拓片可以分为碑和帖两大门类,就书法角度而言,大多属于帖的范围,当然这种说法太过绝对,因为很多碑的拓片,古人也是以此来学习书法者。就从帖的角度来说,我举一个例子,兰亭的真迹,后世见到的都是摹本。对于兰亭序的拓本,今日能够见到最早的就是宋拓,即使如此,你想一想,我们谈善本,大多会讲到宋拓、宋刻,感觉到那个时代距今是何等的遥远。其实,你再想一想,宋代距王羲之所处的晋代,也同样有着很远的距离。古人没有照相技术,一代人一代人只能靠摹写,而每一次摹写都会跟真迹有一定的差异,所以越往后的摹刻之本就距真迹更加失真,如此说来,我们今天看到的帖可靠吗?产生这种怀疑的原因,就是大家见不到真迹,这是第一层的疑问。
接下来第二层的疑问就产生了,王羲之的书法是晋代的通行笔体吗?显然不是。那他为什么被称为“书圣”?因为那个时代只有他写成这样,他是那个时代唯一一个写成这样的,如果还有人也能写成这样,那他也就没有了“书圣”这个伟大的称号了。所以说,我们想了解晋代社会的主流书写方式,如果从王羲之下手,就不全面了。那如何才能了解到晋代书法的普遍面貌呢?晋代的其他书法作品今天很难看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晋代时刻的碑,来了解那个时代的书风。晋代碑刻在当时所刻都是为了实用,就是留下文字记录而已,所以我们说它才是真正代表了那个时代普遍的书风,那才是晋代书法的主流风貌。以此类推,每个时代的碑刻都实际代表了当时的普遍意义的书风和书写崇尚。
人们突然意识到,要想了解哪个时代的书风,那么应该是从碑刻入手,而不是帖,这样到清代中期碑刻的研究又开始兴盛起来了。黄小松到龙门发现了许多造像的题款,认为这才是北朝真正的流行书风,因为当年刊刻这些造像题款的人,肯定不是为了让后世学习书法。他们在造像旁刻上这些字,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记录一段史实。自从黄小松发现龙门造像题款之后,他的访碑行为渐渐在天下风行了起来,而有不少的学者开始通过这些拓片来研究真正魏晋时代的书风,于是就有包世臣的《艺舟双楫》,是他首次提出“北碑”的这个概念。当年黄小松在龙门发现了最有价值的四个造像刻石,而他所拓的这种拓片被后世称之为“龙门四品”,在他之后,有不少的爱好者踵其步伐,在龙门石窟内寻找着古代刊刻的文字,而后就有了“龙门二十品”,“龙门五百品”,以至于到后来,造像上的几个字也会被捶拓下来,将这些汇在一起,就被通称为“龙门一千五百品”。
龙门造像题记的发现,对中国书风的转变有着重大影响,从此之后,无论是写书法之人,还是相关的研究者,都开始提倡魏碑书风,而黄小松可谓是这种风气的启迪人物,所以说黄小松对于清代书法风气的改变居功至伟。他当年所拓的“龙门四品”初拓本后来归了金农,金农很喜欢,他的漆书书风也是有此本源的。金农之后,“龙门四品”辗转又归于翁同龢。翁同龢得到了黄小松所拓的“龙门四品”很是高兴,他将得碑的过程记录在了日记中,也正因为这种喜爱,他还在这两册碑帖的后空白页上写了幅《小松访碑图》。虽然这幅图不是他的首创,他也是摹写别人的绘本,但这也足可看出他对该册拓本是何等的喜爱。为了这两册碑帖,他特意让自己的夫人做了两个布包袱,而这个布包袱的原物今日仍在。而今,这两册碑帖藏在了寒斋。
到了康有为,他扩而广之,在包世臣的著作基础之上,又写出了《广艺舟双楫》。这部书很有影响力,而康有为极力提倡“北碑”的观念,在社会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在此之前,学书法之人,大多看重帖而轻视碑。自从这部书的出现,在人们心目中,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倒了过来,而相应地,研究者也从帖学转到了碑学。
当然,任何学术的探讨都不是一面倒,究竟是碑重要还是帖重要,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当初刊碑之前的写样并不是后世看到的模样,可能只是经过石匠摹刻之后,才成为了今天人所看到的书法字风,所以说今天碑石上所表现出的书法风格,也并不能等同于刻碑时代的书法风貌。
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碑刻都有价值,相对而言,碑中最看重的还是汉魏碑。但在汉魏之前,还有秦朝的刻石,然而秦刻石流传至今者,仅有泰山刻石最为可靠。而在秦刻石之前,还有石鼓文,关于石鼓文的刊刻年代,从唐代开始,一直争论到了今天,在这里不展开论述。因此说,汉代之前的碑刻流传至今者,特别少见。正是物以稀为贵的原因,使得汉魏广受重视,而相应的初期拓本也变得极有价值。但这种说法也并不等于汉魏之后的碑帖就没有价值,比如周绍良就大量收藏唐代墓志。因为唐代国力强,所以当时的有钱人刊刻了许多高广的大碑,同时,唐人刻了大批量的墓志,因为多,所以很长的时期里没有人来收集。但这些碑文的墓志好多是当时名人所写,往往成为文人文集的一部分。为了补充《全唐文》,周绍良先生就收集了大量的唐代墓志。这也就是王国维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的理论实践。而今天您也同样带来了这样一张拓片,且该拓片所刻文字也是古代失收者,所以,您的这个行动,正印证了这样的理论。
贾建钢:从《书楼寻踪》到《书魂寻踪》,也即您的“寻踪”著述,从1997年开始至今已经20年了。从“书楼”到“书魂”,在读者看来,是通过寻访一个个古书被藏之所转向为藏书家灵魂所寄的墓园,来逐渐建构起一个丰富的田野考察式的学术空间。由“书楼”寻踪的客体世界到“书魂”所托的主体精神世界探询,在您看来,这有着怎样的一种视野转向与叙述模式的转变?这种以田野寻访考察的方式意在建构起一个什么样的古籍收藏研究的学术形态?
韦力:关于寻踪,来由最初很是偶然。大约20年前有一个期刊叫《书窗》,大概是长沙办的杂志,现在早就停刊了。在最初的几期,刊登了一位作者拍的藏书楼,我对这个内容很感兴趣。我从中是受到了许多启发,所以我不是书楼寻访系列实际的开创者。因为那位作者描述的一个藏书楼我去过,但是跟他所述情形不太相同。于是我跟他书信沟通,而他说并没亲自去过那个藏书楼,是朋友帮他拍摄的资料,然后就写出来发表了。我于是开始怀疑过去很多的这种记录,就想亲自去找,考察一下,搜寻些真实的情况。我先试着寻访了几处藏书楼,就生出许多感触。我发现过去的许多记载与现实的情形存在诸多不符,于是决定尽量多地寻访,记录下来寻访到的真实情况。
由于大部分藏书楼的文献资料比较少,且都是记载一些不着边际的东西。例如近代大藏书家叶德辉是长沙湘潭人,大家本能地觉得他的藏书楼应该处在湘潭或者长沙,然而当时这两地都不是重要的藏书中心,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藏书的中心位于苏州、吴兴、常熟一带,既然如此,叶德辉为什么在湖南搞出了这么有名的藏书楼呢?就算藏书楼在长沙所建,那么他所藏的那些珍善本来自于哪里呢?一番探讨之后方得知,他在苏州还有旧居,而他的藏书大多是得自该处。而对于这些的了解,也正是我寻访后的所得。
这就是实地探访的发现,通过这些探访和文献的印证,这一系列的做法突然让我意识到,过去的大多数记载都值得怀疑了,到现在也没有人来把它真正弄清楚,不能说是相互转抄吧,但基本上是不清楚的。当我查阅相关的资料时,发现大家记载的错误都是一样的,那我就觉得很有必要澄清落实一下它的所在。从这个角度讲,就有必要把所有的藏书楼都找一找。有了这个疑问,才有了我后来的行动,而后就一路地跑了下来。其实这种寻访,看似简单,在实际操作中却有着不小的难度,而最初的难度则是具体文献的缺失。
关于我查资料的方式,主要线索是从地方志中寻得。古代的藏书楼记录好多是通过地方志记载的,但这种记载只是古地名,而这个古地名是今天的何处,这就需要做古今地名的转换,而后再通过地方志的朋友确定这个地方指的是现在的哪里。古代的藏书家多是有钱人。一般说来,古书尤其是珍善本级别的古书,并没有进入到寻常百姓家。中华文明虽然历史悠久,但识字之人始终是少数,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虽然有多种,但书籍昂贵,一般人买不起,这也是古代识字人少的原因之一。因此藏书家肯定是居于城市繁华中心一带,一般这些处所又是现代城市重点建设的区域,有很多藏书楼都被拆除不存了。
我每一趟寻访会连续跑几个地方,然后都要拍照整理保存。回想到书楼拍照的经历也是很难,当地的很多人不了解,还经常造成种种误会。比如清代岭南三大家之一的梁佩兰,他的藏书楼在广州一个地方,那里300年来的地名没有改变,但是当地的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这个老街巷了。我记得当时我就走到跟前了,一问路人还是不知,后来猛然抬头看到路牌,原来是近在眼前而不知啊!这就是我遇见的寻访之难。还有清代一些重要的藏书家,很有财力,有大的庄园,解放后他们的财产处所,就变成了革命胜利的成果,他们的所藏有的被收归国有,而当年的藏书楼也多被机关或民宅占用,到如今,不论是被公家占用,还是私人所使用者,现在想进内拍照,都一样的不容易。有的藏书楼成为私宅之后,又经过了多次的转让,一般而言,名人故居往往只有使用权,没有买卖权,只能维护,不能卖出。办产权交易手续繁复,以前还没有这么多的麻烦,后来《文物法》越来越严格,这使得名人故居的转让变得更加不容易。也正因为如此,现在的房屋使用者,他就对采访的人没有好感。
寻访的另一个难点,就是故居处在学校里。小学中学的校园是最难进入,校方出于安全考虑,不知道来访者是什么来历,所以一般人不会让进,得有介绍信或证明。但即使我持有介绍信,而到一些学校门卫那里,也同样没用,他认为县官不如现管,无论你介绍信有多大的名头,也比不上他们校长的一句。但谁有可能遍识天下各地的校长呢?
经过寻访之难以后,我心态就转变了。以前是为了落实一件藏书事实而已,后来发现很多地方建的各种纪念馆,很多都是为了现实的功利目地而建造。而历史上那些纯粹的藏书家在社会上往往不被重视和纪念,我内心中就产生了一种不平。我们总说我们民族有灿烂的文明和历史,而我们这些骄傲的来由都是基于历代的书籍记载,而这些书籍的流传也正是这些藏书家们一代一代辛苦努力的结果。但是我们今天都忽略了为我们的文明贡献那么多且大的藏书家。他们不应该被忘记,如果我们只以自己的灿烂历史为骄傲,却忘记了那些文本的传承者,这也是一种功利。所以我的寻访藏书楼之旅,就是以这种行动为了纪念这些不应当忘记的人。通过寻访,而后写成小文,将其发表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藏书家。原本我的藏书楼之旅就是为了落实古代藏书楼的具体方位,但随着寻访过程,我的寻访初衷也渐渐改变,但是我觉得这个改变令我的寻访更加有意义。
通过书楼的寻访,更加印证了我固有的认识,那就是书楼只是书的藏放地,而藏书楼真正的灵魂是藏书家。藏书就和我们编古人或前人文集一样,所以藏书家藏哪些书,或者不藏哪些书,每一种取舍就代表了藏书家的价值观,即所谓选学。藏书家也是这样,藏书家也是有他独特的价值观的。藏书家是藏书楼的灵魂,同样,今天也没有什么人纪念他们。没有人寻访他们的墓地来纪念他们,这也是一种新的不平,他们的贡献和他们受到的待遇相悖,由于这样的寻访所以就形成了“书魂寻踪”。这就是我的写作从《书楼寻踪》到《书魂寻踪》的原因,这不是简单地爱屋及乌,因为书楼爱上了书楼的主人,而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其目的根本上是这些藏书家不能被历史忘记。如果单纯地要阐述藏书家的藏书观,大家依然不爱看,但是把藏书事迹融入到寻访过程中,目的是让大家读后更感兴趣。
这就是从“书楼”到“书魂”的寻踪过程经历以及我的初步建构。
贾建钢:北京大学陈平原先生对于写作有“第三种笔墨”的说法,除了特别正式严整的论著和抒情散文写作之外,您的著述大多将浓重的嗜书情怀打并入文字,这种负有沧桑感的温情与理解,相信您将一如既往地在未来的写作中延续这种特别的格调。
韦力:我对自己的文笔没有那么强的信心,但是我的行文腔调也的确有着自己的考量。以我的感觉,学院式的研究著作写法,虽然谨严而周到,但这很难做到让一般读者喜闻乐见。而同样,抒情类的散文,有着太多的“啊啊啊”等大量的感慨语,我不敢说这叫滥情。但显然,把这样的腔调用在古代文章中,多少还是让人觉得有些别扭,所以我就选择了第三条路。因为我试图将历史史料跟轻松的散文做一个调和,让这种文章变得既有史实,同时读上去也不感到太累。
其实我也知道,这样的写法也是一种冒险,因为很可能两头不讨好:学者觉得这种写法不专业,而一般读者又感觉到这种文体不通俗,可是我以这个腔调写了两三年之后,还算反应不错。如此说来,我的这个冒险还算成功。也正因为如此,接下来的寻访之文,我还会按照这种笔风写下去,直写到人们有了审美疲劳,看到我的文章就倒胃口而止。
贾建钢:您刚刚出版的《觅宗记》可谓巨作,这包含了您多年知行合一式的深度积累,请您介绍下此著的整体寻访和写作框架是怎样的?
韦力:这是我的文化寻踪的一个体系。现在我的写作可归结为两类,一类是与书有关的书,都是谈书的,以书为中心。后来我在寻踪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不断阐述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大都是从文献角度纪念,而没有从寻访的角度去纪念,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把文化融入到寻访过程中?但这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这么广阔的地域上,留下来的历史遗迹那么多,它们都是归属于哪一个领域的,首先要搞清楚每一个领域的构成。我大概用了一年半时间,来系统地阅读通史著作,还有多种文学史、哲学史、宗教史、思想史等等,从中找出谁才是某一类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个体,于是做寻访计划,列出名单,逐渐做出了一个十几万字的提纲。最初分了八个门类,每个时代每个门类中的核心人物,然后确定在哪,在不在,弄出详细的单子,利用五年时间把全部地方寻访完。
这个计划足够庞大,这与我的性格有关。我喜欢这种比较庞大的架构和体系,不喜欢在小地方雕琢,我愿意去做一些宏大的叙事。可是没想到的意外是,在寻访的过程中,在第三年半的时候把腿跑断了。修养半年之后我又能走路了,回想在医院中经历的痛苦不堪,我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对于寻访也产生动摇,不想再跑下去了,也不能再跑了,命都差点儿没了,世间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吗?我突然间意识到生命太短暂了,一瞬间本能的自我保护和自救,一个意外让自己深感不幸。但有些时候又会转念思之:应该感谢上天,给我留了一条命,既然如此,那就应该高高兴兴地去享受生命中的快乐。出院之后没多久又故态重生,想到死很容易,人生不做什么也是死。既然死亡是生命的必然,那只有做事才是或然。没死之前应该还是做点高兴的事,既然寻访、写作这些事情是有意义的,那我还是要做下去,为什么要限制自己去做愉快的事情呢!
通过这段时期的变化,从此以后我反而加快了写作的步伐。《觅宗记》只是我的传统文化寻踪系列书系中的第一部,但是已经写到第五部了,只是出版比较慢而已。人生是无常的,没人规定我应该活多长时间,既然有这么多的事值得我去做,我更应该加快脚步。但这不是我刻意的,是内心常常督促我要赶紧去完成。基于这两个原因,我就边寻访边补充,到现在基本寻访结束而主要是进行写作了。
关于《觅宗记》,我想说明的是,佛教文化虽然不是本土产生的宗教,但却对中国传统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影响巨大。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得到了大发展,而此时在印度却日渐衰落了。佛教为什么进入中国以后会得到这么大的发展。因为佛学思想弥补了中国人在思维方式上的缺失。印度佛学中有一种因明学,就是讲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等等学问的。而我们谈的孔子儒家思想,他的思想是缺乏归纳推理的,难以周延,想要得到最终的结论,就必须是把所有的材料穷尽才行。而中国本土的宗教应属道教,但道教思维中也同样不具备严密的思维逻辑。但中国有儒学,有时儒学也被称为儒教,但由于儒学对中国人价值观的构建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儒学起到了准国教的地位。而儒教是用伦理来稳定社会。儒教认为佛教不讲人伦,不讲求社会秩序,虽然如此,佛教在中国的长期存在也必然有其原因,这就是我为什么寻访佛教的缘由。《觅宗记》我作为第一部来写作,就是因为佛教思想比较成体系。儒教没有这样一个世间完整递传的体系。而古代的中国人特别喜欢纳妾、生孩子,因为没有后代,祠堂慢慢也就会衰落,家族也就慢慢消失了,这就使得一些古代名人的遗迹因为无人维护而渐渐消失。寻访过程也是一个思索的过程,是对过去的印证或纠偏。
从某种程度上说,而今的这些历史遗迹现况,也同样反映出后人对待这些前贤的态度,从这个角度而言,我的寻访,也是对现实的部分反映。寻访过程中就会发现人们是怎么对待这些对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这可以视作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寻访和总结。我也相信未来会重新理解这段寻访的历史。
近来我的重点放在了完成文章方面,虽然这个过程中仍然有一些必要的寻访要增补,但已然进入了拾遗补缺的阶段,到目前为止,我所完成者,除了《觅宗记》,另外还有《觅理记》《觅诗记》《觅文记》《觅曲记》《觅词记》,这几部书稿在出版社的编辑过程中,应该在2017年都会面世。届时再呈上请教。我的寻访范畴,整体的框架基本上包括了经史、宗教和艺术三部分。关于艺术类的寻踪,其中就包含了书法、绘画、篆刻三个领域。
贾建钢:您的著述完全是活态的纪念文字。您的写作完全可以提供给后来的读书者,这些纪念文字完全可以当作这个历史时段的研究对象。这种原汁原味的丰富记录,将来肯定会被人当作历史材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也堪称一种文化的再记忆,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成一家之言”。您的著述就是一种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
韦力:您这么说太夸赞我了,因为《史记》在后人,也包括我在内,都把它视之为不朽的著作,而我的寻访其价值不及其万一。即便如此,其实我也知道,自己的寻访定有其价值在,因为这样的寻访也概括了我对历史的理解,以及我对这些历史的态度,所以说,这些思考可以当作是一个藏书人眼中的历史。
贾建钢:古人为藏书之所命名往往语有深意,凡是楼阁斋馆、房室轩堂的名号一般都有语典或事典。这一方面显示了藏书家对藏书之所的意义确认,另一方面也传递出藏书行为导致的内在精神超越性的领地建构。请谈谈您对这一藏书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思考?古书中许多递藏有序的藏书印,您如何理解印文中所饱含的藏书情怀与文化意味?
韦力:确如您所言,古人的堂号大多具有各种意义。古人讲“诗言志”,其实我认为堂号也言志,就起堂号的着眼点而言,古人的堂号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古人为自己的书房所起;一类是帝王达官因某书某室而赐予的,但这是少数,前者是主要的。古代藏书家都属于文人了,他们的堂号命名基本与自己的人生境遇、藏书所求所取密切相关。藏书家得到了一个很特殊的有价值的版本,往往为所藏之处起名号,以示标榜。这似乎在古往今来的藏书界形成通例。如大藏书家黄丕烈的书房就称为“百宋一廛”。根据考证,实际上他并不是同时拥有了100部宋版书,他是希望拥有百部宋版,用今天的话来说,将100部宋版书堆在自己房内,让自己愉快,这是一种愿景,这也算是古代藏书家的一种藏书目标。
黄丕烈起了这个书楼名号之后就引起了别人的效仿与竞争。跟他同时的藏书家吴骞,就起了书房名叫“千元十驾”。据考证,其实他也没有搜集到过一千部元版书,这也同样只是表达一种藏书的理想。到了近代,明版书中的精品之一“嘉靖本”是特别受藏书家关注的。在“嘉靖本”书出现之前,一般的每部书都要事先请人书写,然后刻工。但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方式出现,从嘉靖到万历之间产生了商业化的刻书出版,这当中产生了一种刻版的通行字体,由于人们追慕宋版书的精美,所以这种字体被称为“宋体字”,其实是明人眼中的“宋体”。我们今天使用的印刷体就是“嘉靖体”的变体。“嘉靖体”又称“枯柴体”,其特征就是横细竖粗,便于刻工雕版和流水线生产。“嘉靖体”的出现对中国书籍出版影响极大。能不能藏有百部“嘉靖本”书,成为藏书家的一大目标追求,所以藏书家的堂号时有标榜。比如“百嘉堂”,这是上海前几年故去的藏书家黄裳先生的堂号,而实际上他大概只藏有50多部“嘉靖本”书。近代大藏书家邓邦述的堂号称为“百靖斋”,还有近代著名曲学大家吴梅的堂号叫“百嘉室”,但他实际上是收藏了“嘉靖本”43部,而我自己则藏有260多部“嘉靖本”书。因此,给自己起这一类的堂号,并不是个人藏品的客观描述,更多者,这是一种追求的目标,所以说这样的堂号就具有了号召或标榜的意义。这也表明藏书家的态度志存高远,是希望他的藏书所达到的理想状态。
当然这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拥有了某部古书,以示标榜。如山东大藏书家王献唐先生,他当年藏有一部顾千里的批校本和黄丕烈的一部跋本,而这两人批校之书最受后世藏书家所关注,故把他们两人的批本和跋本合称为“顾批黄跋”。而王献唐能够各有一部,于他而言,十分的兴奋,于是他把自己的堂号起为“顾黄书寮”。古人曾说,顾批黄跋毛抄劳校,号为书界四大名品,王先生拥有“顾批黄跋”本,他是否还有毛晋的影钞本和劳权、劳格兄弟的校本,这我不知道,如果有的话,我想他一定会立即将自己的堂号重新起一个。所以说,从书房的名称就可看出,某位藏书家最为钟情于哪本书。反过来讲,堂号也可以暴露一个人的最高收藏水准。上面提到了,还有的堂号乃是皇帝所赐,也有的情况是皇帝赐了一部或一批书给某人,这无论在哪个朝代都是无上光荣的一件事,当然要为此慎重地起出一个堂号了。
仅就藏书家而言,如藏书家邓邦述,他最初的堂号称作“群碧楼”,这是由于他收集了两部唐诗人的集子,一部是《群玉诗集》,一部是《碧云集》,于是合称其书楼为“群碧楼”。可是后来,他把书卖掉了,就改了名号为“梦碧楼”,可见他对藏书的怀念之情。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藏书还在陆续卖出,他由于对藏书的种种感念,取“郊寒岛瘦”之意,为书楼取名为“寒瘦山房”。这其中,通过堂号命名的变迁可以看出藏书家藏书的丰富经历和心态折射。
关于第二个问题藏书印,我觉得印章这种文化现象比较特殊,这与中国的印信有关。我们古代的信用体系不是靠签字,而是靠印信作为凭据。古代的虎符都是这一类的用法。很难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传统。就像古书为什么竖排版从右读起一样。藏书印就是印信体系中的一个分支,通过这个来表示所有权。历史上,人名章之外,后来产生了闲章。闲章一般可以追溯到元代,明代开始在石头上刻,之前铸刻在金属上。明代文彭开始刻文人印,开始把一些喜欢的句子刻在石头上,古人一般说“诗言志”,我借用来,也可以说是“章言志”。古人的藏书章也渐渐成为藏书者的心志表现。我最近写完了一部书叫《朱痕探骊》,已经交给出版社,大概不久之后可以面世。过去的印谱,我们一般都从流派印的审美分析角度来考虑,从技艺技法角度研究印章。读一方印章,我不是专门谈的技法和艺术层面的,我谈的是印章的内容。每个要刻印的人不纯粹是为了表现技法,当然重要的是印章所包含的意义内容,这些都是精神层面的寄托。我的这本《朱痕探骊》是初辑,谈论的范围较窄,是挑选汪启淑的《飞鸿堂印谱》一百多方印为解读对象,很短的时间里就完稿了,这样来看,我的写作状态还是比较疯狂的。
贾建钢:就像郑板桥画中题跋阐述艺术创作的过程时所说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等等,您的写作也是读印而能心领神会,胸有成竹,必欲吐之而后快,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写作。我们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厚积而薄发的那种书写状态!
韦力:谢谢夸赞。其实,每一个藏书章都能表现某一个时段的心境,我这样来解读印章,也表现了治印人的好恶取舍。我自己也会请人把古人的一些话刻成藏书印,我也会把我自己的感悟融进去。比如宋代的赵明诚就是一位大收藏家,金人打到开封时,李清照带着赵明诚收藏的十车藏品一路南逃,而这一路就是她的藏品散失的过程。赵明诚去世之后,李清照遇人不淑,嫁给了一位骗子,这使得赵明诚的旧藏又损失了很多,这个结果让她大为感慨,而后她就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我对这句话特别有感悟,于是把此句刻成了一方闲章。以己及人,古人的收藏遭遇说不定也会哪天降临到我的头上,所以我会把一些达观的态度也刻成闲章,以此来表达我对聚散的态度。同时收藏也是交友的过程,通过与同好分享心得和藏品,以期得到吾道不孤的心理慰籍。正如张岱所说的“人无痴不可以交,以其无真情也。”我对这个话也依然很感慨,我觉得有收藏癖好的人,他就必然是个痴情的人,既然能对物如此有情,那么对人我想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这也就是我对章文的一些感慨,也即刚才所说的“章言志”。
贾建钢:您对自己的书房“芷兰斋”的命名有何寓意或说是情感表达?
韦力:关于我书房“芷兰斋”的名字,大约有两个缘由。一是源于一个朋友的一句话。一个做生意的朋友,他看待一切都可以用钱来量化,其实这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生活未必非得做一种雅人状,不追求雅,也是一种真实,他知道我买书花很多钱,于是就提出去我天津的藏书楼去参观。我的书楼当时正在整理做书签排列,满地摊开都是书,他一见特别感慨,真诚地说了一句:“你这就是一屋子烂纸啊!”我当时就突然想到野兽派画画的来由。野兽派画作的风格大红大黄,当时人们不承认它,他们就搞展览,到维纳斯展厅去展,当时进来一个评论家,认为极其典雅的维纳斯雕像和那些画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差,于是他说了一句:“维纳斯处在野兽之中”,而这些人听到后,反而感到很受用,于是就把自己的这个画派称之为“野兽派”。而这个朋友所说的这句话,我也同样觉得经典,于是我就反其意而用之,把他说的这“烂纸”二字倒过来,就成为了“芷兰”。
其实“芷兰”二字还有着另外的出处。这源于我特别喜欢《岳阳楼记》这篇文章,其中有“岸芷汀兰”的话,当然,这两个字也可以追溯至屈原的诗歌,因为他的作品中时常拿芳草芷兰等来形容君子,后来就当作古代文人的君子寓意,我很欣赏古人的君子之风,所以也希望我的书房里有着大量的芷兰芳草。这也算是我起此堂号的缘由之二吧。我的书房原来叫西苑书楼,处在天津的西苑地区。书楼起“西苑”二字,一是地理上的概念,二者则是源于清初的大文人查为仁当年在天津的西苑这一带建了一个宏大的庄园,名叫水西庄,当时他在这里迎来送往,有很多的文人墨客都汇集于此,可惜这个庄园到了今天已完全没有了痕迹。然而其遗址处在西苑这一带是确定无疑,正因为这个缘由,所以我才想起来到这一带去买房,以此来沾上古人的灵气吧。
贾建钢:目前的学界很难有人具备同样的时间和财力达到您这种丰富的古书收藏实践和文化寻访,从某种程度上说您已经超越了当前科研院所的古籍收藏整理研究为主要学术圈的学者。在大学里搞古籍研究和整理的也很难做到您这样的境界,既寻访、收藏、拍卖,又研究、写作。当今古籍收藏拍卖的递传方式变化对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古籍的收藏整理研究,现在面临着一个市场环境的问题,学科的发展又有交叉性。您看古籍研究,通过这些因素在学术研究上又会有哪些影响?
韦力:现在中国的大学,与古代传统意义上的书院已经差别很大了。现在大学与古代的区别,其重要的标志就是进行了详细的分科。古人其实也强调专和博之间的关系,在康熙年间就有讨论专家与博雅之间的区分了。专家对某一学科进行深入研究,这很好,对某一领域深透的研究有推动。而我则有一些保守意见: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某一个窄而深的问题,搞得专精深入,每个字的差异都能讲得很清楚,这样很好,但是为什么难以贴近一个融会贯通的认识。这就是今人和古人的区别,古人广博性地学习,由博返约,渐渐走向专精,然后发现真理。但我们今人却没有这样一个丰富积累的过程。我们从高中就开始了分科,到大学更是这样。这种学科设置便于透彻深入,但是缺少了整体的观念。而文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比如家里的装饰摆设都代表了一个的审美修养,但某一件摆设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整体审美情趣,只有将他家整体的概念做一个综合分析,你才能得出一个人的品味。因为如果你不了解一个事物与一个事物的关联度,这就像盲人摸象,但我们直奔主题只摸一个部位,一定得不出来全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立足一个全貌来了解中国的文化,要想真正深入,一定要在面上做大,才有条件来深挖。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相通的,不能简单地割裂,研究文化必须融会贯通,寻找他们之间的关联度。在今天的语境下,人们一说“通才”,往往带有贬义,意味着学问研究得不够精深。既知如此,那我为什么还要这样去做?我的关心点并不是在某一个领域去超越专家,我只是想来了解每一个学科之间的关联。所以我认为研究横向的关联也是一种专精。而今各学科专家许许多多,大家充满着对于学问横通的贬斥,我就想看看这个横通到底是怎么样的状态。我喜欢藏书,而藏书需要具备百科知识。因为我不作专门研究,那么我的研究是为我藏书服务的。
当然现在收藏古籍比古人的机会少多了。古人藏书也好,研究也好,比今人在这方面有着太多的便利,举个例子来说,前人买古籍,大多是等候在家中,因为有很多书商会派伙计将书送到家里来,让买主随意挑选。即使这样也并不是看好后就付钱,一般可以留三个月,书商经营一年有四个结账期。放三个月的过程中甚至可以抄录一遍,到了结账的期限,也并非一定要将所看之书买下,需要的则付款,不需要者则原封退回。在这么长的时间内,读书人已经把这本书研究得十分透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在解放以后,95%以上的古书都归入了公共图书馆。在文革之后,才有我这一代的藏书家。时代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不能等着别人给我送过来。现在我得跟书店处好关系,人家才会告诉我现在有什么书。今天的藏书实际情况是由不得我藏什么,而是市面上有什么书我才能买回藏什么书,已经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然后才能根据现有的藏书情况再做专题。当代藏书的现实是很困难的,但对我来讲,感叹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公共图书馆的古籍不可能再流通,就现在的现实情况,怎么建立自己的藏书体系,这就自然地涉及到了拍卖场。
其实我对拍卖的想法最初是排斥的。1995、96年搞拍卖,古籍开始是比较便宜,但后来加价。书店卖300,拍卖就卖几万,但古书没有绝对的价钱,只能有相对的价钱。当时是买方、卖方相互交错的时期。但这个阶段比较短,捡了几年的便宜,当时没有拍卖会,书店为了效益主动与我联系买书。当时挑选的余地比较大。有了拍卖会后,书价随之大涨,于是以后就不卖给我了。古书的定价在拍卖会上,往往是靠倒数第一个、第二个人确立的,其他人的出价都可以忽略不计。拍卖会上的古籍价钱上去了,但是书店却还是原价。所以就立即把书店的古书买回,因此便宜与贵,只是比较而言者。当书价涨上去了,就会立即感到原来的定价特别便宜,恨不得马上就将其买下来,但书店的人也不傻,他们也在关注着市场的变化,一旦某部书拍出了很好的价钱,于是书店的价签就会立即在后面添零。
随着拍卖这种古籍流通形式的新发展,我就慢慢接受了拍卖这种图书流通方式。一是不得不接受,二是我发现它的吸金效应,就是拍卖的形式给卖家以希望。为了这个希望,卖家把古书交给拍卖公司,藏书家买书的渠道就越来越窄,我就只得到拍卖会去买。拍卖会有时也是捡漏的地方,有人认为我纯属矫情,但这是我亲自体会到的实话。拍卖公司成为成功的交易场合之后,卖家开始源源不断向拍场送书,经营者有了选择的余地,拍卖会往往下压卖主的价钱,对于卖主来说,标低价钱会吸引人,然后一步步往上抬价,容易成交。因为拍卖公司也不是图书的购买者,仅仅是中介,所以拍场公司的人压低卖主的起拍价,而卖主认为有道理,因为拍卖公司的人跟他们说,起拍价的高低并不能决定最终的成交价,而低价往往能吸引来更多的购买者,竞争的结果往往使书价抬了上去。这种说辞大多能够使书主接受。如果是买家直接和卖家谈价钱,其艰难程度就要高很多,因为卖家觉得有人想买这部书,肯定是对这部书特别了解,所以无论你出多少钱,卖主都会认为本书的价值一定高于这个价钱,所以说,书主宁肯以低的成交价上拍,也不愿意直接卖给他人。这并不是说拍场的成交价格一定会高于私下买卖,更重要的是上拍给卖主多了一分卖出高价的希望,而书主宁可冒着这个希望落空的危险,也愿意把书送到拍场上去。
其实到拍卖会上买书,也有一些弊端。一般而言,拍卖会的预展期只有两到三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想翻阅几百部书,则很难看到图录中未曾标明出的妙处,好在我有一些便利,我在几家拍卖公司担任顾问,在拍卖之前我可以以顾问的身份仔细研究这些古书。但有时,卖主不能认识到古书的真正学术价值;而拍卖公司呢,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上拍古籍太多,来不及细看;第二种情况是知道古书的真正价值,却故意要制造拍卖现场的烘托效应,因此他们的策略就是不在图录中指明。比如说吧,我曾经拍到过一部黄丕烈题跋的古书。“黄跋本”书大家都清楚,对于藏书家是很珍视的。在一次拍卖会预展时,遇见拍卖公司的朋友,他就问我看了某部书了吗,我看图录上介绍得非常简单,就写着“明刻本”三字,就没更多注意此书。朋友就提醒我再好好看看,我就返回去又仔细查看,这才发现黄丕烈在此书后留下了四跋!因为带有黄丕烈跋语的古书都是国家一级文物,而按照20年前相关的管理规定,一级文物是只允许国家来收购的,因此这部书在拍卖图录上就特意不标出是“黄跋本”,经过朋友的提示,我马上注意到,此书标价才8000元,那我就现场举牌,但也有其他人竞买,后来许多人就犹豫不敢举了,最后拍到5万元成交,当然这部书到现在就是500万也不止了。这就是我认为的拍卖会也是可以“捡漏”的地方。
书跟其他的艺术品不同,比如一张字画,一件瓷器,其实拍一张清晰的图片,就基本可以将拍品一览无余,但古籍则不同,有时候一部书有很多册,而一册书中又有着不同的内容,可是出现在拍卖图录上的古书照片,仅会有一到两页,有时候,负责摄影的人往往从审美角度拍的,古书真正细节的地方他不太明白,当拍卖图录寄到买书人手中时,大家习惯性的先从图录来做出初步的取舍,这样的判断致使一些特殊的内容或者有特殊价值的书,被轻易地否定掉了。这就是看图录来买书的弊端。而因为我的这种顾问头衔,以及跟拍卖公司之间的朋友关系,使得这种弊端得到了部分弥补。拍卖有很多偶然性,大家都有审美疲劳,如前所言,有些书在征集之时,拍卖方为了增加成交率,会有意地压低起拍价格,可是每年两度的拍卖季节,在每一季短短的时间内,有许多家拍卖会同时举办,这使得爱书人颇为疲累,而在拍场中也会出现审美性疲劳,所以当拍场会举办到后期的时候,大多数买家只会关心自己最想得到的几件,而当时有意压低起拍价的书,可能以很便宜的价格成交。然而事先做过功课的人就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捡到便宜。
从宏观角度讲,古书走进了拍场,也算是一种社会进步。拍卖的历史在当今中国也就是20多年时间,但在西方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世界上最著名的两个拍卖公司佳士得和索斯比,在乾隆中期已经成立,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在今日,古书拍卖往往成为书画等艺术品拍卖的附庸,而实际上这是极大的误解。世界上最早的拍卖标的就是从古书开始的,只不过后来古书资源渐渐枯竭了,才转移到字画等艺术品方面。中国拍卖起步很晚,中国古书的流通之前基本两个模式:书店、私人之间的买卖。但只有出现了拍卖,才使得中国书籍流通史出现了一个彻底的变化,这对中国古书流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今往后,很有可能古籍拍卖将是中国古书流通的主渠道。而我恰恰赶上了这样一个巨变期,对我而言,不管是幸也非也,但总之是“与有荣焉”。买家卖家能同在一个场次集中博弈,我认为未来也不会有大的转变,而这只是中国古书流通的一个开端。至于古书资源的逐渐枯竭这已经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当然以后可以从国外征集、回流一些古籍,但这个买卖形式应该是一个不可逆的结果了。
拍卖成为了市场流通的主渠道,卖家得到更好的利润,对于买家来说得到了更好的资讯,为买卖双方都增加了很多便利。对于爱书人来说,拍卖会预展也是个很好的学习过程,因为预展没有进入门槛,任何人都可以到现场随意地翻看这些真本和善本,而现在的公共图书馆因为出于保护古籍的原因,故而能够进馆内随意翻看真善本的读者要少之又少。然而版本鉴定更多的是一种实证科学,而这种经验的获得,必须通过不断地翻阅来增加对版本的认识。由于保护和使用之间的矛盾,使得很多搞研究的人难以看到太多的原本。然而少有人发现,拍卖会的预展还有这样的一个妙处。
我特别建议在大学里学习研究古籍版本目录学、古文献学等等的学者,应该带学生到拍卖会现场来实习观摩,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机会。因为我在一些大学中开展讲座,大学生们经常提到,他们根本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到这些古书。而古籍研究这个学科又必须要求上手,通过上手才能体会了解古书纸张的感觉,感受到书籍的温度,他带给你的心灵震撼远不是站在那里冷静地旁观来实现的。目录版本学是实证科学,现场感更强一些,完全可以用“纸上得来终觉浅”来形容。古籍的版本、整理是形式研究,属于是实物实证研究,只靠照片、网络和教科书的书本知识研究是不靠谱的。
贾建钢:您20年来坚持写古籍拍场述评,实际上这些描述已经对藏书和古籍研究界留下了很丰富的历史记载,您当初是出于什么目的来动手写作这些述评的呢?
韦力:其实我的出发点,是想记录下一段真实的当代古书流通史,有这种想法的初始动机,则是源于我对书楼的寻访,我对一些文本记录的疑问,怀疑部分的藏书史的真实性。但由于书的买卖也是金钱交易,有句名言说,有金钱的地方就有罪恶,假如这句话是真理,那么书籍之间的买卖也一定存在着罪恶,但是既然是罪恶,那就是少有人知道的内幕。其实除了罪恶之外,商业上另有一套规矩和规则,而这些私下的规则又被称之为商业秘密,其实这些秘密才是交易本身的真实。过去有一位大学教授,他曾经写过一个有关藏书史方面的研究专著,恰好也写到了当代,他写到了一部书的重要流传,但这个流传跟我有关系,所以我就知道他写得不符合事实。因为他依据地是一些报道,而我就是其中的参与者,我了解其中的原原本本,我就把这个真实的情况告诉了他,希望他能够改正过来,要不然读者读不到真实的情况,会以讹传讹下去。而这位教授听完我的意见后,回答我说,他所写的任何东西都是有出处的,他的所写是依据一个报纸上刊登的报道,并且他强调他并不介意这个事实本身是什么样的,他只认为他的观点有出处有依据就可以立论了。这件事对我的心理很有影响,我就感觉这原来就是大家所谈的真实,原来这些学术著作都注明了出处就可以了,而这个出处的真伪就不是著者的问题了吗?这突然让我怀疑了到底什么是藏书史的真实呢?他的所写跟我了解到的真实相去甚远,从客观来讲,而今的大学教授等读书人买不起古籍,也是一种客观。但是这种客观限止了相应的学者与专家了解到当代真实的藏书史。
就目前的情况看,这也是一种矛盾:专家学者们虽然有着很好的学问,可是他们无法了解到事情的真相;而亲历其中的这些买书人和卖书人,他们中少有人有能力写出专业的藏书史。而我试图将这两者之间做一个结合。我初始的动机就是这样的。我既然了解这些当代藏书史上的事实,我觉得我有责任来忠实地记录下来,这样,就可以作为一种文献,成为研究藏书史的学者们左右采之的材料了。当然我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什么都不考虑,有时也会采取必要的回避。所以我会有另外一种记录,就是我自己的《藏书日志》,这是我一直坚持记录下来的,把所有的真实都写在其中,这么多年下来也积累了很庞大的篇幅,已经有几百万字了,这里我记录与书有关的一切,写书、藏书、买书、与书的交往等等,我知道是不可能发表的。我的目的很简单,因为我得到了很多不真实的资料记载,于是就是想留下一部真实的藏书资料。同样,拍场记录也是这样的,许多拍场的报道都是与真实的状况相去甚远,我们今天能不能有个真实的历史记录呢?虽然我们不能将问题绝对化,但是我们是不是能更接近真实地记录下来呢?那出于这种理解和认识,报道出一种真实来,让研究藏书史的学者来甄别使用,这就是我坚持写拍场述评的动机和原因。
所以每一场古书拍卖,我都会写述评,而这又会成为一些研究者写藏书史的资料。我就是想描述一种真实的过程,让将来有研究需要的人采集藏书的真实和可靠历史。但是有些评价未免主观而不能道出,别人怎么看待这个真实,怎么解读它,那是研究者的理解,我只是把拍场事实记录下来,不作过多的主观评价,这个时代产生了什么结果,怎么解释同样由读者来判断。我采用这种方法来记录也算是另外的一种用心吧。
贾建钢:您所描述的就是一部藏书家心目中的藏书史。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义责任问题,而是看似简单的一段历史,您却将其真实地记录下来,这真是不简单。
韦力:谢谢您的夸赞,希望我能有机会把这个事情一直进行下去。但近来我忙于文学寻踪的写作,也确实对拍卖上的事情关注得少多了。人的精力有限,想把任何一个事情都做得完美,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贾建钢:您的几部书跋集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相继出版,对学术界收藏界影响很大,您对此又怎样的一个全盘考量?您的书跋写作与古人的题跋有何异同?您对古籍书跋的后续写作有何计划?
韦力:书跋古人很早就有,但这种跋文大多不具有观瞻性,而这种改变则以黄丕烈为标志。他把买书的心情等都融入到里面去,当时人都不理解,认为他的这种写法不学术。但是把学问做出情趣,则是黄丕烈所写书跋的亮点所在,后来唐弢写“书话”,其实就是延续了黄丕烈书跋的风格。1949年以后直到文革之前,由于基本没有了古书买卖,所以后来也就没有古书的书跋了。文革结束之后,上海的黄裳先生又开始写书跋,他做过记者,写文章很漂亮,所以写的书跋诗情画意,很有情趣,就受到人们的喜爱。但是他的书跋是完全站在鉴赏角度来写者,少有考证。
而我的书跋没有他那么风雅和好功底,我觉得书跋可以写藏书心情和处境,但是书跋万变不离其宗,不能离开书,还得有书的考证,留下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我的书跋内容既有古人对书籍的考证,也有今人的一些得书记的内容。我对我的书跋的理解,它既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著作,也不是诗情画意的抒怀散文,它只能是“芷兰斋书跋”。我目前正在写第五集书跋,还没写完。因为我的藏书量比较大,现在写作的书跋文章都是围绕一个体系来写,主要就是围绕我藏书中的稿抄校本这个体系来写作书跋。以前我的书跋都是按照偏好来写者,对哪部书有兴趣就先写哪部书,后来从第四集开始,就有意识地按照专题和体系来组集,比如第四集的主题是“词”,第五集写的是以“诗”为主,现在就是这样一集按照一个主题来写。一年一本这个写法现在看来还比较受欢迎。第五本《芷兰斋书跋》再过一个多月后就能够写完。
贾建钢:您多年来的古籍收藏为您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我也注意到您对古籍书目著录方式的重要探索。您在《芷兰斋书目著录方式》一文中,着重指出“用纸”可为版本判断的重要依据之一。请您详细谈谈纸张如何体现了其在古籍中的重要研究价值?
韦力:把古书用纸作为判断版本的依据,也算是我多年来藏书实践的一大发明。《芷兰斋书目著录方式》其实是我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一次国际目录学研讨会上的讲话稿,后来根据录音整理发表在《文献》上。那篇文章显得很口语化,会议要求每人只讲20分钟,来不及读论文。下面我就来说说我的具体看法。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见到的书籍,除了甲骨文、简帛等之外,99%都是纸墨的结合,这两种东西叠合就构成书页,书页集合到一起就构成了书,因此纸张是书籍的基础。即使按照两分法,纸张也有一半的判断价值。任何书的附着物,都要早于书形成本身,以此类推,这上面的文字绝不可能早于纸,它只能晚于或等于纸的年代,纸张的断代决定了文字的上限。一部书假如使用的是明代的纸,你说是宋版书,这是不可能的。但书纸只能断定上限,还不能简单判断下限。比如这是一张清代的纸,它所印出的书籍版本就不可能是宋元明版的,相应地判断出它只能是清之下的版本。于是纸张成为书籍断代的重要依据。宋刻本书,早期大部分用白麻纸,晚期大部分用黄麻纸,而到了明代,麻纸在做书过程中的用量越来越少,慢慢使用了棉纸和皮纸,这个特点就可以作为断代的依据,前人就有了这种总结。但是,不论古代的书目还是今天的书目,包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吧,通通不著录纸张。既然纸张这么重要,为什么各种书目都不著录呢?
书籍的纸张除了断代价值之外,同时也是区分版本的标志。比如清代的内阁上谕档,就有不少记录了皇帝给待办处下的口谕,有时皇帝指挥得很细,比如说某位臣子向他汇报,书版已经刊刻完毕,请皇帝指示要印多少部。皇帝会具体地说,用连四纸刷五部,而这五部分别陈设在哪个宫内;而后再用太史连纸刷印300部,作为赏赐之用。由这段话即可知道,同一个时期,同一部书,却有着不同的刷印纸张,而这两者之间,数量相差巨大,站在物以稀为贵的角度来说,其珍贵程度也有很大的悬殊。然而,现在的各种公藏目录,都没有纸张这一项。所以说,很难知道,某个馆所藏的某部书,究竟是以何纸所刷印者。而从文物角度来说,作为刷五部的连四纸本,要远远高于太史连纸本,如果目录中没有标示出来,怎么来做相应的定级呢?
既然纸张在定级和区别版本方面有着这样重要的价值,那为什么各个公共图书馆不把纸张作为一个项目来予以著录呢?有的专家告诉我,辨别纸张太难,你用它著录,如果著录错误还不如不增加这种方式,免得误导读者。但我想不能因噎废食呀,别人的看法我不能左右,那我就在自己的书目中来著录。我把自己的藏书目录单列“用纸”一项,希望帮助辨别古书版本。
复旦大学前任校长杨玉良先生在离任之后,钟情于古籍,成立了古籍保护研究院。他曾经亲眼见过南宋古墓中出土如新的古籍,惊叹于古书的纸张,于是咨询我古书用纸的问题,我就向复旦古籍保护研究院捐献了部分古纸,供他们进行科学研究。
贾建钢:据我检索相关文献,您不断总结自己的文化寻访和藏书研究的同时,还关注到哪些值得研究的课题或者建议?请谈谈您接下来的研究思路和著述工作?
韦力:接下来的两年时间吧,我计划要完成我的文化寻踪的相关写作。之后还打算做两个专题,这是在文化寻踪中产生的问题。关于“西学东渐”问题,过去几乎是一边倒的否定传教士对中国彻底的开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的邻国日本却不同,他们很纪念这些侵略过他们国家的人,他们认为是这些人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文明,我们几乎是一边倒地批判给我们带来的半殖民地的局面。但我觉得,传教士对中国的社会还是做出了一些重要的贡献,我觉得不应当遗忘他们的贡献。如果有机会,我要写一本这样的书,当然也同样是以寻踪的方式来着眼。
我的另一个计划,就是关于古纸的搜集整理。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四大发明有造纸和印刷术,也就是说一半都跟纸张有关,中国到现在都没有一部完整的古纸谱作为研究资料。我们常讲自己民族有辉煌的历史文化等等,我想尽自己的可能来做一部中国的纸谱,首先我打算要做的,是从安徽泾县开始把宣纸搞清楚。总之,我认为自己时时刻刻都是民族中的一员,我就要尽自己的能力给这个民族留下来一点像样的东西,这是我的初衷。所以我接下来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要做手工纸谱。宣纸在历史上到底是怎么流传的,到现在生产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我打算一边总结历史,一边搜集与古纸有关的东西。我不想只停留在说和讨论的层面,而是有好的想法就要去付诸实践。没人给我这种责任,但是这可能就是人生的求知,我不想要什么伟大和名誉。既然死是永恒的,那我就在这几十年中做点令自己满意的事吧!
贾建钢:韦先生,您不遗余力藏书、读书、研究、寻访的态度和实际作为真让人感佩,感谢您接受这次丰富的采访,也期待您在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在您的研究领域完成更多更优秀的成果,谢谢!
(责任编辑:苏红霞 校对:李俊丹)
G258.83
A
1673-2030(2017)01-0005-12
2016-12-31
[采访者]贾建钢(1976—),男,山东临清人,副教授,《邯郸学院学报》编辑部副主任。
[受访者]韦力(1964—),男,北京人,古籍收藏家,文化学者,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