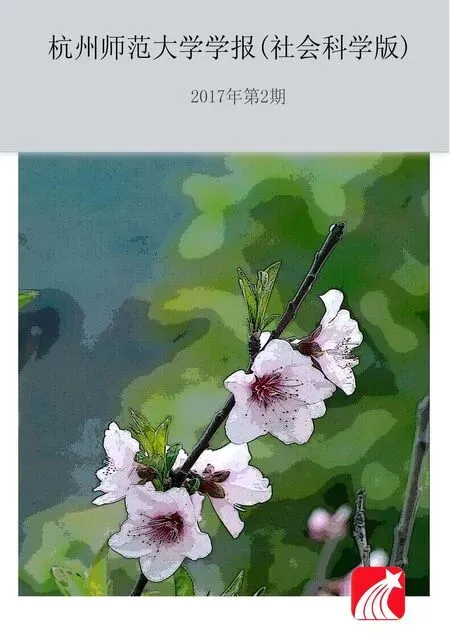鲁迅《野草》“虚无”的精神现象学解读
王 蓓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上海 200241)
鲁迅《野草》“虚无”的精神现象学解读
王 蓓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上海 200241)
《精神现象学》中意识的对象化理论,对理解鲁迅《野草》的“虚无”具有极好的理论借鉴意义。不同的是,鲁迅并非将“虚无”内构于纯精神思辨中予以克服。《野草》时期的鲁迅,正经历着他生命历程中最为黑暗苦闷的时光。恰是这种基于现实的深切感受,促使他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决绝态度,开启了一条真正立足于社会历史实践、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自我完成(自我对象化、对象自我化回环往复)的“虚无”之路。本文以精神现象学为研究视角,以《野草》中的“虚无”为研究对象,在鲁迅思想发展的动程中,梳理《野草》“虚无”的内涵及其形成过程,并对其作为一种自否定的历史性运动予以新的体认,最终将鲁迅“虚无”的辩证法还原至感性的现实活动中予以把握。
鲁迅;《野草》;虚无;对象化;精神现象学
《野草》连《题辞》共收入24篇散文诗,均得自于晦暗现实的苦闷体验。在其英文译本序中,鲁迅清楚地交代了那些诱发其创作动机的现实事件,这些经验型的事件在构成野草成书原因的同时,也成了鲁迅内在精神喷发的火山口。恰恰是这种基于现实的深切感受,促使鲁迅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决绝态度,开启了一条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自我完成的“虚无”之路。这条“虚无”之路,在《精神现象学》中被黑格尔视作是精神内部自我纯化的必经之途,在《野草》中则显现为鲁迅立足于现实生活,充分经验各种意识对象进程中的绝望之旅。
一
1927年9月,鲁迅在杂文《怎么写》中对《野草·题辞》中的“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作了如下解释:
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1](PP.18-19)
这里无疑汇聚了鲁迅纠葛的精神丝缕。远处的“坟冢”、“佛寺”、海天相接,瞬时激发了他关于生命的复杂体验,生命生成的过程顿时在他眼前流动、浮显,这即是沉默时的充实;然而要将这积淀在心田的感受全部外化托出,即把自我意识作对象化呈现,就会发现其间充斥了愿望的零落,生存的死灭,那些曾经确证的自我顿时变得模糊、值得怀疑,这就是鲁迅“将开口”的“虚无”。这“虚无”,乃是鲁迅驻足于现实中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显现为现象的意识的全部领域”[2](P.55)的怀疑。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导言中,把这条怀疑之路称为人精神历程中的“自我完成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乃是对现象知识的非真理性的一种自觉的洞见,对于这种怀疑而言,毋宁只有真正没现实化的概念才是最实在的东西。”[2](P.55)在黑格尔看来,人的自我意识乃是一个不断将自身外化为对象,并不断扬弃这种对象化,最终回复到自身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意识对象本身是作为否定和扬弃自身的东西存在的,“对意识来说是正在消逝着的东西”[3](P.104),因此意识的对象性就是虚无。由此,对鲁迅的名句“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我们可以作如下解释:没有现实化(对象化)的概念(意识)是“最实在”(“充实”)的,而概念(意识)的现实化(对象化)是“非真理性”(“空虚”)的。因此客观对象确定性(真理性)的逝去与演变也就成了《野草》虚无意识的逻辑起点,鲁迅以此开启了一条精神现象学意义上最为彻底的怀疑之路。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我完成的怀疑主义,并不同于那种“严肃地追求真理和从事科学的人所自以为业已具备了的那种决心,即……不因权威而听从别人的思想,决心亲自审查一切而只承认自己的行动是真实的”[2](P.55)。我认为,黑格尔所说的“决心”,与“五四”启蒙运动以来鲁迅曾深陷的那种只遵从自我独立理智的启蒙主义信念如出一辙。早在留日时期,鲁迅就渴慕在西方启蒙精神的映照下,由彼及我地贬黜枯槁的传统价值。他曾与尼采一样,站在新旧时代的交汇点上,决心对尚且处于“十全停滞的生活”的中国作破坏式的幽愤之思。他极力宣扬摩罗诗人身上“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4](P.101)的“强力意志”,并以此重构出“以力抗强”、“非达不已”的启蒙话语实践。然而这种只遵从自我确信的“抱诚守真”之启蒙主义观念,给鲁迅带来的却仍然是“空虚”*鲁迅在小说《伤逝》中质疑了子君觉醒后的豁达无畏:“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而对这空虚却并未自觉。”鲁迅所说的“空虚”与黑格尔所说的一味“遵从自己的确信”的“虚浮”,在思想上可谓同气相求。对启蒙的质疑也指向鲁迅自身,1918年《狂人日记》中“狂人”痛苦地捧呈出了自己也有“四千年吃人的履历”的灵魂即是明证。。在《野草·希望》中,鲁迅这样写道: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
“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的歌声,乃是鲁迅早年“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4](P.84)的真实写照。然而这种只遵从自我的确信与盲从权威其实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是一个虚空罢了”。在《怎么写》这篇杂文中,鲁迅以文学化的表达陈述了这一观点:“尼采爱看血写的书。但我想,血写的文章,……它比文章自然更惊心动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变色,容易消磨。”[1](P.19)对早期尼采式启蒙主义“决心”的审视使得鲁迅发现,这所谓的血的“精义”其实并不必然地导引出真理*《复仇》(其二)中牺牲被庸众所钉杀,《颓败线的颤动》中老妇在血与泪的苦痛中养育了女儿,却遭受着成年的女儿及女婿的“冷骂与毒笑”,血泪浇铸的生命并不必然导引出真实的自我确证。,它仅是鲁迅意识发展进程中的怀疑之始(开始怀疑权威),还未真正让他踏上“怀疑之路”。真正的怀疑之路乃是一个现实的生成过程,是自我在人生的长途中,不断地扬弃过往的虚妄,突破既存的框架(外在的权威和内在自我的虚浮),从而在否定虚无的绝望之处开启一条本真意义上的希望之路。这也就是《野草》中所谓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真义所在,即当面对以往虚妄的信念而产生绝望时,你的认知层次实际上已经超越了过往的“是”与“非”的虚浮,进入到了一个等待你去开拓的新的认识领域,希望就由此产生了。
在黑格尔看来,这条永无休止的怀疑之路的内驱力之根源,在于人的自我意识发展过程中的“否定性”环节——虚无。由于个体直接把自我视为现实化的客观对象,这个客观对象的性质本身“对于自我意识来说是一种障碍和异化,因此,对对象是一种否定的东西、自我扬弃的东西,是一种虚无性”[3](P.108)。换言之,在意识发展的进程里,对这种现实化对象的体认将最终作为非真理性(不真实性)的认定被扬弃,因此自我对象化的过程就反倒成其为个体自我自身的毁灭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毁灭”的结果并非是使自我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它乃是针对个体意识发展进程中特定阶段、特定方面的否定。黑格尔认为这种特定的“否定”事实上是通往终极目的地的“过渡”性环节,它不仅否定了过往,还预示着新的认识环节的展开。这对理解鲁迅《野草》的“虚无”有极好的借鉴意义。1924年鲁迅开始投入《野草》的创作,在“无聊”与“苦闷”的虚无中,他再次带着“遗忘”试图踏上一条求生的“新路”。这样的求生逻辑无疑根植于他的生命诉求:“因为还活着”,就不能惮于前路的消隐,求心啮己的活动就仍需以“虚无”为起点。这正如鲁迅自己所认识的那样:“‘一步步的现在过去’,自然可以比较的不为环境所苦,但‘现在的我’中,既然‘含有原先的我’,而这‘我’又有不满于时代环境之心,则苦痛也依然相续。……也只好……‘有不平而不悲观’,也即来信之所谓‘养精蓄锐以待及锋而试’罢。”[5](PP.25-26)这意味着心陷“虚无”并不惮于“前路”的消隐,乃在于“虚无”本身亦蕴藏着巨大的反弹力:它的出现将预示着新生起点的建立。
正因为此,鲁迅不能安于生命历程中的任何一种形态,为此他要不断怀疑当下的合法性,否定和扬弃任何阻碍新生的力量,这就使他滋生出一种过客式的“息不下”的心境,即拒斥生命中任何确定的栖身之所,直至走到了“虚无”的“坟”。在鲁迅那里,“坟”并不是生命终结后“一无所有”的幻灭象征,而是以“埋葬”来隐喻行动主体对过往经验的反思与否定。关于这点,他在《坟》的题记中有过提示:“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蹑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6](P.4)这样看来,过客行走的终极目的并非是为了成为某种规定的形态,而是凭借自我超越的“走”获得质的提升,个体精神的成长也就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否定过往、超越“这时”、创造新生的旅程中历史地养成。《墓碣文》则以死尸抉心自食的感性场景,隐喻鲁迅向内透视的精神历程。文中,墓中死尸把“尝心”作为探求“心之本味”的途径,这一行动从象征层面暗合“认识自我如何可能”的哲学性难题。然而从精神现象学角度看,处于时间和空间中不断变化的“自我”,不可能“存在于表示某种确定结果的或可以直接予以认识的一个命题里”[2](P.26);它只能在不断认识自我,又不断地否定即存自我的经验领域中艰难地生成。
由此看来,《野草》的“虚无”已抛弃了传统“静观”哲学的“随喜”内里,俨然是一种具有现代生命意识的历史性运动。关于这点,鲁迅在《题辞》中有明确的表达:“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综观整个生命运动的过程,否定过往并非仅仅只是让“过去的生命死亡”,更是因为“死亡”使过去的生命经验得以自明,让他“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真正知照他每一个历史瞬间都曾在创造中新生,在新生中死亡,又在死亡中复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并不意味着生命创造的一切终将在历史的时空里灰飞烟灭,恰恰相反,正是腐朽教他觉知:过去的经历已流转成了新生萌动的地基,否定后诸多的“这时”一起汇聚为生命的经验之流,使得生命成为一个永恒开放的系统。
二
1919年,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这样写道:“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6](PP.136-137)鲁迅把后起的生命形态视为以前的生命形态的批判与否定;以从前生命形态的覆灭,作为后起的生命生长的起点,所有的死亡与否定——“虚无”在此构成了整个生命运动的全部经验,生命正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涵容着这些收获不断前进与提升。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将这种具有否定意义的“虚无”看作是自我意识发展的推动性力量。他把人的精神世界即自我意识的发展,描述成一个将“自己变成他物、或变成它自己的对象和扬弃这个他物的运动”[2](P.23)过程。自我意识要达到绝对自为的状态,第一步就是要认识自己,将自我异化为与自身不同一的对象。这个“不同一性”即是黑格尔所说的“一般否定性”,即虚无。在这个环节里,自我本身与对象都是不完善的,需要利用这个“一般否定性”来推动自身向前运动。值得注意的是,“虚无”作为一种否定性的推动力量并不是从外部发生的,而是源于自我意识自由本相的内源性“自否定”。在《狗的驳诘》中,鲁迅就展现了这种自我意识“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2](P.11),文中“狗”分裂成人的另一重自我意识对自我进行审视。以“狗”说自己“愧不如人”发难,迫使“人”在异己的对象(“狗”)眼中看见了他自身非人的一面。在“狗”的一再追问下(自我对象化过程中),人洞悉了自我的本质与现实化人的不同一,从而推动其对自身的否定,人便在这种否定中获得了返回自身的可能。在哲人们看来,“自否定是一个人惟一可能的活法,它就是生活本身”,“是人在每一瞬间历史地自我创造、自我发展的方式,它永远是一个开放系统,永远是一个有待完成的开放系统”[7](PP.26-27)。鲁迅正是在此意义上为自我探求本心开启了新的路径。《墓碣文》中“死尸”抉心自食,即以“自否定”的方式展开:将“心”剖出自食,是将“心”变成异己的对象加以审视。以这种酷烈的方式求知本味,其目的在于使“心之本味”从抽象普遍向具体可感的实在外化。然而,酷烈的创痛掩盖了心之本味,使得“心之本味”求而未果,“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此处鲁迅以省略号作结,预示着“不得本味”的求索历程没有结束,它仍然在以一种“自啮”的方式延续着。
《野草》中的“梦”系列,可看作是“自啮”运动的体现。其中七篇直接以“我梦见自己……”作为开头,即是进入了厨川白村所谓的“肉眼合,而心眼开”的“静思”[8](P.69),即以我心观我心之“味”,将自我放在一个对象的位置来加以审视和反思。这意味着在一个非现实的境界里,绝对化地直呈内在生命运动的轨迹。这种将自我对象化的否定性认知方式及其历史运动,是鲁迅精神历程中一条永恒开放的绝对认知之路,是不断建立世界,又不断打破所建立世界的过程本身。《失掉的好地狱》就以人与魔鬼的暴力对抗来隐喻人内在意识在求索过程中的不安分不停歇:当人类战胜了魔鬼,“是鬼魂的不幸”;当魔鬼统治了人类,“人类又开始绝叫”。这意味着人的自我意识是一个始终处于否定和驱逐状态的动态结构。如黑格尔所说:“当每一方面自以为获得了胜利、达到了安静的统一时,那末,它就立刻从统一体中被驱逐出来。”[2](P.140)正是这样一种否定和驱逐的本性,孕育了人于绝望境地之中的超越意识。这与《摩罗诗力说》中的“撒旦意志”构成了精神层面的呼应:“神,一权力也;撒但,亦一权力也。惟撒但之力,即生于神,神力若亡,不为之代;上则以力抗天帝,下则以力制众生,行之背驰,莫甚于此。顾其制众生也,即以抗故。倘其众生同抗,更何制之云?”[4](PP.80-81)无论从“立人”的视域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纬度,以精神现象学的视域观之,撒旦作为神、人的对立面,它永远是不断被否定、被驱逐的。这正如黑格尔所看到的那样,自我意识乃是一个树立双重对立面的动态结构,唯在其对立面才会看到自己的虚妄不实。当自我意识到自己与本身并不同一时,处于其中对立的双方将无法在其对立面获得“安息”,它自身就会利用这个“虚无”推动自己向前运动,并且总是试图在自己的对立面中重新创造自己*参见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158-159页中对“变化的意识”的描述。。由此将生命放在一个有机的系统中考察便不难发现:“真理就是它自己的完成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圆圈,预悬它的终点为目的并以它的终点为起点,而且只当它实现了并达到了它的终点它才是现实的。”[2](P.11)
那么,这种自否定的活动何以不至于陷入无限的循环之中呢?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最后以“绝对精神”封闭了整个循环,即“当实体已完全表明其自己即是主体的时候,精神也就使它的具体存在与它的本质同一了”[2](P.24),此时“虚妄的东西也不再是作为虚妄的东西而成为真理的一个环节”[2](P.26),生命在绝对意义上完成了它所有的求索活动。以此来观照《野草》之“虚无”,如在《墓碣文》的最后,鲁迅以虚拟的语态对死尸“心”(本味)与“心的对象”(徐徐食得之味)作了假设性的同一,即:“待我成尘之时,你必见我的微笑。”“成尘”意味着有形的生命体完全逝去,至此自我将带着全部否定后的收获返回自身,成为“实体性的内容”,“心”从根本上克服了自身与其对象之间的不同一性,完全处于绝对无弊的状态,各个否定阶段的虚无在此揭下了虚妄的面纱,成了真理自身,这即是否定辩证法的最终归宿——回到“心本身”。不过,鲁迅敏锐地意识到这种绝对的同一在现实历史中是无法实现的。梦系列中“梦境的破碎或毁灭”,即是作为鲁迅返回现实世界的明证。1926年他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这样写道:“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6](P.300)这并不意味着鲁迅自我否定的精神进程没有黑格尔那样彻底,而是鲁迅把人的自我生成看作是一个过程同时,还把人的历史看作是作为“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3](P.97);认为人只有自觉地直面具体的鲜活现实,“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才能在感性活动中真正地实现自否定,从而实现如哲人们所说的“对自己世界永无止境的冒险开拓”[7](P.28)。这种直面现实人生的清醒、决绝,是与黑格尔把精神运动的过程描述为“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的最大区别。
三
以上借助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之自我意识(精神)的对立与外化的现象学理论,阐述了鲁迅《野草》“虚无”的内核。从辩证法上看,鲁迅与黑格尔可谓不谋而合。但鲁迅对“异化自我”的否定和扬弃与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异化”在取径上却并不完全一致。在黑格尔看来,精神的发展过程即绝对理念认识自身、克服自身片面性、并回复到自身的过程。在这个辩证运动的过程中,“自我”呈现为一个普遍的、抽象的精神性主体;鲁迅是自实际的生存境域来体味自我决断的艰难,其“自我”则呈现为一个具体的、现实的生存性主体。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他非常推崇西方克尔凯郭尔的关于“个体”的存在主义学说*鲁迅的“虚无”意识受西方存在主义之父克尔凯郭尔影响在学界已有论述,克尔凯郭尔关于“自我”的学说亦在黑格尔哲学的直接影响下和对其的回应中形成。克尔凯郭尔认为,个体的内在性是独特的、具体的,他否定将自我的现实生存建构为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反对黑格尔把自我意识的主体视为抽象的“精神主体”,认为现实中“生存主体”——“个体”才是真理之所在。这种对个体生存的主体性和超越性的自觉也正是鲁迅推崇克尔凯郭尔哲学的内在原因。在《野草》中,这种作为个体的生存性的独特体验随处可见。然而,这并非意味着鲁迅的“虚无”就是克尔凯郭尔式的,克尔凯郭尔所强调的主体性割裂了主体与现实社会的联系,其主体最终沦为一个孤独的个体。就这一点而言,克尔凯郭尔并未超越马克思所批判的黑尔格对“自我意识”的抽象性思考。鲁迅亦是从“个体”生存角度来体味人的异化,将个体生存置于异化的社会现实中,并通过现实的感性活动来否定和扬弃这种异化感和虚无感。在鲁迅看来,社会虽导致了个体的分裂和瓦解,却是个性和自由得以发展的条件。这也是鲁迅与克尔凯郭尔最大的不同,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的“虚无”意识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产生了契合。,主张把独特的个体置于具体的生存现实中来体认,但他并不认为可以如克氏那般,割裂个体与社会的联系来独断地认识个体的内在性,进而主张在个体的社会性现实生存感受中体味人的异化,即通过社会性实践来认识自我之于现实的无力感,同时否定和扬弃这种“无力于现实”的“虚无”。这种在真实人生体验中生成的现实“自我”,超越了黑格尔“精神”(自我)的抽象性,在个体的现实生存基础上重建了新的实践起点,并由此划出了鲁迅生存哲学与西方哲人之间的界限。因此只有把鲁迅“虚无”的辩证法还原至感性的现实活动中,才能对之予以真正的把握。
在《一觉》中鲁迅这样写道:“飘渺的名园中,奇花盛开着,红颜的静女正在超然无事地逍遥,鹤唳一声,白云郁然而起……。这自然使人神往的罢,然而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一觉》的写作时间已近《野草》的尾声,此时的鲁迅业已经过了女师大风波、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以及“三一八”惨案等一系列事件。他深切地意识到,人要从抽象的概念生成为切实具体的生命,除了一次次地投入现实的河流,过自己未知的生活,别无他途。对此,黑格尔这样说道:“抽象的东西,无论属于感性存在的或属于单纯的思想事物的,先将自己予以异化,然后从这个异化中返回自身,这样,原来没经验过的东西才呈现出它的现实性和真理性,才是意识的财产。”[2](P.23)换言之,人要从抽象走向具体,就必须要经历这样一个将自我外化为他物的对象化过程。然而黑格尔所谓的意识的对象化是发生在意识内部的,马克思在洞悉了这种片面的唯心主义的同时,创造性地发现:“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3](P.106)这意味着人的生成过程乃是在现实中外化自己的本质力量,通过对象来表现和确证自己的过程。这点在《死火》中表现得尤为深切,文中被我“温热”的“死火”无论是“留下”,抑或跳出冰谷,其命运均难逃“毁灭”的虚无。选择前者固然暂得凝固的形象,然而这种从未在对象身上确证过自己价值的生命样态意味着它不过徒有火的形式,实质不过是如马克思所说的“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3](P.107)。要让这个抽象的存在变得具体,唯有通过重燃自己,将“我”送出冰谷方能得以完成。这是由于“燃烧”的感性活动使它从凝固的形(抽象意义的存在)踏上了现实之火的生成之路;唯其如此,“死火”才能在他物之中真正获得确证自己生命的力量。
由此可见,生命的实现过程乃是生命通过实践对象化的过程,生命只有在处于对立面的对象身上才能认识自己、否定自己、发展自己,才能现实地显现自己的本质能力。这一点在《失掉的好地狱》的文末有明显的体现。文中人类战胜了鬼魂,作者写道:“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之所以仍要寻“野兽与恶鬼”,即在于“抽象的人”要变为现实的人,不能仅仅止于打败自身中的“野兽和恶鬼”,而应在这条怀疑(猜疑)之路上不断地通过实践将自己对象化,在树立自身的对立面(寻找自身经验中的野兽和恶鬼)的过程中,审视自己、否定自己、扬弃自己。唯有如此,人才能在自我生成性的运动中感受到生命的实在性。《野草》的写作,即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对象化的生命进程中得以生成的。《野草》创作期间,鲁迅多次置身于政治与文化论争的风口浪尖,甚至一度被迫逃离北京,却“照例同黑暗捣乱”*鲁迅在1926年6月17日《致李秉中》的信中坦言自己意欲离开北京到他处休整一段时间,他如是写道:“自己一人去,期间是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此后我还想仍去热闹的地方,照例捣乱。”。对此他这样写道:“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9](PP.4-5)于现实中获得的“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即是鲁迅在自我对象化的历程中不断认识自我、洗炼自我的明证。之所以鲁迅将这些杂感视为“无聊”的东西,乃在于其间蕴含着他对晦暗现实的不满,对无力于现实之自我的否定及扬弃。与此同时,他对这些杂感有着别样的深情,则在于这些从生活实践中孕育出来的经验是证明和实现他的生命价值不可或缺的对象。在现实的经验中否定无力于现实的自我,重建新的实践起点,如此循环往复,进而获得求证自我的本质性力量,这是鲁迅辗转于“风沙”般现实里生存的全部意义。
如此一来,人对象化的过程就绝不仅仅止于主体对客体的对象化,而是通过实践,主体能动地将自己的能力作用于客观对象的同时,客体世界也将反哺主体,使之不断地在诸多被扬弃的“虚无”中把握生命的经验之流与世界的本真实相。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只要我有了一个对象,则这个对象就以我作为对象。”[3](P.106)1925年所作的《这样的战士》,就是置身于“无物之阵”的孤绝斗士通过实践往返于自我与现实对象之间的典型一例。在与“无物之物”的对峙中,坚执的战士反复地经历着“扑空”与重新“投枪”的运动。显然,“无物之物”的终胜与战士自身的衰老并没有造成他幻灭的意绪,反而在与它们一次又一次的搏击中激发了他倔强的斗志。这里“投枪”的动作,不可不谓熔铸了战士全部的生命经验。它既把战士与“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相区别,又让他们内构于自己的行动中,并对其予以能动的体认,从而在对失败经验的否定与扬弃中孕育出重新投枪的巨大反弹力。毋庸置疑,反弹力只有依靠战士的行动方能得以实现。
再看《复仇》(其二)。文中的耶稣宁可经受酷刑的创痛,也不喝让他神志迷离的“没药”,为的就是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样对付他们的神之子,而且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以这样的方式对对象加以审视,不仅是对对象即刻表现出来的残忍与血污的否定,更是用一种反思的态度来观瞻自己实践力量(对象化过程)中所存的虚浮,这种特定的虚无乃是促他返回自身的巨大推力。当肉刑的痛苦加剧,他在钉尖穿透掌心的痛楚中升华出别样的柔和。这乃是其在对象非人的一面中感受到痛苦的同时,清醒地预见到了艰难的布道之路绝不会随着自己肉身的死亡而终结,因为此刻的绝望正是孕育未来的永久希望的初始。终于,他在“碎骨的大痛楚”中“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这是由于他模糊的自我在审视对象的过程中逐渐清晰:他的布道之路已然让他摆脱了与对象的同一性,他早已从众人顽冥的残虐中解脱出来,在一次次与血污的抗击中成为了人“自己”,这样的欢喜乃是在主体与对象的相互异化中体会到对自我本质确证的欢喜。
很显然,这里神之子的经历带有明显的自况意味。《野草》成书之前,鲁迅已在“人生的长途”上经历了数度沉浮。自旅日时期力倡文艺救国继而投身新文化运动,再到1925年介入女师大风波被卸职,期间一连串的失败确使他“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10](P.439)。这样的无聊虽造成了他短暂的沉默,却迫他“反省,看见自己了”[10](P.439):鲁迅对自身的判断,也随之经历了由最初的“立说”的“启蒙者”和寂寞中的“呐喊者”,再到社会文明的“批评者”的转变。这一轨迹囊括了鲁迅二十余年思想变化的丰富内容,同时也隐含了他置身于“风沙般”现实中实践方式的调整。
现实生活中的是非与成败无疑浇铸了鲁迅生命对象化过程中的虚无,然而正是有了这些“虚无”,他才有了意识到自身的可能。关于这点,鲁迅在《题辞》的结尾处显示出了他对这种生命运动自明的狂喜:“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和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原本是生命中对立的两极,此刻统一在象征“我”的个体生命链条——《野草》内,成为确证其生命意义不可或缺的对象。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3](P.88)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鲁迅《野草》的“虚无”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资源中具有弥足珍贵的研究价值。
在黑格尔看来,人的精神是一个“不断外化、对立化与不断扬弃外化、扬弃对立化而达到曲折前进的统一过程”[11](PP.47-48)。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鲁迅并不将个体自为的生存置于抽象的思辨之中,而是立足于现实的历史,将具体的生活经验据为己有或者加以扬弃,使旧的、逝去的生命形态变成新生萌动的起点。在此意义上,《野草》也将成为鲁迅历史的生命形态,在追求新生之路的进程中最终也将被鲁迅历史地扬弃。我想,这才是鲁迅说“《野草》是再也不会有”的真正缘由。
[1]鲁迅:《怎么写(夜记之一)》,《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2][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3][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4]鲁迅:《坟》,《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5]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6]鲁迅:《坟》,《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7]邓晓芒:《“自否定”哲学原理》,《实践唯物论新解:开出现象学之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8][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
[9]鲁迅:《华盖集》,《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10]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11]周志山:《〈精神现象学〉论“社会关系”和人的生成》,《学术研究》,2002年第11期。
(责任编辑:沈松华)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Nihility inWildGrassby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WANG B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The objectification theory inThePhenomenologyofMind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nihility” inWildGrasswritten by Lu Xun. However, Lu Xun didn’t attempt to overcome “nihility” on the basis of total spiritual reasoning as he was experiencing the most painful time in his life during his creation ofWildGrass. Based on his deep experience upon the reality, he determined to start a practical path of “nihility” rooted in the society and the history through a resolute attitude of “despair means hope”, thus achieving the recycle of self-objectification and object-individualization in a spiritual phenomenological mann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nihility” inWildGrass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Lu Xun’s thoughts, and proposes a new perception upon this historical movement of self negation by sorting out its connotations and procedures. On the return from dialectics to perceptual activities, “nihility” of Lu Xun is supposed to be interpreted.
Lu Xun;WildGrass; nihility; objectification;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2016-05-06
王蓓,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研究。
I210.97
A
1674-2338(2017)02-0096-07
10.3969/j.issn.1674-2338.2017.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