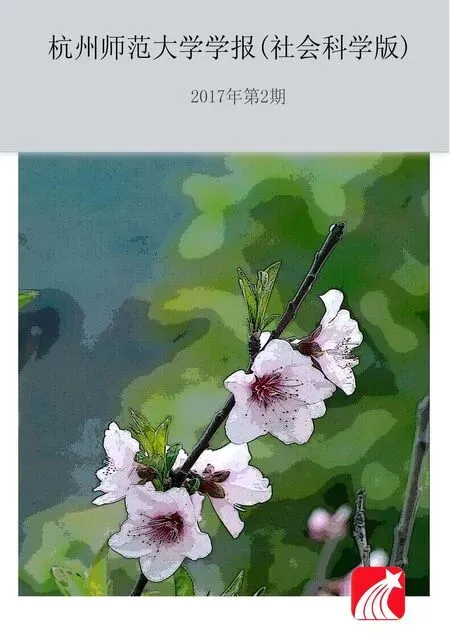巴特的“愉悦”与巴塔耶的“痛苦”
杨 威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200241;第二军医大学 人文社科部, 上海 200433)
巴特的“愉悦”与巴塔耶的“痛苦”
杨 威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200241;第二军医大学 人文社科部, 上海 200433)
巴特的“愉悦”与巴塔耶的“痛苦”既呈现出字面上鲜明的对比和反差,也具有内在的联系和共通性。两者都指涉了迷失自我、摒弃知识和拆解体系等含义,在这方面它们其实是一致的;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巴特的“愉悦”关注文本的后结构主义生成,而巴塔耶的“痛苦”则旨在以神秘体验拒斥理性思考及其话语。
巴特;巴塔耶;“愉悦”;“痛苦”;后结构主义
“愉悦”(la plaisir)和“痛苦”(le supplice,又译为“刑苦”)这两个概念,分别来自罗兰·巴特的《文本的愉悦》(LaPlaisirdutexte,1973)和乔治·巴塔耶的《内在经验》(L’expérienceintérieure,1943)。“愉悦”是《文本的愉悦》书名的关键词;“痛苦”则是贯穿《内在经验》的主线。这两个词,不仅作为对比鲜明的情绪性描述可以引发兴趣,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我们通过一种巴特式的开放性阅读尝试思想上的“混搭”游戏,从而呈现巴特与巴塔耶之间的思想关联。
一
巴特在词句的混杂断续中展开愉悦的写作,这使《文本的愉悦》一书最终呈现为四十六个断片(fragment),分散无序地堆砌在一起。然而,就像铃村和成认为的,“要理解巴特,这一部书就足够了,它是凝聚着巴特思想精华的重要著作”。[1](P.7)那么,在这部“重要著作”中,巴特的“愉悦”究竟指什么呢?
首先要澄清,“愉悦”并不以主体对客体的审美或参与为基础。屠友祥教授把巴特的“愉悦”(又译为“悦”)与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优美”作为参照,指出这是一种只与主体联系而与客体无涉的浑然同一的快适感觉。[2](P.1,译注)然而,严格说来,“愉悦”不是审美意义上的。在审美中,对客体的凝思也会产生愉悦的美感,然而,这种审美之愉悦往往以主、客体的设定为基础,这样就把文本当作了一种“物”。同样,“愉悦”也不能在通常的实践意义上来理解。在实践中,主体通过谋划与行动参与到对象之中,在改造对象的过程中获得自我确证之满足。巴特的“愉悦”,从根本上说不以主、客体的关系结构为基础。
其次,“愉悦”也不是基于欲望或期待的兴奋。巴特说:“文之悦并非肉身脱衣舞或叙事悬念之悦。”[2](P.19)在这两种情形中,都存在一种不断的、渐次的剥露,而兴奋点始终寄寓在欲望对象或悬而未决的期待之上。这种对欲望对象的急切渴念,是对“愉悦”的摧折缩减。“我们总是谈论欲望,而不是悦;欲望具认识论的气派,悦则无。”[2](P.70)而对对象完整呈现的秩序性安排,在巴特看来则是很乏味的。巴特的“愉悦”,也与这种完整性、秩序性无关。
从含义上说,“愉悦”既是愉悦,也是陶醉(又译为“醉”)。在1973年3月的一次专访中,巴特谈到:“在我的意图内,‘文之悦’指涉完全未感知过的审美之物,尤其是文学之物,此物是醉(jouissance),失去知觉(迷失)的样态,取消了主体的样态。……可惜,法语没有一个词能同时笼罩悦和醉;如此,须接受‘文之悦’的含混表达,它时而专指(与醉相对的悦),时而泛指(悦和醉)。”[2](中译本弁言,P.5)这样也就要求我们把“愉悦”与“陶醉”这两者结合起来理解。愉悦,是幸福怡然的状态,是个体在整体文化基础上散逸、漂移的快适;陶醉,则是一种销魂境地,意味着文化的碎裂和自我的解体。巴特写道:“悦的文:欣快得以满足、充注、引发的文;源自文化而不是与之背离的文,和阅读的适意经验密不可分的文。醉的文:置于迷失(perte)之境的文,令人不适的文(或许已至某种厌烦的地步),动摇了读者之历史、文化、心理的定式,凿松了他的趣味、价值观、记忆的坚牢,它与语言的关系处于危机点上。”[2](P.23)简言之,自我的持存同一,是“愉悦”;自我的解体迷失,是“陶醉”。如果说“愉悦”可以参照康德的“优美”,那么“陶醉”则可以参照柏拉图的“迷狂”。然而,愉悦与陶醉的对立,并不是截然相对的,而是一种具有共通性的微妙差异。正如巴特在增补的词语解释中所说的:“悦和醉的对立有点儿是愚弄人的东西;……这是种不确定位置的对立,是个话语离合器。”[2](PP.82-83)事实上,两者应该说是一对“活生生的矛盾体”,在两者的共在中,“一个分裂的主体,借着文,同时欣然品味着自我和自我之崩溃两者间的一致性”。[2](P.30)
“愉悦”与“陶醉”,是相对于知识而言的。知识是一种冷静的对待,“愉悦”与“醉”则是沉浸其中的共在。“没有比把文本想象成知识的对象(用来反思、分析、比较、映照等)更令人沮丧的了。文本是愉悦的对象。”[3](P.7)然而,这里遇到的困难在于,当自我陶醉时,这种陶醉是无法表达的。表达,就意味着要进行一种出离“陶醉”之后的话语叙述。因此,“陶醉”不可说,而“愉悦”却是可以用话语表达的。“愉悦”是可以言说的“陶醉”。这就显示了“愉悦”与“陶醉”的区分以及选择以“愉悦”来同时表达这两者的必要性。
通往“愉悦”与“陶醉”的途径是共在,并在共在中不断生成。用巴特的话来说,这就如同“与我所爱者在一起,且想及其他一些事”。[2](P.34)美妙的念头,在这种共在中产生;有效的创作,也在这种共在中进行。在这里,文本是敞开的可能性,是一片自身在无尽生成的空间。它拒绝作为意义的工具,拒绝成为系统而凝固下来。巴特强调“文本的愉悦”,就是强调“文本”(又译为“文”)的生成。“文(Texte)的意思是织物(Tissu);不过迄今为止我们总是将此织物视作产品,视作已然织就的面纱,在其背后,忽隐忽露地闪现着意义(真理)。如今我们以这织物来强调生成观念,也就是说,在不停地编织之中,文被织就,被加工出来;主体隐没于这织物——这纹理内,自我消融了,一如蜘蛛叠化于蜘蛛网这极富创造性的分泌物内。”[2](P.76)在这个过程中,巴特的“愉悦”中止了所指,凝冻了所有认识进程而成为“中性之物”。文本于是成为漂浮的能指。
二
巴特以“愉悦”为主题谈论文本的生成,巴塔耶则以“痛苦”的内在经验进行对谋划和话语性思考的拒绝。
与海德格尔关注此在的时间性类似,巴塔耶也关注在人类自我中时间性的构造意义。对巴塔耶来说,这种时间性主要体现在“谋划”中。什么是谋划呢?谋划是人类在世界上“行动”时遵从的原则。“简单说来,即‘现在此时’做某事、进行操作、从事活动,惟有‘期待’着到‘之后理应到来之时’能将其成果弄到手,能拥有某物,能对自己有益才能实行——所谓‘谋划’亦即这样一种行为模式。”[4](P.37)谋划,就是将“现在此时”系于“之后理应到来之时”,就是将实存向更加迟后延期,“此时此地的生”唯有作为彼时到达目标的过程、作为彼时完成事物的手段才有意义。巴塔耶认为,基督教教义实为造就现代谋划观念的一个源头,是它将人类的精神一直向着彼岸悬立,从而在谋划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内在经验》的第一部分“内在经验的一个导论的手稿”中,巴塔耶写道:“反对谋划观念,占据了这本书的本质性部分。”[5](P.18)这种反对,是通过以“痛苦”为主题的各章展开的。
那么,“痛苦”指什么呢?巴塔耶说:“去面对不可能性——过度的、不容置疑的——当在我看来再也没有什么是可能产生神性体验的;这就类似于痛苦。”[5](P.45)痛苦就是直面“不可能性”的体验,就是在失去了神性及其信仰之后,在失去了自我的确定性之后,沉入存在的黑夜,成为无法认知的“空无”(néant)的体验。它显然不是单纯地指称通常所说的肉体疼痛,也不是精神上的烦忧苦闷;作为一个生存论意义上的哲学概念,它特别地意指一种使理性无效的人类体验。在“痛苦”中理性是虚弱无能的,理性失去了它的支配地位。这种“痛苦”的内心体验,是行动、行动所依赖的谋划以及投入谋划的存在方式的话语性思考的对立面。话语性的思考,可以在从事谋划和行动的人身上看到。“谋划不仅是行动所暗含、所必需的存在方式——它也是处于荒谬的时间中的存在样式:它将存在交付于更晚的时刻。”[5](P.59)巴塔耶的“痛苦”,是对行动、对理性、对话语的取消,意味着对谋划及其所包含的时间性的反对。
这种“痛苦”是如何对谋划及其所包含的时间性进行批判的呢?首先,“痛苦”批判了救赎观念。基督教的救赎观念是造成谋划观念的罪魁祸首。它与“谋划”合谋,以禁欲和苦行压制了人类生存中的即时性活动,比如色情,“救赎是使色情(身体的酒神式耗费)与对无延迟的生存的怀旧分离开来的唯一手段”。[5](P.60)而巴塔耶要寻求的,却正是无延迟的生存。与这种谋划式的时间相对,巴塔耶的时间是孩子气的时间,它没有成年人的深谋远虑,而只有欲望的即时满足。其次,“痛苦”也批判了对和谐的关切。和谐是实现谋划的具体方式,它将谋划引向好的结果。使和谐得以彰显的是谋划者,他获得了平静,消除了对欲望的孩子气的不耐心。“美的艺术”(beaux-arts)中的和谐,则在另一种意义上实现谋划。在美的艺术中,谋划所包含的和谐的生存方式被直接变成现实;它基于谋划的人的形象创造一个世界,以各种艺术形式来反映这一形象。和谐,作为谋划,抛开了那种流动的、转瞬即逝的时间,将这样的时间抛回到外部;它所倚重的原则就是复制,通过复制将所有的可能性凝固成永恒。显然,复制就是对流动的时间的模仿,把瞬间的片段从时间之流中截取出来,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凝固的时间,进而创造出可以保存之物。这种凝固的时间在谋划之下往往又以“将来”为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复制就转变成了对时间的一种稳定的投资。艺术从谋划中借用了这种复制,它复制的是欲望,这使人们能够在艺术中看到欲望,但是,这并非欲望的真实的、活生生的满足,而是欲望的再现,是“画饼充饥”。“在艺术中,欲望回来了,但它首先是消除时间(消除欲望)的欲望,而在谋划中,只有拒斥欲望。”[5](P.71)谋划是奴性的,只是劳动而不能享受成果,对欲望只是简单的拒斥,而在艺术中,人们获得了主权,但是,这只是可以消除欲望的主权,作为消除欲望的欲望,它很少能达到目标,而更多的是重新燃起了欲望。由此看来,艺术作为谋划的补充,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解放。对巴塔耶来说,剩下的就只有非知以及与之相联的狂喜了。如果能够出离自我,如果自我(ipse)放弃了自我和对自身的知识,转向非知,痛苦就会变成狂喜,而要脱离谋划的牢狱,“出路就是狂喜”。[5](P.73)在狂喜中,不再存在客体,主体也不再意识到自己,主体、客体都溶解了。甚至,就连这被写作的“话语”,作为巴塔耶用以逃离谋划的谋划,也只是他与分享他的痛苦、渴望他的痛苦的“他者”之间的联系而已。最终,他将作为那“最后的人”,“掐死自己”。[5](P.76)这种狂喜,作为脱离谋划的出路,最终将通向至高性或自主性的瞬间。通过批判“救赎”和“和谐”,巴塔耶批判了谋划及其代表的人的生存方式的时间性,也消解了既成的人类之“我”。
在这个过程中,巴塔耶的写作也是采取了思索笔记、格言警句的形式,呈现为一系列散乱的片断;在内容上,则体现为一种语言的耗费,即用语言消解语言自身,并以此来指示出语言所“不可能”指示的东西。巴塔耶质疑话语和语言,在他的作品中,激情总是挣脱了话语的框架,在行文中四溢,话语性的思考成为体验的仆人;而语言则似乎是应该被憎恨的,它就像思想与生命之间的一道屏障,使人无法进行鲜活、直接和充分的表达。在《内在经验》中,巴塔耶对语言的憎恨就表现为词语的献祭,也就是让词语被随意支配,让词语自己毁灭自己,以这种方式让语言说出语言之外的东西。这种对词语的“大屠杀”,是悖谬性地让语言面对他者,以此来重新激活语言。
三
巴特与巴塔耶之间有诸多理论上的关联。巴特不仅谈论了许多巴塔耶也曾谈论过的话题,而且多次直接谈论巴塔耶。仅在《文本的愉悦》中,这样的直接谈论就至少有五处:他用“神经症”来指称巴塔耶所谈及的“不可能”的事物,并指出正是这种“神经症”才使写作成为可能;[2](P.14)他指出巴塔耶带有几分“隐伏的英雄主义”,对某种表述异常敏感,在这里,作者仍在战斗;[2](P.40)他用巴塔耶作例子谈论陶醉和恐惧的近似,指出巴塔耶能写作癫狂,却不能直接写作恐惧,以此说明恐惧之无法写作;[2](P.60)他指出巴塔耶借助“出乎意料之外的”唯物主义,即低俗唯物主义,来闪避唯心主义,以此探讨如何寻觅对立项的第三项;[2](P.67)他在谈论“醉”与“梦”的颠倒情形时,借用巴塔耶的《爱德华夫人》指出“醉的文”是“一个全然可读的轶事,却含着种种不可能存在的感觉”,而“梦是一个未开化的轶事,由完全开化的感觉构织而成”。[2](P.72)巴特阅读巴塔耶,我们则要阅读巴特的阅读。那么,在“愉悦”与“痛苦”的对照之下,如何看待巴特与巴塔耶之间的理论关联呢?
一方面,巴特的“愉悦”与巴塔耶的“痛苦”之间有共通之处。在理论内容上,巴塔耶的“痛苦”,就近似于巴特的“陶醉”。“痛苦”与“陶醉”,情形一致,功效近似,都意味着自我和理智的丧失。而在巴塔耶处于语言的悖谬性使用的地方,巴特则提出了“愉悦”。“陶醉”不可说,“愉悦”可以说。“悦的作者(及其读者)接纳文字:他退出了醉,便有权利和力量去表述它”。[2](P.30)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愉悦”是“痛苦”与可表达性的结合。这里还涉及对于表达的看法。
在理论表达上,巴特和巴特耶都批判了外在的描述。巴塔耶说:“在体验中没有什么是被陈述的,被陈述的东西如果不止是手段,那也是和手段一样的某种障碍;重要的不再是关于风的陈述,而是风本身。”[5](P.25)在同样的含义上,巴特也说:“悦的文并不一定是叙述愉悦的文,醉的文决非讲述那种魂销情迷之醉的文。”[2](P.67)巴特的这句话,如果套换成巴塔耶的句式就是:重要的不再是关于“愉悦”的叙述,而是“愉悦”本身。
在理论结构上,可以认为,巴特和巴塔耶同样都把“空无”作为理论的内核。巴塔耶的理论旨归是至尊性或自主权,并反复强调它其实就是“空无”。他说:“自主权是空无,我努力要说的是,把它作为一个物是多么笨拙(却又不可避免)。”[6](P.256)巴塔耶的思想依据其从物到人的主线层层深入,在逻辑构造上就犹如一个洋葱,虽然每剥开一层都有新鲜、刺激之感,但是最终等待我们的却只是一个“空无”。尤金·沙克尔(Eugene Thacker)还借此指出,巴塔耶将空无或虚空置入哲学思想之核心,是对哲学与神学关系的康德式划界处理的超越。[7](P.262)与此类似,巴特则直接用洋葱头作比喻来阐释自己的文本理论。“就是说,文本为一多层构造,其中没有中心,没有意义。除去它层层包裹的无限性,此外一无所有!”[8](P.308)巴特事实上更加自觉地呈现了这种空心状的理论构造。
另一方面,巴特的“愉悦”与巴塔耶的“痛苦”之间当然有微妙差别。其中,核心的差别在于后结构主义的文本生成与神秘体验的理性消解之间的不同,这在言说背景、批判对象和思想指向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第一,巴塔耶以生存论为背景,而巴特则以语言学、符号学为背景。巴塔耶避开了概念体系的演绎,直接关注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本身。他说:“我活在感性的经验里,而不是逻辑的解释里。”[5](P.45)在这个意义上,“巴塔耶的著作体现为对存在的理由的一种深刻的拒绝,这种关于存在理由的追问,被他视为理性的一种疾病。”[9](P.27)所以,巴塔耶并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沿着形而上学的方向去建构一种“基础本体论”,而是在内在生活的领域直接地阐发和描述了他对于存在的探索与领悟。巴特是作为批评家和符号学家出场的。他的语言观深受索绪尔的影响。索绪尔将言语活动拆分为语言和言语,其中,语言是既定的系统,言语则包含着一种演变;语言是潜存于一个社会群体全部成员的脑海里,言语则是个人在具体情境下的偶然表达。与此类似,巴特区分了群体语言(langage)、整体语言(langue)和个体语言(parole)。而且,他后期还在朱莉叶·克莉斯特娃影响下,“从一种产品的符号学转变到一种生产的符号学”。[10](P.198)这构成了两者思想背景上的重要差异。
第二,巴塔耶的“痛苦”针对的是时间性,巴特的“愉悦”对应的则是体系性。如前文所述,巴塔耶通过“痛苦”对谋划及其所包含的时间性进行了深刻批判。巴特的“造反”对象不止是谋划的理性,而是体系性。他拆解句法结构,拒绝观念体系。句子是有等级的,包括了主句、从句等结构;而语句形式也呈现着意识形态活动,正如克莉斯特娃所说:“凡业已完成了的语句均要冒成为意识形态之物的风险。”[2](P.61)巴特自指说:“他时时将语言世界(言语域)想作偏执狂的无边且无限的冲突。唯一的存留者是体(systèmes)”,它作为意识形态本质内容的体系化表现缠扰、包围着我们,我们只有栖居于内;文则是散逸的,经由文,“体被拆去了边,散开来了”。[2](P.39)
第三,巴塔耶的“痛苦”指向连续性,巴特的“愉悦”则通往身体。巴塔耶通过“痛苦”勾勒了一条从自我出发而通达自我之外的路线,而在作为有限个体的自我消解之后,其去向就是回归连续性。这正如在“吾忘我”之后,达到“物我齐一”之境。在题为《不可能》(L’Impossible)的一段诗里,巴塔耶曾写到:“我是棺材的空/和不在的自我/在普遍的整体中。”[11](P.106)在这里,自我溶解于存在论意义上的普遍,传统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都被浸染于一种深深的连续性中”。[4](P.215)与此不同,巴特则通过“愉悦”完成了从意义追求到尼采式非道德论的转向,他总结说:“后来真理逐渐地显现出来,我也许可以说这是一个赤裸裸的真理,人们之所以写作,是因为说到底人们喜欢写作,此事带来愉悦。”[10](P.211)在文本给出的“愉悦”中,“我重新获得的不是我的‘主体性’,而是我的‘独特性’,这种已给使得我的身体与其他的身体区别开来,并适应自身的苦和悦:我重新获得的恰是我的醉的身体。”[2](P.75)巴特的“愉悦”,最终将“主体”瓦解为“身体”。
如果我们站在后来者的视角概括这些差异,或许可以说,巴塔耶在“痛苦”中完成的,是身为作者把“杀死”自己的过程呈现出来;而巴特之所以“愉悦”,则在于他已经完成了“作者之死”。
[1][日]铃村和成:《巴特:文本的愉悦》,戚印平、黄卫东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2][法]罗兰·巴特:《文之悦》,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3]Roland Barthes,Sade,Fourier,Loyola, trans. Richard Mill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
[4][日]汤浅博雄:《巴塔耶:消尽》,赵汉英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5]Georges Bataille,L’expérienceintérieure, Paris: Editions Gallimard,1954.
[6]Georges Bataille,Sovereignty, trans. Robert Hurley, New York: Zone Book,1993.
[7]Eugene Thacker,Afterlif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
[8]赵一凡:《从胡塞尔到德里达——西方文论讲稿》,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9]Michael Richardson,GeorgesBataill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5.
[10][法]路易-让·卡尔韦:《结构与符号:罗兰·巴特传》,车槿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11]Fred Botting and Scott Wilson, ed.,TheBatailleReader, Oxford and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1997.
(责任编辑:沈松华)
Barthes’ “Plaisir” and Bataille’s “Supplice”
YANG We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The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Barthes’ concept “plaisir” and Bataille’s concept “supplice”, though clearly in parallel and contrast with each other, have inner re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m. They both refer to the loss of self, the refusal of knowledge and the destruction of system, and thus have meanings in common.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that “plaisir” focuses on the post-structuralist generation of text while “supplice” aims to refuse rational thought and discourse with mystic experience.
Barthes; Bataille; plaisir; supplice; post-structuralism
2016-09-23
上海市“阳光计划”项目“后现代哲学的范式与路径”(15YG09)的研究成果。
杨威,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第二军医大学人文社科部副教授,主要从事法国哲学研究。
B151
A
1674-2338(2017)02-0074-05
10.3969/j.issn.1674-2338.2017.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