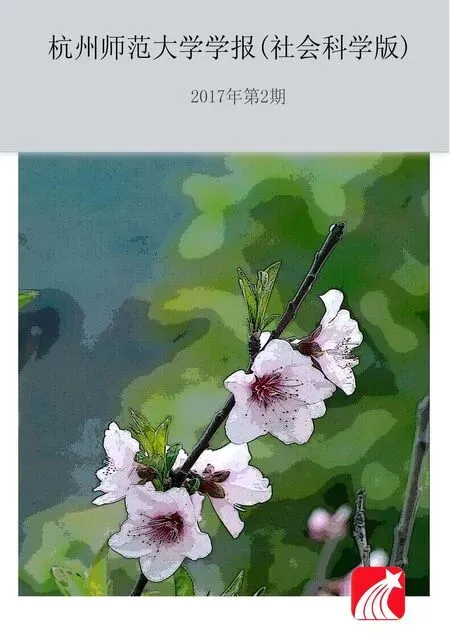从基础主义到“康德式”建构主义
——兼论事实与价值在契约式推理中的互契性和局限性
张祖辽, 王雷雨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从基础主义到“康德式”建构主义
——兼论事实与价值在契约式推理中的互契性和局限性
张祖辽, 王雷雨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公平性是契约论的内在诉求,对契约之公平性的证成存在事实和价值两条路径。前者试图用历史事实来说明证成起点的真实性,后者采取思想实验的手段论证证成起点的价值合理性。近代契约论同时诉诸事实和价值,但其基础主义色彩使这两种路径同时失效。当代契约论则以“康德式”建构主义立场将证成重心置于价值维度,引入动态化的思想实验来不断消解证成起点可能带有的独断性。不过,纯粹的价值性论证无法使“康德式”建构主义的契约推理逻辑走向彻底,而是不得不在逻辑推理的起点再次引入事实维度。
契约论;基础主义;建构主义;康德式;卢梭;罗尔斯
契约理论兴起的前提是个体意识的觉醒,而个体意识的觉醒则要求尊重每个个体的承认和选择。契约论正是试图通过每个个体都能公平参与的契约行为来对权力的合法性或原则的客观性提供辩护,据此,“基于个体权利建构起来的现代主权国家,具有强烈的契约论色彩”[1](PP.64-71)。从“承认”和“选择”的角度看,公平性应当是契约论的内在要求,不过,从契约论的逻辑结构看,契约式推理的逻辑起点是“自然状态(natural position)”或“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而这一起点必然预设人们的某种前见(presupposition)。这个前见要么被视为自然存在的历史“事实”,要么被解释为人为设定的政治“价值”。前见的存在与契约论要求的公平性构成难以化解的张力,契约理论中的“实然”与“假然”之争也与这一张力直接相关。实然的逻辑试图用“自然的”历史事实解释前见的真实性;假然的逻辑则力图用思想实验来论证某种政治价值是“对”的,是“应当如此设定”的。本文认为,基础主义意义的近代契约论由于推理的静态性而必然使事实和价值两个解释维度陷入困境,“康德式”建构主义意义的当代契约论立足价值维度纳入时间性,使契约式推理具有动态化的可能。但纯粹的价值维度无法使“康德式”建构主义的证成逻辑走向彻底,从而不得不再次援引事实维度。本文将从近代契约论入手对这两种进路进行剖析。
一、近代契约论:兼顾“事实”与“价值”
近代契约论的完整结构包括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和政府解体三个环节,其中,“自然状态”乃是其逻辑起点。通过从“自然状态”向“政治社会”的过渡,契约主义者希望论证一个核心问题,即“自然状态”下“自然”的历史“事实”决定了所有人都希望走出自然状态,订立契约,进入政治社会。因此,契约的缔结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公平的。通过所有个体的公平选择,政治权利、政治义务的合法性可以得到证成。据此解释,近代契约主义者希望从事实层面为契约论的公平性辩护。这一点在卢梭那里十分明显,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著作中用史学叙事方式来描述古代人类社会中的各种不平等事例,以表明自然状态在历史上确有其事。*亦可参见霍布斯和洛克的相关论述。比如,霍布斯认为:“我相信决不会整个世界普遍出现这种状况,但有许多地方的人现在却是这样生活的。因为美洲有许多地方的野蛮民族除开小家庭以外并无其他政府,而小家庭中的协调则又完全取决于自然欲望,他们今天还生活在我在上面所说的那种野蛮残忍的状态中。”参见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5页。洛克也有类似观点:“假如我们因为很少听见过人们处在自然状态,就不能推定他们曾经是处在这种状态中的,那我们也可以因为很少听见过萨尔曼那奈尔或塞克西斯的军队在成人和编入军队以前的情况,就推定他们根本没有经过儿童的阶段了。政府到处都是先于记载而存在的,而文字的使用,都是在一个民族经过长期持续的公民社会,享受了其他更必需的技艺为他们提供的安全、便利和丰富的生活之后,才开始的。”参见洛克《政府论》,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2页。
然而,尽管卢梭等人描绘的自然状态看似充满了“自然的”历史事实,理论家们也希望直接以自然状态的真实性来确保社会契约的真实性,但实际上自然状态却根本不足以被纯然解释为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而是在论证中必然掺杂人为设定的主观价值。这样一来,近代契约论的逻辑起点就带有主观性和独断性色彩。比如,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一方面分别构想出自己的“自然状态”,并或多或少试图让读者相信,历史上确实存在一个真实的“自然状态”;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很清楚,历史不能作为契约式证成的唯一依据,原因有二:首先,契约主义者们对“自然状态”的描绘并非严格的考古发现,从而与史学考证的科学结论可能不符;其次,即使他们对自然状态的描绘确实基于史学考证,仍然无法为契约的规范效力提供充分解释。因为近代契约论乃是试图基于人性这一普遍主义立场而对所有时代中的所有人推导出普适性结论,而现代人对待政治权力、政治义务的态度与古人并不相同,古人为走出自然状态而签订的契约不应当决定着现代人对待政治权力和政治义务的基本态度。[2](PP.39-50)因此,近代契约论虽不乏事实性诉求,但该理路的内在困境则使其不得不引入价值性的证成进路,这一进路的主要证成手段乃是“假定”性的思想实验。[3](P.18)
作为一种证成手段,思想实验在政治哲学中并不鲜见。与实证性色彩较强的政治科学不同,政治哲学乃是通过思辨性话语对制度、原则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进行论证与解释。政治哲学通常“在反驳一个一般性原则时,对该原则的捍卫者提出出乎意料的事例,追问其直觉反应,继而表明对方的直觉是与那种原则相冲突的”[4](P.68)。这些事例主要来自人们的想象,像缸中之脑、火车困境等思想实验甚至根本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但运用这些事例却能在论辩中给予对方以极大思想冲击力。
近代契约论即力图用历史上或许并不存在的“契约”来为政治权利和义务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当然,与上述思想实验相比,近代契约论所设计的思想实验与日常生活要贴近得多,实验程度也十分有限,不外乎是运用经验主义传统中的“思想加减法”来“减去”政府,分离出纯粹的人性,以此推导出政府缺位状态下的“自然状态”。在他们看来,尽管无法通过历史或考古手段科学地说明政府产生之前的各种“自然事实”,但从逻辑角度看,“减去”政府之后剩下的纯粹人性至少应当足以构成前政治社会的“逻辑事实”。因此,近代契约论之公平性的落脚点并非历史,而是逻辑,亦即用思想实验的假然手段搭建起基本证成框架。
然而,即便引入思想实验,近代契约论仍不足以对自身的公平性作出足够辩护。比如,运用“思想的减法”减去政府之后,自然的人性和自然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子,哲学家们莫衷一是。实际上,自然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们并不关心,毋宁说,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自然状态“应当”是什么样子,即“应当”从怎样的前见入手进行理论建构,并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反向论证该前见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他们在推理之前早已认定了所要去辩护的政治价值,推理的起点并非全然客观和中立。举霍布斯为例,“人性本恶”是其契约论预设的逻辑起点,对这一起点的辩护则在其理论建构过程中展开。比如,霍布斯举了诸如外出旅行需携带武器、独自居家需闩门锁箱等例子来试图使其读者相信,人性的确是恶的,没有主权者的自然状态必然陷入残酷的丛林法则。[2](P.11)不过,这些例子并非严格的逻辑论证,而是掺杂着不少劝诫性修辞。霍布斯很清楚,对那些与他有着相同或相似前见的人们来说,这些例子的确能产生不小说服力,但对于不具备、甚至是反对这些前见的人们而言,这一论证会十分苍白。因为从逻辑上看,霍布斯的辩护至多只能证明这个世界存在恶人,但证明不了人性本恶。霍布斯的契约论虽表面上承认每个个体都有选择和承认的权利,但实际上无法真正公正对待所有立约主体。洛克、卢梭等人预设的前见同样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赞同。因此,近代契约论至多只能局限在某种特定语境下,用思想实验的方式为某种政治价值提供较“强”、较公正的辩护,而无法得出普遍主义结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近代哲学家希望用契约论化解分歧,但引入契约论的后果却是使分歧更加不可调和。
因此,近代契约论同时诉诸事实和价值,但这两条进路都无法对推理起点(前见)提供足够反思。原因在于近代契约论的背后乃是基础主义的方法论立场。在其看来,不同“前见”可能引发的争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从这些前见出发推导出其所认同的政治价值。因为在基础主义看来,“一种证成是否成功,关键是能否在推理链条的最底端找到一个可以固定不变的‘基础’,这个‘基础’给整个推理链条提供根本动力和合法性”[5]。照此解释,基础主义意义的契约论是静态的,从固定不变的前提只能推导出固定不变的结论。这样一来,如果其设定的推理前提带有独断性,那么,这种独断性将以程序正义的推理立场传导到结论,并随着推理环节的逻辑进展不断得到加强。多元文化的当代语境下,这种推理模式显然难以得到普遍接受。从事实和价值的区别来看,事实维度一旦经过“真”或“假”的认定就不存在再行修正的可能性,但立场、观点等价值维度则能随着人们的反思不断作出调整。尽管近代建构式推理过强的基础主义色彩使其对价值的反思和调整同样变得不可能,但价值本身的可变性则为当代契约论指出一条新路,那就是在推理中纳入某种机制,使作为逻辑起点的“价值”在契约论中能够不断对自身进行反思和调整。
二、《正义论》:对“原初状态”的建构主义反思
从康德开始,思想实验成为契约论的主要进路,罗尔斯《正义论》于1971年的出版则意味着“康德式”建构主义在方法论层面取代基础主义。从基础主义的困境出发,“康德式”建构主义试图在当代多元主义语境下为契约式推理提供另一种思路,即以某种政治价值为推理基点,以动态的推理机制不断反思和调整该价值,使假然的契约式结论不断贴近人们实然的生活世界。但这种不间断的“贴近”机制在《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中有两种不同体现。本文先从《正义论》切入。
概言之,《正义论》试图用契约论为“两个正义原则”的客观性和确定性辩护。所谓客观性是指“两个正义原则”可以合乎情理地被人们广为接受,就此而言,客观性与公平性基本等同。确定性则就“两个正义原则”本身而言。罗尔斯并非意在建构一套全新的正义原则,相反,“两个正义原则”的大部分内容历史上早已存在,罗尔斯不过是从多种正义观中先行认定这一正义观,并采取新的方法再次为其辩护。[6](P.94)
据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正义论》:若用契约论来为“两个正义原则”辩护,必须公平对待每个选择者,也就是公平对待每个人在各自的生活实践中形成并坚信的正义观。不过,与“自然状态”不同,“原初状态”不再以任何“历史事实”为依据,而是依据特定政治价值拟定的理论“假定”。在《正义论》中,原初状态(无知之幕)是直接根据“两个正义原则”拟定的,而“两个正义原则”本身即是众多正义观中的一种。因此,无知之幕本身就是一种排他性的政治价值。既然如此,罗尔斯必须回答这一价值何以能够取得持不同正义观的其他人的认同。罗尔斯的解决思路即是通过由“原初状态—反思平衡”构成的动态思想实验逐步验证“两个正义原则”的合理性。
表面来看,原初状态集中体现着罗尔斯的契约论,因为原初状态中“各方”的做法非常类似自然状态下契约的缔结。自然状态给出缔结契约的公平条件,原初状态似乎也有类似功能。原初状态体现着一种公平选择理念,无知之幕对所有特殊信息的遮蔽意味着在选择问题上,“各方”都只能依据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诉求在“最大最小值”的机制下选择出可以被同时接受的正义原则。*罗尔斯政治哲学区分了三种主体:原初状态中的各方、良序社会中的公民以及考察这“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我们。本文涉及第一和第三种主体。前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假定,后者则是日常实践中真实的“我和你”。参见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62页。这一点,看似不成任何问题。但如果仅仅用原初状态来理解契约的话,我们会面临如下困惑:“契约”一词似乎必须包含各方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的博弈。也就是说,只有在利益多元,不同主体愿意且能够相互商谈和博弈的情况下契约才有意义,而无知之幕却掩盖了所有诉求和分歧,把原本可以就这些分歧商谈和博弈的利益主体化约为绝对同一的人格,“最大最小值”原则的实质则是把单个“自我”放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序列中进行同一性的利益认定,这就根本谈不上、也用不着人际间的商谈和博弈。有论者就此指出:“原初状态毋宁说是不正当地使用了协约或契约的思想……通过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似乎抹去了任何协约或契约的真正背景,通过消除了异议的可能性,协约这一概念完全失去了意义。”[7](P.88)此外,原初状态并不专指无知之幕,除了无知之幕,还可以根据其他正义观(政治价值)拟定出多种形态。比如,根据功利主义原则就可以拟定一种“不偏不倚的观察者”[6](P.93)。出于对公平性的考虑,罗尔斯必须对将作为前见的“两个正义原则”设为起点的合理性给出足够的解释,但原初状态本身显然远远不够。
据此理由,本文认为,原初状态虽是一种以价值为本位的思想实验,但无法对契约论及其公平性作出足够解释。不过,《正义论》中的思想实验并未止步于此,较之原初状态,反思平衡的实验程度更深。奥尼尔指出:“(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再次更为深入地使用了协约的概念,这种对协约概念的深层使用体现在反思的平衡中。”[7](P.89)照此解释,《正义论》的契约特质不在于原初状态,而在于反思平衡,不过,反思平衡如何体现出《正义论》的契约主义意蕴,奥尼尔语焉不详。下面,本文将就此对《正义论》进行重构性诠释。
反思平衡与原初状态在《正义论》的证成语境下是一个统一体。原初状态虽谈不上塑造立约环境,但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就是以“道德几何学”的方式将某种正义观给假然的“各方”清晰呈现出来。[6](P.93)反思平衡则意在将这个已得到清晰呈现的正义观再次拉回“我们”实然的生活世界中,让持有不同正义观的“我们”再次进行比对和权衡,不断在逻辑和生活两个层面“叩其两端”,使逻辑和生活归于统一和平衡。
除此之外,反思平衡还有更深层的证成依据,即解决原初状态无法解决的公平性问题。从反思平衡的立场来看,任何原初状态都不足以不加批判地作为证成起点,其结论自然也不足以作为证成终点。相反,原初状态不过是使某种正义观变得更加清晰的第一步,其实质是用实验的方式“暂且”认定某种正义观的合理性,反思平衡则通过实验来对这种暂定的合理性进行进一步验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原初状态和自然状态的又一个区别:在近代,某种“前见”是否合理,理由全部由“自然状态”提供,但“原初状态”充其量只能提供一半理由,另一半则需要“反思平衡”提供。因此,原初状态不能等同于自然状态,应该说,自然状态应基本等同于原初状态和反思平衡的总和。
如此,问题就很清楚了,《正义论》的确只谈到无知之幕这一种原初状态,但并不表明罗尔斯从一开始就认为原初状态的其他形式必然是错的,更不表明它们不应当进入《正义论》的证成视野。而是说,“两个正义原则”不过是在检验顺序上“偶然地”成为思想实验的首个出场者。在这场思想实验中,生活、实践中的“我们”正是在反思平衡过程中对“两个正义原则”的合理性进行最终的反思、权衡和博弈。其结果,要么是认同并接受无知之幕及其与之对应的“两个正义原则”,要么是对无知之幕或“两个正义原则”进行细节性修订,要么则是对二者进行彻底否定,根据其他正义观另行拟定相应的原初状态继续思想实验,直到某种原初状态在反思平衡的实验中最终可以被“我们”所接受。因此,如果反思平衡在《正义论》中足够彻底,“我们”便可以将任何正义观都纳入其视野,在动态的证成过程中逐步消解前见所可能带有的主观性和独断性,向客观性不断贴近。
三、《政治自由主义》:对“人的观念”的实验性再反思
从证成角度看,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不再将某种具体的正义观设定为证成起点,而是将一种特定的“人的观念”作为证成起点,并直接根据“人的观念”来拟定原初状态。这一设定使问题更加复杂。因为“正义观”及其对应的“原初状态”乃是一种价值性、立场性设定。尽管《正义论》未能成功地将其纳入反思平衡的反思和修正机制,但至少《正义论》逻辑上承认这一点。而“人的观念”面临的独断论质疑远甚于“无知之幕”,因为《政治自由主义》除了谈到其所认同的“人的观念”,通篇都没有再行论述“人的观念”的其他可能性,从而使其设定更具形而上学的独断意义。*罗尔斯将“人的观念”设定为:“在必要程度上拥有两种道德人格能力,即正义感的能力和善观念的能力。”参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1页。不过,即便在民主国家内部,这一设定也不乏质疑,比如,W. Galston就曾谈到,“罗尔斯的人的观念与自由和平等的美国式理解有所偏离,并导向一种与那些最为美国人所信奉的正义原则极为不同的正义原则。”参见W. Galston, Moral Personality and Liberral Theory: John Rawls’ Dewey Lectures,Political Theory, vol.17,1982,pp.515-516。对此,《政治自由主义》的做法首先是基于其特殊主义立场引入一种更精致的思想实验。
“人的观念”并非最早出场于《政治自由主义》,而是在《正义论》中就已作为一个潜在的证成要素逐步浮出水面。《正义论》中的反思平衡之所以不彻底,是因为罗尔斯为契约的缔结设定了“基本善”和“亚里士多德原则”这两个前提,而这两个前提并不在“我们”的权衡和博弈范围内。*“无知之幕”对“各方”的遮蔽使其失去选择动机。基本善和亚里士多德原则即重新为“各方”设定选择动机。前者是一种普遍性的利益动机,后者则是一种普遍性的心理动机。参见罗尔斯《正义论》,第311-314、335-342页。因此,本文对《正义论》之契约主义意蕴的“思想实验”式解读充其量只是一种尝试性重构。这一点,从罗尔斯对“无知之幕”的许多描述性定语中就可见一斑。*比如,罗尔斯经常用“弱”的、“恰当”的、“被广泛接受的”等定语来描述无知之幕。因此,《正义论》的证成重心实际上没有落在反思平衡,而是落在原初状态。参见罗尔斯《正义论》,第11、15页。而罗尔斯对原初状态之所以如此自信,则是由于他预设了一种“康德式”人的观念。“康德设想的这种道德立法将在人们是作为自由而平等的理性存在物的条件下被一致同意。对原初状态的描述就是解释这个观念的一个尝试。”[6](P.198)
可见,对于“人的观念”,《正义论》的态度是不得不承认,因为这与其道德建构主义追求的公平性相矛盾,而这一矛盾也的确使道德建构主义走向终结。但从1980年的杜威讲座开始,“人的观念”即被明确作为证成起点。证成起点的这一转换有其内在原因,《政治自由主义》设定的语境不再是“一般多元论”,而是“合乎情理的多元论(reasonable pluralism)”,在这一语境下,包括“两个正义原则”在内的所有正义观,连同与其对应的原初状态在各自语境下都具备合情理性。因此,站在不偏不倚的建构主义立场,任何正义观都不能再在实验中作为逻辑起点,否则,它们将从一开始就具备理所当然的合情理性,从而无法对不同正义原则在公共政治领域的恰当性作出衡量。《政治自由主义》则希望为“两个正义原则”在公共政治领域中的中立性和客观性辩护。因此,《政治自由主义》必须首先把“民主社会之公共政治文化”中最基本的理念讲清楚,在此基础上论证“两个正义原则”在公共政治领域中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如此,问题就转变为:《政治自由主义》所论述的“人的观念”究竟能否如罗尔斯所相信的那样客观而真实地反映出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罗尔斯对此必须作出解释,这一解释的本质仍是一种思想实验。该思想实验的本质乃是持有不同“人的观念”的“我们”运用反思平衡对不同的“人的观念”进行有次序的契约式权衡和博弈。在这一实验式解读中,反思平衡能更彻底地使证成成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暂定化“过程”,而这一“过程”则是针对如下矛盾:罗尔斯认为,“人的观念”是民主社会之公共政治文化中的核心观念,但罗尔斯对公共政治文化的态度存在矛盾。一方面,罗尔斯认为它是由宗教宽容等“已定的信念”汇集而来的[8](P.7),但另一方面,罗尔斯谈到,“这些确信都是些临时固定的观点……是人们隐隐约约意识到的基本理念和原则的共同积累”[8](PP.54-55)。如此一来,我们必须追问:若是这些观念不过是被人们“隐隐约约意识到”,并需要进一步解释的话,罗尔斯凭什么以建构主义的名义将其设定为逻辑起点?
我们通过与《正义论》的对比来呈现该实验对“人的观念”之独断性的化解机制。
如上所述,《正义论》中反思平衡的两端分别是“两个正义原则”和“我们”所持的各种正义观,原初状态在其中扮演中介性角色,随着反思平衡的不断深入,这个中介的内容和形式至少具备进一步确证、被部分修正和被彻底更易的三种可能性。但《政治自由主义》语境下反思平衡的两端则是“我们”和各种“人的观念”,原初状态的内容和结构则直接依据“人的观念”得到拟定,与各种正义观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此时的“中介”乃是“人的观念”和原初状态共同构成的统一体。原初状态虽仍是思想实验的第一步,但这一步骤的目的已不再是将某种正义观明晰化,而是将某种“人的观念”明晰化,因为“人的观念”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才是真正的价值前见。如此来看,答案很清楚:《政治自由主义》设定的“人的观念”并非不可商讨,而是完全可以在反思平衡中被持有不同“人的观念”的“我们”所反思、权衡和博弈。博弈结果同样至少有三种可能:第一,“人的观念”的确能够体现出现代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无知之幕也的确是准确的设定;第二,“人的观念”只能部分体现出现代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因此需要对“人的观念”及其结论作出相应调整;第三,“人的观念”完全无法体现现代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观念,其结论也与现代民主社会背道而驰。需要总结、抽象出新的“人的观念”,开始新的思想实验。因此,《政治自由主义》对“人的观念”所作的界定不过是在时间意义上首先进入实验程序,若是“我们”通过反思平衡最终无法认同这种人的观念的话,就需要用其他“人的观念”继续实验。
不过,上述实验式契约推理对“康德式”建构主义而言仍不充分。因为反思平衡对“人的观念”的反思和调整较之《正义论》尽管更为彻底,但对这一政治价值的反思应当围绕明确的基点。因为不论从直觉还是逻辑来看,对“人”都应当有一种普遍性的界定,否则,不但不同语境间的商谈、理解会变得不可能,也不符合现代政治哲学对普遍性的一贯追求。对此,罗尔斯的做法是从“人的观念”中抽象出一种最普遍、最一般的“人的概念”,以“概念”为基点对“观念”进行解释。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围绕“人的概念”这一基点分别对各种“人的观念”进行“加厚”。而“加厚”的具体要求取决于“我们”在不同语境下进行契约式商谈和博弈。*观念(conception)和概念(concept)的区分对罗尔斯政治哲学十分重要。“概念是一个术语的意义,而一特殊观念还包括运用它的原则……人们可以在概念的意义上取得一致,但是相互之间仍然存有矛盾。”简言之,概念是普遍的,但观念各有各的特殊性。参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第99-100页。
至此,“康德式”建构主义的契约式推理已走到逻辑尽头。因为“人的观念”即便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存在被调整和修正的可能性,从而是为一种多元性的价值立场。但“人的概念”则是对“人”最普遍的一元化设定,这一设定必然游离于反思平衡之外。因此,“人的概念”只能被“拟定(lay out)”,无法被建构。[8](PP.98-101)如果我们仍沿用“康德式”建构主义的逻辑和立场来对这个被拟定的“人的概念”不断追问的话,其结果只能导致逻辑上的无限后退。罗尔斯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也陷入“人的概念”与“实践理性原则”互释的循环论证。[9](PP.3-16,37)本文认为,“人的概念”的确意味着“康德式”建构主义的契约推理已走到尽头,因为“人的概念”如何设定,已不再关乎逻辑推理,而是应当再次引入历史,通过对历史的体察、认知和挖掘来使这一“概念”不断贴近历史的本意。这样一来,“人的概念”不再像“人的观念”那样属于价值的范畴,而是属于事实的范畴。“康德式”建构主义也无法成为一种纯粹关乎政治价值的契约式推理,而是必须在其逻辑链条的起点纳入历史主义,对该起点进行历史性反思。
四、结论
近代契约论的退场在于多元文化语境下事实性和价值性解释的双重失效。当代契约论则试图运用纯粹的思想实验对推理起点进行动态的反思,其成熟形态即是将对人的理解作为契约式推理起点,通过反思平衡来使对人的理解更加客观。然而,尽管契约论的“康德式”建构主义形态较之基础主义形态在多元主义语境下更具解释力,但该形态离不开对“人”进行基本的认知和理解,而这一认知和理解不能局限于纯粹的价值设定和逻辑推理,而是必须通过对历史的发掘重新引入事实判断。
[1]孙向晨:《民族国家、文明国家与天下意识》,《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
[2]宋宽锋:《论证与解释——政治哲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4]曹钦:《反思平衡与思想实验》,《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5]张祖辽:《从困境到重构:论罗尔斯政治哲学中反思平衡的两种形态》,《人文杂志》,2015年第9期。
[6][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7]包利民:《当代社会契约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8][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1年。
[9]韩水法:《政治构成主义的悬空状态》,《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责任编辑:沈松华)
From Foundationalism to Kantian Constructivism: the Coherence and Limitation of Fact and Value in the Reasoning of Social Contract Theory
ZHANG Zu-liao, WANG Lei-yu
(School of Marxism,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There are two routes, namely fact and value, of justification to the fairness of social contract theory. The route of fact attempts to prove that the starting point of justification is true by historical facts while the value route aims to justify that some certain values are reasonable by thought experiments. Modern social contract theory appeals to the route of fact and value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its background of foundationalism leads them both to failur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social contract selected the value route as the right one in the position of Kantian constructivism and brought a kind of dynamic experiment to dispel the arbitrariness of logical starting point. However, Kantian constructivism still has to bring the route of fact to the justification, or it can’t be a thorough political methodology.
Social contract theory; foundationalism; constructivism; Kantian; Rousseau; Rawls
2016-10-0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政治哲学中的‘康德式’建构主义理论研究”(16YJC720029)的研究成果。
张祖辽,哲学博士,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王雷雨,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B712.59;D095.654.1
A
1674-2338(2017)02-0068-06
10.3969/j.issn.1674-2338.2017.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