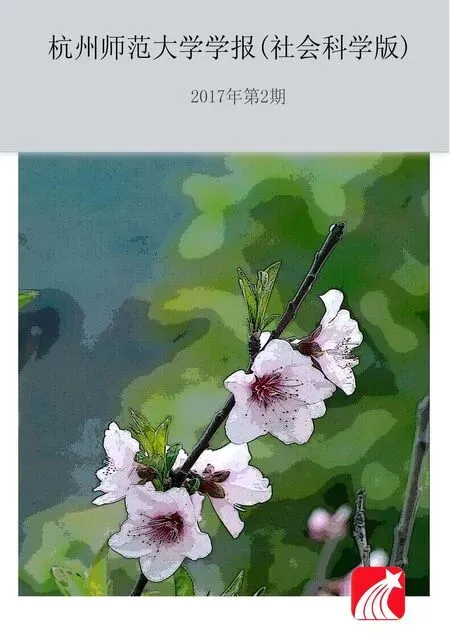中国新文学第一部“完全忏悔”之作
——再论《古船》
王达敏
(安徽大学 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中国新文学第一部“完全忏悔”之作
——再论《古船》
王达敏
(安徽大学 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古船》是一部反思之作,以家族之间的恩怨沉浮及附于其上的阶级斗争反映时代的演变,古老的洼狸镇四十余年的历史是中国当代的缩影。但《古船》更是一部忏悔之作,而且是中国新文学第一部“完全忏悔”之作。所谓“完全忏悔”,是指忏悔者走完了忏悔全程:由知罪、归罪到负罪、赎罪再到人性新生、灵魂复活。身负家族原罪和阶级原罪的民间贵族之子抱朴主动忏悔赎罪,并将“人之罪”转化为“我之罪”,最终告别了“旧我”而跃入“新我”之境。而文学评论中经常提及的忏悔者见素和四爷爷,严格地说,他们不是真正的忏悔形象。前者知罪认罪里隐含着“复仇而不得”的无奈之感,后者的忏悔是根据民间伦理准则而有选择性的领罪。
《古船》;张炜;忏悔;家族原罪;阶级原罪
被芦青河淤泥掩埋千年的“古船”重见天日,但它早已折断风帆,船体残破朽碎,成为时间终了的意象。而于1986年扬帆起航的《古船》已经驶入宽广永恒的正典之域,尽管它不甚完美,但它是原创性、经典性的。张炜亦坦言:《古船》有缺陷,毛病很多,它“必然地保留了那个年纪的艺术和思想的残缺,但却被更为重要的东西所弥补和援助了”[1](P.397)。这“更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张炜没有直说,可意思还是能够把握的,那就是纯粹、勇气和青春的创造力。而在我看来,这“更重要的东西”则是原创性和经典性。《古船》自出版以来,不同年代对它的评价,最终都落到原创性、史诗性和经典性上。80年代,雷达著文评价《古船》是“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的碑石”[2](P.232);罗强烈认为《古船》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少数几部具备了史诗品格的长篇小说之一”[3](P.13)。90年代,王彬彬的评价较罗强烈又进了一步,指出“《古船》不但是近数十年中国长篇小说中最优秀的几部之一,而且也是七十多年新文学史上的长篇佳作”[4](P.57)。郜元宝从经典性的思想深度方面立论,认为“《古船》不仅浓缩了80年代中国文学的批判力量,代表了80年代反思的深度,也为90年代的小说设立了一个并不容易超越的水准”[5](P.68)。新世纪,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说《古船》“无论在内容、风格还是历史视角方面,都称得上突破之作。张炜创造了中国小说的一座里程碑、一部对一切人类进行言说的作品”[6]。刘再复直言《古船》是“一本难得的杰作”[7](P.69)。
《古船》这种原创性、史诗性和经典性品质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三种创造。一是它与莫言的“红高粱系列”、乔良的《灵旗》等小说一道,成为新历史小说的滥觞。而在史诗水平上表现新历史小说所体现的新的历史观,即用民间历史观或客观历史观突破正统历史观,对民国以来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当代历史如土改、大跃进、共产风、文化大革命进行颠覆性的重新审视,《古船》应该是最具深度和力度的第一部。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它深广的影响,看到它对甚至包括《故乡天下黄花》《旧址》《白鹿原》《羊的门》《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在内的优秀作品的沾溉。二是它以家族之间的恩怨沉浮及附于其上的阶级斗争反映时代的演变,古老的洼狸镇四十余年的历史是中国当代的缩影。三是它具有悲悯性质的古典主义气质,即具有史诗的深厚、崇高和正典的纯粹持久。
其实,《古船》更是一部忏悔之作。从根本上说,《古船》的原创性、史诗性和经典性是由忏悔意识来支撑的。《古船》的忏悔意识和忏悔形象的价值,只有到新世纪才逐渐显现出来。我的判断是:《古船》是一部纯正的忏悔之作,而且是中国新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第一部“完全忏悔”之作。
一
“完全忏悔”概念源自基督教。基督教神学关于“完全忏悔”与“不完全忏悔”的区分,始于中世纪,特别是12世纪以降的天主教神学,从忏悔行动、忏悔对象、忏悔情状和忏悔后果等方面,对这两种忏悔作了比较。其区别之要点:“完全忏悔”指基于上帝之爱并回应上帝之爱的幡然悔悟,充满了感恩和自由之释然,其忏悔最终实现的是人的“新生”和重获自由。“不完全忏悔”则是因为道德上的恶行,畏惧上帝的惩罚之正义而引起的悔罪,伴随着由恐惧和悔恨而产生的不安,其忏悔之后果是恶行本身的效应非但没有消除,还严重阻碍了“完全忏悔”的发生。[8](P.87)
借用基督教“完全忏悔”的概念来表述《古船》主角隋抱朴忏悔的性质,其语义必然有所变化。在基督教神学里,它是忏悔类型在内涵方面的表述,而在本文里,它则是忏悔过程是否完整完善的表述。我所定义的“完全忏悔”是指人物走完了忏悔的全程,其过程由三个相互联系又相互递进的环节构成:良心发现、人性觉醒(知罪、归罪)→人性剖析、灵魂搏斗(负罪、赎罪)→人性升华、精神超越(人性新生、灵魂复活)。隋抱朴从对家族罪恶(原罪)的忏悔到对阶级罪恶(原罪)的忏悔,再到对人类罪恶的忏悔,即由知罪、认罪到负罪、赎罪再到精神超越,是“完全忏悔”的完整表述。
隋抱朴是中国民间贵族之子,又是乡镇磨坊里的思想者。他身负双重原罪,一个是家族原罪,一个是阶级原罪。他的家族原罪意识源自他父亲隋迎之。洼狸镇老隋家是民族资本家,起初只有一个小小的粉丝作坊,到隋恒德这一代,老隋家的粉丝工业达到极盛。他们在河两岸拥有最大的粉丝厂,并在南方和东北的几个大城市开了粉庄和钱庄,其影响甚至远及海外,辉煌了好几辈子。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老隋家传到隋迎之这一代。土改前夕,亲家欠债赖债被人打死,隋迎之惊吓至极,顿时产生了一种负罪感,觉得老隋家的财富是剥削穷人之所得。接下去的日子里,隋迎之日夜计算着隋家从祖辈开始欠下的债。抱朴问父亲欠谁的债,父亲说:“我们欠大家的。”全镇最富有的人家居然欠下别人的债,抱朴怎么也不信。他问到底欠谁的?欠多少?父亲回答:“里里外外,所有的穷人!我们从老辈儿就开始拖欠……”一个星期之后,隋迎之骑马外出还账,“从今天起,只有一个小粉丝作坊算是他们老隋家的,其余粉丝工厂,全交出去了!”土改时,他因交出了粉丝厂而落得开明绅士的身份,躲过了公开的批斗。而那些土地多、开工厂的人,均被批斗、镇压。然而,尽管他躲过了批斗却没有躲过土改激进分子赵多多的恐吓,临终前,他对抱朴说:“老隋家的欠账还没有还完,事情得及早做,没工夫了。”隋家的原罪就这样经由父亲隋迎之传给了儿子隋抱朴。犹如灵魂附体,这种原罪意识把抱朴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忏悔者。他的原罪意识和忏悔意识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对老隋家、对自己的谴责达到了绝对不能容忍的地步。他总认为老隋家罪恶深重,他要替家族赎罪,而且把所有的罪恶都记在自己的身上,“我是老隋家的人哪!”“我是老隋家有罪的一个人!”抱朴对家族罪恶的自觉担当,显示了自我忏悔的道德自觉和自我审判的人性力量。
这种源自中国民间的“忏悔贵族”,尽管根植于中国现实土壤,但在精神气质上则与俄罗斯文学的“忏悔贵族”遥相呼应,一脉相承。我相信,最喜欢托尔斯泰且每年必读《复活》一两次的张炜,是从托尔斯泰及其《复活》等小说中汲取了精神资源,然后才创作出《古船》及隋抱朴形象的,二者之间有着互文关系。比如托尔斯泰,出身显贵,又当过军官,年轻时代过着放荡的贵族生活,但作为作家,他一生都在与各种罪恶作坚决的斗争。他目睹农民被贵族地主盘剥而处境悲惨,于是深感自己作为贵族地主阶级的“罪恶”,他不能原谅自己,经过长久的反省和忏悔,他终于抛弃贵族立场,完全站到农民立场。他放弃财产,自己参加劳动,自食其力。他与他所处的贵族阶级彻底决裂,惊世骇俗,连深爱他的夫人也无法理解。各种势力聚集阴谋,对托尔斯泰进行迫害,威逼他承认错误,收回对教会的攻击。托尔斯泰始终不屈服,82岁那年离家出走,病死在阿斯达波沃车站。
文学创作是托尔斯泰忏悔的真情告白,他不仅写作了代表“19世纪全世界的良心”的自传《忏悔录》,而且还把“忏悔意识”灌注到《一个地主的早晨》《复活》等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中,创造了一个个“忏悔贵族”形象,《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忏悔形象。
《古船》仿佛是《复活》的中国版。有作者指出张炜的文学创作与托尔斯泰有多方面的意义联系,比如贵族忏悔。托尔斯泰笔下的贵族对自己的身世家族有一种负罪感,并因负罪而至赎罪,因而都具有忏悔意识。张炜笔下的贵族忏悔,其原因也同托尔斯泰一样,认为自己家族世代脱离劳动,靠剥削他人积累财富,不劳而获,由此而指出家族之所以衰败是获罪遭罪的结果。死去的已经死去了,那么活着的人就要承担起赎罪的责任。因此,张炜笔下的人物除具有贵族意识外,还具有忏悔意识。[9](P.94)应该说,这种比较还是纸面文章。关键是两个国度的“忏悔贵族”在精神气质上有着相似性,他们同属于世界文学“忏悔家族”成员,又同为“忏悔贵族”一脉,也就是说,张炜的中国民间忏悔贵族与托尔斯泰笔下世代承袭的忏悔贵族的相似,主要是精神气质方面的。尽管如此,两个国度的两个民族的“忏悔贵族”毕竟产生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并受不同的现实力量的规约,因此,他们的忏悔前因与忏悔路径有所差异。中国民间资本家隋迎之、隋抱朴父子之忏悔,首先是被残酷现实惊恐,进而醒悟而产生负罪感的,而聂赫留朵夫等俄罗斯贵族之忏悔,则是由宗教忏悔伦理注入其中而产生罪感意识的,并自始至终在灵魂之域展开,因而更具崇高性和震撼力。
再说阶级原罪。我们曾根据战争和革命的需要,把人分成“属己”与“异己”两个敌对阶级。这种二元对立的区分泾渭分明,敌与我、善与恶、好与坏一目了然。战争年代的地主、富农和封建贵族、资本家统统被划为敌对阶级,阶级的区分成为20世纪中国最大的政治事件。这种阶级的划分并未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在接下来的从土改开始的“革命年代”,阶级成分观念在中国牢牢地扎下根,“阶级”成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流语汇,而“阶级”又总是与“革命”联手,“阶级”是“革命”的重要内容,“革命”是“阶级”的表现形式。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改到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几乎都是针对地富阶级、反革命右派和资产阶级的。根据战争模式划分阶级阵营,好处是简单易辨识,弊处是盲目粗暴,贻害无穷。于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被划定为何种阶级,是人间与地狱的区别。抱朴生于富贵之家,先天命定了他要承受阶级原罪,而不问他是否愿意。尽管老隋家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衰退,并于40年代逐渐被老赵家取代;尽管隋迎之真心诚意地忏悔赎罪,把产业全部交了出去,由此获得了开明绅士的身份;尽管隋抱朴甘愿负罪,认领痛苦,放弃家族复仇,但革命内部对隋家阶级属性的定性却是难以改变的,这就决定了作为贵族之子的抱朴不仅要认领家族原罪,还要被迫承受阶级原罪。
家族原罪被阶级原罪的巨大破坏力所绑架,老隋家就在劫难逃了。视老隋家为仇敌的赵多多,借助革命之力、阶级之势,迅速地由一个流氓无产者摇身一变而成为新生革命政权的一员战将,他发誓:要把老隋家的人统统干掉!土改时期,他违反党的政策,丧心病狂地迫害老隋家,先是吓死隋迎之,继而三番五次地领人抄家,接着又害死茴子。“文化大革命”开始,隋家兄妹三人成为造反派迫害的对象,屡受侮辱毒打。
家族原罪和阶级原罪原本一体两面,源出一途,却意义有别。对于抱朴,家族原罪是他甘愿认领的负罪,与善和良知有关,与人性的质量有关;而阶级原罪却是强加于他的负罪,与恶和暴力有关,与血统论有关。怎样承受这两种性质的原罪,对抱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二
紧随罪感意识而产生的是赎罪意识。知罪要负罪,而负罪的目的是赎罪,只有进入到忏悔第二环节的赎罪,真正有价值的忏悔才算开始。
身负双重原罪的抱朴,首先要面对的是家族原罪。按常理,父亲还了一个星期的账,又交出了全部粉丝工厂,作为隋家后代的抱朴实际上已经无罪可赎了,也就是说,他不应该再承担还债、赎罪之责了。但罪感意识早已渗透到抱朴的灵魂深处,他觉得怎么也还不清祖辈留下的欠债。这笔债既实际又模糊,经常纠缠着他的,是父亲一开始就盘算的那一笔数不清的账:“夜晚显得漫长而乏味了。睡不着,就算那笔账。他有时想着父亲——也许两辈人算的是一笔账,父亲没有算完,儿子再接上。”这种负罪感让他异常痛苦:“他继续算那笔账。密密的数码日夜咬着他,像水蛭一样吸附在他的皮肤上。他从屋里走到屋外,走到粉丝房或‘洼狸大商店’中,它们都悬挂在他的身上,令人发痒地吮着。”但明眼人很快发现,抱朴在既无罪可赎又无人向他追罪的情况下继续为家族赎罪,实际上是把“无罪知罪”化为生命力量,在赎罪中磨砺精神,以求道德的完善和良心的安宁。
当家族原罪在土改革命中被强行纳入阶级原罪之域后,抱朴无可反抗,但要他束手领罪,又非他所愿。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像耶稣那样,甘愿背负沉重的十字架为人类犯下的罪恶赎罪。抱朴用同情、宽容的态度看待世界,将“人之罪”转化为“我之罪”,在行动上,就是放弃复仇,阻止“阶级”的相互残害。而要将其实施起来,最好的对策莫过于托尔斯泰式的“勿报复”、“勿以恶抗恶”的“不低抗主义”。刘再复、林岗称“抱朴是一个不自觉的托尔斯泰论者,但却是一个更加伦理化的中国托尔斯泰论者”。[7](P.71)
说得没错。目睹了家道的毁灭,继母茴子被凌辱自尽,以及兄妹三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侮辱、迫害的经历,按理说,抱朴应该产生仇恨并生复仇之心。如果说,在阶级原罪紧紧捆绑着他们的年代,他们即便有复仇之心,也无复仇之胆,那么,到了阶级原罪日益松驰的改革开放年代,他们要实施复仇行动就水到渠成了,何况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具备了复仇的能力,更何况他们的复仇直接面对的不是整个“阶级”,而是有选择地针对直接迫害他们的人,具体地说,他们要复仇的第一个人无疑是土改中的流氓无产者、“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赵多多,其次是洼狸镇的太上皇赵炳(四爷爷)。但他自始至终没生丝毫复仇之心,而且极力阻止弟弟见素去复仇,兄弟二人由此产生矛盾。
洼狸镇近四十年的阶级斗争,说穿了,就是老隋家与老赵家的家族之斗,而决定两家命运的主要因素,是阶级力量而非家族力量。但家族力量往往附势而上成为帮凶,有时直接代阶级行使权力,其破坏力既隐蔽又凶残,表现在赵多多身上,那就是丧心病狂地迫害老隋家。现在好了,时代变了,一心想着向老赵家复仇的见素终于盼来了机会。洼狸镇改革初年,赵多多承包了粉丝厂,见素不能容忍粉丝厂姓赵。他对抱朴说:“我要夺回赵多多的粉丝大厂。粉丝大厂姓隋。它该是你的、我的。”抱朴摇摇头,告诫见素:“它谁的也不是。它是洼狸镇的。”言下之意,粉丝厂既不是你的我的,也不是赵多多的,它是全洼狸镇人的。他怕见素没有明白他说的话,于是忍痛地说起父亲的不幸,以开导毫无负罪感的弟弟。他说父亲开始也以为粉丝厂是老隋家的,结果这个误会害得他后来吐血,两次骑马外出还债,最后死在一片红高粱地里。见素显然听不进抱朴的话,他执意要报复。
这里的路被堵住了,但并不妨碍见素改变思路,采取另一种报复方式:寻找机会下手制造“倒缸”。“倒缸”是粉丝作业中的重大事故,重者会导致企业崩溃。此事他没有做成,但暗暗喜欢他的大喜姑娘见他有此意,制造了“倒缸”。他希望抱朴不要来“扶缸”,让赵多多损失越大他越解恨。抱朴遵从当地民间伦理的准则,不仅来“扶缸”了,而且还严厉地指责见素的不仁不义:“粉丝厂‘倒缸’没人扶,就是全镇的耻辱!‘扶缸如救火’,自古洼狸镇就有这句话。”粉丝厂每次“倒缸”,无一例外均由抱朴全力以赴解决。这种行为既是道德的善举,更是抱朴以此替家族、替自己,进而替制造罪恶的人赎罪之举。见素辩解,言其事不是自己干的,但他起意了。抱朴相信此事非见素所为,由于他起意了,起意就有罪。“不过我心里早就把这笔账记在老隋家身上了。我老想这是老隋家人犯下的一个罪过,太对不起洼狸镇……”
抱朴之所以极力阻止见素复仇,是因为他目睹了太多的复仇制造的苦难和流血祸及众生。《古船》里,不论是还乡团令人发指的杀人,还是穷人肆意报复的杀人;不论是因为阶级对立的杀人,还是出于家族世仇的杀人,其要害都是复仇,且复仇的方式、残忍的手段如出一辙。因此,他有充分的理由去说服见素忘掉仇恨,放弃报复。他对见素说:“镇上人就是这么撕来撕去,血流成河。你让我告诉你过去的事,我还是不能。我没有那样的胆量,我说过我害怕你。你有胆量,我不想和你一模一样的胆量。如果别人来撕我,我用拳头挡开他也就够了。如果坏人向好人伸出爪子,我能用拳头保护好人也就够了。……我最怕的就是撕咬别人的人。因为他们是兽不是人,就是他们使整个洼狸镇血流成河。我害怕回想那样的日子,我害怕苦难!”害怕苦难必然怨恨制造苦难的人,可抱朴的怨恨并非指向某个具体的人,比如赵多多、赵炳,他说:“我不是恨着哪一个人,我是恨整个的苦难、残忍。”我们可以将抱朴这句话理解为他对“人之恶”的恐惧与否定。正是对“人之恶”的防范与恐惧,抱朴患上了“怯病”,其症状是胆小怕事、犹豫不决、瞻前顾后、吞吞吐吐、怕与人处、自我折磨,像鸵鸟一样,将身子缩进古堡似的磨屋,一边伴着老磨迟缓地磨着岁月,一边思考世事人生。他自己给出的理由是:“后来我还想就这么一辈子了,坐到老磨屋里吧,让老磨一天到黑这么磨,把性子磨钝、磨秃,把整个儿人都磨痴磨呆才好!”
这肯定不是他的真实想法,而是无奈之举。作为一个为家族进而为人类赎罪的忏悔者,仅有思想是不行的,还要有实质意义上的行动,而抱朴恰恰是一个长于思索少于行动的思想者,为此,他的内心非常痛苦,长久地承受着自责的煎熬和灵魂的搏斗。他羡慕桂桂天真不记恨,可自己做不到;他恨自己胆子太小,顾这顾那,既害了小葵,又毁了自己的下半辈子;他恨自己没敢站出来夺下老多多手里的粉丝厂,把它交给镇上人,结果使整个洼狸镇都遭受了损失;他更恨自己怕这怕那,偏偏又知道恨、知道爱。他经常处于两难之境,他最恨苦难、残忍及制造罪恶的人,然而,要阻止罪恶的发生蔓延,他就要行动,而行动就意味着以恶抗恶,这是他不愿做也不愿看到的;不采取阻止罪恶的行动,罪恶就会任其发展,这又会让他痛心疾首。中国的忏悔者走到“革命时代”,常常会陷入困境,进则亡,退则败,看来,托尔斯泰“勿以恶抗恶”的“不抵抗主义”最终也救不了抱朴。负罪的抱朴之赎罪不能完全遁入内心,他必须走出古老腐朽的磨屋而采取相应的行动,这就把抱朴及《古船》的忏悔叙事逼到了险象环生的境地,抱朴忏悔赎罪是否成功取决于他如何超越此境而跃上新境。
三
但跃入忏悔赎罪新境是艰难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文学缺乏忏悔意识,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忏悔形象,如《狂人日记》里的“狂人”、《伤逝》里的涓生、《古船》里的隋见素和四爷爷、《活着》里的福贵、《大浴女》里的尹小跳、《男人立正》里的陈道生、《水在时间之下》里的“水上灯”、《万箭穿心》里的李宝莉、《蛙》里的姑姑、《认罪书》里的金金、梁知、梁新等人物,其忏悔的最好水平,均止于赎罪阶段,即忏悔的第二阶段,而不能像《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和《罪与罚》里的拉斯柯尼科夫那样,最终在基督教超越性伦理的引导下进入人性升华、灵魂复活之境。唯有《古船》里的隋抱朴是个例外,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后代,他主动承受着祖辈犯下的“家族原罪”和自己犯下的“当下之罪”,还要被迫承受“阶级之罪”,是一个自觉地承受苦难而避免洼狸镇人流血受苦的人。在经受人性的拷问后,特别是在《共产党宣言》思想的引领下,他最终走向了生命的复活,即跃入忏悔赎罪的第三阶段,使《古船》成为中国新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中第一部“完全忏悔”之作,抱朴自然成为中国新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中第一个“完全忏悔”形象。
如同忏悔正典之作,《古船》仍然采取“罪与罚”的忏悔形式。这里的“罚”是抱朴自我归罪后的“自罚”,无论是替家族、替自己赎罪,还是替人类的罪恶赎罪,都是自觉的领受。抱朴避免洼狸镇人流血受苦的方式,是在有限地阻止见素复仇的情况下,主要以自己受苦的方式,即躲进磨屋而不参与复仇的方式来制止流血和苦难。在中国现实语境中,苦难的表现形态主要有三:一是由物质性的匮乏而引起的物质性苦难;二是由不幸的命运或种种权力压迫造成的生存性苦难;三是由价值失范、意义虚无和精神焦虑造成的精神性苦难。而民间中国对待苦难亦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屈服于苦难或厄运而忍辱苟活;第二种境界,承受苦难,与苦难同在,在默默的隐忍或抵抗中化解苦难,作被动式的有限度的抗争,多数处于苦难中的普通百姓活在这种境界。这种境界最好的走向,是通向生命本真状态,乐观地活着,如《活着》里的福贵;第三种境界,主动积极地抗争苦难,在体验苦难中体现出生命的强大和精神的崇高,并为人类提供可以效仿的理想的道德原则和精神向度。
表面看来,抱朴的受苦与苦难的第二种表现形态及应对苦难的第二种境界相似,深入其中体会考量,发现二者有着质的差别。中国民间通常的苦难形态及忏悔者应对苦难的态度,借助陈思和的说法,是“忏悔主体从抽象的人转移到具体的人”或“作者自身”,即“忏悔的人”;而抱朴自觉承受“家族原罪”和“阶级原罪”进而承受“人之罪”,是“人的忏悔”,即以“人的罪恶”为对象的忏悔。在20世纪中国,“忏悔的人”之忏悔始终停留在具体的和阶级的层次上,而以人的缺陷、人的罪恶为对象的忏悔,即“人的忏悔”则表现为20世纪现代科学成果在人对自身认识范畴中的一种折射,表现为人对自身局限(在文学中往往以“恶行”来表征局限)的深刻理解和感悟,“这种忏悔的对象不是个人,它指向个人具体背后的某种人类普遍性”。[10](PP.81-82)[11](PP.109-210)简单地说,前者是具体的人的忏悔,不像后者那样,具有超越自身而为“人之罪”赎罪的博大胸怀。
这种源于忏悔的受苦意识明显带有宗教伦理的特色,具体地说,带有托尔斯泰的特色。我们借助舍勒的受苦理论来透析抱朴的受苦及忏悔的意义。舍勒说:一切受苦都是“替代性”和“自甘性”的,以便整体受苦较轻。根据人类受苦及对待受苦和痛苦的态度,舍勒将其概括为这样一些方式:使受苦对象化和听天由命(或主动忍受);享受主义地逃避痛苦;漠化痛苦直至麻木;英勇式的抗争并战胜受苦;抑制受苦感,并以幻觉论否认受苦;视一切受苦为惩罚,并以此使受苦合法化;最后是神奇无比、微言大义的基督教受苦论:福乐的受苦,并通过上帝的慈爱在受苦中施予的拯救,将人从受苦中赎救出来——“十字架的大道”。但如何对待痛苦和受苦,始终存在着两条截然对立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主动从外部反抗受苦的客观自然的或社会的原因,即坚决“抵抗不幸”,这曾是西方主动型英雄式的抵抗。第二条道路不是要根除不幸和承受不幸之苦,而是尽可能彻底圆满地排除随意的自发的抵抗,以便从内部阻止一切可能的承受不幸之受苦,这种不抵抗不幸而通过忍受不幸,承受不幸之苦,以佛陀为代表。基督教吸收了“勿抗不幸”的思想。虽然基督教不会对不幸和恶听之任之,但在东正教会(又以俄国东正教为甚),被动忍受痛苦和靠不抵抗来消除不幸的理念,几乎在各个方面压倒了主动排除不幸和邪恶的思想,这一点已被伟大的俄国作家和思想家(特别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证明。“他们诗意化、先知化地赞美恭顺的被动性忍耐品质”,这种被动性英雄品质之楷模理念,已深植为心性质素,既迥异于主动性英雄品质之西方理念,也显著地不同于印度、尤其佛教对待痛苦、受苦、不幸的方式,[12](PP.641-654)自然也有别于民间中国对待痛苦、受苦的方式。
抱朴身上的托尔斯泰痕迹非常明显,他不能容忍家族复仇和阶级之间的相互残杀,不能容忍苦难和流血祸及无辜百姓,为此,他常常孤坐磨屋思考。对待恶,他放弃以恶抗恶的方式,在思索和隐忍中承受苦难。但是,这种赎罪方式既不利于忏悔跃入人性新境,也不利于复仇及苦难的消除。这时的抱朴思想中急需引入一种更先进且更具行动性的精神资源。我们发现,抱朴多年反复研读的《共产党宣言》承担了这个重任。久读《共产党宣言》,抱朴天目顿开,豁然开朗,竟然从中领悟到这是“一本讨论过生活的书,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书”;两位伟大人物见过的苦难比谁都多,他们只想着让受苦的人尽快地摆脱血泪。为什么这本书影响巨大,要用全世界的文字写出来,“就因为他们在和全世界的人一块儿想过生活的办法”。
《共产党宣言》的奥义变成抱朴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与见素彻夜的深谈之中。他说:“怎么过生活?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绝不是!你错就错在把它当成一个人的事情。那些吃亏的人,都是因为把它当成了自己的事情”,“一个人千万不能把过生活当成自己一个人的事情,那样为自己就会去拼命,洼狸镇又会流血。”世事复杂,道理却简单,只要大家想着一起过好生活,彼此善爱,就会放弃复仇,摆脱苦难、不幸和流血,就会把生活过好。
忏悔跃入生命新境非常艰难,但在抱朴身上,却在不经意间就实现了,不能不说是个天大的奇迹!这个中国民间的思想者,是如何实现这一伟大思想工程的呢?仔细辨析,其间的思想脉络还是清楚的,其思想逻辑是这样演进的:抱朴身上突出地显现出两种思想,一种是托尔斯泰宗教特色的“勿以恶抗恶”的“不低抗主义”思想(托尔斯泰宗教观即托尔斯泰主义是东正教传统与西方启蒙思想的融合,其主要思想是“爱一切人”、“勿以恶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此中还包含着中国传统的内省意识,以及自觉为“人之罪”赎罪的受苦情怀;二是《共产党宣言》通过阶级斗争而达到解放全人类的宏大思想中所蕴含的“大家一起过生活”的朴素思想。这两种思想属于两种思想体系,在中国当代语境中,贬抑前者盛赞后者早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张炜不能不受其影响。因此,二者之间很难通融,对立倒是它们的常态。关于这一点,早有学者提出质疑,雷达指出:作者通过抱朴钻研《共产党宣言》,“试图刻划一个初具共产主义理想的农村新人,但在我看来,他更像一个怀抱大仁大爱的人道主义者”。他的忏悔和拯救之道,带有抽象的人道精神和“理想化”的虚幻色彩,其忏悔的东方式的含有禁欲色彩,他能否真正顿悟《共产党宣言》,“成为真正的新人,令人担心”。[2](PP.236-237)吴俊直言抱朴手不释卷地诵读《共产党宣言》,“是作品中一处最大的牵强附会”,很大程度上,它恐怕只是一种“点缀”,一个由作者生硬安排的“契机”。“它反映了作者在掉进了观念陷阱之后,无暇分辨是非曲直而随意拿起一件现成的武器盲目挥舞时所显露出来的一种窘态。”但吴俊有一句话很要紧,他说:尽管我质疑《共产党宣言》对抱朴生活转折的合理性,但我比任何人都更加坚定不移地相信,只有《共产党宣言》思想的巨大历史穿透力和现实感召力,才使抱朴最终由一个被扭曲的人升华为真正自由解放的人。[13](PP.82-84)换言之,《古船》只有如此嫁接,才能完成理论预设。至于理论是否符合现实,那就只能存疑了。
我的理解是,由于作者揭示了托尔斯泰宗教伦理和《共产党宣言》中都蕴含着希望人类摆脱苦难的思想,故而在托尔斯泰宗教伦理之上再植入《共产党宣言》中“大家一起过好生活”的超越性思想,就会出现人物精神新变的奇迹。当前者先期到达抱朴意识中时,后者由于抱朴的“怯病”而处于纯粹思索状态。当“思想者”脱胎换骨要采取行动时,后者则顺势而入,迅速成为引领抱朴进入生命新境的主要精神力量。
仿佛是身体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量,抱朴觉得他不能再犹豫、再像死人一样孤坐磨屋,他催促自己走出磨屋,振作起来,和全镇人一起过好生活,不能让苦难和流血老跟着洼狸镇人。他内心充满力量,而好运恰恰也在这时降临于他。粉丝厂形势急剧恶化,面临倒闭,恶人赵多多于绝望中醉酒撞车自焚,抱朴自荐担任粉丝公司经理,洼狸镇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抱朴“新人”形象由此产生。
四
《古船》里纯粹意义上的忏悔形象,我个人以为,仅抱朴一人。至于评论中经常提到的见素和四爷爷是不是忏悔形象,或者说他们的忏悔是否真正意义上的忏悔,我有自己的理解。
见素是为家族而战的复仇者,它的主要对手是赵氏家族的“恶人”赵多多。赵多多承包经营粉丝厂,在他看来,粉丝厂应该姓隋,是他和抱朴的。尽管父亲在三十多年前已经将粉丝厂全交了出去,但在见素的意识里,粉丝厂是隋家的,赵多多承包经营粉丝厂,是隋家的奇耻大辱。所以,他朝思暮想的一件事,就是从赵多多手里夺回粉丝厂,以达到复仇的目的。他的复仇计划和复仇行动总是受挫,最后,他甚至想联合老赵家的人对付抱朴,虽然未果,但他起意了,起意就有罪。在一部以赎罪拯救为主旨的小说里,是不允许复仇占有上位的,于是,在抱朴决定告别“旧我”而向“新我”跃入之时,见素莫名其妙地得了不治之症。绝望之际,见素对哥哥敞开心扉,说了这么一段带有忏悔意味的话:
我回城后想来想去,决定还是把粉丝公司夺回来,不管它落在谁手里,一定要让它姓隋。因为你多次表示过,它不能姓隋!我积攒着力气,一边通过张王氏和四爷爷联系,准备最后打这一仗能赢,能把你打败,夺回粉丝公司!……你看吧哥哥,我昏到这样,我想联合老赵家的人来对付你了,我住院前几天还在想这些。你现在骂我吧,打死我我也不还手,因为我起意了。不过还是老天有眼——它在紧急关口判了我的死刑,让我害了绝症。那场争斗再没有了,老天惩罚了我,我对你、对大喜、对一切别的人犯下的罪过,一下子了结了。
这段话首先是认错懊悔,然后才是知罪认罪,且知罪认罪里还隐含着“复仇而不得”的无奈之感。这说明,见素的浅显忏悔与真正出自“否定与建构”双向运作的忏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也就是在他说完这段话后,他仍然纠缠于母亲的死因,当他终于从抱朴叙述中得知真相后,又起了复仇的恶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见素不是忏悔形象,他的认错懊悔是特定情境中良知的一时醒悟,由于它的力量远逊于强大的复仇之力,所以不能将认错懊悔发展到知罪认罪进而赎罪的水平。
四爷爷赵炳是个厉害的角色,他既是赵氏家族的最高权威,又是洼狸镇永远不倒的土皇帝。从土改到大跃进,他主掌洼狸镇,该做的都做完了后,他“功成身退”。他深谙进退之道,虽辞官隐退,但洼狸镇还在他的掌控之中,好多大事还是他说了算。他左右着洼狸镇的现实关系及全镇人的命运,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可他对这些罪过从未有过忏悔。他的忏悔仅限于奸污少女含章一事上。而他给出的忏悔原因却是:“我明白我已破了规矩,这个事情上不会有好结果。”他知道含章终究有一天会向他复仇,于是等着这个“结果”的到来。他认为一切都在规矩里,坏了规矩就要受罚。这哪是忏悔,分明是后悔性的认错,把罪责降到犯错上。而他向含章的真情道白,分明又有知足与认罪混杂的成分:“我已知足。我是什么人?洼狸镇上一个穷光蛋。你是老隋家的小姐,又是第一美貌。我死而无憾,所以我就等着结果。”只有等到这个“结果”即含章刀刺他之后,我们才从他那声长叹中听到了忏悔之音:“我对老隋家人做得……太过了。我该当是这个……结果!”
尽管如此,笔者仍然认定四爷爷不是一个真正的忏悔者,他充其量只是一个根据民间伦理准则而有选择性地领罪的人。
[1]张炜:《古船·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
[2]雷达:《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的碑石》,《当代》,1987年第5期。
[3]罗强烈:《思想的雕像:〈古船〉的主题结构》,《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4]王彬彬:《悲悯与慨叹——重读〈古船〉与初读〈九月寓言〉》,《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
[5]郜元宝:《“意识形态”与“大地”的二元转化——略说张炜的〈古船〉和〈九月寓言〉》,《社会科学》,1994年第7期。
[6]张炜:《古船》封底,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
[7]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
[8]黄瑞成:《“忏悔”释义》,《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1期。
[9]张中峰、孙世军:《张炜创作中的托尔斯泰“痕迹”》,《殷都学刊》,2004年第1期。
[10]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忏悔意识》,《上海文学》,1986年第2期。
[11]祥耘、陈思和:《忏悔意识在世界的传播及其对中国的辐射》,《学术界》,2010年第3期。
[12]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上],林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13]吴俊:《原罪的忏悔,人性的迷狂——〈古船〉人物论》,《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2期。
(责任编辑:沈松华)
The First “Full Confession” Work in Chinese New Literature——A Further Discussion onTheOldBoat
WANG Da-m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TheOldBoatis a reflective work which mirrors the evolution of the times by depicting vicissitudes and hatreds between families and accessory class struggles, where the ancient Wali Town’s over-40-year history serves as an epitome of contemporary China. However,TheOldBoatis more of a confession, and is the first “full confession” work in Chinese new literature. So-called “full confession” means that confessor has gone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a confession: from acknowledgement, inculpation to bearing, atonement and to reborn of humanity and resurgence of soul. Baopu, son of a folk noble family who bears original sins of his family and his class, shows repentance and atones on his own initiative, interprets “people’s crime” into “my crime”, and finally parts with his “former self” and leaps into a “new self”. Strictly speaking, confessors Jiansu and Zhao Bing, who are often mentioned in literature reviews, are not real confessors. The former has no choice but to realize and acknowledge his guilt due to a “failed revenge”, and the latter’s confession is a selective acknowledgement of guilt based on codes of ethics.
TheOldBoat; Zhang Wei; confession; original sin of family; original sin of class
2016-06-01
王达敏,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评论中心主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小说、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
I207.425
A
1674-2338(2017)02-0088-08
10.3969/j.issn.1674-2338.2017.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