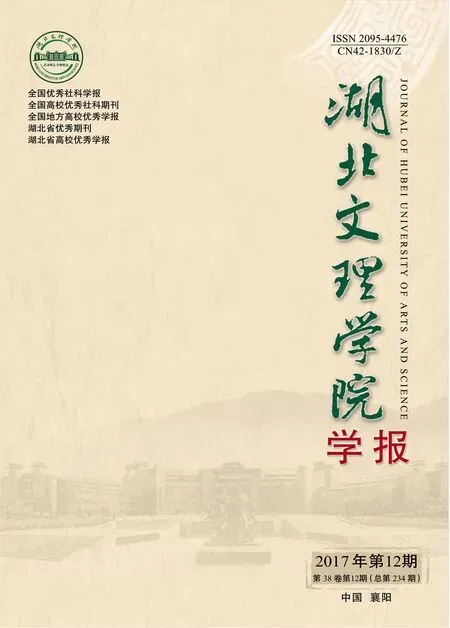《文心雕龙》“江山之助”说探究
梁雅阁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文心雕龙》“江山之助”说探究
梁雅阁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江山之助”是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文学命题,此命题揭示出自然景物通过美的感召作用于诗人的内心,使诗人内心情感动荡,进而发于吟咏,形诸文字。但是,如何把自然景物完美地融入进文学创作中,宋齐以来的诗人多走偏颇之径。刘勰在此篇中揭示了齐宋文学在描写自然景物上的错误,并指出了山水景物描摹的典范,屈原在景物的描绘中融入情的寄托,实现主观与客观的完美统一,是近代诗人应该效法的典范。刘勰欲借屈原的“江山之助”纠宋齐文风之弊端。
刘勰;《文心雕龙》;江山之助;屈原;宋齐文风
I206.2/.4
A
2095 -4476(2017)12-0063 -05
2017-05-18;
2017-06-20
梁雅阁(1995—),女,河南洛阳人,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一部优秀的文学批评专著,学术界对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使之成为能与红学、选学相提并论的一门显学。极大的关注热情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单就《物色》篇而言,研究成果就多不胜数,其中更是有像王运熙、张少康、王元化、周振甫等名家的研究,其成果如星辰般光亮闪耀。首先是关于《物色》篇位置的归属问题,学术界的大家们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归入创作论,或归入批判论,目前仍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还有一大类是对于《物色》内容层面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以《物色》全篇为研究视点,或认为《物色》篇是论述自然景色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或认为“物色”观是对山水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或认为“物色”观是谈文学鉴赏的;或提出“物色”观涉及创作论与鉴赏论两个方面;或主张“物色”观是谈论诗文写作技巧的。然而,对于此篇进行细微探究的文章并不多见,故文章拟从《物色》篇中“江山之助”一词出发,结合《文心雕龙》全书,并联系屈原的创作和宋齐时期文学的发展状况,对“江山之助”说进行详细的探究分析。
在《物色》篇中,刘勰提出了“江山之助”这一重要的命题:“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1]694-695“江山之助”表面上的涵义是说自然山水对诗人文学创作的助益作用,然而联系刘勰在其它篇目中对楚辞的论述以及屈原的生平经历可得知,“江山之助”一词的涵义并不是如此简单,它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一方面,“江山”助益了屈原的文学创作,香花香草、青山秀水在《楚辞》中大量地涌现,云烟大泽的自然环境助长了屈原作品中天马行空、驰骋飞跃地想象;另一方面,刘勰在《物色》篇中使用这一典故,并非一味地鼓励文人们完全沉浸在山林皋壤中,从中汲取创作的情思,还应包含有劝诫当时文人应以屈原对山水的描摹为典范,纠正当时玄言、山水文学中的奇厥、诡巧之偏的深层含义。
一、“江山之助”的溯源探析
“江山之助”一词出自《文心雕龙·物色》篇。按照张少康先生的观点:“《文心雕龙》中的《物色》篇是专门探讨文学创作中的人和自然关系的。”[2]也即是探讨自然景物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江山之助”作为其枝干下的一个小命题,其含义自然与篇目的主旨思想相关联。简言之,“江山之助”主要是说自然山水在文学创作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对于自然景物触动诗人的心灵,使诗人产生创作的欲望,前人已多有论说。首先是先秦时期的“物感说”。《礼记·乐记》中有言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3]在这里是以音乐来说明的,物能够影响到心灵的悲哀与欢乐,这种感情会进一步反映到音乐中去,呈现出一个物——心——音的过程。“物感说”已经初步具备了刘勰“物色论”的某些含义。但是,《礼记》中所言的“物”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它远远超出了《文心雕龙》中“物色”的范围。到了后来,陆机在《文赋》中也论述到“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4]762陆机已将景与情的关系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春季芳香四溢、生机盎然容易触动诗人欢快的情思;深秋萧瑟凄怆、落叶飘零,更容易牵动诗人苦闷的愁绪。相较于“物感说”,陆机不过从音乐过渡到了文学,且论述的更为具体详尽而已,其本质上仍没有脱离物色触动诗人心灵情感的内涵。稍后,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歌咏。”[5]钟嵘所论重在阐释诗歌创作的源泉,诗人由景生情,并把此情寄托于歌咏。
《礼记》《文赋》《诗品》都对物与情、情与文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其实质性的内涵基本一致,但总体上看,这些论述都较为简洁,真正对心与物、情与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则是刘勰。在《物色》篇中,刘勰主要论述了自然景物与诗人创作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情以物兴”,自然景色感召人心,诗人内心的情感受到触动,形成文字,吟于声音。另一方面,“物以情观”,诗人对于自然景物的感触并不是机械式地反映,而是要经过心灵与景物的双重契合。
“江山之助”是刘勰物色论的一个方面,其侧重在自然景物对诗人情感的触动作用。诗人看到了美丽可爱的景色,内心自然会欢欣;看到凄凉幽怆的环境,内心就会苦闷。而诗歌是言志或缘情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4]2029这种由景物引发的心灵情感的触动最终将形诸于诗文。简言之,江山,即自然景物为诗人提供了一种文学创作的情感动机。细思文学史上,因触景生情而吟于歌咏的文学作品十分常见。比如在《诗经·王风·君子于役》中,妻子看到太阳已经沉落西山,牛羊也已经缓缓归来,因而思念在远方服役的丈夫。《诗经》中此类触景生情的例子还很多,后人多概括为比兴的手法,所谓“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6]其中,也多涉及到因物生情、触景生情的含义。到了后来,文学史上第一首保存完整的山水诗——曹操的《观沧海》,即是因“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7]的壮阔景象触动内心豪迈乐观、积极进取的精神气魄,故而“歌以咏志”。自然景物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是不带有任何情感色彩的,但是诗人大多有一颗敏感而多情的心,他们看山不仅仅是山,看水也不仅仅是水,自然景物是可以进行心灵交流、引发情感共鸣的朋友,因此,他们的情感因为景物而变化,文辞也就因为情感而产生了。正是因为有了“物色之动,心亦摇焉”[1]695的情感动机,诗人们才能创作出众多文质兼美的山水田园诗歌。从这个角度讲,只要善于融会贯通,写景抒情做到详略得当,自然万物就能成为诗人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这也正是刘勰在《物色》篇中想要表达的主要含义。
二、“江山之助”与屈原创作
(一)屈原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江山之助
考察屈原流传下来的作品,“江山之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楚地自然山水景物在屈原作品中的大量涌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香草香花这一类意象。在《楚辞》一书中,这些香花香草不但出现的次数繁多,而且就物象本身的名称来看也纷繁多样。诗人多次歌咏到芳草的有:蕙、茝、荃、芭、荪、春兰、秋菊、留夷、揭车、杜衡、芳芷、薜荔、杜若、芰荷、芙蓉、兰草、辛夷、芳椒、江离、胡绳、菌桂等。这些自然景物直接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既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内容,又增强了艺术的美感,形成了一种比兴寄托的手法,或象征诗人自身高洁不屈的美质,或象征诗人心怀爱慕而又高高在上的君王。此外,楚地景物中的青山秀水也在作品中被多次地歌咏。失意的诗人徘徊漫步在山水田野之间,这些香花香草自然而然地映入眼帘,进而触动内心的情思,自己身怀美质却被猜忌、被疏远、被流放,君王受小人蒙蔽、遥不可及,这一系列的悲痛心酸不时地咏上心头,故而诗人发愤以抒情,吟咏出不朽的佳篇。另一方面,楚地高山大泽、云烟变幻的自然环境也助长了诗人漫无边际地驰骋想象。无论是就《离骚》还是整部《楚辞》而言,神奇浪漫而又大胆奇特的想象是其一大特色。这种浪漫主义的想象虽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楚地流传已久的巫文化传统,但楚地云烟缥缈、深山茂林的自然环境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种奇特的想象。王夫之《楚辞通释·序例》中云:“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嶔戌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矗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8]故而在《离骚》中,诗人可以任意想象:“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9]19这些神奇的想象为诗人艰辛的求女之路染上了浪漫的色彩,为作品增添了不少的生机和活力,令人心驰神往。这种浪漫的想象思维毫无疑问离不开楚地特有的自然环境。詹锳在《文心雕龙义证》中对此也给予了肯定:“楚于山则有九疑南岳之高,于水则有江汉沅湘之大,于湖潴则有云梦洞庭之巨浸,其间崖谷洲渚,森林鱼鸟之胜,诗人讴歌之天国在焉。故《湘君》一篇,言地理者十九,虽作者或有意铺陈,然使其不遇此等境地以为文学之资,将亦束手而无所凭借矣。”[10]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江山的确对屈原的创作带来助益之用。
(二)其他因素对屈原创作的影响
刘勰在文中说“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1]695“抑亦”是也许、或许的意思,用来表示推测。首先刘勰对屈原因江山之助而能深刻洞悉到《国风》和《离骚》的情韵并不是持绝对肯定的态度。其次,对于“抑亦江山之助乎”是感叹还是反问的语气,众多研究《文心雕龙》的名家看法也是不一致的。范文澜、杨明照和吴林伯的本子用的都是感叹号,詹锳、王运熙和周振甫的本子用的都是问号,虽然说只是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的差异,但是其中的情感语气却大不相同。
《文心雕龙》一书中论述到《离骚》的地方还有很多,结合其他地方的论述可以初步探知到刘勰对屈原创作《离骚》的原因的认知。《文心雕龙》一书中,刘勰对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态度是略微复杂的,并不像对《诗经》等儒家经典著作那样是明显的褒扬与推崇的态度。在《辨骚》篇中刘勰指出《楚辞》四处异于经典的地方: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但是,从整体上把握,刘勰对《楚辞》还是肯定多于否定的。《诠赋》篇认为“楚人理赋”为“鸿裁之寰域”和“雅文之枢辖”;《时序》篇说“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采于风云”[1]672;《物色》篇也说到“诗骚所标,并据要害”[1]694。 故而,在刘勰看来,《楚辞》也可以称得上是文学史上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对于屈原缘何能创作出《离骚》这等优秀的作品,刘勰也多次有所涉及。《辨骚》赞曰:“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1]48在自然山水前强调了屈原自身的惊人之才和凌云壮志;《明诗》云:“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1]66,这里强调了楚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对屈原创作《离骚》的影响;《时序》中还提及到了战国时期纵横诡辩之风对《楚辞》创作的影响。综上所述可以得知,在刘勰看来,江山之助只是屈原成就不朽杰作其中部分的因素,甚至不占及最主要的原因。故而吴林伯在《<文心雕龙>义疏》中将“助”解释为:“表示产生情思的因素,江山只起辅佐作用。”[11]实为确切之论。
那么其他文学批评者又是如何看待屈原文学创作的缘起呢?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4]1864明人胡应麟《诗薮·内篇》评价《离骚》说:“屈原氏兴,以瑰奇浩瀚之才,属纵横艰大之运,因牢骚愁怨之感,发沉雄伟博之辞。”[12]历来评论家似乎更看重不幸的命运遭际对屈原文学创作的影响,认为屈原被流亡的坎坷命运对于创作产生的影响更为重要。这一论断是十分有道理的。屈原在《九章·惜诵》篇也开篇明义点出“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9]108。但是,就“江山之助”一词说来,他是否本身就包含有遭受放逐、远离朝堂的含义呢?汪春泓先生在《关于<文心雕龙>“江山之助”的本义》一文中有过详细的探讨。作者通过考察“江山”一词的渊源以及后代对“江山之助”的接受,认为“江山之助”恰恰不是指自然景物的助益,“江山”不等同于“山林皋壤”,而是指缘于朝廷斗争所造成的屈原的不幸的命运,是指社会政治因素。[13]诚如作者所论,庄子最初在使用“江山”一词时云:“彼其道远而险,又有江山,我无舟车,奈何?”[14]“江山”在这里是包含有道远且险的意思,后代诗人使用“江山”一词,也多少含有这层意思。作者的论证十分严密,材料证据也十分充实可靠。但是据此就可以在“江山之助”与政治坎坷之间划等号了吗?实际情况恐怕未必如此。刘勰把“江山之助”这一命题归入于《物色》篇,他的本意仍是在强调江山景物的助益作用。回归到屈原的作品中来说,读者确实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楚地特有景物、风俗的助益作用,诗人天马行空、奇特瑰丽的想象,以及对山水草木的反复吟咏,都是楚地独有景观的反映,故而《楚辞》一书与北方的《诗经》呈现出的是两种迥然不同的美学风格。张少康先生认为:“刘勰在《物色》篇里最后这几句论说,正是强调了心物之默契,有待于作家深入到现实中去,那里是有深厚的艺术宝藏在等待诗人去开发的。”[15]从《物色》篇来看,刘勰确实是在强调自然景物对文学创作的助益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刘勰又肯定了其它众多因素对于《楚辞》的创作的影响,其实这两者之间并不是矛盾的,表明了刘勰欲借“江山之助”寄予深层含义。综合考虑可以认为,刘勰在此借用屈原的典故,除了有鼓励文人从山林皋壤中汲取创作的文思外,还包含有一种劝诫作用:文人应学习屈原对于自然景物的描写,能够做到详略得当,善于会通,并在景物中寄寓人生的情感体验,进而创作出优美的诗篇。这其中是寄托着刘勰纠正当时文风的奇巧浮靡之弊端的希望的。
三、“江山之助”与宋齐文风
《文心雕龙》一书中,刘勰对宋齐时期的文风,是颇多诟病的。在《序志》《明诗》《通变》《定势》《时序》《物色》等篇中,刘勰多次指责当时不良的文学风尚。比如:《定势》篇所云:“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1]531刘勰对宋齐时期的诡巧讹滥、刻意求新的文风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就《物色》篇来看,刘勰虽然表面肯定了当时山水文学景物刻画逼真的特点:“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印字而知时也。”[1]694但是,在看似客观的叙述中,刘勰对山水文学还是有褒有贬的。当时的山水诗人描写自然景物大都崇尚形似,作为南朝文学重要代表人物的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他们的诗文创作都表现出“尚巧似”的特点。刘勰虽然并不完全否定这种“形似”的手法,但是却指出其缺乏真实情意的弊端。即便是“窥情风景之上”[1]694,他们所写之情只是细致观察后得到的景物自身的各种情态,并非诗人内心与山水景物的交融契合后形成的真切的情意。这一点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自然界实际并没能真正构成他们生活和抒发心情的一部分,自然在他们的艺术中大都只是徒供描画、错彩镂金的僵化物。”[16]采用《情采》篇的观点来说,当时的山水文学多存在“为文造情”的弊端,这些对于文学的健康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刘勰对此深表痛心,故而以屈原的“江山之助”为典范,为山水景物的描写树立了标杆。
据《序志》篇可知,刘勰创作《文心雕龙》一书,本有矫正当时文坛不良风尚的动机。为纠正当时文坛上的这种不良风气,刘勰为山水诗人指明了效法学习的典范——《诗经》和《离骚》,而屈原是能够深切洞监其中情韵之人,是他们师法的对象。屈原的作品在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中注重抒发情志,寄托了诗人政治讽谏的深意,而这些正是当时诗人创作中严重缺乏的。江山助屈原成就了光辉篇章,自然也不会亏待了近代的诗人,只要他们能够像屈原一般,在景物的描绘中融入情的寄托,实现主观与客观地完美统一,“目既往还,心亦吐纳”,[1]695一定也能创作出优秀的诗文佳篇。
“作者著《物色》,以为文章有借于江山风物之助;然反对‘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于此不能不辩也。”[17]郭晋稀之注道出了刘勰创作《物色》篇的主旨所在,江山助益文学创作,正是刘勰想要表达的一个主张,至于如何写好自然景物,屈原的景物描写正好可奉为圭臬。结合《物色》全篇,作者并没有包含政治坎坷的深意在里面。至于后人在使用到“江山之助”时,如《新唐书·张说传》中记载:“既谪岳州,而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之助云。”[18]岳州位于湖南一带,恰好与屈原生活的楚地有着相似的山水景致。至于“江山之助”恰好与仕途失意联系到了一块,恐怕要另当别论了。
[1]刘 勰.文心雕龙注[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2]张少康.《文心雕龙》的物色论——刘勰论文学创作的主观与客观[J].北京大学学报,1985(5):94 -101.
[3]钱 玄.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1:494.
[4]萧 统.文选[M].李 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钟 嵘.诗品集注[M].曹 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
[6]朱 熹.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2.
[7]安徽毫县《曹操集》译注小组.曹操集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42.
[8]王夫之.楚辞通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4.
[9]林家骊.楚辞[M].北京:中华书局,2015.
[10]詹 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760.
[11]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576.
[12]胡应麟.诗薮[M].北京:中华书局,1958:4.
[13]汪春泓.关于《文心雕龙》“江山之助”的本义[J].文学评论,2003(3):133 -139.
[1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583.
[15]张少康.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44 -245.
[16]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161.
[17]刘 勰.文心雕龙[M].郭晋稀,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4:385.
[18]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410.
“Jiangshan ZhiZhu” in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LIANG Yag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
“Jiangshan ZhiZhu” is an important literature proposition, proposed by Liu Xie in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Wuse.It holds that the beauty of natural scenery inspires a poet’s heart, and makes the poet’s inner feelings unstable.Then this emotion will be expressed in literature.But how do we integrate natural scenes with literature faultlessly? Most poets have gone a wrong way since the period of SongQi.In this article, Liu Xie reveals the mistakes of SongQi literature in describing natural scenery,and points out the model of landscape description.Qu Yuan integrates emotion sustenance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scenery,and achieves perfect unity of the subjective and the objective,which is a model that modern poets should follow.Liu Xie wants to correct the disadvantages in literatures from the period of SongQi by advocating Qu Yuan’s “Jiangshan ZhiZhu”.
Liu Xie;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Jiangshan ZhiZhu; QuYuan; style of writing in the period of SongQi
倪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