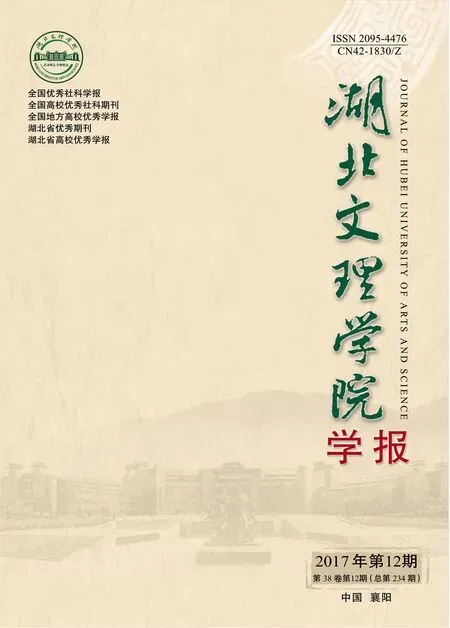徐嘉瑞基于“平民文学”思想的文学创作语言观
吴婉婷
(云南艺术学院 艺术文化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徐嘉瑞基于“平民文学”思想的文学创作语言观
吴婉婷
(云南艺术学院 艺术文化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徐嘉瑞以“平民文学”为其学术思想的核心,重视底层民众对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也重视文学对平民大众之影响。基于此,徐嘉瑞的文学创作以文学语言作为媒介,通过语言的选择和使用体现其“平民文学”思想。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受到不同历史语境的影响,处于不断深化和拓展的状态,徐嘉瑞对文学语言的使用亦在不同时期进行了调整和变化,使用明白如话的白话、质朴本色的云南方言俗语和通俗易通的大众语进行文学创作。
徐嘉瑞;平民文学;白话;方言俗语;大众语
I206.6
A
2095-4476(2017)12-0047-05
2017-08-28;
2017-09-21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5C063Y)
吴婉婷(1983—),女,云南昆明人,云南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徐嘉瑞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大家,集文学家、理论家和文史家于一身,在戏剧、历史、民间文艺和文学创作等多个领域均有较高建树。20世纪初中国多元交汇碰撞的话语背景对徐嘉瑞学术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但无论他接受何种思想影响,他的“学术思想始终贯穿了‘民本’思想”[1]4,“先生在史学、新诗、戏剧、音乐、杂文、时评等众多领域的写作实践无不贯穿‘平民文学’这一信条,且终生孜孜不倦、从未舍弃,是为一大楷模”[1]4,徐嘉瑞是在“平民文学”思想指导下开展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创作的。
从2008年出版的《徐嘉瑞全集》的目录来看,徐嘉瑞的文学创作包括:诗集十部、创作长诗三首、根据民间传说改编创作长诗两首、创作戏剧作品五部、根据民间传说改编创作戏剧两部和写作杂文数十篇。徐嘉瑞的文学创作与他的“平民文学”思想相互呼应,尤其是通过文学语言的使用体现“平民文学”思想,也用“平民文学”思想指导具体文学语言的选择。
一、徐嘉瑞“平民文学”思想的内涵
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浪潮影响到云南,多位在昆学者创办进步报刊宣传“五四”新思想,如《尚志》《救国日刊》《澎湃》等。徐嘉瑞是云南较早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者,是云南宣传“五四”新思想的代表人物,当时即使没有稿酬,他也经常在《救国日刊》等进步报刊上投稿发文①这段历史主要依据《救国日刊》创办者张天放的回忆文章《昆明的〈救国日刊〉与昆明的五四运动》中的记录。。徐嘉瑞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背景下提倡“平民文学”,既受到当时“人的文学”思潮的影响,也具有自己的独特理解。
徐嘉瑞“平民文学”的核心思想是尊重底层民众,重视普通百姓的价值和创造力,同时也认为文学作品对平民百姓具有思想教育作用,在这一核心思想之下,其具体内涵随时代变化和徐嘉瑞思想发展在不断深化拓展。换言之,“平民文学”思想并非是徐嘉瑞于一时一地提出的,不能以一种静态的、单一的观点简单诠释,需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既要关注20世纪初的社会时局、文化思潮的演变,也要关注徐嘉瑞的思想变化,由此才可见出徐嘉瑞的“平民文学”观的全貌。对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的理解,需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徐嘉瑞最早在1923年出版的个人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古文学概论》中提出了“平民文学”的概念,该书从内容、形式、作者身份和音乐四个方面对“平民文学”进行了界定:认为“平民文学”是在内容上“取材于社会,取材于民间,摹写人生”;在形式上“无一定方式,写实的、生动的”;在作者的身份上是“非知识阶级,非官僚,无名者”;在音乐上“可协之音律”。徐嘉瑞早期对“平民文学”的界定与“民间文学”的概念十分接近,且《中古文学概论》中的“平民文学”作品的选材上也多是民间的诗歌和歌谣小调,如汉魏时期的《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等,徐嘉瑞认为这些作品不只出自一人之手,没有具体的作者,符合民间文学的集体性的特点。另外,徐嘉瑞从1929年开始写作的《中国文学史大纲》也认为“平民文学”是指“民间文学”,如他认为《诗经》中“风”是“各国民俗歌谣之诗”。
中期,徐嘉瑞于1936年出版了《近古文学概论》,书中一方面延续了《中古文学概论》中提出的“平民文学”是民间文学的观点,有意识地将“平民文学”与“通俗文学”进行区分,他说“平民文学一语,久已流行。然其观念甚为暧昧,盖多流于形式分类:以为浅易明白之文学,即平民文学;能作浅易明白之文章者,即为平民文学家;此大谬也”[1]77。徐嘉瑞再次强调了“平民文学”的“民间性”:“这民众文学的特点,是集体的,非个人主义的,所以找不出作家主名;是普遍的,平凡的,所以非常浅近明白,容易流行;是共通的,社会的,所以具有类型性;是从作家生活里呼喊出来的,所以还没有分工,还没有成为文人学士专有的职业……民众文学,尚有一特殊之性质,即口耳相传是也。”[1]76从民间文学具有的集体性、口头性、传承性和变异性的特点对照来看,徐嘉瑞在此书中仍是把“平民文学”和“民间文学”等同起来。另一方面,徐嘉瑞将“平民文学”等同于“民间文学”的同时,也认为“平民文学”还指“大众文学”。徐嘉瑞的《近古文学概论》出版于1936年,“五四”文学运动这时已退潮,左翼文学思潮成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的主导,“文学大众化”运动是左翼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徐嘉瑞作为较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学者,他的学术研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徐嘉瑞在《近古文学概论》《诗经选读》等著作中虽仍认为“平民文学”主要指民间文学,但他在1938年和1939之间发表了多篇关于“文学大众化”的文章,如《诗歌和民族性》《“九一八”后中国新诗运动的路标》《高兰的朗诵诗》《大众化的三个问题》和《悼“海的歌手”邵冠祥》等,在这些文章中,“平民文学”的内涵更多地与革命的“大众文学”联系在一起,强调文学作品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表达大众的生活、思想和意识,要用大众的语言和形式进行文学创作。可以说,这一时期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既指“民间文学”,更指由进步的文学家使用通俗的形式和语言创作的、能为普通民众接受的革命的“大众文学”。
后期,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不再存在平民和贵族阶层的对立,同时也由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思想的影响,徐嘉瑞在建国后不再直接使用“平民文学”一词,“平民文学”向以工农兵为主要接受者的文学转变,但“平民文学”作为徐嘉瑞文学思想的底色仍在延续,表现为以下三方面。首先,徐嘉瑞重视对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其次,徐嘉瑞延续了对平民的生活现实的关注,针对社会生活中的大小事件发表了多篇短文。再次,徐嘉瑞在这一时期还创作多部以普通百姓为主角的文学作品,如《望夫云》《和振古歌》。可见,徐嘉瑞的“平民文学”观在建国后受到政治思想影响以潜在形式延续,他也在思想中持续了对普通民众的关切和尊重,但在具体文章的概念标书中,“平民文学”为“工农兵文学”或“人民文学”所取代。
综上所述,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是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文学”的文学思潮、“文学大众化”运动和新中国文艺方针政策的呼应和具化。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徐嘉瑞“平民文学”观内涵从文学创作主体,到文学作品本身,到文学作品的受众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拓展。
二、徐嘉瑞的文学语言体现的“平民文学”思想
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说:“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可见语言不仅是文学创作的工具,更是表达思想的载体。徐嘉瑞在文学创作中对语言的使用是围绕着他的“平民文学”思想展开的。当然,如前所述,徐嘉瑞的“平民文学”思想由于受到不同文学思潮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处于不断拓展、变化中,徐嘉瑞对文学语言的具体运用,在不同时期也进行了调整变化,反之对徐嘉瑞不同时期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的研究亦可见出其“平民文学”思想发展的过程。
(一)使用白话
徐嘉瑞认为由民众创作的和为民众创作的文学作品,在语言上应是“浅近明白,容易流行”的,要使用“明白如话”的语言。徐嘉瑞对白话语言的支持和倡导主要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中自觉地使用白话语言。
“五四”文学革命的内容之一是语言革命,即用白话取代文言。“五四”以来的学者们对中国传统古文进行了全面的质疑和反思。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和《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等文章和论著中,对古文文学和古文进行了否定。陈独秀认为文言“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批评东晋以来的骈文律诗,“诗之有,文之有骈,皆发源于南北朝,大成于唐代。更进而为排律,为四六。此等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正统文学,极其长技,不过如涂脂粉之泥塑美人。以视八股试帖之价值,未必能高几何,可谓为文学之末运!”[2]15此外,在“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中,胡适和陈独秀的支持者们也对文言进行了激烈批驳,如钱玄同将文言文称为“千年来腐臭之文学”;傅斯年认为古文文学导致文言分离,“虽深芜庞杂,已成要死”;徐嘉瑞也认为古文“以奇异罕见之字,堆砌而成。恶滥之风,莫此为甚。”这些学者的观点在今天看来虽过于激进,对古文的全面否定也还值得商榷,不过在二十世纪初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对僵化陈腐的文学语言之反思确有较大的开创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影响云南时,徐嘉瑞只是一位24岁的年轻学者,他抱着满腔热情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中。徐嘉瑞早年的文学创作多为古典诗词,如1914年的《湖上竹枝词》、1915年的《翠湖杂吟》、1916年的《哀青岛》和1919年的《荒村》等诗。受到“五四”白话文运动影响后,徐嘉瑞和朋友刘尧民成为云南第一批进行新诗创作的文学家,自觉地使用白话进行诗歌创作。1921年11月徐嘉瑞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白话新诗——《农家生活》(一)、(二),诗歌用生动鲜活的语言描写的农村丰收的喜悦,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平仄押韵,字句对仗相比,这首诗完全是口语式的即兴抒发。诗中的“真好”“也喜欢得个飞起来了”“又晴”“又好”“又大”“人呵”“马呵”等语言,均为口语,没有典故的运用,也没有华丽的修辞,使读者感到有如一个挑担前行的农民的既质朴又热情的口头叙述。
此后,从1921年至1940年左右,徐嘉瑞陆续创作了大量的白话新诗,如《神之眼》《自然之火》《开辟之歌》和《菩提树》等,其中有对农村生活的描写、有对国民党的反抗、有对青年的期盼,还有鼓舞军民抗日的热情等等。另外,徐嘉瑞的戏剧和杂文均是用通俗明了的白话创作而成。徐嘉瑞更利用报刊杂志作为阵地,积极宣传白话文[3],从1920年开始,徐嘉瑞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多份报刊,如《均报》《救国日报》和《澎湃》等。这些报刊在当时主要是宣传“五四”的进步思想,“在昆明,首先以白话文进行宣传的报刊,那就是一九一八年出版的《救国日刊》,它以民主主义的思想为旗帜,积极宣传反帝爱国的主张。”[4]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发展至后期并未真正融入民众,虽然胡适也认为“白话文的‘白’,是戏台上的‘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化”[5]。但在他领导下的“白话文运动”的文学语言并未真正实现通俗化和大众化,未真正创作出通俗明了的、易为普通百姓接受的文学作品。原因主要在于领导“白话文运动”的胡适等学者,接受的是西方精英教育,他们倾向于知识分子阶层典雅化的审美趣味,在文学语言运用问题上,他们从学术观念和学术资源上均受到西方思想影响,在“白话文运动”中多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指导运动的开展,没有真正地走向民间,融入民众,导致后期的文学语言出现了欧化的倾向。与他们不同,徐嘉瑞对文学语言的运用是以“平民文学”思想为基本立场,他的文学思想不仅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也受到他生长的这片土地——云南民族民间文化的影响,他在提倡使用白话的同时,更对来自民间的方言俗语有一种天然的喜爱,在白话语言的资源上,徐嘉瑞更主张是通过向民间学习获取,而非一味欧化,提倡学习民歌民谣,创作出了能反映民众审美趣味的文学作品。所以在胡适等学者走上了文学语言欧式化道路之时,徐嘉瑞的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仍保持着浓郁的民间色彩。
(二)使用云南民间方言俗语
语言是文学作品的重要载体,语言的出现和运用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并逐渐内化为人类的思维方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陈独秀等学者认为文言是承载中国封建思想文化的载体,要想建立民主、平等的新社会,就必须反对文言文,反对文言文代表的封建文化,建立起以白话文为代表的新的思想体系。在文学革命中,对于如何运用白话进行文学创作,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胡适等学者主张从西方文学名著中获取语言资源,胡适说“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做我们的模范”,“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2]54。胡适的学生傅斯年也在《怎样做白话文》中提出“直用西洋词法”来创作白话文学。于是“白话文运动”后期出现了文学语言欧化现象,左翼文学家批评他们使用的文学语言并不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仍反映的是资产阶级权贵的思想,瞿秋白批评这些“心肝脾肺都浸在‘欧风美雨’里”的学者,“对于中国社会的价值,真正没用,同样的没用。”
徐嘉瑞自幼生活的云南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他是听着大理白族的歌谣和传说故事,受着民族民间文化的熏陶成长起来的,他对于来自民间的方言俗语有着本能的认同。云南少数民族的普通百姓把日常口语随手拈来,整合成歌,唱起来自然亲切,这些民间方言俗语就成了徐嘉瑞文学语言的宝库,这是徐嘉瑞在文学语言运用上与胡适等学者最大的区别。
方言多指云南本地语言,俗语是指在民间流行的固定的词语或句子,徐嘉瑞感受到民间方言俗语自然自在的质朴之美,也喜欢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使用方言俗语。云南方言在徐嘉瑞的杂文中多见,如《妻的问题》中的“土咧土气”、“脑后的一条尾巴,也老是梳着理着拖着摆着”;《一对恋人》中提到的“婆娘”、“应当要以我为主位才合”;《么台了》一文的标题“么台了”,还有《忏悔》中的“佩服了佩服”等语言,均是云南昆明本地方言的表达方式,体现出明显的语言地域性。徐嘉瑞的戏剧创作中,尤其是花灯戏,由于是民间土戏,在人物对话里更是常用云南的方言,如《姑嫂拖枪》中王大嫂的唱词:“这两个死砍头的,把我的男人杀了,把我家的谷子烧了,又把我搭(和)我的姑太拉了出来,要整哪样?”,“天啊!死砍头的,你来把我杀掉,我倒能挨(同)你去”等,其中的“要整哪样”意思是“要做什么”、“挨”与“搭”都是“和”的意思,这些语言表达都是云南方言。另外,徐嘉瑞也常将民间俗语用于戏剧创作中,同样在花灯戏《姑嫂拖枪》中,为了表现民众对新中国建立的欢欣,剧中百姓合唱起了“十二杯酒”:“五月里,看樱桃,樱桃花开似火烧。樱桃花开红似火,花烧火了天王庙。六月里,荷花香,五星红旗真好看。我家有的高粱酒,要与你们醉一场……冬月里,冬貝冬,糯米粑粑火上烘莫嫌粑粑不好吃,莫嫌火炉心不红:腊月里,梅花香,解放军来到云南。二十五省人都有,要与你们跳一场。”这“十二杯酒”原是产生于陕西的民歌,语言简短明快,传入云南后加入了本地的风俗特色,显得曲风流畅自然。
徐嘉瑞认为在文学作品中加入方言俗语,这些语言越俗越好,“越俗的越近于真,可以说越土越好,因为其中有真的生活,真的性情”[6]13。徐嘉瑞文学创作中运用的方言俗语体现出他文学思想的平民色彩,也为他之后文学创作倡导使用“大众语”提供了丰富的语言资源。
(三)使用“大众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至1922年逐渐落潮,中国社会局势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发生巨变。1924年在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增强了革命的力量,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来临。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同年7月15日公开宣布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并大肆捕杀中共党人,全国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中。1931年,日本侵华的步伐加剧,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这时,“五四”时期表现个性解放的文学逐渐转向表达更广阔的社会内容,与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联系在一起。徐嘉瑞亲历了社会的动荡,他的学生惨遭迫害使他痛心,白色恐怖的威胁使他惊心,作为一名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徐嘉瑞深感不仅应重视民众的创造力,更应通过文学唤醒底层民众,让他们加入革命队伍。随着“平民文学”思想的发展,徐嘉瑞将底层民众视为文学服务的对象,认为为了实现文学对民众的教育任务,文学创作用应使用平民大众可以理解的语言,创作者需实现文学语言大众化,要使用“大众语”。“大众语”提出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的崛起”,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影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们否定了“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认为“白话,是那时新兴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因他们阶级本身的缺陷,不能进一步干个彻底。他们只在字面上‘白’与‘不白’地兜圈,不敢深入到社会的底层去和大众相联系”[7],认为白话也只是资产阶级的特权,于是提倡文学创作要使用让底层民众真正“说得出,看得懂,看得明白”的“大众语”。
徐嘉瑞积极投身于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大众化”运动,认为可直接使用民间方言俗语进行文学创作,也认为知识分子可通过学习民间创作出通俗易懂语言。在徐嘉瑞文学创作中,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白话文时,文学创作的语言其实并未真正实现白话的浅显明白,如他在1924年发表的《日本女流小说家紫式部》中有这样的语言:“日本王朝时代,实为日本文学之黄金时代,在文学史上,放一大光明。尤以当时女流作者人才辈出,皆挥其绚烂之笔,以抒写其天才的作品。就中如《源氏物语》,实为此时期之代表作家也……紫式部既达于妙龄,乃嫁藤原宣孝。宣孝亦富于学琴瑟静好歹,生二女焉。然幸福不能永续,至长保三年四月,其夫宣孝遂抛弃其爱妻爱儿,长与亏世辞矣。紫式部之悲恸,已臻极顶。《源氏物语》,实紫式部之泪的人生观之结晶也。”[6]433这样的语言仍是文白夹杂,并不符合口语的通俗流畅。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40年代,徐嘉瑞受到政治思潮的影响后,文学创作主张使用大众语,语言更加浅近直白,如他在1937年创作的《中国的声音》:

该诗的语言简短有力,感情色彩更加浓烈,如口语般直接,使普通读者便于理解,语言具有更明显的平民性。此外,徐嘉瑞的《中华民族的歌唱》《全国总动员》《无声的炸弹》《二等兵陈龙》《飞将军孙桐岗》和《新从军行》等诗,均是用自由浅近的语言创作,通俗得如白话一般,符合底层大众的审美趣味。
在诗歌创作之外,徐嘉瑞部分杂文的语言甚至是将普通民众的口语未经任何加工地使用在文中,如《身分》中的“七乱八糟的说了一些,连自己也莫名其大舞台对过是些什么,算啦,算啦,不要再说啦。但上面是说些什么呢,也不得不表明一下,作为本篇的结束”[8]535;《反帝标语之被撕去》中的“现在桂系军阀快要倒台了,而满墙满壁革命化的标语又将映入我们的眼帘了,岂不快哉!说到这里,小伙计应该申明一下,小伙计并不是希望电杆墙壁都革命化起来就算完事,是希望中央和民众们都实行我们的标语,实行我们的口号,那才有深切的意义呢”[8]544;还有《烟袋师》中的“然则,管他妈的能不能,横竖我们只知道烟袋师是可鄙的,其他的如烟袋师一般的人也是可鄙的,我们只消明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不再加注解了[8]557”,这些语言不仅通俗,而且俚俗,在民众的教育程度不高的背景下,确是可以迎合普通大众的审美趣味,使杂文中的思想易被接受。
徐嘉瑞对大众语的支持和提倡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局势变化及其“平民文学”思想发展而展开的,是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具有浓郁政治色彩的文学语言,对激励民众的革命热情具有积极作用。不过站在今天文学的立场,反观徐嘉瑞创作中使用的“大众语”,语言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感染力被过多强调,文学语言的语气都过于绝对,表现出一种非此即彼的政治极性思维,文学语言的独立审美价值被大大削弱。对比来看,“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文学语言观颇有值得借鉴之处,他在倡导使用白话的同时,认为“文学之文,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其本义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陈独秀提出“文学美文之美”的四个要素是“结构之佳”“择词之丽”“文气之清新”和“表情之真切”,突出了文学语言之文学性的特质。
综上所述,文学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媒介,徐嘉瑞通过文学语言的选择和使用体现其“平民文学”思想,其“平民文学”思想认为文学创作的主体是平民,文学服务的对象亦是平民,所以徐嘉瑞的文学创作既使用民间方言俗语,也使用通俗易懂的大众语,创作出能为普通百姓接受和理解的文学作品。
[1]马 曜.徐嘉瑞全集:卷一[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4.
[2]朱德发,赵佃强.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五四时期白话文学文献史料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徐 演.徐嘉瑞略传[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51.
[4]熊朝雋.五四时期的昆明文艺活动[J].昆明师范学院学报,1980(6):48 -50.
[5]胡 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M].赵家璧,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86.
[6]马 曜.徐嘉瑞全集:卷四[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7]若 生.建设“大众语文”应有的认识[N].申报·本埠增刊,1934-7-4.
[8]马 曜.徐嘉瑞全集:卷三[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Language View of Literary Creation of Xu Jiarui Based on “Civilian Literature” Thought
WU Wanting
(School of Art and Culture, Yunnan Arts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Regarding the “civilian literature” as the core of his academic thoughts, Xu Jiarui attaches importance to both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common people on the literature development and the influence of literature on the common people.Based on this, Xu Jiarui takes the literary language as the medium for his literary creation to re⁃flect his thought of“civilian literature” through the selection and use of languages.Affected by different historical contexts, Xu Jiarui’s thought of“civilian literature” has always been deepened and expanded constantly.The use of the literary language by Xu Jiarui has also been adjusted and changed at different times, such as the use of ver⁃nacular Chinese as plain as ordinary speech,simple and unadorned Yunnan dialects and vulgarisms and colloquial popular dialect for literary creation.
Xu Jiarui; civilian literature; vernacular Chinese; dialects and vulgarisms; popular dialect
倪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