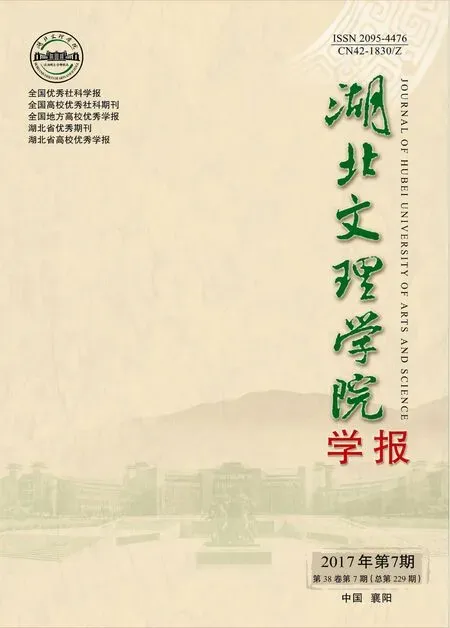也谈“误读”与“乱译”
——以美国《独立宣言》汉译本为例
曹秀萍
(湖北文理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部,湖北 襄阳 441053)
也谈“误读”与“乱译”
——以美国《独立宣言》汉译本为例
曹秀萍
(湖北文理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部,湖北 襄阳 441053)
从翻译中“误读”现象的定义和分类出发,以清末民初美国《独立宣言》传教士版汉译本和革命党人版汉译本为例,分别描述了“积极误读”和“消极误读”的典型表现以及由此引发的“乱译”现象,并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阐述了“误读”与“乱译”现象背后所隐藏的时代变革、翻译动机等深层原因及其特定的历史意义。最后,从哲学解释学角度出发,指出“误读”现象是译者视域融合不可避免的结果,要正确看待其客观存在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意义。
“误读”;“乱译”;《独立宣言》
翻译中的“误读”是指在异质文化碰撞中,译者作为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基于自身的时代背景、文化传统、价值取向、思维模式、语言特点等影响,对翻译文本及其所代表的异质文化所进行的选择、解构和过滤。“误读”现象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译者的“前理解”或所谓的“偏见”,即译者已具备的知识、体验、传统、价值观等“前结构”。吕俊[1]将这种偏见区分为积极偏见和消极偏见,前者是指那种帮助我们进入文本并在阅读与阐释过程中有建设性、合法性和生成性的先见,后者是指由于人们错误的认识或知识而造成的阻碍理解或导致错误理解的不合理的盲目先见。据此,我们可以将“误读”现象区分为积极误读和消极误读。积极误读又叫做主观性误读或策略性误读,是指译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翻译动机、完成特定的历史使命或迎合特定的翻译标准而有意识地将自身已有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认知体验等“先知先见”强加给原文。消极误读又叫做客观性误读或缺失性误读,是指由于译者双语能力不足、背景知识匮乏或认知体验欠缺等客观条件的局限所导致的对原文意义和风格的背离。无论是积极误读还是消极误读,其结果均会造成对原文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误译。
翻译本体论及其推崇者认为,误读和误译是对原文作者及译文受众的强暴与操控,故将其视为翻译实践中的败笔,斥之为“乱译”“曲译”,甚至“歪译”,唯恐避之不及。然而从社会文化和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误读和乱译现象从侧面折射出当时译者所代表的主体文化与原文所代表的客体文化之间的碰撞、拒斥与交融。其历时研究可管窥当时主体文化的时代局限与发展轨迹,探究翻译在拓展客体文化的概念外延、丰富主体文化的思想内涵、进而促进主客体文化交流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其共时研究可管窥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同翻译主体所秉持的翻译动机和政治立场,探究翻译作为政治工具在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中的积极作用。以下本文将以美国《独立宣言》汉译本为例,具体阐述其中的“误读”与“乱译”现象及其特定的社会意义。
一、《独立宣言》汉译本中的积极“误读”与“乱译”
自1838年美国《独立宣言》第一个汉译本(裨治文版)问世以来,至今已有十余种汉译本陆续出版。其翻译主体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清末民初以裨治文、蔚利高、林乐知为代表的美国在华传教士;二是清末民初以邹容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三是新中国成立后以郭圣铭、赵一凡等为代表的翻译研究者。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传教士版本和革命党人版本中的积极误读与乱译现象尤为集中,也更具代表性,突出表现在文本选择、思想内容和形式风格等三个方面。
(一)文本选择
清末民初,我国内外交困,民族危难,各界有志之士纷纷将目光投向国外,希冀通过翻译和借鉴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资产阶级革命经验,找到救亡图存的民族发展道路,从而掀起了一股以西方政治文本和政治小说为主要题材的翻译热潮。启蒙意义和教化功能成为当时翻译选材的首要标准,文学价值则退居其次。这种为满足自身需求和由于自身文化视域的限制而导致的对外国经典文学的忽视,本身就是对客体文化的误读。[2]美国《独立宣言》最初进入中国翻译界的过程亦是如此。如果说裨治文等在华传教士向中国民众推介这一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培育适合福音传播的政治土壤,完成“精神狩猎”的神圣使命,那么革命党人选择反复重译这一政治文本的目的,则是为了构建革命话语,点燃革命火种,启迪民智,振聋发聩,拯救国家,振兴民族。虽然翻译动机截然不同,但两派译者不约而同选择了该文本,并分别赋予了它不同的历史使命,这种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态度本身就是对该政治文本的积极误读。
(二)思想内容
传教士特殊的文化身份和基督教对社会变革及进步思想固有的保守与偏见,再加之鸦片战争前清廷严酷的禁教环境,大部分传教士版本都着重突出《独立宣言》的宗教法则,而对其核心思想“unalienable Rights(不可剥夺的权利)”及其革命内涵(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则普遍选择了漏读或模糊处理。直至20世纪以后,以林乐知为代表的传教士才较为忠实地将其译为“生命、自由与幸福”,以附和当时的启蒙话语和革命浪潮。与此相反,邹容等革命党人有意误读并削弱了《独立宣言》的宗教背景,将“权利”的理据归结为“天”,而不是“Creator(造物主)”。同时,着力拓展“Rights(权利)”的概念内涵,创造性地增添了“男女平等”“言论、思想、出版自由”等具体阐释,以突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诉求和“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主张。翻译的操控论认为,那些对自己所处系统的意识形态感到不满的人,会利用重写其他系统的元素来实现自己的目的。[3]以上两派译者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利用译者独特的“权利哲学”,对该文本的思想内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过滤与操纵,以实现各自不同的政治目的,这被认为是美国《独立宣言》在晚清中国传播过程中的最高成就[4],也是对原文最大程度的误读与叛逆。
(三)形式风格
原文作为一篇政论文体裁的革命宣言,语言风格不卑不亢,有理有据,义正词严,铿锵有力,但传教士汉译本却处处流露出对世人“安分守己”的规劝和对天朝“唯我独尊”遗风的恭顺。以裨治文版本[5]为例,译文语言采取文言文表达方式,以取悦天朝士大夫阶层;为避免忤逆清廷统治阶层,故意漏读原文中的革命语言,转而规劝世人遵循“上帝旨意”,语言风格整体较为温婉。而革命党人汉译本则大相径庭,译文语言文白夹杂,以启迪更多国人和平民阶层;为突出“民主、平等、自由”等政治诉求,译文以法律条文的形式逐一列出各项权利,并逐条进行阐释和延伸。然而最富有叛逆性的误读,莫过于革命党人[6]创造性地将原文政论文体裁转换为战斗檄文,不仅将标题改写为“北美合众国宣告独立檄文”,而且言辞间弥漫着十足的火药味,无形中增强了译文内容的煽动性和感染力。翻译的操控论认为,译文读者群的特点对采用什么样的策略翻译那些具有文化特色的词语、篇章和写作技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3]24上述两派译者为取悦读者群,都采用了以译文的可接受性为首要原则的归化翻译策略,但由于各自读者群的特点和翻译目的截然不同,双方归化的程度与方式也不尽相同,传教士趋于保守,而革命党人则趋于激进,虽然基调迥然,却都对原文的形式与风格进行了创造性地误读与误译。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的译者,无论是在华传教士还是革命党人,都不再仅仅是“往来于文化彼岸的艄公”,各自为翻译赋予了厚重的历史使命,前者将自己定位为“精神狩猎的拓疆者”,后者将自己定位为“唤醒国人反抗侵略的号手”。他们利用译者独特的“权利哲学”,通过对翻译题材的积极选择和对原文思想内涵、形式风格的积极误读,在译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革命诉求。这种积极的“乱译”既实现了译者自身的预期目标,又构建了革命话语,传播了革命火种,推动了社会变革。在这一意义上,翻译活动已不再仅仅是语际文字转换,而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更是一场为实现阶级目的、维护集团利益的政治对话。
二、《独立宣言》汉译本中的消极“误读”与“乱译”
撇开积极误读与乱译现象及其背后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姑且不论,在《独立宣言》诸多汉译本中,消极误读以及由此引发的乱译现象亦可谓俯拾皆是。如原文中的“Congress”一词,原本是指发表宣言时的“大陆会议”,但早期的传教士译为“衿耆(议事大臣)”,后来的革命党人译为“国会”,均不得其意。究其原因,应该是我国资产阶级革命相对滞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导致政治建制词汇在译文文化中出现对应空缺。又如原文中“Creator”一词到底该译为“上帝”“天”还是“造物主”?这一争议在早期的传教士和革命党人的汉译本中一直存在,至今在坊间仍引发热议,如学者范学德[7]就曾专门撰文,指出在当下流行的《独立宣言》中译本中,原文最重要的一句话“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被译为“人人生而平等”,这是“大错特错”,并且是“不应该出现的错误”。可见译者的宗教背景知识对解读和翻译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另一个消极误读和乱译的经典案例则是文本标题中的“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在被忽略了一个多世纪以后,终于有学者(如齐文颖[8]、杨玉圣[9]、李道揆[10]、黄卫峰[11]等)在考证勘察之后发文拨乱反正,指出该术语应译为“美利坚联合的各邦(州)”,而不是“美利坚合众国”,从而避免了对历史的误读。
总体而言,导致消极误读与乱译的原因大致可归结为三:一是主体文化的社会变革与时代发展相对滞后,导致客体文化中的一些新鲜事物译入时找不到对应的词汇而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或干脆漏译。二是译者对客体文化中的政治、宗教、历史、地理等文化背景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和认知体验,导致信息传达失真或失误。三是译者本身职业道德和专业素养不够过硬,对翻译对象不求甚解,缺乏必要的考证和校勘,导致以讹传讹,误导读者。其中,由译者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养的欠缺所导致的消极误读,以及由此引发的“曲译”和“歪译”,都是翻译伦理所不允许的,在翻译实践中应尽量避免。但由客观条件的局限和主观认知的欠缺所导致的消极误读和乱译,由于被刻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可供现代研究者沿着时间轴顺藤摸瓜,追溯这些误译所折射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迁的轨迹,故而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独立宣言》被反复重译超过十余次,却因种种“误读”与“乱译”而饱受诟病,“直到今天,我国却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独立宣言》中文本的标准本”[10]147,以致于有学者建议“中华美国学会成立一个小组,依靠集体的智慧,重新翻译美国《独立宣言》,……,最后译出一部可称为“信、达、雅”的《独立宣言》的中文本。”[10]150对此,笔者以为,这种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学术负责而精益求精、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固然可敬,但应谨防过犹不及,陷入客观批评主义追求终极“理想范本”的歧途。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认为,理解的过程就是理解者的偏见(即已有的认知和体验)所形成的特殊视域与文本的初始视域不断交融,最终实现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的过程。但由于理解者与原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存在差异,双方视域必然存在一定的偏差,可能会无限接近,但不可能实现视域的完全重合。同时,“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绝不会完全束缚于任何一种观点,因此绝不可能有真正封闭的视域。”[12]271任何一部堪称“信、达、雅”的经典译作都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必然会被后来的其它译本所超越。因此,我们要用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正确看待历代译本中的误读与误译现象及其特定的社会意义。
[1] 吕 俊,侯向群.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视角[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2] 崔丽芳.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的误读现象[J].南开学报,2000(3):47-52.
[3]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ng of Literary Fame[M]. London: Routledge Co.ltd., 1992.
[4] 潘光哲.“革命理由”的“理论旅行”——美国《独立宣言》在晚清中国[M]//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北京:中华书局,2008.
[5] 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节选)[M]//近代史资料.刘路生,点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40-42.
[6] 北美合众国宣告独立檄文[N].民国报,1912-1-11.
[7] 范学德.美国《独立宣言》翻译犯了大错?[EB/OL].(2016-07-23)[2017-02-09].https://sanwen8.cn/p/24743Gs.html.
[8] 齐文颖.《独立宣言》是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标志吗?[J].世界历史,1985(1):46-50.
[9] 杨玉圣.《独立宣言》史事考[G]//齐文颖.美国史探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0] 李道揆.美国《独立宣言》中文本译文的问题及改进建议[J].美国研究,2001(2):146-150.
[11] 黄安年.也谈美国《独立宣言》中译本[EB/OL].(2005-04-09)[2017-02-09].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13286&cid=21.
[12] GADAMER H G. Truth and Method [M]. New York: the Continum Publishing Co.,1975.
(责任编辑:刘应竹)
On Misinterpretation and Distortion: Taking Chinese Versions ofTheDeclarationofIndependenceas an Example
CAO Xiuping
(College English Department, Hube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Xiangyang 441053, China)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of the phenomenon ofmisinterpretation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paper describes typically positive and negative misinterpretations and the consequent distortions which are manifested in the Chinese versions ofTheDeclarationofIndependencetranslated respectively by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China and revolutionarie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lso, it demonstrates the underlying reasons behind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ose phenomena, inclu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imes, the purpose of translation, etc.,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ocial context then. Furthermore, it points out that mis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from the fusion of the translator’s horizons, and thus its objective existence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under certain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deserve proper recognition.
misinterpretation; distortion;TheDeclarationofIndependence
2017-04-13;
2017-06-21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4G328)
曹秀萍(1976— ),女,湖北襄阳人,湖北文理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讲师。
H085.3
A
2095-4476(2017)07-008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