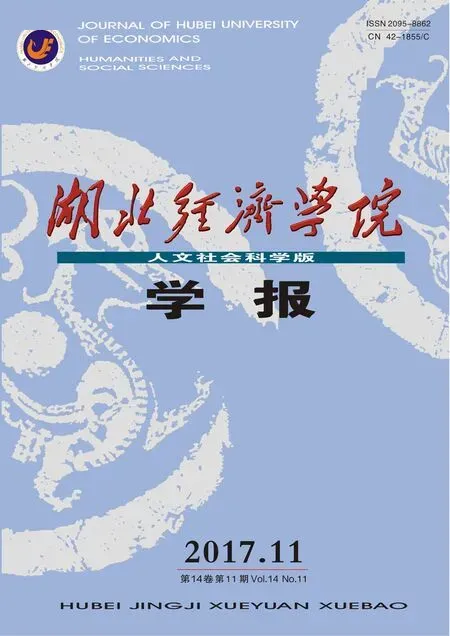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与沈从文的《边城》之现代主义主题的对比
杨秀丽
(南京晓庄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与沈从文的《边城》之现代主义主题的对比
杨秀丽
(南京晓庄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和中国作家沈从文作为各自国家转型时期重要的现代主义小说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对舍伍德·安德森和沈从文的比较研究涉猎较少,可参考的资料有限。本文将瞩目两位作家的代表作《小城畸人》和《边城》,侧重论述现代主义主题在这两部作品中的不同呈现,结论部分同时也指出他们都在各自的作品中传递了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终极关怀。
舍伍德·安德森;沈从文;《小城畸人》;《边城》;现代主义主题
一、引言
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被福克纳奉为 “我们这一代作家的父亲”[1],但大众对其作品的接受并不如福克纳期许的那样:事实上安德森除了在发表其成名作《小城畸人》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内受到热捧外,在其后的漫长时间内很少被人提及甚至被遗忘,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评论界才重新评估其作为美国现代主义文学引路人的重要地位,自此开始尝试对其作品进行多角度的阐释。沈从文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文学家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直以来备受关注,《边城》是其小说创作的一个制高点。国内近三十年来围绕沈从文和外国作家的比较研究覆盖了部分欧美作家,其中最主要的成果集中在与福克纳的平行研究上。
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对舍伍德·安德森和沈从文的比较研究涉猎较少,能够查找的文献资料也非常有限。本文认为舍伍德·安德森和沈从文作为各自国家转型时期的重要的现代主义作家,以自己熟悉的家乡风土人情为题材,创造了杰出的、显性的“小城文学”的文本,借由比较《小城畸人》和《边城》中体现的现代主义主题,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作家作品及其文学影响。
二、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与沈从文的《边城》之现代主义主题的对比
(一)《小城畸人》——“爱的失落”
美国社会在从手工业文明向机械文明转变的过程中,人们无法适应物质至上、人文精神匮乏的工业社会,由一开始的无所适从到逐渐变得悲愤、失望,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丧失了对自己生活的掌控能力。安德森笔下的“畸人”大都敏感、富有洞察力,他们怀揣梦想与追求却不能以恰当的方式诉诸于人,只得被迫封闭自己,游离于所置身的社会边缘,甚至于为该社会所不容。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持续冲突让这群人日益孤独,“当这种孤独发展到极致,畸形便成了他们生命的特征”[2]。
《小城畸人》中形形色色的主人公在不同程度上都期望与人亲近以期排解自己的孤独和悲伤,但他们渴望爱与理解的努力都被交流的障碍不费吹灰之力地化解殆尽。虽同是交流障碍,但“畸人”们的症状却各不相同。
《小镇畸人》中的大多数畸人属于对他人封闭、对自我倾诉的人。他们就像是黑暗里的舞者,在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安全的空间里才能释放出激情澎湃的思绪。他们所有的想法只能倾诉给自己,或者给非人的实物听。一旦面对活生生的人,他们便不知该如何表达心声。《上帝的力量》里的柯蒂斯·哈特曼是温斯堡长老会教堂的牧师,习惯于星期日的早晨在钟楼上的小屋里祈祷,那一小方天地使他卸下庄重、寂静的外表束缚,尽抒内心所想。《孤独》中的伊诺克“开始依靠灵敏的想象力来创造他自己的人物,他可以和他们进行真心的交谈,对他们解释他无法对活人解释的事情”[3]。《纸团》里的里菲医生终日 “一个人在散发霉味的诊室里不停地忙碌着”[3],他不是忙于治疗病患,而是每当自己独处有思绪奔涌出来的时候他就要在纸片上匆忙记录下来,纸片越积越多,直到最后一叠纸片变成一个硬硬的纸团,他便将纸团扔掉,再重新来过,堆砌新的纸团。里菲一生沉醉于他的这个周而复始的纸团游戏,因为这是他排遣烦恼的唯一方式。他从不刻意主动地接近旁人并与之交流,他只有在妻子在世的时候会偶尔透露给她一点他记录在纸片上的想法。
安德森笔下还有一类畸人属于愿对他人倾诉、但交流无果型的人。这种交流障碍或表现为词不达意,或表现为无意义的喋喋不休。他们是发自内心地想和人交谈,但他们总是心口不一。纵然他们有千头万绪想要对人表达,可是他们往往拙于言辞,恰当地表达自我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无法逾越的任务。《母亲》中的伊丽莎白极度关心儿子,希望儿子不要囿于温斯堡这个小镇,而要去往更宽广的地方追逐理想的生活。她原本想要循循善诱地让儿子明白自己的苦心,话到嘴边却变成了不痛不痒的 “我想你应该出去和男孩子们在一起。你老是在家里闷着。[3]”《古怪》中的埃尔默·考利是个进城做小生意的农民。在温士堡,他感觉受到排挤,为正统人士所不容,没有人愿意接近他,他觉得是因为自己的言行不合常规,人们对他有偏见。他懊恼之余找到乔治·威拉德,因为“他认为乔治·威拉德是属于这个小镇的,是小镇的典型”[3],他渴望倾诉自己不打算“古怪”下去的决心,然而却向无辜的乔治大打出手,暴力成了他向别人表达自我的方式,最终反而让自己显得更加古怪。《异想天开》中的乔·韦林时时处在讲话的欲望之下,他的讲话不分时间、场合,一旦他想讲话随便逮个人就行,更重要的是他讲话的内容往往使听者困惑,因为所讲之事跟听者无关、跟当下的事也无关,于是人们避之犹恐不及,乔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怪人。乔·韦林不在乎听者是谁,他只要听者的在场,满腹的思绪是他一个人承受不了的压力,于是他寻求与他人的交流,可是他误以为只要说出口了就是交流,事实上他的语言没有任何交流功能,这种无意义的喋喋不休于事无补,使他陷入了表达的困境。
现代主义小说强调表现人的主观心灵世界,具有内倾型特征。安德森在他的小说中会淡化或虚化人物的语言、行为表象,他所关注的始终是“事物的本质”[4]。为此他抛开社会、文化、伦理对人物形成的桎梏,尝试从人物当下的处境出发,以当局者的身份和眼光认识和了解世界,从而获得与人物内心活动相似的心理体验。安德森在他的艺术创作中并不以详尽描述见长,他只撷取能透射人的内心情感的片段着墨,譬如夕阳西下的农田,恣意摆动的双手,屋前年代久远失修的门廊等。正如马尔科姆·考利所说的,“安德森有着归纳的天赋,能于瞬间浓缩整个的人生[5]。”在《小城畸人》一书中安德森不动声色地披露了主人公们彷徨不安、平淡琐碎的生活中的珍贵片刻,并通过肢体动作、人物话语和顿悟等手法将他们呈现出来。正是这样的触动人心的时刻使得对畸人群像的“审美”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可能,因为这样的时刻以一种强烈而震慑人心的方式揭开了被误解的面纱——畸人们是一群满怀美好理想和愿望的人,他们渴求爱与理解的需求没有错。在温斯堡镇这个人与人彼此隔膜的小镇,畸人们都愿意接近《温斯堡鹰报》的年轻记者乔治·威拉德,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年轻人涉世未深、敏感、富有同情心,代表着小镇的精神。因此,乔治自然也就成了众多畸人们吐露心声、自然展现美好时刻的见证者。
《小城畸人》中物质上和精神上都窘迫的“畸人”们在笔者看来不仅不会引起人的厌恶感,反而会激发人的理解和同情。安德森对这些畸人的精神追求的认可和肯定不时见诸于笔端,并不吝流露自己对这些行为怪异的人们深深的人文主义关怀。在安德森眼里,畸人们一如《纸团》中描述的那样,就像“果园里生长的畸形的小苹果”,然而“只有很少的人知道畸形苹果的甜滋味”[3]。
(二)《边城》——“爱的守护”
如果说在《小城畸人》一书中,爱被曲解、被遗忘,那么在《边城》中爱则得到了守护。沈从文在《边城》一书的《题记》中这样写道“我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来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即或这支笔如何笨拙,或尚不至于离题太远。[6]1”作家钟爱湘西这方热土及生活于此的子民,在他的笔下,人们是正直、诚实的,他用尽笔墨书写他们伟大而又平凡、美丽而又琐碎的生活,坦言“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地写下去[6]。”
在《边城》一书中,沈从文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川、湘交界处的古镇茶峒。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小镇,作家对它进行了艺术加工,诗化了它的美好。作家选择这样一个地方作为故事的发生地,有着深刻的用意:一方面源于对湘西故土的眷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此地位置偏僻,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避免受到大城市意识形态的冲击,生活于此地的人们依然可以保持宜居的生活状态,从而为人物角色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保障。纵观《边城》的描述,里面的自然风景清新得直抵人心,如饮醇酿。民风淳朴,人们坦荡相处,热心相助。尽管小说以爱情为叙事主线,男女主人公在故事的结尾均未有爱的归宿,然而全书却没有充斥爱恨纠缠的痛苦、愤懑的灰色基调,取而代之的是淡然、温馨的氛围,这不得不让人向往沈从文所营造的梦幻般的、为爱所笼罩的文学世界,可以说沈从文是一个行走在湘西的浪漫的诗人。
纵观全书,《边城》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纯净无暇的、童话般的湘西小城,对充斥着物质利益、尔虞我诈的现代社会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抒发了现代人内心的渴求。在这部小说的描述里,爱得以被理解和维护,体现在两个方面:
人与自然的和谐。茶峒城边的小溪为川湘来往孔道,由于当地没有财力搭建桥,人们便依靠渡船往返。“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做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6]。”字里行间流露出茶峒古城美如诗画的风景沁人心脾,让人流连忘返。河中游鱼来回穿梭,水中倒映着高山和房屋。人们傍水而居,依靠得天独厚的条件酿酒、卖山货,做着各种小营生。小城中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如下面这段描述:“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看天空被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十四中寨逢场,城中生意人过中寨收买山货的很多,过渡人也特别多,祖父在溪中渡船上忙个不息[6]。”小城的空气中充满了泥土、草木的芳香,虽然这里的人们物质不是很富足,但是对于大自然已然赋予他们的财富很知足。
人与人的和谐。首先,普通人之间相处融洽。书中讲到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但还是有渡客心中不安,抓起一把钱撒到船板上,渡船工见状就会很生气,拾起钱如数返还给那人,并申明自己是有口粮和公饷的人。平日里在小城里可以随处看到几个中年妇女穿着浆洗干净的蓝布衣裳,躬着腰在阳光下一边说话一边做事。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安详。甚至于住在吊脚楼里的妓女,如果有相中的水手,也就不谈钱的事,结下恩情,如文中所言:“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6]。”其次,亲人间血溶于水。老船工的女儿与一戎兵相识暗结珠胎,意欲私奔,但想到孤独的父亲还是放弃了远走他乡。那位兵士见她无远走的勇气,同时也不想毁军人的名誉,便服毒自尽。船夫女儿念及腹中骨肉,选择活下来。已经知悉情况的老船夫没有怪罪女儿,权当没有这回事。待小孩生下来之后,船夫女儿故意喝了很多冷水死去了,去赴和兵士的生死之约。老船夫将遗孤抚养长大,取名翠翠,翠翠长大后对祖父也非常尊敬和孝顺。从翠翠这一家来看,无论是老船夫父女之间,还是老船夫爷孙之间,都流露出了浓浓的亲情。亲情以一种更为浓烈的方式体现在船总两个儿子天保与傩送身上。两兄弟同时爱上了翠翠,但翠翠心仪的是傩送。大哥天保主动退出,并决定离开家乡去大城市闯荡,但坐船时不幸溺亡。傩送心怀内疚最后也选择离开茶峒。两兄弟以各自的方式选择不伤害彼此,这与绝大多数小说中兄弟反目的情节天壤之别。再次,爱人之间情深意长。傩送和翠翠属意彼此,尽管傩送在故事的结尾因为大哥的去世不能释怀而离开茶峒,翠翠像祖父那样当起了摆渡者,日复一日地等候着恋人的归来。
沈从文在《边城》中刻意营造了桃花源般的小城氛围,将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降到最低点,他这样的良苦用心旨在向世人昭示:面对充斥着利益纷争的世界他坚信人性中纯良的一面是最值得被放大和发扬下去的,人们需要从传统文化和美德中吸取能量,在心中构建和固守一个不被打扰的理想世界。
三、结语
结合两位作家的社会背景不难发现:安德森所处的时期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刚刚兴起的阶段,新型经济极大地冲击了原有的手工业经济;沈从文身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当时国内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很大,基础薄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对边陲小镇的影响微乎其微。一言以蔽之,在这种转型时期中,旧的体制尚未完全褪去,新的秩序还有待完善,地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小城镇易受新旧体制更迭的影响,这种影响或大或小。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和沈从文的《边城》所描画的小城是他们情感的寄托,也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似向我们展示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一个中西部小镇居民的写意简笔画,而沈从文的《边城》则铺陈了一幅二十世纪初叶中国湘西一个边陲小城的原生态画卷。两者显然具有不同的地域审美特征,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地域特征才滋生了世界文学范围内繁花似锦的“小城文学”文本。
尽管《小城畸人》和《边城》在表现现代主义主题上侧重点不一样,但无论是“爱的失落”还是“爱的守护”都折射出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怀念和不舍,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建造起来的世界是作家所珍爱的。两位作家都对处于社会变动期的国家的命运倾注了深深的忧患意识,引领读者思考如何寻求复兴民族的正确道路,极大地表现出了作为文化工作者的社会自觉性和责任感。无一例外,他们都在各自的作品中传递了对人性的关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终极关怀,在此现代主义主题得到了升华。
[1]Bradbury,Malcolm and David,Palmers,eds.The American Novel and the Nineteen Twenties [C].London: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td.,1971:122.
[2]叶巧莉.现代主义的显形——试析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说艺术.[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9,(5).
[3]舍伍德·安德森著.刘士聪译.小城畸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4]张强.舍伍德·安德森研究综论[J].外国文学研究,2003,(1):148.
[5]Cowley,Malcolm.Introduction to Winesburg,Ohio.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60.ⅶ.
[6]沈从文.沈从文精选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
杨秀丽(1982- ),女,江苏盐城人,硕士,南京晓庄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