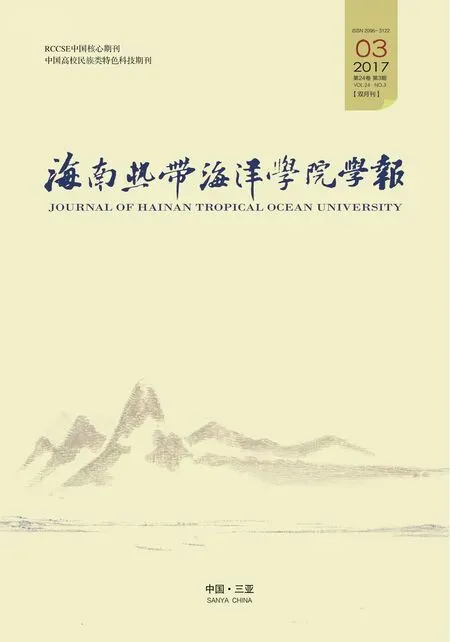论“零度写作”与白描手法
鲁彦臻
(广西大学 文学院,南宁 530004)
论“零度写作”与白描手法
鲁彦臻
(广西大学 文学院,南宁 530004)
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理论强调作者思想感情的零度介入,提倡语言形式的自由与写作主体的消解,希望以此来挽救当时西方学界中的写作危机。中国的白描手法与零度写作有着许多的共通性,将二者相互对话,有助于我们辩证地发现中性叙事模式下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历史传承。
罗兰·巴特;零度写作;白描;叙事方式
二战之后的西方思想界充斥着一种虚无主义的悲观情绪。存在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下,罗兰·巴特针对萨特的介入式的写作在1953年出版的《写作的零度》中提出了“零度写作”的理论主张。萨特认为,作者应该在作品中具有主动性,以人道情怀的抒发和伦理自由的高歌为创作动机,针对这种喧嚣一时的文学功利性的写作主张,巴特提出了自己的反对主张:“零度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写作和非语式写作,可以准确地说,这就是一种新闻式的写作……这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有或者说是一种纯洁的写作。”[1]这一点在加缪的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的小说中融入了大量的“零度”创作手法,以一种冷淡的不介入的零度艺术手法,展现出一种作者“不在”的叙事风格。
加缪的“零度”叙事风格打破了西方传统的小说写作模式,挣脱了古典主义写作束缚,就其小说中独特的叙事手法而言,与中国传统小说中的白描写作手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将名声大噪的后现代写作手法与中国传统叙事手法置于同一桌面上让其相互对话,难免会有牵强造作的嫌疑,但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在某一种意义上,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引合而相与比较的;在另一种意义上,每一事物都是个别而无可比拟的。”[2]笔者将跨文化从“零度写作”和白描手法的对比中有所启悟,希望发掘出中西叙述观异同之后的叙事语境和历史传承。
一、 理论起源方式
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理论的提出不仅受制于当时统治阶级话语专权的时代背景,同时也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首先,在古典主义盛行的大环境中,传统权威的文学神话色彩浓郁,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式、振臂高呼式的写作方式一度占据了文学界中的主流地位,文学逐渐演变成一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附属品和传声筒。紧随其后的革命式写作、马克思主义写作等与利益阶层挂钩的权利式写作,都使得语言渐渐丧失其应有的自由属性,成为统治集团进行意识形态宣扬的传播利器。这种为统治阶级高歌猛进的古典主义的写作方式虽凸显出语言的工具性却忽略了语言特有的自由属性,给当时的文学界带来巨大的语言写作危机。其次,在世界大战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战前理性主义所倡导的理性规律开始遭到人们的质疑和反对,与此同时一直扮演着全知全能上帝角色的作者也逐渐被人们所怀疑和批判。在如火如荼的质疑声中,语言学慢慢地进入了人民大众的视野之中。索绪尔的“语言不再是各种‘内容’的字词要素的总和,语言应该是一种不再依附于外界的一个独立的形式系统”[3]使巴特深刻的意识到“文学仅仅是语言和符号系统,文学的本质不在于它所传达的内容,而是系统本身”[4]。在语言学崭露头角之前,也有不同时期的文学家尝试过将目光投向语言本身,譬如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开始追求语言组合的自由与随性,福楼拜的“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写作风格也强调作家对语言的精雕细琢等,直到加缪的小说《局外人》的出现,一种白色的、中性的、无动于衷的写作风格得到了巴特由衷的赞赏,它的出现不仅有助于巴特“零度写作”理论的提出,更创造出一种可实现、可参考的实践范本。
与顺应时势而出的“零度写作”的理论相比,中国白描手法作为一种文法术语的诞生则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初出现在中国古代画论中的普遍术语“白描”,初始时指彩色画卷的底稿或未上色的图画、壁画,后多寓指一种保留流畅潇洒线条的独特绘画技法,有别于落墨、烘染等其他绘画技巧。随着书法用笔方法被引入绘画技巧之中,加之人们对于绘画线条造型水平的提高,使得这些笔墨清秀隽永的绘画手稿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美感,从唐代吴道子的“焦墨线中,略施微染”[5]到宋代李公麟的“扫去粉黛、淡毫清墨”[6],白描的出现和深入发展,标志着一种新的绘画风格的兴起和繁盛。而将白描这个画论术语引入小说批评领域的第一人则是金圣叹,他在《水浒传》第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描写雪景的文字后面批道:“寻着踪迹四字,真是绘雪高手,龙眠白描,庶几有此。”[7]但使人略感缺憾的是,金圣叹仅从比喻和对画论手法的借鉴这一角度来使用“白描”这一术语,并没有一种将其作为文学批评术语的自觉性和前瞻性,但令人欣慰的是,这一实践启发了后来评点者关于这一方面的文论意识和文法觉悟。不过,这也使我们后来在研究“白描”这一文论术语时要清楚地意识到:作为文学批评术语而确立的“白描”,其最初是从中国古代的绘画术语中引荐过来并实现了从画论术语向文学评论术语的一次转变。直到清代的文学批评家张竹坡才真正地将白描确立为一个纯粹的文学评论术语,并且加以相关的理论论述和文学批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这一术语在文学评论界的使用。到了近现代,鲁迅在评点《孽海花》时对白描的艺术特点拓展出更深的描述和解释,并在理论史上提高了白描手法的文论高度。
白描手法从古代画论术语向中国文法术语的转变有别于一般文法术语的发展轨迹,相较于为解决古典写作危机而出现的零度写作,这二者在理论起源方式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作为一种崭新的写作方式出现的零度写作有着它特定的时代背景,尽管白描与其产生时的时代背景有着显著的不同,但是二者却不约而同的表现出一种“零度”的写作气息。
二、 叙事方式的异同比较
我们在阅读传统小说的时候往往会发现作者对作品的意图以及情节发展走向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读者总能找到隐匿其间的主体意识,甚至能够挖掘出作者潜在的世界观、价值观等。如果我们早已习惯了传统小说的写作模式的话,那么在面对作者“不在”的叙事风格的时候就会有茫然无措之感。通过对加缪的小说和中国白描小说相对比,我们试图发现这两种给予读者以巨大的自主意识和自由空间的写作风格在叙事模式上的异同。
(一)叙事语言:直陈式的言简意赅
无论是“零度写作”还是白描手法在塑造人物形象或者叙述故事情节的时候,语言使用都显得简约凝练而不加修饰,无论作品中的人物对话或者情节描写都没有过多的侵入感性化的语言话语,甚至连作者的情绪踪迹都显得无路可寻。
加缪的小说《局外人》中对于莫尔索百无聊赖在阳台上望着窗外发呆的时候有这样一副画面描写:“两个穿海军服的小男孩,短裤长得过膝盖,笔挺的衣服使他们手足无措;一个小女孩,头上扎着一个粉红色的大花结,脚上穿着黑漆皮鞋。他们后面,是一位高大的母亲,穿着栗色的绸连衣裙,父亲是个相当瘦弱的矮个儿,我见过。他戴着一顶平顶窄檐的草帽,扎着蝴蝶结,手上一根手杖。”[8]17在这里,我们是很难看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色彩的,唯一有的只是一些形容词堆积出来的空白的、直接的铺陈式的语言拼图。不仅对于人物描写是如此,甚至关于对话,作者也采用了一种无所谓的话语态度应对,譬如文中一开头就写了他母亲的死亡,当门房问他是否想看一看他母亲的时候,他直接回答:“不想。”门房又再次问他“为什么?”,他又再次回答“不知道”,这样的冷漠的、无所谓的对话在文中还有多次重复,当玛丽问他是否愿意和她结婚的时候,莫尔索依然表示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结不结婚都行,如果她想,我们就结”[8]25,在后来关乎自己生死的审讯之中,作者更是把这种零度的情感色彩发挥的淋漓尽致:“‘您就不怀着希望了吗?您就这样一边活着一边想着您将整个儿地死去吗?’我回答到:‘是的。’”[8]79看完加缪的小说后,我们再来谈谈白描情节的典范之作:“却说那众庄客引了二十余人,拖枪拽棒,却奔到草屋下看时,不见了林冲,却寻着踪迹赶将来。只见倒在了地上,花枪丢在了一边。”[9]金圣叹因这一段第一次在文学批评史中运用了白描这一术语,可见,这一段的白描运用确实深入人心,“踪迹”二字以简洁的笔墨形象的写出了雪景的苍茫无垠和落雪深深,在语言的简约干练之外更多了生动传神的艺术美感。鲁迅对于白描的应用也是得心应手,小说中不少人物描写都能寻觅到白描的身影:“还是乱蓬蓬的须发;苍白的长方脸,然而衰瘦了。……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去了光彩。”[10]208“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地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11]“华大妈听到‘痨病’这两个字,变了一点脸色,似乎有些不高兴;但立刻堆上笑,搭讪着走开了。”[10]45透过简洁的人物线条、直观的语言叙述所塑造出来的形神兼备的人物形象背后,我们可以发现白描的作用简直功不可没。
白描与零度写作在叙事语言上确实有许多共通之处,日常事物在小说中如同镜子一般被完全还原出本来面貌,给人一种寡淡、素净之感,语言也无任何烘托和修饰的华丽辞藻,营造出脱繁去俗、融形于色的独特艺术形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掇其精神”的话就能发现二者的不同之处:相对于零度写作中作者意识绝对脱离于文本中的零感情添加,白描“以质朴的文字抓住描写对象的特征,以叙代描,……以少胜多,平中见奇”[12],就如同鲁迅所说的“有真意,去粉饰” 一样融入作者淡淡的温情真意流露于其中。
(二)叙事视角:作者“不在”
“零度写作”和白描都有一种主体“不在”的特征,表现为作品中不再有作者的影子来参与作品的创作,在写作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白色的、中性的写作状态。在这里,他们都是强调的是作者感情的隐匿,期待叙述者能够以一种不介入的态度和旁观者的视角去对待所描述的事实和事件。
尽管我们在读《局外人》的时候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文中是以第一人称“我”为中心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展开,但是作为读者仍然会发现“我”始终以一种“局外人”的姿态矗立于文本之外。在文本的内容叙写中,无论是“我”为母亲奔丧中充斥着的大量毫无感情色彩的环境描写还是“我”在杀人的时候打出的四发子弹仿佛也只是“我在苦难之门上短促地叩了四下”,又或是我在被捕面临审讯的时候,“我倒挺有兴趣去见识见识是如何打官司的,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打官司呢”这种无所谓的态度,都能发现作者仅仅是一个文字记录者,文中场景的转换、“我”的任何所思所想,仿佛仅仅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与他人无关,与世界无关,与作者更是毫无瓜葛。情节的发生依赖于一幕幕场景的转换和人物的更换来加以推动,如此既能保证作者的不介入的姿态又能完美的呈现出完整的故事情节,同时又能增加读者的自由阅读空间,因而在结构中也实现了作者“不在”的全局呈现。与零度写作中袒露无疑的作者“不在”的叙事特征相比,白描中作者的视角淡化就显得含蓄许多,这一点可以从《儒林外史》中发现一二。吴敬梓在描写周进撞号板时这样写道:“周进一进了号,见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不知道是悲从中来的发泄,还是灵光乍现的奋力一搏,周进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13]作者以神来之笔描绘了周进为考取功名悲伤寻死的可怜可悲可笑之事,虽然作者万分同情他,但笔力刻画之处始终与叙事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即站在高处俯瞰众生,以喜剧的形式透彻的展现悲剧的内容。亦或是鲁迅的《祝福》中有一段关于祥林嫂的精彩描写:“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象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10]167这段纯粹的线条勾勒描写,笔力深刻,着墨不多却能准备的把祥林嫂的困苦的生活、所面临的处境和当时的时势描绘的生动传神、极简意深,与此同时作者始终以一种不在场的叙事口吻进行有距离的人物描写,近乎原生态的逼真写实给读者更加真切的现场感和冲击感。
如果从叙事视角来看加缪的零度写作实践确实达到了巴特所提倡的中性的和惰性的形式状态,但是巴特同时发现,无论写作语言多么透明、中性,无论作者怎样的置身事外,都无法达到一种全然的绝对的作者“不在”的这样一种写作状态,“零度的写作”理论从哲理层面看只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家园。但是这种写作模式消解了传统的写作模式和统治阶级的意识枷锁,让语言来主导文本表达内容和形式,还原了语言原始形态的本真色彩。“零度写作”理论的中国实践形式——白描,在叙事视角方面确实显露出作者“不在”的主体自由,但仍具民族特色,即以叙述者的缺席来彰显意义的存在,这一点类似古人常常提到的“钟鼎象物”“温娇燃犀”。道家强调“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在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下形成的白描手法以不言而言,无形无迹的写作手法自然呈现出言意之美。
(三)叙事情节:片段与谋篇
加缪的小说因为多采用白描的语言进行非感性化的情节叙述,所以在情节的具体推动上主要依赖于简约凝练的文字融合以及片段式的情节连接。在《局外人》中开头一句:“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8]1震惊了世人,这样浅显直接的文字流露出来的是一股冷漠惨淡的冰冷气息。随之而来的就是“我”参加母亲葬礼的情节刻画,在这一幕场景中,充斥在读者眼前的是由“我”的视线交织出来的大量的人、事、景物组成的一幕幕机械画面。之后“我”与玛丽相处的过程、在海滩上杀害阿拉伯人的记叙以及逮捕后的审讯经历即使都是故事的主要情节,但是在情节的衔接上似乎没有什么必然性和规律性,每一个故事情节似乎都是独立的,如同被作者串联起来的片段一般,乏善可陈的故事情节却因为语言的高度凝练并没有妨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构建。
相对于加缪采用的多重艺术手法搭建起来的艺术象牙塔,白描在情节的设置上就显得平淡许多。曹雪芹也是一位十分擅长白描的大家。他精于绘画,在情节设置中对白描手法有诸多借鉴却往往又不露声色,笔墨不多却心思巧妙,使我们从有限的文字中看到丰富而广博的历史内容。《红楼梦》中女伶龄官的故事就很有代表性,她的情感线暗暗埋藏在在十八回、三十回和三十六回中,三部分层层递进,明断暗续,虽然每一回中对龄官着墨不多,但是却将龄官和贾蔷之间纯洁含蓄的情感描写的细腻婉转、深情动人,正所谓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鲁迅在继承了古代白描小说的基础上,将传统的白描艺术推向了一个新高度。譬如:“她打了一个寒噤,连忙住口,因为她看到七大人忽然两眼向上翻,圆脸一仰,细长胡子围着的嘴里,同时发出一种高大摇曳的声音来了。‘来……兮!’七大人说。”[10]316淡淡几处细笔勾勒便将一个油头滑脸的土豪姿态描绘得栩栩如生,通过鲜明的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谋篇布局,展现朴实无华的生活常态。零度写作与白描对叙事的情节处置显然有着明显的不同,一个侧重于艺术手法的功能性的应用,一个倾向于无声处的不动声色,恰如鲁迅谈到白描手法时强调的“少做作,勿卖弄”。
三、 理论影响
加缪的零度写作手法为巴特的“零度写作”理论提供了成熟的实践范例,而巴特的《零度的写作》也为加缪的小说给予理论上的支持,二者的成功打破了传统写作的束缚,在倡导言论自由的同时,对当时的文学界也产生了巨大的启示作用。零度的写作强调对写作本体的关注,如同一声惊蛰的春雷一般震惊了当时的文学界,正如巴特所说:“写作的天命,即将语言从权势话语中挣脱出来,从法西斯的囚笼中解脱出来,从压抑的阴影中走出来。”[14]零度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一元理论体系给文学界带来的精神束缚,丰富了文本的多元性和灵活性,消解了权威的文本中心论,它的出现是时代催生的产物,但是这种理论并没有完全彻底的解救写作,承载着巨大的颠覆性的语言乌托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白描则属于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文论术语,最初源于古代绘画中的艺术技法术语,之后经过金圣叹的点评时的初次引用而被关注,随之张竹坡便发现白描手法的好处而对其大力使用和发展,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延及后世。作为一名现实主义大师的鲁迅,不仅继承和发扬古代小说的白描艺术,在理论上丰富和充实了白描的内涵阐述将白描作为文学批评术语确立下来,形成自己独特的白描观,同时也在实践上不断创新并将其推向一个形式中的新高度。“鲁迅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剖析,前提是他对真实的社会人生有着深切的关注”[15],鲁迅对白描有意识的使用和开拓,正是其这一“深切关注”的表现手法之一。鲁迅提升了白描作为文学理论术语的理论高度,在理论和实践中实现了白描从绘画术语向文学批评术语的彻底转换。在鲁迅之后,也有许多学者诸如孙犁、汪曾祺等写作大家在艺术创作中践行着对白描的推崇和拥护,并且形成了各自独立的气质和风格。
零度写作和白描作为中西两种不同的写作技法,二者都保持着对零度写作气息的高度敏感性,并且在实践中有着许多的共通性。将二者放在比较诗学的大平台中进行简单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发现中性叙事模式下的不同文化语境和历史传承,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中国白描叙事理论。
[1] 项晓敏.零度写作与人的自由:罗兰·巴尔特美学思想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4.
[2] 陈跃红.同异之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202.
[3] 光辉.罗兰·巴特作者消亡思想述评[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11.
[4] 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21.
[5] 简墨.国画之美[M].济南:济南出版社,2013:115.
[6] 阮荣春.中国美术史[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15:153.
[7] 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44.
[8] [法]加缪.局外人[M].柳鸣九,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9] [明]施耐庵,[清]金圣叹.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上[M].批评.长春:长春出版社,2014:108.
[10] 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小说全集[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
[11] 鲁迅.鲁迅文集[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44.
[12] 姜岚.叙述与描写:中语纪实文学的美学表现[J].琼州学院学报,2014(6):65-70.
[13] [清]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9:32.
[14] 汪民安.谁是罗兰·巴特[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36.
[15] 周启星.论鲁迅《野草》中二元对立思维的生成及其超越意义[J].琼州学院学报,2015(1):74-79.
(编校:王旭东)
The “Zero Writing” and Line Drawing
LU Yan-zhe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Roland Bart’s “zero writing” theory emphasizes the zero involvement of the author’s thoughts and feelings, advocating the freedom of language form and the digestion of the writing subject, hoping to save the writing crisis in the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While China’s line drawing practice has many convergence with zero writing. A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can help us to find the dialectical neutral narrative modes of the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s and historical inherita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Roland Bart; zero writing; white drawing; narrative style
格式:鲁彦臻.论“零度写作”与白描手法[J].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7(3):88-92+107.
2017-03-17
鲁彦臻(1989-),女,湖北襄阳人,广西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201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民间文学、西方文艺理论。
I04
A
2096-3122(2017)03-0088-05
10.13307/j.issn.2096-3122.2017.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