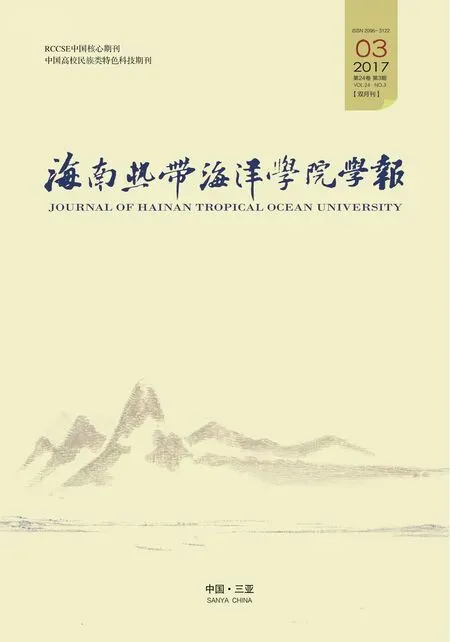从改编与原创文本效应看小说作者与影视编剧的创作生态
何 昕
(湖南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永州 425000)
从改编与原创文本效应看小说作者与影视编剧的创作生态
何 昕
(湖南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永州 425000)
日益繁荣的国内影视市场需要大量的影视文本。影视文本除了原创文本就是改编文本,然而,根据小说改编的文本却比原创文本的质量要高,口碑要好,获奖的概率要高。造成这种落差的原因有许多,将小说作者的创作生态与影视编剧的创作生态对比,创作生态的截然不同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影视事业要蓬勃发展,改善影视编剧恶劣的创作生态是当务之急。
文本;编剧;创作生态;自主性
作为影视艺术创意的基础——剧本,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根据小说改编的“改编本”;二是“原创本”。二者虽然都是剧作家操刀之作,然而,效应却相差甚远:依据小说改编文本拍摄的影视剧,评奖概率和观众口碑相对要高;依据原创文本拍摄的影视剧,评奖概率和观众口碑相对要低。剧本是影视艺术的基础,基础牢固不牢固决定了影视艺术的命运。从剧本质量来分析,原创文本质量不如改编文本质量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巨大的落差呢?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索。
一、 创作生态对作家创作的张扬与钳制
“创作生态是指作家创作的外部环境,包括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生态。”[1]文学创作是作家的个体行为,是作家为现实生活所感动,根据对生活的审美体验,通过头脑的加工改造,以语言为材料创造出艺术形象,形成可供读者欣赏的文学作品的精神生产活动。创作生态和作家创作是个什么关系呢?
文学创作的本质是文学自主性。一个好的作家的创作,不应该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生态环境,作家都应该坚守创作的自主性,秉持自己对生活的审美认识和审美创造,不受凡间世俗的纷扰。然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2],外部的创作生态必然要在作家创作中得到反映。
正如自然生态会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一样,社会生态对代表个体行为的创作来说亦具有支配性影响。积极的创作生态会促使作家创作张扬,精神勃发,昂扬向上,状态和水平进入一个空前的高度;消极的创作生态会令作家沉沦慵坠,心灵沙化,步入创作的类型化、价值取向的单一化和创作思维的模式化。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创作生态对作家的影响,我们通过剖析“改编本”与“原创本”,就一目了然。
(一)“改编本”受到小说故事情节和人物的限制
作家是文学创作的审美主体。作家在现实的生活体验中,通过叙述故事情节和人物活动,来表达自己的审美体验和审美评价。编剧在对小说改编的时候,不再是文本的审美主体,表达的也不是自己在生活体验中获得的审美体验和审美评价,他在文本中反映的是小说作者建构的故事,叙述的是小说作者建构的人物活动,宣扬的是小说作者的审美体验,表达的是小说作者的审美评价。他只不过是小说作者的代言人或传声筒,而丧失了文学创作审美主体的自我。
《芙蓉镇》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影片的大部分情节、人物、对话和场景与小说高度一致。当然,改编小说并不等于全盘接收,小说与影视毕竟是不同的语言艺术。小说可以不受时间跨度的限制,可以设置众多的人物角色,也可以设置纷繁复杂的情节线索,对于太虚的文字叙述也不用忌讳;影视由于时间长度的限制,不可能悉数照搬,它只能在小说的基础上有所选择,或增或减:减,就是把太长的时间跨度进行压缩、过于纷繁的情节脉络进行删节、过虚的无法用影视图像表达的语言叙述要回避;增,就是遴选出小说中符合影视市场需求的元素进行放大。这就是影视切入小说改编的美学逻辑。总之,无论是增添或是删减,无论是强调突出还是精练简化,改编文本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活动发展,都脱离不了小说故事的窠臼。
(二)“改编本”受到小说流行元素的限制
作家为了最大范围地吸引读者,必然要在小说中添加诸如时尚、凶杀、魔幻、情爱、枪击、战争等流行元素。编剧在改编的时候也必然受到小说原有的流行元素的限制。
流行元素不是作品的调味品,可以随意添加,必须要与作品的故事情节有机融合,成为情节进展的推力。像《哈利·波特》,这是一个魔幻故事,哈利·波特与伏地魔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因此,围绕这种关系的探索,成为故事的核心,探险成为哈利·波特的生活内容,与伏地魔的较量成为哈利·波特的使命,书中的魔幻元素、历险元素、正面与反面的较量元素,与故事是血肉相连的,人们在接受元素的冲击时,也是在接受故事情节的冲击,或者说是经受人物命运的冲击。
正因为流行元素是故事情节的有机体,不能随意添加,编剧在改编的时候,也会受到种种限制:他反映的是小说作者选择的流行元素,一些流行元素可能编剧不喜欢,为了故事的整体流畅不得不保留;而编剧喜欢的一些流行元素却无法添加,因为要添加就得改变原有的故事情节另行建构。
(三)“改编本”受到小说时代元素的限制
时代元素包含两个含义:一是指对一个时代大众心理的把握;二是指一个时代流行的词语、情调和意识形态。前者是一种主观臆测,后者是一种客观反映。每一个影视制作人必须认真思考和研究大众的心理。不同时代的观众有不同的喜好。然而,对大众心理的把握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各人有各人的认识和看法。小说反映的只是小说作者对读者心理的把握,编剧在改编的时候也会受到小说时代元素的制约,反映出来的时代元素自然也是小说作者的认识和把握。
二、 自主性:小说作者的创作生态
经小说提供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流行元素和时代元素的“改编本”,保证了影视制作的成功。这种现象的背后,反映出小说作者积极的创作生态。
小说是一种叙事性的文学体裁,通过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环境的描述来概括地表现社会生活的矛盾。小说塑造的人物和情节并不是作者的凭空想象和臆造,她是作者对生活的审美体验和价值判断。由此可见,小说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由于小说表达出的只能是个人对世界的独特的感悟,所以小说创作带有个体性特征。小说作者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各个协会和文艺单位的专业作家;一类是散布社会的文学爱好者。这些人长期生活在工厂、农村、边疆、海岛等基层,对生活有着深刻地体验。即使是专业作家,他们也会扎根基层,去体验生活的真谛。作家不是万能的,他们闪现的才华都是在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域里获得的真知灼见。写他们熟悉的生活、题材,使用他们熟悉的表达方式,一旦超出这个范围,他们就会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小说作者从生活积累之初,就获得与生活的自然和谐,这是小说得以成功的基础。生活为小说作者毫无保留地提供了原生态貌,为他们的体验提供了保障,为他们的审美认识和价值判断奠定了基础。具体地说就是:(1)为他们未来的写作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取向;(2)从生活中获得的多向度观照,使作者快速实现现实与人性深处的沟通;(3)作者与生活的水乳交融会刺激作者创作主体性地张扬,精神更加昂扬勃发;(4)和谐的生活体验在改变作者生活认识的同时,也在改变作者的心理体验,激发写作方式的异彩纷呈,让未来的写作出现崭新的态势。
小说作者的自主性不仅体现在作者与生活的和谐,更体现在进入创作状态后环境的和谐、心情的和谐以及磨砺的和谐。小说作者从生活中获得愉悦的审美体验后,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自我表现,要把自己的审美体验诉诸作品,要把自己对生活的审美评价告诉他人,这是作者的自我需求。所表达的是个人对生活的独特感悟,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在作品出来之前,作者并不需要外界的任何关注。小说作者的创作生态正是体现出作者与环境的这种和谐:没有任何人知道作者在写什么?进展如何?写得快还是慢,写得顺畅还是纠结,没有人知道。环境与作者是和谐的,作者是在自由自在地写作,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来干预。直到作者杀青封笔,把作品呈现在编辑面前,这才揭开作品的面纱。
一个作者,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自主地建构故事、塑造人物、表达对生活的看法,心情是十分愉悦的。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作者的写作状态,激起他的写作冲动,催生他的倾诉愿望,他与作品将会融为一体,能够感受到作品人物的呼吸,与之心与心相通,使他不由自主地为作品里的人物去抗争,去奋斗,作者的精神会由此而超升,认识会由此而升华,力量会由此而凝聚,会迫使自己以更高的标准去完成这次的艺术实践。艺术实践也会趋向前所未有的深度。写作内心的和谐还会使作者具有百倍的勇气去沉淀生活、思想和作品。作者从提笔之初就像修真者一样拂去尘埃和泥垢,远离尘世的喧嚣,远离金钱利禄,平心静气进行自我“修炼”。即使是作品杀青,他们也会回过头,以苛刻的目光审视自己的作品,反复磨砺自己的作品,哪怕这种磨砺是痛苦的也无所谓。忍受磨砺的痛苦去追求作品的完美从古至今不乏其人:曹雪芹对《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蒲松龄写《聊斋》,花费了大半辈子心血;托尔斯泰写《复活》,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作家数易其稿,描写对象和主题几经提炼与深化,才最终写出了这部大书;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前前后后七易其稿。古人和外国人如此,国内的当代作家又何尝不是这样?成都女作家海尼历时10年研究、写作,数易其稿,出版了长篇小说《金面》。正是由于作者处于和谐宁静的创作生态,才能淡泊名利,甘于寂寞,忍受清苦,坚守创作自主性,呕心沥血精心打造自己的作品,才有“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佳作问世。
三、 限制性:影视编剧的创作生态
小说作者和谐的创作生态,催生出佳作问世,为编剧的改编奠定了基础。编剧在改编小说的时候,看似受到小说的种种限制,然而,正是这种限制让改编文本得以成功;而编剧的原创文本,看似自主却毫无自主可言,受到方方面面的限制,处于一种恶劣的创作生态。编剧在自主创作文本时受到的种种限制来自内外两个方面:
(一)外部环境对原创本的创作形成致命性的钳制
拍电影拍电视剧都需要钱,没有钱拍不了影视作品,这是影视生产的铁的法则。现在搞商品经济,拍片子的钱得从社会上去融资。于是大量的资本开始涌进来,当看到搞影视作品有利可图的时候,资本更是呈爆炸式增长。资本的涌入解决了缺钱的难题,却改变了影视作品生产的生态环境。以前是把拍片子当成艺术来经营,精雕细刻,十年磨一剑,剧不感人死不休。资本涌入之后,投资方是要求利润回馈的,于是把拍片子当成商品来经营。追求的不是艺术而是金钱。在利润的驱使下,时间便压缩成一条缝隙,十天半月拿出剧本,三五个月拍摄一部影片,剧作者、导演和演员全都变成投资方的打工者,任其驱使。急功近利的根源就在于投资方急于投资回馈。
资本的爆炸式增长从客观上也造成中国的影视人疲于奔命。就拿电影来说吧,中国每年要拍600多部电影,而国内根本没有这么多套优秀的编剧、导演和主演。据说100套都不到。这就从客观上造成量和质的矛盾。每年要拍出这600多部电影,剧作者、导演和主演都疲于奔命,敷衍了事。
一部作品的产生实际上是作者长期生活积累的反映。作者的生活底蕴越是深厚,作品越是厚重。没有生活的感召,没有生活体验的激情,硬写是写不出来的。勉强挤出来的东西,注定是七拼八凑没有血肉。在利润的驱动下,制作方根本不让编剧去从容地深入生活,认识生活,体验生活,编剧对生活的审美认识当然就无从谈起,编剧只是制作方手里的一种工具:制作方只要看到哪种影视作品大卖了,就要求编剧去写类似的文本,也不管编剧有没有这方面的生活,有没有这种审美体验,都要求编剧去写。创作的自主性被制作方踏进了污泥之中。“快”,成了制作方的原则。快快克隆、快快抄袭、快快拼接,拍出来的片子,都是似曾相识,更有一些恶搞的片子,烂得不成样子。如今资本成了文学的主宰。在资本的主导下,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可以写,追求感官刺激,追求暴力与色情,泛娱乐化,一味地迎合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
(二)编剧内心的浮躁加重了原创文本创作生态的恶劣
如果说编剧的自主性创作除了投资方的阉割外,那么,作为创作主体的创作人编剧来说,他们内心的浮躁则加剧了原创文本创作生态的恶劣。
创作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小说作者在生活中沉浸了多少年,才把在生活中获取的审美体验通过作品呈现于人。马克思也曾经说过:“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3]而一些编剧本身就轻视生活,怕吃苦,怕花工夫,不愿深入生活、深入基层,只是凭自己的艺术功底,“闭门造车”。艺术功底再深厚,也不能代替生活体验。道理很简单:艺术功底是一种技巧,生活体验是对生活的认识。只有技巧没有对生活的认识等于是无米之炊,一个厨师再高明,没有原料他也做不出精美的菜肴。可悲的是,许多剧作者以为仅仅凭借自己的编剧技巧,就可以包打天下通行无阻,什么题材都写,甚至十天半月写一个作品。这样的作品还会有厚度有深度吗?还会让观众感动吗?
编剧,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被迫纳入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整体之中后,在某些编剧那里,文学创作的自我表现逐渐淡漠。他们追求的不再是文学创作本身而是金钱。客观地说,在影视制作链中,编剧的报酬少得可怜,导演和演员的收入高于编剧几百倍上千倍的大有人在。编剧就是在这种高低悬殊的金钱关系的刺激下显得心浮气躁,丢失了自我,毫无创作自主性可言。剧作家成了投资方的工具,文学创作又成了剧作家的工具,文学的精神性目的荡然无存,投资方和市场成了唯一导向,文学失去它的本来意义。
四、 改善剧作家的创作生态
“改编本”与“原创本”的优劣对比,所反映的并不是小说作者与剧作家的高低本质,而是折射出不同的创作生态对作家的不同影响。当消极的创作生态对剧作家的负面影响已经不是鲜见的个例,而是绝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建构一篇理论文章所能承载,而是给社会的一个警醒:再这样下去,我们要实现影视大国的梦想就会沦为泡影。我们必须改变剧作家的创作生态:
首先,要想改善原创文本的创作生态,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好商业投资与利润回馈的问题。其实,利润回馈与拍好片子并不矛盾。因为只有拍出一部好片子,才会获得观众的拥戴,才能赚钱。就像科幻电影《阿凡达》那样,在有了创意后,制作方没有急于拍摄,而是悉心打磨,硬是沉淀了十四年之久,认为确实成熟了,这才开拍。一拍又拍了四年之久,终于打造出一部科幻巨献,震惊全世界。这种精心打磨的《阿凡达》,获得了6亿110万美元的高额回报。如果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拍摄出来的烂片会使观众厌恶,今后再也不会走进剧场。如何处理好利润回馈与精雕细琢的关系,这里有战略眼光的问题。对于那些想捞一把就走的短视行为,最好的方式就是抵制。其次,改善创作生态,作为创作主体的剧作家当仁不让。剧作家一方面要奔走呼吁,争取改变投资方的短视行为,争取社会支持,为原创文本获取良好的创作生态。对于剧作家本人,这里有一个提倡什么、坚持什么的问题。
目前,剧作家的敬业精神受到商品大潮的挑战:坚持作家的良心和责任就会受到冷落,坚持文学创作的自主性就会失去当前的物质利益。然而,从作家创作的精神责任来说,作家是要有所坚守的:一是要坚守艺术的信仰和良心;二是要坚守艺术的尊严和价值。作家生活在现实之中,他的创作必然会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干预和制约,这时候,就需要作家有足够的勇气和坚定的意志力,按照自我理念去维护创作的尊严,维护文学的自主性。在这方面,许多大作家都是我们的精神楷模,法国的伟大作家卢梭,一生穷愁潦倒,他从来不为贫穷叹息一声。一些权贵要用势利收买他,卢梭不为所动。他有一段精彩的讲话:
为面包而写作,不久就会窒息我的天才,毁灭我的才华。我的才华不在我的笔上,而在我的心里,完全是由一种超逸而豪迈的运思方式产生出来的,也只有这种运思方式才能使我的才华发荣滋长。任何刚劲的东西,任何伟大的东西,都不会从一支唯利是图的笔下产生出来的。需求和贪欲也许会使我写得快点,却不能使我写得好些。企求成功的欲望纵然没有把我送进纵横捭阖的小集团,也会使我尽量少说些真实有用的话,多说些哗众取宠之词,因而我就不能成为原来有可能成为的卓越作家,而只能是一个东涂西抹的文字匠了。不能,绝对不能。我始终感觉到,作家的地位只有在它不是一个行业的时候才能保持,才能是光彩的和可敬的。[4]
我们不是卢梭,马克思也不否认文学的经济价值,因为原创文本只有在采用并进入拍摄,才能实现它的兑换价值,否则,就只能是一种潜在的价值存在。在商品经济社会,作家可以让自己的作品进入流通环节,不过,这个阶段应该是在创作完成之后而不是创作完成之前。小说作者和剧作家的区别就在这里:小说作者是在脱离了审美关系回到了现实之中,再将作品拿去兑换现实价值;剧作家还未脱离审美关系就把自己工具化了,唯投资人马首是瞻,把创作当成谋生的手段。“在现实生活中,既要纵浪大化于现实世界之中,融入生活,追求物的享受,而自我也要适时地从现实的大我中抽离出来,保持独特的个性。”[5]
无须讳言,目前,小说作者与影视编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生态,两种创作生态带来改编文本与原创文本的巨大落差,这就像沿河两岸的风景:一边繁荣,一边凋零;一边和谐,一边冲突;一边静谧,一边喧嚣;一边清澈,一边浑浊,形成鲜明的对比。希望影视界重视剧作家的创作生态,回归文学创作的自主性,繁荣中国未来的影视事业。
[1] 李盛涛.论生态文化思想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潜在影响[J].安康学院学报,2010(4):62-64.
[2]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6.
[3] 孙绿怡.文学创作与评论学习指导[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6:130.
[4] [法]卢梭.忏悔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379.
[5] 赵淑英.宗白华美学思想的灵性人格及其当代意义[J].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6(6):106-111.
(编校:王旭东)
On the Literary Creative Ecologies of Novel’s Authors and Screenwri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Adaption and Original Text
HE X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Hunan 425000, China)
A lot of film texts are needed in the domestic film market. Film texts include original text and adaptation. However, adaptation has higher quality, better reputation and higher award than original text.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is,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 literary creative ecologie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It is a task of top prioroty to improve the bad literary creative ecology of the screenwriter so as to guarantee the health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ilm cause.
novel; original text; adaptation; literary creative ecologies; autonomy
格式:何昕.从改编与原创文本效应看小说作者与影视编剧的创作生态[J].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2017(3):82-87.
2017-02-22
何昕(1979-),女,湖南永州人,湖南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学。
I207.35
A
2096-3122(2017)03-0082-06
10.13307/j.issn.2096-3122.2017.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