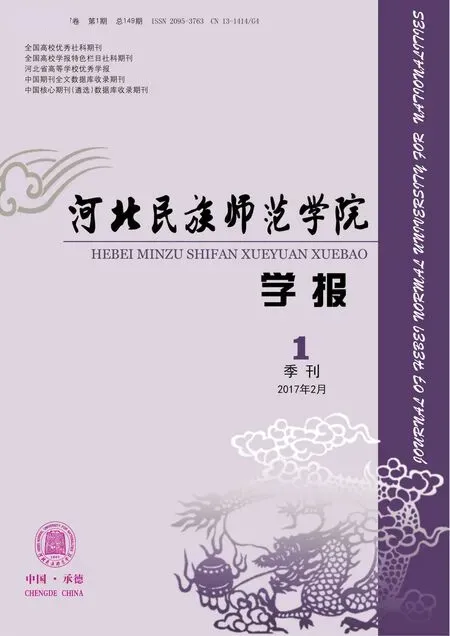朝向“彼在”的“此在”
——评李仕淦的散文诗集《旅行者》
孙丽君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朝向“彼在”的“此在”
——评李仕淦的散文诗集《旅行者》
孙丽君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在路上”是诗人李仕淦赋予生命存在的基本姿态,他的散文诗集《旅行者》以对生命旅行的叙述,谱写了一首关于生命、文化、文明甚至是宇宙的史诗。在李仕淦的笔下,“旅行者”的旅行是从“荒漠”出发、于“河流”溯源并无限趋向于“天光”弥漫的澄明之境的过程,它将“此在”的生命与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和对历史、文明以及万物的溯源相融合,建构起一个生命与旅行同构、历史与文明合流、人性与神性同在的宏大架构。
李仕淦;《旅行者》;荒漠;河流;天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诗坛涌现出一股股令人措手不及的诗歌潮流,与之相应,新的诗歌流派与新的创作理念可谓层出不穷、前仆后继,“朦胧诗”对于“大写的人”的追求、“第三代”诗歌对于世俗生活的回归,以及上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下半身”写作等,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是:从历史溯源与文化梦想的建设中退出并将书写的重点转向“此在”的现世生活。自不待言,这种转向暗合了现实社会与潮流文化的发展方向,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言“如果关于国家、阶级、生产方式、经济正义等抽象的问题已被证明是此时此刻难以解决的,那么人们总是会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某些更私人、更接近、更感性、更个别的事物。”[1]对于当前的诗歌创作而言,与文化、历史的疏离以及与现实、世俗的合谋构成了其创作的重要方向之一,而这种转向的结果之一便是往日光彩熠熠的诗歌逐渐在“媚俗化”、“口水化”的批判标签中失去了它的光环。事实上,在纷繁芜杂的当代诗坛,依然存在着许多坚守诗性的诗歌创作者,“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就是这样一群在荆棘乱丛中守卫诗歌神性的创作群体,周庆荣、灵焚、爱斐儿、白月、弥唱等人均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着诗歌美学的探索,作为“我们”散文诗创作群体的一员,诗人李仕淦的诗歌创作特色是十分明显的,他的诗集《旅行者》以“在路上”的哲学完成了对于历史、文化、生命甚至是宇宙万物的溯源与追寻,它将“此在”的生命与世俗生活剥离,是一部洋溢着人性与神性的文化史、文明史甚至是生命史。在诗集的后记《旅行者告白》中,诗人写道:“旅行者从‘荒漠出发’,于‘河流’溯源、流淌,在‘天光’弥漫无际的透明、清澈中,彻底归入时光和天地万物大生命一体存在的澄明自在。”诗人赋予旅行以过程意义和终极意义,即重视“此在”的旅途亦对旅途的终极所归表示期待,这既是对“第三代”诗歌以来追求“此在”生活哲学的继承与批判,也是对“我们”散文诗群明确提出“意义化写作”理念的践行,与此同时,正是这场始于源点、经历风景并最终抵达本真的旅行使生命与万物走向皈依。
一、从“荒漠”出发
由于“生命不知疲倦,它不歇息于任何一个等级系统中,它是持续的换喻,是绝对的动词,绝对的谓语,这个谓语不带宾语,它永远不会落实下来,平静下来,固定下来,它甚至不会在漫漫旅途中坐下来叹息。”[2]持续的运动是生命的本质特征,对于生命而言,旅行以“在路上”的姿态构成了其存在的隐喻性意义。同样,对于诗人李仕淦而言,存在就是一场始终位于路上的旅行,正如他本人在《旅行者告白》中所提及的:“无论是现实,还是理想,之于我都在路上。肉体流放,灵魂飘泊,‘居无定所’构成大半人生常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存在因无止境的旅行而失去了轴心,在李仕淦的笔下,正是旅行赋予了生命以“在场”和终极性意义,换言之,只有经历旅行,生命才能被风景雕琢得更美,也只有经过旅行,生命才能通向最初与最终的美好。李仕淦将存在的状态与“旅行者”的形象相勾连意在建设一种生命与旅行同构的宏达隐喻,自不待言,隐喻的本质是建立在相似性结构的基础之上,是人类认知与获取事物最为古老的方式之一,正如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中所指出的:“相似性成了形式最为粗糙的经验物”,“只有两个事物的相似性已至少引起了它们的比较,它们之间才能确立起相等或秩序关系。”[3]就个体生命而言,存在便意味着在时间的线条上永不停息地走向终结,它的本质正在于其“向死而生”的过程,在此意以上,旅行可视为生命本质的抽象,而李仕淦笔下的“旅行者”形象正是将生命本质抽象为旅行的产物。
与此同时,李仕淦笔下的生命状态与旅行中的风景类型同样达成了一种相似性契约,李仕淦将旅行的起点定位于“荒漠”,暗合了生命起初的荒原性特征,并指涉出生命通过旅行而变得丰富与富饶的意义。在组诗《旅行者和旅行者的琴》中,有关旅行的起初,诗人勾勒了一幅“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历史画卷:“又是黄昏,晚霞如血的丝绸垂下再一次缠紧孤独的身影,旅行者站立万里平川,闭上双眼,不必回首或眺望,长河落日中琴声已再一次挑起大漠孤烟。”古典诗词中那个经典而熟悉的游客形象再一次出现,那种“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古老画面被再一次勾绘,毋庸讳言,在中国的传统诗词中,荒漠与军人、行者、游客之间实现了一种自然而又经典的关联,如“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岑参《碛中作》)、“昼伏宵行经大漠,云阴月黑风沙恶”(白居易《缚戎人》),而李仕淦笔下衣衫褴褛身负爱琴的“旅行者”形象同样是荒漠中的过客,这种在传统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游子意象可称为“过客原型”,有关原型的定义,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经有过如下表述:“原型是一种形象,或为妖魔,或为人,或为某种活动,它们在历史过程中不断重现,凡是创造性幻想得以自由表现的地方,就有它们的踪影”[4],在此意义上,荒漠中的“旅行者”形象本身就是一个向历史文化与共同记忆回归的动态符码,而“荒漠”作为旅行出发的地点,不仅仅是千百年来文化历史的基因沿袭,更是对生命起初状态的一种隐喻性描写,在《旅行者与旅行者的琴》中,诗人写道:“赤裸的躯体是旅行者唯一的行李,琴是旅行者的一只手臂,是躯体的一部分,深深地插进体内的一根骨头,或者说旅行者本身就是一把琴”,不必赘言,“赤裸的躯体”既是生命个体来到世界的本初状态,也是“旅行者”起程时的姿态,在此,“赤裸”、“荒漠”与生命本初、旅行起初均达成了一致性。然而,既然“旅行的意义在于旅行过程本身,风景在路上”(《旅行者与旅行者的琴》),荒漠作为旅行的起点,不失为一种重要的风景,落日、飞鸟、马匹、野狼,一个荒凉、萧条而又充满野性的世界;而篝火熏黑石壁的山洞、兵马俑雄关威严庞大神秘的阵形、金字塔以及莫高窟黑暗狭长的隧道则构筑了另一个承载文明而又被现代文明所抛弃的世界;在此意义上,“荒漠”并不“荒芜”,它是自然与文明的起初。从“荒漠”出发便意味从最原始的自然出发、从文明的源头出发,经历灵与肉、生与死、天堂与地狱,并最终抵达生命、历史及其文明的源头,不难发现,这是一场从起点出发、历经风景洗礼而又重返起点的旅程,正如诗人在《旅行者与旅行者的琴》所写到的:“琴声渴望到达的地方,旅行者把它叫着远方或故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旅行是一场简单的返源行为,相反,它是生命主体膨胀与自我确认的过程,正如那个“充满英雄载誉而归的返乡冲动”的荷尔德琳与“手持宝剑冲刺太阳王座”的殉道者海子,“旅行”确认了他们的价值与意义。作为“旅行者”形影相随的躯体或者是行礼,琴是“旅行者作为存在性主体的存在抉择与存在方式”,“是声音,是旋律,是歌唱,使旅行者的旅行成为审美而充满诗意”《(旅行者告白)》,在此意以上,琴是一种游荡于主客之间的身体符号与文化符号,一方面,琴是一种乐器,是诗意旅途的佐料,是人类文化与文明的提喻;另一方,琴又是“旅行者的一只手臂,是躯体的一部分”(《旅行者与旅行者的琴》),是能动主体的存在方式;可见,琴是促成旅行者与历史文化之间难以剥离关系的代表性符码,而也正是这一符号的出现,使从“荒漠”出发的“旅行者”在抵达终点时发生了质的转变,因为经过旅途洗礼的生命已经不再是起初时的赤裸状态,而是经历了野蛮与文明、战争与和平、历史与现在并成为有担当、有责任的价值主体。
二、于“河流”溯源
在李仕淦的散文诗集《旅行者》中,“河流”无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在组诗《给母亲》中,李仕淦写道:“沿着河流抵达脚下这一块土地,回首只有落叶和雨雪的回声萧萧。……//沿着河流抵达脚下的这一块土地,我们已把足迹踏向另一颗星球,而我们无法穿越风的翅膀返回最初的地平线。”前面讲过,诗人李仕淦在后记《旅行者告白》中曾谈及旅行是从“荒漠”出发、于“河流”溯源并通向澄明之境的“此在”过程,作为自然风景,“河流”是旅行途中司空见惯的自然之物,而作为生命、文明与文化的承载,“河流”则是生命密码与多彩文明的渊薮。不难发现,在诗歌文本中,“河流”是一个古老而又炙手可热的意象,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诗经·关雎》)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王之涣《登鹳雀楼》),“河流”作为一个重要的母题或原型反复出现于诗歌文本之中,并构成了人类生命历史与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在李仕淦的笔下,“河流”为“旅行者” 朝向灵魂返乡与生命澄明之境提供了路径,在《旅行者与旅行者的琴》中,诗人写道:“我在一条河中冲撞、漂流,波涛汹涌”,“河流”所裹挟的历史与文明正是“旅行者”所要经历的风景。然而,由于河流割断了大地原有的纹路,改变了道路的方向,文学作品中的“河流”意象往往是一种阻断与障碍的象征,如“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中的“长江”构成了诗人与友人之间相聚的阻碍,学者孙胜杰曾经指出:“河流是一种阻隔,空间上会产生距离感,这种距离感的强化会使河流阻隔成为人类的潜意识,经过岁月的淘洗进入人类的文化记忆,成为人类理想、愿望实现的障碍。”[5]虽然“河流”为“旅行者”提供了通向历史与文明的路径,但“冲撞、漂流”等动作亦表达了这条道路并非是畅通无阻的,它需要“旅行者”的能动性力量,与此同时,“河流”所具有的阻断之意在其隐喻意义上亦有所表现,在组诗《河流》中,诗人写道:“欲望的暗流一次又一次地冲垮理性的闸门,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交出泪水,一次又一次在死亡的废墟中学会承受与忏悔。”在此,诗人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人类因欲望而产生的野蛮与暴虐行为,这条被冠之以“暗流”的欲望之河不仅使真善美离场,更使生命告急、物种濒危,正如诗人在诗中所言:“河水缓慢而虚弱地流淌,漂浮着油污、死婴和腐烂的心脏。生物暴毙、物种灭绝,堆积蔓延的垃圾成为未来孩子们的乐园——”在此意以上,“河流”不仅以其隐喻性指向参与了“阻断”文明的行为,亦成为映射生态与存在的一面镜子,它将因人类欲望膨胀与理性丧失的后果毫不留情地呈现出来。
然而,在对“河流”所具有多重指向中,源流的意义却占据着核心的位置。不必赘言,“旅行者”的旅行并非是一场简单的物理性位移,而是一场穿越时空、生死、蛮荒与文明、战争与和平的文化之旅与生命之旅,由于世界万物源生于同一滴水,所有河流源发于同一滴水,只有沿着“河流”的方向,在“河流”中追溯、溯源,才能通向生命最初的清澈与天人合一、与神同在的澄明之境。在诗集《旅行者》中,“河流”源头是一个将生与死、野蛮与文明、始点与终点混合的漩涡,是旅行者沿河流出发而又抵达的位置,在组诗《旅行者和旅行者的琴》中,诗人写道:“旅行者站立河流源头:此岸即彼岸,异乡即故乡,地域即天堂。/旅行者站立河流源头:时间之起点与终点,宇宙秘密之中心。”可见,传统文本中“河流”所具有的阻断意义并没有给“旅行者”带来绝对性的障碍与困扰,相反,“河流源头”在此成为一种阻断的终结,一种形而上的纽带,它将文明与野蛮掩埋、将天堂与地域等值、将起点与终点对接……似乎世间的区别都可以在奔腾的河流中模糊、淡化。自不待言,李仕淦笔下的“河流”并不是单纯的自然之物,而是生命、时空、文明与万物的渊薮,沿着纵横交错与蜿蜒曲折的河流,诗人将目光放置于整个文明史与文化史之上,追溯同源、展望未来,以“河流”的灵魂与精神架构起人类精神或是生命精神。在无数交错蜿蜒、绵延万年的河流中,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恒河与黄河分别构筑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中国的文明圣史,而沿“河流”溯源则是对自然生命与古老文明的追溯,在诗歌《河流》中,诗人写道:“四条大河,包含着大地疼痛、世纪荣辱,四条奔腾流动的道路一同穿越了洪荒亘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四大流域,孕育、滋养四种文明,一如四座摇篮诞生、成长的四个兄弟和四姐妹/一路走来,一路为自己神圣加冕,头顶皇冠闪耀独自奇异的光芒。”“河流”孕育了不同的人种、信仰和文明,却浇灌着同一色彩的血液,因此,诗人接着讲到:“无论肤色、语言、信仰,不分黑发、棕发、黑眼睛、蓝眼睛,都是河流的孩子,都是太阳神、月亮神的后裔,水和血浇灌的身躯都拥有着不死的大河之魂。”不难发现,“河流”与“血液”构成一组可以在某些语境中互换的符号,由于“河流”遍布大地犹如“血管”遍布身体,于“河流”中流动的水与于身体里流动的血液不仅在其材质上具有一致性,更在其动态与形象上存在一致性,“水”与“血”仍然是一组建立在相似性法则基础之上的事物,是最古老与传统的关联方式之一。在中国古老的神话故事“盘古开天辟地”中,正是盘古的血液变成了奔流不息的江河,使万物与文明的发生成为可能。诗人借助“河流”与“血”之间这种古老而又可靠的关联,再现了生命、文明与“河流”之间古老而又复杂的关系,然而,作为一种具有原型意义的映射关系,这种关联所触动的并不仅仅是个体的思绪,而是人类的共同记忆,正如荣格所指出的:“一个原型的影响力,无论是采取直接体验的形式还是通过叙述语言表达出来,我们之所激动是因为它发出了比我们自己的声音强烈得多的声音。谁讲到了原始意象,谁就道出了一千个人的声音,可以使人心醉神迷、为之倾倒。他把个人的命运纳入人类的命运,并在我们身上唤起那些时时激励着人类摆脱危险、熬过漫漫长夜的亲切力量”[6]诗人对“河流”与“血”这一古老关联的再叙将处于人类文化记忆底层的集体无意识挖掘出来,实现了人类向自身的认同与确认,事实上,早在诗歌《高过我们的血》中,诗人就写道:“还有什么更低,低过流水?/还有什么更高,高过我们的血?……比流水更低的是谦卑与坚韧。/比我们的血更高的是责任与担当。”能与“水”和“血”相比较的只有品质,而将“水”和“血”相关联的不仅仅是其外在形态,更是其内在所持有的品行。在组诗《河流》中,诗人再次写道:“时间深处,一条大河奔腾于我们体内,一条大河奔腾于我们体外”,体内之河正是我们的血液之流,而体外之河则是养育不同人种、语言与文明的源流,而同样的血液、同一源流共同创造了这五彩缤纷的世界,它们有着共同的不变的意念以及对于爱与美的永恒的追求,正如诗人在组诗《河流》所写下的:“水的意念和血的意志不曾改变”,虽然“河流书写着动荡变迁的历史”,但“道路的方向不曾改变。”由于“时间深处,我们——是同一条河流”(《河流》),既存的所有来自同一滴水、同一条河流,“这是每一滴河流的歌唱,是源自第一滴水之万物万灵的合唱”(《河流》),在水与血的渗透中,生命与河流再一次同构,“与河流一起走来,我们就是河流”(《河流》)。通过对“河流”与“血”的叙述,诗集《旅行者》不仅表述了文明与生命同构的整体性经验,还构筑起一个展现人类共同记忆、关注人类共同命运、呼唤人类共同未来的宏大架构。
三、趋向“天光”弥漫之境
“天光”是诗人为“旅行者”预设的终极目的,在组诗《天光》里,“李仕淦触及到宇宙大爆炸、时间和空间的起点、智慧设计论、上帝的创世七日等和世界发生、人类起源相关的信息,在作者的磅礴思绪和激越想象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知识信息、形而上的终极存在之思与个体当下的生命困厄激烈碰撞,产生出境界阔大、诗意深远的奇诡诗篇。”[7]自不待言,“光”是“创世纪”过程中首先出现的事物,原始太初,上帝创造了天地,然而,天地一片混沌,渊面黑暗,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作为与黑暗相对的事物,光照亮与滋润了万物,并使生命与万物的存在成为可能,它承载着最原始的光明与希望,参与到万物运转的秩序之中,正如诗人所言:“因为光,水和火和土循环穿透,季节的短尺丈量着我与万物共同的历史”(《天光之四:黑洞或深渊》)。由于光使白昼从黑夜中剥离,使春夏秋冬循环交替,与之相应,时间以一种轮回的方式见证了生命的代代相传,在此意义上,光的规则代表了生命与万物的运行规则,在《天光之二:时间或轮回》中,诗人写道:“无法记忆泥土如何长出骨头,血从何处来抵达我体内,而多少次生离死别我呼喊着你,多少次复活与惊醒只在你光芒的撕裂与缝合中。”光使土与水运转,诞生了骨头与血液,光的轮回弥合了生与死的罅隙,使生命在朝向光芒的旅途中轮回不息,不难发现,此处的“我”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个体,而是生命在时空中的抽象与凝结,而对于光的向往,构成了生生不息的生命的永恒追求,正如诗人所言:“我永恒的追求只因你无处不在的光芒和弥漫无极的牵引”(天光之三:引力或诱惑)。作为“旅行”的终极趋向,“天光”是神性弥漫、万物合一、澄明透彻与真善美的同在之境,无限趋近“天光”是生命的唯一方向与前景。在组诗《天光》中,诗人以卓越的想象力叙述了生命在参与朝向光之旅中的状态:“此刻,此刻一切正在进行——而我,在光的哪一条纬度上飞翔与滑行?”(《天光之一:奇点或开始》),生命在遁形的光线上飞翔与滑行充盈着存在的激情,与郭沫若先生“我在我的神经上飞跑”(《天狗》)所产生的自我气势相吻合,显示了诗人为追求真善美而张扬的主体性意识。
然而,主体性意识同样会倒向自我欲望的膨胀以及对他者立法的行为,正如学者陈旭光所言:“主体(subject)作为现代哲学的‘元话语’,标志着人在同客体(object)之绝对对峙中的中心地位和为万物立法(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先验性特权。”[8]不必赘言,人类主体性的扩张既可以是一种生命精神的张扬与对真善美法则的追求,亦可以成为滋生贪念与欲望的土壤。而在追求中陷入欲望漩涡的人类不仅丧失了理性与信仰,更在一条没有光芒的道路上走向崩溃:“是怎样的欲望,吞噬与膨胀,使美遭受肆意践踏,使审美成为丛林法则的暴力?!//是怎样的疯狂,傲慢与偏见,使理性丧失、信仰崩溃,在罪与罚中宣告生存的失败?!”(《天光之七:万物理论或灵》)人类内心的黑暗驱走了光与美,欲望的膨胀使生存陷入危机,作为生命符号与万物之灵的“我”为人类偏离光芒抛弃真善美的行为而感到惭愧并为之忏悔,由于黑暗蒙蔽了人类的内心,使生命处于一片混沌的无光之中,另一场关于“自我”的“创世纪”诞生了,为此,诗人在《天光之八:大设计或神》中写道:“然而,这是我的第七日。在这一日,我已经创造了自己,创造了世界”,在“创世纪”的故事中,“第七日”被定为“圣日”,正是在这一天,万物齐备,上帝赐福,而在李仕淦的笔下,这场关于“自我”的“创世纪”不仅是世界创造了“我”,亦是“我”创造了世界,作为人类符号的“我”不仅从自然提喻以及被创造的客体位置走向兼具能动性的主客双重身份,更从一个贪婪、自私的主体走向一个灵肉合一、至善至美的价值主体,这种主体的更新无疑是生命精神的一次升华,是宇宙秩序的一次更新,是人类与万物走向灵性与神性的起始。
四、结语
诗集《旅行者》是诠释诗人李仕淦“在路上”哲学的经典之作,“旅行者”是诗人对个体存在状态的命名,也是对所有生命姿态的总结与概括,正如诗中所言:“谁都是旅行者,正如对于这个世界谁都是过客”(《旅行者和旅行者的琴》),然而,诗人并非意在传递一种有关生存的虚无哲学,而是在朝向死亡与终结的过程中去把握与理解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曾言:“死作为此在借以向其死亡存在的存在方式的名称。因此就得说,此在从不完结。但此在只有在死的时候,才能够亡故。”[9]在李仕淦的笔下,永恒的“此在”被叙述为一场生命的旅行,这既是一场个体生命的旅行,亦代代相传的整体性生命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伴随旅行的是个体生命与人类的担当,是万物价值的实现与确立,是天人合一、与神同在的澄明之境的无限趋向,正如诗人在《旅行者告白》中所讲到的:“但旅行,拒绝漫游,后者是主体无意识、无方向、无着落的随波飘荡,而前者则是主体超越意识与生命的灵魂返乡,是人类物种生命自我神性的启示与召唤,自由而必然无限趋近于与神同在的终极信仰。”诗集《旅行者》通过对生命旅行姿态的叙述与解读,将个体与人类、万物与宇宙的命运相勾连,谱写了一篇关于历史、文明、生命与宇宙的诗史,在当下趋近世俗的诗歌创作中,这无疑是一次诗歌秩序的改写。
[1](英)特里·伊格尔顿 著,华明 译.后现代主义的幻象[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2.
[2] 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61.
[3](法)米歇尔·福柯 著,莫伟民 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上海:三联书店,2001:90.
[4](瑞士)卡尔·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学的关系[A].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96.
[5] 孙胜杰.中国文学中“河流”原型意象的“阻隔”母题[J].学术交流,2016 (5).
[6](瑞士)卡尔·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学的关系[A].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97.
[7]荣光启.散文诗:当代汉语诗歌的一种新高度[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
[8]陈旭光.主体、自我和作为话语的象征—“后朦胧诗”转型论[J].诗探索.1995(4).
[9](德)马丁·海德格尔 著,陈嘉映、王庆节 译.存在与时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296-297.
The Travel From "Dasein"To "Other" A Review Of Li Shigan′s Prose Poetry AnthologyTravellers
SUN Li-jun
(Chinese Poetry Research Center,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China)
"On the road" is the basic state of lives in the Li Shigan’s poetry, from the narration of the lives’ travel, his Prose poetry anthologytravellersconstitutes a history of lives,culture ,civilization and even the universe's epic. Under Li Shigan's pen, travelers start from "deserts", experience "rivers" and tend to "heaven lights" infinitely, which combines the "Dasein" with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lives, and constructs a grand architecture of lives with travel, history with civilization and humanity with divinity.
Li Shigan;travellers; deserts; rivers; heaven lights
I206
:A
2095-3763(2017)-0044-06
10.16729/j.cnki.jhnun.2017.01.008
2016-12-13
孙丽君(1988— ),女,山东莒南人,首都师范大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