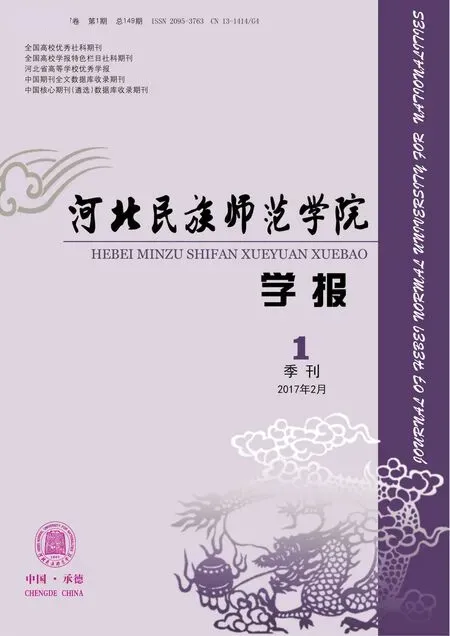论努尔哈赤传说的形成基础
刘先福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论努尔哈赤传说的形成基础
刘先福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
民间传说并不会凭空而来,它的形成有着诸多的现实基础。创编传说的素材大多来自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关于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传说正是满族民众从东北地区特有生境出发,在历史基础上综合现实生活的民间讲述。从众多传说文本中,我们既看到了努尔哈赤作为英雄人物的一面,也看到了他作为普通满族人的一面。这些传说艺术化地反映了满族特有的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内容。
满族;努尔哈赤;民间传说;生境;民俗生活
民间传说并不会凭空而来,它的形成有着诸多的现实基础。创作传说的素材大多来自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有了这些“砖瓦”,再附加上记忆中的英雄人物,就大体完成了最基本的民间传说组建。作为沟通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民间传说不仅在讲述风格上,而且在主题思想上都渗透着质朴的地方话语。尽管这些素材并不具备统一性,但混搭的效果反而彰显了民间叙事的独特魅力。
努尔哈赤被民众称为“罕王”,既是满族英雄,又是一代帝王。有关他的传说广泛流传在东北地区。这些传说的情节并不拘泥于历史细节,但也不是随意杜撰,而是充分反映出满族民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将当代传承的关于努尔哈赤的传说逐一拆开,划分出努尔哈赤传说的构成元素,力图全面阐释民众生活世界与传说文本所构拟的精神世界之间的联系。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个传说文本中,民俗生活的各个维度往往是兼而有之的。
一、满族生境构成及认知
传说的素材根基于人类的自然生境与社会生境,以及对二者的综合认知。生境本是生态学概念,强调的是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影响。不可否认,自然环境是人类永远都要面对的显要问题。文化生态学认为,环境与文化存在辩证式的相互作用。环境对于人类而言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非仅仅是限制性和选择性的作用。[1]P136也就是说,人类只有在与环境的交流中,才完整塑造了文化模式。这些因素是我们在讨论传说文本形成时所不能忽略掉的。
简言之,“各民族对环境认识的取向,对环境认识的深度、广度和精度,主要源自于他们生产活动的实践需要和生存需要,此外,不同谋取食物的生存方式对环境的认识也有着不同的要求。”[2]传说的形成离不开这样的过程:在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下生活的民众,不断地在与周围世界的互动中创造文化,经过了一再地选择与调适,终于建构起来一系列符合自身发展的生计方式、社会组织与信仰宗教体系。
就满族而言,其生境构成及认知,离不开建州女真世代积累的生活智慧与地方性知识。经过数次迁徙,女真的生计方式也在与其他民族的学习中得到成长和丰富。原有的狩猎为主导的一整套文化系统,也随着农耕、畜牧的增加而产生变化。早期的哈拉组织(老氏族)也随之瓦解,并逐级发展成穆昆(新氏族),乌克孙(家族)和包(家庭)。[3]P37信仰方面,除萨满教外,佛教、道教等其他宗教也被纳入到满族的信仰体系中。
满族生活的中国东北地区,从整体来看是一个“山环水绕”的区域,东、北、西三面有山,南面向海。这样的地貌造就了生态类型的多样和物产资源的丰富。然而,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冬季寒冷漫长,交通不便等不利因素,一直以来并没有得到更好的开发。同时,生态区位的差异也使得内部的发展并不均衡。长久以来,满族及其先民就在这样一片土地上生息繁衍。
满族民间叙事也在此基础上得以产生并传承。“叙事文本的空间也可以视为满族社会现实生活空间的缩影。”[4]P173仅从努尔哈赤传说的文本来看,这种认知表现得并不充分,原因在于传说本身的叙事目的并不是传播生产与生活知识,而是建构过去的历史与现在的生活之间的联系,且努尔哈赤作为民族英雄和祖先,讲述上带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严肃性,没有太多的发挥空间。因此,这些文本并没有更多涉及对动植物的认知与日常生活的经验。不过,在多姿多彩的民间故事中,满族人的生态思维和生存之道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即便如此,努尔哈赤传说还是提到了不少动植物的内容。比如,有多个文本提到虎崇拜,可见老虎在当时狩猎生产中的重要地位。野猪也是常见的动物,“努尔哈赤”的满语意思就是“野猪皮”。传说中也提到了一些植物的特征,如常见桑树、杨树、腊木、柳树等,还有对草药的认知,如靰鞡草可以保暖,龙胆草可以治跌打损伤,马粪包可以止血等。
当然,远不止这些例子。传说中所体现的生态观念对于今天处在环境矛盾之中的现代人来说,尤为重要。从传说角度折射出的满族生境构成及认知,更能帮助我们准确地把握传说的内涵和理解民间社会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
二、生计方式
生计方式和经济类型是一个族群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基础与保障。一般来讲,生计方式取决于客观的自然条件和资源情况。对于东北地区生活的女真人,狩猎一直是最主要的食物来源,而且这些物产通过边关的马市交换,可以获得铁器等其他生产的必备品,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到了清代,骑射技能也仍是满族人的基本科目。当代流传的努尔哈赤传说中有许多关于彼时女真人狩猎、采参、淘金情形的生动描述。这些信息完全出于切实的生活感受,即便时过境迁依然保留在口头传统中,特别是保留在描叙少年努尔哈赤困苦生活的传说中。
(一)狩猎
可能是明代建州女真的生计方式已经发生了转变,在努尔哈赤传说中鲜有详细描述集体围猎的内容。不过倒有努尔哈赤射虎救人的故事。
《石柱子的来历》讲到,“只见一只吊睛大老虎,横叼着一个人在跑,罕王拈弓搭箭,一箭射去,正中老虎头上,疼得它大吼一声,扔下人带着箭逃跑了。”
《小罕打虎》讲到,“这青年随后就背身搭箭,飕一箭正好射中老虎的左眼。那猛虎疼得嗷的大吼一声,蹿起老高,便栽倒在地上,又拼命挣扎起来,朝着李总兵扑了过来。……就在这千钧一发的节骨眼上,只听得弓弦一响,飕的一箭,又正好射中了老虎的右眼。这回老虎的左右两只眼珠子上,都插着一支箭,疼得老虎直打磨磨。方才射箭的那个青年人毫不怠慢,又搭箭弯弓,飕的射出第三支箭,这一箭又正好射中老虎的‘前夹半子’,这回那老虎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抽搐几下,一蹬腿就完蛋了。”
传说中赞颂了努尔哈赤的箭法,而这对于一个狩猎民族是相当重要的。明代女真人根据狩猎生产不同,分两种部落,“一是农、猎兼资部落,既耕种又狩猎,二是不事农业,终年狩猎部落。”[5]P41随着建州女真农业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狩猎经济已经让位于农耕,但骑射本领与狩猎养成的集体劳作习惯,却依旧延续到征战和八旗制度中。
(二)采参
采参是女真人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人参作为名贵作物和中药材,在女真人与明朝的贸易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民间采参也称“挖棒槌”,有一整套的规矩和程序,还有诸多禁忌和行业用语,如管领头人叫“参把头”,人参的各个等级也都有不同叫法。
《罕王采参》中讲到,“那时候,咱这有上山放山的,放山就是采人参,也叫挖棒槌。放山得会一帮子人,约莫十几个人,这帮人里,有头棍、二棍、末棍、边棍。放山时候,每个人都得拿个索罗棍,用它扒拉草,先打草惊蛇,蛇走了,再找人参。”
明朝曾通过“停止互市”来打击女真人,导致人参腐烂数万斤,造成了女真人惨痛的经济损失。据史料记载,“曩时卖参与大明国,以水浸润,明人嫌湿推延。国人恐水参难以耐久,急售之价,又甚廉,太祖欲熏熟晒干,诸臣不从。太祖不徇众言,遂熏晒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6]而努尔哈赤发明的“蒸参之法”在传说中也有反映,不过反倒将发明权给予了普通民众,但还是把这种方法处理的人参叫做“罕王参”。
如《罕王赏参》讲,因为人参放置太久而腐烂,罕王将其分发给众人。一位披甲的瞎眼讷讷(妈妈)误把人参给蒸熟了。不料,罕王又询问大家如何使用人参,披甲只得如实禀告。罕王看过蒸熟的红参后,认为这正是最好的贮存方法,这位披甲也因此得到了封赏。
(三)淘金
东北地区的金矿主要在黑龙江和吉林。据说唐宋年间,吉林桦甸的夹皮沟已有采金业。历史上,民间的淘金活动虽有被官方禁止,但仍一直延续下来。淘金也叫沙金,就是从河溪泥沙中提取金粉和小颗粒,工作十分辛苦。
《七星泡》讲到,努尔哈赤因为救了一位落水的白发老人,而获赠了七粒金豆子,实际上是夜明珠。他出于好心,“看淘金的人们顶着风雨,抡锤砸石,急水冲沙,十分辛苦,就从怀里掏出了夜明珠,交给了淘金的人们。人们把这七颗珍珠放在河边的石头上,珍珠立刻放起光来,就象七颗明亮的星星,把这儿照得通亮通亮的。”而后,有人去抢夜明珠,努尔哈赤一气之下把珠子踩在脚下,却不见了。后来人们不断地为找珍珠挖地,直到出现了七个水泡子。
有关淘金的两则传说,《七星泡》流传在吉林珲春一带,《七颗红痦子》流传在黑龙江勃和哈达一带,两篇互为异文,只不过一个挖出了水泡子,一个成了罕王脚底下的红痦子。淘金传说的流传地点与金矿的分布有着一致性,辽宁地区暂未发现类似的传说。对于努尔哈赤脚底下七颗红痦子的另一种解释是,新宾地区传说中所宣扬的“天命观”思想[7]P28-29,即“脚踏七星”是与生俱来的。
三、社会组织与民俗
努尔哈赤传说所反映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隐含了满族社会形态的演变,也提到了东北地区常见的“拉帮套”婚姻、“半拉子”劳动力、结义兄弟、采参帮、淘金帮等一些社会组织风俗。
(一)八旗制度
八旗制度最初源自女真人氏族社会时期的集体狩猎制度。在金代,发展成“猛安”和“谋克”组织形式。猛安是千夫长,谋克是百夫长。据金代史籍记载,“部卒之数,初无定制,至太祖即位之二年,既以二千五百破耶律谢十,始命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继而诸部来降,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8]
到了努尔哈赤起兵之后,他建立起一支分四个兵种的军队。据《李朝实录》记,“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兄弟,以建州卫酋长李以难等为麾下属。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多造弓矢等物,分其军四运:一曰环刀军,二曰铁锤军,三曰串赤军,四曰能射军。间间练习,胁制群胡。”[9]这就是四旗兵的雏形。
万历二十四年(1596),朝鲜人见到了当时建州女真的军旗,“旗用青、黄、赤、白、黑,各付二幅,长可二尺许。”[10]这样的五色旗帜在下面的传说也提到。
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编制四色旗。万历四十三年(1615)增为八旗。每三百人设一个牛录额真,五个牛录设一个甲喇额真,五个甲喇设一个固山额真。在黄、红、蓝、白的基础上,增设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共合八旗。而“牛录”一词就是满语“大箭”的意思,掌握“大箭”正是当初“出猎开围”的行动指挥者的象征。
有关八旗的三则传说都带有“天命”色彩,简述如下。
《神箭分旗》讲到,努尔哈赤意外得到了金代开国的宝弓,想用它来分旗。“金代是分五种颜色:红、黄、蓝、白、黑。红色代表太阳,黄色代表土,白色代表水,蓝色代表天,黑色代表铁。但是铁又生于土,有了土就可以不要黑色了。这样就只剩下四种颜色了。我们女真人,靠天靠地,有水有日,就能发迹。……罕王派人从山里采来四色石:有血红色的红石头;有天鹅色的白石头;蓝烟色的蓝石头;闪光的黄石头。把这四色石头,放在供奉祖先的石罐里。”努尔哈赤先让佐领每人闭眼取石头,按颜色分四队,再让四个儿子等候分旗。罕王的箭射到哪面旗帜,哪个儿子就领受这个旗的军队。
《龙旗和八旗》与《八旗和启运殿》是两则神话性比较强的传说,前者讲的是,小罕子做了一个金龙戏珠的梦,后来按照梦中所见制作了龙旗,又将手下各部分为四旗,人多后,又分出四旗,共合八旗。于是八旗兵有了“随龙来”的说法。后者讲的是,八条小龙组合成了一个“金”字,落在启运殿,拱开了日月,象征着明朝灭亡。这些龙落在了布上,被后金国当成了八块龙图案的旗标,于是就有了八旗,龙王变成老罕王,带领八条小龙打天下。
(二)其他社会民俗
《罕王出世(一)》讲述的是,仙女之子王镐与大罕的妻子生下了小罕。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东北民间存在的一种“拉帮套”婚姻模式,也有称作“招养夫婚”。“拉帮套”本是赶车用语,有拉旁边的马匹,以帮助大车前行的意思。引申义指已婚女子因为丈夫失去劳动能力,而为了养家,不得已另招一人为夫,共同负担家庭。这篇传说就内容来讲,本是为了突出王镐的不凡及与小罕的特殊关系,意在强调罕王的身世。但正因为“拉帮套”确实存在,而成为了传说的素材。
《半拉子背》讲的是,小罕子做“半拉子”时帮助穷人惩治财主的故事。“半拉子”指未成年的长工,干同样的活,只能拿到一半的工钱。这种雇佣关系在当时也是普遍存在。
《努尔哈赤结拜弟兄》讲的是,努尔哈赤逃难被丛氏祖先搭救,为了报答,结为异姓兄弟。这种“拟血亲”的关系意在通过结拜团结众人,形成类似血缘关系的集体合力。在努尔哈赤的其他传说中,也多次提到满族八大姓佟、关、马、索、齐、富、那、郎都是他的磕头弟兄,而这些姓氏也有许多起源传说。
四、宗教信仰与祭祀活动
民间信仰、宗教与各种祭祀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将人类从现实生活的困苦中暂时脱离出来,得到心灵和情感上的寄托和慰藉。广义的信仰包含了多样的崇拜对象,伴随着一个民族的形成,也经历了演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检视传说的一个重要维度,信仰因素不仅围绕着某个神灵和庙宇展开,更渗透到传说的方方面面。民间传说的讲述往往不经意间就掺杂了个人或族群的信仰。某些带有超自然的叙述对于“可信性”的基本特征不但没有减损,反而有所增加。
满族信仰体系十分复杂。总的来说,既有原始的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和萨满信仰,也有后来的佛教、道教,并衍生出各种祭祀活动。这些民间信仰与宗教信仰有的是女真人的传统,有的则是出于统治的需要。这些内容都在努尔哈赤传说中较为全面地呈现。另外,此处讨论的民间信仰与祭祀活动也可看作是萨满教信仰体系在不同层面的反映。
(一)民间信仰
努尔哈赤传说中对动物崇拜和人神崇拜的描述较多。如乌鹊崇拜。在所有“小罕逃难”的异文中,乌鹊救命的情节单元是不可缺少的。《努尔哈赤与黑帝庙》中还为乌鸦建造了庙宇。满族人“将乌鹊视为连结天地之间的使者,清代满族家家户户‘设竿祭天’,并且在竿上设斗,以肉米等物生置其中‘用以饲乌’。”[11]P366再如老虎崇拜。被称为“山神爷”的老虎是民间放山和淘金活动前都要去祭拜的神灵。还有蛇崇拜。在《努尔哈赤封蛇王》中,大蟒蛇拦路,要罕王封官,获得了“青蟒贝子”的称号。
在人神崇拜中,救过罕王的歪梨妈妈、笊篱姑姑传说较多,而在清代到达鼎盛时期的关公崇拜也成为努尔哈赤传说的一大特征,这与国家层面的大力倡导分不开。建州女真随着南迁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逐步加深。努尔哈赤本人就对关羽的忠勇仁义倍加推崇。“关玛法”的故事也逐渐被满族人所熟知,这样也就顺理成章的进入了民间传说中。
《赫图阿拉城》讲述了老城关帝庙的起源,有“先建庙后建城”的传说。在《兴兵堡的来历》中,从他人口中讲出,努尔哈赤是真龙天子,有关公保驾的天命观。《关帝庙》讲的是,罕王在梦中受王杲指点,假扮关公退敌的故事。《白脸关帝庙》讲的是,罕王要建关帝庙,找画匠给关公画像,可是画得再像也要被杀头。最后一个刘画匠索性按照罕王的相貌画了一个白脸的关公,反而得到了赏赐。
(二)萨满教
满族崇信萨满教,赫图阿拉老城中的“堂子”就是萨满祭天场所。皇太极后,民间禁止设立堂子,只由皇家独享。满族民间萨满分为两种:氏族萨满,俗称家萨满;职业跳神萨满,俗称野萨满。“家萨满主持宗族或家族中的各种祭祀,有时也给人治病。跳神萨满主要是召神、驱邪治病,地位低于家萨满”[12]P544。
《王八泡子的传说》讲到,洪水过后,水里出现了妖怪。老罕王就派神通广大的萨满大神前来查妖捉怪。于是,萨满跳起虎神舞,用“龙须、凤发、金丝”编织成宝网,降伏了水中的妖怪王八精。
《花翎顶戴的来历》中萨满罕讨子·差玛奉罕王命去为达子香公主治病。“正走之间,辽河洪水上涨,拦住了他们的去路。一百多萨满摆开阵势,对天祷告,差玛与天神沟通,天神命河神让路,还派来神鹰帮助他们渡河。”这些情节充分显示出萨满的威力。
《凤凰山的传说》讲到,继妃衮代去世,罕王因为有愧于她,而心神不宁,先请了和尚、道士为她驱灾避祸,都不奏效。于是,罕王想到请萨满来祭祀衮代。传说中详细描述了萨满祭祀的程序和“出神”的状态。最后,罕王亲自祭奠了衮代,她化作丹凤飞走,落足的地方就成为了今天的凤凰山。
(三)民间祭祀
背灯祭属于萨满祭祀的活动,一般属于家萨满的范畴,在午夜进行,要熄灭灯火。所祭祀的神灵多是星神或者黑夜守护神之类。但是,民间传说则认为是在祭祀“歪梨妈妈”,也就是李成梁的小妾。因为她裸身而死,所以“背灯”以显恭敬。
《满族吃背灯肉的传说》讲到,“李夫人因为搭救小罕子而死,而且她是被李总兵从被窝里拽出来打死的,死的时候身上没穿衣服。满族人感谢她搭救先祖,祭祀她的时候,怕她害羞,所以都背着灯光。就是在献肉、献酒祭拜她的时候,要熄灭屋里所有的灯,祭祀完了才重新点灯。好让李夫人来享受满族后人给她祭祀的猪肉,这就是满族吃背灯肉习俗的缘由。”属于原始自然崇拜的背灯祭与供奉“歪梨妈妈”的关联,显然是由信仰衍生的传说,并且“歪梨妈妈”在民间又有多个不同称呼,佛托妈妈①关于“佛托”两个字的写法,这里是按照故事家查树源的说法,而县卷本中则记为“佛拓”。至于佛托老母与佛托妈妈的关系,查树源并没有解释,而认为佛托像摇钱树一样,主要的寓意是保佑子孙富有。另外,据学者考证,“佛托”一词本是满语,可译为“原始之长”,或“柳枝”,佛托妈妈是女性祖先神和生育神。(参见张德玉.“佛托妈妈性别考辨”[A].满族发源地历史研究[C].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399-406.)也是其中之一。
插佛托是新宾满族人的风俗。据《兴京县志》记载,“清明节民人祭墓并修墓填土,旗人以彩纸制佛头插坟上。”[13]民间传说中的解释是附会到了一个叫“佛托老母”的满族战争女神身上。《插佛拓的由来》讲到,佛托老母本是小罕子的师傅,为了助阵而下山。小罕子的妻子佛三娘,也就是佛托老母的侄女不幸战死。佛托老母伤心之余,将拂尘插在了佛三娘的坟上。“事后,凡是满族人家死了人,就用木棍做杆,用四色纸做成像拂尘的东西,插在坟头上,表示祭奠。因为这是佛托老母留下的,人们就管这叫插佛托。”这个风俗一直传承至今。
从背灯祭到插佛托,民间信仰经历了族群社会心理的变迁。其外显的传说文本,或者说解释体系,也随之改变,由星辰的自然形象,生成了佛托妈妈和佛托老母这些人格化的神祇。二者在形象上虽有差异,但在信仰层面上趋于统一,并且附会到努尔哈赤传说中,增强了传承的有效性。
结语
综上所述,一个地方的生境与其叙事传统是不可分割的。努尔哈赤传说的形成来源于满族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信仰体系各个方面。民众正是依靠这些来自身边的素材,结合世代传承的族群记忆,不断讲述祖先的历史。因此,从众多努尔哈赤传说文本中,我们既看到了他作为英雄人物的一面,也看到了他作为普通满族人的一面。这些讲述者身边的民俗文化就是传说形成的重要基础。伴随着传说的播衍,族群的生活世界也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传承。
[1]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
[2]管彦波.民族的环境取向与地方性的生态认知[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2).
[3]刘小萌.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江帆.满族生态与民俗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5]滕绍箴,滕瑶.满族游牧经济[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6]《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乙巳年.
[7]金洪汉.清太祖传说[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8]《金史》卷44《兵志》.
[9]《李朝实录》宣祖二十二年七月丁巳.
[10]《李朝实录》宣祖二十九年正月丁酉.
[11]刘小萌.满族的社会与生活[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12]张佳生.满族文化史[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8.
[13]《兴京县志》第8卷,礼俗.
On the Forming Foundations of Nurhaci Legends
LIU Xian-fu
(Chinese National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Folk legends doesn’t come out of nowhere, their formation has many reality foundations. The sources for composing legends are mostly from people’s material life and spirit world. The legends about Nurhaci, the founding father of Qing Dynasty told by Manchurians, integrated with reality, are based on the history and the special habitat of Northeast region. From numerous legends we can see the image of Nurhaci as a heroic figure and an ordinary Manchu people as well. These legends artistically reflected the special means of livelihood,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belief of Manchu people.
Manchu; Nurhaci; folk legend; habitat; folk life
K291/297
A
2095-3763(2017)-0001-06
10.16729/j.cnki.jhnun.2017.01.001
2016-08-30
刘先福(1984- ),男,辽宁沈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俗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满族民间文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